《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docx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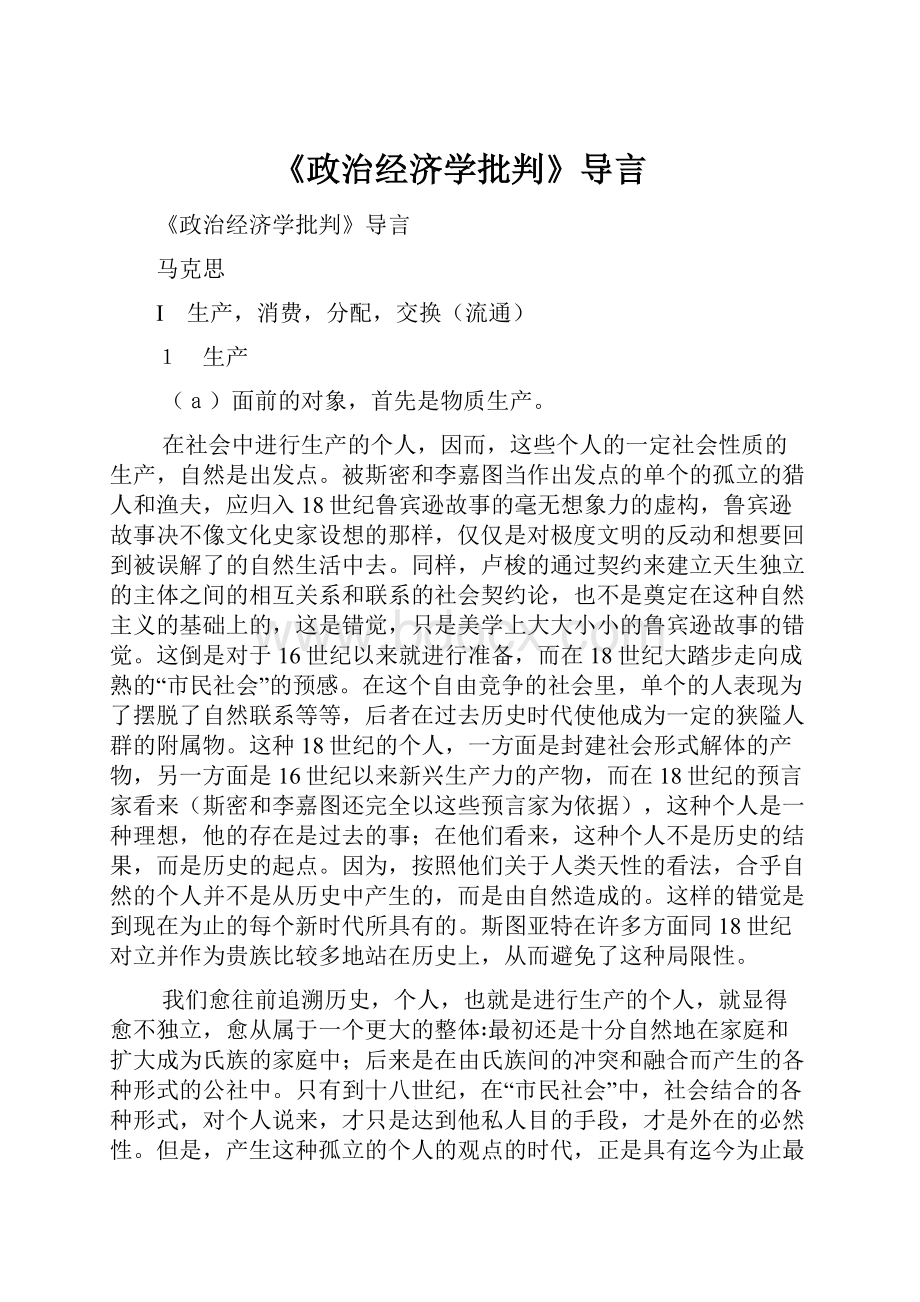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
I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1 生产
(a)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
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18世纪鲁宾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鲁宾逊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
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宾逊故事的错觉。
这倒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
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
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他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
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
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愈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愈不独立,愈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
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
但是,产生这种孤立的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来看是一般关系)的时代。
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再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方面无须多说。
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
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做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这种观念对亚当及普罗米修斯已经是现成的,后来他就被付诸实行等等。
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腔滥调更加乏味的了。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
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只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
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目标、共同规定。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
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如果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那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了本质的差别。
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
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
没有过去的,累积下来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
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
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累积下来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的话。
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
生产总是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是他们的总体。
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
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
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及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
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
生产一般。
特殊生产部门。
生产的总体。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好像应当包括∶
(1)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
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要说明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
可是,我们将会知道,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
(2)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
要把这些在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升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生产率程度不同的各个时期-这种研究超出本题应有的范围,但就属于本题范围来说,在叙述竞争,累积等等时是要谈到的。
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
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一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条件如离海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
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
但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谈的并不是这一切。
相反,照他们的意见,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脱离历史而独立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
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
反之,在分配上,好像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
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与生产与分配的现实关系,下面这一点总应当是一开始就明白的∶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
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
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占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或者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等等那一份产品的规律。
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1)所有制,(2)司法,警察等对所有制的保护,对此要极简单地答复一下∶
关于第一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藉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
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
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私有制。
(而且还把对立的形式即无所有作为条件。
)历史却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这种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还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
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所有制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
可是,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末,这是同义反复。
什么也不据为己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
关于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
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
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
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射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模糊地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观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
肤浅的表象是:
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它享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
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
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因为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
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人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偶然的个人的规定性来媒介。
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分量);交换决定个人对于分配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
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
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地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着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或者是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基础上,或者是在他们之下。
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家过于重视生产,把它当作目的本身。
说分配也是同样重要的。
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那种把分配当作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的经济见解。
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理解。
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中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把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
(a)[生产和消费]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
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
个人在生产当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和消耗这种能力,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耗完全一样。
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
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特性,这种自然形状和特性倒是消耗掉了。
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
不过,这一点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作生产的消费。
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起来是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即否定”。
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后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我们且观察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
例如,吃喝是消费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
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它任何消费形式也都可以这样说。
消费的生产。
可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
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
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
生产同消费合而为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
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
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
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
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
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
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
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
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
(1)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
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
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
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末,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向,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
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
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
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
(1)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
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生产在这方面创造出,生产出消费。
(2)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
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
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
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
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
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
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
(3)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
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后,-如果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做媒介的。
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
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
因此,生产不仅作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
(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
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
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
(1)直接的同一性:
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
消费的生产。
生产的消费。
政治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生产的消费,可是还做了一个区别。
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后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
关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于后者的研究是关于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
(2)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他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
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
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
这在经济学中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3)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直接是生产;而且生产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像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
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在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的时候,在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毁掉的时候;在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达到完美的程度的时候;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
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在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的时候,然后是在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的时候。
这和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后的同一性,经济学在论述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时,曾多次加以解释。
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同一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
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萨伊就是个例子;他的说法是,就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
或者,就人类一般来说,也是这样。
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的错误,因为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是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
此外,把社会当作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观察,是对它做了不正确的观察,思辨式的观察。
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
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
如果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或者许多单个个人的活动,它们无论如何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
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
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
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因消费了它而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
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它个人的关系。
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
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末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
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插进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
那末,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处于生产之旁和生产之外呢?
(b)[生产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
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
说到资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
(1)当作生产要素;(2)当作收入源泉,当作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
利息和利润,就它们作为资本增殖和扩大的形式,因而作为资本自身的生产的要素来说,本身也出现在生产中。
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
他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
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
同样,工资也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
在一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另一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
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末,它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
最后,地租-我们直接地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形式-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劳动一样。
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
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
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
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简直是幻觉。
因此,像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最受责备的就是他们眼中只有生产,他们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他们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
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指他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个生产-的地位,因而分配先于生产。
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产。
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门从事雇佣劳动。
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和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
就整个社会来看,从一方面说,分配似乎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乎是先经济的事实。
一个征服者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
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
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粉碎成小块,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
或者,立法使地产永远属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作]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它像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
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
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彷佛离开生产很远,对生产是独立的。
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
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
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
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么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
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产工具的一定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于生产,成为生产的前提,那末就应该答复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
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
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了,如果它们对于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另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了。
它们在生产内部不断地改变。
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
现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
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分析。
然而,这些问题即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也可以同样给予简短的回答。
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
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份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
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
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
例如,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
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省服从于这些条件,因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