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论坛十周年.docx
《中华网论坛十周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华网论坛十周年.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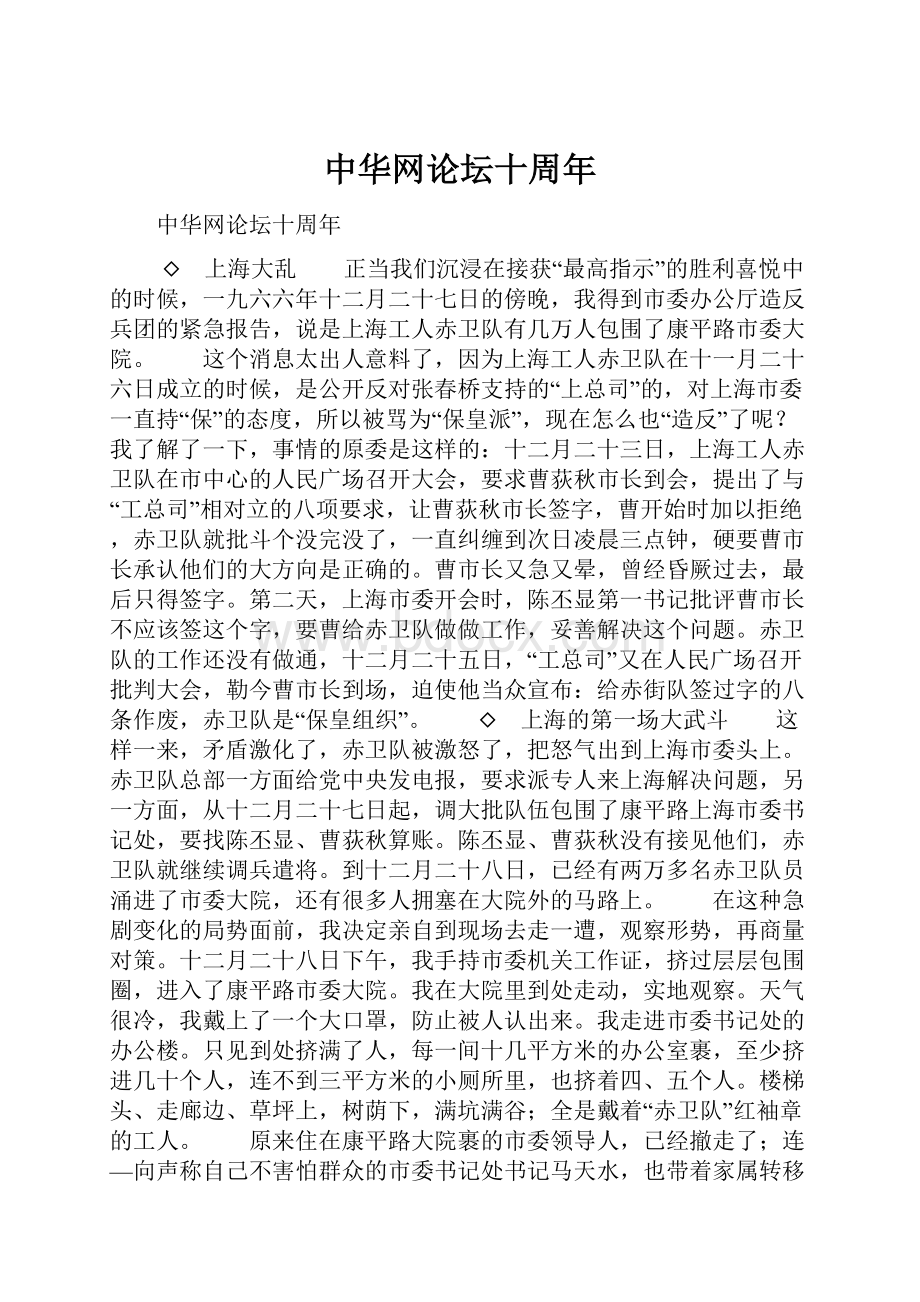
中华网论坛十周年
中华网论坛十周年
◇ 上海大乱 正当我们沉浸在接获“最高指示”的胜利喜悦中的时候,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傍晚,我得到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紧急报告,说是上海工人赤卫队有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
这个消息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的时候,是公开反对张春桥支持的“上总司”的,对上海市委一直持“保”的态度,所以被骂为“保皇派”,现在怎么也“造反”了呢?
我了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大会,要求曹荻秋市长到会,提出了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八项要求,让曹荻秋市长签字,曹开始时加以拒绝,赤卫队就批斗个没完没了,一直纠缠到次日凌晨三点钟,硬要曹市长承认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曹市长又急又晕,曾经昏厥过去,最后只得签字。
第二天,上海市委开会时,陈丕显第一书记批评曹市长不应该签这个字,要曹给赤卫队做做工作,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赤卫队的工作还没有做通,十二月二十五日,“工总司”又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大会,勒今曹市长到场,迫使他当众宣布:
给赤街队签过字的八条作废,赤卫队是“保皇组织”。
◇ 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 这样一来,矛盾激化了,赤卫队被激怒了,把怒气出到上海市委头上。
赤卫队总部一方面给党中央发电报,要求派专人来上海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调大批队伍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账。
陈丕显、曹荻秋没有接见他们,赤卫队就继续调兵遣将。
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已经有两万多名赤卫队员涌进了市委大院,还有很多人拥塞在大院外的马路上。
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局势面前,我决定亲自到现场去走一遭,观察形势,再商量对策。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手持市委机关工作证,挤过层层包围圈,进入了康平路市委大院。
我在大院里到处走动,实地观察。
天气很冷,我戴上了一个大口罩,防止被人认出来。
我走进市委书记处的办公楼。
只见到处挤满了人,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裹,至少挤进几十个人,连不到三平方米的小厕所里,也挤着四、五个人。
楼梯头、走廊边、草坪上,树荫下,满坑满谷;全是戴着“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
原来住在康平路大院裹的市委领导人,已经撤走了;连—向声称自己不害怕群众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也带着家属转移了。
整个大院裹只剩下已故的原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家属以及张春桥的一家。
赤卫队的头头们进人康平路大院之后,到过张春桥的家里,要求张的妻子李文静为他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反映赤卫队的要求,随后就退了出来。
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属,都是安全的。
我找到位于大院中部公寓里的张春桥的家。
从后面的那座水泥楼梯悄悄地绕道走上去,走到张家的后门口,从玻璃门朝里张望,客厅里不见人影;我试着敲敲后窗,轻轻喊了几声,也没有人答应,估计李文静和孩子们因为害怕,都躲到内室去了。
我再返回到大院裹,观察动静;只见赤卫队员们因为总部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见不到陈丕显和曹荻秋,情绪十分低落,有的人用毛笔在墙上写大标语:
“曹老头决没有好下场!
”“赤卫队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
”发泄自己的不满。
在现场看不到有人在作宣传鼓动,加上队员们通宵集合包围市委,大家根本没有休息,现在许多人就席地而坐,背靠着背,睑上显露出十分疲惫的神色。
有几个工厂的食堂,用黄鱼车给本厂的工人送饭菜来,吃剩的饭菜,连同写着各个工厂厂名的搪瓷盆碗,到处乱扔,满地狼藉;还有的单位送来几百箱饼干,高高地堆在空地上;看到这些情景,我的心里暗暗高兴,我想:
市委这下子彻底被动和孤立了;因为把两派群众都得罪了。
我觉得现在正是从政治上瓦解工人赤卫队的最好时机。
正当我兴冲冲地走出康下路市委大院的时候,忽然看见有许多打着红旗的队伍,从徐家汇、宛平路、余庆路等方向向康平路涌来,红旗上印着醒目的黄字: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队”,他们迅速把康平路大院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起来。
我上前一问,回说队伍是“工总司”二兵团调来的,有的人还说什么“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我们是来保卫中央文革的”!
这时,在康平路大院门口,两支观点不同的队伍对峙着,互不相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我马上回到市委写作班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我说:
“'工总司’这种做法真蠢,康平路市委大院现在是一座空城,让赤卫队呆在那里,没有几天就会溃散的。
现在二兵团调了大批队伍去包围;反而刺激了赤卫队的情绪,弄得不好,可能要出事。
” 历史组的朱水嘉说:
“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准备召开全市的批判大会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康平路去唱'空城计’,不要睬它。
”哲学组的郭仁杰说:
“赶快想办法找找'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头头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要他们把队伍撤走。
” 于是,我要市委写作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找王洪文他们,可是到处找不到。
我说:
“这样对峙下去,双方很可能要大打出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造反派就被动了。
我们还是搞文的,要大家把矛头对准市委,从政治上瓦解赤卫队。
” 我马上通知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在康平路大院边缘上的一百八十一号楼里,设立一个联络点;要党刊《支部生活》编辑部造反队负责,在康平路大院四周高楼上,安装起几只高音喇叭。
我布置历史组、文学组的几支笔杆子,立刻起草传单;我自己也亲自撰写了一份《赤卫队为什么要大闹龙宫?
》,呼吁赤卫队员们反戈一击,杀回工厂去,向市委的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传单写好后立刻被打印出来,还抄成大字报,在康平路大院周围散发和张贴,并且通过高音喇叭连续向大院内广播。
经过政治攻势之后,有一批赤卫队员取下自己的袖章,偷偷从人缝里溜走了,留在大院裹坚持不走,被包围着的还剩一万多人。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一些愤怒的赤卫队员把怒火倾泻到市委头上,在康平路大院里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
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从康平路连夜给正在北京的张春桥通了电话。
二十九日早上,市委写作班的红色保密电话机铃声响了,我拿起听筒,是李文静打来的,她说:
“昨天半夜里我和春桥通了电话,讲了康平路大院里的情况,春桥说:
现在赤卫队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要告诉徐景贤转告上海各个造反组织注意,不要让赤卫队把胜利果实夺走了!
” 接到张春桥的电话以后,我向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员作了传达,并且和几个领导核心商量如何落实张春桥的指示。
我说:
“春桥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们造的反,让赤卫队摘了果子,岂不前功尽弃?
我们召开大会的口号看来要升级了,不能再用'火烧’、'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
大会一过年就开,口径要统一,按春桥同志的电话指示精神,正式喊出:
'打倒陈、曹!
打倒上海市委!
’” 当天晚上,在紧挨着康平路大院的荣昌路六十号临时指挥部裹,我派出的王承龙。
朱维锋和“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耿金章在知道了张春桥的来电以后,不愿用“文攻”,继续增调大批工人造反队,急于指挥他们打进去。
半夜过后,耿金章不听劝阻、一声今下,工人造反队发起了冲锋,蜂拥进入市委大院,边冲边打,把疲劳过度、毫无斗志的赤卫队员们打得落花流水,有的人还被从二楼阳台上推下楼去,摔成重伤。
赤卫队员们被俘虏以后,排成长长的单列纵队,鱼贯走出康平路市委的大门。
所有的人都被当场剥去赤卫队的袖章,高举双手作出投降的姿势,每个人的手里还要拿一根稻草,表示到市委来“捞稻草”的意思,然后排成六路到四周的马路上集中,听取训话后才被释放回家。
耿金章他们打胜以后便扬长而去,留下的伤员只好由市委大院裹的后勤工作人员集中处理,清点下来受伤的共计九十一人,其中最严重的被打断腿骨,于是当即叫来救护车把伤员分别送往华山医院、瑞金医院和华东医院救冶。
等到清点处理完伤员,已经是—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半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唉,总算没有打死人,不然造反派政治上很被动,怎么向春桥同志交代呢?
” 这场万人大武斗,在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武斗结束以后不到半小时,张春桥从北京亲自打电话给我,向我详细询问了武斗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
张春桥听完汇报,用他那由于抽烟过度而显得有些沙哑的嗓音,斩钉截铁地说:
“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大造声势。
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
临了,他又说:
“再也不要提'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了!
” 我回答“我知道啦!
最近几天,我们准备集中全力,召开一次'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
”
◇ 周总理下令抓赤卫队头目 工人赤卫队挨了一顿打,当然是不肯善罢甘休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赤卫队的一些头头鼓动了一批队员、冲进了上海北火车站,准备仿照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安亭事件”中的做法,乘火车上北京请愿、告状去。
提起“安亭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王洪文联合各厂的工人造反队,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宣布“工总司”正式成立,因为上海市委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王洪文、潘国平等会后就串连两千多人到市委请愿,市委负责人拒不接见,他们就到北站搭火车北上请愿。
火车开到嘉定县安亭车站时,被阻在支线上不能前进,工人造反队索性在沪宁线上静坐,造成铁路交通中断三十小时又三十四分钟。
这件事震动了中央文革,先是陈伯达发来电报,接着张春桥又受命从北京飞来谈判,最后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沪宁线才恢复交通。
现在,赤卫队就提出:
“工总司”可以乘火车上北京请愿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呢?
我对赤卫队的做法很反感,我想由他们去闹吧,反正上诲市委自食其果、他们总会向中央报告的;而我已经有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了。
趁着过除夕夜的机会,我回到常熟路瑞华公寓自己家裹,早早地上了床。
当我正在沉沉熟睡的时候,床边的电话铃急骤地响起来。
我抓起听筒,传来的是长途台女接线员的声音:
“是徐景贤同志吗?
北京张春桥同志要找您……” 我打开床灯,看了一下手表:
零点十分。
哦,已经是元旦了。
”全面内战”的一九六七年来临了!
张春桥在电话的那头着急地说:
“上海的赤卫队闹着要乘火车到北京来告状,中央不同意,但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有一个赤卫队的头头,名字叫王玉玺,他利用职权同意调车,我们知道了都很生气。
刚才中央开会研究了,已经由总理直接打电话通知上海市委陈丕显,要他到铁路分局去对王玉玺采取措施。
同时,还告诉陈不显,让他召集各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开一个会,讨论一下怎么把上海的秩序稳定下来。
赤卫队几千人上北京的话怎么办呀,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嘛!
不过,现在陈丕显说话可能不灵了,造反派的头头们不肯听他的,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你可以在会上说一说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 我听完电话,赶快穿衣起床,妻子在一旁埋怨着:
“过年也过不安稳,”我说“可能这几天回不了家喽!
”几分钟以后,市委办公厅就派小车把我送到了东湖路市委招待所。
不一会儿,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络绎不绝地来到了东湖招待所的餐厅:
北京和外地的几个著名的红卫兵组织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几乎都到齐了,有北大“捍卫团”,有清华“井冈山”,有北航“红旗”,有北京地质学院、体育学院、电影学院,此外,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驻沪红卫兵代表。
上海的红卫兵组织有“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等。
“工总司”的王洪文来得比较迟,他穿着一身较旧的黄绿色棉军装,戴着雷锋式的棉军帽,满脸病容,他瓮声瓮气地对我说:
“我这几天感冒了,正在发烧。
今天开什么会呀?
”我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最后一个来到会场的是“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他虽然打着“工总司”的旗号;但根本不听王洪文和潘国平的。
耿金章披着一件军大衣,足蹬一双高筒皮靴,使他那又瘦又矮的个子显得神气起来。
他—阵风似地卷进室内,摆出一副刚从前线归来的指挥官的架势,咋咋呼呼地说:
“我刚刚从昆山回来。
被我们从康平路打走的赤卫队又集中起来了,他们在北站没有上得了火车,几千人转移到昆山,准备从那儿上火车。
我已经把我们二兵团的队伍调去了:
把赤卫队堵住在昆山城里……”耿金章小时候生活很苦,被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后来又成了“解放”战士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到上海才当上了工人。
他打过仗,所以现在又用部队的那一套办法去对付赤卫队。
大家听到他从昆山带来的消息,马上议论纷纷,对如何处理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各抒己见。
正当与会者在七嘴八舌的时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来了。
当时他还兼着上海警备区的第一政委,身穿一身军装,一进门就操着福建口音告诉大家:
“我刚才接到总理的电话,总理说:
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访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总理要我同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协商,一起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接到电话以后,我赶到上海铁路分局了解情况去了,那个调度所的负责人王玉玺,擅自签字同意发车,破坏交通,我已经按照总理的指示,把他扣押了起来……” 陈丕显边说着边脱下军大衣,然后在白布铺成的长条桌子前面坐下,继续向大家介绍上海当前的严重局势:
……赤卫队要北上告状,现在被阻拦在江苏昆山一带。
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八十多个工作人员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员,都离开了岗位。
沪宁线的铁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
从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到现在的二十六个小时中,已经停开客车二十六列,有五万多旅客不能上车,还有五万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停开的货车有三十八列,中途停下的还有二十二列,货物积压了好几万吨。
还有最严重的,就是整个上海市只剩一个星期的存粮了。
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
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听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嚷开了,有的指责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有的要陈丕显自己到昆山去处理问题,还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乘机要陈丕显批条子给他们配备几辆摩托车做联络用。
我一看这个混乱的局面,觉得离开张春桥的电话要求太远了。
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假如由我出面帮陈丕显说话,难免有当“保皇派”的嫌疑。
情急之中我想出了—个办法——我走到会场正中,站在陈丕显的对面,大声说:
造反派的战友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散在昆山和其他地方的几千名赤卫队员弄回厂里去,使沪宁钱铁路畅通,把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恢复起来。
究竟谁应该对这个局面负责呢,就是你,陈丕显!
你这个市委第一书记长期躲在幕后指挥,让市长曹荻秋站在前台,你们先是不承认工人造反队,扶植了一支赤卫队,然后又想把赤卫队甩掉。
你们才是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祸首,这笔账我们以后再跟你清算!
接着,我传达了刚才张春桥打给我的电话。
大家一听,觉得我的来头不小,便安静下来,“炮司”的几个红卫兵还一字一句地记下张春桥的“中央文革特急来电”,马上出去印发传单了。
我顺势出主意说“现在我们这些造反组织,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出一个联合声明:
号召全市群众把矛头对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反戈一击,回到上海的各个岗位上来,抓革命、促生产。
我们还要勒令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坚守岗位,听从革命造反派的指挥,维护上海的革命秩序,这个声明写好以后,让陈丕显签字马上送到市委印刷厂去,大量印发。
……至于昆山那一边,刚才我已经和'工总司’王洪文、耿金章同志商量过了,我们立刻赶到那里去,做做赤卫队的工作,动员他们回上海。
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坚决和各兄弟组织的战友们站在—起,并肩战斗!
” 大家同意我的建议,我又逼住陈丕显问道:
“陈丕显,你同意不同意?
” 在陈丕显表示同意之后,我们当场进行了分工,中央音乐学院驻沪的红卫乒舒泽池、王立平和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愿意执笔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陈丕显陪在旁边等着签字付印;至于我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带了其他几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立即奔赴昆山。
一切商量完毕,已经晨曦初露,东方微白,东湖招待所的食堂裹端出几笼白馒头,我们吃了几个,便跳上“工总司”二兵团调来的一辆敞篷卡车,向昆山进发……
◇ 张春桥、姚文元飞抵上海 我和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在昆山活动了一整天,又赶往苏州,最后在城外的一所大庙裹,集中了上千名溃散的赤卫队员。
我们和铁路分局打了好久交道,才调来一列客车;大家蜂拥上车,抵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的清晨了。
我回到上诲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仔细读了几遍。
接着,我到市委机关联络站检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准备工作。
这次大会的全部发言稿,由写作班历史组的朱永嘉、吴瑞武负责撰写;大会的一、二、三号通今,由哲学组郭仁杰和上海作家协会的几个人负责撰写;大会的组织工作,由市委党校的程绮华抓总。
我强调:
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只晓得冲冲杀杀,把握不住主攻的方向,连一篇发言稿都拿不出来,只能由我们先做幕后工作;但是,等到开会的时候,大会的主持人、发言人以及宣读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全部通令的人员,要由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来担任,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拉出工人和学生的队伍来。
这次大会要正式宣布“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有一个大联合的声势,如果光靠我们这些机关造反派,那是孤掌难鸣的。
于是,我们在市委党校召开了几次各群众组织的协商会;经过争吵和辩论,最后确定大会在一月六日召开。
正当我们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月三日下午,姚文元忽然又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他问道:
“武康路二号写作班的地方,现在干什么用?
”我回答:
“现在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的内部办公地点,我们对外联络,都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
”姚文元说:
“春桥和我想要用武康路二号这个地方,你看行不行?
”我一时不太明白:
他们要用,怎么用?
但我连连回答:
“行的,可以的!
”我乘机向他汇报了—下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筹备情况,他不表态,只是说:
“这件事我需要和春桥商量一下。
”便把电话挂了。
听完电话,我马上找郭仁杰一起分析。
郭仁杰原来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师,总支副书记,调来写作班哲学组以后,仍和复旦的红卫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推动市委写作班造反的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现在又成了市委机关联络站的领导核心。
我把他看成是我的智囊,凡事都要和他商量。
他听说姚文元的电话以后,和我一样感到突然和兴奋,我们研究后一致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肯定要到上海来了!
所以他们要用武康路二号……,但是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来,要来多久,来干什么……都还是个谜。
一月四日的上午,我正在武康路二号起草大会的程序,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拎起听筒,姚文元的大嗓门仿佛就在近旁:
“徐景贤吗?
春桥和我已经到上海了!
”呵,想不到有这么快,他们一来,我就有了直接的依靠了,“今天下午,你找几个写作班的核心,等在武康路二号,我们想来听听情况,关于那个大会怎么开,也一起谈一下。
关于我们来上海的事,暂时要保密。
” 电话通了以后不久,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就带了市委警卫处的人员来检查会场了。
我安排出写作班楼下东厅,作为他们接见的地点。
下午两点多钟,穿着军装、披着军大衣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两个人当时没有担任任何军职,但自从毛泽东穿着军装接见红卫兵以后,所有的中央文革成员都穿起军装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热情地和我、郭仁杰、程绮华、朱水嘉、吴瑞武、王知常等一一握手。
大家围着长桌子坐下,张春桥首先开了腔:
写作班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
最近,中央文革正在起草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条,里面也吸收了你们的经验。
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的成员时,肯定了你们的造反,文元已经给你们传达过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先见见你们…… 张春桥说到这里,略为停顿一下,脱下军帽放在桌上,用手抚了一下他那稍带卷曲的头发,慢悠悠地点了一支烟,接着往下说:
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
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
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
你们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不必等我们。
这时,姚文元插话说:
“你们讲一讲最近有些什么动向,那个大会打算什么时候开?
” 我当即把“康平路事件”以后的上海形势,作了一个概要的汇报,特别提到自从张春桥打来电话,指出赤卫队已经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提醒我们不要让别人把胜利果实夺走了之后,联络站就集中全力,准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现在已经准备就绪。
接着,我就把大会的名称、发起单位、八个发言的题目和发言人的姓名,三个通令的内容等,统统作了汇报。
当我谈到有一个重点发言准备让“工总司”王洪文来讲,内容是“安亭事件”以后市委常委围攻张春桥的情况时,张春桥马上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他从黄色玳瑁眼镜后面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问道:
“这个情况你们怎么知道的?
” 我回答:
“我们翻阅了市委档案室裹的档案,这些情况是从当时市委常委会的原始记录中摘出来的。
” 张春桥恍然大悟,说:
“大会发言稿给我看一下。
” 我马上答应:
“草稿已经送到报社排印去了,等清样出来以后就送给您审查。
” 张春桥点点头。
我又说:
“开大会的准备工作经过几个发起单位的讨论,大都取得一致了,我们提出一月六日上午开会,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和市委常委们都要到场接受批斗,根据气象预报,那天可能有雨雪,所以我们建议大会放在文化广场室内开,'工总司’提出要拉到人民广场露天去开,我们怕效果不好,所以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今天你们两位来了,关于开会的时间、地点,要向你们请示,请你们决定。
” 张春桥沉吟了一下,征求了姚文元的意见,然后说:
“关于大会的开法和内容,我和文元都没有什么意见,就照你们的安排开。
至于会场究竟放在文化广场还是放在人民广场,我们打算明天找'工总司’的人见见面,到时候听听他们的意见再定吧!
” 谈话结束以后,张春桥先走了,姚文元单独留了下来。
因为我听说他回到上海后还没有见过家属,所以我和他打了招呼,派人去把他在卢湾区任街道党委书记的妻子金英,接到武康路二号来见面。
在这等候的间隙中,我们两人独处,他向我详细询问了市委写作班人员在造反过程中的表现,我一一作了回答。
我认识姚文元已经有十多年了,自从他从卢湾区调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以后又调到《解放》杂志和《解放日报》,我们的交往日益密切。
六十年代初期,我写了一篇杂文《不做“冷酷的观众”》,发表以后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姚文元知道以后马上挺身而出,写了一篇杂文《井非“挨批”》,为我作了辩护,我很感激他。
以后,他生了肝炎,我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就把他的情况向市委写了报告,经过市委批准,让他住院治疗,等他的病基本痊愈以后,再由市卫生局安排,转到青岛去进行疗养。
为了答谢我的关心,他送给我一本著作《在前进的道路上》,并在扉页上题句:
蝇死魔走战士在,黝励夜色听鸡鸣。
姚文元的日常生活很朴素,甚至有些落拓。
他常年穿一身蓝卡其中山装,脚上是一双圆口布鞋,肩上挂着一只草绿色的背包,背包里除了书以外,时常可以翻到早上吃剩下来的面包等点心。
有一次,还拣出过半块油炸粢饭糕。
他就以这身装束,到处走动,曾经步行到上海锦江饭店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在大门口就被“挡驾”了:
不让进。
为此,我为他愤愤不平,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
我曾想:
我们这些小人物,一定要在政治上、文学上搞出些名堂来,让那些瞧不起我们的“庞然大物”瞧瞧,争一口气。
此刻,我和刚从北京回来的姚文元两人对坐在武康路二号的东客厅裹,听他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
他对这里非常熟悉,就在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里,他吃在这里,睡在这里,至今在二楼仍保留着他的写作室。
他告诉我:
这次回上海张春桥和他都住在兴国路招待所。
我知道过去这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才有资格住的地方。
他让我今后通过红色保密电话机和他们直接联系,但是电话号码只能我一个人知道,不要外传。
我把他说的一切都记在小本子上,又抬头凝视着面前的这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
他是过去的姚文元,又不像过去的姚文元,他的一身军装,使我难以和他过去穿的蓝卡其中山装联系起来。
他的谈话一如既往,但又略带一点矜持,并且显得颇为小心谨慎。
我觉得在他的身上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
但是我又想不管怎么样,姚文元现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我应该接受他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