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扔掉拐杖一例歇斯底里麻痹症结构派家庭治疗案例报告.docx
《17扔掉拐杖一例歇斯底里麻痹症结构派家庭治疗案例报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17扔掉拐杖一例歇斯底里麻痹症结构派家庭治疗案例报告.docx(2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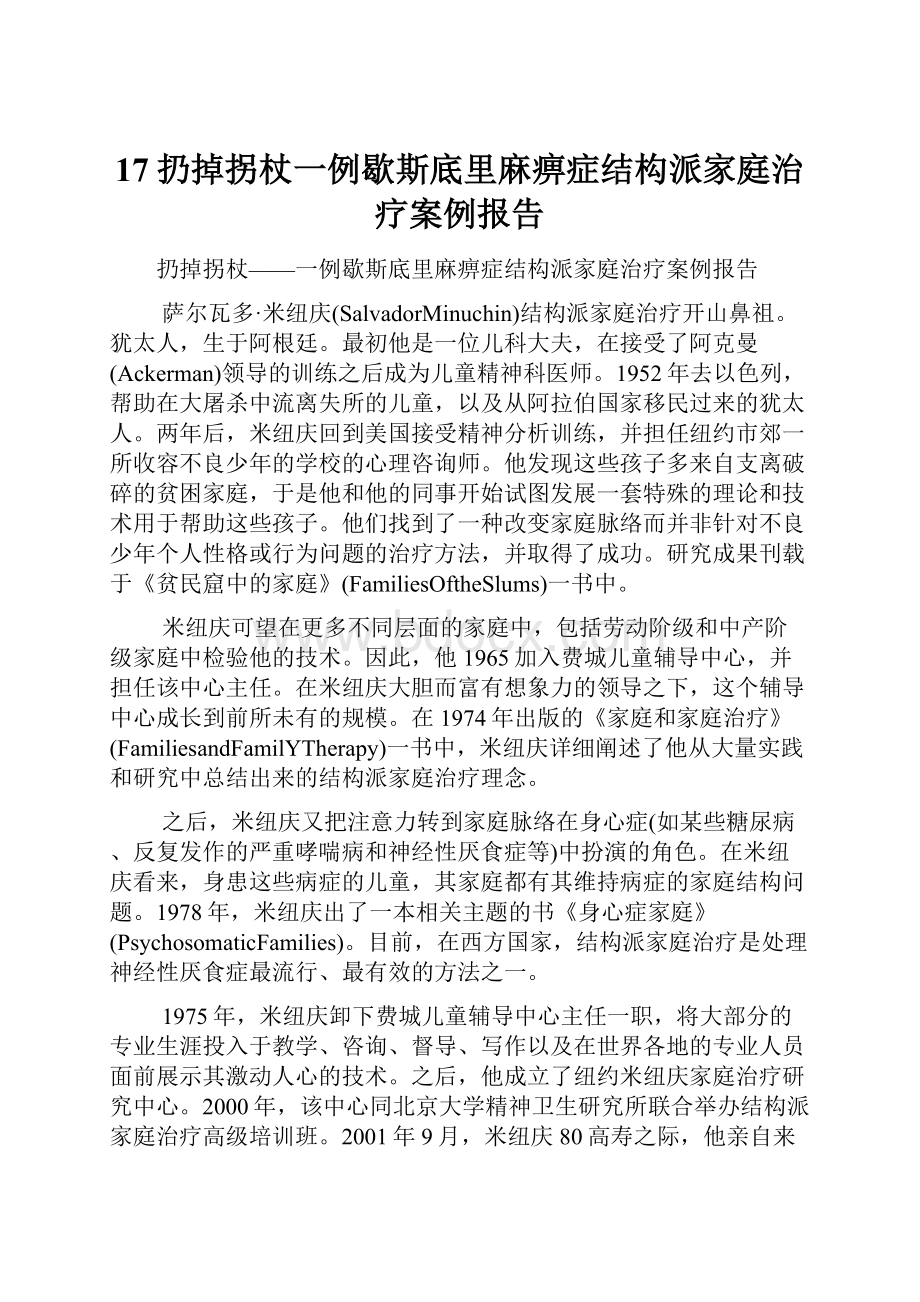
17扔掉拐杖一例歇斯底里麻痹症结构派家庭治疗案例报告
扔掉拐杖——一例歇斯底里麻痹症结构派家庭治疗案例报告
萨尔瓦多·米纽庆(SalvadorMinuchin)结构派家庭治疗开山鼻祖。
犹太人,生于阿根廷。
最初他是一位儿科大夫,在接受了阿克曼(Ackerman)领导的训练之后成为儿童精神科医师。
1952年去以色列,帮助在大屠杀中流离失所的儿童,以及从阿拉伯国家移民过来的犹太人。
两年后,米纽庆回到美国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并担任纽约市郊一所收容不良少年的学校的心理咨询师。
他发现这些孩子多来自支离破碎的贫困家庭,于是他和他的同事开始试图发展一套特殊的理论和技术用于帮助这些孩子。
他们找到了一种改变家庭脉络而并非针对不良少年个人性格或行为问题的治疗方法,并取得了成功。
研究成果刊载于《贫民窟中的家庭》(FamiliesOftheSlums)一书中。
米纽庆可望在更多不同层面的家庭中,包括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中检验他的技术。
因此,他1965加入费城儿童辅导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
在米纽庆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领导之下,这个辅导中心成长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在1974年出版的《家庭和家庭治疗》(FamiliesandFamilYTherapy)一书中,米纽庆详细阐述了他从大量实践和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结构派家庭治疗理念。
之后,米纽庆又把注意力转到家庭脉络在身心症(如某些糖尿病、反复发作的严重哮喘病和神经性厌食症等)中扮演的角色。
在米纽庆看来,身患这些病症的儿童,其家庭都有其维持病症的家庭结构问题。
1978年,米纽庆出了一本相关主题的书《身心症家庭》(PsychosomaticFamilies)。
目前,在西方国家,结构派家庭治疗是处理神经性厌食症最流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1975年,米纽庆卸下费城儿童辅导中心主任一职,将大部分的专业生涯投入于教学、咨询、督导、写作以及在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员面前展示其激动人心的技术。
之后,他成立了纽约米纽庆家庭治疗研究中心。
2000年,该中心同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联合举办结构派家庭治疗高级培训班。
2001年9月,米纽庆80高寿之际,他亲自来到北京,作为第三次培训的主训师和督导。
他的智慧、力量、理念和技术再次征服了人们。
本案例选自米纽庆最新出版的《家庭治疗》(FamilyHealing)一书。
(朱臻雯)
扔掉拐杖——
一例歇斯底里麻痹症结构派家庭治疗案例报告
古老而神秘的病症
案例当事人叫吉尔,11岁,女孩,患歇斯底里麻痹症。
最后一次大规模歇斯底里麻痹症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好几百名被俘士兵受到敢死队攻击,心生畏惧,担心被俘后的名誉受辱。
结果他们以潜意识的方式来解除这一心理危机。
众士兵都出现梦游似的神志恍惚,以及全身僵硬、麻痹等症状。
由此可见,士兵们的症状并非由躯体病变造成的,而是由心理因素的影响导致的。
这些奇怪难解的身心失衡,自古以来就困扰着治疗师。
古希腊人认为歇斯底里是因为子宫偏移引起的。
在中世纪黑暗时代,众人相信歇斯底里是巫师、妖法造成的。
弗洛伊德也相信歇斯底里是“着魔”,不过那是潜意识的渴望,而非自然的力量。
其问题根源在于潜意识中隐藏的性幻想。
现在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用歇斯底里麻痹症这一19世纪欧洲的方式来表达冲突了。
当时,歇斯底里麻痹症患者是被孤立的生物,像标本一样,被人们从环境中隔离出来。
20世纪的歇斯底里麻痹症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女孩子的家庭脉络是怎样的呢?
普通而熟悉的家庭
打电话来预约咨询的是吉尔的外祖父——约瑟夫·帕斯奎瑞罗。
吉尔一家因为她父亲的工作关系,已经举家搬至南美洲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斯加。
父亲的公司同意把吉尔一家送到费城,并慷慨支付一个月的治疗费用。
米纽庆一向讨厌用时间评估疗效,他喜欢在该结束的时候结束。
但是,米纽庆从不拒绝挑战,最终他还是决定受理了这个案例。
第一次见这个家庭时,米纽庆发现不仅全体成员穿戴体面,甚至6岁大的小弟弟也在阅读。
米纽庆先自我介绍,然后一位看起来年高德劭的男士站起来说他就是约瑟夫·帕斯奎瑞罗,并引介了他的妻子罗丝,女儿珍妮特·索德,孙女吉尔,孙子大维。
吉尔的父亲因公务缠身,几天后才能到。
这一家人走进治疗室,吉尔牢牢抓住母亲的手臂,一只脚是拖着走的。
同一边的手臂也是僵硬的。
吉尔重重坐下来,垂头缩肩地陷在椅子里。
她弯腰驼背,是企图隐藏含苞待放的青春吗?
这又让人想起了弗洛伊德。
这样的症状,跟恐惧成为青少年有关系吗?
明显看得出,这个小姑娘正在转变成年轻的女士。
索德太太安顿好吉尔,坐在她旁边,然后告诉治疗师,一件意外让她女儿半身麻痹了。
那是在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旁。
天气很热,晴空万里。
吉尔跟一些男生在池畔玩,被那些男生推下去。
只听吉尔一声尖叫,在水里猛烈扭动,大声叫着爸爸。
父亲一开始以为只是游戏,旋即感到事态严重,立即跳下水,把吉尔拉上来。
吉尔被拉出游泳池以后,无法站立。
他们赶忙把吉尔送到急症室,吉尔同意住院接受观察,只是查了又查,结果都很正常。
然而,吉尔的左腿、左肩就是无法动弹。
后来吉尔在复健部接受物理治疗。
半年过去,毫无进展。
吉尔仔细听着这个讲了几十次的故事。
她深色的眼睛在祖父母与母亲之间焦虑地穿梭着。
从这一事故以及随后的检验中都找不出线索可以解释为何一名健康的11岁孩子无法移动她的腿和手臂。
米纽庆问他们在加拉斯加住了多久。
索德太太解释说,她先生是地质工程师,在一家国际原油公司工作。
因职务关系,常在中东地区或中、南美洲居住两至三年。
来加拉斯加之前,先生在德州休斯敦工作。
他们在那里有一栋美丽的房子,她也在一家小学谋得满意的职位。
不过只待了两年,丈夫就被派到加拉斯加。
她要辞去教职,离开所有的朋友,实在很难过。
到加拉斯加的前几个月,她一直努力调整,好几星期过去了,家具一直没运来,工人甚至还在装修房子。
米纽庆开始猜想,索德太太有没有拖延从休斯敦搬到委内瑞拉的时日,以及吉尔的半个身体是否也是不愿搬家的象征。
其实,在治疗的前几分钟,米纽庆就已经做出了假设:
也许,孩子的麻痹表达了母亲对搬家的怨恨。
随着进一步的探讨,第一次的假设通常都会多次改变,但非常有用,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用来组织收集到的信息。
米纽庆一边倾听,一边观察家人的谈话。
外祖母罗丝很健谈,有话直说,说话速度快,没讲几句就笑起来了,而且可以滔滔不绝地分析。
“这样说吧,如果你想听我的意见,我不认为全世界的任何拖延对孩子来说是健康的。
”
索德太太抱怨到张罗吉尔的生活起居负担太重。
“理查从不在家,他总是在工作。
”
帕斯奎瑞罗太太补充说,她女儿的意思是:
“理查应该把心思更多地放在家庭上,而不是那宝贵的事业。
”索德太太接受母亲的支持。
在这同时,帕斯奎瑞罗太太又心疼起孙女来,“可怜的吉尔……”然后打断女儿说的话。
珍似乎很习惯,偶尔有些不耐烦,但没说什么。
吉尔仍陷在椅子里。
她穿着旧的夏令营T恤。
吉尔本该非常年轻有活力,可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家人的谈话,就像大人一样。
他母亲似乎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刚开始,吉尔的弟弟津津有味地听着大人的交谈,但没多久就失去了兴趣。
有时候,某些内容会吸引他的注意,可是大部分的时间他无聊地发呆。
米纽庆觉得跟着这家人连结起来非常快。
他们都是好人,也许在他们之间有太多纠缠不清的芝麻绿豆小事,但他们是却很温和亲切。
之后,米纽庆将挑战他们,把他们推人未知的境地。
此刻,米纽庆正集中精神,努力构建咨询关系。
吉尔是很开朗的年轻女孩子,眼睛乌黑,皮肤光滑,光泽的黑发扎成一个马尾。
像大多数的老大,她的表达能力很强。
米纽庆问她喜欢做什么,她说:
“我喜欢抓蜥蜴,看鸟,还有摘热带花朵。
”她不喜欢上学,因为同学的年纪都比她大。
米纽庆喜欢她,她也看得出来。
虽然吉尔早已接受过详细检查,但米纽庆还是安排她去儿童医院进行彻底的检查,再确认一下。
米纽庆不希望像有些精神科大夫那样,对某些纯医学的问题做出自以为是的心理学解释。
他安排吉尔一家每周治疗三次,一个月总共只有十二次,而且已经用了一次了。
母女联盟,父亲落单
三天后第二次治疗,全家都到。
索德先生曾建议岳父母留在家里,他觉得没有必要全家一起看医生。
理查·索德个子高,头发密而黑,皮肤晒得逞深褐色。
他是个帅气的男人,讲话的声音丰富,有变化,而且力求精准,很有力量与权威感。
吉尔缓步走进咨询室,紧紧抓住母亲,理查走在后面,在太太后面站了一会儿,帮吉尔坐进椅子。
大家坐定后,米纽庆发现理查跟家人在一起时,似乎少了些自信,不像在接待室里寒暄时那样。
米纽庆开始描绘这个家庭的初步结构图。
吉尔的病让家人把注意力盯在她的症状上。
这样的一出戏是再自然不过了。
吉尔这个人已经让位给“残障吉尔”,不能走路变成她的身份证,也成了他人试图接近吉尔的大门或障碍。
但事情本不应该如此。
吉尔紧抓着母亲,明显可以看出母亲在家庭里的分量,理查是有距离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距离。
他像是被妻子领进治疗室的,这个家是太太在负责。
当然,这只是地图而已,就像所有的地图只能显示大概风景,无法呈现所有细节。
当我们把家庭关系简化成图表,用以表示成员间的亲疏时,一定会抹煞某些人性,但是也必有所得,那就是“清晰度”。
从这个地图可以看到,这个不寻常的个案似乎并不是那么非比寻常。
歇斯底里麻痹症,确实很不寻常,但整个家庭的互动,支持这种症状的互动,却是令人伤心的熟悉。
那正是一般出问题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特征:
母亲对子女的亲密,取代了婚姻的亲密,因为他们的婚姻没有进一步发展,也没有破裂。
这种家庭类型太普遍了,根本无法解释这一不平常的症状,那依然是个谜。
吉尔卡在目前的状态中,而且像水泥一样硬化。
杰·海利(JayHaley)曾发展出三阶段的策略,用来撬开他所谓的“跨代联盟”,其目的是要引导子女迈向独立自主。
第一步就是要勾回较疏远的父亲或母亲,让他们跟依赖的孩子在一起;同时,也是要隔开与子女关系紧密的父亲或母亲。
对这个家庭而言,第一步是必要的,米纽庆决定推动理查,让他跟吉尔靠紧一些。
因此,在第三回合诊疗时,米纽庆向理查提出以下计划:
由于珍妮特已经很讨厌被人当活拐杖,因此下一星期理查应该负责照顾吉尔,只要吉尔想去哪里,只能请爸爸帮忙,不能叫妈妈,父亲要当拐杖。
米纽庆很担心理查会不会像大多数的父亲,对于照顾子女很不在行。
第二步则是要让理查与珍妮特互相亲近。
唯有这对夫妇能够在两人和子女之间建立界线,他们才能表达妨碍他们亲密性的冲突。
第三步是直接针对吉尔的,探索她病症的意义,并挑战其麻痹的效应。
诊断很容易,但真正去执行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这样的策略是治疗科学,在治疗路途上侦查出地雷就是艺术了,而且只剩下九个回合。
“坐”在父母中间的吉尔
治疗策略只是通则,治疗结果则是个人能耐。
三天之后,增进父亲与女儿亲近的策略生效。
理查接替了照顾责任,然而就像大多数父代母职的生手:
他开始支配东支配西。
当吉尔有需要时,他会帮助她,不需要时,他也要帮忙,理查不仅把手臂借给吉尔,甚至在吉尔安静的时候,替吉尔打气。
吉尔的心情倍受搅扰,最终她就用沉默进行控诉。
理查没有适应女儿的节奏,反而坚持要女儿适应他的节奏,如果吉尔不接受,他就生气。
吉尔很气愤,做出一般依赖的孩子常做的事,她开始增加要求,需要更多帮助,让父亲更没有耐心。
现在,珍妮特很焦虑,理查很疲惫,很烦躁。
但父亲的做法只能让女儿的坏脾气愈演愈烈。
米纽庆发现这并不是他要的结果。
他的目标是要让孩子更独立自主。
第一步已经启动,父亲也参与了,但是吉尔跟父亲走在一起仍然是个可怜的跛子,每一步都要用力拖着走。
她重重靠在父亲的臂膀上,腿在后面拖着,这很让人难受。
吉尔坐在父母中间,她的样子看起来像个阴晴不定的青少年,下巴放在拳头上,用违抗的怒色盯着某个角落。
米纽庆决定暂时不理会吉尔。
她的家人都在她头上盘旋,好像她是朵娇嫩的兰花。
也许,吉尔需要的是温室之外的其他东西。
因此,米纽庆问起她父母有关加拉斯加的事情。
理查很喜欢。
他的加拉斯加是个很美好的地方,有温暖阳光、清凉微风,还有迷人的广场、喷泉、餐厅、夜总会以及友善的居民。
珍妮特痛恨她失去了休斯顿那栋美丽古典的西班牙房子,也失去工作、朋友、父母。
加拉斯加是“乡巴佬的城镇,贴满水泥与玻璃。
这个城没有灵魂。
”
米纽庆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听起来他们好像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理查微笑,笑得好玩。
珍妮特一脸正经,觉得没那么好笑。
米纽庆问孩子们怎么想,因为这可以看出他们站在父母的哪一边。
大维含糊地说:
“不知道。
”毫无生气。
吉尔则说:
“我恨死你了,那里无聊得要命。
”她站在哪一边不言而喻。
“我刚才说,听起来你们俩好像住在不同的地方,那只是开玩笑,也许那一点也不好笑。
珍妮特,你能向理查解释你为什么不愿失去休斯顿?
尽量让他们了解你的感受。
”
他们的对话很僵硬,很紧张,也很形式化。
珍妮特对孩子们的学校不满,觉得被当地的社区隔离,唯一能交往的人只有理查石油公司的同事。
“说来说去都是石油,听一阵子就很腻了。
”
“为什么你对每件事都那么消极?
”理查的声音空洞,而且是苦苦的,“如果你去找个工作,或多交朋友,就不会有那么多抱怨了。
”
“可是你总是在工作,”吉尔插嘴了,好像在指明什么,“为什么你不偶尔回来一下,带我们出去玩?
”
吉尔坐在父母中间。
米纽庆站起来,走向她。
“吉尔,请跟你妈妈换一个位置。
”边说边帮她换到另一张椅子,“现在,珍妮特,跟你丈夫谈谈。
”
结果并没有太多不同:
散乱的对话,以及愠怒的小孩。
吉尔很不习惯被卷入话题中,她倒在椅子扶手上,寒着脸,叹着气。
孩子的防御不多,如果有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真的有必要吗?
”理查说,“吉尔看起来像在发愁。
”
米纽庆说:
“吉尔现在的行为,就像不顺心的5岁小孩。
先别管她,继续和珍妮特谈话。
”
米纽庆现在正进入第二步,在孩子面前支持这对夫妇的独立自主。
把吉尔的行为拿出来攻击,说她像5岁小孩,目的是要她与父母隔离。
对小孩正确的“侮辱”,可刺激他们趋向成熟。
如果父母觉得被攻击,他们的不舒服就是有用的“中断”,中断孩子对他们的干扰与过度责任感。
海誓山盟今不再
在第五回合里,米纽庆想单独会见这对夫妇,因此请理查把孩子们带到接待室,然后再回来。
米纽庆要探索他们夫妇相处的难题。
珍妮特初遇理查时,他24岁,英俊、自信、真诚,他生长在康乃迪克州,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念私立学校,宾州大学毕业,拥有地质工程硕士学位。
他是忠诚的共和党党员,在国际原油公司分属机构上班。
她觉得他定位清楚,而且不像她认识的其他男生,他不会不时纠缠。
可是,随着时光的消逝,独立的珍妮特把理查的这项优点看成是距离与逃避。
珍妮特是独生女,出生在费城北边,那里有一整排的古典石屋,环绕着老橡树。
她父亲以保险生意起家,后来在37岁那一年,转行成为高中历史老师。
母亲负责照顾家庭。
珍妮特从宾州大学毕业后,有意从事新闻工作,但她遇上理查,谈了恋爱,就把雄心壮志献给家庭了。
家里有个不凡的男人,他需要珍妮特。
她觉得,这样就够了。
理查很快被珍妮特率真的情感吸引了。
她的幽默与温暖解除了理查家庭教育的约束。
就跟珍妮特一样,他与梦想成婚,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梦想。
一旦以往的海誓山盟不在,心爱的人变得难以共同生活,心情是很难受的。
逐渐地,他们各走各的路。
他们渴望爱,却又固守现状。
听他们两人交谈,很是伤感。
两个人都伤痕累累,满腹苦水。
还好,他们更多地在倾诉悲伤,而少有反唇相讥。
米纽庆希望这种谈话风格,能够提醒他们曾经相爱过,因而有再度和好的可能。
他们若能重新结合,吉尔就会获得空间,走自己的路。
比吉尔还小的珍妮特
该是请出祖父母的时候了。
早在第一回合的诊疗里,米纽庆就看出珍妮特对理查的疏理,是受了她与父母的粘连关系的支持。
所有的家庭背后都有一个大家族。
虽然美国许多新成立的家庭常切断他们的亲族关系,但大家族仍然存在,整个家族资源只是冬眠状态。
如何不让这些资源越界,需要在新家庭成立的最初几年,好好协商彼此的界限。
聪明的父母会尊重这个界限。
如果他们不尊重,大家族将不再是种资源,而是无尽的麻烦。
第六次诊疗,索德夫妇到达后,珍妮特的父母并没有出现。
米纽庆有点担心。
还好,帕斯奎瑞罗夫妇只是迟到。
罗丝红着脸,喘着气,讲着一长串的故事,说她如何乘火车搭错巴士,很大方地讲出细节。
珍妮特不耐烦地插嘴说:
“妈,你就是不肯搭计程车。
”
她母亲微笑着,没说什么。
父亲则说,没关系,有什么关系?
重要的是,他们全到了。
他没有挑战太太,只是息事宁人。
当丈夫说话时,珍妮特的母亲叹气,拨了一下额头的卷曲白发。
理查脸上有痛苦的表情。
划清界限的策略之一就是,让珍妮特与理查协商出与帕斯奎瑞罗夫妇相敬如宾的距离,其中包括接受理查,视他为大家庭的一份子。
珍妮特与理查开始讨论她的父母是否接纳他。
珍妮特说,理查不尊重她对父母的孝心,实在很难谈。
他试图解释,最近这几年已经有所改变,“我认为我已经在做了……”可是珍妮特听不进去。
索德夫妇卡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上,“珍妮特,好像你对于赢得争论的兴趣大过于接纳理查。
你仍然用旧的耳朵听他讲话,难道你不能送他一个微笑吗?
”珍妮特笑了,大声笑。
“这样很好,”米纽庆说,“我需要你更多地微笑,经常地。
”
“反之亦然。
”珍妮特的母亲轻声强调。
“美丽的补充。
”理查这样说,没有很成功地掩饰他的烦色。
“不是这样,”米纽庆更直接地挑明,“她已经做了某些她知道不该做的事。
珍妮特,为什么你母亲会认为,你还是需要她的保护?
”
“不知道。
”
“哦?
”
“她只是想帮忙。
”
“可是她知道,现在是你跟你丈夫的事,她还是插手进来。
她真的干涉到你们俩。
婚姻初期,母亲帮忙自己的子女,这无可厚非。
可是她一直坚持你还是她的小女儿,即使结婚十七年之后。
”
“她只是有必要才介入,”珍妮特说,“而且没有失败过”。
“你必须帮助你母亲,请他不要介入你与你丈夫的事。
如果你能帮父母这个忙,会有好处的。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女婿,你也不会觉得被两边拉扯。
”
理查抓住米纽庆丢的救生圈,打开了往日的伤痛。
“我是很尊敬你的母亲,然而事情演变成这样,我对你母亲的尊重破裂了。
我一直想控制自己的脾气。
他们来访,我快快乐乐接待,去拜访你们时,我也很高兴。
”他看着岳父说。
帕斯奎瑞罗先生也看着他说:
“你也许有那种感觉,可是你并没有让我们知道。
”
“不对”,他太太突然接口,他把手放在太太的肩膀上说,“让我讲完。
”随即转向女婿。
“举个例子好了,上一次我去你们家,我觉得好像是个外人。
”
“是被人怠慢。
”帕斯奎瑞罗太太补充说。
“拜托,我不需要你的帮忙。
”他的声音严厉起来,“因为,我感觉到的是你的冷淡、遥远。
你从没有真正想要沟通,这就是我感受到的。
所以,请想想你用的表情、你用的声音,还有你的态度——那么遥远,那么冷淡。
想想长期以来你的样子——酸苦不悦,阴霾倨傲。
我们都从你那里感受到了。
”帕斯奎瑞罗先生好像忍了很久了。
“你也许尊敬我们,这是一回事。
可是彼此感觉到自在,彼此都能放松,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
老先生的控诉旋绕在空气中,所有人静默了几分钟。
理查没有回应。
他僵在位置上,像块怨恨的石头。
接着珍妮特说:
“我知道双方互相的怨恨。
”
“太强烈的字眼,”她母亲说道,希望事情缓和下来,“只是偶尔有些不满。
”
“你不满意什么?
”珍妮特想知道。
“他对你的行为,以及对大家的行为。
”
“你先提到他对我的行为,你指什么?
你曾经这样对理查说过吗?
”
“等一下,”米纽庆说,“珍妮特,你必须帮助母亲,方法之一就是让她知道理查对你的行为不关她的事,如果你能帮助她,她就会跳出你们的婚姻关系。
你办得到吗?
”
“我没有跟她讲过太多什么。
”帕斯奎瑞罗太太说,没有人乐意染上爱管闲事之嫌。
“哦,妈妈。
”珍妮特说。
“你的事我看到的不多。
我只看到你的负担。
”
“妈,我不觉得那是负担,那只是家务琐事。
如果我觉得有负担,会找你讨论的。
”
“珍妮特,”米纽庆说,“你觉得你母亲怎么看你?
”她笑着说:
“比吉尔还小。
”
“所以你让她保护你?
”
“唉,她是很难抗拒的女士。
”
“不过,虽然她喜欢管闲事,但这是得到你认可的。
要想帮助吉尔,方法之一就是建立可接受的界线。
如果你帮助母亲,不让她介入你的婚姻,就会建立模式,不让女儿介入你的婚姻,因为她也很会管闲事。
你的母亲管闲事,但有帮助。
你的女儿管闲事,却是过分要求。
”
吉尔没有病,她是在介入和管闲事。
她在扮演外祖母的角色。
这真是恐怖的传统。
理查开始说话了: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父亲对我表示了一些意见,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
”
米纽庆赶忙打断:
“在你回答之前,我要你了解理查话中含义。
他是在问:
‘你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父亲这边?
’”
再度的沉默。
接着珍妮特说:
“我站在你这边。
”她似乎是真心的。
几分钟后,珍妮特的母亲在谈话中又插嘴提问题。
珍妮特说:
“妈,拜托,我们正在私人交谈。
”
很容易就可看出外祖母的介入与多管闲事造成了问题。
但是,界限不清却是由双方面造成的。
当某人介入,另一方就必须忍受。
米纽庆很高兴珍妮特采用他的语言,来建立界线与独立自主。
吉尔是问题,但不是唯一的。
另一个问题是吉尔的祖父母认为珍妮特与理查之间未解决的冲突需要他们的帮助。
十天之前,这家庭的情况可清楚界定为:
他们是正常家庭,有位出现病症的小孩。
结果导致大家努力照顾小孩,放大了帮助,却窄化了选择性。
现在,这个定论出现了新的挑战:
情况并没有那么清楚,困惑可能激发出新的观点。
治疗的推进有好几个层次。
虽然米纽庆强调夫妇与整个大家庭的问题,吉尔的症状并没有离开他的关注,或整个家庭的关注。
自从把父亲当作拐杖,吉尔已经更有活力了,但现在是走得更远的时候了。
诊疗接近尾声时,米纽庆问吉尔自从意外后生活有什么混乱。
她提到行动不方便与看了很多医生,对于跛脚似乎没特别难过。
米纽庆告诉她与她父母,进一步的康复计划是吉尔必须学习在没有父母的协助下走路。
他将请教儿童医院的整形外科,然后造出吉尔专用的特殊拐杖。
在这同时,米纽庆也告诉理查,在下次诊疗时带把坚固的雨伞,他可以开始教吉尔走路了。
用心灵走路
下一回合之前,米纽庆接到神经科检验报告,在研究过病历,执行所有必要的检测后,神经科医师找不出任何器官或结构上的理由,说明为何吉尔无法正常行走。
报告上说:
“所有功能都能完全正常运作。
”吉尔的疾病在她心里。
吉尔被送到整形外科,做出适用的拐杖。
技术人员问吉尔,有没有喜欢的颜色,是紫色。
她有了一根紫色拐杖。
索德家人出现在第八回诊疗时,大维没出现。
理查看不出他来的必要。
米纽庆决定不要节外生枝。
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没有获得家庭关爱的兄弟姐妹,另有自己的问题,但时间有限,而且还有更严重的病症要处理。
全家人一起进来,米纽庆很高兴看到理查带着一把看起来相当坚牢的新雨伞。
不像一般治疗师,他们只专注个人,而且必须仰赖病人报告生活发生了什么事件。
家庭治疗师可以把他们的生活搬人治疗室。
在这一回合里,米纽庆将强化第一步,藉着教吉尔用拐杖走路,让理查更亲近女儿。
理查试着帮女儿站起来,递给她雨伞,问她是否能拄着雨伞支撑自己。
他还不习惯扮演护士角色,吉尔向母亲投去哀求的一瞥。
“很好,”米纽庆说,“珍妮特跟我会站在房间的另一边,让你们有更多空间进行练习。
”
现在理查果断了点,成功地让吉尔拄着雨伞单独站着。
在他的有力敦促下,吉尔走了几小步,然后啜泣,塌倒向椅子。
“我害怕!
”她的父母看起来很烦恼。
吉尔很可怜,很无助。
对他们三人来说,这是个困难时刻。
要母亲退到后面只当观察者,实在很难。
吉尔怕跌倒,过多地关注她那无法使用的腿。
她的麻痹来自真实的恐惧,父亲急着想帮她,但不知该如何着手。
忧虑与挫折让他有点苛求。
女儿的眼泪软化了他,但是他挫败的感觉更甚于同情。
“做得很好!
理查,你必须帮助女儿克服恐惧,非常好。
你们俩开始得很棒。
”
对索德一家来说,现在的课题是吉尔要学习行走,即使他们都很怕。
对米纽庆来说,他的课题是延长父亲与女儿的互动,并帮助父亲,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他对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