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docx
《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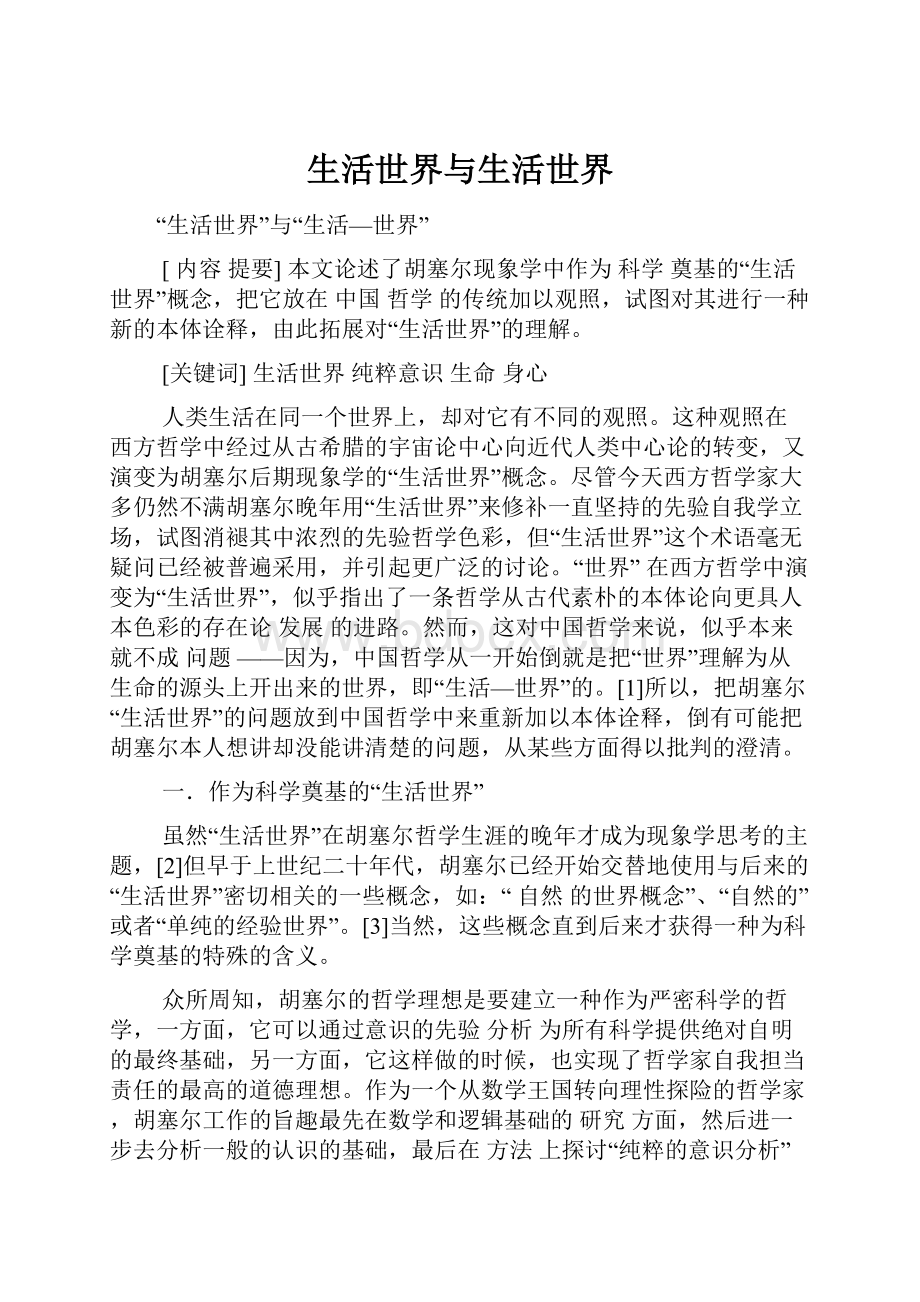
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与“生活—世界”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胡塞尔现象学中作为科学奠基的“生活世界”概念,把它放在中国哲学的传统加以观照,试图对其进行一种新的本体诠释,由此拓展对“生活世界”的理解。
[关键词]生活世界纯粹意识生命身心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却对它有不同的观照。
这种观照在西方哲学中经过从古希腊的宇宙论中心向近代人类中心论的转变,又演变为胡塞尔后期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
尽管今天西方哲学家大多仍然不满胡塞尔晚年用“生活世界”来修补一直坚持的先验自我学立场,试图消褪其中浓烈的先验哲学色彩,但“生活世界”这个术语毫无疑问已经被普遍采用,并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世界”在西方哲学中演变为“生活世界”,似乎指出了一条哲学从古代素朴的本体论向更具人本色彩的存在论发展的进路。
然而,这对中国哲学来说,似乎本来就不成问题——因为,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倒就是把“世界”理解为从生命的源头上开出来的世界,即“生活—世界”的。
[1]所以,把胡塞尔“生活世界”的问题放到中国哲学中来重新加以本体诠释,倒有可能把胡塞尔本人想讲却没能讲清楚的问题,从某些方面得以批判的澄清。
一.作为科学奠基的“生活世界”
虽然“生活世界”在胡塞尔哲学生涯的晚年才成为现象学思考的主题,[2]但早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胡塞尔已经开始交替地使用与后来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一些概念,如:
“自然的世界概念”、“自然的”或者“单纯的经验世界”。
[3]当然,这些概念直到后来才获得一种为科学奠基的特殊的含义。
众所周知,胡塞尔的哲学理想是要建立一种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意识的先验分析为所有科学提供绝对自明的最终基础,另一方面,它这样做的时候,也实现了哲学家自我担当责任的最高的道德理想。
作为一个从数学王国转向理性探险的哲学家,胡塞尔工作的旨趣最先在数学和逻辑基础的研究方面,然后进一步去分析一般的认识的基础,最后在方法上探讨“纯粹的意识分析”,这样一步步逼近最终能为科学奠基,从而解决世界之所以作为如此世界而存在这样一个本体论的哲学问题。
当然,这样一种把世界存在的本体论放在现象学的纯粹意识范围内加以解决的思考,导致了一种现象学的对纯粹意识的自我理解的方法论。
而对纯粹意识构造的对象作意向分析的描述,最能直接支撑的学科就是心理学、特别是布伦坦诺的意动心理学。
为了避免涉嫌心理主义,纯化为科学奠基的立场,胡塞尔顺理成章地提出“现象学还原”这样一种新的哲学方法论。
[4]事实上,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一种不停地对世界构造的方法论的基础本身进行的追问。
[5]同时,有关科学——不管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精神科学,还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客观科学——的统一性和世界的内在结构的问题亦始终凸显在现象学哲学研究的舞台上。
现象学哲学要把各门具体的科学统一起来,这是因为世界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本质要求。
哲学一旦揭示出世界的内在结构——各门具体科学都与它有关——那么,它作为普遍科学而要为具体科学奠定绝对基础的理想不言而喻就会实现。
[6]
在某种意义上说,胡塞尔把一生的哲学工作都放在如何为科学的认识活动奠定一个绝对基础的思考上。
“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为实证科学奠基,而且也是为了在新的探索路径上再次寻找现象学哲学的自我奠基。
[7]所谓再次探询现象学哲学的自我奠基,指的是胡塞尔在不可能抛弃“先验自我”、“先验还原”等先验现象学的基本概念,坚持原有的先验自我学立场的前提下,用“生活世界”来解决他一直在思考的那些“普遍的存在问题和真理问题”的一种尝试。
[8]所以,对“生活世界”的讨论,要联系胡塞尔晚年现象学研究中解决普遍的存在问题和真理问题的思考。
如果说基于先验自我的纯粹意识的意向分析像根红线贯穿《理念》,而又一直延伸到《笛卡儿沉思》对交互主体性构造的话,那么“生活世界”作为胡塞尔《危机》的主题,则可以被视为这根红线的末端。
[9]事实上,胡塞尔的哲学思考是相当有连续性的——始终围绕着在先验自我基础上的那个科学的奠基问题。
激发起胡塞尔对基础问题思考的最直接的思想来源恐怕不是康德,而是笛卡儿。
显然,胡塞尔不满笛卡儿身体心灵二分的二元论观点,坚信无论自然的还是精神的东西,都应该在人的最原初的经验中被给予。
从现象学哲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精神科学,都要共同面对那个“单纯的经验世界”,只不过审视的具体对象和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如果人们返回那个他们总是在素朴的原初性中经验到的世界的完全原初的具体性,如果人们通过方法抽象的实现牢牢地把握住这个作为原初领域的具体直观的世界,那么,自然主义的心理学和精神科学就不可能混织在一起,人们也不再会把精神解释为物质身体单纯因果的联结,或者作为关于物理物质性的平衡主义的因果序列。
人们从来就不应该把人和动物看成心物结合的机器,或者就看成为平衡主义的双重机器。
”[10]这里,胡塞尔的企图不仅是为了修补笛卡儿以来欧洲人关于世界的图景,而且更是为了与这个世界图象有关的科学的奠基工作。
“这里宁可是一切与世界有关的科学的源泉,因此,科学每次原本清楚的划分,都必须通过返回经验世界来完成……每个特殊的科学领域都必须使我们回返到本原的经验世界的某个领域。
我们这里发现了可能的世界科学的一种有彻底根据的划分,即分门别类的原初出发点。
”[11]所以,“生活世界”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中,首先是作为客观科学的根本问题提出来的。
作为科学的基础,“生活世界”具有本源性,是人类一切有意义活动的发源处,也就是一切认识效准和客观知识的来源。
事实上,即使胡塞尔大谈“生活世界”,却一直持守基于先验自我的“现象学还原”的思维方法。
对于他来说,科学向自己经验基础的回返,意味着返回到“单纯的”或者“纯粹的”经验中,即返回到前概念的的经验。
一切科学由此得以最终奠基的那个单纯经验的世界“始于所有经验的思维”,[12]在其中“那些给出谓词的、理论化的活动,就像所有其他给经验对象以某种新的含义的活动那样,统统不起作用。
”[13]换言之,“先于所有的商量、斟酌、奠基、理论化的活动,一个绝对统一的、连续的、本身相互关联的世界是在经验本身的统一中被经验到的。
”[14]这是一个单纯的、前概念的知觉的和回忆的世界,是单纯直观的世界。
在胡塞尔的《笛卡儿沉思》中,这个世界又被称之为“原初的世界”或者“本有的领域”,也就是那个由单一的主体,通过对交互主体习惯交往作通盘的抽象之后,原本地经验着的和可以经验的世界。
[15]
所以,“生活世界”是由纯经验所构成的世界,它通过人生的原初经验而出现,并且总带有非主题的匿名边缘,并永远向未来的经验敞开;然后,它才被进一步通过科学理论化的活动开启出有意义的对象,才变成为客观主义意义上的永恒实体。
[16]欧洲在17世纪通过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把自然加以数学化的工作,使得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有了一系列意义非同寻常的转变,但其结果却是科学客观主义的盛行。
胡塞尔在他的《危机》一书中,用了整整40页的篇幅来讨论因伽利略而导致的世界观念的改变。
他把这种本末倒置的科学客观主义思想,看成恰恰是现代科学危机的根源。
显然,为了消除危机的根源,胡塞尔认为有必要回到作为科学根基的“生活世界”中去。
[17]因为,“生活世界”具有先于科学客观世界的在先性。
用胡塞尔的话来说,这种在先性便是“生活世界的先天性”。
[18]
无疑,科学活动是我们有目的地去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们生存、活着、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因之,我们才有对科学知识的意义与有效性的追问,才有了哲学化、理论化的实践活动,这个逻辑是不言而喻的。
一方面,“生活世界”总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前给予的“真正具体的周遭世界”,[19]另一方面,它对于我们来说,又是在相对性的不停运动中的存在者之大全;一方面,“生活世界”是相对于具体经验着的那个主体来说的一个直观地经验到的世界,另一方面,它又是在日常生活中,由人类共同担当起责任的世界。
一句话,“生活世界”是原本主体化了世界,而科学世界则是由此被赋予“科学”的世界。
换句话来说,科学世界之所以为科学世界,其根据是主体性的生活,它在“世界”中的展开。
[20]因此,生活世界的主体性和科学世界的客观性的不同在于,“后者是一个理论-逻辑的底层结构,即原则上是不可感知的、在其本来的自己存在中不可经验的底层结构;而在生活世界方面作为主体的东西恰好始终是通过它的真正的可经验性而被表示出来的。
生活世界是本原明证性的范围。
”[21]
客观科学的逻辑底层尽管超越直观主体的生活世界,但它只有在返回生活世界的明证性才具有自己的真理性。
这里,胡塞尔原来使用的先验悬隔不仅需要新的意义澄清,而且也需要探讨一种回返主体性的意义转换。
把问题挑明了来说,就是在“生活世界”中,胡塞尔原来使用的一些重要的构造现象学的概念,如“意义的根基”、“意义的源泉”、“意义的转变”和“意义的叠盖”等等,并没有获得世俗的意义,它们还是具有先验现象学的意义。
因此,“生活世界”在现象学的框架内,虽然起着为客观科学奠基的作用,但归根结底还得承认先验自我的最终构成的主导地位。
[22]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不得不面对两个棘手的问题:
一个涉及到普遍悬隔的引入和说明——“生活世界”是现象学悬隔后的凸显的关于世界的整体意义标示,还是本身就需要首先放在“括号”中的前给予性的经验对象?
另一个问题关系胡塞尔执著的那种普遍的、起着最终奠基作用的先验主体性——既然“生活世界”归根结底还是先验主体性“构成”的结果,那么,它与其他构造的东西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生活世界”的构成不也要服从一个普遍的意识活动的结构吗?
“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就是这个普遍的意识结构吗?
[23]如果胡塞尔顺着“生活世界”消去自我意识构造的先验性,真正返回到自我在世界中的本真生活,那么,“生活世界”不失为现象学哲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但这样一来,胡塞尔不就成了海德格尔,而先验现象学不也就变成存在哲学了吗?
[24]
二.“生活世界”的本体诠释
胡塞尔在先验现象学中推不开、甩不掉的棘手难题,放到中国哲学思维里头加以观照,倒不见得是一件有多么特别令人烦心的事情。
我们试着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放在中国哲学中作本体论的诠释,指的是用中国哲学的生命整体观来重新还原胡塞尔的整套先验现象学还原。
换句话来说,用中国哲学的“生活——世界”来为胡塞尔在其现象学的先验自我中被纯粹化了主客体同一性进行“奠基”。
[25]由是,“生活世界”当应真正回到生活中来,使之作为世界伸延出去,成为真正的由生命担当起来的“生活—世界”。
中国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它的活水源头就是人的生命本身。
中国哲学以生命为对象,强调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去调节、运转和安顿生命。
[26]人的生命包括生存、生存展开的各种世俗的、或纯意识的活动。
如此看来,胡塞尔执著的现象学的纯粹意识分析仅是生存活动的一个部分而已,并不是生存的全部,尽管他天真地相信通过它可以在整体上把握生存的意义。
生命是理解世界——现象学还原不过是这种理解的先行步骤——的基础,也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谈“生活世界”,首先得谈生活本身。
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理性之了解亦非只客观了解而已,要能融纳于生命方为真实,且必须有相应之生命为其基点。
”[27]当然,胡塞尔并不是没意识到这一点。
问题是他的感奋点是为科学奠基的认识根据说明,是所谓纯粹意识的意向分析,而不是直接面对纯粹意识活动展开前的生命本身。
[28]这里要作的事情是,把胡塞尔经过先验还原才得到的“生活世界”重新还原为真实生命活动的“生活——世界”本身。
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再作生命的还原,是我们对“生活世界”作本体诠释的方法论要求。
否则,我们像《西游记》的孙大圣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手心那样,无法摆脱先验还原所划定的自我论巢臼。
这样一来,难道我们不怕陷入胡塞尔批评过的素朴的、非反省的“自然主义”吗?
中国哲学是这样一种还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理性思维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命题无疑是反自然主义的深刻命题,它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第一,天人本来合一;第二,天人应归合一。
天人本来合一指的是天人相通,天人相类。
所谓天人相通,是认为天与人不是相对待之二物,而本来就是一息息相通之整体,其间实无判隔。
同时,天是人伦道德之本原,人伦道德出于天。
[29]甚至可以说,只有承认了“天人合一”思想,“生活世界”才有它——用胡塞尔喜欢的词Begruendung来表达——成存的根基,由此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出来,成为“生活—世界”。
中国哲学家把“生”看作是通贯于天地人我万有一切所成之总体的创造性根源。
《易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又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寥寥数语,深切著明,一下字就把世界的创发、变化讲得清清楚楚。
“天地之大德”是因“人之参与”而有天地之大德。
中国哲学由中庸、易传之形而上的立言,经由宋明理学而往人的心性论走,就避开了所谓“自然主义”的谬误。
早在周秦之际的儒家作品《礼运》中,已经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之说。
这表明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不将世界推开去说,而是将世界与人关连成一个整体来对待。
这样,就不需要像欧洲哲学那样拐了个大弯后,才由胡塞尔在所谓主体的纯意识中来为世界重新奠基,从而搞出个囿于先验主体性而说不清、理还乱的“生活世界”。
这正应了宋代大儒陆象山那句名言:
“宇宙原不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30]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实践论是通而为一的。
不是像胡塞尔那样由人的先验意识去纯化一个形而上的最终根据说明,也不是像康德那样由人的道德实践论而开启一个道德的形而上的根据说明,而是它本身就体现了“天、地、人交与参赞”。
[31]“交与参赞”的强调是要阐明一主客交融的“非主体论”的立场。
就是说,个人的心与宇宙本来是一体的,只是人自己把自己同宇宙“限隔”了。
这种“限隔”的总根源不是别的,恰好就是胡塞尔本来想用来消融主客对立的那种“现象学还原”。
“还原”就是一种“限隔”,一限隔就凸显了那个“私”,有“私”就有“智执”,就把世界作为“意向对象”而与我的“意向活动”分隔开来。
[32]从这个角度来说,宋明理学中不论是陆王的“心即理”的“本心论”,还是程朱的“性即理”的“天理论”,都容易从“主”“客”两侧滑向胡塞尔现象学的还原论。
按照某种新儒家的立场,“本心论”与“天理论”应销融于“气的感通”这一中国哲学的大传统中,这样才能解其蔽。
[33]
胡塞尔也谈生活实践,但所强调的是纯粹意识的活动、纯理论化的活动。
他把生活的本质看成是在意识中展开的意识活动,是意识之流的流动。
而中国哲学讲的生活,是人以其身体、心灵通而为一展开的实存活动,侧重的是人的道德自觉,而非认识的形而上学追问。
因此,“身体”与“心灵”是通而为一的,不是像欧洲唯心论那样“以心控身”,而是“身心一如”。
欧洲哲学中的唯心论讲“以心控身”,是身心分离为二。
中国哲学讲“身心一如”则是打破这种分离,回到生命本身原先的无分别相、无执着相。
欧洲哲学特别是胡塞尔现象学,强调“以心控身”,与此相连的是强调“以识执境”。
胡塞尔谈“生活世界”,始终是在纯粹意识中打转转。
中国哲学讲的是“身心一如”,与此相连的则是“境识俱泯”,一切都返归于生命之源。
进一步说,我们批评胡塞尔的“以心控身”的纯意识本体论,因为,如此一来,身体就成为心灵的主宰者,身体是从属于心灵的,或者说“身”成了“心”之构造物,“心”则为“身”之给予者。
[34]把纯粹意识还原为生活实际本身,就是破除这种主奴式的身心论,回到原初的主客交融式的身心论;不再是“以心控身”,而是生活本身的“健身正心”。
[35]我们讲“健身正心”、“身心一如”,不再强调胡塞尔现象学中纯粹意识分析式的“一念警恻便觉与天地相似”,而是“天地人交与参赞”。
强调“身”的活动带起“心”的活动,“心”的活动又润化“身”的活动。
总之,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所谓生活是人以其身体、心灵通而为一所展开的实存活动,这是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实——存——活——动”。
因此,首先是人的生活本身然后才是意识的构造把处于历史中的世界给展开了、给凸显出来了。
人的生活就是绵延不息的、刹那生灭的时间的当下化。
生命的展开就是时间,而时间的绵延不息并不是胡塞尔所讲的那种中性化的统摄一切的意识流,也不是一种可在意识中加以对象化的存在。
[36]我们说时间就其绵延不息、刹那生灭来说,并非纯粹意识之流,亦非意识一对象化之存在,而根本上是类似佛教所讲的“空”。
[37]“空”是使得一切实有之所以可能的天地,这是在人还没有赋予对象以意义、即未始有命名之前的存在,即老子所说的所谓“无名天地之始”[38]。
“空”并非是要经过先验还原才可获得的纯粹意识;即使胡塞尔现象学的还原,也得回返到“境识俱泯”的生命本身上来说,由此可知时间天地乃是道之彰显所伴随而生者。
“空”使得“天地人交与参赞而成之总体”因之而得开显,就此开显而为不息绵延。
“绵延”与“人”之参赞化育密切相关,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展开的历程。
生命的展开就是从“空”走向“存在之充实”,使之成其为“生活——世界”。
儒学强调的是从生命的源头出发,经由“内圣外王”的进路,实现“天人合一”的道德形而上理想。
佛老皆强调回溯性的哲学反思工作,即回到生命本真的道体之空无,而儒家则强调落实于存在之真实。
正如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强调“存在地呼应”,是进入与实现客观了解的关键。
它是生命的感通和共鸣效应。
吾人由此与古人的生命智慧,得“相应之契悟”、“相应之契会”,达成理解。
[39]
世界存在之真实,在胡塞尔那里表现为“意义的给予”,这是落在人的“意识构造”层面而说的。
对中国哲学来说,“世界”之作为“生活世界”,是由生命的“空”层面走向“存有的开显”进而走向“存有的执定”的层面。
“意识构造”并不是随“一念”之转而起现,而是在存有的开显历程中,有所转进。
胡塞尔通过“生活世界”来为科学奠基,进而解决存在的问题和真理的问题。
但是,他讲生活一方面比近代欧洲所凸显的自我哲学高明,但另一方面却未能跳出所谓纯粹意识的逻辑进路。
我们现在依靠中国哲学回到生命的源头,这里是无时间相,无空间相,但却是一切开显的根源。
我们一再强调世界并不是落在意识构造而成为世界,而是在生存的根源处本为一体。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哲学谈论的问题核心集中在“生生”,而胡塞尔现象学的问题则集中于“意义”。
换言之,我们说“世界”便隐含“生生”意义,就是一种“生活—世界”。
相对而言,胡塞尔所论的“生活世界”还是在纯粹意识中的对象化的存在,尽管是作为存在之根据的那种存在。
综括所论,可以试着这样来重新诠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
“生”乃贯穿天地人我万有一切所成而又交互参赞的创造性根源,也是“先验自我”由以凸显的本源处;“活”乃人以其身体、心灵通而为一展开的实存活动,由此,意识构造活动才有可能展开;“世”是绵延不息的生命历程,也是由“无名天地之始”走向“存有的开显”进而走向“存有的执定”的历程;“界”是广延伸展的空间区隔,万物由此有位相而得以把握。
进一步说,“生活”并非纯粹意识的活动,而是由通贯于天地人我万有一切所成之总体而又交互参赞的创造性根源,落实于人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实存而有”,以其身体、心灵通而为一,因之而展开的实存活动。
“世界”是由此开显出来的生命事物的活动场域,是绵延不息的生命历程与身处有待的空间标定。
时间历程本来就是纯粹的绵延,广袤空间亦本为无边无际,但有了人在生活中的意识构造活动,才有了“世”和“界”,亦因此而能得交错。
生活之为生活是因为人之“生”而“活”,世界之为世界亦因人之参与而有“世”和“界”。
“生活世界”是“生—活—世—界”,是“生活—世界”,是天地人三才,人参与于天地之间而开显的世界。
三.“生活世界”批判
世界在欧洲哲学史上由原先的宇宙论对象转向后来的认识实在论对象,经由胡塞尔现象学纯粹意识分析的“生活世界”,进一步转向海德格尔的“在世中的存在”[40],实际上是从最初素朴的宇宙论,经由精致的主体意识论而一步步走向对人生命存在的本根思考。
由此,欧洲哲学从传统的本体论走向一种较为接近中国哲学思考的生命本体论。
[41]生命本体论是从人的生存出发对世界所作的本体承诺,对世界作任何本体的承诺——诠释都要建立在生命的基础上,因为它本身才是唯一的认识的出发点和根据。
我们与胡塞尔现象学有所区别的地方在于,对生命的体现、把握不必非要经由“现象学还原”不可。
[42]或者说,“现象学还原”必须拓宽为一种“生命的还原”,从狭窄的纯粹意识论中跳出来,返回到真正的生命本身。
胡塞尔从“先验自我”的思考走向“生活世界”,本身已经说明“现象学还原”遇到不可避免的困难。
可惜胡塞尔并没有放弃他的先验哲学立场和由此所作的纯粹意识分析,从而彻底地把“生活世界”当作放在“生活”中来考察的“世界”。
其实,胡塞尔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关键是在欧洲哲学的传统中,可供他挖掘的思想资源并不多。
所以,他的感奋点、兴趣点不能不仍然囿于柏拉图——笛卡儿这样一条欧洲哲学的知识论路向。
[43]实际上,讨论“生活世界”,根本上不是为科学的奠基,而是揭示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
而要作到这一点,哲学家非得要从以纯主体性意识为中心的观照转到以感通互动为依归的立约天地。
我可以肯定地说,“生活世界”的本体真实性不可能在纯粹意识中寻到,而只可以在感通互动的社会交往中遇见。
[44]
在中国哲学中,我们恰恰可以找到许多欧洲哲学对生命本体论较为缺乏的思想资源。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生命”,儒学、宋明理学是“生命的学问”,儒家义理本来就是其真实生命所呈现,亦在启发人的真实生命。
生命进路、生命智慧之存在地呼应,原是传成与理解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的客观要求;客观了解的有效性必待生命存在的参与始得实现。
我们基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而理解的“生活—世界”,就不单单是科学认识之出发点,更是生存体验和道德实践的原初点和基准点。
所谓“天人合一”,它的意义在于要求解决“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探求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综观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可以归结为天、道;性、命;理、气;心、性。
这些本体论范畴也不仅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更具有道德实践的意义[45],这才是“生活—世界”的应有之义。
虽然孔子所讲的“天”,大都有意志的“天”,它是统治一切的主宰;孔子的“天生德于予”,已经赋予“天”以道德的含义,但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先把本体论与道德论扭在一起加以系统谈论的应是孟子。
他主张天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与”,天道有道德意义,而人禀受天道,因此,人性才有道德意义的。
人之性善有天为根据。
“尽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46]“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在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万物皆备于我矣。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47]孟子所谓人性之善,乃“天之所与我者”。
后来的宋儒张载也指出: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
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
圣人尽性,不以闻见牿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
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48]另一位宋儒程伊川更是认为,“道与理一也,……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性之有动者谓之情:
凡此数者皆一也。
”[49]“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
”[50]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不就在天人的互动中直接无碍地向我们呈现出来了吗?
。
无疑,胡塞尔已经走到了“生活世界”面前,但他不可能走出“先验自我”的框框。
我们需要把他再往前推一推,使他真正在生活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看”到生活。
首先,对于“现象学还原”,我们需要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使之转变为“生命的还原”。
[51]胡塞尔的偏执在于深信“先验意识”真的具有一种普遍的固定结构,它足以支配、主导“生活世界”的内在呈现。
在胡塞尔看来,我们只有通过“现象学还原”,回到“先验自我”的立场上才能发现这种普遍的意识结构。
问题在于,“现象学的先验还原”只进入纯粹意识,还没有进入生命的本真存在状态,而人的纯粹意识状态当然不是他的生命的本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