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游世思想.docx
《庄子的游世思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庄子的游世思想.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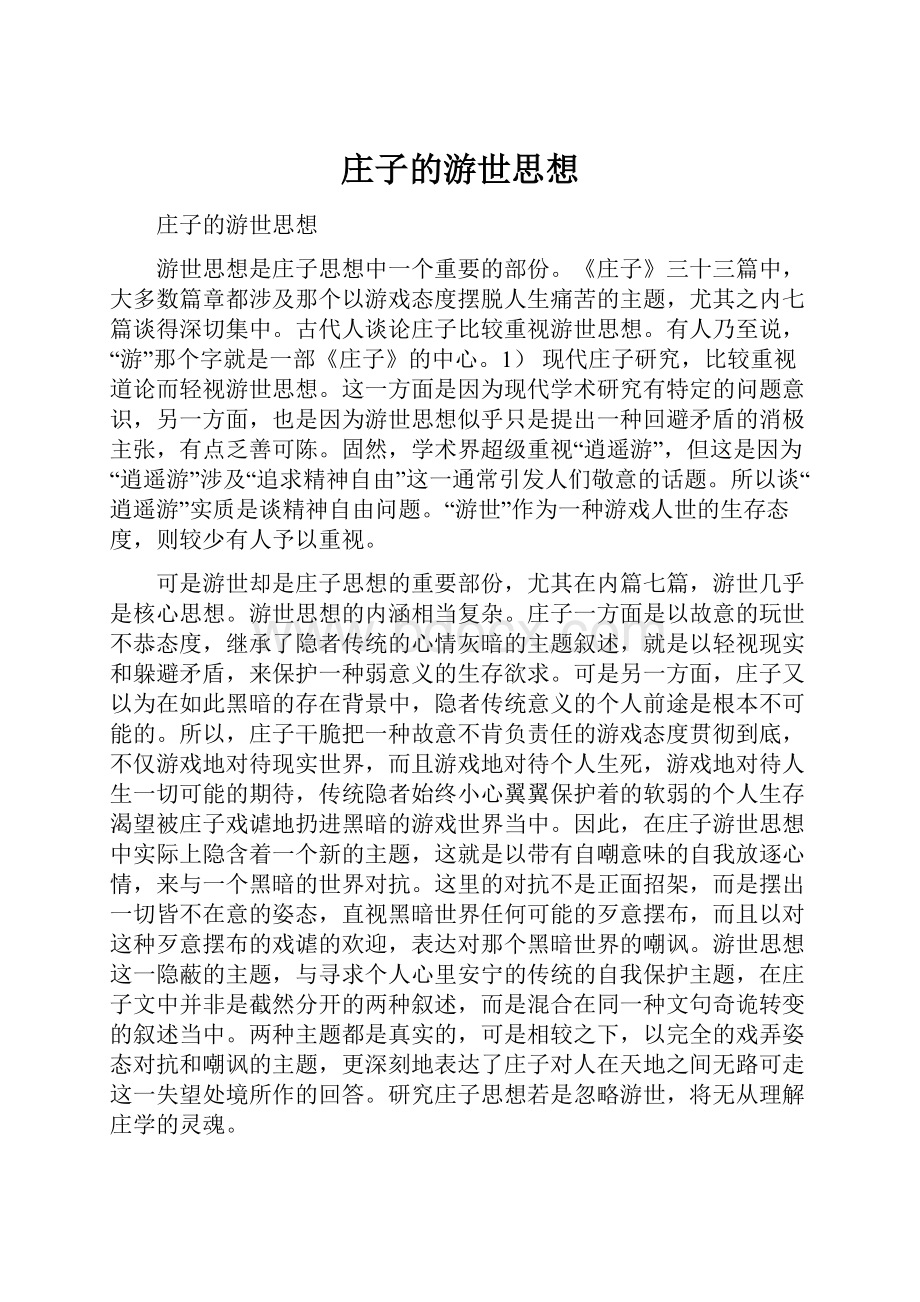
庄子的游世思想
庄子的游世思想
游世思想是庄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部份。
《庄子》三十三篇中,大多数篇章都涉及那个以游戏态度摆脱人生痛苦的主题,尤其之内七篇谈得深切集中。
古代人谈论庄子比较重视游世思想。
有人乃至说,“游”那个字就是一部《庄子》的中心。
1)现代庄子研究,比较重视道论而轻视游世思想。
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学术研究有特定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世思想似乎只是提出一种回避矛盾的消极主张,有点乏善可陈。
固然,学术界超级重视“逍遥游”,但这是因为“逍遥游”涉及“追求精神自由”这一通常引发人们敬意的话题。
所以谈“逍遥游”实质是谈精神自由问题。
“游世”作为一种游戏人世的生存态度,则较少有人予以重视。
可是游世却是庄子思想的重要部份,尤其在内篇七篇,游世几乎是核心思想。
游世思想的内涵相当复杂。
庄子一方面是以故意的玩世不恭态度,继承了隐者传统的心情灰暗的主题叙述,就是以轻视现实和躲避矛盾,来保护一种弱意义的生存欲求。
可是另一方面,庄子又以为在如此黑暗的存在背景中,隐者传统意义的个人前途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庄子干脆把一种故意不肯负责任的游戏态度贯彻到底,不仅游戏地对待现实世界,而且游戏地对待个人生死,游戏地对待人生一切可能的期待,传统隐者始终小心翼翼保护着的软弱的个人生存渴望被庄子戏谑地扔进黑暗的游戏世界当中。
因此,在庄子游世思想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以带有自嘲意味的自我放逐心情,来与一个黑暗的世界对抗。
这里的对抗不是正面招架,而是摆出一切皆不在意的姿态,直视黑暗世界任何可能的歹意摆布,而且以对这种歹意摆布的戏谑的欢迎,表达对那个黑暗世界的嘲讽。
游世思想这一隐蔽的主题,与寻求个人心里安宁的传统的自我保护主题,在庄子文中并非是截然分开的两种叙述,而是混合在同一种文句奇诡转变的叙述当中。
两种主题都是真实的,可是相较之下,以完全的戏弄姿态对抗和嘲讽的主题,更深刻地表达了庄子对人在天地之间无路可走这一失望处境所作的回答。
研究庄子思想若是忽略游世,将无从理解庄学的灵魂。
一、从避世到游世
传统隐者的思想核心是保全自己。
用杨朱派总结的说法叫做“重已”,用孟子替杨朱派总结的说法,叫做“为我”。
“为我”那个说法,有一种反道德的自私含义,这是孟子带有情感色彩的说法。
但大体上能够代表隐者和以隐者为背景的道家人物的思想。
冯友兰就曾指出,道家的中心思想就是“为我”。
2)道家各派人物理解之“我”,含义大有不同,有人注重逍遥闲适,有人注重卫生长寿,有人注重品行高洁,3)有人注重纵欲的快乐,有人注重“六欲皆得其宜”的身心协调。
4)但这些不同的理论有一个一路点,就是都在一个混乱黑暗世道里寻求保护自己。
这是隐者群体的传统思想。
在庄子思想中,也有这一层传统的寻求乱世自我保护的想法。
虽然这一层想法在庄子的整个思想系统中不居于核心地位,因为庄子最终以为自我保护办不到,而且这躯壳的自我是不是值得珍视仍是问题,但庄子毕竟也谈到了自我保护问题。
在《庄子》各篇中,乱世自保的问题说得比较杂。
本文不预备对此做过细的分析,只想抓住庄子养生自保思想最有代表性的观念,看庄子与隐者思想的相同处安在,不同处又安在。
庄子养生自保思想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无用”。
庄子也谈其它的养生保身方式,但特别喜欢谈论“无用”的益处。
《庄子》许多篇都说到“无用之用”的观念,其中尤其内篇的《逍遍游》、《养生主》、《人世世》和外篇的《山木》诸篇讲的较为集中。
“无用”是庄子独家之言,其他道家诸子不见有人提及过。
固然以“无用”自保的想法与传统的隐者自保方式也有相通处。
隐者避世而居,实质就是以无用于世而自保。
《论语》中的楚狂接舆,《楚辞·渔父》中的渔父,都曾批评用世者(孔子与屈原)不知自保。
《韩非子》中说杨朱派是“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这也是一种无用自保。
可是庄子特别点出“无用”二字,却别有含义,与隐者诸子客观上的无用自保有若干不同。
第一点不同是庄子的“无用”表现了隐者从避世到游世的转变。
避世是隐者传统的态度,《论语·微子》中隐者桀溺对孔子门生子路说:
“且而(你)与其从避人之士(指孔子)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
”避世就是躲避政治,找一个清静之地过日子。
隐者避世态度隐含了一个想法,乱世能不能自我保全,关键是自己主观上想不想隐退。
《论语》里批评孔子的隐者,注重的就是那个进仍是退的主观选择。
后来的杨朱派谈贵生问题,注重的也仍是自己如何选择。
似乎只要自己愿意隐退,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可是庄子不如此看。
“无用”固然是主观上选择隐退,这一点庄子与以前的隐者是一样的。
可是仅仅选择隐退并非解决问题,个人不想介入社会,社会却要来干与个人。
所以只是避世不解决问题,而是应当“游”于世上,关键是要谨慎地避免矛盾,在夹缝中游。
《养生主》篇有一段讲养生道理的著名寓言“庖丁解牛”。
庖丁说他解牛时刀刃从不硬折骨节,老是从裂缝当中批过去,“彼节者(骨节处)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那个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的比喻,就很形象地说明游世的态度。
《山木》篇中有一段寓言,说庄子带着门生行于山中,见有一棵大树枝叶茂盛,却是一棵“不材”之木,这棵树因其“不材”而活得专门好,没有被木工伐去。
庄子等人出了山,住在故人家,故人杀“雁”(鹅)招待,把一只不会叫的雁杀了,留下了会叫的。
这是一个用心很深的比喻。
不会叫的雁招惹了谁呢?
最后灾祸仍是找到它头上,仍是被杀掉了。
这说明乱世全身免祸十分艰难。
避世隐居以求自保,已经很难做到。
孟子曾经说到齐国的隐士陈仲子,这是一个一心想与世隔间,过自己清静生活的人,但却做不到。
孟子挖苦说,除非他变成蚯蚓钻到土里,不然清静的愿望就不能实现。
(《孟子·藤文公下》)《战国策·齐策》中记赵威后问齐国的使臣说,那个“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于陵子仲(即陈仲子),你们大王为何到今天还不把他杀了?
赵威后建议杀陈仲子的理由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
政治家强烈的集权意识使“无用”也成为罪名。
这就是主人家雁因不能鸣而被杀的现实背景。
庄子的“无用”主义与传统隐者的第二点不同,是有一种嘲弄隐者精神自尊的意思。
这一点对于理解庄子思想的精神特质比前面一点更重要。
传统隐者有一种对个人生活和自我形象的认真。
他们能够傲视王侯,厌弃社会责任,但他们对自己的安危和道德形象大多是一本正经的。
前面提到的陈仲子,是这种一本正经的典型。
孟子说他自己织鞋,妻子漂麻为生,即便饿到头晕眼花,也不肯吃其贵族哥哥的饭,以为那是不洁的饭。
有一次在母亲那儿无心识吃了他人送给哥哥的鹅,赶紧出去吐出来。
这毫无疑问是在认真地坚持某种东西。
5)战国时的隐者未必都能像陈仲子那样高傲猖介,可是在隐居避世中坚持某种干净理想应是很普遍的。
战国时隐者中的传说人物巢父、许由、务光之类,就是按照这种干净理想中编造出来的。
这形象中包括着隐者群体对社会现实失望以后转向个人生活的最后希望,这希望不仅是为了个人能够活着,而且是为了成心义地活着。
可是这自我尊严的最后希望却被庄子以嘲弄的语气消解了。
庄子有时也认同传统隐者对个人干净理想的坚守,可是有的时候,庄子却发表了一种嘲弄这种理想的观点。
这种嘲弄很少作为一种宣言直接从字面上说出来,而是渗透于庄子描述“无用”游世的那些文字当中。
《人世世》篇写到如此一名一身邋遢,有点无赖气的游世高手: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
挫针治足以生活;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
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
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这位支离疏活得很自在,他病残得不成样子,却能够缝洗衣服、簸米筛糠度日。
兵役摇役来了,正常人要逃匿躲避,他能够大摇大摆,政府赈济贫困,他又能够安享三钟米十捆柴。
这就是“无用”的益处。
可是在这位“无用”高人的身上,咱们看不到战国时隐者形象通常有的那种自尊,这是一个“二混子”的形象。
什么干净自尊全都没有了,只要有利处就自鸣得意,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
支离疏的混世气息,不在于全身怪病,而在于安然地以怪病为武器谋求益处。
在这以“无用”为用的满不在意的混子形象中,隐者传统暗中坚持的最后一点自尊被消解了,只剩下一个再无任何精神分量的“活着”。
支离疏并非是庄子笔下偶一出现的惫赖人物,而是一系列成心味的形象中的一个。
最意味深长的说法,是《养生主》里面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
缘督以为经,能够保生,能够全身,能够养亲,能够尽年。
”其中“为恶无近刑”一句,古今注庄者,鲜有直接承认庄子以为能够做坏事。
庄子怎么能提倡做坏事呢?
但事实上庄子在这里说的就是能够做坏事,只要不受刑法制裁就好了。
这里的关键不是庄子鼓励人“为恶”,而是对做人是不是应有某种准则故意不在意。
活命就行,并无什么原则,没有什么精神上令人安慰的东西。
为何不能做点坏事?
为何不能因做坏事不受惩罚而自鸣得意?
“为恶无近刑”这一段就有这种语含嘲弄的自鸣得意,与“庖丁解牛”从骨节裂缝中批刀入去的自鸣得意,支离疏甩着膀子在抓兵役的官差前大摇大摆的自鸣得意是一样的。
庄子提倡的全身自保方式,与战国时流传的隐者形象相较,与宋尹派、杨朱派这些道家派别提倡的自我保全之道相较,无疑是有嘲弄自尊的消极含义。
问题是应当如何理解庄子思想这种不要尊严的消极态度?
庄子本人是如此的人吗?
庄子自己曾用这种消沉的方式处世吗?
庄子说“为恶无近刑”,讲支离疏以怪病谋求益处的故事,他是认真地向世人推荐自以为得计的处世之道,真的因为小计巧保全自己而沾沾自喜吗?
从《庄子》三十三篇大体偏向看,咱们以为庄子根本是一个十分重视生存的精神质量的人。
其实,《庄子》中保留的一些庄子生平小故事,就已说明庄子是一个认真的人,是一个对个人品质有严肃要求,决不肯马虎苟且的人:
楚威王礼聘庄子,庄子不去;(《秋水》)惠子在梁国为相,深恐庄子名高取代自己,庄子对他说,南方的凤鸟只肯止息在梧桐树上,只肯饮干净的醴泉,岂肯同猫头鹰夺食死鼠;(《秋水》)宋人曹商出使秦国,得秦王赏识而购车百乘,庄子对他说,秦王那个人,他人侍奉他越发无耻下作,他愈高兴,赏赐就愈多;(《列御寇》)庄子穿补丁的平民见魏王,魏王说“何先生之惫也?
”庄子说,一个人不能行道德才叫“惫”,穿破衣只是“贫”,不是“惫”。
(《山木》)这些有关庄子事迹的故事固然有夸张的成份,可是总有一点事实按照。
这许多故事都说明庄子的清高,应当是以庄子本人的品质为基础。
所以咱们以为,庄子本人的行为处世方式,没有背离隐者那种自尊自重的传统。
若是庄子真的是滑头混世的人,而且以此在隐者圈子中自开一派,传课授徒,那必然会有另一种类型的庄子生平小故事流传下来。
那么,庄子以夸张的语气宣扬消极混世,就是还有效意。
我以为这种宣扬,是一个认真的人因为愤世而故意否定自己的认真,是以嘲弄自己所属的人类群体,来表达对黑暗不可理喻的“存在”完全不负责任的激愤心情。
虽然传统隐者就已经消极地对待世界,但他们坚持某种有原则的生活方式,这在客观上就是以为世界虽然黑暗,总还留了干净的地方,还能够允许独善其身的生活。
庄子嘲讽这种独善其身的认真,以为世界完全黑暗,不可能有认真的个人生活。
既然如此,就以对个人形象的满不在意来对抗这完全的黑暗。
活在那个世上已不值得再认真坚持任何东西了,那就干脆以从身躯到品质都残缺不全的样子,来与这残缺不全的世界周旋。
乱世自我保全的问题,是隐者传统的问题。
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己,也是对自我保全方式的一种进展。
但“无用”的自保方式中含有两层既彼此联系又有些矛盾的意思。
一层意思是形式上更灵活一些,不拘泥任何原则,不避开人群,乃至不必然避开政治,所谓“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
(《山水》)纯从技能的意义上说,这是比先辈隐者“避世主义”更高超的存身之道。
另一层意思是消解个人的自尊。
因为以这种灵活游世的方式来保全生命就必需不在意一切原则和尊严,把生命变成毫无心义的“支离疏主义”。
这两层意思是相联系的,但又是有矛盾的。
支离疏这种意义的活着,是不是还能算生命的目标?
若是说自我保尽是隐者文化一百年以来的核心命题的话,那么这命题到庄子这儿发挥到了顶,同时也掏空了内容,开始走向问题的反面。
活着已经没有价值了。
庄子以夸张的语气描述消极游世的人生,他一方面固然是仍在探讨自保的方式,可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决不是在赞美这以最后的方式在黑暗世道里保全下来的生命;他是在嘲讽这种毫无精神分量的生命。
通过嘲弄这最后可能的活着的方式,庄子表达了对那个世界的轻蔑:
那个无可理喻的世界,只配让人如此活着。
二、戏谑生命的低微
游世思想就其完全的意义而言,是舍弃了自我保全。
游世思想的本意,也要为个人寻觅前途,可是庄子对世道黑暗看得太深,因此感觉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前途根本不可能,个人是找不到安居之地的。
那么人生活着怎么办?
庄子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干脆舍弃寻觅个人前途,一切任从命运摆布。
世道既是完全的黑暗,生命在宇宙背景中既是完全孤独无助,那就没必要再挣扎着寻觅黑暗世道里不可能找到的东西,干脆无所谓地没入黑暗当中。
无所谓地没入黑暗,有两种表现,一是就以黑暗的方式活着,这就是上一节所说的“支离疏主义”。
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安然面对灾祸和死亡。
《庄子》各篇中,常可见一些戏谑生命的生死游戏之言。
庄子游世思想包括戏谑地面对死亡,这一点以前的研究者早就注意到了。
可是以往对庄子生死游戏之言的理解,偏重于寻求心里的安宁,而很少言及庄子埋在游戏之言下的激愤与嘲讽。
6)这应该说是一个疏漏。
或许从本源上说,偏于从寻求精神安宁和心里知足的路子来理解庄学,这是郭象注在以后引出的学术传统。
可是那个传统却有待于检讨。
《大宗师》篇有一段关于“安命”的寓言: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为友。
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
曰:
“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
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
”阴阳之气有□,其心闲而无事,□□而鉴于井。
曰:
“嗟乎!
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
”
子祀曰:
“汝恶之乎?
”曰:
“亡,予何恶!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
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
其妻子环而泣之。
子犁往问之,曰:
“叱!
避!
无怛化!
”倚其户与之语曰:
“伟哉造化!
又将奚以汝为?
将奚以汝适?
以汝为鼠肝乎?
以汝为虫臂乎?
”子来曰:
“……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成然寐,蘧然觉
这一章文字的主题是说齐一生死,安命不争,这是没有问题的,可里面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子舆出现如此怪异的转变,这固然是为了表现这位世外高人在残酷命运眼前的旷达。
可是看得出,庄子同时是在借子舆的病变,曲折地表达另一种意思,那就是生命的低微和可羞。
人生在宇宙之间,不是什么万物之灵,就是一个普通的生物。
不仅如此,那个生物还完全无力把握自己。
造化宰制着人的命运。
造化并非是神,不是一个成心识的主宰者,它就是宇宙当中那无情盲目的力量。
可是那个造化对个人来讲是不可抗拒的,同时又恍如是怀着歹意。
造化播弄人恍如是播弄虫子。
人的生命在宇宙的背景中是无根的,他随时可能被轻易地消灭,也随时可能变成一个可悲的佝偻着的残疾人。
这就是人的低微可羞。
人在宇宙之间的低微可羞,是常常引发出宗教情绪的事项。
英国小说家毛姆在《刀锋》中让他的主人公拉里去参加空战,然后一个超级熟悉的战友,一个昨天还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被打成一团血肉。
那个景象令拉里超级震惊,事后他对人说,他那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羞愧。
人的生命怎么是如此脆弱低微的东西,一下就被毁灭成一团不堪入目的血肉?
这种强烈的羞愧感激发了埋在拉里心灵深处的宗教情绪,使他走向印度,向古老的东方宗教寻求对生命的解答。
庄子写子舆和子来的故事,必然有与此相类似的“羞愧”体验,就是对人的生命在本原意义上的低微的体验。
但庄子与毛姆不同,他不是让他笔下的人物去寻觅精神支持,来对抗造物把人置于如此低微的境界,从头令人的生命取得尊严。
他是让他的人物充分地沉浸在那种低微的境界中,不仅不思振作,反而愿意更深地沉浸在尚未到来而想象中随时可能到来的更完全的低微当中。
在上面的引文中,随遇而安只是那里面的一部份意向,其中更深的含义是与把人置于如此可悲境界的造物周旋到底。
乃至随遇而安的心情都与这种周旋到底的悲忿有关。
把左臂变成鸡,右臂变成弹,把整个人变成鼠肝虫臂,这固然都是夸张,人是不可能变成如此的。
连子来“曲偻发背,上有五管……”如此的病况也是夸张,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变成那种怪样子。
问题在于,使庄子写出这段文字的生活经验,必然是足以使一个有宗教情绪的人体验到人的生命在本质意义上低微的那种惨重经验。
而庄子游世理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是抗拒这种低微处境,使生命的意义取得升腾。
他反而用夸张的形容把人钉死在这种低微处境中。
沦入低微的人竟能用戏谑的言词谈论自己的悲惨处境,而且戏谑自己将可能沉入更可悲可羞的处境,他如此谈论不仅没有羞耻感,反而有一种不可摧毁的周旋到底的决心。
无论是“支离疏主义”,仍是戏谑生命低微,都是故意羞辱人那个类群的形象,把他们置于悲惨的环境,让他们没有尊严,也不想要尊严,就以一种毫无亮色的虫子一般的形象“游戏”地活着。
这种无灵魂的人类形象,固然是指示了在一个毫无道理可言的天地里生活下去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但另一方面,这种形象也揭露了人的存在背景的黑暗,和对那个存在背景毅然不抱丝毫希望的冷漠心清。
前人理解庄子的游世思想,偏重寻求精神安宁这一面,固然是有按照的,但如果是仅仅看到这一面而不顾庄子的冷嘲,那就会把庄子思想误解成一种自寻快乐的庸人哲学。
庄子何尝不喜好隐者传统的追求个人闲适宁静的生活态度。
这在《庄子》留存的许多文字能够看得出来。
可是庄子本性中原有一种激烈的东西,使他不能安于闲适宁静。
《逍遥游》开篇身长千里,直飞九万里高空的大鹏,就象征这不安闲适的激烈。
而庄子的游戏人世思想,不论是“支离疏主义”,仍是齐一生死,其中本质的东西,都与这种心里激烈有关。
从庄子的生平事迹看,似乎他并非是自甘于卑贱的游戏,或是生死都漫不在意,他更像是喜欢宁静悠闲。
可是理论上,他却恰恰论证宁静悠闲的不可能,用许多笔墨写尽世道黑暗,造化无情,以戏谑的口气把他笔下的寓言人物从谨慎平稳的生活程式中拉出来,扔进多变而不友好的黑色背景中。
这就是因为他心里的激烈。
三、客串存在的角色
庄子游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贯彻一种完全的游戏姿态。
在前面两节里,咱们分析了庄子如何以故意的戏弄姿态处置隐者最后郑重坚持的东西,自尊自适的个人生活和生命本身。
这种故意的戏弄姿态(专门是生死问题上),表明庄子在重生的隐者群中开出一个独特的新思路。
可是庄子把游戏意识贯彻到底的思想还不只是表此刻这里。
庄子完全的游戏姿态,还表现为成心识地拆除人心里深处对世界的信赖,把人生可能取得某种稳固未来的期待从根本上摧毁。
生死是一般人意识深处最后执著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对宇宙的最终合理性的期待也是人意识深处最后执著的一个问题。
而且后者可能更深刻一些。
因为其中包括着对身后的终极归宿的期待。
这种对宇宙合理性的期待变成自觉的精神诉求,就是宗教的本源。
宗教表达了对宇宙最终具有合理性,个人最终会在这合理性中取得安置的信赖感。
庄子时期的隐者没有发明宗教,可是隐者群对于永生的追求,和由此衍生的不死观念、神仙观念,都表明了他们对人能够在宇宙最终合理性中取得安置有一种信赖。
另外,像战国时《易传》的思想,阴阳家的思想,浸润着微弱的个人在宇宙结构中找到背景按照的喜悦,能够说都具有宗教的意味。
庄子完全的游戏态度,有时就是针对这种隐蔽在人心深处的对宇宙最终合理性的依赖感。
若是说这种依赖感是宗教的本源的话,那么,庄子思想可说是有某种“反宗教”的意味。
这不是指他像后来的王充那样依据经验常识反对妄诞。
庄子的“反宗教”是在意识到人心深处有对存在最终合理性的信赖感的前提下,自觉摧毁这种想象中的合理性,把人置于本体论意义的虚无中。
庄子不曾反对具有神学形式的一般宗教,他有时还借用各类神灵的名字表达思想。
可是庄子明确地表达了对能够作为个人生命最终庇护的存在深层结构的不信赖乃至敌意,这就是一种反宗教意识。
《逍遥游》篇把这种自觉拆除外部世界依赖感的反宗教游戏姿态称为“无所待”。
关于《逍遥游》篇的“无待”思想,论者多赞其达到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
却不知,“无所待”虽然表面有一种自鸣得意的神气,实质却是斩断个人与世界之间任何靠得住的联系。
斩断这种联系就意味着消除对存在稳固性的空想,消除许多宗教都追求的终极安置。
所以“无待”实际上是把人置于绝对虚无当中,是以故意做出的兴高采烈,高声宣布对终极存在决不信赖的灵魂放逐宣言。
庄子文中,不时可见一种成心拒绝最终归宿地的虚无心识。
在《齐物论》篇,庄子还通过一种逻辑的方式系统地论证了终极存在的虚幻性,这就是相对主义理论。
《齐物论》篇在庄子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这一篇为完全的游世态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庄子在《齐物论》篇运用的相对主义方式是诡辩性的,单从逻辑学的意义看或许并无多大价值。
可是在相对主义思想方式背后,更深的含义是对于人生的存在背景的精神瓦解。
其在哲学上的含义却十分深刻。
简单地说,相对主义的思想方式是如此的:
你说有一个什么东西重要,我就可以够指出,你说的那个东西只是从你的特定角度看重要,换一个角度看就未必,而在那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特定角度具有高于一切的优势。
因此一切存在物的价值都只有相对的意义,这种相对化的判定是绝对的。
指出这种方式在逻辑上的毛病并非难,问题在于,庄子为何要论证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呢?
庄子的真正用意,我以为是要描述一种存在的无根性。
人生在任何意义上都处于一种没有稳固按照的境界。
人生的经验进程和追求目标本质上都是相对的。
这“相对”不是一个稳固的宇宙构架中的有限部份,而是绝对无秩序的具体显示,是一个一应俱全却又变易无方的存在大场景中飘忽不定的片断。
人生的经验进程就是无数如此的片断,人生可能的任何追求目标也是如此的片断,因此,人与世界之间找不到稳固的联系,只有随意飘荡在怪诞的存在场景当中。
这种生存的怪诞,存在的无根性最形象的比喻就是梦境。
庄子多次谈到这种梦的比喻: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
梦当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
(《齐物论》)
人与外部世界之间联系的偶然性、不稳固性,便如梦境一样。
这里要注意的是,庄子描述的人生存在的梦境感,不只是一层梦。
若是是一层梦,似乎还能够等待梦醒以后的真实,似乎存在的按照还有希望显露。
庄子特别指出,人生在梦中,是犹如梦中之梦,是所谓“梦当中又占其梦焉。
”一个人即便明白了人生如在梦中,能够告知他人大家都在做梦,这警告之言仍是梦中之言。
《齐物论》篇借孔子之口告知他人:
“丘也与汝,皆梦也,予谓汝梦,亦梦也。
”《大宗师》篇又借孔子之口对颜回说:
“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
其梦者乎?
”就是讲这种层叠的梦境。
这里不是玩弄文字游戏。
这种层叠的梦境,喻示存在的背景构架一片混乱,毫无坚实性稳固性,而且看不到通向坚实稳固的可能。
个人的存在,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就是悬浮在偶然性的虚空当中。
个人不可能对未来有任何希望,因为他明白,最终的合理性是不存在的。
人与世界之间找不到稳固的联系,人无法对宇宙的终极存在怀有信赖,这使得个人存在成为一粒无根浮尘。
但是,游戏的姿态并非到此为止。
在这种无根的状况中,连个人自我存在的肯定性也变得飘忽可疑起来。
“自我”是肯定的吗?
若是是肯定的,它应当呈现为某种稳固的存在特征。
可是由于自我与世界彼此关系的不肯定性,这种稳固特征是找不到的,于是我是不是真的“我”也变成了值得怀疑的问题: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
不知周也。
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齐物论》)
庄周做梦成了蝴蝶,醒来又成了庄周。
究竟是庄周梦为蝴蝶,仍是蝴蝶梦为庄周,这是弄不清楚的。
所以庄子主张不要固执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