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意识.docx
《论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意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意识.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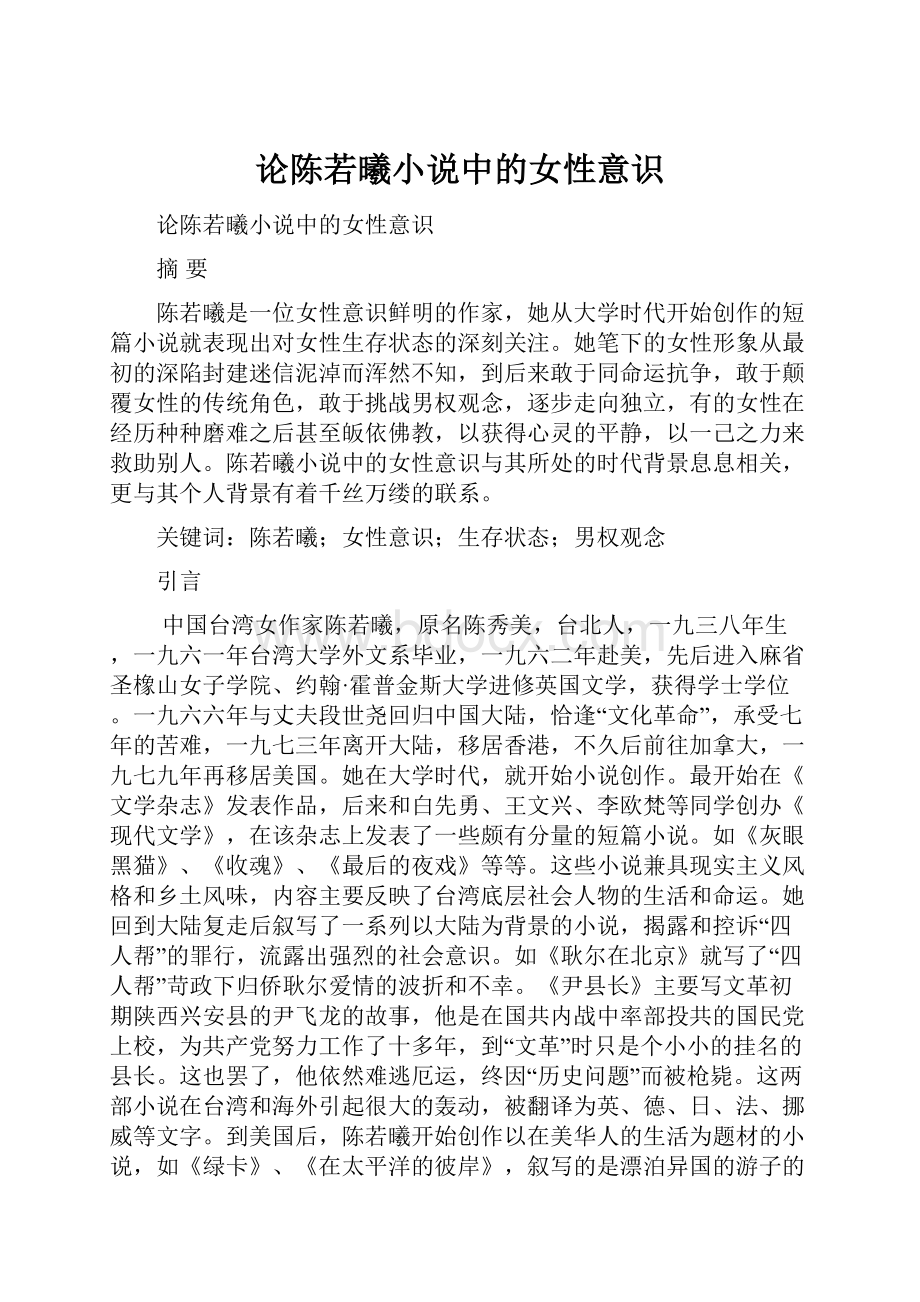
论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论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
陈若曦是一位女性意识鲜明的作家,她从大学时代开始创作的短篇小说就表现出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注。
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从最初的深陷封建迷信泥淖而浑然不知,到后来敢于同命运抗争,敢于颠覆女性的传统角色,敢于挑战男权观念,逐步走向独立,有的女性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甚至皈依佛教,以获得心灵的平静,以一己之力来救助别人。
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更与其个人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
陈若曦;女性意识;生存状态;男权观念
引言
中国台湾女作家陈若曦,原名陈秀美,台北人,一九三八年生,一九六一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九六二年赴美,先后进入麻省圣橡山女子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英国文学,获得学士学位。
一九六六年与丈夫段世尧回归中国大陆,恰逢“文化革命”,承受七年的苦难,一九七三年离开大陆,移居香港,不久后前往加拿大,一九七九年再移居美国。
她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小说创作。
最开始在《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后来和白先勇、王文兴、李欧梵等同学创办《现代文学》,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些颇有分量的短篇小说。
如《灰眼黑猫》、《收魂》、《最后的夜戏》等等。
这些小说兼具现实主义风格和乡土风味,内容主要反映了台湾底层社会人物的生活和命运。
她回到大陆复走后叙写了一系列以大陆为背景的小说,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流露出强烈的社会意识。
如《耿尔在北京》就写了“四人帮”苛政下归侨耿尔爱情的波折和不幸。
《尹县长》主要写文革初期陕西兴安县的尹飞龙的故事,他是在国共内战中率部投共的国民党上校,为共产党努力工作了十多年,到“文革”时只是个小小的挂名的县长。
这也罢了,他依然难逃厄运,终因“历史问题”而被枪毙。
这两部小说在台湾和海外引起很大的轰动,被翻译为英、德、日、法、挪威等文字。
到美国后,陈若曦开始创作以在美华人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如《绿卡》、《在太平洋的彼岸》,叙写的是漂泊异国的游子的处境、思想感情和心中的希望。
同时,《丈夫自己的空间》、《我们上雷诺去》等小说描写了在美华人女性的婚姻状态。
作为一位真诚而本色的女作家,陈若曦格外关注女性的生存、地位、命运与处境,她的创作呈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我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题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
”[1]在现代社会以前,女性是没有性别意识的,对“我是谁?
我要干什么?
”这种具有哲学意味的人生终极追问,在其意识范围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女性的生存实质是对男性的依赖、服从、惟命,女性的一切文化特征都由男性文化来确定。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受教育女性的增加,参与社会机会活动的增多,日渐独立的经济,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一大批的女性登上社会和文学的舞台。
六十年代,台湾社会上出现大批的女性作家,她们在创作中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陈若曦便是其中一个。
尽管陈若曦不像张爱玲专注描写男人与女人的情感纠葛,也不像李昂一样主张新女性主义,但是她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塑造敢于挑战传统爱情模式的华人女性形象,不断探索女性自我救赎的道路,流露出很强烈的女性意识。
一、对底层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
纵观陈若曦在台湾期间的小说创作,我们发现在台湾中下层社会人物生活和命运的主题创作下,始终贯穿着陈若曦对底层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
陈若曦的出生背景决定她以“中下等社会家常平淡之事”为己任,通过描绘中下层社会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各种人情世态揭露社会矛盾,她很早就抱定了为社会中下层人物而写作的宗旨,并在自己的创作中诉之笔墨:
“家里来往的亲友不是务工,便是务农,朴实无华。
也许生活方式略有不同,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对生活的奋斗,照样的狂热炽烈,七情六欲的表达更加真实、健康”,“所下了决心,写作的目标,便是刻画他们的生活。
”[2]她以女性的视角,把关注的目光锁在那些深受现实处境之苦的下层女性身上。
比如《收魂》中的母亲和姐姐、《最后的夜戏》中的金喜仔、《灰眼黑猫》中的文姐等,她们要么深陷封建迷信的泥淖,要么为生存苦苦挣扎。
(一)深陷封建迷信泥淖的女性
陈若曦在自己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深陷封建迷信泥淖的女性形象,她们在封建迷信的熏陶下,没有意识到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
《收魂》叙述了弟弟阿萱病危在医院,他的家人却在家里为阿萱“招魂”,忙得不亦乐乎的过程。
在儿子病危之际,阿萱的母亲不知所措,对她来说,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只要儿子能恢复健康就为良策,才把希望寄托在封建迷信上,她请来道士,为儿子收魂,祛除病痛与灾难。
母亲非常自觉地安排着道士所需的收魂用品,并且整个准备的过程显得格外急切,容不得半点差错,可见母亲对封建迷信深信不疑,而年轻一代的姐姐身上也有封建迷信的影子,文中写到“在道士被父亲请来后,她为道士采摘一朵供桌上的用的花蕊,跑到前院墙角边,发现她和弟弟合种的一株玫瑰,花儿全谢了,她马上想到了‘死’”[3]姐姐还协助母亲准备道士收魂用的道具。
母亲希望儿子健康的迫切之心,我们可以理解。
在儿子病危之际,她可以求助于医术高超的医生,使儿子恢复健康,而不是请道士收魂,寄希望于封建迷信。
那么,收魂的效果如何呢?
阿生伯给这个气氛紧张的家带来了噩耗,即阿弟死了,无疑给这个家蒙上一层绝望的气息。
家里希望阿弟身体健康的美梦破灭。
但母亲与姐姐仍然坚信父亲的话,“父亲走进来,微笑着:
‘道士说了,贵人出现在东方,午夜便安然无恙。
进来吧,生伯,我已经替他收过魂了。
’”[4]在既定的残酷事实面前,阿萱一家始终如一地相信封建迷信,令人震惊的是她们把它作为正确的信念。
这不得不说封建迷信的根深蒂固,何其哀哉!
在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传统的观念与封建思想已经沉淀成一种民族无意识的文化心理,深深烙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给女性带来心理重压。
《妇人桃花》的女主人公桃花因生病卧床不起,已有半年之久,她丈夫四出寻医,却始终不见起色,最后不得不向阎婆仔求助。
阎婆仔是与道士的职业功能相当的人。
桃花居然认同丈夫的做法,她被人引入封建迷信的路途。
文中写到:
“她分发一块黑布给女人。
女人接了,自动把眼睛蒙起,两端布头在脑后系个结。
”[5]以及后来阎婆仔的问与答,可见她也深陷封建迷信的泥淖。
难以置信的是梁在禾附身在桃花的身上,向桃花“索命”与诉讼心中的仇恨,更加滑稽的是丈夫见桃花不醒,答应自己的一子一女改承梁姓,还包括以后的孩子依然如此。
神奇的事再次发生,“日头刚西沉,妇人便豁然而醒。
”“妇人的病无药而愈。
”[6]桃花是一个深陷封建迷信的无辜女子,她的无辜是被人带入封建迷信的围城,承受封建迷信的折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她同样深陷封建迷信的事实。
(二)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女性
面对残酷的生存处境,众多的女性已经甘愿忍受封建思想的迫害,但仍有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女性存在。
《最后的夜戏》中的金喜仔是同生存与命运抗争的典型代表。
这篇小说主要通过台湾歌仔戏旦角金喜仔一次演出的台前台后交织的情景,结合对过去的回忆,来反映台湾艺人艰难的生活与多舛的命运。
她来芦州,三次演出的境遇每况愈下,在无情的历史明镜中,我们看到在坎坷的人生路上,岁月早已夺去她的年华和外貌,剩下衰弱的躯体、吸毒的恶习和待哺的儿子——小宝。
面对生活给她的苦难和毒害,金喜仔没有默默无闻地忍受,她要同命运抗争,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
她的亲生儿子阿宝,经人算命说是天生的“过继命”,要是不给别人就养不大。
可是她居然不信命,非要跟命运抗衡,哪怕是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
“她张开嘴,榨尽全身的力气,从喉咙底下硬往外迫出一句唱词‘啊——’”[7]深刻地刻画出为养家糊口,她拼命地赚钱,希冀以此来改善家境的坚强形象。
但是面对歌仔戏逐渐衰落的残酷现状,“在这个歌仔戏没落的时候,戏旦已经今远非昔比了。
十年前,旦角由她挑,唱一台戏的收入可以吃喝一个月。
现在老板只要不满意,可以随时解雇她。
她早已看出这个环锁:
生存、吸毒、生存…………它紧紧锁住她,再也逃不掉。
她爱唱戏,除了唱戏,她想不出还会做什么事。
”[8],她不得不面对生活的困境,接受残酷的现实,这就是一个女人的无奈。
同时,歌仔戏老板的压迫与剥削无疑是雪上加霜。
戏老板多次警告她不许带小孩到戏院,生怕影响自己的生意,但她仍然坚持边在戏院工作,边在戏院养孩子,把儿子带在身边。
期望自己赚钱和养育儿子两不误,终究徒劳。
这些都体现金喜仔敢于同命运作苦苦挣扎的精神,这种精神令每个人折服,值得赞扬与推崇。
尽管她的最终结局恐怕是骨肉分离,不得不把亲生儿子送人。
不然,她的生存也会面临危机,但是那份抗争的勇气与执着令人敬佩。
深受束缚与压迫的女性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
女性要想摆脱这份束缚与压迫,就必须同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进行抗争。
在《灰眼黑猫》中,作者通过好友阿蒂的独特视角,告诉“我”女性朋友文姐的噩耗,即文姐死了。
再倒叙文姐在青少年时如何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文姐的手非常巧,制作的风筝在孩子们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小伙伴们很乐意跟她一起玩,那样会得到很多的乐趣。
正因为孤儿大生无微不至地关心她,他俩的志趣又相投,她便与孤儿大生相好,追求着自己的美好理想。
文姐追求婚姻的自由,但受到父亲的阻扰,她的父亲认为女孩子是赔钱货,表露出浓重的封建思想,再加上他贪杯好酒,为追求金钱,把她嫁给乡村首富大年,他是一个吃喝嫖赌无一不精的男人,可见文姐深受封建的剥削与压迫。
文姐对于幸福自由的生活敢于追求,对于不合理的命运敢于奋起反抗,我们不难发现她的反抗精神。
但只能是鸡蛋碰石头,在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下,文姐不得不屈服。
她忍受婆家的虐待和折磨,自己的孩子也被他们隐藏起来,最后,她气愤成疯,死于非命。
对于文姐的死,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
“文姐他究竟是黑猫还是旧制度的牺牲品呢?
我不能回答。
”[9]又说“让腐朽的制度——带着它所造成的罪恶——在地的一角沉沦下去吧!
”[10]表现出作者对台湾封建制度的抨击与揭露。
总之,在陈若曦的作品中,女性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她从底层女性的悲惨的日常生活出发,关注她们的生与死,冷暖与爱情等这些基本的人生问题。
她用平实之作揭示底层女性艰难的生存状态,这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台湾女性文学作品中是不易看到的。
二、对敢于挑战男权观念的华人女性书写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打上男权文化的烙印。
“所谓男权文化,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的说法,就是男性主义中心社会,指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以男性为中心的。
”[11]文化体系赋予男性绝对的权威。
自从人类进入父权社会,母权社会的辉煌一去不复返,犹如星辰陨落,女性的地位江河日下,最终跌入社会谷底,几乎永无翻身的可能。
女性遭受社会的歧视与压迫,沦为家庭和男性的附庸,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
在男权社会里,男性被赋予绝对的主宰权。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已经改变自己的观念,依附于男性和家庭的家庭妇女不再是人们心中理想的女性角色。
陈若曦在后期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一批大胆挑战男权观念,大胆颠覆传统爱情婚姻模式的华人女性形象。
《贵州女人》中的原小学教师水月,她是从贵州偏僻的山区嫁到美国唐人街来的,并且成为餐馆老板。
她毫不隐瞒嫁给比自己年长40岁的男人翁德和的目标是为了个人的出路。
在穷乡僻壤,她看不到前途,恋爱遭到过挫折,家里又欠债,无奈中才把希望寄托在这场婚姻上。
由于翁德和不要她生孩子,在认识阿炳之前,喜爱孩子的水月不得不听从翁德和的意见。
但在认识阿炳以后,水月展示对生育权的自主,她怀上阿炳的孩子。
当水月得知阿炳要与别人结婚时,她身上的反叛精神彻底爆发出来。
她非常得恼恨,不满男性把自己看成是男性交易的“物”,却忽视她同样作为“人”应有的七情六欲,情感自由的追求。
水月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力,不禁向翁德和、阿炳质问:
“我成了什么,啊?
”这往往是传统女性所不敢的行为,她们只能听从男性社会的安排,泯灭个人的意志。
水月的出走透视出她要求摆脱男权压制,自由支配自身一切活动的自主意识。
而老人翁德和处于害怕水月离开他的恐惧当中,显然,水月掌握两人关系的主动权。
华人女性挑战男权权威,她们成为拥有自由婚姻选择权的女人。
在作者的作品中,她对水月的行为采取支持的态度,说明陈若曦认同这类女人。
因为她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力。
女人也是人,理应有这样的权力,其他人没有权力与职责过问。
《我们上雷诺去》中那个“身无分文又独自跑到美国来”的戚芳远,用婚姻做赌注,达到长期留在美国的目的。
她和一位75岁的老头结婚。
她大胆承认:
“如果有更好更快的办法,我们今天也不会到雷诺来,你有一天会明白,我不是自私的女人”,女友示意她:
“也许还能活上十年也说不定——十年啊!
”她居然说:
“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我都熬过去了。
再熬十年……那也是一眨眼的事。
”[3]这句话隐晦表明:
老头一去世,她就把丈夫与儿子接到美国来生活。
这里没有传统道德的约束力,更没有父母之命的权威,有的是心甘情愿的交易。
根本不存在悲剧,只是一幕戏剧罢了。
陈若曦小说中的华人女性拥有对婚姻自主的选择权,如《演戏》中的女主公丽仪,五年前就与丈夫离婚,为了不伤害女儿的幼小心灵,而居住在一起,但是分房而睡,像朋友一般。
毋庸置疑她是一位自由的女性,彼此之间拥有离婚和再嫁的权利。
小说通过和气、松弛的氛围来表现这对貌合心离的离异夫妻之间自由的生活方式。
相对丽仪而言,这种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是她获取人心的自由,无需演戏了。
像陈若曦说的一样,当今婚姻不一定是终身大事,是一种生活方式。
更多的人们领悟到独立和自我满足才会使自己处于不失败的位置。
这些都是挑战了男权观念的华人女性,她们解开了封建传统的锁链,从中寻找女性的真正自我。
3、对女性自我救赎道路的探索
陈若曦作为一位感情真挚、理性冷静的女作家,认识到女性作为一个弱势性别群体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处境追究构成性别歧视背后的父权制文化结构和性别角色的规定。
在女性历史和现实中表现出来的悲惨命运,受男权文化压迫的境遇,并不是她们作为生命主体本身的错,在于她们处于男权文化底蕴深厚的不平等社会。
陈若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揭露,期盼女性挣脱被奴役的处境,孜孜不倦探索女性自我救赎的道路。
在后期的小说创作中,陈若曦笔下有的女性逐渐走向独立,有的女性皈依佛教,获得心灵的平静,以一己之力来救助别人。
陈若曦确实在2001年出版《慧心莲》给那些历经坎坷、婚姻遭遇不幸的女人指明了新的方向,那就是重新追求人生,寻觅生命的价值所在。
《慧心莲》叙写一家三代女人坎坷命运的故事。
主人公是几位女性,母亲杜阿春是一位传统的女性,年轻时不惜无名分为他人生下两个女儿,岂料生父意外去世,得不到一点费用,女儿身上永远被背负着“父不详”的标签。
后来她嫁给一个外来的军人,终因性格不合而分开。
她在别人的感化下成为与人为善的信徒,将佛堂作为自己的最后的港湾。
留学的两个女儿也同样遭遇婚姻的不幸。
长女是美慧,她高中毕业后嫁给了王金土,本应拥有个幸福的家庭,也拥有那样幸福的资本。
她有一双儿女,却无缘无故遭到丈夫的折磨,后来发展到自杀,最终一心向佛,削发为尼,法号“承依”。
次女美心,人如其名,美丽动人成为中国台湾赫赫有名的电影明星,追求她的人可想而之有很多。
但是她偏偏喜欢了有妇之夫,一个姓吴的男人,还生下一个儿子阿弟。
世间是变幻莫测的,她的儿子竟在一场车祸中死去,办完葬礼的她一心向佛,进入佛堂。
时代终归是不同了,现在的中国台湾,皈依佛门已经不是苦度残生,而成为一种人生选择,更可以说是一种掌管或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尚”。
像美惠的女儿美莲所说的那样,现在的年轻人想出家的有很多。
她个人认为是很好的人生规划和选择。
所以她大学毕业后承袭母亲的志愿,自愿成为法号“勤礼”的佛门弟子,被派到中国大陆浙江天台寺取经修学,她的男友也选择成为天主教教士。
从杜家三代女人身上,已经没有冲动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泰然自若、安闲自在的生活态度,最难能可贵的是她们身上有一种不易磨灭的东西——情感寄托的信仰。
所以,承依最终成为海光寺的主持,她的母亲引以为荣。
令人震惊的是杜家三代信女,一起出现在中国台湾“九一二”地震的救助现场,加入救援的队伍。
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灵魂自由,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寄托,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心灵洗礼。
生活中因失恋自杀的女性,忽视自己可以帮助受难人民的社会价值。
她们轻易放弃生命,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
其实,她们可以奉献社会,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
宗教可以洗涤你的灵魂,使你淡忘世间的痛苦,获得安之如素的生活态度,摆脱自身的情感纠葛,重新找到心灵的乐土,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
陈若曦后期的小说创作给人以极有价值的启发。
她认为有的女性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有的女性则皈依佛教,获得心灵的平静,以一己之力来救助别人。
四、女性意识的形成原因
在漫长的男权社会进程中,女性基本丧失性别的主体地位,她们的自我意识被掩埋,她们的权力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的意识才逐渐觉醒,一批女性逐步登上文学的舞台。
这个时期的文坛,女性的创作明显增加。
陈若曦小说弥漫着浓重的女性意识色彩,这种女性意识的形成,固然与作家个人的心理素质、创作思想密不可分,但是,作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作家的个人背景,也往往影响着作家的女性意识的发展。
(一)历史时代背景
当代台湾女性文学源于四十年代末大陆迁台的女作家人生流寓和文学聚合。
众多的大陆女作家的到来,填补了台湾文学的一页空白。
林海音、郭良惠、谢冰莹、苏雪莹等台湾女作家群体的形成,她们积极筹建妇女文学社团,创办《妇女文学》杂志,这些标志着女性文学的兴起。
当时的台湾女性文学仍然以“五四”以来中国传统女性文学为基础,倡导写实手法。
她们有选择地传承这些传统,打破了当时男作家的主宰文坛的局面。
她们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创作的求新意识和反封建的特点,并且开创台湾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先河。
陈若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成长,潜移默化地关注着女性的艰苦生活状态和不幸的婚姻。
她从女性的写作视角出发,以台湾底层社会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作为创作的起点,向世人展现女性生存的状态和自我意识。
(二)个人背景
陈若曦女性意识的形成,不仅依赖于她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而且与作家自身成长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陈若曦从小生长在台湾乡下,她在台湾生活了整整二十六年,度过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台湾的生活经历对她产生深远的影响。
陈若曦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木匠,她的邻居是一位失业的工人,她曾说:
“我从小对工人农民就有一种亲切感,好像自己是属于他们的,这对我不管写作、为人,还有处事都要影响,并且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12]正因为她觉得自己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的苦难、命运与挣扎都牵动她的神经,造成陈若曦早期的小说以台湾底层社会女性的生活和悲惨的命运作为创作主题。
她所创作的语言和文字都带有泥土味,与我国的写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她说:
“我一直走的是写实主义路线,在以前,我基本是乡土的,现在则是反映社会现实,也就是写实路线,我所用的都是传统技巧。
”[13]台湾是陈若曦女性文学的创作起点,她发表的早期小说透露出台湾底层女性的悲苦生活和悲惨命运。
陈若曦与丈夫回归大陆,后来她离开大陆,她和亿万的大陆同胞一起经历一次巨大动乱的磨难和洗礼。
她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自己年轻时也曾回归过,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思想还是很纯真,很浪漫的。
以后虽然坎坷,倒也没有后悔,只是无限的感伤而已。
这可能像少女的初恋,永远有股淡淡的甜意。
”[14]一九七三年陈若曦到香港,次年移居过加拿大,又旅居过美国。
陈若曦对华人女性的自我意识与人生际遇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她以强烈的成熟的女性意识进行着文学创作。
陈若曦的小说反映女性意识的变化,一直探索女性救赎的道路。
她给处在黑暗的深渊的人指明的道路,犹如夜空的点点星光,照亮她们前进的道路。
她指明的道路,不仅适合女性,而且适合男性,更适合全人类。
结语
我认为女性得到真正的精神自由,除了女性地位提升,还要注意她们的主体意识是否完整,更为重要的是女性本体的自由。
立足于这样的意义,我们需要通过“铿锵玫瑰”的文学叙事揭露现代女性的变化与挣扎,在女性的“边缘”处探讨书写所丢失的热情与苦痛,快乐与悲伤。
蕴藏超过女性本身的意味。
追溯陈若曦小说的女性意识的变化,我们不难发觉自始至终贯穿着女性特定存在的理性思考。
因此,在作者的笔下,新时代的女性之路,想必是很多的,选择的指挥棒就在她们自己的手中。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流变:
从新个人主义到新整体主义[J].社会科学战线,1998(5):
103.
[2]陈若曦.陈若曦自选集·后记[M].台湾:
台北联经出版社,1976,7:
102.
[3][4]陈若曦.陈若曦中短篇小说[M].福建:
海峡出版社,1985,1:
57.63.
[5][6]陈若曦.陈若曦自选集[M].台湾:
联经出版社,1976,5:
98.104.
[7][8]陈若曦.陈若曦小说选[M].杭州:
广播出版社,1983,12:
91.94.
[9][10]陈若曦.陈若曦作品[M].福建:
福建出版社,1996,11:
112.114.
[11]转引王艳玲.旧文明背景下一个性别的整体坠落[J].现代文学名作欣赏,2006(6):
81.
[12]陈若曦.陈若曦自选集·序[M].台湾:
台北联经出版社,1976,5;2.
[13]陈若曦.忆大陆[J].明报周刊,1984(5):
12.
[14]陈若曦.坚持·无悔[M].台湾:
九歌出版社,2011,10:
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