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的觉悟与沉迷.docx
《庐隐的觉悟与沉迷.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庐隐的觉悟与沉迷.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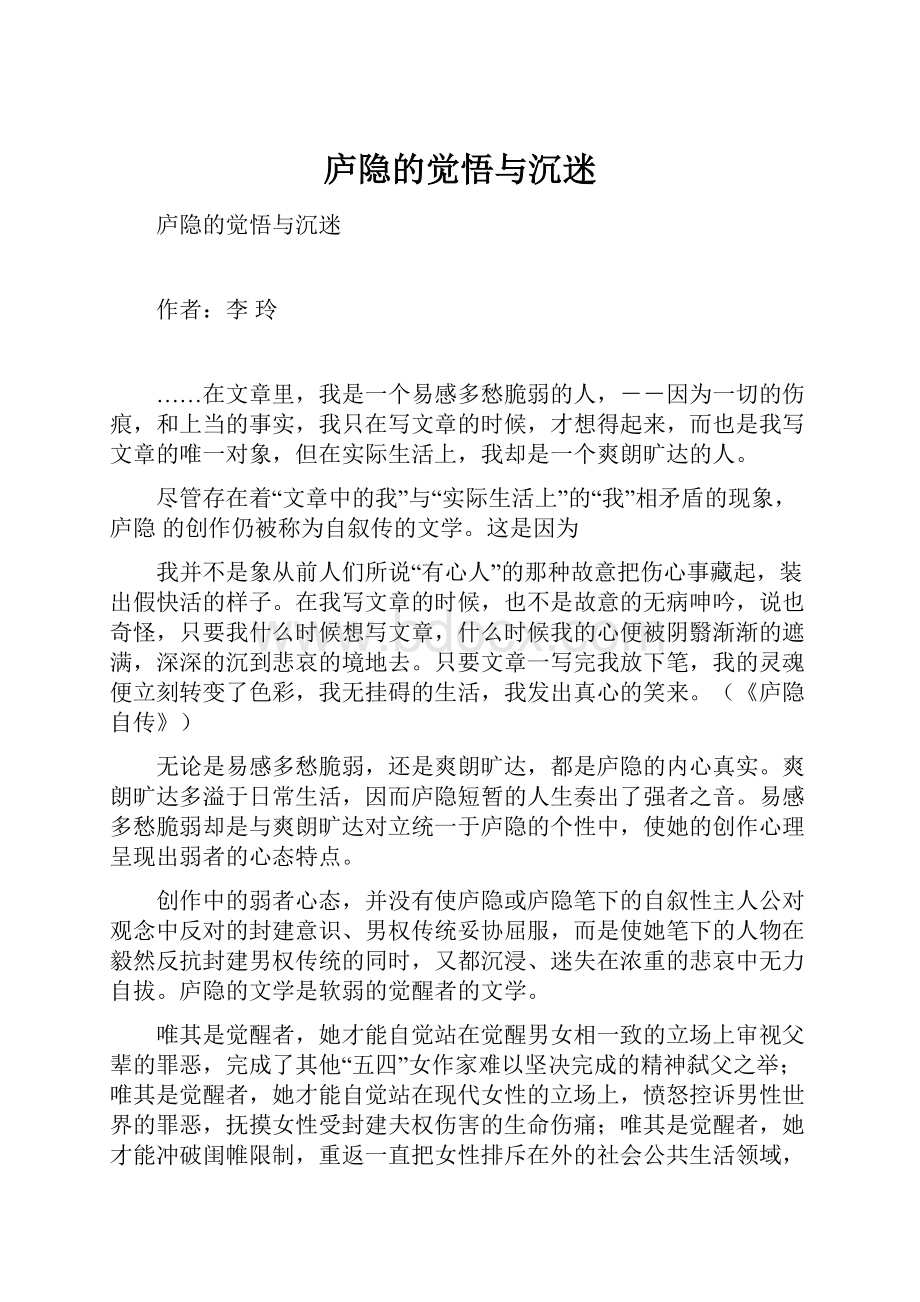
庐隐的觉悟与沉迷
庐隐的觉悟与沉迷
作者:
李玲
……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的唯一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
尽管存在着“文章中的我”与“实际生活上”的“我”相矛盾的现象,庐隐的创作仍被称为自叙传的文学。
这是因为
我并不是象从前人们所说“有心人”的那种故意把伤心事藏起,装出假快活的样子。
在我写文章的时候,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想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的遮满,深深的沉到悲哀的境地去。
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变了色彩,我无挂碍的生活,我发出真心的笑来。
(《庐隐自传》)
无论是易感多愁脆弱,还是爽朗旷达,都是庐隐的内心真实。
爽朗旷达多溢于日常生活,因而庐隐短暂的人生奏出了强者之音。
易感多愁脆弱却是与爽朗旷达对立统一于庐隐的个性中,使她的创作心理呈现出弱者的心态特点。
创作中的弱者心态,并没有使庐隐或庐隐笔下的自叙性主人公对观念中反对的封建意识、男权传统妥协屈服,而是使她笔下的人物在毅然反抗封建男权传统的同时,又都沉浸、迷失在浓重的悲哀中无力自拔。
庐隐的文学是软弱的觉醒者的文学。
唯其是觉醒者,她才能自觉站在觉醒男女相一致的立场上审视父辈的罪恶,完成了其他“五四”女作家难以坚决完成的精神弑父之举;唯其是觉醒者,她才能自觉站在现代女性的立场上,愤怒控诉男性世界的罪恶,抚摸女性受封建夫权伤害的生命伤痛;唯其是觉醒者,她才能冲破闺帷限制,重返一直把女性排斥在外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关注社会众生,把深厚的同情奉献给下层受苦人。
也正因为她还只是一个软弱的觉醒者,她诉说现代女性人生无奈的文字远远超过其批判性文字。
第一代现代女性面对强大男权世界的生命无力感、对婚姻生活的迷惘、对人生哲理的困惑、对青春女性同性情谊的留恋,均是庐隐笔下“五四”女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也正出于梦魇初醒时的软弱无力,她有时甚至难以理性地去内省自己的心灵世界,常常不能用审美的距离感来把握生活素材,一任其多数创作失去艺术的节制,流为典型的宣泄性文学。
一、女性的三重觉醒
作为现代最先觉醒的第一代女作家之一,在反叛封建男权这一点上,庐隐比起其他“五四”姊妹们,具有更强的自觉意识。
这既表现在她自觉的弑父意识上,也表现在她对男性夫权意识的审视、批判上,同时还表现在她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主动介入上。
(一)精神“弑父”:
“五四”是一个精神弑父的时代。
鉴于封建文化家国同构的特点,“五四”先驱反对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呼唤“立人”,是把家庭内的反对男性家长专制与社会层面的反对主奴等级专制结合起来的。
精神弑父与精神弑主是“五四”青年争取做人权利斗争的两面。
父性权威,作为压制青春生命的力量,在“五四”启蒙文化中一直处于被审问、被批判的位置。
“五四”先驱鲁迅、陈独秀、吴虞、周作人等均有抨击封建父权的激烈言论。
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便以“幼者本位”的进化论哲学否定“父为子纲”的封建伦理。
但由于天然的亲情联系,和初步觉醒者的稚嫩心态,父母在实际的情感体验中同时又是“五四”青年无法割舍的心灵依靠。
两类矛盾对立的情感互相牵扯,“五四”女作家暂时还无力从中整合出完整统一而又复杂多层的父亲形象,一般总是对青年与父亲的关系保持沉默,从而回避自己反叛父权与渴望父爱的心理矛盾。
只有在庐隐、冰心、石评梅、凌叔华等的小部分创作中,父亲形象才是清晰的。
冰心、石评梅抒写了超越封建纲常的父女亲情,塑造了慈爱、开明的父亲形象,代表现代女性理直气壮地舒展了渴望父爱之心。
冰心在问题小说《斯人独憔悴》、《是谁断送了你》中,揭露了父辈的落后、专制,但叙述者、隐含作者认同子辈仰视父辈的眼光,对“父亲”的否定还是怨多于怒。
凌叔华在《一件喜事》、《八月节》中揭露了“父亲”在不对等的性爱关系中对妻妾们的伤害,也写出了“父亲”对儿女的宽厚、和气以及其中所含的冷漠意味,从子辈和女性的角度表达了对“父亲”这一男性的复杂情感。
第一位真正严厉地审判“父亲”、把“父亲”钉在道德的耻辱架上进行无情诅咒的女作家是庐隐。
小说《父亲》中,庐隐塑造了一个荒淫无耻的父亲形象。
“……我父亲十六七岁的时候,就不成器,专喜欢作不正当的事情,什么嫖呵!
赌呵!
”他气死了“我”的母亲,娶了暗娼,又隐瞒婚史,花言巧语,骗娶了富有的良家独女,使这沦为偏室的年轻女子痛苦不堪。
平时,他虚荣下流,“喜欢说大话”,善于敲诈行骗,还吸食鸦片。
这个父亲,集人性之恶于一身,是个一无是处的反面角色。
庐隐从子辈的视角审视了父亲的道德堕落,在肯定子辈对庶母的爱恋中使父辈与子辈的冲突急剧尖锐化。
子辈“我”爱恋悲愁美丽的庶母,“坐在她的旁边,看她那不胜清怨的面容,又听她悲切凄凉的声音,我简直醉了,醉于神秘的恋爱,醉于妙婉的歌声。
”但年轻的庶母终因受父亲的伤害太深抑郁而死。
这里,父子矛盾既是由于新旧道德立场的对峙,也是由于父亲对子辈恋爱对象的伤害、由于父亲对子辈性爱利益的侵夺。
庐隐站在子辈的立场严厉审判了父辈的罪恶,是非判断上一反传统把父妾定为父辈的性财产、子辈不可产生非分之想的父权纲常,而以父子平等的普遍道德尺度衡量父辈的婚姻、以真挚的爱为这一庶母与名义上的子辈之间的恋爱确立合法性,完成了其他“五四”儿女难以完成的精神弑父过程。
庐隐由此有别于其他以父母为精神庇护所的“五四”女儿,比她们多一份决绝,也多一份孤独;多一份成熟,也多一份沧桑。
庐隐作为女作家,把同辈女性塑造成小说中受父辈欺骗的庶母,把同辈男性塑造成同情、爱恋女性的有情人,并且完全认同了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男性青年的情感取向,说明庐隐在审父的时候是以男女立场一致的现代青年同盟作为精神支柱的。
父亲、庶母和“我”作为小说人物,分别代表旧道德、美而受害的弱者以及多情无奈的现代青年,性格均单一静止,具有明显的概念化倾向,说明庐隐的弑父意识,可能主要来源于“五四”反对父权文化的社会思潮,而不是从个人生活经历中自然萌发的精神现象。
但无论如何,对父辈的审判,大胆冲破了封建伦理观念,因而具有了彻底反叛封建礼教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
(二)控诉夫权:
控诉封建夫权对女性的伤害是庐隐创作的重要主题。
在这类涉及两性关系的创作中,庐隐从女性视点勾勒了一系列欺侮女性的男性形象。
他们或通过骗婚骗情,谋取钱财(《父亲》、《兰田的忏悔录》);或“看待妻子,仿佛是一副行头,阔了就要换行头,……”(《一幕》、《时代的牺牲者》);或以单方面的封建贞操观念要求女性为自己守节(《沦落》);或以自由恋爱为手段欺骗女性,始乱终弃,使女性陷入绝境(《兰田的忏悔录》、《歧路》)。
在“五四”这一精神“弑父”的时代里,青年普遍幻想从父母的手中争得自由恋爱的权利便能走进幸福。
胡适的《终身大事》便是这一集体幻想的典型表现。
庐隐则从女性经验出发,戳破了男女青年同盟的美丽梦想,发现了即便是自由恋爱这一现代爱情规则也会被利用、蜕变为男子欺骗、诱惑女性的幌子,而失去了它本来包含的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涵。
《兰田的忏悔录》中,兰田在家被逼嫁给有三房如夫人的纨绔子弟,父亲、继母、未婚夫凭借封建男权的具体形式--父权、夫权,一起迫害她;兰田逃到社会上,又有男子何仁、王义以自由恋爱为名,欺骗、玩弄她。
何仁既与兰田恋爱、订婚,诈其钱财;又同时与另一美丽女子恋爱、结婚,置兰田于绝境。
叙述者借人物芝姐之口说“人类是特别的残酷,恐怕兰田真是没有病好的希望呢!
……天下不止一个兰田……我辈都不能不存戒心。
”庐隐通过兰田的悲剧为男权压迫下的女性生存状况感到惊惧。
她痛心地揭示出,女性要摆脱男权桎梏,仅仅有女子一方思想意识的觉醒是不够的,而需要男女两性在性爱意识上均实现现代化才可能,需要整个社会意识的进步、发展才行。
“我热烈的感情,能象温柔的绸带缠着你,使你如醉般的睡在我的臂上,但你若背过脸去,和另一个少年送你的眼波,我也能使这温柔的绸带,变成猛鸷的毒蛇,将你如困羊般送了命。
……只是我活的时候,我绝不能使曾经和我接近的人,更和别人演一样的剧。
”庐隐在《沦落》中,触目惊心地展示了男性的性占有心理对女性生命的压制。
海军部军官赵海能尽管自有妻室,却不许对自己以身报恩的女学生松文与别人恋爱。
女性在赵海能这类男性的视野中,不过是自己消费过之后哪怕把她毁灭了也不能被别的男人消费的性所有物,根本不是具有追求幸福资格的独立的人。
原本爱恋松文的少年,得知松文受伤害的生存真相后,“……他渐渐生了鄙薄松文的念头,他想自己纯洁的爱情,只能给那青春而美丽的贞女。
”庐隐愤怒地揭示出了单方面要求女性贞节的旧道德依旧是这一新旧过渡时代男子继续压制女性的工具,女性仍不过是男性为主体社会中的性客体。
她以同类敏感之心深切哀怜落在男性性霸权之中无力挣扎的弱女子。
庐隐笔下欺侮女性的男子,既有旧式的家长、少爷,还有新式的大学生、留学生。
他们在个人品性上,均具有虚伪、欺诈、自私、无耻的特点,背后都倚仗着强大的男权社会意识。
这表明庐隐对在性爱意识上仍然固守封建男权的男性世界有着强烈的失望、厌憎和无奈。
庐隐是“五四”时代对落后男性世界道德鞭挞最为激烈的女作家之一,代表了丁玲之前“五四”女作家女性立场的最高度。
庐隐对男性世界的批判是与对整个社会的男权中心意识的批判相结合的。
《沦落》中,松文的困境不仅来自于伤害她的两个男子赵海能和那原本爱她的少年,也来自周围的众女同学。
同学中除了彬彩一人同情她之外,别人给予她的只是“有毒质的针”的议论,只是“无情的嘲笑”。
这种带着窥隐心理的刻薄舆论甚至连累到同情她的朋友“都要被凌辱”。
以致于“彬彩本想搬到医院去看护她。
因怕同学们的冷嘲热骂,把她的心吓冷了。
虽然心里怜她,面子上也不愿亲近她。
”而兰田在愁病之中,“实际上除了一个抱有上帝爱同胞心的芝姐外,似乎无人不是在窃窃的私议着我的污点,有几个简直当面给我以难堪!
”男权社会中的公共舆论不仅不谴责伤害女性的无行男子,反而以封建的女性贞操观鄙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
即使是同为女性者,也难以在心灵中滋生出受伤害者之间的相互同情、怜惜,而是认同占统治地位的男权意识、以奴化精神来唾弃女性同胞。
这样,庐隐对男权世界的批判,就由对男性世界无行行为的控诉而拓展到了整个社会男权封建意识的清算,具有更为深厚的思想覆盖面和穿透力了。
庐隐始终站在女性立场上来审视男性世界的丑恶,自觉把深切的同情给予处在弱者位置上的女性。
其笔下受侮弄的女性尽管几乎一律都难以在行动上反抗男性世界的强权,却也不复是在男权铁屋子中沉睡的女奴。
她们的软弱是觉醒者的软弱。
她们在行动的无力中,并没有放弃思想、道德方面对男权世界的控诉、审问,保持了富有主体意识的人的思想锋芒。
庐隐笔下受伤害的女性,一般总能以人的价值尺度衡量自己在恋爱、婚姻中的处境,所以,一旦受到男子朝三暮四行为的侮弄,悲哀、愤恨之余,已不会再把怨怼洒向同为男权牺牲品的其他女子。
她以人的眼光审视其他女子与自己恋人、丈夫的关系,往往能更充分体验女性在封建男权统治下的不幸,而同情受伤害的女性同胞,与之结成受害者同盟,在情感上相互慰藉,从道义上批判无行男子的恶劣行为。
庐隐的《兰田的怅悔录》、《时代的牺牲者》便表现了同受男权伤害的女性之间的情谊。
新婚的何仁夫人知道兰田与何仁的关系、知道兰田受欺骗的真相后,赶来看望兰田,哀痛地对她说:
“姐姐,我们同作了牺牲品了呵!
”把仇恨共同指向侮弄女子的男性,而不是去忌恨同受欺骗的女同胞。
《时代的牺牲者》中,手工教员李秀贞的丈夫张道怀留学归来,设计谋抛妻弃子,欲另娶有钱有貌的年轻女子林雅瑜。
林雅瑜得知真相后,亦与母亲一同来看望李秀贞,痛心地对她说:
“唉!
李先生,我们是一样的不幸呵!
”李秀贞“听了林小姐的话,仿佛已找到旅行沙漠的伴侣了”。
她们也同样结成弱者的精神同盟,共同谴责“没有品性的男人”。
这种弱者同盟相对于猖獗的男权势力来说,还显得十分无力。
受伤害的女性只能在精神上彼此声援、情感上相互慰藉,并不能在行动上惩罚恶人,甚至也无力在社会上造成正面的舆论力量,倒是自身反而要受到不公正社会的唾弃。
女性之间的相互同情还不足以形成改变女性处境的现实力量。
兰田、李秀贞以及何仁夫人等受伤害之后终究还是只能沉沦于抑郁痛苦中,甚至绝望而死。
尽管面对现实,女性之间的情谊十分软弱无力,但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思想内涵却是以往女性文学所不可能达到的。
妻妾相安、以不妒之封建道德共同服侍一个男子是女性的彻底奴化;妻对丈夫其他配偶的妒嫉是女性作为人的自我意识未曾泯灭的自然反映,妒嫉者凭直觉只是知道自己受到了受害,却难以真正明白伤害自己的力量是什么,反可能纵容元凶、伤害无辜;而受害女性之间相互同情则是女性人的意识完全觉醒之后的自觉行为,其中包含着对女性受男权奴役处境的明晰观照、包含着对女性作为人的尊严的共同维护。
受害女性的软弱无力状态并不意味着向男权妥协,而是包含着对社会落后意识的谴责,包含着对把女性作为人的新时代的急切呼唤。
纯粹代女性控诉的立场,也使庐隐在同情受害女性的同时较少对女性世界展开反思、自省。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定了庐隐的思想深度。
(三)介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庐隐对女性的同情是对弱者的同情。
这既是同为女性的心灵共鸣,也与庐隐偏向于弱者的人道主义思想有关。
庐隐把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推及到青春女性自我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中,为“五四”女性文学赢得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也使其创作在主观抒情的主导倾向之外,还兼具了写实这另一种风采,充分体现了她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文学追求。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女性由与男子平等的人沦为附属于男性的女奴,就是从女性被排挤出社会生活领域、圈定在家庭的围墙内开始的。
是否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实际上是决定女性命运、女性素质的一个妇女解放的基本问题。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一种审美表现形态,不仅难以超越生活实际去正面想象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情形,也难以超越社会对女性角色的限定去正面表现女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愿望。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的妇女生活和女性内心世界绝大多数都在家庭伦理关系、男女两性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琐事中展开。
近代,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社会意识的发展,革命女杰秋瑾在诗词创作中抒发了“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豪情,表现了女性介入社会生活的愿望和胆识。
但这种体现妇女自觉精神的女性创作,在凄风苦雨的封建末世仍是荒野中寂寞的呼喊,得不到普遍的回应。
只有到“五四”时代,妇女解放成为先进思想界的广泛共识后,女性文学才第一次大量表现了妇女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思考,多方位展示了现代女性冲破家庭藩篱后的精神风采,使妇女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母题,与女性对自我的言说并举,不可偏废。
庐隐与冰心便是“五四”女作家群中思考社会问题最为深广的两位。
其广阔的社会视野表明先进的现代女性在“五四”思潮震荡下,既能抚摸自身伤痛,也能审美地把握女性个人生活空间之外的广阔的社会人生。
庐隐这类关怀现实人生的创作,均为“问题小说”。
其关注面非常广,且具有明确的现实批判立场和现代悲剧意识。
不同于冰心对爱与美的歌唱,庐隐主要侧重于揭示社会的丑恶,多从受伤害者的角度控诉病态社会对生命的残害。
她同情因为贫寒而失去爱情的知识分子(《一个著作者》),悲悯受阶级压迫而致死的下层妇女(《一封信》),怜恤被卖为仆的孤儿(《西窗风雨》),思考机械文明对人的灵魂的压抑问题(《灵魂可以卖吗》),痛斥执政府枪杀请愿学生(《两个小学生》),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月下的回忆》、《扶桑印影》、《最后的光荣》)。
庐隐的人道主义情怀闪耀着觉醒者的现代思想光芒。
其批判锋芒时时能超越对制造生命悲剧的单个人的谴责,而指向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
《一个著作者》中,才华横溢的青年著作者邵浮尘与美丽女子沁芬相恋,但沁芬终被父母强行嫁给富有的罗频,沁芬和邵浮尘终痛苦而死。
庐隐并没有简单地把罗频丑化为奸邪小人,而是把他处理为同样是这一桩缺少相互共鸣之爱的婚姻的受害者。
这样,“问题小说”的锋芒就指向了把“生命和爱情”“强买去”的市侩主义的婚姻准则,指向了包办婚姻,具有更为深广的批判意义,耐人寻思。
《灵魂可以卖吗》,则借女工荷姑的自述,质问现代工业文明在买去了工人的时间和劳力的同时,也使人陷入了“不想什么”、“不见得有什么愉快”的精神麻木状态。
这种思考,发现了当时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的现代工业之压抑人性的弊病,是极为敏锐的。
与同时期冰心的“问题小说”比,庐隐的“问题小说”,并没有努力去捧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着重于提出问题。
庐隐往往与人物一起对社会现象感到迷惘、无奈,从而引发读者自己去思考、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这是由于庐隐和冰心二人的文学观之不同。
冰心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侧重于引导人生,庐隐则侧重于表现人生。
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毅然反叛礼教,满怀愤恨控诉封建父权、夫权,把深切的同情奉献给女性以及其他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是庐隐觉悟的一面。
与女性的现代觉悟同时并存于庐隐心底的,是初步觉醒者直面人生时的无奈和怯惧。
首先,在现代爱情与封建礼教的对峙中,庐隐既能站在青年的立场,肯定爱情;同时又受制于礼教的强大压力而感到四面楚歌,陷入精神憔悴中无力自持。
中篇小说《海滨故人》中,自叙传主人公露沙与家中已有包办婚姻的梓青相恋,她不忍置梓青旧式婚姻的妻子于无地生存之境,“身为女子,已经不幸!
若再被人离弃,还有生路吗?
况且因为我的缘故,我更何心?
”这是新女性对生命已经没有放飞能力的旧式女性的悲悯情怀,是过渡时代个性主义对人道主义所作的无可奈何的退却。
但显然,露沙、梓青的爱情痛苦远不止于这一不得已的对旧女性的居高临下的关怀。
露沙在给爱人、友人的信中分别写到:
沙怯懦胜人,何况刺激频仍,脆弱之心房,有不堪更受惊震之忧矣!
沙与梓青非不能铲除礼教之束缚,树神圣情爱之旗帜,特人类残苛已极,其毒焰足逼人至死!
是可惧耳!
这种忧惧显然根源于爱情的合法性与社会舆论之间的矛盾,根源于现代爱情与传统礼教之间的不兼容性。
露沙的怯懦并非由于现代爱情信念的匮乏,而只是因为新旧道德两方力量悬殊而产生的勇气不足。
她深知自己爱情的神圣、合法,却依然难以睥睨明里暗里的黑暗,而陷入憔悴痛苦中。
这既体现了先觉者处境的险恶,这种险恶鲁迅的《伤逝》已有充分的描述;同时也表明庐隐作为第一代觉醒的现代女性在精神上还不够成熟,不具备鲁迅等启蒙思想家面对黑暗时的坚定顽强。
心态上的忧惧柔弱奠定了庐隐创作愁苦悲哀的情感基调。
也正是出于初步觉醒者的弱质心态,庐隐对青年向礼教妥协的软弱行为往往同情、理解有余,批判、否定不足。
在庐隐的创作中,女性青年对礼教的妥协至少有两种形式:
一是屈服于父权专制,放弃自由恋爱;二是屈服于男权文化的女性评价标准,否定自我生命。
《海滨故人》中,云青钟情于蔚然,父亲不赞成,云青便无一句违拗父意的话,
云青又何尝不痛苦?
但她宁愿眼泪向里流,也绝不肯和父母说一句硬话。
至于她的父母又不曾十分了解她,以为她既不提起,自然并不是非蔚然不嫁。
……
而后云青向朋友自剖说
云自幼即受礼教之熏染。
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汨没吾顶,亦难洗前此之遗毒,况父母对云又非恶意,云又安忍与抗乎?
乃近闻外来传言,又多误会,以为家庭强制,实则云之自身愿为家庭牺牲,何能委责家庭,……
终至于无抵抗地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幸福。
而在蔚然与他人结婚时,她一方面理智地写贺诗表示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又在小说创作中暗暗泄露了自己内心挣扎的苦情,知道“许多青年男女的幸福”,都被“礼教胜利”“这戴紫金冠的魔鬼剥夺了”。
作家庐隐深切同情笔下人物云青失去爱情的痛苦,却与自叙传主人公露沙一起认同了云青的做法,未曾进一步去质问这种牺牲有没有价值,不能深入去鞭挞新青年身上残存的礼教遗毒,她深深地“哀其不幸”,却未曾去“怒其不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哀苦之情有余,愤激之志不足,限制了作品反封建的思想力度。
《海滨故人》中写到,
心悟前年和一个青年叫王文义的订婚,两人感情极好,已经结婚有期,不幸心悟忽然出起天花来,……好了之后脸上便落了许多麻点,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偏偏心悟古怪心肠,她说“男子娶妻,没一个不讲究容貌的,王文义当日再三向她求婚,也不过因为爱她的貌,现在貌既残缺,还有什么可说,王文义纵不好意思,提出退婚的话,而他的家人已经有闲话了。
与其结婚后使王文义不满意,倒不如先自己退婚呢!
”王文义起初也不肯答应,后来经不起家人的劝告,也就答应了。
即便是身为新女性的朱心悟,依然自觉认同传统男权文化要么把女性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要么把女性作为满足男性欲望的色鉴赏、色消费对象这一陈腐观念,而不能把女性的价值定位在女性人格、女性内在精神上,依然不能确立女性与男性同为主体的现代性别观念,这样,就由女性色的消失而自我贬抑地否定了女性的全部生命价值。
庐隐小说《沦落》中的男女主人公,都以“不是含苞未放的花”比喻女性失去处女身份,在谴责对女性进行性侵犯的男子时,也包含着对受害女性生命价值的否定。
女主人公松文在相当程度上也认同社会舆论而把自己受到性伤害的生命当作已经贬值的次品看待。
“当女人变成花朵的时候,在一种隐喻的物神式距离之中,我们就可以避开女性的欲望与差异,也避免见到她的非‘菲勒斯’本质,这样,菲勒斯的完整性就受到保护。
”庐隐以女性的敏感对女性柔弱被动的命运表示深切同情,对男子恣意伤害女性的行为感到愤慨,却也与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一样,无法进一步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处女崇拜情结,却未曾进一步去剖析松文思想中的不觉悟因素。
其深层心理还是摆脱不了把女性价值定位为男人的性享乐、性专制对象的封建糟粕。
这说明庐隐作为第一代觉醒女性,既有批判封建男权的强烈意识,具有可贵的人的自觉,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封建男权对女性的贬抑。
同一篇小说中,庐隐还屡屡以“含苞未放的花”、“含露的百合”比喻女性,与以“毒蜂”比喻男子相比,隐匿了女性的主体性,而强调女性传统的被动特质,同样表明庐隐的深层心理中受到封建男权文化的影响。
惊悸于男权伤害女性的历史和现实,庐隐在面对异性世界时,也存在着矛盾的心理。
她笔下的自叙性女主人公,一方面能与相爱的男子一起反叛礼教,追求自由爱情;另一方面,面对不爱的男子,通常又把他们的求爱行为,理解成是对女性的算计。
《或人的悲哀》中,女主人公亚侠发现孙成与继梓两位男子关怀、照料自己,原来各自都含着情爱的目的,便“失惊”而感慨到“那里想到他们的贪心,如此利害!
竟要作成套子,把我束住呢?
”认为“我现在是被钓的鱼,他们是要抢着钓我的渔夫,”并悲哀地感叹“人与人的交际不过如此呵!
”而不能以每个人都有爱、被爱和不爱的权利来从容地把握两性关系、平等地对待异性世界。
庐隐认同地表现了弱者的这种过分警觉和惊惧,既在客观上表现了“五四”时代仍然还有许多男子把女子当作猎物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说明庐隐等“五四”女性在性爱意识方面,还没有完全从女性受伤害、受侮辱的男权阴影中摆脱出来。
不仅封建礼教、男权力量让庐隐心悸而陷入愁苦,即使是新青年由爱情而组合的现代家庭,也时常让庐隐感到无所适从。
小说《前尘》、《胜利以后》、《何处是归程》,散文《最后的命运》便直接表现了庐隐对婚姻的困惑。
庐隐对婚姻的迷惘,首先是源于女子对过往少女生活的追还,是女性由少女转变为少妇这一角色转换过程中自然的心理不适现象。
它与女性对爱情、婚姻的向往、追求并存,但并未对爱情、婚姻的神圣性构成否定。
《胜利之后》中,沁芝给朋友琼芳的信中说
总之想到当初我同绍青结婚,所经过的愁苦艰辛,而有今日的胜利,自然足以骄人,但同时回味前尘,也不免五内凄楚。
《前尘》里,抒情女主人公觉得
实在说伊为什么伤心,便是伊自己也说不来,或者是留恋旧的生趣,生出的嫩稚的悲感;或者是伊强烈的热望,永不息止奔疲的现状。
伊觉得想望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
这种改变生活方式之后的惆怅、忧伤往往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甜蜜体验相交织,共同构成复杂立体的人类心理现象。
对新女性这一心灵幽秘的细致体察,庐隐是第一人。
新女性在争得婚姻自主的“胜利之后”又产生新的精神忧伤,更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