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docx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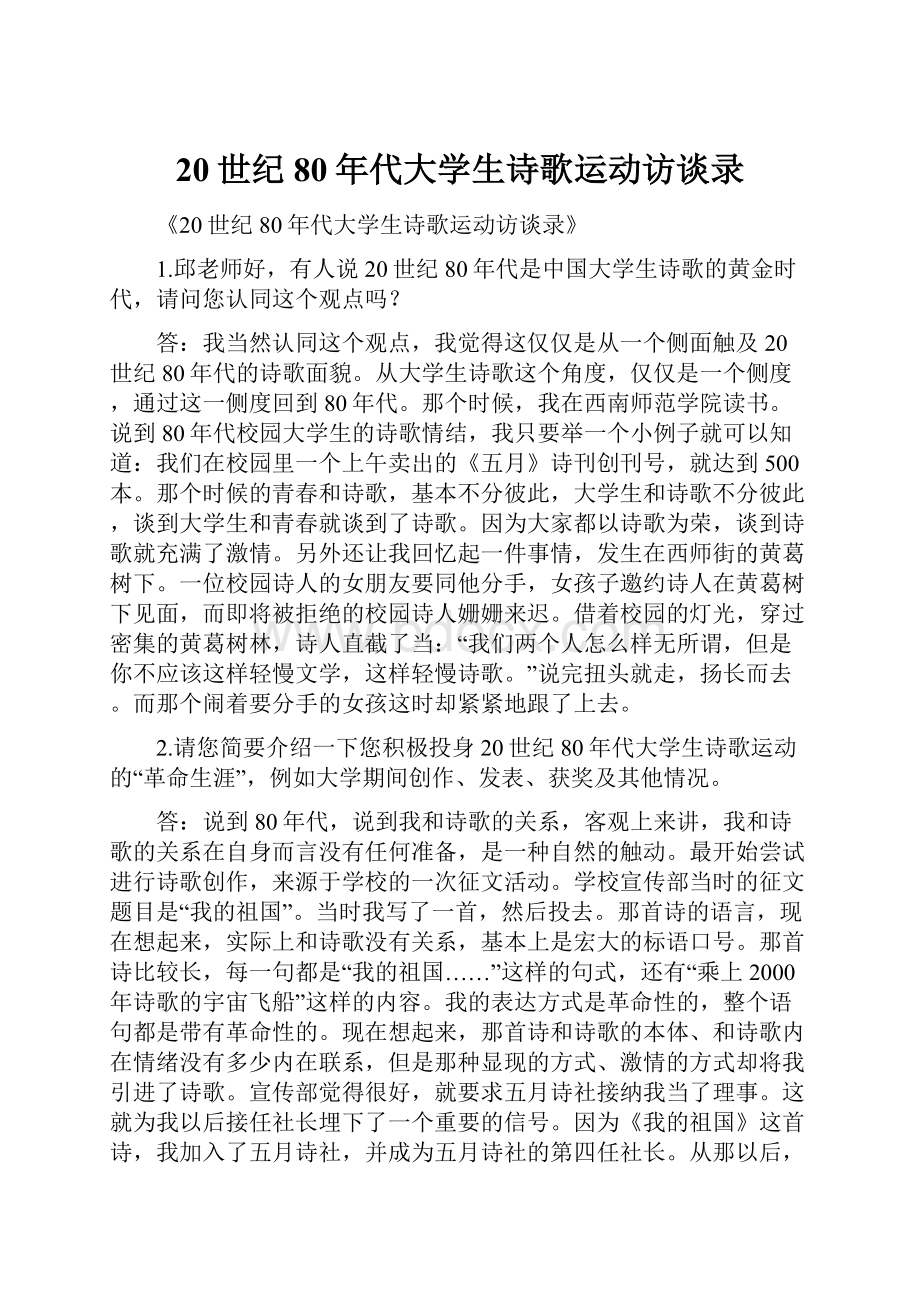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
1.邱老师好,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请问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
我当然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仅仅是从一个侧面触及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面貌。
从大学生诗歌这个角度,仅仅是一个侧度,通过这一侧度回到80年代。
那个时候,我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
说到80年代校园大学生的诗歌情结,我只要举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
我们在校园里一个上午卖出的《五月》诗刊创刊号,就达到500本。
那个时候的青春和诗歌,基本不分彼此,大学生和诗歌不分彼此,谈到大学生和青春就谈到了诗歌。
因为大家都以诗歌为荣,谈到诗歌就充满了激情。
另外还让我回忆起一件事情,发生在西师街的黄葛树下。
一位校园诗人的女朋友要同他分手,女孩子邀约诗人在黄葛树下见面,而即将被拒绝的校园诗人姗姗来迟。
借着校园的灯光,穿过密集的黄葛树林,诗人直截了当:
“我们两个人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你不应该这样轻慢文学,这样轻慢诗歌。
”说完扭头就走,扬长而去。
而那个闹着要分手的女孩这时却紧紧地跟了上去。
2.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积极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例如大学期间创作、发表、获奖及其他情况。
答:
说到80年代,说到我和诗歌的关系,客观上来讲,我和诗歌的关系在自身而言没有任何准备,是一种自然的触动。
最开始尝试进行诗歌创作,来源于学校的一次征文活动。
学校宣传部当时的征文题目是“我的祖国”。
当时我写了一首,然后投去。
那首诗的语言,现在想起来,实际上和诗歌没有关系,基本上是宏大的标语口号。
那首诗比较长,每一句都是“我的祖国……”这样的句式,还有“乘上2000年诗歌的宇宙飞船”这样的内容。
我的表达方式是革命性的,整个语句都是带有革命性的。
现在想起来,那首诗和诗歌的本体、和诗歌内在情绪没有多少内在联系,但是那种显现的方式、激情的方式却将我引进了诗歌。
宣传部觉得很好,就要求五月诗社接纳我当了理事。
这就为我以后接任社长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信号。
因为《我的祖国》这首诗,我加入了五月诗社,并成为五月诗社的第四任社长。
从那以后,诗歌与我的关系,借用王朔小说的名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正是这样一种情结,诗歌对我来讲:
成也诗歌,败也诗歌;好也诗歌,坏也诗歌。
诗歌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有诗歌就能触动我,不管在哪一种情绪状态的背景下都能够触动我。
90年代曾经有段时间,我一度想要主动切断与诗歌的联系,但依然无法真正从本质上断绝。
不是我在找它,就是它在找我,成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形。
在积极参加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过程中,每个诗人的表现都是狂热的。
这种狂热性,是不知不觉就被点燃的。
那个时代谈诗歌、谈诗人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我们当时听说北岛到重庆来、到大学校园来,其他任何意义上的诱惑都无法超越诗歌带给我们的诱惑。
那种狂热是无法描述的。
比如诗人周伦佑曾说过:
我要冒雨到桥头看水。
今天很多人在涨大水、涨洪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冲动,但是当时校园中诗歌的激情和写诗的风潮,就会让人感受到:
这句诗似乎不是文学,是当时生活现状的直接呈现。
3.作为您在80年代创作的诗歌《南方少年》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
这组《南方少年》,是让我走向诗歌之路的很关键的一组诗歌。
回想起这组诗,现在仍然感觉很欣喜。
1985年,我住在桃园二舍的512房间,当时的校园诗歌朋友贺庆来找我说,最近大学生诗歌非常活跃、非常流行。
在当时我们并不十分知晓大学生诗歌,只知道朦胧诗,知道北岛、知道杨炼、知道顾城,对“大学生诗歌”还缺乏一个基本的概念,从诗歌刊物上了解到的校园诗人有许德民、潘洗尘,以及我们西师的胡万俊、程宝林等,感觉他们的诗歌带有一种纯粹抒情化的口语诗歌倾向。
于是我也写作了《南方少年》组诗。
在创作完成之初,压根儿没有想到要投稿给《诗刊》,而贺庆来到寝室说:
“我觉得这首诗不错,可以投给《诗刊》。
”按贺庆的建议,我在信封上将诗刊的地址写好,然后直接寄给李晓雨。
李晓雨是李瑛的女儿,是《诗刊》的编辑。
她不久回复了一封信说:
你的诗歌我们已经收到,请放心,我已经转给相应的主编。
我记得好像是邹狄帆。
这一首诗歌接下来还是有故事的,大概过了一个月,在1985年年底过春节的时候,贺庆来找我。
现在贺庆是重庆《眼镜》杂志社的社长,当时也写诗,而且还写得不错,写法属于现实主义手法,写得情真意切。
因为是西师的家属,所以贺庆经常在校园内活动。
他当时跑来跟我说:
走,你的诗歌已经发表了。
我还在诧异怎么可能。
而他讲:
在《光明日报》中这一期《诗刊》的要目栏已经公示出来了。
当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打着手电筒到西师街的广告栏,发现《诗刊》将我的地址弄错了,误成云南师范学院。
这一期的《诗刊》正好推出大学生诗作全国选,收录了七个人。
那一本样刊,寄往云南师范学院后查无此人,千转万转才邮寄到西南师范学院,终于抵达我的手中。
正是这组诗歌,很纯粹,引发了很多幻想。
当然,就我整体的诗歌写作来说它算不上代表作,但是,它是一组有故事的诗歌,而且应该是我真正的处女作。
诗歌发表之后,收到过很多封因为诗歌而动心的信件,其中我记忆较深的是三个地方邮寄来的,一封来自河南,另一封来自浙江的宁波,还有一封来自东北。
来自浙江的那封,在整个信件之中,没有逗号、没有句号,连绵不绝,大概是弗洛伊德式的精神意识流写作。
信里说,墨水以及眼泪和在一起,写着写着直到烛光开始模糊。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彼此没有任何音讯。
还有一位来信的女读者来自东北的渤海湾,说要采摘一片白桦叶一直飘呀飘,乘着这片白桦叶,从长江口一直回溯到重庆的嘉陵江再到朝天门。
而且说,她是东北唯一的一双大眼睛。
看这些意象,又是渤海湾,又是白桦叶,又是长江口,又是唯一的一双大眼睛,充满着唯美主义的抒情色彩。
当然,至今我也没有看到这一双大眼睛。
这是当时这一组诗歌留下来的故事。
4.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
在社团中您曾经担任过什么角色?
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
答:
可以说,我从一开始写诗,就与诗歌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
首先我加入了五月诗社,后来成为了五月诗社的社长;接着,我们一起创建了重庆大学生联合诗社,在后来我担任了联合诗社的社长。
当时,重庆还属于四川,没有直辖,我们还筹划了四川省大学生联合诗社活动。
当时,我曾积极编辑《五月》诗刊,《五月》第二辑是在我任期间刊行的,接着又编辑了“校园之春”大学生诗报,后来又做了二十世纪诗歌总集特辑,这一名称起得很大。
这些都是在学校组办的诗歌活动,而且刊印诗歌刊物。
一做诗歌,就办诗歌刊物,做成铅字印刷的刊物,需要我们自己跑到印刷厂和检字工人一起,一颗字一颗字地编排模板。
所以后来我们一度拒绝用电脑写作,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写诗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在印刷厂里排字工人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铜模中搜索、捡出来。
当时,如果一首诗的错别字很多,检字工人的工作量就很大。
举办或参加了这些诗歌活动,在一方面,诗人不是写一首诗就单纯放在那里,一旦写作一首诗,向其他人表达的欲望就很强。
我印象中比较深的一次诗歌活动,是吕进老师主持的校园诗歌朗诵音乐会。
吕进老师,当时是校园诗歌活动的风向标,通过吕老师来发起并举办的诗歌活动极其多。
学校主办的这次诗歌音乐晚会,来了很多诗人。
这些诗人里,我记得清楚的,有一个东北的诗人,姓谢。
这个活动里,诗人都是亲自朗诵诗歌,只有一些诗歌是请了中文系、音乐系的同学来朗诵。
那种情景记得很清楚,朗诵中诗人都上台去,各种乡音、土音,汇成了诗歌声音的交响曲。
音乐系的李丹阳,和我一样都是82级的,唱了《月之故乡》。
这首歌的词作者的是彭邦桢。
他是著名诗人,后来去了美国。
诗歌音乐晚会上,人山人海,在现在的东方红行政楼那个位置举行。
诗歌活动里,我也朗诵了杨牧的一首诗《我是青年》。
那个时候我的普通话比较差,基本上是“h”“f”不分,一句话里面都有几个字读错音,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所谓乡音未改,但是激情呀勇气呀高涨,朗诵的时候,台下的人都大笑不止。
5.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参加诗歌活动?
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
答:
我当五月诗社和联合诗社社长时,诗歌的交流活动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在这期间,重庆高校的诗歌势力地图是怎样呢?
我们西南师范学院影响力比较大,我们有个五月诗社。
此外,位于主城区沙坪坝的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学院也很有影响力。
主城区沙坪坝高校密集,包括当时的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学院、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四川外语学院、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这些高校都位于沙坪坝区,所以做起诗歌活动来就具有了相当的优势。
这样呢,就形成了两大诗歌势力辐射区。
第一辐射区,肯定是沙坪坝。
重师张建明、燕晓冬,(燕晓冬还没毕业,张建明就要马上毕业了)他们联合重庆大学的王琪博一起到西南师范学院来成立联合诗社。
当时我们西南师范学院大学生的诗歌创作成就相对高些,尤其是五月诗社的第三届社长胡万俊,可以说在全国大学生当中,诗歌发表量算得上是最大的。
那个时候,选社长的标准是看谁的诗歌发表量大。
因此,第一届的联合诗社社长是胡万俊。
我们成立了重庆大学生联合诗社之后,诗歌大串联这方面的活动就相对较多了。
西南师范学院相对于主城来说较为偏僻,但人文学科是我们的优势,写诗的比较多,诗歌的爱好者也比较多。
当时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大学、还有四川外国语学院等,张枣就是在川外,这几所学校相互之间的诗歌串联活动比较多。
高校大学生诗人中间,成为好朋友的还有刘太亨、燕晓冬、尚仲敏等,后来都成了好朋友,还有李元胜。
李元胜比我们年级要高,他是81级。
还有我们现在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的虞吉,我们一起做五月诗社的活动。
6.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啊?
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
有没有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
关于和读者之间书信的往来,刚刚在《南方少年》这组诗的故事中有提到过一些。
来自东北的读者,名字叫王冷舒,名字读起来感觉特别好听;浙江宁波的来信,作者好像叫毛玉梅。
相反,自己觉得后来诗歌写得好了,收到的来信却少了。
因为处于大学生时代的抒情背景逐渐消失,逐渐远去。
另外,和诗人之间的通信也比较多,当时联系最多的应该是周伦佑。
和周伦佑的交往是我加入“非非”的一个基本原因。
我在担任五月诗社社长的时候请杨黎、万夏、蓝马等来作过很多文学及诗歌讲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周伦佐、周伦佑。
伦佐、伦佑这一对双胞胎太厉害了,可以拿着喇叭筒从早上八点钟一直讲到晚上八点钟,到处宣传,他们的演讲口才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他们的表达方式,都是“考你的博士去吧”这种,很厉害。
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和“非非”建立起联系的。
7.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
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
许德民的诗歌,在当时大学生诗歌创作比较有代表性,明显受到当时朦胧诗人梁小斌的影响。
他的诗歌比较有社会责任感,有批判意识,有社会担当感,我们现在不是在提倡社会担当么,但是我们当时大学生的社会担当感是和理想主义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还比如当时曾担任五月诗社社长的胡万俊,他发表的诗歌比较多,基本上每一周都能收到用稿通知。
所以,当时他在我们大学生诗人中间地位是很高的。
而且诗歌写得好的人,日常学习生活中朋友交往、男女恋爱的机会也多得多,就像现在社会中有房子、有票子、有车子的人,他们受到的待遇会比较好。
再有程宝林的《雨季来临》,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诗句,那种青春洋溢,那种热情的感觉的表达。
当然,这一时期大学生诗歌的创作也有很多青涩的成分存在,有很多稚嫩的成分,但是,这也是诗歌中很纯粹的成分,饱含着蕴藏着青春气息。
青春就是和雨季和春天密切联系起来的,不是一种汹涌澎湃的激情,是第一次潮涌,初潮的感觉,是雨横山间的感觉。
那种激昂的青春气息,溢于言表。
重新回忆当时那种写作的表达方式,可能现在看来,似乎和诗歌没有多少关系,尤其是和先锋写作、观念写作关系不是很密切,但是当时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我们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的动向,那种理想主义、那种热情。
8.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学生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您还有印象吗?
答:
那当然有印象,而且记忆深刻。
这里可以谈到燕晓冬,他的一首诗歌的题目就叫做《第101首》,很有意思:
第101首诗发表在自己的油印物上,第101首诗遭到50次退稿。
燕晓冬的这首诗,可以算作是一种革命性的话语。
这种写法是在朝口语化发展,很调侃,很机智。
我觉得当时的这种大学生诗歌写作,和小说写作中例如王朔等人的风格相比,是一种暗合。
写作语言机制中的无意识,有一种背景。
那个时候的诗歌油印刊物像搞地下刊物似的,和当年的地下党似乎没有两样,而且好像潜意识中就有这样一种感受,是一种革命。
这种诗歌创作和做诗歌事业的方式,当时真的和革命没有两样,因为在80年代理想主义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非常值得留恋的一件事情。
尽管这个时间段不长,但是我生活在那样一个时间里,感觉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现在回忆起来,依然鼓舞我、激发我,内心无法平静。
我们所做的诗歌刊物,刊物质量算是比较好一点儿的。
我们做了油印刊物,而且是更高端的铅字印刷。
我主持发行五月诗刊第二期《校园之春》和校园诗报时,重庆大学生运动会恰好在我们学校举行。
在那个大操场上,诗报一天之内卖了上千份。
而印刷呢,我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检字,把诗作转化成铅字。
我们考察诗歌写作水平,就是看你的作品转化成铅字没有。
我当五月诗社社长期间,还做了“新古典主义”专辑。
“新古典主义”大概做了三、四辑,从宣言到诗歌作品,很全面。
9.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
这个意义和价值,那就太大了。
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处于理想主义时期。
现在流行江南style,我觉得我作为回忆者,80年代可以称作80style。
那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时代,人性充满着觉醒,文学觉醒,美学觉醒;文学热、美学热、思想热、诗歌热、美术热,都是在那么一个时代。
归根结底是思想热。
那个时候的思想,基本上是不休眠的,是一座火山,那是理想主义最具有激情的时代。
我们今天很多人回忆说,那是一个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时代。
也许是吧,但我觉得我们现在所缺少的就是这种乌托邦思想,我们太现实了。
我们怎么变得那么现实了?
而在80年代,我们不那么现实,我们那么具有情怀,有那种乌托邦的气质,所以我们生活得很空灵、生活得很充实,一点儿也不空洞。
我们那种血管的膨胀,都是和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感觉每一天都很鼓舞。
写出了哪怕写一个意象,一个词汇,一个句子,上升到一首诗,都让自己很鼓舞,那种幸福就不是用今天的指数来衡量的,不是一般的指标能抵达的,那是一种无边无际。
我觉得:
今天为了多收了那么三五斗,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们付出了自己的心性,我们付出了自己赖以追求的激情和动力。
我们变得实在是太现实了,现实到没有任何想象力,没有任何其他冲动,我们一直拿着尺子在丈量今天又收入了多少金钱。
我们就变成这样了,这真是变得太没有意思了。
而在那时候,为一个词语,为一种表达,甚至为一种声音,都可以受到鼓舞、受到触动。
我觉得这才是最珍贵的,情义无价,文学无价,语言无价,激情无价,理想无价。
我觉得这才是人的最根本的属性。
有学者说80年代受到“文革”时代激情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抽离出来作价值判断。
尤其是不能够将80年代的理想和激情,判断为“文革”的遗风,这是一种要命的划界。
为什么呢?
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们不能够简单地以一个“好”来了事,一个“坏”来了事。
那么从“文革”时代留下来的某种理想主义,也有着其特殊的价值,我们不能说:
只要是“文革”就是坏的,只要是发展就是好的。
像战争,战争留下创伤,但是也留下来一种战争本身体现出来的英雄精神。
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遗产。
我们不能够将“文革”这一时间段整个抽掉不要,不能这样。
我们不能够贴一个标签,只要是与“文革”有关的任何东西都是坏的,不能够这样。
因为,人性太复杂的。
这个问题的探讨很重要。
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时代再回到“文革”时期,“文革”时期的激情中我们的主体是抽空的,但是“文革”结束之后,思想解放带来的对“文革”的反思,理想主义的复兴,理想主义的再次来临,这就是积极的,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正能量没有什么二致,它们是吻合的。
10.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
我最大的收获是80年代点燃了我生命中本身就有的文学之火、诗性之火,就根本上来说,就是点燃了我的理想主义之火。
当然,后来自己也一度变得很现实,为了生存,我当了很多年的经济记者。
但是我内心里面始终意识到如果我一直那样走下去,那会是很危险的,是走向了悬崖。
当经济记者时期,见识了很多有地位的人,最低级别的都是总经理什么的,见面先是大量旁敲侧击的叙事,最后才说让他们上版面。
这运用了文学功底呀,是曲径通幽,曲线救国。
当时,一个A4纸大的版面给的稿费很高,8000元,算是收入高了。
现在的稿费当然更高了,但是现在叫我再去做,我绝对不去了。
因为做那种工作会让情怀变坏,变得只盯别人的荷包,而不再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态。
欲望是无限的,会把人带向消费,带向刺激。
但我们的内心精神空间也是无限的,所以庄子说:
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
所乐,乐什么呢,乐于道。
而80年代正是这样乐于道的时代,也恰好是我的大学时期,两者是融汇在一起的。
能够经历那个时代,是人生无悔的一个标志。
11.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
我赞同这一个观点。
它恰好是一个衔接点,是一根焊条。
而且从精神角度上来说,它也是一个无缝焊接的时期。
如果展开来讲,怎么讲呢?
它承前是怎么承的?
中国恢复高考之后,还原了大学校园文化知识氛围。
客观来讲,这不单单是文化知识的氛围,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人的自由心性。
大学生活,真正让人打开了心性,打开了思想之门,才真正获得了自由。
而诗歌恰好是抵达自由的最好方式。
因为什么呢,它是语言的艺术,是带有本源性的艺术。
大学生诗歌运动焊接了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运动。
朦胧诗呢,它有着抗争的姿态。
我们常说,愤怒出诗人。
朦胧派诗歌是有愤怒的,但是这种愤怒是渗透在语言中的,是反叛意识形态的控制。
大学生诗歌则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与语言有了对接。
它又向下带动了第三代诗歌。
口语化写作也可以说是大学生诗歌带来的。
第三代诗歌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实际上,它吸收了朦胧诗和大学生诗歌的营养,虽然这种吸收常常停留在技术层面上。
大学生诗歌和第三代诗歌后来有一种融合,它也就成了口语化写作的主力军。
第三代诗人里面,比如李亚伟、万夏、韩东、于坚等,其实都属于大学生诗歌阵营里的主将。
为什么大学生诗歌能够承上启下,以口语化写作去触及时代的语境?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大学生诗歌由于写作主体阅读面广,由于思想比较自由活跃,由于其表达正好是走出校园的,带有一种反叛基质。
然后,大学生的浪漫情怀与对现实的介入意识又恰当地结合了起来,有着处于发散状态的思考锋芒。
这种思考是发散状态的,不是线型的。
教学往往是线型的,把一篇课文归纳成体现着中心思想的什么什么。
而真正的写作,用符号学理论来说,是对语言的重新编码。
这种编码不是科学编码,是人文编码,是无意识推动的,带有爆炸性。
它是写作语言的核爆炸,会呈现蘑菇云的状态。
大学生诗歌运动不仅仅承上启下,并不只是起了连接两头的功能。
我觉得,它不单纯是连接,我刚才用的是“焊接”。
焊接就有融为一体的意思。
后来的新派小说都从大学生诗歌中吸收了营养。
大学生由于恰好经历青春,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短暂阶段。
但当他们和现实一接触,他们的青春浪漫就能够和现实结合起来,使得他们的诗歌既然唯美的基质又有切实的刺痛感。
譬如燕晓冬的《第101首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第101首诗发表在自己的油印物上/第101首诗遭到50次退稿”,“顺便说一句/为了扩大我的影响/凡寄给你的刊物/邮费、包装费、手续费一律免收”,它们就有一种机趣和调侃的口吻。
大学生诗歌尽管带有学生腔,但它也有青春带来的激情与机趣。
12.大学生诗歌具体继承了朦胧派诗歌的那些艺术遗产?
答:
首先是语言。
朦胧派的诗歌被章明他们认为是朦胧的。
他们其实是把朦胧和晦涩等同了。
朦胧和晦涩有差别,朦胧是一种审美效果,晦涩是一种认识和理解的受阻。
大学生诗歌从朦胧诗那里继承了通过翻译西方现代派作品而转化成的现代汉语表达手段。
这种表达手段指向现实。
文言文有着为文而言的倾向。
古代的日常交往语言依然是口语,比如说评书、话本等等体现出来的那种语言。
而现代主义就是要让语言口语化。
第二,大学生诗歌也继承了朦胧诗的批判意识。
当然大学生诗歌的批判与朦胧诗的批判有区别。
朦胧诗的批判是到美刺为止,而大学生诗歌则有一种反讽。
这种反讽建基于深刻的认识。
反讽与讽刺不同。
讽刺是为讽刺为讽刺,为挖苦而挖苦,为愤怒而愤怒;反讽则可以自嘲,可以幽默,有着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惟”所表达的意味。
就是说,我没有那么高尚,我做不了英雄,只能做一个普通人。
我做不了一个完美的人,因为我本身就有缺陷。
第三,大学生诗歌也继承了朦胧派的意象艺术。
大学生诗歌和后来的口语化写作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意象艺术,但我并不认为它们颠覆了意象本身。
我们汉语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意象性。
意象显现是我们生命存在状态的一个投射。
汉语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有着强烈的逻辑性。
因此,我们翻译过来的意象派的诗歌,也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意象派的诗歌通过词语的对撞,通过反逻辑来构成诗性表达。
汉语就不同,它本身就有形象性。
“在天成像,在地成形。
唯人参与,方得形象”,如果只有象,是死亡的。
所以我们要把人的情怀、意志、思想注入象。
西方的拼音文字有逻辑性,但却与人的生命状态分离了。
汉语则没有,它不但象形,还会意。
13.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
有什么感想吗?
答:
我一般不太愿意讲得和失。
周易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好:
事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
在80年代,诗歌融入到了我的生活,成也诗歌,败也诗歌,我无法割舍它。
如果非要说得失,那我觉得,得到的更多,失去的在当时觉得很多,但现在则觉得无足挂齿。
诗歌提示给我一种生命方式。
这种生命方式的力量越来越大。
我之所以没有生活得那么局促,那么狭隘,很大程度上利益于诗歌的无限性。
现在我甚至觉得失去的也是一种得到。
比如说,你经历一段危险的时期,你很紧张,想着怎样逃生,但当危险过后,你跟朋友们叙述这过程,它就是你生命的细节,就是你所珍惜的生命的一部分。
14.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
我有多少读者,我无法测算。
我不会乐观得以为很多人在读我的诗歌,当然,也不会悲观得以为阅读我的诗歌的人少得可怜。
我没有把诗歌写作当作我的职业,但诗歌和我的关系一直很亲密。
它让我保持着不断追求的状态。
今天,当别人谈到我是一个诗人的时候,我还是很自豪。
我也会在内心里面对他们说一声:
谢谢。
我不会假作谦虚说,我算什么诗人。
我会感谢他们还记得我。
现在呢,我已经进入了孔子所说的“五十知天命”的状态。
我开始读《周易》。
我读它不是为了以学问来装饰自己,而是说它回答的问题正是我们生命存在状态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它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基因宝库。
孔子说:
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当你到达这个人生阶段,该经历的风雨都经历过了,该经历的磨难也经历过了,你对事物的判断就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偏激。
我现在的生命状态应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段落。
我没有因为这个段落而消极,没有变成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
过去如果别人瞎判断我,我会有情绪。
现在谁怎样评价我,我也没有什么情绪。
我会想他是从哪个角度,那个侧面来评价我的。
至于他或她了不了解我的内心,我觉得别人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我不可能强求别人能够了解。
现在我可以比较有信心地说,了解我的,还是只有邱正伦。
我经常会抽身出来反省自己,没有像别人所说的很张狂,我觉得我不是这样子的。
我不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包装自己。
如果别人说对了我的缺点,我会毫无戒备地接受。
如果没有说对,我则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