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流水意象.docx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流水意象.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流水意象.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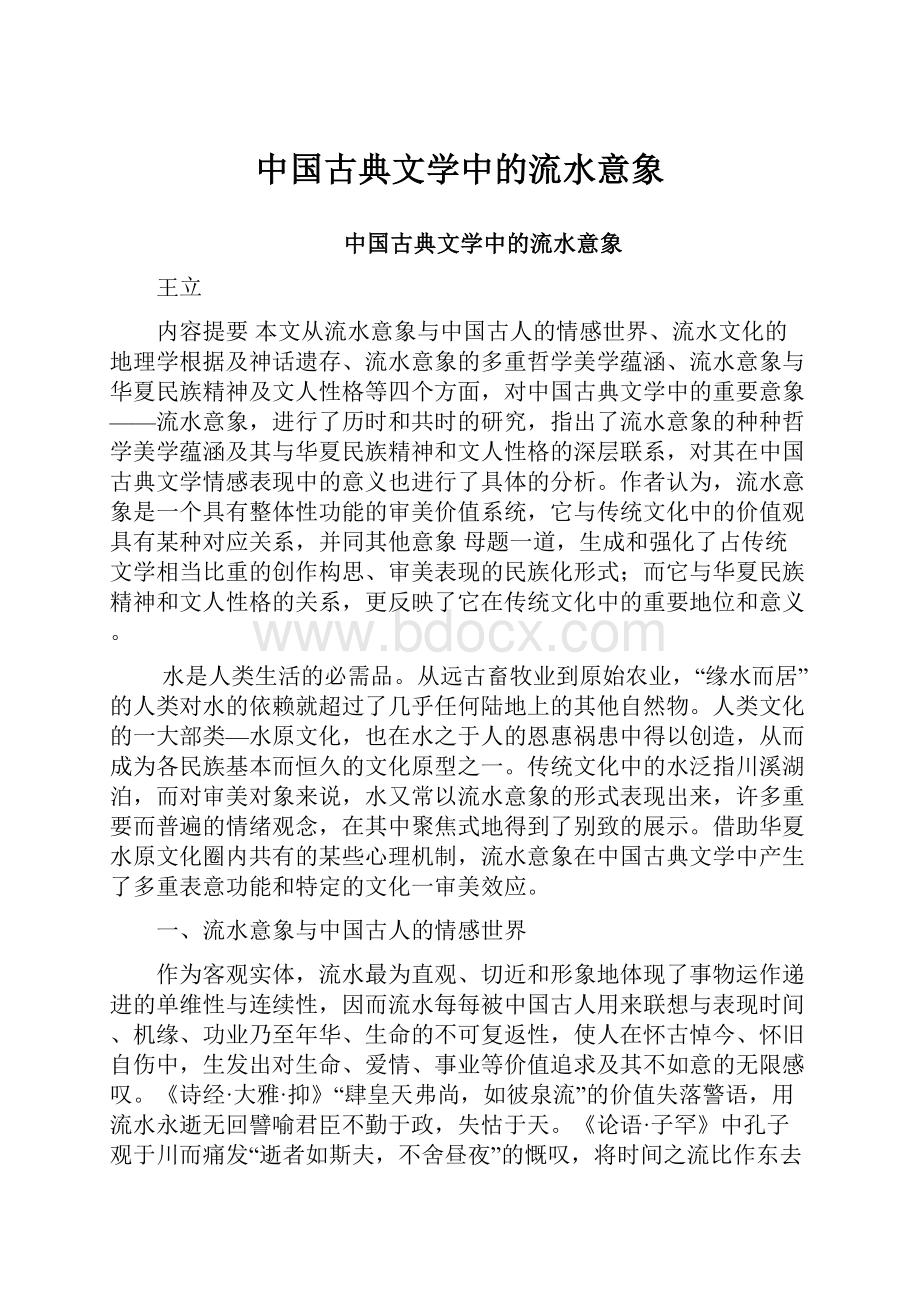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流水意象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流水意象
王立
内容提要本文从流水意象与中国古人的情感世界、流水文化的地理学根据及神话遗存、流水意象的多重哲学美学蕴涵、流水意象与华夏民族精神及文人性格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意象——流水意象,进行了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指出了流水意象的种种哲学美学蕴涵及其与华夏民族精神和文人性格的深层联系,对其在中国古典文学情感表现中的意义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作者认为,流水意象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功能的审美价值系统,它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具有某种对应关系,并同其他意象母题一道,生成和强化了占传统文学相当比重的创作构思、审美表现的民族化形式;而它与华夏民族精神和文人性格的关系,更反映了它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
从远古畜牧业到原始农业,“缘水而居”的人类对水的依赖就超过了几乎任何陆地上的其他自然物。
人类文化的一大部类—水原文化,也在水之于人的恩惠祸患中得以创造,从而成为各民族基本而恒久的文化原型之一。
传统文化中的水泛指川溪湖泊,而对审美对象来说,水又常以流水意象的形式表现出来,许多重要而普遍的情绪观念,在其中聚焦式地得到了别致的展示。
借助华夏水原文化圈内共有的某些心理机制,流水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产生了多重表意功能和特定的文化一审美效应。
一、流水意象与中国古人的情感世界
作为客观实体,流水最为直观、切近和形象地体现了事物运作递进的单维性与连续性,因而流水每每被中国古人用来联想与表现时间、机缘、功业乃至年华、生命的不可复返性,使人在怀古悼今、怀旧自伤中,生发出对生命、爱情、事业等价值追求及其不如意的无限感叹。
《诗经·大雅·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的价值失落警语,用流水永逝无回譬喻君臣不勤于政,失怙于天。
《论语·子罕》中孔子观于川而痛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慨叹,将时间之流比作东去之水。
汉诗“百川东入海,何时复西归”,陆机《叹逝赋》“悲夫!
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变;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寄寓物我相照之意;张协《杂诗十首》其二“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
川上之叹逝,前修以自勖”,郭璞《游仙诗》“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延伸为岁老独悲之慨。
北朝乐府《陇上壮士歌》“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则重现了易水送别之恨。
流水常使人因物思己,顿发今昔盛衰、瞻前感伤之嗟,陶渊明在《闲情赋》中也写下了“寄弱志于归波”的得意忘言之句。
而爱情的一失不可重圆,又与上述的人生感慨何其相似:
“黄葛结蒙笼,生在洛溪边。
花落逐水去,何当顺流还?
——还亦不复鲜!
”[1]
如果说,晋宋后长江中下游经济繁荣、水路交通发达与经商多远行,导致了离情别绪骤然增多,流水遂多寄寓愁情恋语;那么,北方则缘其征战频繁、戍卒离乡背井,造成了闻水声而涌现不绝如缕的思乡之情。
古人曾体会出南北方流水有疾徐清浊之别,《管子·水地》说“楚之水淖弱而清”,当非虚语;而作为北朝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流水意象,“陇头流水”则特指征夫怀乡的焦灼情苦:
登垅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
墟宇桑梓,与云霞一色。
其上有悬溜吐于山中,汇为澄潭,名曰万石潭。
流溢散下,皆注于渭。
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
……俗歌云:
“陇头流水,鸣声呜咽。
遥望秦川,肝肠断绝。
”[2]
目眺耳闻,特定风物的感召形成了条件反射,令断肠人益增愁思。
《乐府诗集》卷二一载梁元帝以降赋陇水诗多首,如张正见“羌笛含流咽,胡茄杂水悲”,江总“人将蓬共转,水与啼俱咽”,王建“征人塞耳马不行,未到陇头闻水声”等等,这些流水意象,渐渐内化为诗人心中之景,于是就有了所谓“陇头水,千古不堪闻”之说。
中国古人对物候农时相当敏感,随着文人主体情性的觉醒和发展,流水意象常与惜时叹逝情愫相伴而生[3]。
如《金楼子·立言》称:
“驰光不流,逝川倏忽,尺日为宝,寸阴可惜”;《颜氏家训·勉学》云:
“光阴可惜,譬诸流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
唐宋以降,流水意象的涵泳代代层累。
如李白《古风》三九、《江上吟》感流水而悟富贵功名不可久驻:
“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功名富贵苦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张九龄《登荆州城望江二首》亦吟哦“滔滔大江水……经阅几世人”;白居易《不二门》的“流年似流水,奔注无昏昼”,与杜牧《洋河阻冰》相仿佛:
“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廖世美《烛影摇红·题安陆多景楼》“催促年光,旧来流水知何处”和陆游《黄州》“江声不尽英雄恨”等,也都倾诉了岁月磋跎带给人的难于排解的牢落感。
“击楫中流”[4]作为英雄欲复兴山河所痛发的铁誓代码,每当社稷艰危、国将不国时,辄为志士仁人所惯道,两宋之交至南宋更不乏此咏。
如陈人杰《沁园春》“满目江山无限愁,关情处,是闻鸡半夜,击楫中流”;张孝祥《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文及翁《贺新郎》“簇乐红妆摇画艇,间中流,击楫谁人是?
千古恨,几时洗”等等,不一而足。
直至清人,还在抒发这类难于平复的缺失怆痛、无力回天的于心不甘。
流水意象的一个亚原型是“覆水不收”。
约于战国末年定稿的《鹖冠子》载:
“太公既封齐侯,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之,令收之,惟得少泥,公曰:
‘谁言离更合,覆水定难收。
’”《后汉书·何进传》也有类似语。
意象与母题(motif)的互可转化性于此可见。
李白《妾薄命》、《白头吟》均以此状君情妾意难再重圆,元人移植到朱买臣身上是顺理成章的。
沙正卿〔越调〕《斗鹌鹑·闺情》叹惋:
“休休!
方信道相思是歹征候,害的来不明不久,是做的沾粘,到如今泼水难收”;明人小说则称:
“尔女已是覆水难收,何不宛转成就了他。
”[5]情爱与女性青春的失落,往往泛化为整个人生的悲慨:
“悠悠岁月如流,叹水覆,杳难收。
”[6]显示了意象系统的内在沟通整合。
流水意象母题在文学内部中的运动,在后世的叙事文学中,更得到了全面的展开。
如杂剧《单刀会》写关羽面对江水大发“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之慨,是性格化的本色之语。
被毛宗岗父子置于《三国演义》卷首的杨慎《临江仙》云: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由浩荡东流的长江缅怀历史上风云人物的浮生短暂。
且不说《牡丹亭》中杜丽娘的“似水流年”之嗟,便是《红楼梦》的整体意脉风神,也几乎离不开一个水意象[7]。
为什么时代有别遭际各异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对流水意象如此偏爱?
简而言之,这是因为它充溢着人生的悲剧色彩和深沉的历史感。
作为个体的青春、生命、功名及历史繁华的“有”,是非永恒性的存在,它终究要归于“无”。
而流水在这种存在向虚无运动的过程中,突出显示了存在与时间的关系。
正是借助于对流水的观照和对流水意象的休认品味,中国古人的生命意识、人生悲剧感与历史宇宙观念互为整合,共同得到了动态性的真实呈露。
流水意象的上述文化意旨,主要体现了个体和社会乃至子宙运动的主客关系,反决了主体无法超越时间规定性与自身有限性的痛苦,因而较为恒久稳定。
而人生日常主活万绪千端的情感,则赋予流水意象另一层面的符号喻指,即随机性地表达某种人生意绪的缠绵与难于割舍。
《楚辞·九歌》写湘夫人、湘君远望相思,观流水而横流涕,神人之语实诉人世界女情肠。
汉武帝《李夫人赋》云:
“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此意愈明。
钱鍾书《管锥编》精辟指出:
“徐干《室思》‘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六朝以还,寖成套语”[8]这种“现成思路”说明,特定意象汇聚着文人阶层对山水自然美的体察,不断为主体情赏意属,广为认同。
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
“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
创古迄今,舳舻相接。
思尽波涛,悲满潭壑。
”《管锥编》评后八句曰:
‘波涛’取其流动,适契连绵起伏之‘思’,……然波涛无极,言‘尽’而实谓‘思’亦不尽’。
”[9]也是以空间之绵远昭示时间之久长。
唐人重友情,离别契阔中的“相思”多表友情而非恋情,流水在离别主题中承担了重要角色。
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韩愈《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河之水,去悠悠。
我不如,水东流”。
白居易《长相思》也将“汴水流,泗水流”同“思悠悠,恨悠悠”对举。
流水又是最早由诗入词的意象之一。
如孙光宪《洗溪沙》“思君流水去茫茫”,而此前沈宇《乐世词》已有“送君肠断秋江水,一去东流何时归”。
宋代以流水喻别情的词作更绵延不衰,连欧阳修、寇准这样的高官显达也不例外。
前者如《踏莎行》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后者如《夜度娘》的“日暮汀洲一望时,柔情不断如春水。
”
海外学人曾指出:
“临水送别”这母题最早可能是楚辞中的“登山临水送将归”和“超北梁兮永辞,送美人兮南浦”。
汉至六朝的别诗多以临水送别为旨。
……(所以李白《送友人》中此类句子的写作)是要藉着这些声音的同时,呈现受诗者的意识里(受诗者是李白的友人,必然也是一个熟识这些诗的诗人),和他同时跃入古代这些空间,和其中各个独例的“别情”里,来诉说他们之间仿佛总合前人的别情[10]。
文学史的整体性正体现在这种意象母题的交汇中。
流水意象有机地融入送别主题,是以其淳厚的人伦情味、生命意蕴等交相辉映为前提的。
“临水送别”之所以能构成富有特定寓意与伤感的母题,正得力于流水意象系统的象征意趣。
自然界中水的流动经艺术本体的集散,泛化并反馈到主体内心的想象空间,因而一种特殊形态的流水—泪水,也就加入到流水意象系列中。
西晋刘琨《扶风歌》已有“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南朝吴歌《华山畿》“泪如漏刻水,尽夜流不息”,“长江不应满,是依泪成许”,鲍照《吴歌三首》“但观流水还,识是侬流下”,“观见流水还,识是侬泪流”似此。
岑参《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
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国流”,李白《去妇词》“相思若循环,枕席生流泉”等皆然。
苏轼《江城子》有“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秦观《江城子》又有“便作春江都是泪,也流不尽、许多愁”;而珠帘秀〔正宫〕《醉西施》继之以“满眼春江都是泪,也流不尽、许多愁”。
然而,不管是江水、河水、溪水、泉水还是泪水,是流尽流不尽,流到流不到,水似乎总是在不停地流,其深层底蕴便是主体情感之流的不可遏止与绵延无穷。
卡西尔《人论》指出:
“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
但是这些运动的形式、韵律、节奏是不能与任何单一情感状态同日而语的。
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
……”[11]中国古代文人的悲悲喜喜,柔情与壮志,希望与恐惧等情感,当然并非简单线性对应地赋予流水意象,而是多线并进、交错组合地纠结一处,牵一而动万。
在个别文本情境中,流水意象往往展示的是其历时性系统的通体蕴味,它在古人情感系统中的兴奋点,一般聚集在主体自我价值上,因而常常带有一定的理性哲思。
而这同流水意象系统背后的水原文化的底蕴是分不开的。
二、水原文化的地理学根据及神话遗存
古代中国属“水利社会”,因而水无疑是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
需要建构了价值,早自传说中伏羲氏所画八卦,即有两卦(坎、兑)与水有关。
而西北高东南低的总体地势和难于根治的黄河水患,自大禹治水始,就现实地横亘在华夏民族的生存发展之路上。
水的治理无法回避且令人困扰,许多政治、宗教、哲学等文化观念,都与治水或水崇拜息息相关。
水在传统文化中通常并不指海,像东汉焦延寿《易林》“海为水王,聪圣且明”的说法是罕见的特例,因为知识阶层一直对海体认疏隔,而对水却十分熟悉、亲和。
如
《说苑·辨物》云:
四渎者何谓也?
江、河、淮、济也。
四渎何以视诸侯?
能荡涤垢浊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云雨千里焉。
为施甚大,故视诸侯也。
所以,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组织滥觞于治水,的确不无道理。
甲骨文中多以“工”来称“官”:
“工,我工,多工都是官名。
”[12]有名的共工,即为管理共水的氏族首领。
据《孟子·滕文公下》等载,大禹正是由于改进了共工的治水方法才得以成功。
其故事所以为后人有口皆碑、宣扬夸大,不仅说明治水对氏族群体的生存至关重要,从而凝聚并完善了社会组织;更说明人们对具有特殊技术及组织能力的卓异人才的企盼神化。
同时,海内合一意识也由此深入人心。
在情况有所变化的秦朝以后,水利同政治制度的联系仍然存在。
治水事业的推行,确能在某些场合加强专制官僚政治,因为“大规模的讲求水利,只有在专制统一局面下才特别有可能与必要”[13]。
水的现实功用,更早且更持久地刺激了神秘主义想象。
上古神话中的“河伯”是最早的水神。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商朝人祖先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郭璞注:
河伯、仆牛皆人姓名)。
《古本竹书纪年》亦称:
“河伯、仆牛皆人姓名托寄也。
”河伯专司黄河祀典,其后继人为冯夷。
后其族化为几个分支各自迁徙,遂有了楚地的《九歌·河伯》[14]。
《山海经·海内北经》中的“冰夷人面而乘龙”,即为冯夷、河伯。
《博物志》卷七说:
“昔夏禹观河,见长人鱼身而出曰:
‘吾河精。
’岂河伯也?
冯夷,华阴潼乡人也,得仙道,化为河伯……”河伯传说之所以枝蔓丛生,是因为祭河盛典乃国家头等大事之一。
殷人始向河岳沉祭以求年、求雨:
…巳,其求年于河,雨?
(《甲》3640)
求年于河,寮三牢,沉三牛,俎牢。
(《掇》550)
乙酉卜,贞:
使人于河沉三羊,三牛,三月。
(《粹》36)
相传帝尧还曾筑坛祭河,获《龙马河图》[15]。
《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祭河的过程。
《礼记·祭法》郑注引《春秋传》“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不时,于是乎萗之”,说明了祭河的多种功用。
殷人祭河是区域性的,而周代官方则祭天下名川。
至秦代后各地建庙供奉当地河神。
王逸释《楚辞·天问》引《传》:
“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
河伯上诉天帝曰:
‘为我杀羿。
’天帝曰:
‘尔何故得见射?
’河伯曰:
‘我时化为白龙出游。
’天帝曰:
‘使汝深守神灵,羿何从得犯汝?
今为虫兽,当为人所射,固其宜也。
羿何罪软?
”这则较早的中原神话已将河伯人格化,并赋予其化龙之能。
又传闻“澹台子羽赍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
阳侯波起,两蛟夹船。
子羽左操璧,右操剑,击蛟皆死。
既济,三投璧于河,河伯三跃而归之。
子羽毁璧而去。
”[16]由于河伯酷爱玉璧,因而玉璧是沉祭之俗中重要的沉祭物,秦始皇南巡渡江,汉武帝堵瓠子决口时均沉璧。
河神的人格化,离不开人们对巨大水兽的神秘体认。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
“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
”这些今已灭绝或罕见的水兽,强化了水神的真实性及相关信仰。
《周礼·大宗伯》的“以狸沉祭山川林泽”及人所熟知的河伯娶妇陋俗可证。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载:
“古冶子曰:
‘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中流。
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
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
津人皆曰:
‘河伯也!
’视之,则大鼋之首也。
”[17]《礼记·月令》还载有祭泉水神的习俗,言仲夏之月,“命有司为民祈山川百源”。
这反映了人类依赖水源、试图将其神圣化而加以保护的思想[18]。
流水使人将宇宙自然神秘化与人格化,而人格化的水神因其同古人生活需要的切近,又促使人们去生发再造心中的水神。
现实之维与想象之维,神话原型与民俗心理交互作用着。
建造都江堰的李冰被奉若神明后,附会的治龙理水传闻便丛集继至。
据说灌口二郎即为其子,而巫支祁、杨将军、黄大王等故事也广为缘饰孳乳[19]。
神话传说的膨胀延展,往往与民俗风习的生成凝定相伴而行。
从中外比较角度看,流水意象的文化意旨似非孤立偶然,各民族水原文化带有某些趋同性质。
如水的再生功能,就较直接地渗透到丧葬、成年、婚嫁与诞生这四大人生礼仪中。
“奈河”是幽明间的界河;《后汉书·礼仪志》载大丧制:
“登遐,沐浴如礼”;印第安人葬前要洗尸;印度教徒必以死后骨灰撒入恒河为夙愿;中国自古文人多水死[20],许多烈女也以自溺求得灵魂洁净[21];各民族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几乎都有沐浴情节,仙女洗澡意味着新婚——再生的前奏。
婴儿出生后洗礼亦不限于犹太民族,胡朴安《中华风物志》记述安徽“婴儿三日后,必为之净洗,谓之洗三朝”。
日本也有此俗。
P·E·威尔赖特曾解释洗礼的意义说:
“来自于它的复活的特性:
水既是洁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
因为水既象征着纯洁又象征着新生命。
”基督教的洗礼则把这两种观念结合在一起:
“洗礼用水一方面象征着洗去原罪的污浊,另一方面又象征着即将开始的精神上的新生。
”[22]
华夏古俗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与外域、尤其是西方习俗的不同之处。
除了水的再生功能形成于农耕群体对水的渴求这类明显原因,与水相关的民俗更反映出传统文化的务实倾向,即偏重世俗而非宗教,且因对特定物候重视而加以周期序化,还透露出些许生命悲剧意识。
祈福免灾的修禊活动,即基于对水的诸功能信奉。
《韩诗》称春秋时郑国便有此俗,应劭《风俗通义》载:
“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
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
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大福)也。
”《后汉书·礼仪志》载:
“是月上已,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
絜者,含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絜之矣。
”魏晋后上已节由三月上旬已日改为三月三日,西晋时这一天“洛中公王以下,莫不方轨连轸,并至南浮桥边禊,男则朱服耀路,女则锦绮燦烂”[23]。
东晋后,王公大臣、文人学士也多在这天踏青水边,以至在杜甫的《丽人行》中,此俗仍然可见。
咏上巳佳节的诗赋中,常有对自然美的讴歌,像夏侯湛《禊赋》、张协《洛禊赋》、阮瞻《上巳会赋》等皆是。
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章诗》“清晨戏洛水,薄暮宿兰池”,萧纲《曲水联句诗》“岸烛斜临水,波光上映楼”等,描绘了水边游玩的场景与心情。
古人常由水畔聚会唱和而感发出深邃的生命意识。
像王羲之与名士谢安、孙绰等宴集兰亭,留下了清新疏朗的《兰亭序》,较石崇在“金谷之会”上“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咏叹,更有出蓝之色[24]。
随着中国文学从经学、神学的桎梏中日愈解放出来,水边祈福的神秘旨归渐为赏景赋诗的娱乐性所冲淡。
而随着古人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流水意象蕴涵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了较大的拓展。
三、流水意象的多重哲学美学蕴涵
神话传说的历史化与制度民俗的心灵化,使流水意象作为错综复杂的观念载体日渐明晰。
《管子·水地》云:
“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
”认为水有人的才性,水关人世,“水者何也?
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故曰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
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
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水的实用功能被推广到稳定社会与治世之道,甚或由外在的人化世界反诸主体自身:
“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
……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
”
东晋玄学家指出: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
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耶?
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
”[25]这感受不只驻足在借山水化郁结的达观之想,也不限于光景迁移、新故互换带给人的“乐与时去,悲亦系之”。
自先秦的“比德”风习,早就在流水意象中较完备地灌注了哲理、伦理等象征意义。
人们在对潺潺流水、滔滔逝川的观照时省思自身,萌生了由物观物到反观诸身的自我意识。
个体人生情境百态纷呈的复杂感受,交织进这种自我意识的省察中,极为契合当代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有机体并不是凭借局部的和各自独立的事件来对局部的刺激发生反应的,反之,乃是凭借一种整体性的过程来对一个现实的刺激丛进行反应的,这种整体性的过程,作为一个机能的整体,乃是有机体对整个情境的反应。
”[26]作为华夏文化圈的有机生命体,中国古人带有农耕民族温厚诚笃的天性,又因宗法制对血缘伦理的强调而极富道德感;因而在对流水的解悟及阐发的哲理中,突出体出了民族特征。
《孟子·告子上》言人的善性同流水趋下的本性类似,《尽心上》进而认为: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以流水来勉励君子通达于道须孜孜以求。
《离娄下》又云:
“徐子曰:
‘仲尼亟称于水,曰:
‘水哉,水哉!
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
‘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
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
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流水之有本有源,如同君子要有立身行事的根本,否则人就一似无源之水,干涸立待。
在这里,人格尺度与价值观念被对象化地投射到流水意象上,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入世进取与务实精神。
《荀子·宥坐》将实用需求、审美观照与伦理关怀的诸般哲思交融在一起,假托孔子之口进行了系统的表达:
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
其流也埤下,据拘必循其理,似义。
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
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
主量必平,似法。
盈不求概,似正。
淖约微达,似察。
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
其万折也必东,似志。
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流水意象如此被具象化、人格化,并同人世伦理规范、美德异能一一对应起来;而流水成为实行这些规范美德的楷模,实际上也就是儒家力求实现的“理想人格”。
流水意象荟萃的众多美德简直完美无缺,正说明儒家伦理之于人格规范的严格与全面。
杂家著作《尸子》也采此说:
“水有四德:
沐浴群生,通流万物,仁也;扬清激浊,荡去滓秽,义也;柔而难犯,弱而能胜,勇也;导江疏河,恶盈流谦,智也。
”《春秋繁露·山川颂》亦袭此,言水似力者、勇者、武者、有德者。
《说苑·杂言》(《韩诗外传》二五章类似)讲得更为透辟:
夫智者何以乐水也?
曰:
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
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
动而下之,其似有礼者。
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
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
不清以入,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者。
众人取乎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
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
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
是知之所以乐水也。
显然,流水的哲理意义被不断充实完善,并定向延伸。
而对个体的伦理要求,又被神圣化并推及到其对群体的功用上。
人们赋予了水以多种伦理化的象征蕴涵,而象征一旦形成又被用来引导、规范人的行为。
儒家教化思想竟能由流水意象精妙地呈示出来,真是意味深长。
老子褒举流水也牵涉到其学说体系的核心: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流水的这种不争之争、似柔实刚的质性,使道家始祖从中找出了理念的对应之点。
《淮南子·原道训》进而强调:
“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
……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像之类,莫争于水”,“柔弱者,道之要也。
”《庄子·山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在《礼记·表记》中作“君子之接如水”,均与小人之交甘若醴相对。
于是,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与处世之道,在道家哲学中也得到了说明,并补充了儒士的内圣外王、自强不息的价值追求。
意象母题就这样冲破了门户之见,流水那百折不回、滴水石穿的韧性为儒道两家从不同角度认同发挥,成为君子或儒或道、或出或处的现实和心理参照物。
汉代的神学氛围,赋予水一种统摄万物的神秘色彩,渐为后起的道教所吸收。
《陔余丛考》卷三五称:
“道家有所谓天地水三官者,《归震川集》有《三官庙记》,云其说出于道家,以天地水为三元,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皆帝君尊称焉。
”
《庄子·秋水》以流水入海后的浩渺无垠喻得道后的境界,尤为魏晋玄学所阐扬。
水虽如《晋书》纪瞻本传所言“内性柔弱,以含容为质”,但这含容之性恰恰说明了人内心世界的包容深远。
《世说新语·德行》载名士郭林宗称黄叔度:
“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西晋玄学家阮修《上巳会诗》言“水有七德,知者所娱”;刘宋时宗炳《画山水序》提出:
“夫圣人以神法道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
”这些见解,虽未摆脱乐山乐水的传统模式和释道二教的影响,但主体情性却愈显突出。
在唐代三教合流的文化氛围中,流水意象也呈现出多种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倾向。
杜甫《江亭》“水流心不竞”与“云在意俱迟”并举,表达了淡若止水、旷达率意的人生态度。
刘禹锡《叹水别白二十二》:
“水,至清,尽美。
从一勺,至千里。
利人利物,时行时止。
道性净皆然,交情淡若此。
……两心相忆似流波,潺潺日夜无穷已。
”在吟咏流水的瞬间,诗人的种种体验、回忆与联想百念交集,种种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