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身份转换与北魏文化的正统认知探讨.docx
《华夷身份转换与北魏文化的正统认知探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华夷身份转换与北魏文化的正统认知探讨.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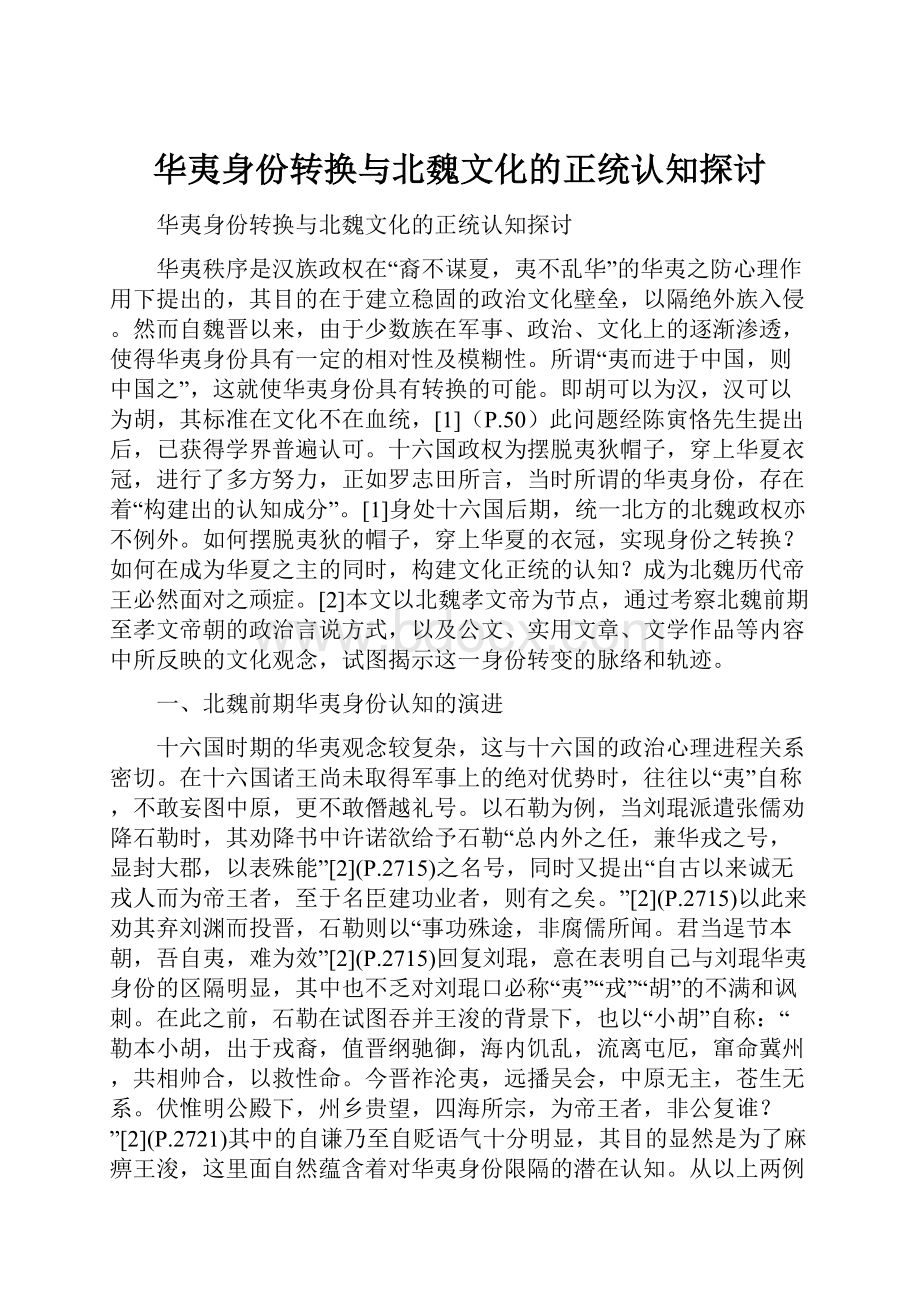
华夷身份转换与北魏文化的正统认知探讨
华夷身份转换与北魏文化的正统认知探讨
华夷秩序是汉族政权在“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华夷之防心理作用下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建立稳固的政治文化壁垒,以隔绝外族入侵。
然而自魏晋以来,由于少数族在军事、政治、文化上的逐渐渗透,使得华夷身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及模糊性。
所谓“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就使华夷身份具有转换的可能。
即胡可以为汉,汉可以为胡,其标准在文化不在血统,[1](P.50)此问题经陈寅恪先生提出后,已获得学界普遍认可。
十六国政权为摆脱夷狄帽子,穿上华夏衣冠,进行了多方努力,正如罗志田所言,当时所谓的华夷身份,存在着“构建出的认知成分”。
[1]身处十六国后期,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亦不例外。
如何摆脱夷狄的帽子,穿上华夏的衣冠,实现身份之转换?
如何在成为华夏之主的同时,构建文化正统的认知?
成为北魏历代帝王必然面对之顽症。
[2]本文以北魏孝文帝为节点,通过考察北魏前期至孝文帝朝的政治言说方式,以及公文、实用文章、文学作品等内容中所反映的文化观念,试图揭示这一身份转变的脉络和轨迹。
一、北魏前期华夷身份认知的演进
十六国时期的华夷观念较复杂,这与十六国的政治心理进程关系密切。
在十六国诸王尚未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时,往往以“夷”自称,不敢妄图中原,更不敢僭越礼号。
以石勒为例,当刘琨派遣张儒劝降石勒时,其劝降书中许诺欲给予石勒“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显封大郡,以表殊能”[2](P.2715)之名号,同时又提出“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
”[2](P.2715)以此来劝其弃刘渊而投晋,石勒则以“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
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2](P.2715)回复刘琨,意在表明自己与刘琨华夷身份的区隔明显,其中也不乏对刘琨口必称“夷”“戎”“胡”的不满和讽刺。
在此之前,石勒在试图吞并王浚的背景下,也以“小胡”自称:
“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驰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
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
伏惟明公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
”[2](P.2721)其中的自谦乃至自贬语气十分明显,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麻痹王浚,这里面自然蕴含着对华夷身份限隔的潜在认知。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石勒称自己为夷族时,或屈从于对方的军事实力之强盛,或出于麻痹敌人的情绪,而当时机足够成熟时,所谓的夷狄身份以及“吾自夷”的虚伪表述,已经不能掩盖其称王称帝的野心。
其他诸国君主,皆不乏“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众也”[2](P.1686)的认知,即使短暂统一北方的前秦,也不免以夷狄的身份自居。
苻坚南伐前,苻融每谏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穷兵极武,未有不亡。
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
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
”[2](P.2935)其所谏阻的理由乃是国家为戎族,在正朔的问题上没有优势,而东晋乃是天命所归,可知苻融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仍是“夷夏殊途”。
然而,此时前秦也已开始通过文教改变夷族身份的尝试,如苻坚的大力推进文教事业,《晋书·苻登载记》上称苻坚“变夷从夏”,又称其“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
其目的是为了改变“畏吾众”以服晋人的武力征服方式,向获得晋人心理上的认同过渡,这为北魏明元帝后进行一系列的“文德与武功俱运”的国策制定提供了前车之鉴。
道武帝之前,亦即代国时期的拓跋族,仍然延续十六国诸王对华夷认知的态度,其华夷身份之区别仍很明确。
如在被封为代王之前的力微时期,其太子沙漠汗因“风彩被服,同于南夏”[3](P.4)而被离间杀害,可见其时拓跋族内部对于华夷差异十分介怀。
到了猗卢时期,在帮助刘琨收复并州失地的同时,向西晋称臣,以表明自己无心图华的心理,受晋愍帝封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
[3](P.9)当成都李雄政权向其请求与之平分天下时,亦并不予以采纳,可知猗卢尊晋之心十分坚定。
而当刘曜杀害晋愍帝之后,当时的代王郁律对大臣称:
“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
”[3](P.9)由此可见,虽然此时慕容氏、拓跋氏等政权秉持“勤王杖义”之举,尊两晋为正统,但实际上内心仍十分倾向于早日摆脱夷狄身份,获取中原认可。
十六国诸王的华夷意识,其实反映了一种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希望能够通过武力,以获取中原地域为基础,进而获取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中原部分领土,但尊晋的强大心理惯性以及汉族士人的传统认知,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3]从少数族政权角度看,这是不足以称雄中原的权宜之计,从中原士人角度看,中原汉人在面临东晋多次北伐不利的情况下,已然接受了少数族政权地位难以撼摇的事实,故而,汉族士人心理开始发生倾斜,从最初的排斥,到与少数族政权试探性地配合,逐渐走向文化上的以夏变夷路线。
道武帝时期,是拓跋氏向华夷秩序挑战的初步尝试。
道武帝初建魏国时期,在心理上并非十分自信,这从其“定国号为魏”的诏书中即可看出:
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
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
民俗虽殊,抚之在德。
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
宜仍先号,以为魏焉。
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3](P.32-33)
其中“天下分裂,诸华乏主”一句颇耐斟酌,其意一方面是指当时华夏内部虚空,诸国皆有入主华夏的机会和可能;另一方面表达了自身对于入主中原并不具有十足的信心,同时,对于拓跋族在中原士人内心的认可程度,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因此,此次议定国号,最终决定“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继承曹魏统序,获取一定的认可基础,并表明入主中原的态度坚决。
继天兴元年(398年)以后,天兴三年(400年)道武帝即颁布了“天命诏”。
其中提出:
“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又称“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
”[3](P.37)当时,拓跋珪虽然新平后燕,但南有后秦,西有赫连,北有高车、柔然,形势并非稳固。
所以此时颁布的“天命诏”其目的在于向其他政权宣示,中原领土除大魏外,其余皆不得天命所赐。
因此以“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3](P.37)加以警示,此可谓舆论战的一种方式,这使得拓跋珪在向华夷身份转化之路上迈进了一步。
如果说道武帝时期的身份塑造某种程度上是形式大于内容,那么到了太武帝时期,华夷身份的冲突随着需求的急切以及改革的深入,触及到实质性内容,崔浩的“国史之狱”,实则是北魏内部华夷身份冲突集中爆发的体现。
对于史书编撰的重视,反映了太武帝建构文化统序的愿望,而几次三番修史不成,则反映了其对自身形象塑造的问题十分在意,甚至不惜杀害几位非常重要的史官,以此来向汉人宣示华夷身份之于北魏正统塑造意义的重大。
修史的过程,其实正是修去拓跋族“夷”的身份,建立起“华”的角色定位之过程。
因此,当崔浩修史将拓跋先世列于衢路时,“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4](P.3942)可知北人对于身份的认知十分介意。
这与当初太武帝对崔浩提出修史要“务从实录”的要求显然背道而驰,可见从夷变华的身份塑造进程,对于拓跋氏来说痛苦且漫长。
[4]
太武帝对崔浩等汉族士人的惩罚诚然有过激之处,其目的无非为了表达修史虽然以汉人为主,但史之内容需符合拓跋氏之立场和文化准则。
因此崔浩的国史之狱某种程度上说是华夷身份认知所触发的悲剧,这也说明华夷身份的认知问题在太武帝时期已经触及到了核心内容。
至文成帝、献文帝时期,华夷身份的认知已经不再局限于理论的探讨,而是沿着太武帝的思路继续开拓。
如文成帝和平四年(463年)相继颁布了“定婚丧条格诏”、“贵族不婚卑姓诏”,试图通过婚丧制度的确定,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尊卑高下,宜令区别”,[3](P.122)表面看来此举是实现国家内部的尊卑定位,实则是希望结束鲜卑族早期闺门不肃的状态,以向华夏文明靠拢。
又如献文帝在延兴二年(472年)“祀孔子庙禁妇女合杂”规定在祭祀孔子庙时“制用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改变以往“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的野蛮状态。
[3](P.136)而观此时献文帝的诏书中,与之前最大的变化在于,每于诏书中称引《诗》《书》《易》等儒家典籍,这也是向华夏文明靠拢的一种表现。
这一切为孝文帝时期华夷身份的彻底转化铺平了道路。
[1]罗志田《有教无类:
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
“一些已部分‘汉化’的胡族的重新‘胡化’,即‘胡胡化’。
‘杂胡化’的现象提示出,那时北方各族间的胡化、汉化可能是多层次反反复复进行的,其‘胡’的程度和含义都充满了构建出的认知成分。
”(《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2期。
)
[2]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
“北魏在军事上已经树立霸主地位后,是建立政权的合‘法’性,所谓法,既是得到国内汉族士人的承认,又是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
而胡族身份是其取得合法性的最大障碍。
对此,北魏的胡族身份的摆脱,依靠两种手段,一则构建新的内外系统,如将北方柔然、高丽、南朝视为僭伪政权,这可看作摆脱夷狄帽子的阶段。
二在形式上建立中华正统身份,如建立制度,汉化过程,定鼎洛廛等方式,这是戴上华夏帽子的阶段。
而文化的构建,是在真正成为华夏族的关键阶段。
这种华夏思想的制约和摆脱,是左右北魏进行汉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来从此角度所论甚少。
”(《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
[3]这从十六国对于“天下”的认知,以及对国内封王的名号即可看出,这是其在军事实力上不足以合并诸国,政治身份上不足以服众的权益之举。
(参见王安泰:
《皇帝的天下与单于的天下——十六国时期天下体系的构筑》,童岭主编:
《皇帝单于士人:
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97页。
)
[4]从拓跋焘的“以为暴扬国恶”到孝文帝时期“不讳国恶”,“北魏王朝的国史案已超出史家实录传统的文化冲突,而上升到夷狄与华夏之间的文化交锋。
”(张碧波《北魏王国国史案的背后——一场特殊形态的华夷文化冲突》,《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5期)
孝文帝在迁都之前一系列礼制上的改革举措,无不体现了追求华夷身份转变的诉求。
太和十四年(490)八月重订五德运次,依据汉将秦视为闰统,故将十六国之秦、赵、燕等国视为闰统,排除在外,直接承晋为水德,此种做法正是为了迎合汉族士人对晋朝的认同心理。
在太和十五年(491)八月期间,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减省祭祀的改革,其目的是剔除鲜卑早期原始祭祀方式,进一步向中原正统祭祀规范化靠拢。
进而,太和十八年(494)“诏罢西郊祭天”,西郊祭天的行为,实际上是拓跋民族的原始祭天方式的遗留,[5](P.511)对其扬弃,意味着放弃蛮夷的祭祀方式,而正式步入华夏祭祀系统。
种种迹象表明,孝文帝华夷身份转换的行动已经进入深化时期。
以定鼎嵩洛为界限,孝文帝时期华夷意识的转变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迁都之前缺乏华夷转换的坚实基础,迁都之后,在地域上已经抢先占有优势,在身份转变上便多了一层自信。
历来讨论孝文帝迁都问题,皆关注其汉化改革上的意义,实则在孝文帝汉化过程中,无不蕴含其对华夷身份的介怀,以及试图彻底摆脱夷族身份制约的心理障碍。
孝文帝时期华夷身份的转变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手段:
其一,向内宣示继承统序,在血统与正统之间寻求平衡点。
此点延续了十六国时期诸王多从上古帝王中寻求例证的做法。
如汉刘渊曾云:
“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生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
”[2](P.2649)慕容廆亦曰:
“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
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
”[2](P.2813)刘渊和慕容廆皆针对国家内部胡汉之间认同感差的问题而言,即通过上古帝王的身份出发,以此来消除隔阂。
这在北魏后来修史的过程中也曾用到,如《魏书·序记》里称拓跋族是黄帝之后裔,就是为通过血统的认证消除华夷之区别。
在孝文帝迁都以后,华夷的地理区隔已然泯灭,定鼎嵩洛成为北魏由夷变夏的最大自信。
此时北魏大可堂而皇之地称“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
”[3](P.2744)
孝文帝迁都后一个重要的举措即祭祀山川五岳,其目的是向内宣示华夏身份的正统性。
在孝文帝本人所作几篇祭祀山川五岳的文稿中,可明显看出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文化意识,如其《祭嵩高山文》曰:
“朕承法统,诞邀休宏。
开物成务,载铄盛龄。
迁宇柳方,阐绳廛城。
则直之兴,百堵若星。
”[6](P.78)《祭河文》曰:
“惟圣作则,惟禹克遵。
浮楫飞帆,洞厥百川。
朕承宝历,克纂乾文。
”[6](P.80)此外,孝文帝尚有《祭恒岳文》、《祭岱岳文》、《祭济文》等多篇祭祀山川河流之文,内容上多表现对自身华夏身份的认可和自信。
太武帝时期曾利用一系列手段确定正统身份,如改元太平真君年号,试图利用谶纬祥瑞事件以树立正统,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常山王素,恒农王奚斤等人联名上奏:
“自古以来,祯祥之验,未有今日之焕炳也。
斯乃上灵降命,国家无穷之征也。
……宜以石文之征,宣告四海,令方外儹窃,知天命有归。
”[3](P.2955)借助外界手段,或自我虚构的祥瑞事件,对外宣示“天命有归”,这其实正是对自身华夏身份不够自信的表现。
而到了孝文帝时期,此类手段早已不屑或无需使用,这是因为迁都洛阳提供了在平成时代所难以企及的先天条件,孝文帝只需以华夏帝王身份进行祭祀天地山川,实现统序的认证即可。
其二,向外改变夷虏对象,实现身份的互换。
其具体方式是将敕勒、柔然视为虏,将南朝视为夷。
此种手法早在献文帝时期即已采取,如其对高丽进行了身份的互换,延兴二年(472年)八月,献文帝在《答百济国王余庆诏》中称:
“卿在东隅,处五服之外,不远山海,归诚魏阙,欣嘉至意,用戢于怀。
朕承万世之业,君临四海,统御群生。
”[3](P.2218)将百济视为“五服之外”,并定位为“藩臣”,实与夷狄相等同。
孝文帝时期,最能体现身份转换的则是针对北方的柔然以及南朝。
高允在《北伐颂》中称:
“北虏旧隶,禀政在蕃,往因时□,逃命北辕。
世袭凶轨,背忠食言,招亡聚盗,丑类实繁。
”[3](P.1085)将柔然视为“北虏”,进行口诛笔伐。
《魏书·高闾传》载高闾上表孝文帝曰:
“北狄悍愚,同于禽兽”、“今故宜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北狄、北虏指的也是柔然(蠕蠕)。
可再举数例为证,《魏书·袁翻传》载袁翻上书曰:
“然夷不乱华,殷鉴无远,覆车在于刘石,毁辙固不可寻。
”《魏书·扬播传附杨椿》载杨椿上书: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羁縻而已。
”张彝《上历帝圜表》称:
“海东杂种之渠,衡南异服之帅,沙西毡头之戎,漠北辫发之虏,重译纳贡,请吏称藩。
”拓跋族早期出于游牧民族,其习性与敕勒、柔然相似,风俗多以辫发为主(南朝亦因此称其为“索虏”),至迁都洛阳改为汉服后,竟将柔然视为“漠北辫发之虏”,可谓讽刺。
从诸臣子的奏表中可以看出,此时北魏贬称北方诸族,显然已完全将华夷的位置进行了置换。
针对南朝政权,将其视之为“岛夷”是北魏实现身份转换的重要手段,《魏书·礼志一》载,太和十四年(490年)八月议定五德行次,中书监高闾上表曰:
“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
伏惟圣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统历,功侔百王。
”将刘裕、萧道成视为蛮夷。
又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诏书称:
“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
可诏荆、郢、东荆三州,敕勒蛮民,勿有侵暴。
”[3](P.175)将南朝荆、郢、东荆三州等同于敕勒蛮民。
此外,《魏书》之中,多称南朝诸国为“岛夷”,这当然是史官的一贯作风。
[1]
除了在史书上大做文章,北魏更试图在洛阳构建华夏正统的秩序,其手段是利用洛阳先天的地域优势。
如在《洛阳伽蓝记》中有“四夷馆”的记载: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
道东有四馆。
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
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
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
”[7](P.145)“四里”的名称中显然蕴含了对北魏政权正统的自我肯定,同时也意味着对东南西北各处政权正统性的否定,所谓“归正”即“归于正统”之意。
总之,通过多方努力,运用多种手段,以迁都和汉化为标志的华夏身份转换,在孝文帝时期已经基本完成。
这使其对内的统治更具有正统的约束力,对外的交往更具有坚实的理论后盾,由此,孝文帝将政治正统的构建转换到文化正统的构建上,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1]对此,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早已明辨,《史通·断限》曰:
“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
”
孝文帝时期文化正统的构筑,首先建立在军事实力的优势上。
孝文帝时期在军事上已对南朝处于极大优势,因此君臣常抱有混同南北的信心,如元英上奏南伐齐朝时称:
“窃以区区宝卷,罔顾天常,凭恃山河,敢抗中国。
……士治之师再兴,孙皓之缚重至,齐文轨而大同,混天地而为一。
”[3](P.497)孝文帝亦常言:
“密迩江扬,不当早晚,会是朕物”[3](P.1055)、“朕承天驭宇,方欲清一寰域”(太和二十二年诏书)[3](P.965),“齐文轨”、“清寰域”似已成为此时北魏君臣口中之常事,此种军事自信乃是建立文化自信、树立文化正统的前提和基础。
然而,孝文帝毕竟深知拓跋族在文化上落后于南朝的事实,尤其在经过了崔浩的国史之狱后,北朝文人高允等人已“不为文二十年”,文化的复兴显然不能一蹴而就,故欲建立文化自信,必须经大力提倡与鼓励。
对此,孝文帝以身作则,率先倡导文化复兴,《魏书·文苑传序》载:
“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
衣冠仰止,咸慕新风。
”肯定了孝文帝在北魏文学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孝文帝其人“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有兴而作。
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
自余文章,百有余篇。
”[3](P.187)冯太后的教导使其精通汉文化,对汉文化的喜爱是其能够进行汉化的前提,“及其成也,不改一字”也表示孝文帝本身具备出众的才华。
因此,北魏老臣张衮早年提出的“文德与武功俱运”的期许,到了孝文帝时期得以实现,成为一种必然结果。
孝文帝对文学的倡导能够激励文人创作热情的恢复,他时常鼓励朝臣在朝堂上赋诗申义,使“武士弯弓,文人下笔”,《魏书·郑羲传》中记载的一段朝堂上的联诗,颇能展现孝文帝对于文化正统树立的信心:
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
“白日光天无不耀,江左一隅独未照。
”彭城王勰续歌曰:
“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江外,”郑懿歌曰:
“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
“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
”道昭歌曰:
“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
”高祖又歌曰:
“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
”宋弁歌曰:
“文王政教兮晕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谓道昭曰:
“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遂命邢峦总集叙记。
当尔之年,卿频丁艰祸,每眷文席,常用慨然。
”[3](P.1240)
酒酣之际,孝文帝感慨江南一带尚未统一的遗憾,循此思路,诸臣子或赞美或奉承,尽显混一南北的自信。
从“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中可见,孝文帝朝君臣赋诗成为常态,并且注意将其收编成集,以供流传。
孝文帝对于自己的文章多注意整理收集,他曾作《吊比干文》,并令刘芳注,称其“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
”[3](P.1221)其集书之举乃是希望能够流传于下,目的在于推崇北魏文化之发达,同时昭示内外,彰显文化正统之所在与混一南北之决心。
《南齐书·魏虏传》中对孝文帝的简短评价:
“知谈义,解属文,轻果有远略。
”已经足以说明孝文帝文化自信构建所收到的成效之显著。
在此显著成效的催逼之下,士人多北魏将视为文化正统之所在,如高闾上表曰:
“大魏应期绍祚,照临万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谧”[3](P.1207),称颂北魏政权顺应天时;程俊《庆国颂》:
“於皇大魏,则天承祜。
叠圣三宗,重明四祖。
岂伊殷周,遐契三五”[3](P.1348),言北魏承绍三皇五帝之顾名;高允《鹿苑赋》:
“启重基于朔土,系轩辕之洪裔”,信其为黄帝后裔;又其《酒训》颂赞:
“今大魏应图,重明御世,化之所暨,无思不服,仁风敦洽于四海。
”这已不单是奉承歌颂,而是从北魏符合中原正统地位的前提出发,对政权合理性予以承认、对文化正统性予以彰显的表现。
而在南北对话当中,文化正统的认知成为矛盾之焦点。
北魏早期与南朝的对话,在文化交锋上往往表现出劣势。
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北魏太武帝率军队南下,“至彭城,立毡屋于戏马台以望城中”[4](P.3955),武陵王刘骏遣使者张畅与李孝伯谈判,此为南北对话之开端,在此过程中,两人针对称谓、礼法、道义、国家正统诸问题进行了你来我往的讨论,综合《宋书》和《魏书》记载的内容来看,北魏实际并不占上风,其所以能够与之平等对话,乃在于军事实力上的优势,并且两人谈话中并没有触及文化上的内容。
而到了孝文帝,则格外注重外交场合在文化交锋上的得失,在太和初年,孝文帝命卢昶出使南朝时,特意嘱咐副使王清石称:
“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语致虑。
若彼先有所知所识,欲见便见,须论即论。
卢昶正是宽柔君子,无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诗,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复罢也。
凡使人之体,以和为贵,勿递相矜夸,见于色貌,失将命之体。
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规诲。
”[3](P.1055)主使卢昶属范阳卢氏,虽有高门风范但性格宽柔且乏文采,因此孝文帝特别强调副使不要在赋诗的环节上失掉尊严,其对外交中文化之重视可见一斑。
在吸收了一批南来文人,激励了本朝沉寂多年的汉族士人,引导了拓跋贵族文化转变后,孝文帝成功地扭转了北魏早期外交往来中文化上处于劣势的情况。
至此以后,南北双方在交往中,以文化做武器“宣扬此化,多非彼僭”遂成为常态,文化正统的交锋愈加犀利。
如孝文帝时期李彪前后六次出使南齐,在折冲樽俎过之间,不仅赢得本朝“輶轩骤指,声骇江南”的评价,更赢得南朝人“奇其謇谔”的赞叹。
[3](P.1390)此后,孝静帝时期出使梁朝的李谐,在外交中同样表现出以正统文化自居之姿态。
梁朝范胥针对邺城与洛阳的地理位置变化进行嘲讽:
“洛阳既称盛美,何事迁邺?
”李谐答曰:
“不常厥邑,于兹五邦,王者无外,所在关河,复何所怪?
”紧接着范胥又问曰:
“金陵王气兆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
”李谐答曰:
“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
紫盖黄旗,终于入洛,无乃自害也?
有口之说,乃是俳谐,亦何足道!
”[3](P.1460-1461)两人你来我往,在文化正统上的针锋相对可谓不分胜负。
而北朝在文化正统论争中彻底战胜南朝的标志,当首推《洛阳伽蓝记》中杨元慎与陈庆之的对话。
《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注曰:
(陈)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
“魏朝甚盛,犹曰五胡。
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
”元慎正色曰:
“江左假息,僻居一隅。
地多湿蛰,攒育虫蚁,□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
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
浮于三江,棹于五湖。
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
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
虽立君臣,上慢下暴。
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
加以山阴请婿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
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瘿之为丑。
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
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淩百王而独高。
宜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
”[7](P.113)
杨元慎从地理位置、风俗习惯、礼乐宪章、人伦道德等各个角度,对南朝的正统性进行了严厉抨击,其结果使陈庆之等人“杜口流汗,合声不言”。
陈庆之在回南朝之后,对北朝大加赞叹,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
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7](P.114)此事可说是北朝自认在文化正统的论争中战胜南朝的一大快事。
当然,《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的北朝立场也需加以考虑,其史实的真实性值得考辨,但其中所蕴含的对于正统文化的认知转变当无疑义。
而到了北齐,南朝以文化取胜北朝的优势已经几乎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