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张继龙《阿勒坦汗与土默特》的引用问题.docx
《2张继龙《阿勒坦汗与土默特》的引用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2张继龙《阿勒坦汗与土默特》的引用问题.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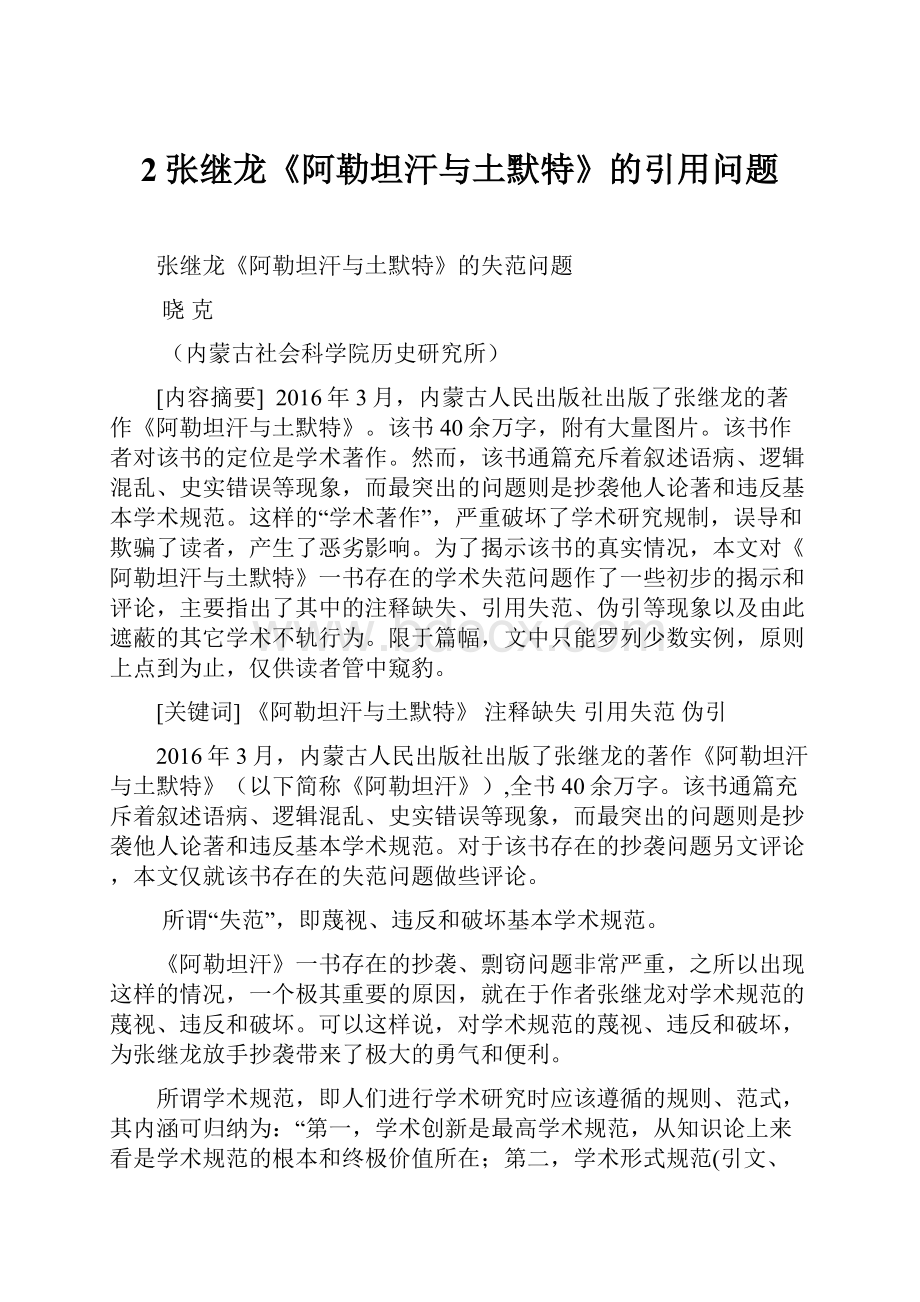
2张继龙《阿勒坦汗与土默特》的引用问题
张继龙《阿勒坦汗与土默特》的失范问题
晓克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内容摘要]2016年3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继龙的著作《阿勒坦汗与土默特》。
该书40余万字,附有大量图片。
该书作者对该书的定位是学术著作。
然而,该书通篇充斥着叙述语病、逻辑混乱、史实错误等现象,而最突出的问题则是抄袭他人论著和违反基本学术规范。
这样的“学术著作”,严重破坏了学术研究规制,误导和欺骗了读者,产生了恶劣影响。
为了揭示该书的真实情况,本文对《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一书存在的学术失范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揭示和评论,主要指出了其中的注释缺失、引用失范、伪引等现象以及由此遮蔽的其它学术不轨行为。
限于篇幅,文中只能罗列少数实例,原则上点到为止,仅供读者管中窥豹。
[关键词]《阿勒坦汗与土默特》注释缺失引用失范伪引
2016年3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继龙的著作《阿勒坦汗与土默特》(以下简称《阿勒坦汗》),全书40余万字。
该书通篇充斥着叙述语病、逻辑混乱、史实错误等现象,而最突出的问题则是抄袭他人论著和违反基本学术规范。
对于该书存在的抄袭问题另文评论,本文仅就该书存在的失范问题做些评论。
所谓“失范”,即蔑视、违反和破坏基本学术规范。
《阿勒坦汗》一书存在的抄袭、剽窃问题非常严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张继龙对学术规范的蔑视、违反和破坏。
可以这样说,对学术规范的蔑视、违反和破坏,为张继龙放手抄袭带来了极大的勇气和便利。
所谓学术规范,即人们进行学术研究时应该遵循的规则、范式,其内涵可归纳为:
“第一,学术创新是最高学术规范,从知识论上来看是学术规范的根本和终极价值所在;第二,学术形式规范(引文、注释、实证等)是学术规范的基本和核心;第三,学风和道德是学术规范存在和生效的根本和精神追求。
”“……学术规范应包含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学术研究中的具体规则,如引文出处,对引用成果的说明等;另一方面是高层次的规范,包括学术制度和学风。
”可见,学术规范最基本和核心的内容就是对论著中引文、注释符合范式的要求,抛开这个最基础、核心的要求,其它学术规范一概无从谈起。
一、注释问题
在学术论著中,注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防止抄袭实际上涉及到注释规范的问题。
……严格地说,注释是学术论文写作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注释至少包括了注明与解释两种功能。
一种是文献性的注释,其功能是注出文献的确切来源。
防止抄袭就是要把好文献性注释这一关,大凡引用了别人的观点、说法和资料,就应明确地在注释中标注出来。
”如果在注释方面作弊:
做伪注或更加恶劣的无注,就一定会为各种抄袭剽窃行为的发生留下空间,创造条件。
那么,翻开张继龙的《阿勒坦汗》一书看看,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洋洋四十余万字的书中,居然没有找到一条注释,严重违反了最基本、最核心的学术规范,并由此导致了其它严重违背学术伦理道德的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行为,突出地表现为抄袭、剽窃问题。
可以说,全书不作注释,目的就是给抄袭、剽窃留下巨大操作空间,创造便利条件。
试看一例。
《阿勒坦汗》第265页:
此时,明朝对于应该由谁来继承顺义王位也毫无主张,采取了观望
态度。
《明神宗实录》记载,“袭封一节宜俟彼大势已定,伦序已明,自
行求乞”后,才可以进行。
明朝的这种暧昧、观望的拖沓态度,客观上
为顺义王位之争留下了空间。
由于缺失了注释,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读者一定会认为这是张继龙自己做出的研究和论述,但是,参照一下《土默特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段内容来自于抄袭。
《土默特史》第203页:
此时,明朝对于应该由谁来继承顺义王位毫无主张,采取了观望
态度,认为:
“袭封一节宜俟彼大势已定,伦序已明,自行求乞”②后,
才可以进行。
明朝的这种暧昧、拖沓的态度,客观上为土默特万户内部
发生王位之争的动乱留下了空间。
原文注释②注文为:
“《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三,万历三十五年五月丙寅。
”张继龙为了隐去注释,并且达到看似与《土默特史》表述有所不同的目的,把《土默特史》的注释当作他书中的正文。
再看一例。
《阿勒坦汗》第281~282页:
四世达赖在十四岁以前,一直居住在土默特地区。
“蒙古的六大部
落每天向四世达赖喇嘛奉献的礼物像国王征收的赋税一样多。
”这是五
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四世达赖喇嘛传》中对四世达赖喇嘛在土
默特地区居住时的描述。
可见,蒙古地区当时对四世达赖喇嘛的崇信程
度。
当四世达赖喇嘛长到该拜师学经的年龄时,西藏方面希望四世达赖
能尽快入藏学习,重振格鲁派在西藏的地位。
而土默特方面一是其父母
对孩子的留恋;二是土默特方面也一心想留住灵童,借此确立自己在蒙
藏地区的权威,迟迟不让灵童上路。
后经过西藏僧俗两届的再三邀请,
加之熟悉蒙古人习俗的三世达赖喇嘛大管家巴丹嘉措的巧妙周旋,土默
特部终于同意让四世达赖喇嘛进藏拜师受戒,学习佛法。
李文君《西海蒙古史》第176~177页:
四世达赖喇嘛在十四岁以前,为了利益北方众生,他一直居住在蒙
古。
蒙古六大部落每天向四世达赖喇嘛奉献的礼物像国王征收的赋税一
样多⑤。
当灵童长到该拜师学经的年龄时,西藏方面希望灵童能尽快入
藏学习,重振格鲁派在西藏的地位;而土默特方面一心想留住灵童,借
此确立自己在蒙藏地区不可动摇的权威,迟迟不让灵童上路。
后经过西
藏僧俗两届的再三邀请,加之熟悉蒙古人习俗的三世达赖喇嘛大管家巴
丹嘉措的巧妙周旋,蒙古人终于同意了让灵童进藏拜师受戒,学习佛法。
原文注释⑤注文为:
“阿旺罗桑嘉措:
《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等译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该注释说明从“四世达赖喇嘛在十四岁以前”一句,到“……像国王征收的赋税一样多”这段叙述,引自《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一书,此后的论述是《西海蒙古史》作者自己做出的。
对照《西海蒙古史》的这段内容,来看看张继龙是如何规避注释规范而作弊的。
首先,他肢解了李文君的引文,只将后半段加上引号:
“蒙古的六大部落每天向四世达赖喇嘛奉献的礼物像国王征收的赋税一样多”,之后再加上一句貌似说明出处的话:
“这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四世达赖喇嘛传》中对四世达赖喇嘛在土默特地区居住时的描述”,不过是把李文君所做注释变成正文而已,目的就是避开注释。
还由于引号的限定,便使引号前出自《四世达赖喇嘛传》作者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话,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张继龙的话。
其次,他把李文君注释之后的论述抄入自己的书中,既不加引号,更不出注释,堂而皇之地窃为己有
二、引用问题
引用,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学术研究,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过程,必须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才可得以推进,这个基础主要由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构成,引用前人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是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经之路。
历史学研究更是离不开对文献资料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引用。
引用如此重要,在学术研究发展中,对引用的规范自然成为了学术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杨玉圣主编:
《学术规范导论》一书中,从伦理的角度对引用提出十条要求,既是学术引用伦理方面的要求,又是学术引用时必须遵循的规范。
在教育部编印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以下简称《学术规范指南》)中,专设一节对“引用与注释规范”作出规定性说明。
《学术规范导论》、《学术规范指南》要求,对于引用,必须通过规范的注释和明确的标识来体现。
而在《阿勒坦汗》一书中没有一条注释,这就必然导致该书在引用方面出现多如牛毛、不堪入目的错误和问题,甚至可以说,在《阿勒坦汗》一书中,基本上没有一处引用没有问题,严重违背和破坏了学术引用规范。
(一)对他人研究论著的引用。
引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他人研究论著的引用。
让我们首先来看《阿勒坦汗》一书在这方面是如何处理的。
《阿勒坦汗》第3页:
长期以来,“土默特”这一部落集团、万户名称,被人们作为蒙古
部落名称来追溯。
其中,有推定《蒙古秘史》中的秃马惕即为土默特
说,推定土默特源自客列亦惕部分支部落秃马兀惕或土别兀惕说,推定
土默特源自蔑儿乞部说,推定土默特源自汪古部说。
这些推定中,土默
特作为部落源自秃马惕说提出最早,影响也最大。
由此,一些人还推定
《亲征录》中的土满土伯夷,《元史》中的土伯燕、秃满、吐麻都是秃
马惕的异称。
还有的推定唐代的都波、阿尔泰鞑靼就是秃巴思,也就是
秃马惕。
还有的推定《辽史》中辽金边外的阻卜后来演化为秃巴思,也
就是后来的秃马惕,认为今俄罗斯境内的图瓦共和国的图瓦人也为由秃
马惕演化而来的民族。
这是该书开篇第二段,也是可以称之为引用的第一处引用。
其中,引用了许多学者探究土默特部落渊源的观点或结论。
在这段文字中,不仅没有见到一部相关研究论著的名称,连研究此问题的前辈或同代学者的人名也未提及一个,统统代之以“人们”、“一些人”、“还有的”等等。
如此漫不经心的引用,如此语焉不详的转述,在古今中外的学术论著中都难得一见。
它不仅无助于说明有关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反而表明张继龙对在他之前研究土默特部落渊源的学者们缺乏最起码的尊重,甚至是刻意贬低和蔑视相关学者及其研究结论。
这样的引用,严重违背了《学术规范导论》的相关要求,也严重违背了《学术规范指南》第4部分“引用与注释规范”第2节“学术引用的规则”第1项:
“引用应尊重原意,不可断章取义”,第3项:
“引用观点应尽可能追溯到相关论说的原创者”,第7项:
“引用应伴以明显的标识,以避免读者误会”,第8项:
“凡引用均须标明真实出处,
提供与引文相关的准确信息”等规则。
引用而不加以规范、必要的说明,就成为了抄袭。
例如,《阿勒坦汗》第21页:
根据蒙古文史籍记载,在达延汗去世后,巴尔斯博罗特曾经继承汗
位,但在位时间极短,不久就去世了。
《阿勒坦汗传》记载说:
“其后
使赛音阿拉克(巴尔斯博罗特的称号)三十岁时即汗位,但未及执理政
事,即为天命所夺,无奈于兔年升天之情如此这般。
”《恒河之流》中
也有他“在位一月而殁”的记载。
巴尔斯博罗特去世的“兔年”是1519
年(蒙古历黄兔年,明正德十四年)。
此时,阿勒坦年仅13岁,衮必
里克14岁。
《土默特史》第85页:
根据蒙古文史籍记载,在达延汗去世后,巴尔斯博罗特曾经继承汗
位,但在位时间极短,不久就去世了。
《阿勒坦汗传》记曰:
“其后使
赛音阿拉克(即巴尔斯博罗特)三十岁时即汗位,但未及执理政事,即
为天命所夺,无奈于兔年升天……”《恒河之流》中也有他“在位一月
而殁”的记载。
巴尔斯博罗特去世的“兔年”是1519年(明正德十四
年),此时,阿勒坦年仅13岁,而阿勒坦汗的长兄衮必里克也只有14
岁。
如此明显的抄袭,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如果从“引用”的角度分析,那么,至少在两方面违反了引用规范:
一、《学术规范指南》4.2.2小节指出:
“引用是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因此,他人文字与作者本人文字之间应当保持合理的平衡,要避免过度引用,尤其是避免过度引用某一个特定作者的论著。
过度引用指的是引用他人文字超过自己的论证,或主要观点和论据以引用为主。
”上面那段文字全部“引用”自《土默特史》,其中并无张继龙的论证,完全符合“过度引用”的特征。
二、《学术规范指南》要求:
“引用应伴以明显的标识,以避免读者误会”,“通常的引用有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直接引用需使用引号,间接引用应当在正文或注释行文时明确向读者其为引用。
”据此要求,《阿勒坦汗》一书首先应该对这段出自《土默特史》的文字做出明显的引用标识,这里显然是“直接引用”,应该使用引号,并做出注释。
但是,该书作者张继龙却没有这样按规矩去做,结果它所造成的已经不是“误会”,而是确凿的抄袭证据。
不言而喻,抄袭的目的就是把别人的劳动成果窃为己有,与偷盗无异。
既然是窃来之物,又要展示于人,就必须尽可能地对其原有的、归他人所有的属性和特征进行改动或泯灭,使之成为看似自己的东西。
而对引用规范的公然违反,与蔑视、违反注释规范一样,其目的全在于此。
《阿勒坦汗》一书中,抄袭之处数不胜数,抄袭程度令人瞠目,对这些出自他人论著的观点、论述,该书作者张继龙都是像以上举例那样“引用”的。
引用他人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相关专题研究论文的引用。
在《学术规范指南》关于“搜集资料的基本要求”的阐述中,将搜集、利用“重要研究论文”作为充分占有资料的重要方面,进行了突出强调。
通观《阿勒坦汗》一书,注释已付阙如,“参考书目”中亦不见论文篇目,在正文中,也未见任何引用他人研究论文的线索,更不用说是明确的标识。
这似乎表明,张继龙在撰写《阿勒坦汗》时,没有参考、借鉴、引用过一篇相关的研究论文。
不仅如此,张继龙连他自己的研究论文都没有引用。
原因很简单:
到目前为止,遍查“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国内权威的期刊网,没有见到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遑论研究论文。
就在这样前无古人,更无个人研究积淀的情况下,洋洋四十余万字的《阿勒坦汗》书稿,在短短十五个月内便横空出世了!
这不禁使人产生强烈的疑问:
张继龙是聪明过人,擅长于做学问?
还是他“引用”了包括研究论文在内的别人的研究成果之后,通过违反和破坏注释、引用等学术规范而将其攫为己有?
二者必居其一,答案显然是后者。
有例为证,《阿勒坦汗》第103页:
在呼和浩特东郊的辽代白塔上,留有几条这些被掳人口被掳情况和
他们本人及亲属逃回明朝的题字,分别摘录如下。
一、“嘉靖三十八年
(1559年)张鲁那在北朝丰州我与达儿汉□□[脱落,缺二字]板升□[脱
落,缺一字]下木匠张进峰[字不清楚,疑为峰字]山西汾州爱子里人氏
蔚州蛋[字不清楚,疑为蛋字]水北村主[应为住字]林[应为临字]行上□
[脱落,缺一字]达儿汉后到北朝多亏你如今众人要登[字不清楚,疑为登
字。
登在现土默特地区口语中为散、离开的意思]□[脱落,缺一字]不
由我说要留下木匠根[应为跟字]通事□□□[脱落,缺三字,应为通事
(翻译)的名字]”。
我们来对照一下李逸友先生《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一文“附录”中公布的相关题记:
使用符号说明:
原来提行加』。
已脱落或漫漶的字用□。
尚有字迹可
寻而不能确定的字注在【】内。
脱落或漫漶字数不明的用⊙。
原来错别
字加注正字在()内。
原有花押用[押]。
《出塞纪略》中载有的在题记前加※。
……
五一七、嘉靖三十八年张鲁那在北朝丰州我与达儿汉□□板升□下
』木匠张进【峰】山西汾州爱子里人氏』蔚州【蛋】水北村主(住)』林
(临)行上□达儿汉后到北朝多亏你』如今众人要【登】□不由我说要留
下』木匠根(跟)通事□□□
稍加留意便可看出,《阿勒坦汗》书中所“摘录”的题记,来自于李逸友先生的论文。
在他所“摘录”的这段题记之后,还“摘录”了李逸友先生论文中所附编号“五一四”的题记。
限于篇幅,这里不再抄录对比。
张继龙在“摘录”之际,不仅无视“引用应伴以明显的标识,以避免读者误会”,“引用须以注释形式标注真实出处,并提供与文献相关的准确信息”的规范,反而在贪他人之功为己有方面做了最大努力:
他首先给出这个题记的来源,是“摘录”自“呼和浩特东郊的辽代白塔上”,以此误导读者,言外之意是他亲自去“白塔上”“摘录”来的;其次,他把李逸友先生对该两条题记的编号“五一七”、“五一四”,改换为自己的编号“一”、“二”;接着,他把李逸友先生文章中的“使用符号说明”文字略去不引,悄然抹去了此段文字的归属特征;最后,他又大费周章一番,将李逸友先生论文“附录”中简洁明了说明校勘意思的符号删掉,代之以繁琐的文字说明,进一步使读者误以为是他对这段题记做出的识读。
然而,在如此操作之际,还是露出了破绽:
他对题记所作的每一处校勘文字说明,都与李逸友先生通过校勘符号表达的说明完全一致。
这绝对不会是偶然巧合,更不会是发生在时隔近四十年之后的巧合!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
张继龙窃取了李逸友先生及其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他扎扎实实地把对李逸友先生论文的引用作成了抄袭。
再看一例。
《阿勒坦汗》第208页:
据青海佑宁寺第三辈活佛土观呼图克图罗藏曲吉尼玛(1737—1802
年)撰写的《大德拉西扎木素师徒传承史》记载,博格达察罕喇嘛出生
于土默特大臣家族。
但该书未指明其出生年代和地点。
据传,他最初是
一个俗人,放荡不羁,举止粗暴,并不居住在村里,而是经常漂泊在呼
和浩特一带诸山谷中。
有一次,他在梦中得到一位白衣人的开导,遂即觉
悟,萌生了出家的意念,于是丢下坐骑与武器,连家也不回,就到了一
位喇嘛跟前,并在那里与修行的两位瑜伽师玛热坚与古扬喇嘛共同修行,
请求“那若六法”的深奥修习方法。
对于《大德拉西扎木素师徒传承史》这部藏文文献,张继龙照样未说明出处。
看起来,这段文字俨然是张继龙引用该文献记载而做出的叙述,其实不然。
我们来对照一下日本学者若松宽《博格达察罕喇嘛及呼和浩特的喇嘛教》一文中的叙述:
……况且,由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即土观呼图克图三世,1737一1802)
于1792年(乾隆十七年)撰写的有关博格达察罕喇嘛及其历代继承人的
传记还存在。
《大德拉西扎木素及诸辈弟子传记》(以下略称《传记》),
见《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全集》,载《GedanSungrabMinyamGyumphelSer-
ies》第2卷,第535一549页,新德里,1969年版。
……
根据《传记》,博格达察罕喇嘛拉西扎木素出生于土默特王之大臣
的家族(见537页),但是未指出其出生年代和地点。
土默特王就是顺义
王。
他最初作为一个俗人,不是安居在乡里,经常漂泊在诸山谷中,举止
粗暴。
有一次,在某地流荡累了,就在一个村里睡着了。
梦中,见一位穿
白衣、手持旗枪的人向他喝道:
“汝乃自色究竟天为众生谋利益而降斯
世者,岂可如此放荡耶?
”言毕突然挺枪向他刺来,穿透了他的身躯。
遂
即觉悟,萌生了出家的意念。
于是丢下坐骑和武器等,连家也没有回,就
到一位喇嘛跟前,受优婆塞戒(居士戒—汉译者注)。
并在那里跟从隐修
瑜伽师玛热坚和古杨两位喇嘛,请求修习“那饶巴六法’的深奥教训圆
满(见537一538页)。
张继龙所说之《传承史》,即为若松宽先生所说之《传记》。
该书收在《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全集》中,只有藏文本。
若松宽先生精通藏文,经常利用藏文资料进行相关专题历史问题研究,这在中外学术界尽人皆知。
他利用藏文《传记》对博格达察罕喇嘛所做的研究即为一例。
反观张继龙,恐怕对藏文是一窍不通。
他所引用的所谓《大德拉西扎木素师徒传承史》,无疑就是若松宽先生所引之《大德拉西扎木素及诸辈弟子传记》。
上揭张继龙所谓“据青海佑宁寺第三辈活佛土观呼图克图罗藏曲吉尼玛(1737—1802年)撰写的《大德拉西扎木素师徒传承史》记载”的内容,只能抄袭自1990年杨绍猷先生汉译的若松宽《博格达察罕喇嘛及呼和浩特的喇嘛教》一文或乔吉先生《蒙古佛教史》的相应部分。
通过上述《阿勒坦汗》一书对李逸友、若松宽先生论文“引用”的情况来看,张继龙在编写《阿勒坦汗》书稿时,曾经参考、借鉴、引用了他人的研究论文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由于未对其作出任何标识,也就自然成为张继龙抄袭他人研究论文的证据。
(二)对历史文献的引用。
引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对历史文献的引用。
《阿勒坦汗》一书在引用历史文献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1、引用二手资料。
《阿勒坦汗》第41页:
“《明史纪事本末·俺答封贡》(白话精评)记载:
……”据《阿勒坦汗》“主要参考书目”可知,这里引用的是辽海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杨旸、敬知本、田禾译评《明史纪事本末》。
无论是在第41页,还是在“主要参考书目”中,张继龙都未能正确地写出该书书名:
《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
该书的第一版是1994年由辽沈书社出版的。
显而易见,《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是在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基础上,经杨旸等人加工、改写后形成的普及性读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在史学论著中是不能引用的。
《学术规范导论》指出:
“征引历史资料,也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第一,选材要精。
其中,引原书而不引转手记载是一项绝对的征引原则。
”张继龙似乎根本不懂这个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在《阿勒坦汗》一书中,所有征引《明史纪事本末》相关记载之处,全部代之以对《白话精评明史纪事本末》的征引。
此外,《阿勒坦汗》一书引用了一些《明实录》、《清实录》的有关记载,在其“主要参考书目”中标明的版本分别为《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明实录·山西史料汇编》、《明实录类纂·河北天津卷》、《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清朝世宗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等,均属二手资料。
2、文献版本不明。
《阿勒坦汗》第2页“据《布里亚特蒙古史》记载:
……”云云。
在此处既未出注说明版本,在书后“主要参考书目”中也未见到该书的任何信息。
不知这《布里亚特蒙古史》是何版本?
是俄文原版,亦或是中文译本?
是何年、由哪里出版?
责任者是谁?
这些相关信息一概不得而知。
这样引用文献记载而不说明文献版本的现象,在《阿勒坦汗》一书中多到了不可胜数的程度。
例如,该书通篇对《皇明北虏考》、《万历武功录》、《三云筹俎考》、《卢龙塞略》、《全边略记》等许多重要明代文献的引用,全部没有标明版本,只是在其“主要参考书目”第5条中,笼统地列出: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二、三、四、五、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对于研究明代蒙古史的学者来说,可以就此推定张继龙在书中引用的上述明代文献,可能就是《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本,但是,究竟具体一部文献出自该《史料汇编》的哪一辑?
还必须一本一本地翻检。
至于该《史料汇编》的责任者、出版社以及每一辑的出版时间这些文献版本的重要信息,全部被张继龙忽略不提了。
这无疑会给读者阅读和验证史料造成不应有的困难。
较之上述,更加拙劣的是,在《阿勒坦汗》书中还引用了一些除明代文献以外的其它历史文献,如《南村辍耕录》、《蒙兀儿史记》、《皇朝通志》、《读史方舆纪要》等等,对这些文献的版本,无论是在该书正文中,还是在“主要参考书目”中,都没有给予任何说明。
3、史料出处笼统。
在《阿勒坦汗》一书中,另一蔚为奇观的现象是史料出处的笼统。
该书第87页:
“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天山)在(哈密)卫北百二十里。
……’”云云。
《读史方舆纪要》为清顾祖禹所撰,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
张继龙所引用的记载,出自其中哪卷哪册?
没有任何交待。
《阿勒坦汗》第102页:
“《明经世文编》记载蒙古地区的汉人说:
‘虏中多半汉人,……’”云云。
《明经世文编》为明人文集选编,明陈子龙等选编,504卷,补遗4卷,篇章宏富。
不知张继龙从哪卷哪册,哪篇具体的文档中找到了该条史料?
此外,还有更出格的做法,即引用史料时,只标出某个出自《明经世文编》的奏疏之名称,而对《明经世文编》却只字不提。
例如该书第7页:
“曾任明兵部尚书,被称为‘五朝元老’的马文升在他的《为驱虏出套以防后患事疏》中,称河套地区……”云云,即为一例。
该书第40页:
“在《万历武功录》的1554年条下,提到明军曾俘虏一个叫‘铁莽提桴鼓’的土默特部小头目,……”《万历武功录》为一纪传体史籍,全书共14卷,176篇,每篇中系年纪事。
不知张继龙所引“1554年条下”出自卷几?
又是来自哪篇传记?
更
不知张继龙如何从该书中找到了公历纪年?
《阿勒坦汗》第116页: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阿勒坦汗向明朝求贡经多次挫折而
不改初衷,他会集博迪大汗和侄子鄂尔多斯部首领纳延达赖济农、兄弟
昆都仑汗巴雅思哈勒,希望各部不要入犯明朝,以争取蒙古和明朝通
贡互市。
……《明神宗实录》所载这次提出通贡互市的具体情况是:
“俺
答会集保只王子、济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头目商议求贡。
……”
这里对《明实录》引用与上述对其它文献的引用一样,没有说明出处。
《明实录》是明代历朝官修编年体史书,全书共13部,2900余卷,500册,卷帙浩繁。
引用其中史料而不说明出处,不仅别人无法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