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平自述咸安政改.docx
《宋亚平自述咸安政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宋亚平自述咸安政改.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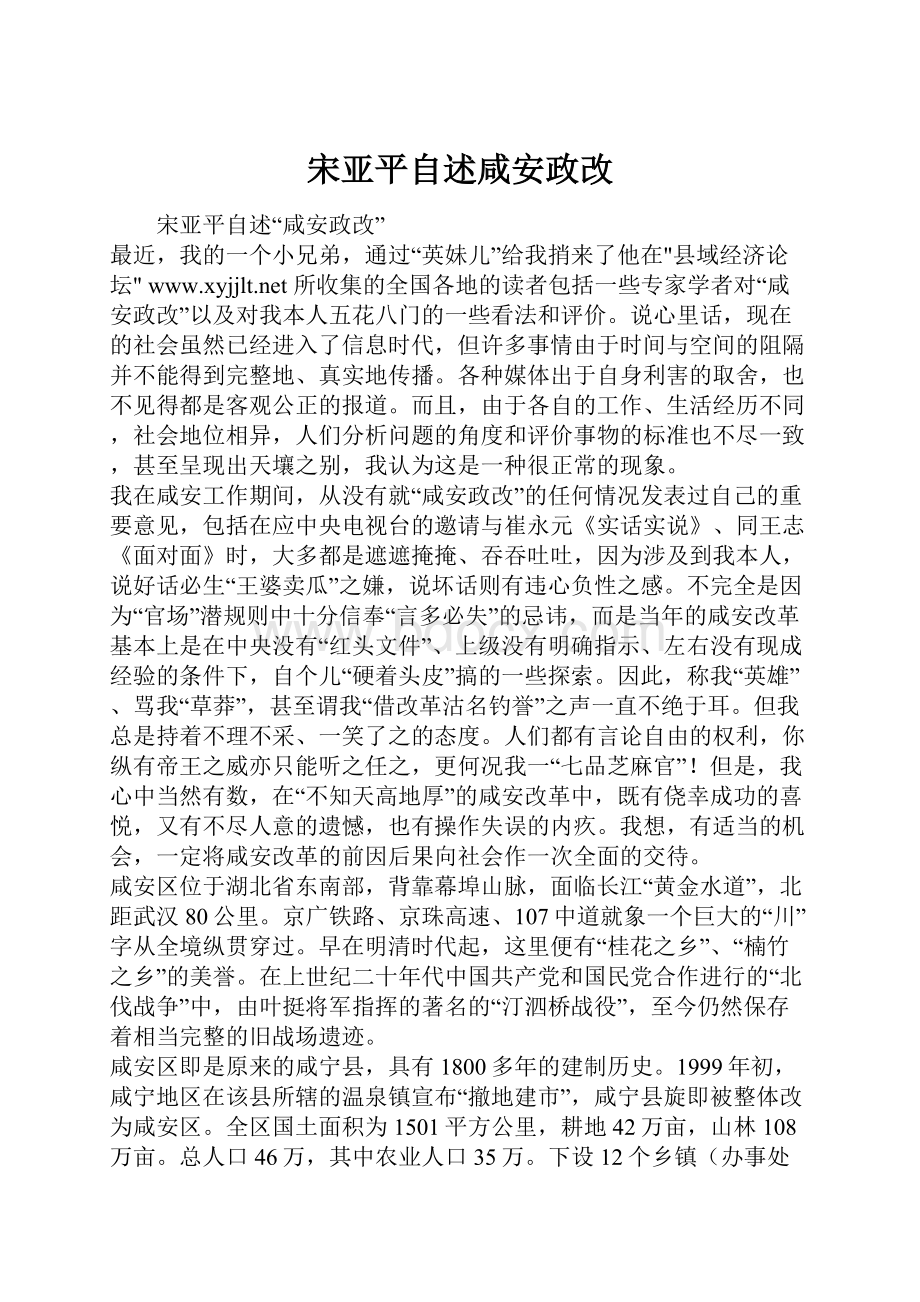
宋亚平自述咸安政改
宋亚平自述“咸安政改”
最近,我的一个小兄弟,通过“英妹儿”给我捎来了他在"县域经济论坛"所收集的全国各地的读者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对“咸安政改”以及对我本人五花八门的一些看法和评价。
说心里话,现在的社会虽然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但许多事情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并不能得到完整地、真实地传播。
各种媒体出于自身利害的取舍,也不见得都是客观公正的报道。
而且,由于各自的工作、生活经历不同,社会地位相异,人们分析问题的角度和评价事物的标准也不尽一致,甚至呈现出天壤之别,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我在咸安工作期间,从没有就“咸安政改”的任何情况发表过自己的重要意见,包括在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与崔永元《实话实说》、同王志《面对面》时,大多都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因为涉及到我本人,说好话必生“王婆卖瓜”之嫌,说坏话则有违心负性之感。
不完全是因为“官场”潜规则中十分信奉“言多必失”的忌讳,而是当年的咸安改革基本上是在中央没有“红头文件”、上级没有明确指示、左右没有现成经验的条件下,自个儿“硬着头皮”搞的一些探索。
因此,称我“英雄”、骂我“草莽”,甚至谓我“借改革沽名钓誉”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但我总是持着不理不采、一笑了之的态度。
人们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你纵有帝王之威亦只能听之任之,更何况我一“七品芝麻官”!
但是,我心中当然有数,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咸安改革中,既有侥幸成功的喜悦,又有不尽人意的遗憾,也有操作失误的内疚。
我想,有适当的机会,一定将咸安改革的前因后果向社会作一次全面的交待。
咸安区位于湖北省东南部,背靠幕埠山脉,面临长江“黄金水道”,北距武汉80公里。
京广铁路、京珠高速、107中道就象一个巨大的“川”字从全境纵贯穿过。
早在明清时代起,这里便有“桂花之乡”、“楠竹之乡”的美誉。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中,由叶挺将军指挥的著名的“汀泗桥战役”,至今仍然保存着相当完整的旧战场遗迹。
咸安区即是原来的咸宁县,具有1800多年的建制历史。
1999年初,咸宁地区在该县所辖的温泉镇宣布“撤地建市”,咸宁县旋即被整体改为咸安区。
全区国土面积为1501平方公里,耕地42万亩,山林108万亩。
总人口46万,其中农业人口35万。
下设12个乡镇(办事处),262个行政村。
虽然此时的农村人口为了符合“撤地建市”的需要已于一夜之间“跑步”进入了城市居民的行列,但“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打渔的照样打渔,种粮的照样种粮”,农业县域的“庐山真面目”几乎没有一丁点儿变化。
2002年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和省政府对县市区采取按统计上报的农村人口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咸安区因而每年少得国家补贴数百万元,干部群众大呼“吃亏”。
作为粮食主产区,咸安不仅在“以粮为纲”的计划经济时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在市场经济时期,也一直遵循着上级政府的指示,尽心尽力地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责任。
只要在县市区基层工作过的人们都知道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凡是农业大县(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县),往往也就是工业弱县、财政穷县。
多年来,咸安区便是湖北省38个贫困县之一。
1998年,咸安区本级可用财力仅为5374万元,而13,111名财政供养人口的前四项基本工资就得支出6708万元。
每到月初,区委、区政府领导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就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借贷甚至“拆东墙补西墙”凑钱给干部发工资。
许多省直机关提起咸安就头痛,就连下县市搞调研也像躲“瘟神”一样绕道走。
我是1999年7月8日从湖北枣阳市常务副市长的任上调到咸安区任区委书记的。
当时,因种种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债务如同当年“愚公先生”门前的太行山和王屋山,昏天黑地的挡在咸安发展的道路上:
农村合作基金会经营亏损3.68亿元;“普九”负债9400万元,粮食挂帐1.5亿元,党政机关办经济实体亏欠2.6亿元,财政赤字3800万元。
窘迫的财政困境非但使得党政机关无法正常运转,而且不断诱发出各种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赞助“五乱”现象屡禁不绝、层出不穷,经济环境十分恶劣。
国有金融机构视咸安为“高危地带”,投资业主则称咸安为“残废陷阱”。
为追讨“血汗钱”,不少债务人在无可奈何之下经常围困区政府大门,堵107国道,甚至冲击京广铁路,连国务院领导都于万忙之中对咸安的社会安定问题作出了专门批示。
中国有句古话“穷则思变”。
事物一旦走到了极端的地步便注定要发生逆转。
1999年也是咸安区“四大家”换届的一年。
从这一年开始,我们按照党中央的方针路线,顺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省、市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充分汲取外地经验教训,紧密联系当地实际,逐步推出了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变改府职能、改变传统领导方式方法、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建立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内容的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举措。
根本目的是化解历史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为解放生产力和经济建设的繁荣发展开辟道路。
特别是2002开始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国内许多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密集报道。
从2003年到2006年期间,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事部、中编办、农业部、计生委等中直单位和27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都先后专程来咸安考察“咸安政改”。
全国各地市县区一级到咸安“学习经验”者更是不计其数。
为此,省政府领导还专门拨款30万元,补贴咸安用于招待外省市来的客人。
一时间,咸安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和“名胜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曾多次到咸安,深入乡村农户和“七站八所”,专门就“咸安政改”特别是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进行调研,倾听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2003年11月4日,省委、省政府以咸安改革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经验为蓝本,出台了《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鄂发[2003]17号)。
2004年先在监利、洪湖、老河口、天门、麻城等7个县(市、区)进行综合改革试点,2005年又在省内全面铺开。
2006年初,省委、省政府组成36个工作组,对全省各县市区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进行检查验收。
至此,按照副省长刘友凡同志的说法:
湖北的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综合改革的主要任务基本上完成。
2003年底,我调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这里工作环境十二分的优美,绿茵茵的大草坪,华盖一样的参天古树,鸟语花香中的办公楼,仿佛身处蓬莱仙阁。
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问我适应不适应?
我听了颇为恼火,问题问得太欠水平,那小孩儿都知道啃苹果比吃地瓜有滋味,这从基层转到大衙门还能不适应?
除非有“贱骨头”的毛病!
我们这里的工作很讲究程式化,如果不是出差的话,早上8点按时上班,下午5:
30分听铃声下班,午间还可以安逸地在沙发上打个盹,睡它一个两眼蒙胧。
周六与周日照例放假休息,一般情况下,你很难在办公室的走廊里遇到一个脚步匆匆的人。
秘书处的同志启示我:
这里是省直领导机构,遇到么事都不要急,纵使是老天坍塌下来了,也自然还有“高个子”顶着。
不管怎么说,这与我在基层工作时那种成年累月的琐碎繁忙和无时不在的巨大精神压力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当然,省里与县里的管理层次不一样,对于工作人员在工作方式方法的要求上也不一样,加之专业化的分工,不能简单地认为不慌不忙就是赋闲。
但是,生活节奏明显放慢,有许多时间可以用来读书、看报、查阅资料,从而有条件将自己过去在咸安改革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问题,财政管理体制问题、金融与投资体制问题、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基础教育问题、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问题、民主政治建设与村民自治问题等等,进行一些比较系统的思考。
其实,此间全国各地正在贯彻中央关于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的方针路线,“咸安模式”已经逐步从湖北走向外省市,为许多地方所借鉴或移植。
一些专家学者和政策部门的官员也开始对“咸安政改”展开研究和讨论,并向我提出要求,希望能够以“当事人”的身份,将当年咸安改革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系统的回忆和具体的描述,也有利于澄清某些一直在流传中的误会,为人们真实地了解这场具有开全国先河意义的农村乡镇改革活动的全貌,客观公正地予以分析和评价提供条件。
我在咸安工作期间就曾经声明过的一个态度:
大家都是凡人而不是神,谁也不能保证搞改革不犯错误。
如果这场改革出了成绩,促进了咸安的发展,当然是大伙儿共同努力奋斗的功劳;倘若我们今天看起来很成功的改革却为明天的改革与发展制造了障碍(而这种事情既是难以预料的也是经常发生的),作为区委书记,我将挺身而出去主动承担祸害咸安百姓的领导责任。
香港《凤凰周刊》的记者玛雅小姐说我这是“耍滑头”。
我说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最讲究“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也最忌讳事后被人们“戳脊梁骨”。
更何况当初我还在咸安书记的任上,万一改革真的“砸了锅”,首先自然是我“吃不了,兜着走”的。
现在,我早已离开咸安了,虽然仍有许多顾虑,但毕竟心境较以前宽松。
对于咸安改革,赞赏也好,咒骂也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事情已经成为过去,是非任世人评说,成败让历史检验。
谈“咸安政改”,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革问题,而必须紧密联系县域经济、县域政治、县域社会的具体实际来有机地展开。
能不能真正地理解咸安的一系列改革活动,为什么要搞这样改革?
改革的目标和动力何在?
改革的主体是谁?
受益者是哪个群体?
受损者又是哪些阶层?
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矛盾与问题?
等等,都需要具有一定的县域工作的经历与经验,至少知道一些县域工作的酸甜苦辣,否则就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两边再怎么声嘶力竭对话,也总归扯不到一起。
在此次给我的众多提问之中,便有明显不懂县域社会基本常识,甚至坐在书斋里凭想当然后拍案而起的对县乡两级基层干部的“正义讨伐”。
在中国,县域所平均拥有的国土面积约为4000多平方公里。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简单地讲,目前世界上将近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其版图面积只相当于甚至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县那么大。
我有一次到新加坡,与几个朋友吃完晚饭后兜风,出租车带着我们沿着边境跑一圈,手中的矿泉水还没有喝完就从东北国门“逛”到了西南国门。
司机见我们游兴未尽并且很扫兴的样子,便知趣地拍了拍方向盘说:
“Sorry,不好意思!
这里可不是你们地大物博的中国,我们新加坡的全部领土只有400平方公里”。
我们听了只好友好地付之一笑,400平方公里,不就等于我们县下面一个普通的乡镇么!
中国的县不仅地盘大,而且人口多。
以我们湖北为例,人口超过100万的县,全省便有10个之多。
其中,天门以176.3万人为“大哥大”,仙桃160万人,监利144.6万人,麻城116.3万人,枣阳109.9万人,公安107.6万人,汉川106.8万人,钟祥103.5万人,浠水1024.9万人,潜江101.3万人。
湖北省县均人口为63.25万人,这个规模在全国尚只能排位“老六”,因为县均人口高出湖北的省份还有江苏(91.73万人)、安徽(76.94万人)、河南(73.75万人)、广东(73.48万人)、山东省(71.81万人),如此众多的县域人口,不说是象梵蒂岗那样针尖大的国家所无法比拟,就连太平洋上许多岛国也是不敢与之相提并论的。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现在共有2030个县和县级市。
如果包括那些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地改市”而配套设置的但在经济成份上仍然是农业为主体的“县改区”的话,全国的县、市、区则总数达到2547个。
人口规模为9.47亿,占总人口的73.3%。
县均人口为45.64万人;国土面积更是占到全国总面积的96%;2005年,县域经济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9.1万亿元,加上其它相关领域的贡献率,接近全国经济总量的60%。
可以说,县域经济占据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我们现在追求工业化与城市化,如果没有县域制度体系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县域经济发展,恐怕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从行政管理体系看,县是我们国家政权结构中最为基本的一个层次,尽管下面还辖有乡镇一级政府,但国家许多现行的政策与法律明确规定,诸如工商、税务、土地、技术监督、劳动人事、交通等等,包括计划生育工作的执法主体都不在乡镇而在县。
所以,县的管理层次虽然比较低,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几乎所有的社会事务和社会责任在这里都有着集中的表现。
我曾经在海南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那里的人们常常在饭后茶余“吹牛”的时候拿海口市的企业老板“开涮”,说某天树上突然掉下一个椰子,竟砸伤了9个总经理。
实际上,我们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要比企业老板多得多,若到了北京的“大衙门”里办事,基本上没有“科长”这一层,甚至连处长也不能算是“官”而只能算是办事员。
但是,中国的干部队伍从上到下都有相对统一的行政级别和工薪待遇,处长与县长属于同等级别的“官员”,没有大小的分界。
不过,一个县纵横几千平方公里,少则几十万人,多则上百万人,工、农、兵、学、商等各个阶层无所不有,穷人、富人和不穷不富的人们杂混其间,好事、坏事、怪事每日都在不断地发生,就像重庆的“麻辣火锅”,酸甜苦咸应有尽有,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最为完整的基础社会体系,其承负的社会责任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远不是那些机关里的处长们所能够简单地类比的。
因此,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与行政建制,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单元和管理层次。
虽然县与县彼此之间大小不一、强弱参差、特色各异,横向看来散得像一袋子互不统属的“马铃薯”,但它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就像青藏高原载着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又托着珠穆朗马峰一样,筑铸成国家这个庞杂而高大的金字塔。
所以,自古以来,历代封建王朝不论是万国来仪的盛唐时期,还是疆土广阔的前清年代,都极为重视县一级政权的社会地位。
尽管县令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论级别远不如朝廷各大衙门内的办事员,论待遇不及皇亲国戚家中的仆人。
然而,就这么个小小“七品芝麻官”,一直都是由皇帝亲自任命。
为什么?
因为一方福祸安危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就系在这个所谓“父母官”的身上。
另外,县一级的行政级别虽然比较低,但行政建制和管理职能健全,面对的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社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触和所处理的都是一些具体而复杂的矛盾事务。
所以,历朝历代选人用人的时候都十分注意“将军起于卒伍,宰相始于郡县”的原则。
毛泽东他老人家也曾经讲过,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就能当好一个省委书记。
由此可以想象,县一级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2001年,我有幸到中央学校参加第三期县委书记班的学习。
同校的“地厅级”班上有在国务院一些委、部、办、局工作的领导干部。
彼此之间来往多了便“混”得比较熟,说起话来也不像开始那样客套,甚至还可以相互开一些带刺儿的玩笑。
我记得有一次在谈及中国当前的“三农”话题时,好几位司局长们似乎是异口同声地“骂”道,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从来都是正确的,问题就在于你们这帮“狗日”的县委书记没有贯彻落实好,才形成了今天这种困难局面。
虽然说话的环境纯属“聊侃”,说话的人也未必是当真,但听话的人特别是作为县委书记的我,心里却是彻头彻尾的不服气。
在我们这个历史以来就坚守中央集权政治的国度里,县一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再怎么“胆大妄为”,也“犟”不过中央的统一号令,并只能在国家法律与政策允许的框架下行动。
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
为什么会出现政策在传递和执行过程中的走样失真?
不能说在我们基层干部队伍中就没有“歪嘴和尚”,但问题恐怕更主要是出在上面。
我们的国家有960万平方公里,不说各省的情况千差万别,就一个县来讲,各乡镇之间的情况也往往很不一样。
现在,绝大多数政策都是由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制定出台的,而且要全面覆盖960万平方公里以追求统一性。
这样就必然会因为各地情况巨大差异而导致无法贯彻执行的局面。
基层的同志因地制宜地变通一下,咋就成“歪嘴和尚”啦?
如果是这样的原因,那就该你上级政府认真检讨一下这些“经”本身是不是“歪经”,不要老是骂下面的同志是“歪嘴和尚”。
这话有些“大衙门”的领导也许不服气,那你就下来当一回县长试试!
前些年,安徽有一对夫妻作家写了本《中国农民调查》的书,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其中,还把我作为正面的典型以较长篇幅写到了湖北的农村改革。
这本书很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有关农民负担的许多具体情况,为广大人们高度重视中国的“三农”问题,促进决策层推动中国农村的税费改革可以说是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作家的生活与工作经历的局限性,他们没有更深入地透彻地去分析农民负担之所以日趋沉重的背后,有着许多不以基层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体制性、机制性的东西,而是十分武断地将责任如同倒拉圾一样几乎全部“泼”到了县乡两级政府和干部的身上。
这本书给人们的强烈感受是,当年“南霸天”、黄世仁、胡汉山等土豪劣绅不仅没有断子绝孙,而且现在的基层干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们还要坏。
按照作家的逻辑推理,因为基层干部极其恶劣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才导致了今天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剑拔弩张”的紧张。
我觉得,这本书误导了广大读者,不利于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客观判断与正确分析。
说到“三农”问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恐怕连建筑工地的小包工头都能懂,这就是:
农村是我们国家的社会基础;农业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农民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基础。
作为一个农民占人口总量70%以上的农业大国,如果农民不能富裕,农业不能繁荣,农村不能进步,这个国家的日子就无法过得顺当和安稳。
若用形象来比喻的话,如果我们过不了“三农”问题这个“坎”,县域经济也无法健康发展,党的十六大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只能是海市蜃楼或者叫做是沙漠上堆砌的大厦,最终必然是一个虚东西,和谐社会也无法和谐起来。
可能有人会认为,没吃过猪肉岂没看过猪走路!
县域是个什么玩艺,还不就是山乡农村么!
我却要奉劝这些大城市里的专家学者和“大衙门”的长官们:
千万不可小视这个“县”。
县不仅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地域基础,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社会基础。
在“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经济境况之中,县域往往就是他们生活秩序中拆不散的“篱笆墙”,知县大人则是为他们当家作主的“父母官”。
即使有能力走出家门、闯荡江湖,无论升官发财,还是漂泊海外,直到今天,人们的心目中也多以“县域”为故乡。
我们平常讲籍贯、认老乡,包括风土人情、方言语种和饮食习惯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几乎都是“县”的概念。
在中国的各种制度建设和文化传承中,县既是地域的范畴,又是亲缘的范畴,更是社会的范畴。
研究县制的演化、分析县域经济和政治的嬗变、了解和掌握那些繁衍生息在县域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生活,对于进一步推动当前的改革和开放,贯彻落实新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也许能够起到某种见微知著的作用。
“三农”问题与县域经济是一根筋上的两个“穴”,痛则连在一起痛,痒也是连在一起痒,谁也离不开谁。
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中西部地区的绝大多数县市区,他们实质上就是一体化的。
如何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一靠国家宏观政策的积极调整,二靠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创新,三靠我们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的埋头苦干。
千万不要因为别人骂我们是“歪嘴和尚”和“土豪劣绅”就委屈、就泄气、就把自己的脚包成“三寸金莲”而不敢再挪动半步。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也是我们咸安政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
现在,我们有些县市的同志经常跑到武汉,甚至跑到上海、北京的一些大学、研究院或什么中心去请那些经济学界所谓著名的专家学者来作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划与政策咨询,看起来好像在走科学决策的程序,实际上“做秀”的意义大于客观效用。
我个人认为,不要去迷信那些经济学界的“精英分子”。
我们国家的股市多年来一直遭受人们的唾骂,成为广大小股东伤心的“献血”地和某些社会阶层暴富的“金矿”区,事已至此,铁证如山了,不是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仍在拚命鼓吹吗!
吴敬连老先生在经济学界显然属于另类,他的良心驱使他对中国股市说了一点直话,很多“精英分子”便“老虎屁股摸不得”,立即群起而攻之,甚至把“文革”时期搞阶级斗争的那一套办法重新端了出来,让我们对很多专家学者的权威性生出了些许的疑心。
曾经有人问过我:
咸安的改革比较系统,是不是事前已经做了充足的理论准备?
我回答说:
当然有,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拥有知识产权的“摸着石头过河”理论。
此人不服,认为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用手摸不着石头了。
我说,那好办,再找根竹竿继续探索不就得了么!
“理论”这个东西并不只有城市和高层才能生产,也不是大专学校和研究院所里的那些教授、研究员们才能够拥有的专利产品。
过去,我们基层干部一听“理论”两字便自惭形秽,肃然起敬,觉得深不可测,高不可攀。
后来慢慢地发现,所谓理论其实就是对于社会事物的深入思考和对实践活动的理性总结。
把它搞得那么复杂与深奥,多半是故弄玄虚来吓唬我们基层干部和老百姓的。
现在看来,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并不是真本事,如果把复杂的理论简单化,让广大老百姓都够明白领会,那才叫做真正的本事。
对于我们工作在县一级领导岗位上的同志来说,县域经济的情况非常复杂,既有带普遍性的东西,也有很多各自的特殊性,千万不要指望别人能够给你一个现成的包医百病的“药方”。
我们长期工作在基层,对县域情况有着极为深刻的了解,这是绝大多数从事理论工作的专家学者们所无法拥有的巨大优势。
如今的县一级领导同志一般都经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只要下了真功夫,就会山不转水转,路不转云转,“再远的路程,也能走出那道弯”来。
所以,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心。
我个人的体会是,即使是专家学者的意见,或抑是外地行之有效的经验,也必须紧密结合本县域的实际,自己思考,自己琢磨,走自己看准了的路子。
记得当年在发展县域经济的问题上曾经有两种模式,一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地位的“苏南模式”,一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
苏南模式通过国家主流媒体的宣扬而被各地所广泛学习,温州模式则因为“不合时宜”而遭遇普遍抵制。
结果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温州模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形成“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时代大潮。
咸安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对破解当前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难题提供了某种借鉴作用,因而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和移植其经验的过程中把它称之为“咸安模式”。
说实话,我不大喜欢动不动就称“模式”,这并不是说县域的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就不存在一些带普遍性质的活动现象和具有规律性的一些东西,而是中国之大,县域之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即使在咸安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并不见得在其他县域就能够生根、开花、结果。
所以,一个地方到底怎么改革才好,绝对不能照搬照抄别人的办法,而是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紧密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来决定。
在这本文章中,我主要是针对咸安的改革情况,尝试对“三农”问题和县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作一些思考和总结。
由于智商不怎么发达,加之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毕竟十分有限,不敢说也不能说这些散发在文字中的思考和总结都是正确的,更不敢也不能说在理论上有什么高度和建树,只能作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提供给仍在县市区工作第一线的同志们和那些对县域经济和农村问题研究有兴趣的同仁们作为参考资料,希望能够得到社会上善意的批评和指正。
一、初到咸安
我的个人经历极为平凡:
宋亚平,男,1957年11月9日出生于湖北省赤壁市。
小学肆业,11岁给生产队放牛养鸭,后来到社办企业护林种茶。
开过拖拉机,当过大厨师,还荣获过人民公社文化站举办的群众文艺小品创作一等奖。
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86年项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工作。
旋即辞去公职,南下广州务工。
也许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发现我有点不大“正常”。
按照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正厅级巡视员的李传青同志的描述:
宋亚平似乎有着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总是不按常规“出牌”。
当许多人受“官”念驱使挤向党政机关的时候,正在“仕途”中一帆风顺的他却毅然辞职“下海”,孤身赴广东打工;当一些莘莘学子挡不住“外面世界真精彩”的诱惑而纷纷南下经商炒股的时候,他却“洗脚上岸”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面壁三年潜心攻读博士研究生;当房地产狂潮席卷天涯,大批“淘金者”携巨资抢渡琼州海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