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及其电影改编《布拉格之恋》的互文研究.docx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及其电影改编《布拉格之恋》的互文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及其电影改编《布拉格之恋》的互文研究.docx(2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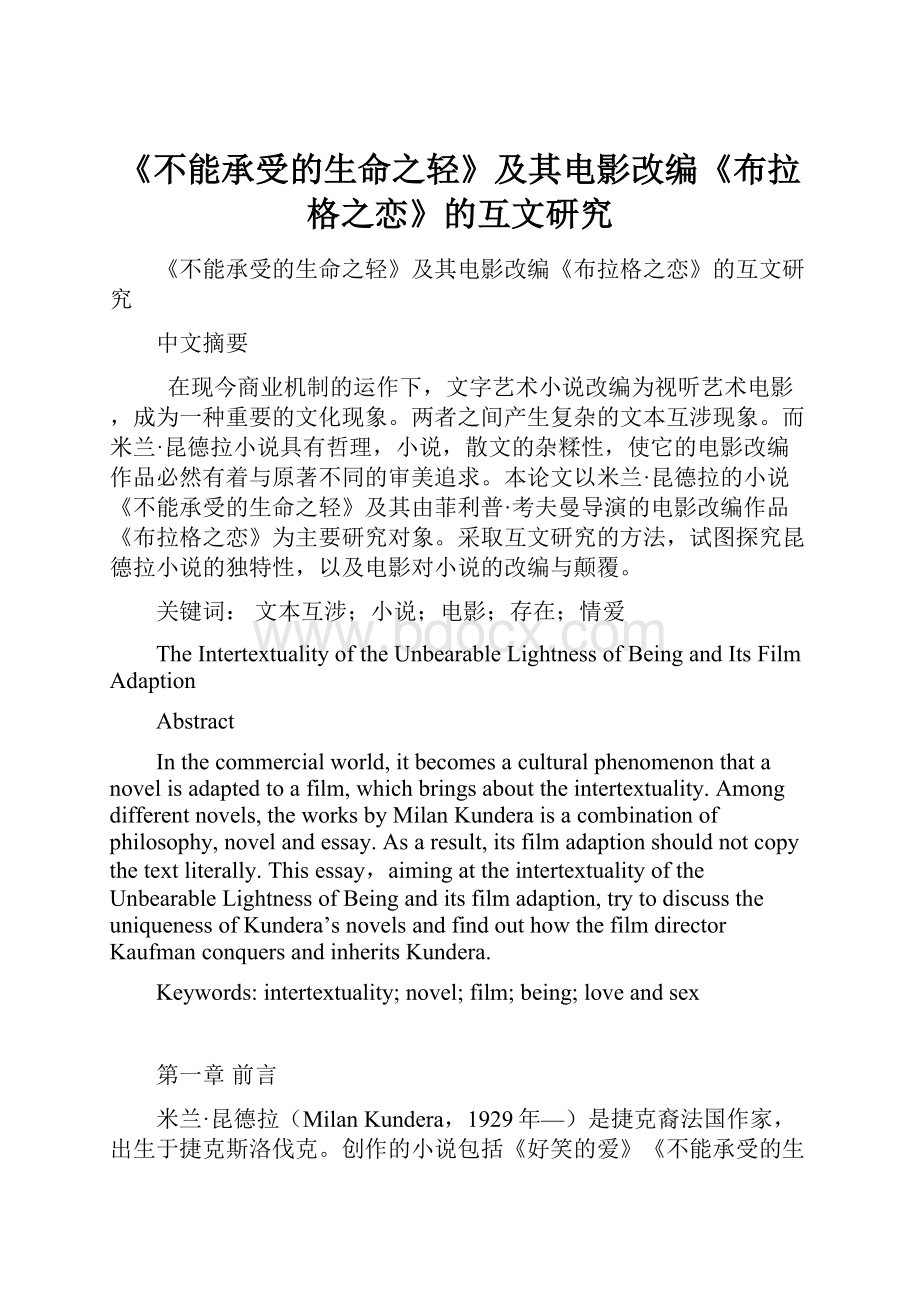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及其电影改编《布拉格之恋》的互文研究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及其电影改编《布拉格之恋》的互文研究
中文摘要
在现今商业机制的运作下,文字艺术小说改编为视听艺术电影,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两者之间产生复杂的文本互涉现象。
而米兰·昆德拉小说具有哲理,小说,散文的杂糅性,使它的电影改编作品必然有着与原著不同的审美追求。
本论文以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及其由菲利普·考夫曼导演的电影改编作品《布拉格之恋》为主要研究对象。
采取互文研究的方法,试图探究昆德拉小说的独特性,以及电影对小说的改编与颠覆。
关键词:
文本互涉;小说;电影;存在;情爱
TheIntertextualityof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andItsFilmAdaption
Abstract
Inthecommercialworld,itbecomesaculturalphenomenonthatanovelisadaptedtoafilm,whichbringsabouttheintertextuality.Amongdifferentnovels,theworksbyMilanKunderaisacombinationofphilosophy,novelandessay.Asaresult,itsfilmadaptionshouldnotcopythetextliterally.Thisessay,aimingattheintertextualityof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anditsfilmadaption,trytodiscusstheuniquenessofKundera’snovelsandfindouthowthefilmdirectorKaufmanconquersandinheritsKundera.
Keywords:
intertextuality;novel;film;being;loveandsex
第一章前言
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1929年—)是捷克裔法国作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
创作的小说包括《好笑的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等等,文学批评著作包括《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
昆德拉从小就受过多方面的艺术熏陶。
青年时代的昆德拉写过诗和剧本,学过哲学,画过画,搞过音乐并从事过电影教学,是捷克新浪潮电影的探索者之一。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曾在艺术领域里四处摸索,试图找到我的方向。
”最终,他选择了小说作为他终身事业。
昆德拉总是在广阔的哲学语境中思考问题,但并非以纯哲学的方式,而是用小说的方式,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
昆德拉善于以反讽手法,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
他的作品表面轻松,实则沉重;表面随意,实则精妙;常常在抵达高潮之际又倏尔笔锋一转,进入非线性、非理性的情节。
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叙事往往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戏剧性经常断开。
叙事者的无处不在的议论与插话让读者无法专心投入故事。
昆德拉所写的故事既非跌宕起伏,也不是惊心动魄,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有很大区别,读者更多的是在叙述者的议论中体悟出小说的主题。
1984年,昆德拉发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这是他移居法国后发表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小说以“布拉格之春”及1968年苏俄入侵捷克为背景,讲述了人生的种种困境与矛盾,包括极权对个人自由的毁灭,个人在轻与重之间的徘徊等等。
1988年,好莱坞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搬上大荧幕。
由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掌镜,虽然是好莱坞导演,但考夫曼同时带有欧洲电影学院派气质,其改编也带上浓浓的欧洲文艺电影风味,而非单纯的好莱坞模式的成品。
并由几位欧洲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MichaelBlakeDay-Lewis),茱丽叶·比诺什(JulietteBinoche),和丽娜·奥琳(LenaOlin)主演。
本片也获得了1988年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的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英国学院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等,1989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和最佳摄影奖的提名,另外也被美国电影学会评选为美国电影史上100部最伟大的爱情电影之一。
由小说改编为电影,涉及到文本互涉现象。
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也称为互文性,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提出,指的是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它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
因此,任何一个文本,都会与其他的文本产生互涉现象。
尤其在小说及其电影改编中,两者构成共同叙事,具有很强的互文性。
这两部作品相继产生并在各自领域获得激赏,在当时引起了评论界的热烈讨论,直至现在,依然反响不断。
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说及其改编电影的研究中,已经有了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成果。
综合来说,研究重心主要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昆德拉小说的不可改编性。
昆德拉的小说具有深刻的矛盾性,他笔下的人物皆是服从于对主题的探询而非对传统小说通过情节塑造人物性格,因而很多评论家认为电影仅仅靠情节的推进无法表达出小说的深刻矛盾性。
另外,也有评论家从电影自身的审美追求出发,认为电影重新诠释了小说的核心内涵。
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都将其重心放在电影情节与原著的比较,较少涉及导演是如何通过拍摄方式、场面调度等电影手段来改编原著的,因此,本论文将让电影对小说的各方面改编都纳入论述范围。
在电影里,有着欧洲艺术电影中一贯对“性”的大胆表现,情节中包含偶然的奇遇场景,大量的梦境、幻觉与留白,让我们看到小说的艺术性在当代商业影视运作中的可能性。
本论文将在具体的文本与影像间展开,旨在研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及其电影改编《布拉格之恋》,针对电影对小说中情爱,政治,存在主题的影像再现,比较在小说的主题中,有哪些部分被电影放大,哪些部分又被消解或扭曲,并分析其成因。
运用互文研究的方法,探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的共性和差异,电影是如何运用镜头语言表现小说这种文字艺术,以及两者各自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取向是否相同。
第二章小说叙事到电影影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影对于长于叙事的小说来说是一种冲击,电影作为视听兼备的叙事艺术,能够将小说用文字所描述的作为物象呈现为形象性叙述。
尤其对那些具体场景中的细节,电影可以将各种内涵蕴含在一幅画面中,甚至可以让某些情节具有预兆性。
而在20世纪,对小说内涵和形式的创新,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代小说已经不再局限于讲述完整的故事,追求情节的曲折起伏,而是有了自己新的“法则”,像对潜意识的呈现,碎片化的叙事,对变型世界的描绘。
米兰·昆德拉正是“革新派”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说与传统的长于“说故事”的小说有明显不同,主要的两大特点是强烈的思辨色彩以及先锋的艺术特色,它像一个“大熔炉”一般,借助各种叙事技巧,在小说中表达他的思考,包括哲学的,政治的,文学的,社会的,人性的等等。
在与他同时期的小说家中,米兰·昆德拉也显得十分另类,他将哲学话语置于具体情境中,在他的艺术蓝图中,小说是一种“最高的智慧综合”。
昆德拉反对作家在小说中努力虚构出来的真实性,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他告诉读者:
小说人物并非诞自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境,一个语句,一个隐喻,在《不朽》中,他直白的表示,阿涅丝诞生于老妇人挥手的姿势。
在他的笔下,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一次筑梦之旅。
小说中的人物并非社会中确证的人,而是用来探询存在的一系列符号,是在游戏与假设中构成的“人的可能性,一种存在的基本方式”。
在叙述中,作者超越个体的生活时间限制,运用复调叙事,使小说人物听控于作者的调令,作者可以随时插话、阐释,甚至与小说人物对话。
而各种叙事手段的运用,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叙述性的还是思考性的,都离不开对小说主题的把握,它们共同旨归于对“存在”各种可能性的思考。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作者将每个人物作为“实验性的自我”,分别打上标记,像组成特蕾莎的关键词分别是:
身体,灵魂,眩晕,软弱,田园牧歌,天堂,托马斯则是轻与重,通过这些“密码”在具体生活的处境和行动中照亮人的存在。
昆德拉并不想以哲学家的方式来从事哲学,而是以小说家的方式来进行哲学思考。
他不想要证明什么,他要做的仅仅是研究问题﹕存在是什么?
嫉妒是什么?
轻是什么?
晕眩是什么?
媚俗是什么?
因此,昆德拉通过自己的实践对小说的“合法性”进行了新的规定,明确小说的本体特征到底是什么,明确什么才是小说独有、而其它体式无法替代的。
他试图重新为小说立法,这也正是他所说的:
“发现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
”
对改编问题,昆德拉持审慎态度,而且由于昆德拉小说的独特性,包括大段大段的抽象论述,跳脱故事情节的哲学思考等。
其电影改编不可能按照原著的风格进行对等的表现,也无法对原著进行解释性的阐述,而是要让原著精神折射在荧光幕上,通过光影来影响观众的心理反应,给予观众同样的想象空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的改编是及其困难的。
对于情节淡化的小说,故事性就相对减弱。
电影在叙述时往往会运用各种非叙事性的元素来构筑电影结构,例如象征,隐喻,视觉冲击等等。
这些我们在《布拉格之恋》中都可以看到。
而且,除了从文字到镜头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差异外,电影的“新作者”导演,还包括商业机制下的制片,编剧对小说的解读也会对改编产生新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看,随着对电影改编的研究发展,小说不再是改编电影唯一的最高范本,忠于原著并非评价电影的最高标准。
有的电影仅仅借助小说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而进行属于电影的大胆颠覆。
尤其对于电影来说,历来有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之分,主要差异在于,商业电影因袭好莱坞的模式,以营利为目的,迎合大众口味,为吸引观众眼球,会掺杂色情、暴力、悬疑、爱情等元素;艺术电影则与世界电影美学思潮相关,追求影片的艺术内涵,往往带有导演个人风格,表达导演个人情感。
由于《布拉格之恋》对小说艺术及思想内涵有所继承,电影本身并非单纯的娱乐产品,从导演叙事来看,这部长达171分钟的电影更偏向于一部艺术电影,但其中也不乏有对商业电影的妥协。
因此,电影作品不再从属于米兰·昆德拉,而是作为制片、导演、编剧的独立作品展示在观众面前。
对电影来说,首先,它的主题与欧洲有着紧密联系,从导演叙事手法看来,也带有欧洲文艺电影特色,其次,从电影的呈现与运作来看,电影是作为一部好莱坞式的作品首先展现在美国人面前的。
因此,电影本身的双重性也为改编带了悬念。
由此,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一个是通过语言运作,一个是通过一系列镜头记录下物质世界的原材料运作。
作为两个独立的叙事单元,两者之间形成复杂的文本互涉现象。
接下来,本论文将具体讨论考夫曼的电影对昆德拉小说的继承与颠覆。
探讨在影像的再现中,是否能够发现小说中对“人类存在”悖论的探询,是否能投射出米兰·昆德拉独到的审美与思想追求。
小说中以情爱、政治探询人类存在的主题又是否能在电影中复现。
2.1存在之思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借科学理性主义带来的“单边危机”来阐明了自己的小说观。
他认为,纯理性的科学使人陷入“对存在的遗忘”。
“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
”而小说则是让人们对存在进行勘探。
像在《小说的艺术》中,他写道:
小说并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
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
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的可能,画出“存在的图”。
而在《帷幕》中,昆德拉进一步表示,人的存在是一种普通而真实的状态,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琐碎、平凡甚至是无意义。
可见在米兰·昆德拉眼中,世界没有唯一真理,它的本质就是相对性,他的小说并非要探询出“究竟什么是存在”,他肯定的是探询本身,他希望在模糊而真实的状态中探询世界的本质。
在一次访谈中,昆德拉指出: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设的。
我是小说家,而小说家不喜欢太肯定的态度。
”这种探询与世界的本质具有一致性——总是并必将以一个悖论式的不满足而告结束。
面对这个巨大的悖论,人们总是习惯用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回答,昆德拉在《昆德拉访谈录》中说人的愚蠢就在于有问必答,小说的智慧则在于对一切提出问题。
昆德拉对存在的探询,是通过对个体生存的非理性和不确定性来指向存在的各种可能性。
在他的每一本小说中,在《好笑的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到后来的《不朽》,这种探索不断深入、走向极致。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使用了大量非理性因素,它们对小说人物在个人的重大决定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揭示出“轻”与“重”界限的模糊性。
当特蕾莎下定决心脱离过去的生活来找托马斯时,昆德拉展示的并非特蕾莎疯狂的爱,而是因为一路上没有吃东西肚子发出的咕咕声,两者的反差粗暴地将理想主义中“灵”与“肉”的统一彻底割裂。
既然小说探询的是人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昆德拉小说的重心自然就不是对情节、人物的雕琢,而是主题。
他认为一个主题就是对一种存在的探询,这种探询建立在一些主题词上。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其中的“生命”一词,在原文中其实是更为抽象的“存在(being)”。
具体地说,该小说探询的是“存在”的“轻”与“重”问题,旨在凸显“存在”的不确定性。
小说将“存在”放在各种具体场景中进行反复的演绎,因此需要经过作者的“造境”来加深小说中的“存在”意识。
小说人物在各自的选择中显示出非理性、非逻辑的一面,从而找回被“理性世界”被剥夺的生命的丰富性。
“存在之轻”正是在作者这种非理性、非逻辑的调度中得以实现。
作者将一切可能性放在小说人物面前让他们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无可复制、不能比较,有时候追求意义的选择却得不到预期中的沉重感,像第六部分“伟大的进军”,正义的和平运动在昆德拉笔下变成一场闹剧,弗兰兹死于街头斗殴与他前往柬埔寨时深重的历史责任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观托马斯无止尽的“性游戏”又让他陷入沉重的对特蕾莎的思念。
在“轻”和“重”之间游走,从一个极端转化成另一个极端,到达了极点的“轻”就变成了可怕的“轻之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主题正是建立在重、轻、灵魂、身体、粪便、媚俗、眩晕、力量、软弱等主题词之上,通过轻与重,灵与肉,美与丑,自由与极权,可笑与严肃各种对立之间的各种可能性,实现对“存在”的探询。
然而昆德拉拒绝明确性,他笔下的“二元对立”并非传统意义上“二元世界”的对立,而是在“二元对立”之间寻求不确定性,这使得他在书中的表态变成一种质疑式商榷式的发问,书中的人物游走在两极之间,进行对存在的各式探询。
2.2电影中存在意识的流失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米兰·昆德拉写于1984年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四位主人公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弗兰兹面对生命的各种困境时,由于无法确证自己想要是什么,也无法检验或修正自己的抉择。
从而,他们每一个人在做抉择时都基于各自对存在的看法。
托马斯渴望叛逃必然,特蕾莎追求灵魂的重量,萨比娜抵制媚俗,弗兰兹想象活在萨比娜赞许的眼光下。
再者,书中以“布拉格之春”及1968年苏俄入侵捷克作为背景,但昆德拉对历史的建构不是单纯地批判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对人性的戕害,不是一种忏悔,而是为了审视人类存在,重视的是历史的存在价值。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时时让笔下的主人公处于模棱两可之中。
特蕾莎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灵与肉,是像自己一直认为的那样,肯定灵魂对肉体的支配,还是像托马斯一样,将灵魂和肉体分离。
有时候,即便是做出了选择,也可能让人物陷入与原初意愿相悖的境地。
萨比娜从孩提时代就渴望背叛,脱离原味,投入未知,但她知道这样的背叛有朝一日总会走到尽头,于是对背叛的陶醉就会变成惶恐不安。
在小说里,为了最大限度地凸显存在的境遇,人物的选择超越了线性的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了说明“存在”的本质往往是充满悖论、非线性、非逻辑的。
为了说明事物的不确定性,昆德拉还用了编撰词典的方式,专门设置了第三部分“不解之词”,讲述某些意义确定的词语对萨比娜和弗兰兹之间的不同内涵。
从电影对小说的改编来看,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再创作活动。
“改编电影不断地解构与建立那些被引用的素材,减缓了感觉的调整与调节的速度。
在这个减速过程中又补充进了图像媒介特有的感官效果。
”再创造的过程势必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误读,而导演菲利普·考夫曼发挥了他一贯的针对电影提炼主题的功力,从篇幅上来看,电影选取了小说中约一半的内容,删去了小说中的哲学成分(主要集中在第三部分“不解之词”和第六部分“伟大的进军”中)和小说中的几个人物:
如托马斯的妻儿,特蕾莎的母亲,对弗兰兹也只保留了他和萨比娜在瑞士交往时的一段,更多的着墨于几人之间的“爱情线索”,从而将昆德拉存在主题简化。
但对导演来说,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欲望的爱情选择,考夫曼将他的电影构建成与原著相同的二元对立上,围绕着“轻”与“重”的主题,将电影展现在病态与活力,美丽与丑陋,自由与极权之中。
将原著中的若干哲思包含在电影画面中,由此将零散化的叙事集中起来,增强了故事的连续性。
这样的改编也让我们看出其改编标准除了小说以外,还包括其他的因素,另外,昆德拉笔下的人物、事件、哲思、叙事方式与商业电影的不相融也是造成这样情况的重要原因。
除去电影中删减了作者出场时所进行的哲思,而就故事本身的具体呈现上看,电影与小说相比,存在之思的流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不确定性”的关注,包括对事件偶然性的去除,和对历史的呈现方式上。
在小说中,各种人物的选择与场景的延续并非为了情节的延续,作者将人物的非理性选择,历史中个体的感受,这些看似与事件无关紧要的因素加以放大,使之变得强烈,而电影中偶然性与非理性的消失与扭曲,正是电影存在意识流失的关键因素。
再次,在叙事方式上,电影也用连贯性取代了小说的复调叙事。
也是使存在意识消解的重要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小说中的几个核心主题在电影中的呈现,审视电影自身具有的重建功能。
2.2.1情爱解读:
灵肉调和与轻重之间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昆德拉就发问:
重便真的残酷,轻便真的美丽?
于是,他解释了何为“重”、“轻”: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有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托马斯身上的“轻”,集中体现为他的“性友谊”中,在这一方面,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通过对情爱的描写,将“灵”与“肉”是背离还是调和的问题置于重要的位置。
如果仅凭借所谓放荡的猎艳行径,根本涵盖不了托马斯的生生死死以、悲欢离合。
因此,小说和电影,都对情色作了延伸和隐喻。
在遇见特蕾莎之前,托马斯一直追求轻盈自在的生活,追求他所谓的“性友谊”。
对他来说,爱情过于沉重。
直到遇见特蕾莎,他的规则第一次受到了质疑,而这种质疑来自于他自己对内心的追问。
对托马斯而言,特蕾莎的到来是一次不期然的偶然,特蕾莎住的小镇偶然发现了一起病症,原本接诊的主任偶然生病、派托马斯代他前往,托马斯偶然在特蕾莎打工的旅馆下榻,他又偶然趁离回布拉格还有一段时间进了旅馆的酒吧,特蕾莎又偶然当班,偶然为托马斯所在的那桌客人提供服务。
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他对特蕾莎产生的无法解释的爱和那个产生爱情的隐喻“她就像是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流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
”昆德拉将这种爱归结为“同情”,因为同情,托马斯不忍让弃儿卷入狂暴汹涌的江涛而搭救,这个单纯的女孩让托马斯在终日无爱的性漂泊闻到了“莫名的幸福的芬芳。
”不可解释,却又无法拒绝。
在电影里,乍看之下,托马斯在一开始就表现出猎艳者的姿态,特蕾莎的初次登场也与书中的让人怜悯的女招待形象不尽相同:
特蕾莎向泳池中纵身一跃,激起的水花搅乱了一旁下棋人们的心,也包括托马斯的心,此时,背景音乐响起雅纳契克晚年的钢琴曲《荒烟蔓草的小径》中的《弗丽德卡的圣母》,代表了特蕾莎纯洁的躯体。
托马斯看着特蕾莎像美人鱼般在水里游动,深邃的眼睛绽放出锐利的光,电影通过长时间对女性身体形象的展示来暗示特蕾莎对托马斯“性吸引”,导演用特蕾莎在更衣室换衣服的剪影诗意地叙述了这种吸引。
再往深一层看来,托马斯和特蕾莎相遇的地点是在温泉小镇的疗养院中,特蕾莎轻盈的体态置于众多病态的身体中是及其突出的。
泳池中,托马斯在观看一群下棋的人,他们围着毛巾,体态臃肿,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特蕾莎曼妙的身姿才引起了注意,随后托马斯立即跟上特蕾莎,电影里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表演这段跟随的戏。
在疗养院中,周围是笨重、病态的人们,托马斯在走过每间病房时,镜头都不忘扫过每间病房的情境,在视觉上,病人们裸露着身体,但完全没有美感,只是在等待着治疗,在听觉上,观众能听到疼痛带来的各种呻吟声。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特蕾莎像出水芙蓉一般遗世而独立。
到了咖啡馆,导演对有了特蕾莎的第一次特写镜头。
镜头的转换代表两人交错的视线,对两人初次见面导演重点表现了“书”,就像小说中说的,书是特蕾莎“进入托马斯世界的通行证”。
在电影里,一个长镜头跟随着特蕾莎的眼睛环视整个咖啡馆,有人下棋、有人看报、有人听广播,最终目光落在托马斯身上,只有他和特蕾莎一样,手中捧书。
书将他们两人与众人分离,在这个住满病人的疗养院中,影射出当时社会的病态,在这个病态的社会中,两个年轻人的互相吸引仿佛不再昆德拉笔下的“偶然”,而是必然的。
可见,对两人相遇的描述,书中将两人爱情的基础归结为“六次偶然性的结果”,并接着“偶然”大谈特谈“偶然事件”在生命的重大意义,正是这种非必然的事件,才让人的生命变得丰富。
而在电影里,随着每一处情节的落实与展现,让观众看到“美”与“丑”,“活力”与“病态”的对立,导演抹去了情节中的哲学意味,而是致力于在故事叙述上层次更加丰富,更加饱满,显示出自己的审美追求和独立于昆德拉的批判意识。
事实上,对情爱的展现,电影情节基本上忠实于原著的描写,几乎每一处情节都能在原著中找到相应的章节。
当特蕾莎住进托马斯家以后,托马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的女友们抱怨他违背了不让女人在家里过夜的法则,他自己也无法因为专情于特蕾莎而放弃他的性友谊。
托马斯通过对“睡觉”与“做爱”的区分表达出“灵”与“肉”的分离。
在电影里,托马斯在一开始就对萨比娜表示,对女人的追逐是为了找到那些微小的不同。
在小说里,由作者直接发问:
他在所有女性身上找寻什么?
她们身上什么在吸引他?
肉体之爱难道不是同一过程的无限重复?
不。
托马斯追寻的不是重复,而是变奏,他追寻女人身上百分之几难以想象之处。
这就是个人的标志,是人类的独特性。
托马斯试图在肉体的无差别中探索肉身的个性化差异。
这就构成了小说中对爱情的隐喻,托马斯实际上“追逐女性的不是感官享乐(感官享受像是额外所得的一笔奖赏),而是征服世界的这一欲念(用解剖刀划开世界这横陈的躯体)。
”因此,这更是一场对极权、对确定性的抗争。
托马斯一再地说服特蕾莎,他与多个女人风流与他对特蕾莎的爱情并不矛盾。
对于特蕾莎而言,由于母亲的关系,她一直渴望与众不同,所以她离开家庭,来到托马斯身边,期盼获得托马斯的爱,她觉得是托马斯将她的灵魂从她体内深处召唤了出来,但托马斯的风流又让她害怕托马斯将她丢回众人之中,失去身体的独特性。
在小说中,通过特蕾莎一系列的梦魇表现她的恐惧。
梦到猫,代表她感到女人的威胁,梦到死后的事情,她害怕肉体独立于灵魂,梦到泳池旁边走边唱等待死亡,代表她害怕托马斯像对待其他女人的身体一样对待她,梦到在画室看到里托马斯和萨比娜做爱,她的内心极其痛苦,却希望能够用肉体之痛代替心灵之痛。
而在电影里,由于时长的限制,将特蕾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