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唐传奇.docx
《第四章 唐传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四章 唐传奇.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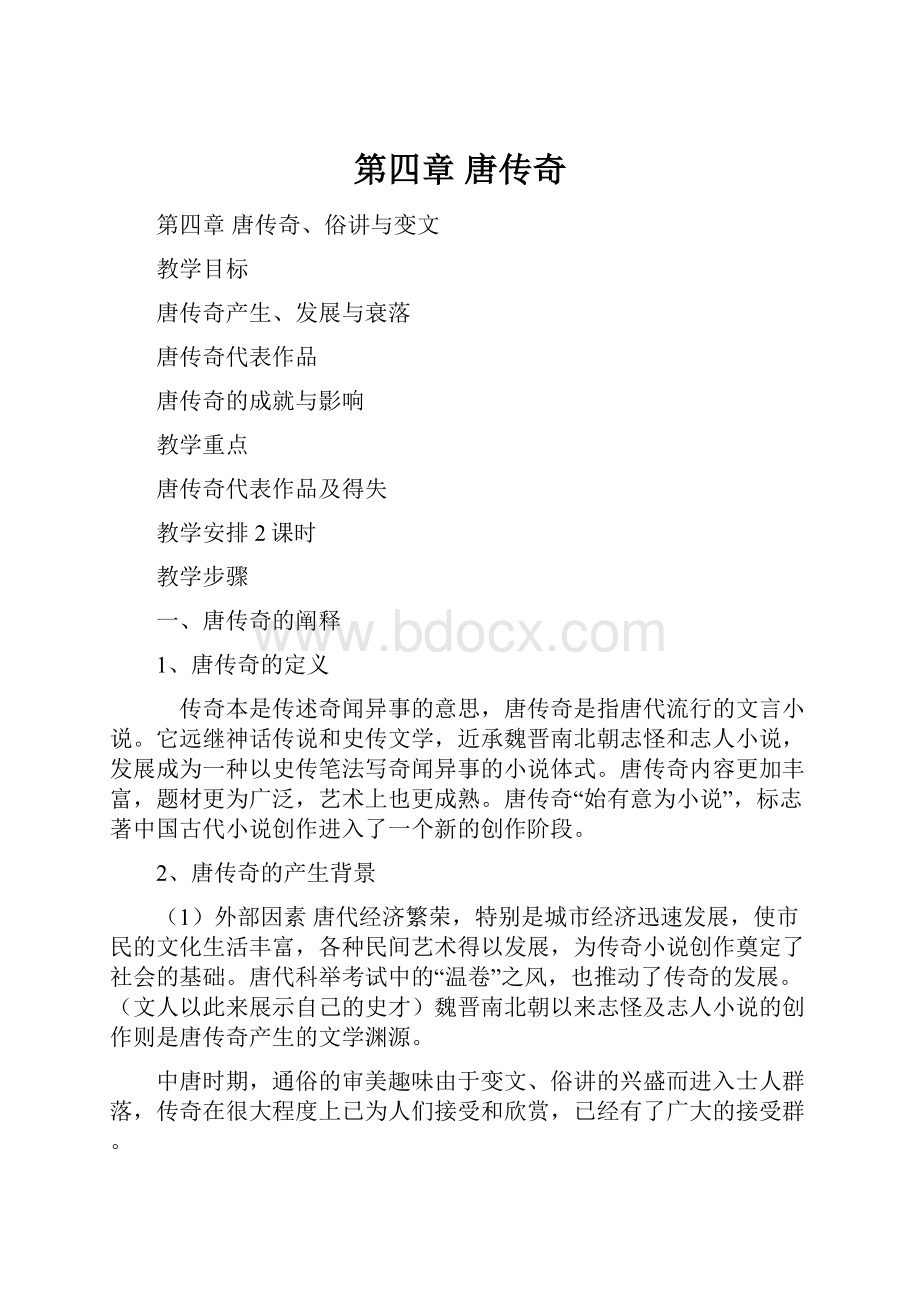
第四章唐传奇
第四章唐传奇、俗讲与变文
教学目标
唐传奇产生、发展与衰落
唐传奇代表作品
唐传奇的成就与影响
教学重点
唐传奇代表作品及得失
教学安排2课时
教学步骤
一、唐传奇的阐释
1、唐传奇的定义
传奇本是传述奇闻异事的意思,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
它远继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近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发展成为一种以史传笔法写奇闻异事的小说体式。
唐传奇内容更加丰富,题材更为广泛,艺术上也更成熟。
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标志著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2、唐传奇的产生背景
(1)外部因素唐代经济繁荣,特别是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使市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各种民间艺术得以发展,为传奇小说创作奠定了社会的基础。
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温卷”之风,也推动了传奇的发展。
(文人以此来展示自己的史才)魏晋南北朝以来志怪及志人小说的创作则是唐传奇产生的文学渊源。
中唐时期,通俗的审美趣味由于变文、俗讲的兴盛而进入士人群落,传奇在很大程度上已为人们接受和欣赏,已经有了广大的接受群。
(2)内部因素唐代各种文学形式的繁荣,并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互相促进,也为唐传奇在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上提供了营养。
中唐成为传奇发展的兴盛期,一是因为小说本身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蓬勃昌盛的各体文学在表现手法所提供的丰富借鉴,如诗歌的抒情写意、散文的叙事状物、辞赋的虚构铺排等艺术技巧在传奇作品中屡见不鲜,而诗歌向传奇的渗入尤为明显,使得诸多传奇作品都具有诗意化的特点。
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虹、李绅等人更以诗人兼传奇家的身份,将歌行与传奇配合起来,用不同体裁不同方式来描写同一件事。
从而提高了传奇的地位,也亏阿达了传奇的影响。
而传奇在叙事上,则与古文的兴盛有一定的关系。
二、唐传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作品
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1)初、盛唐是唐传奇的发轫时期,也是由六朝志怪到成熟的唐传奇的过渡。
作品数量不多,现存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鷟的《游仙窟》,内容近于志怪,艺术上也不够成熟。
《古镜记》作品主人公王度﹐自述大业七年从汾阴侯生处得到一面古镜﹐能辟邪镇妖﹐携之外出﹐先后照出老狐与大蛇所化之精怪﹐并消除了疫病﹐出现了一系列奇迹。
后其弟王绩出外游历山水﹐借用古镜随身携带﹐一路上又消除了许多妖怪。
最后王绩回到长安﹐把古镜还给王度。
大业十三年古镜在匣中发出悲鸣之后﹐突然失踪。
篇中以几则小故事相连缀﹐侈陈灵异﹐辞旨诙诡﹐尚存六朝志怪馀风。
但篇幅较长﹐加强了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稍有文采﹐代表著小说从志怪演进为传奇的一个发展阶段。
《补江总白猿传》写梁大同末年欧阳纥率军南征﹐至长乐﹐妻为白猿精劫走。
欧阳纥率兵入山﹐计杀白猿﹐而妻已孕﹐後生一子﹐状貌如猿猴。
“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於时”。
《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说﹐欧阳纥是唐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父亲。
因欧阳询貌类猕猴﹐当时同僚大臣长孙无忌曾作诗嘲谑(刘餗《隋唐嘉话》及孟棨《本事诗‧嘲戏》)。
“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
它当是同时人所作﹐开了唐人以小说诬蔑他人的风气。
题名中“补江总”三字﹐意谓江总为欧阳纥友﹐纥死後曾收养询﹐故备知其事﹐唯未作传述其事﹐所以补之。
猿猴劫人间妇女为妻﹐古籍中已有记载。
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说:
“南山大玃盗我媚妾。
”其後西晋张华《博物志》等书更有较具体的描述。
本篇在构思上当受其影响。
其内容尚沿袭六朝志怪小说遗风﹐但比起稍前的《古镜记》来﹐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描写也颇为生动﹐在唐代传奇艺术成熟过程中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宋代话本有《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其故事即脱胎於本篇。
《游仙窟》 作者张鷟,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
当时颇负文名。
《唐书·张荐传》记载;“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
”《游仙窟》是用第一人称手法,用一万余字的骈文详细铺陈了一场华丽的艳遇。
自叙奉使河源,途经神仙窟,受到女主人十娘五嫂柔情款待,宿夜而去。
题为“游仙”,实则是写风流艳遇式的庸俗生活,其中夹杂不少色情描写。
鲁迅说它“文近骈丽而时杂鄙语”,郑振铎说:
“它只写得一次的调情,一回的恋爱,一夕的欢娱,却用了千钧的力去写。
”但它一脱志怪小说的怪诞色彩,转向描写现实生活。
在艺术上,散、骈并用,还采用了许多民间谚语,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此书于当时传至日本,对日本文坛颇有影响。
日本学者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称之为日本第一淫书。
它代表了唐代传奇的一个时期的倾向和水平。
《游仙窟》用第一人称单数,自叙旅途中在一处“神仙窟”中的艳遇。
五嫂、十娘都是美丽而善解风情的女子,她们热情招待“下官”,三人相互用诗歌酬答调情,那些诗歌都是提示、咏叹恋情和性爱的。
接着那“下官”就逐渐提出要求:
先是要求牵十娘的素手,说是“但当把手子,寸斩亦甘心”,十娘假意推拒,但五嫂却劝她同意。
“下官”牵手之后,又向十娘要求“暂借可怜腰”(搂住可爱的腰肢);搂住纤腰之后,又要索吻,“若为得口子,余事不承望”。
而接吻之后,那浪子“下官”当然就要得陇望蜀,提出进一步的请求,但是未等他明说,十娘已经用“素手曾经捉,纤腰又被将,即今输口子,余事可平章”之句,暗示既已经接过吻,别的事情都可以商量。
随着五嫂不断从旁撮合,“下官”与十娘的调情渐入佳境,他“夜深情急,透死忘生”,“忍心不得”,“腹里癫狂,心中沸乱”,最后“夜久更深,情急意密”,终于与十娘共效云雨之欢。
(2) 中唐是唐传奇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不仅作家和作品数量最多,而且颇有名家名作涌现。
如陈玄祐的《离魂记》、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
内容题材涉及到爱情、历史、政治、豪侠、志怪、神仙等,但大多作品体现了较强的现实精神,创作方法与艺术技巧更加成熟。
《离魂记》,唐代传奇小说。
收入《太平广记》358卷,鲁迅校辑《唐宋传奇集》也收入此篇。
作者陈玄祐,代宗大历时人,生平事迹不详。
《离魂记》写张倩娘与表兄王宙从小相爱,倩娘父张镒也常说将来当以倩娘嫁王宙。
但二人成年后,张镒竟以倩娘另许他人。
倩娘因此抑郁成病,王宙也托故赴长安,与倩娘诀别。
不料倩娘半夜追来船上,乃一起出走蜀地,同居五年,生有二子。
后倩娘思念父母,与王宙回家探望。
王宙一人先至张镒家说明倩娘私奔事,始知倩娘一直卧病在家,出奔的是倩娘离魂。
两个倩娘相会,即合为一体。
本篇以离奇怪诞的情节,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由的愿望,歌颂了他们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具有典型意义。
篇末写到倩娘的离魂与肉体相合时,巧妙缀上“其衣裳皆重”这样一个细节,给人以似幻似真的感觉。
离魂以求爱情婚姻故事,始见于南朝刘义庆《幽明录·庞阿》。
唐代颇有敷衍为传奇作品的,《太平广记》另收有《灵怪录·郑生》、《独异记·韦隐》,都叙述唐人离魂故事,但描写较本篇更为简略。
元代郑光祖(郑德辉)《述青琐倩女离魂》杂剧,即根据本篇故事演绎而成。
《任氏传》沈既济(约750--800)字不详,德清(今属浙江)人。
唐代小说家,史学家。
唐德宗时做过史馆修撰,《旧唐书》本传称他“博通群籍,史笔尤工”。
(元和姓纂作吴兴武康人。
此从两唐书)生卒年均不详,约唐德宗建中元年前后在世。
《任氏传》唐代传奇小说,是最早的借狐仙写人、写现实生活的作品。
一反以往狐妖鬼魅害人的传统观念,塑造了一个聪明美丽、坚贞多情的狐精形象,具有反封建意义。
(人物:
任氏、郑六、巫师;动物:
苍犬)
《柳毅传》唐代传奇小说,收入《太平广记》419卷,鲁迅校辑《唐宋传奇集》也收入此篇。
曾慥《类说》引《异闻集》题作《洞庭灵姻传》,似是原题。
作者李朝威,生平不详,约中唐时人。
本篇写洞庭龙女远嫁泾川,受其夫泾阳君与公婆虐待,幸遇书生柳毅为传家书至洞庭龙宫,得其叔父钱塘君营救,回归洞庭,钱塘君即令柳毅与龙女成婚。
柳毅因传信乃急人之难,本无私心,且不满钱塘君之蛮横,故严辞拒绝,告辞而去。
但龙女对柳毅已生爱慕之心,自誓不嫁他人,后二人终成眷属。
本篇故事富于想象,情节曲折,而结构谨严。
柳毅的正直磊落,龙女的一往情深,钱塘君的刚直暴烈,性格刻画颇为鲜明。
对龙女和柳毅的心理描写,尤细致真切。
其文体在散行之中夹有骈偶文句和韵语。
文辞亦颇华艳。
《柳毅传》在晚唐已流传颇广。
唐末裴铏所作《传奇》中《萧旷》一篇,已言“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唐末传奇《灵应传》亦言及钱塘君与泾阳君之战,宋代苏州又有柳毅井﹑柳毅桥的附会(范成大《吴郡志》卷六“古迹”﹑卷一七“桥梁”)。
后世据以演成戏曲者,有元代尚仲贤《柳毅传书》﹑明代黄惟楫《龙绡记》﹑许自昌《橘浦记》﹑清代李渔《蜃中楼》等。
评析:
故事发生在唐朝高宗皇帝时期。
一位来自湘乡的书生柳毅,赴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落榜。
返乡时,他取道泾阳想与在那里的朋友话别。
途中他经过一处荒凉无人的郊外,遇见一位姑娘正在孤零零地放羊。
这位姑娘容貌非常美丽,但衣装粗简,满脸憔悴,神情格外凄苦。
柳想觉得好生蹊跷,经过询问,原来这位姑娘是他的乡亲,是洞庭湖龙王的爱女。
她遵从父母的安排,远嫁到这里,做了泾河龙王的儿媳。
然而,丈夫终日寻欢作乐,对妻子薄情寡义。
龙女无法忍受这般虐待,不断诉求抗争。
但公公婆婆袒护儿子,非但对龙女不理不睬,反而百般刁难并役使她在荒郊放牧。
面对洞庭万里迢迢,长天茫茫,龙女欲诉无门,欲哭无泪。
她请求柳毅帮她送书信到洞庭家中。
柳毅非常同情龙女的不幸遭遇,慨然允诺前往洞庭龙宫。
柳毅怀揣书馆兼程赶路,来到洞庭湖畔。
他按照龙女的指点,找到一棵大桔树并叩树三下,果然从碧波间冒出虾兵蟹将。
经他们揭水引路,柳毅进人龙宫,将龙女托书亲手转交给了洞庭龙王,并述说了龙女的悲惨境况。
龙王得知女儿受难,非常伤痛。
龙王的弟弟钱塘君,是个性情开朗、刚直勇猛、疾恶如仇的人。
他一听说侄女在夫家遭受欺辱,顿时大怒,立刻凌空而去,诛杀了泾河逆龙,救出了龙女,使骨肉重新团聚。
龙女深深地爱上了见义勇为的柳毅,钱塘君也希望玉成美事。
但柳毅是个正直的书生,他当初送信救龙女完全是激于义愤;来到龙宫,面对数不尽的奇珍异宝也不为所动,没有任何贪财恋色的个人企图。
所以当钱塘君在酒宴后逼婚时,他虽也有爱慕龙女之心,但克制了私情,晓以人间正义,毅然拒绝。
柳毅告别龙宫后,性情温顺善良的龙女面对他的拒绝没有气馁。
她饱尝过包办婚姻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所以不再依从父母又一次为她安排的婚配,依然执着坚定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在柳毅的妻子亡故后,龙女化做民妇来到鳏居孤独的柳毅身边,与他结为夫妇,直至他们的孩子出世才道出真情。
柳毅被龙女的一片深情所感动,从此而心相印,过着恩爱美满的生活。
柳毅与龙女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出自唐朝人李朝威的短篇小说《柳毅传》。
该篇是唐代爱情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虽然故事还没有脱离六朝小说鬼神志怪的传统,神怪离奇,但充满了人间社会的清新气息,两人的情操和爱情即使在今天也不无教益,所以民间妇孺皆知。
现代剧《龙女牧羊》和《张羽煮海》等也是从本篇脱胎演变而来。
我国发行的“民间传说”系列邮票之四《柳毅传书》,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选取了“龙女托书”、“传书洞庭”、“骨肉团聚”和“义重情深”四个场面,既忠实了原作,又突出了以义为重、以情至深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画龙点睛之妙。
“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咏君山的诗句。
风景如画的君山是洞庭湖上的一个小岛,在它的龙口和龙舌山尾部至今保留着一口柳毅井。
据《巴陵县志》记载,井边原有一棵大桔树,柳毅当年就是从这里下水入龙宫的。
井最早建于何时已难考证,传说它很深,曾有人用四两丝线栓一铜钱试着往下放,线尽而钱尚未着底。
在井的周团还有虾兵蟹将迎接柳毅下湖的浮雕。
今天人们来到君山,自然要拜谒斑竹丛中舜帝的妻子湘妃墓,瞻仰一统中国的秦始皇南巡时留在石壁上的“封山印”,还要品尝一下驰名中外的君山银针茶,当然也不会忘记去看看柳毅井。
往事越千年,洞庭湖涛声依旧,这对爱侣可是别来无恙?
《莺莺传》文笔优美﹐描述生动﹐于叙事中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较好地塑造了崔莺莺的形象。
崔莺莺是一个在封建家庭的严格闺训中长大的少女。
她有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又在内心隐藏得很深﹐甚至有时还会在表面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姿态。
本来﹐通过她的侍婢红娘﹐张生与她已相互用诗表达了爱情。
可是﹐当张生按照她诗中的约定前来相会时﹐她却又“端服严容”﹐正言厉色地数落了张生的“非礼之动”。
数日后﹐当张生已陷于绝望时﹐她忽然又采取大胆的叛逆行动﹐主动夜奔张生住所幽会﹐“曩时端庄﹐不复同矣”。
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和反复﹐真实地反映了她克服犹豫﹑动摇而终于背叛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
但是﹐她在思想上又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社会﹑出身﹑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
她仍然认为私自恋爱结合是不合法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
因而在她遭到遗弃以后﹐就只能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
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
作品中对这一形象的刻画﹐传神写态﹐有血有肉﹐异常鲜明。
相比之下﹐张生的形像则写得较为逊色。
尤其是篇末﹐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无耻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
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
“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尽管如此﹐读者从作品的具体描述中却仍然感到崔莺莺令人同情﹐而张生的负心﹐则令人憎恶。
作品的客观艺术效果与作者的主观议论评价是不一致的。
《霍小玉传》唐代传奇小说,收入《太平广记》487卷。
描写了陇西李益与妓女霍小玉的爱情悲剧。
李益初与霍小玉相恋,同居多日。
得官后,聘表妹卢氏,与小玉断绝。
小玉日夜思念成疾,后得知李益负约,愤恨欲绝。
忽有豪士黄衫客挟持李益至小玉家中,小玉誓言死后必为厉鬼报复。
李益娶卢氏后,因猜忌休妻,“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作者同情霍小玉的悲惨命运,谴责李益的负心,爱憎分明。
与元稹《莺莺传》为张生抛弃崔莺莺辩护判然不同。
《枕中记》唐代传奇《枕中记》的故事大意是:
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卢生郁郁不得志,骑着青驹穿着短衣进京赶考,结果功名不就,垂头丧气。
一天,旅途中经过邯郸,在客店里遇见了得神仙术的道士吕翁(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邯郸记》,将吕翁改为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卢生自叹贫困,道士吕翁便拿出一个瓷枕头让他枕上。
卢生倚枕而卧,一入梦乡便娶了美丽温柔出身清河崔氏的妻子,中了进士,升为陕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
他的5个孩子也高官厚禄,嫁娶高门。
卢生儿孙满堂,享尽荣华富贵。
80岁时,生病久治不愈,终于死亡。
断气时,卢生一惊而醒,转身坐起,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吕翁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小米饭)还没熟哩!
即黄梁梦(黄梁一梦)的由来也是来于此了。
《枕中记》和沈既济另一篇唐代传奇《任氏传》是中唐传奇中创作年代较早的名篇,标志唐传奇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对后世文学颇有影响。
《南柯太守传》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人。
作品有《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
《南柯太守传》剧情为一东平人淳于棼一天在一株古槐树下醉倒,接著梦见自己变成大槐国国王的驸马,任“南柯太守”二十年,与金枝公主生了五男二女,荣耀一时。
后来因与檀萝国交战,吃了败战,金枝公主亦病死,最后被遣发回家,沿途破车惰卒,梦突惊醒,醒来后发现“槐安国”和“檀萝国”竟都是蚁穴,历历如现。
这个故事反映了人生如梦,后来成语有所谓的“南柯一梦”,典史于此,与“黄粱一梦”剧情类似。
(3)晚唐是唐传奇的衰落事情。
虽然作品数量不少,并出现了专集,如牛僧孺的《玄怪录》、皇甫枚的《三水小牍》、裴鉶的《传奇》等,但内容较为单薄,艺术上也较为粗俗。
唯有豪侠题材的作品成就较高,如传为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就是最著名的作品。
《虬髯客传》:
《太平广记》﹑《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等均不署作者名氏﹔《容斋随笔》﹑《宋史‧艺文志》等以为杜光庭作﹔《说郛》﹑《虞初新志》等则题张说作﹔今人所编《唐宋传奇集》均署杜光庭。
按苏鹗《苏氏演义》载“近代学者著《张虬须传》﹐颇行於世”﹐苏鹗与杜光庭同为唐末人﹐不当称杜为“近代学者”。
大约此传曾经杜光庭删节﹐收入其所编之《神仙感遇传》﹐後人遂以为是他的作品。
但张说所撰说也无确证。
本篇写李靖於隋末在长安谒见司空杨素﹐为杨素家妓红拂所倾慕﹐随之出奔﹐途中结识豪侠张虬髯﹐後同至太原﹐通过刘文静会见李世民(即唐太宗)。
虬髯本有争夺天下之志﹐见李世民神气不凡﹐知不能匹敌﹐遂倾其家财资助李靖﹐使辅佐李世民成就功业。
後虬髯入扶馀国自立为王。
篇中故事情节和两个主要人物红拂妓﹑虬髯客均出虚构﹐主旨在表现李世民为真命天子﹐唐室历年长久﹐非出偶然﹐由此宣扬唐王朝统治的合理性。
描写人物颇为精彩﹐红拂的勇敢机智﹐虬髯的豪爽慷慨﹐刻画尤为鲜明突出﹐文笔亦细腻生动﹐艺术成就在唐传奇中属于上乘。
後世戏曲用为题材的﹐有明代张凤翼《红拂记》﹑张太和《红拂记》﹑凌蒙初《虬髯翁》。
又李靖﹑红拂﹑虬髯三人﹐後人亦称“风尘三侠”。
三、唐传奇的艺术成就
1、唐传奇的思想内容唐传奇题材广泛,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
其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是描写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
这类作品表现了对婚姻爱情生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抨击了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和门第等级观念。
其次有讽刺批评社会的一些现象的作品,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体现了一定的现实批判精神。
还有政治历史题材的作品,如《高力士外传》、《长恨歌传》、《东城父老传》等,往往借历史表达思想情感。
此外,描写义侠刺客的题材的作品也不少,如《聂隐娘》、《红线》、《昆仑奴》、《虬髯客传》、《谢小娥传》等,反映了反抗强暴和侠义的思想精神。
另外还有一些描写神仙鬼怪的作品,如《古镜记》、《补江总白猿记》等。
2、唐传奇的艺术成就唐传奇的创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首先,唐传奇在小说发展史上摆脱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写法,对生活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走向了细致化的艺术境地,注重生活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心理的展现,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具有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并且开始注意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娱乐功能。
其次,唐传奇是“有意为小说”,因此在创作手法上较六朝志人的偏重写实增强了虚构性,较六朝志怪的偏重记述传闻增加了再创作性,作家真正开始自觉地进行艺术想像和艺术创造,而且在艺术构思、情节结构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此外,唐传奇的细节描写、心理描写以及语言、词采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主要采用散体古文,适当吸取了民间口语,也常插入诗词,提高了小说的表现力。
展开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
通过虚构的故事和虚构的人物,它比以往的任何文学样式,能够更自由更方便更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趣味,由此而言,它在文学史上有著非常深远的意义。
传奇这种文言小说样式在宋代一度衰落,到元、明又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较唐传奇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的创作,并被改写为白话小说。
事实上,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与传奇体有很大关系。
由于唐传奇的兴起本身与民间文学有一定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民间的素材,这使得文人创作同大众的爱好有所接近,这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在众多的传奇作品中,我们看到追求自由的爱情成为中心主题,而妓女、婢妾这类低贱的社会成员成为作品歌颂的物件,这裏面就反映著大众的心理。
所以它为後世面向市井民众的文艺所吸收。
最显著的是在元明戏曲中,大量移植唐传奇的人物故事进行创作,诸如王实甫《西厢记》源于《莺莺传》,郑德辉《倩女离魂》取材于《离魂记》,石君宝《李亚仙诗酒麴江池》取材于《李娃传》,汤显祖《紫荆记》取材于《霍小玉传》等等,不下于数十种。
可以说,唐传奇为中国古代一大批优秀的戏曲提供了基本素材。
唐传奇也形成了独特的散文体式。
较之六朝骈文,它是自由的文体;较之唐代"古文”,它又多一些骈丽成分和华美的辞藻。
这些特点从小说的要求来看未免过于于文章化,但对後代散文却不无有益的影响。
四、俗讲与变文
1、俗讲与变文产生的背景
俗讲是由六朝以来的斋讲演变而成的,它是指应用转读(咏经)、梵呗(赞呗)、唱导等手法进行佛经的通俗演讲。
这种讲演因地制宜地通过杂说因缘比喻,使一般大众更易理解佛教经论义理,从而达到了随类化俗之目的。
在古代,俗讲对于佛教义理的普及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2、俗讲
唐代俗讲相当盛行。
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载,武宗会昌元年(841)仅京都长安一次就有七座寺院同时开讲,自“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俗讲法师有海岸、体虚、文溆等多人。
其中文溆尤为著名。
赵璘《因话录》卷四角部载:
有文淑(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
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
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
普通民众对俗讲趋之若鹜,以至“仍闻开讲日,湖上少渔船”;“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
连皇帝也曾“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
朝野上下,风靡一时。
俗讲由佛家讲经衍出,讲者尽为僧徒,即所谓俗讲僧。
他们有主咏经的都讲,主讲解的法师,主吟偈赞的梵呗等。
俗讲有一定仪轨,维那鸣钟集众;法师、都讲上堂升高座,作梵,念菩萨;说押座;开题,说庄严、忏悔、受三归、请五戒、称佛名等。
正式讲经,先由都讲咏经原文若干,法师即就经文敷陈讲解,继以唱辞。
一段完了,例以套语催经;于是都讲再咏经若干,次又由法师解说。
如此反复,直至讲毕,以解座文结束。
俗讲的底本,就是讲经文。
敦煌遗书中尚保存有十来种。
最为完好者为《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此外尚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双恩记》等等,都是散韵结合,说唱兼行。
说为浅近文言或口语,唱为七言,间用三三句式六言或五言。
其上往往有平、断、侧、吟之类的辞语,标示声腔唱法。
讲经文取材全为佛经,思想内容不外佛教的无常、无我、苦空、业惑、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修持戒定慧,以求涅槃解脱等等教义。
其中一些作品,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叙事、描绘、抒情等手法,广譬博喻,纵横骋说,把深奥的教义转化为生活展示,往往突破宗教藩篱,映照出现实世界,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新奇别致的内容,张驰起伏的情节,通俗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
如《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伯2305号)旨在说明供养人间师僧,即是敬奉佛菩萨,却用一位国王毅然抛弃人世的荣华富贵,屡遭种种磨难仍甘于为仙人供给走使,执着追求大乘真理的故事来表现。
情节波澜起伏,故事娓娓动听。
又如,《维摩诘讲经文》,现存两个系统的七种八卷片断,规模宏伟,想象丰富,甚有文学色彩。
其中对于魔女的描写,极铺陈渲染之能事,辞藻华丽,带有骈文的节奏声韵之美。
3、变文
唐五代时与俗讲同时流行的民间说唱伎艺尚有“转变”。
转变,就是说唱变文,当时极为盛行,上自宫廷,下至闹市,都有演出,且出现了演出的专门场所“变场”。
变文,或简称“变”,乃转变的底本,在敦煌说唱类的作品中保存较多。
现知明确标名“变文”或“变”者有八种:
《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八相变》、《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汉将王陵变》、《舜子变》(又题《舜子至孝变文》)、《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又题《前汉刘家太子传》)。
此外,尚有题残佚,据其体制也应属变文一类者为《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目连变文》等数种。
上述作品,除《舜子变》基本为六言韵语、体近赋文,《刘家太子变》全为散说、体近话本外,其馀共同特点是:
一、说唱相间,散韵组合演述故事。
说为表白宣讲,多用俗语或浅近骈体;唱为行腔咏歌,多为押偶句韵的七言诗。
这种体制,虽与讲经文相似,但变文一般不引原经文,唱辞末句也无催经套语,不标“平”、“断”、“侧”。
这说明唱腔与讲经文也不同。
二、说白与吟唱转换时,每有习用的过阶语作提示,如“……处若为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