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惊奇的山谷》.docx
《浅析《惊奇的山谷》.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浅析《惊奇的山谷》.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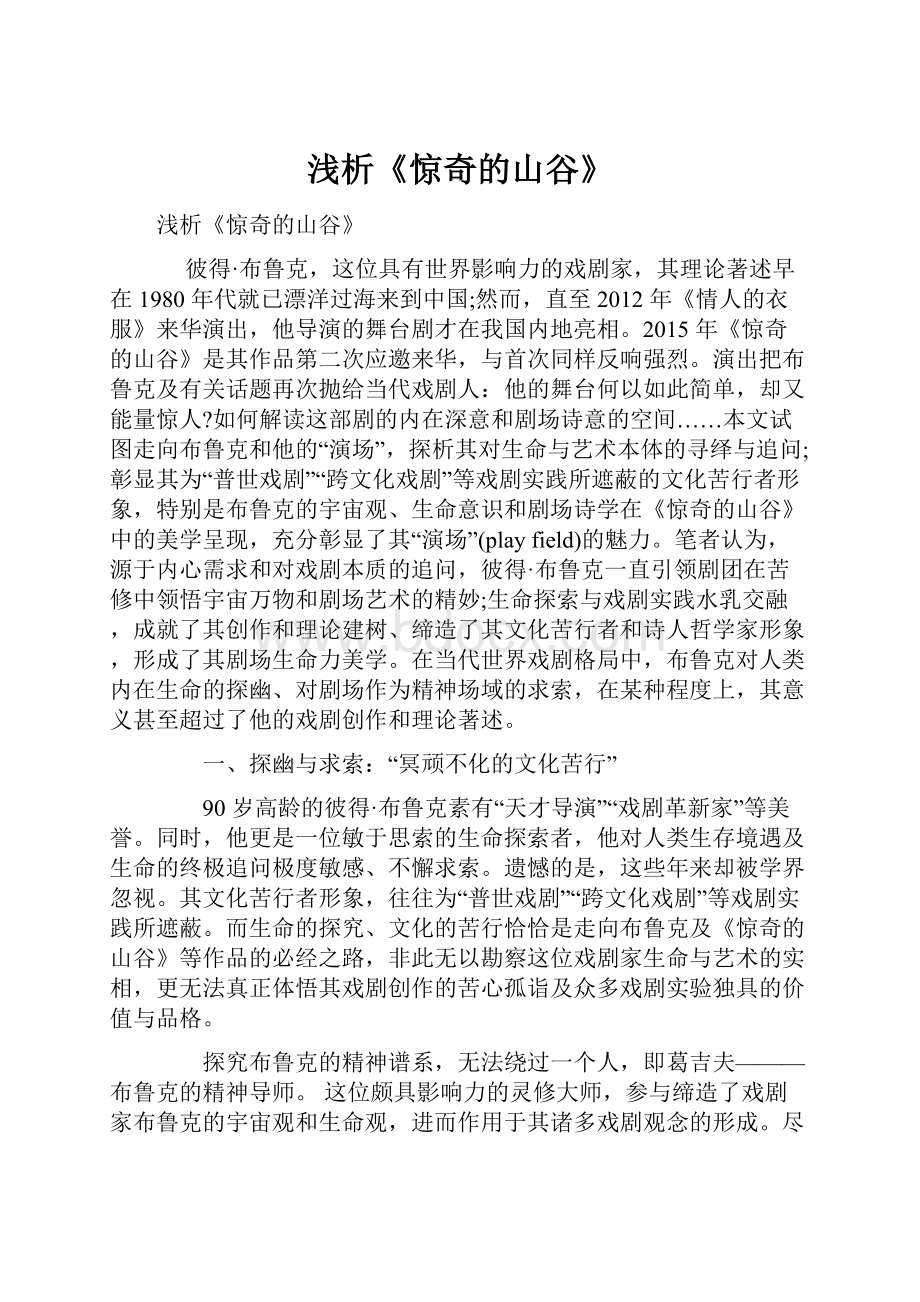
浅析《惊奇的山谷》
浅析《惊奇的山谷》
彼得·布鲁克,这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戏剧家,其理论著述早在1980年代就已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然而,直至2012年《情人的衣服》来华演出,他导演的舞台剧才在我国内地亮相。
2015年《惊奇的山谷》是其作品第二次应邀来华,与首次同样反响强烈。
演出把布鲁克及有关话题再次抛给当代戏剧人:
他的舞台何以如此简单,却又能量惊人?
如何解读这部剧的内在深意和剧场诗意的空间……本文试图走向布鲁克和他的“演场”,探析其对生命与艺术本体的寻绎与追问;彰显其为“普世戏剧”“跨文化戏剧”等戏剧实践所遮蔽的文化苦行者形象,特别是布鲁克的宇宙观、生命意识和剧场诗学在《惊奇的山谷》中的美学呈现,充分彰显了其“演场”(playfield)的魅力。
笔者认为,源于内心需求和对戏剧本质的追问,彼得·布鲁克一直引领剧团在苦修中领悟宇宙万物和剧场艺术的精妙;生命探索与戏剧实践水乳交融,成就了其创作和理论建树、缔造了其文化苦行者和诗人哲学家形象,形成了其剧场生命力美学。
在当代世界戏剧格局中,布鲁克对人类内在生命的探幽、对剧场作为精神场域的求索,在某种程度上,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他的戏剧创作和理论著述。
一、探幽与求索:
“冥顽不化的文化苦行”
90岁高龄的彼得·布鲁克素有“天才导演”“戏剧革新家”等美誉。
同时,他更是一位敏于思索的生命探索者,他对人类生存境遇及生命的终极追问极度敏感、不懈求索。
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却被学界忽视。
其文化苦行者形象,往往为“普世戏剧”“跨文化戏剧”等戏剧实践所遮蔽。
而生命的探究、文化的苦行恰恰是走向布鲁克及《惊奇的山谷》等作品的必经之路,非此无以勘察这位戏剧家生命与艺术的实相,更无法真正体悟其戏剧创作的苦心孤诣及众多戏剧实验独具的价值与品格。
探究布鲁克的精神谱系,无法绕过一个人,即葛吉夫———布鲁克的精神导师。
这位颇具影响力的灵修大师,参与缔造了戏剧家布鲁克的宇宙观和生命观,进而作用于其诸多戏剧观念的形成。
尽管诸多人与事都曾对布鲁克的艺术与人生产生过影响,但其深切程度与深远意义都远不及葛吉夫及其“第四道”学说。
早在1950年代初,布鲁克开始追随葛吉夫学说,不定期告别纷繁的外部世界,投入形而上的研修之中。
葛吉夫“第四道”学说的理论核心即行动和能量,该理论认为,普通人在“睡眠”中生活和死去,不追问生活的意义;只有通过不同的训练达到“醒来”的状态,人才能走向真正“自我”。
受此影响,布鲁克一直强调在生命与文化“寻根”中积累经验,重视在经验基础上行动。
在戏剧创新中,他执着于探索生命的觉知:
在省察中,明心见性。
1950至1970年代,与布鲁克生命的觉知与艺术的探索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影片《与奇人相遇》的拍摄。
布鲁克之所以成为执导这部影片的不二人选缘于1952年,这一年他成为了葛吉夫传人之一珍·希普的弟子。
1960年代初,修行中的布鲁克远赴阿富汗,寻找“东方”的“第四条道路”。
1978年又重返阿富汗,拍摄这部以葛吉夫人生传奇为主题的影片,诠释葛吉夫的“第四道”———人的探索之路。
“第四道”是重变通之路,更适于人对自我的探索。
布鲁克认为,葛吉夫“比任何人都有趣,他在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
……他又将东方保留和发展的东西和今天可能只在西方能找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他坦言:
“在二十世纪,最让人感兴趣,也是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男人。
”“我很久前就读过他的作品,因此有了很多很多的结果”。
布鲁克生命与戏剧实践如影随形的表演方法和日常训练的探索,无疑是与“奇人”相遇的结果之一。
①
1970年代,“国际剧场研究中心”创建之后的几年里,布鲁克率领这个以表演和研究戏剧本质为己任的剧团经历了艰苦环境的磨砺。
除了演员常规训练,布鲁克与同仁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户外排演之路———1971年前往伊朗、1972-1973年非洲之行。
在伊朗,剧团进行了三个月的即兴表演和语言训练,并排演了众神话融合的《奥格哈斯特》一剧。
这是一次在伊朗慈悲山之巅超大空间的特别演出,在古波斯帝国的残桓废墟之上,在历史、神话、现实的交织中,演出从黄昏到第二天清晨,演员和观众都经历了一场攀登、行走的苦行,进而沉浸在聆听中。
神话故事通过演员声音的节奏、音调和质感回响在山谷之间,雄浑悲苦、余味无穷……这种类宗教体验,除了演员训练之外,更是布鲁克对人与文化有深意的探索。
“演场”之所以选择伊朗,是因为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与交流的汇聚地,布鲁克看重的是对波斯文化源头的追溯。
他“一直在寻找的作品总是两个基本层面:
演员内部丰富的激情和外部———故事素材或者是艺术指导上的———召唤,但这一切都必须用来应对挑战。
”他希望在情感贫乏的年代,通过戏剧,感知的能力打开人们内在的情感之门,使得人内在生命得到更生动的体现。
非洲之行中,布鲁克同样在意于这个特定的场域及其丰富复杂的传统———在传统的非洲生活中,“想象”被视为扮演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它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在现实与虚构、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之间往返。
在文化和戏剧寻根中,布鲁克更着意于声音、身体的内在状态和神秘性的探源,形成了独具生命力的即兴表演和身体、声音等训练方法。
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大量应用于其后众多戏剧排演与创新之中,包括印度史诗剧《摩诃婆罗多》的演出。
1985年长达九个小时的《摩诃婆罗多》在世界戏剧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部旷世之作,无疑是布鲁克及同仁十余年灵修与文化探寻之路上的硕果,仅剧作写作就长达十二年之久。
《摩诃婆罗多》之所以如此吸引布鲁克和他的演员,缘于它不仅仅是印度史诗,更是人类故事。
布鲁克试图通过复杂的人物探讨各种问题,从现实跨越到精神和形而上学。
因为史诗题材本身的宏大鲜活,为布鲁克生命和戏剧探索提供了各种尝试的机会。
为了找到要表达的意义,探寻让别人能够理解的表演方式,他们模仿和套用了一些古老的手法,如搏击、吟诵、即兴,讲故事……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员在讲同一个故事时,各种技艺和文化汇聚成一面镜子,返照出令人警醒的主题———“我们的世界越来越深地滑入《摩诃婆罗多》所预言的憎恶和仇恨之中,我们为黑暗所包围,行将到达人类堕落的极致———远远超出了所有古代圣贤的预见。
……如何生存,是当今的一个急迫问题……不仅是如何生存,还有为什么”。
从现世、精神到形而上学,《摩诃婆罗多》可谓博大精深。
尽管这个戏剧壮举自诞生之日起一直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戏剧巨制与布鲁克众多经典创作一样,因为深度、广度、终极追问的多面性和严肃性而具有了恒久性和超越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鲁克的戏剧实践,一如既往地从传统中寻找创新的灵感,重新诠释戏剧经典。
同时,对人心与人生的关注更多聚焦于人性的繁复和对生存与生命形而上的追问与体悟。
代表性的创作有探索神经病理科学与身体关系的“三部曲”和“宗教三部曲”。
前者分别是:
《那个男人》、《我是一个现象》以及《惊奇的山谷》。
与此呼应,《提尔诺·波卡》、《黑天之死》和《大宗教裁判》构成了其“宗教三部曲”。
这些作品以更趋纯净的剧场艺术探索,潜沉于人性深处的奥秘及对人类终极意义和人文关怀的求索。
布鲁克曾经坦言,神经病理学“三部曲”创作的构想缘于《摩诃婆罗多》之后的困惑和思考。
相对前两部,《惊奇的山谷》走得更远,“演场”的能量释放几近极致,甚至比同类题材的影视剧走得更稳健、微妙。
布鲁克多次强调,戏剧是隐喻,帮你更清晰地看清生活。
这些戏看似单纯,却处处有伏笔;剧的台词已经脱去了其物质性的外壳,潜入剧的整体能量系统。
在回忆录中,彼得·布鲁克自称“冥顽不化的文化苦行者”。
他认为,修行使我们认识到精神世界的意义,只有在生活的厚度中才能找到。
“要说在戏剧方面一次又一次指引我的……只有我自己内心深深的期待了。
”正是源于内心需求和对戏剧本质的追问,布鲁克率领剧团一次次远行,在苦修中领悟宇宙万物和戏剧的精妙,不断探索理想的演出场所———那个“空的空间”,因此,有了“敞开的门”,有了布鲁克各类室内外“演场”及其独特的美学趣味与品格。
当有评论家称他演出的空间为“演场”(playingfield)时,布鲁克对这个说法非常满意,认为,“演场”“就是一个用来玩耍的空间”,这个称呼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初衷。
二、剧场生命力美学:
“此时此刻能量惊人”
在对布鲁克剧场美学观念影响巨大的人之中,除了“第四道”的精神导师外,还有阿尔托、格洛托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等,但是,布鲁克并没有躺在既有理论温床上坐享其成,而是不断尝试如何在剧场这个特定的“演场”释放生命的能量、不断探索如何让“演场”的生命鲜活有力、不可抗拒。
长久以来,布鲁克不断尝试如何在剧场这个特定的“演场”释放生命的能量,不断探索如何让“演场”的生命鲜活有力、不可抗拒。
旷日持久的生命探索与不懈的戏剧实践,不断建构和丰富彼得·布鲁克的创作和理论建树。
布鲁克认为,“生命本质最伟大的理论,如果不与辛苦得来的个人经验结合在一起,是毫无意义的”。
长期探究使他谙熟于如何从一分钟进入下一分钟;而演员自己所受到的训练与艺术直觉也足以让他们具有超强的内在创造力,在排演中各显神通,用生命的能量给作品和角色注入思想与活力。
正因此,布鲁克提出了“即时戏剧”。
“即时”即当下,即此时此刻。
布鲁克不止一次说过,“我在剧场所做的都是活在当下”。
他说,“我把整个世界当成了一个开罐的起子。
我让世界各地的声音、形状和态度作用于演员的感官,让他们找到一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好角色能让他们超越自己表面能力所及的高度”。
“即时戏剧”是布鲁克多年身体力行的生命力戏剧观。
对他而言,剧场就是生命,就是生命能量的释放。
布鲁克一向关注演员鲜活的生命和表演中生命的火花,他认为,那种富于想象的鲜活的生命力,是“能够将作品和观众连接起来的———不可抗拒的现场的生命”。
他强调,一个好的演员必须在身体上常保持警醒,这样才能与声音、思想和动作产生新鲜流畅的互动,声音和动作才能达成平衡和具有统一性。
在《惊奇的山谷》中,一个个片段、一段段对话仿佛从日常生活对话的录音带上拷贝下来的,一切自然而然。
但事实上,没有一句台词不是富于创造性的,他们调动了多年的生活积累和表演才华,找到并掌控台词的能量、能量运行和释放的时机,伴随一个个有机片段共同编织剧中特有的诗意氛围。
这部剧只有一女两男三名演员,外加一名乐手。
三名演员都是一人饰多角,转换自如。
他们每个人都有敏捷的思想、真实的情感以及超强的平衡和协调的肢体的能力。
比如,萨米被发现有超人的记忆能力后微妙的心理和困惑中迷茫的眼神、夸张的手势;再如,在测试萨米记忆能力时两名男演员记录她复述内容的无实物表演;还有,无感男子靠眼睛艰难地进行肢体控制和他内心的困境等等,演员的思想、情感和肢体配合默契,机敏、松弛而有力。
在北京演后谈中,回应观众对表演松弛自如的好奇和赞美,演员说,他们的表演并不是“松弛”,只是布鲁克为他们过滤了不必要的“紧张”,于是他们“拥有了自由,打开了身体、感觉和思想,一旦做到这点,真实的个性因为被展示,进而在所有方面释放光彩。
”
戏剧可谓手艺活,导演和演员创作中的细节打磨往往最见功力。
在布鲁克的舞台创作中,几乎文本中所有的细节都被他带领演员悉心“过滤”,每个片段、每个故事无一不被深入勘测、推敲。
有关“过滤”的记录出自布鲁克一次意大利之旅。
在回忆录里,布鲁克记录了在意大利,他和很多同行在一家酒庄聚会,讨论“剧场导演”的定义。
隔墙传来过滤葡萄的榨压声,一个意大利导演提出意大利语单词“distillatori”,意思是“过滤者”。
从那一刻起,布鲁克对这个词充满敬畏……其实,与酿酒一样,戏剧也是个地道的手艺活。
众多创作足以证明布鲁克这位“过滤者”的本领。
在戏剧这个手艺活中,最见功力的就是细节处理。
在布鲁克看来,“在词与词之间无声的间隔里,当然还在这个词的内部,都潜藏着一个来自于角色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能量系统。
如果你能想办法找到它,并且,如果你找到可以把它掩盖起来的艺术,你就能成功地说出这些简单的词,给予观众生命感觉。
本质上它就是生命,但它处于被压缩的时空中,是具有更强烈更浓缩的形态的生命”。
而讲故事又是细节的能量得以释放的重要途径,也是演员与观众之间情感联系的纽带。
和众多导演艺术家一样,布鲁克尤其谙熟讲故事之“道”,而且他尤其擅长“如何把故事讲得鲜活有吸引力”,“让观众看到一个人在以自己的身份讲故事,这时观众和这个人之间就有一种美好的、温暖的联系”。
在《惊奇的山谷》这部戏中,布鲁克显然已经探到了萨米等扮演者潜在的能量,并将之有效掩盖在被压缩的时空中,用讲故事的方式与观众的生命发生了神奇的联系。
萨米和几位病患分别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用故事展示了自己,更带入并吸引了观众。
看过演出无法不承认,几十年来,在苦行者布鲁克引导下的演员都是讲故事高手,都具有超强的亲和力,他们将各地迥异的生活体验、各种生命的感知和经验有效地植入创作,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时,与细节和故事相互依托的是剧中戏剧情势的诗意营造。
这部剧不是传统的戏剧性叙事体式,更接近布莱希特的史诗剧。
全剧以萨米的故事为主,其他病患的故事穿插其间。
戏以《鸟的会议》开场,富于张力的诗意语言、意境和韵律之美为全剧奠定了基调,建构了诗剧所特有的诗美意境。
剧中故事的片段都相对独立、自成一体,而在对人、宇宙和生命的探寻上,每个片段有机关联,最后,在诗句的吟咏中结束:
如果,观看到整个世界被火烧尽,和现实相比,那可能也只是一场梦。
即使,从水中之鱼到天上之月,一切归于虚空,我们也总能在墙角找到一只蚂蚁残破的腿。
即使世界突然被毁灭,也无法否认一粒沙子的存在。
如果抹去人类存在的一切痕迹,那就去看看藏在雨滴里的秘密。
伴随萨米的诗意独白,三位演员静穆,极目远眺,默默凝视。
此时似乎再精彩的表演也不足以与之抗衡。
静观———不是表演的表演,极致的表演;至此,全剧在一个个片段中不断积累的能量在这个极致的静场中得以释放……在现场长久的宁静中,观众和演员一样,收心内视,沉浸在无边的静穆中,沉浸在“此时此刻”里。
此时,恰到好处的“留白”显示了布鲁克通透澄明的哲学修为和艺术造诣。
而这也许就是布鲁克不止一次强调的:
戏剧指的不是剧场,也不是文本、演员、风格或者形式。
戏剧的本质全在一个叫做“此时此刻”的谜里面。
此时此刻能量惊人。
“此时此刻”,演员以生命的火花点燃了观众的内心,布鲁克诗意的叙事所营造的神秘的彼岸世界与现实人生的生命此岸达成联盟。
在戏剧情境营造上的“空”与“舍”,细节与故事编织上“深”与“实”融会贯通,在东西方文化和人类智慧中尽显其生命探寻的美学趣味。
整部剧在貌似轻松的大脑探险游戏中,抵达了真力弥漫的高妙意境———也许这正是布鲁克期盼的,经由戏剧,人的心灵期待抵达的真境!
三、剧场,内在觉醒的诗意空间
剧场(Theatra)就是RRA,即“排练·演出·观众”,这是布鲁克著名的命题。
在他看来,剧场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探测戏剧生命力的强弱绝然离不开富于活力的排练,更离不开弥漫在剧场中的现场的戏剧氛围、戏剧情境中的情感状态及观众的反响;只有在“演场”的游戏中人类才能展现自由、想象力和创造力。
《惊奇的山谷》就是最恰切的明证。
戏剧空间往往不再是一般意义上仅供演出的场所,而是为表演提供的充满活力的诗意栖地。
在剧场这个奇妙的“演场”,瞬间即永恒,戏剧情景与观众欣赏心理有机交融。
正因此,除了人物形象外,戏剧空间也不失为一种形象;导演者无不为打造个性化的戏剧空间形象苦苦求索、殚精竭虑,彼得·布鲁克也不例外,其剧场空间的探索与生命探寻之间环环相扣、有机交织。
剧场之于布鲁克,就是他诗意的栖地,更是寄托哲思的场域———人类存在的秘密是什么?
人类的命运将如何?
人们能继续生活下去吗……与此相辅相成,布鲁克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我要做戏?
什么是戏剧?
我要做什么样的戏剧……这种“寻找”和“追问”业已成为布鲁克诸多作品的潜在情结和主题原型。
以《惊奇的山谷》为例,其剧情演进、戏剧动作大都依靠密集的语言、错落的节奏,在“言辞与意义的角力”中完成。
剧的开篇,布鲁克运用波斯叙事长诗《飞鸟大会》,以寓言体诗句为全剧的旨趣埋下伏笔,观众不得不思考,飞鸟与剧中人和全剧有怎样的关联,我与飞鸟又有什么相关。
《飞鸟大会》讲的是30只鸟踏上寻找鸟中之王凤凰的旅途,在此过程中它们要穿越7座山谷,即人自我修炼过程的七阶段(祈祷、热爱、认知、禁欲、认主、困惑和寂灭)。
到了最后一座山谷时,它们被挡在真理门外,最后,真理的大门终于打开,它们看到了自己,原来它们自己就是凤凰。
这首诗对布鲁克的吸引力极大,早在非洲之行时就已经将其中的片断付诸排练和即兴演出。
意味深长的是,这部剧取自诗中众鸟要飞跃的第六座山谷———“惊奇的山谷”———是惊奇,也是困惑。
正如诗中不知自身为凤凰的众鸟一样,尚未获得重生的萨米,困于“惊奇的山谷”,迷失、彷徨……。
剧中用了巨大篇幅拼写出但丁《神曲》中的诗句:
人生之旅,我行走过半
却落入森林,四周幽暗
正确的路,已迷失不见
萨米深知自己“身在一片黑暗的森林里,迷失正路”。
因超常的记忆,她被视为奇人,成为了“病患”;与困厄中的萨米一样,夏博朗和卡尔也因为特异的联觉能力被视为“异类”,被排挤在正常生活之外。
在迷失中的萨米困惑、探寻,告别了记忆的废墟,但之后呢?
真的能像凤凰一样重生吗?
剧中极富韵味和美感的台词背后,是感性与理性的并置、现实与幻境的杂糅。
通过演员在“演场”非凡的演技,我们得以由萨米的视角观看世界,考量生命的困惑和人生的悖论:
拥有即是失去,强者恰恰也是弱者;患者是正常人,正常人也是患者。
同时,从萨米等联觉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布鲁克为我们提供了凝视人类身体和大脑这个神秘世界的特殊视角———神经。
神经,关乎身体和精神,却因其隐蔽往往被忽视。
事实上,被高度发达的科技和数字控制的现代人,紧张、焦虑、绝望已经为常态,神经的病痛业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巨大困境。
面对前行中人类的大悲哀,如何学会放弃?
如何勇敢地面对四伏的危机?
反抗还是绝望?
抑或在绝望中反抗……这是人类发展的悖论,是个体人的困惑,更是布鲁克乃至每个个体生命的隐喻。
不是吗?
在这个神秘的世界里,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绊脚石”,我们每个人就是寻求新生的鸟。
由此,不难发现《惊奇的山谷》这部戏,小命题里有大叙述、大格局,也不难探测出暗含其间布鲁克的内心情怀。
1990年代至今,布鲁克愈发推崇极简风格,努力把戏从限制想象力的装饰性叙述中解放出来。
极简灵动的叙事、简约质朴的舞台,为观众留下更多想象和游戏的空间。
正因此,继此前演出中箱子、棍子等道具的妙用后,“地毯”成为了重要的舞台语汇。
早在非洲之行时,地毯就是布鲁克和演员们旅途的必备品。
之后的几十年,地毯这个日常化的生活物件,逐渐成为布鲁克世界各地“演场”的“神器”。
“地毯是一个虽然中性,却富有吸引力的区域,那上面能发生任何事情……将表演限制在地毯上进行,结果充满了奇妙的矛盾:
一方面,缩小表演空间的做法让表演收益颇多。
空间集中以后,演员不再在全剧乱跑,让表演从某种现实主义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地毯变成了一个正式的空间,一个为表演而准备的空间”。
地毯变成了表演空间,一个用来游戏的自由空间;表演的能量和演出的质量在这个特定的空间自在而诗意地流淌。
地毯之于布鲁克是“演场”游戏的载体;更是精神担当的场域。
布鲁克曾说,“只要一到了地毯上,他就担起了责任”。
在《惊奇的山谷》中,只有原木色的三把椅子和一个小方桌,舞台两侧分别是一个衣架、一台小钢琴。
他们被灵活安置于一块乳白色的方形地毯之上,简洁到了极点。
其中地毯所在空间日常、质朴,与早年神话题材和印度史诗等作品中超大、开放的空间迥然不同,却又遥相呼应,相映成趣。
早年布鲁克创作的那些非室内的环境剧场作品,阵容浩大、叙事恢宏。
超大空间这种开放式戏剧空间,是其对人类文化及历史境遇激情豪迈式的戏剧再现。
借助超大空间讲述人类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与文明碰撞中,让东西方文化圆融共处。
与小剧场静观净化不同,超大空间的演出极具“盛典效应”和仪式感,更容易在艺术感染中实现艺术的乌托邦幻想,达成理想与现实的和解。
在超大空间,理想和现实融会的历史瞬间也许就是布鲁克这位艺术家在戏剧这个乌托邦王国称雄的时刻,更是每个有作为的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境界。
而从浩大、开放、称雄为王的世界回归到质朴、通透、无为而治的天地,足见布鲁克宇宙观、生命观及其剧场美学思想的变异与发展。
在《敞开的门》中,布鲁克多次谈到,近年在精神欲求和导演审美上,他更着意“直觉感受”与“凝神静观”。
这恰恰与道禅神似,也契合印度古典哲学中的“斯丰塔”(Sphota)。
对于宇宙人生和戏剧艺术,布鲁克静观自得,似乎已经通透万物,别有妙悟;从而形成了包括《惊奇的山谷》在内的近期剧作“辞约而旨丰”、“体约而不芜”、“余味日新”的特点。
对彼得·布鲁克而言,戏剧是生命的探寻,剧场是内在觉醒的诗意空间。
他一向憎恶僵化,并以大胆的艺术与生命探索反抗僵化的戏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匠艺做派。
“演场”生命能量的探索和众多戏剧创新实践,使他成为了剧场艺术保持持久生命力的象征。
在格洛托夫斯基《迈向质朴戏剧》一书《序》中,布鲁克写道:
“他在工作上的全力以赴、真心诚意和精确严谨只能导致这样一个情况:
向我们提出挑战。
”其实,布鲁克何尝不是一位“在工作上的全力以赴、真心诚意和精确严谨”的戏剧家?
对于我国戏剧人而言,他的存在和所作所为又何尝不是“向我们提出挑战”?
面对彼得·布鲁克这位戏剧前辈,面对其人生与艺术的创新与求索,我们有能力接受挑战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