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docx
《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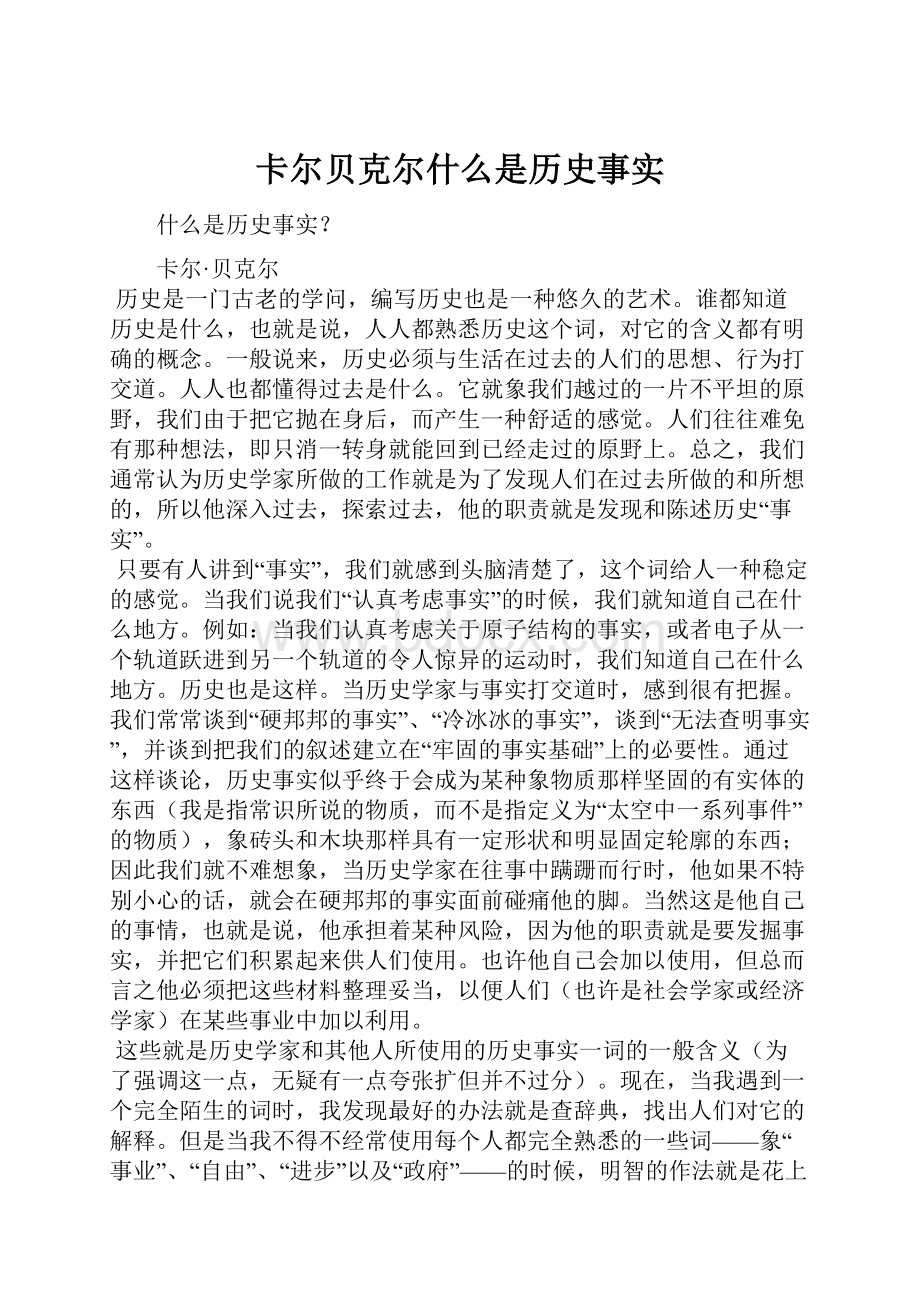
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
什么是历史事实?
卡尔·贝克尔
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学问,编写历史也是一种悠久的艺术。
谁都知道历史是什么,也就是说,人人都熟悉历史这个词,对它的含义都有明确的概念。
一般说来,历史必须与生活在过去的人们的思想、行为打交道。
人人也都懂得过去是什么。
它就象我们越过的一片不平坦的原野,我们由于把它抛在身后,而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
人们往往难免有那种想法,即只消一转身就能回到已经走过的原野上。
总之,我们通常认为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发现人们在过去所做的和所想的,所以他深入过去,探索过去,他的职责就是发现和陈述历史“事实”。
只要有人讲到“事实”,我们就感到头脑清楚了,这个词给人一种稳定的感觉。
当我们说我们“认真考虑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例如:
当我们认真考虑关于原子结构的事实,或者电子从一个轨道跃进到另一个轨道的令人惊异的运动时,我们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历史也是这样。
当历史学家与事实打交道时,感到很有把握。
我们常常谈到“硬邦邦的事实”、“冷冰冰的事实”,谈到“无法查明事实”,并谈到把我们的叙述建立在“牢固的事实基础”上的必要性。
通过这样谈论,历史事实似乎终于会成为某种象物质那样坚固的有实体的东西(我是指常识所说的物质,而不是指定义为“太空中一系列事件”的物质),象砖头和木块那样具有一定形状和明显固定轮廓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难想象,当历史学家在往事中蹒跚而行时,他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就会在硬邦邦的事实面前碰痛他的脚。
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承担着某种风险,因为他的职责就是要发掘事实,并把它们积累起来供人们使用。
也许他自己会加以使用,但总而言之他必须把这些材料整理妥当,以便人们(也许是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在某些事业中加以利用。
这些就是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所使用的历史事实一词的一般含义(为了强调这一点,无疑有一点夸张扩但并不过分)。
现在,当我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词时,我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查辞典,找出人们对它的解释。
但是当我不得不经常使用每个人都完全熟悉的一些词——象“事业”、“自由”、“进步”以及“政府”——的时候,明智的作法就是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思考它们。
其结果往往令人吃惊,因为我常常注意到我一直谈的是词,而不是真实的事物。
是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一个词,同时,我怀疑,至少对我们史学家来说,对这个词比过去作更多的思考是否值得。
因此暂时让历史学家们奔波于过去的原野中去积累冷冰冰的事实吧,我则愿意探究一下,历史事实是否就象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是硬邦邦的,月淘i
固定形态的东西。
在这种探索中,我将提出三个简单的问题。
不错,我可以提出问题,但是我不能保证作出回答。
这些问题是:
1.历史事实是什么?
2.历史事实在哪里?
3.历史事实发生于何时?
请注意,我用的时态是现在时,而不是过去时,比如说,如果我们对“大宪章”这一事实有兴趣的话,那末,我们对它产生兴趣并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缘故,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因为我生活在现代,不是生活在1215年,如果我们毕竟对这个“大宪章”感兴趣的话,那末我们必定是由于它现在是什么,而不是由于它过去是什么而对它感兴趣的。
那末,首先,历史事实是什么呢?
我们来举个简单事实,它就象历史学家经常谈起的那样“简单”,即,“公元前四十九年凯撒渡过卢比孔河”,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而且显然具有某种重要性,因为在任何一部关于伟大的凯撒的历史著作中都提到它。
但这几个事实果真这样简单吗?
它具有我们一般认为是简单历史事实那样清晰的轮廓么?
我们谈论凯撒横渡卢比孔河,当然并不是指他一个人横渡,而是指他和他的军队一起横渡。
卢比孔河是一条小河,我不清楚凯撒的军队渡这条河用了多少时间;但是,这次渡河肯定伴有许多人的许多动作,许多语言和许多思想。
这就是说,许许多多较小的“事实”组成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
恺撒渡过卢比孔河。
如果有一个叫詹姆斯•乔伊斯的人知道并且叙述所有这些事实的话,那么无疑需要有一本七百九十四页厚的书来描述凯撒渡卢洪界河这个事实。
因此,简单的事实最后看来绝不就是一个简单种事实,而是许许多多事实的一个简单的概括罢了。
无论如何,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也有许多人在别的时候渡过了卢比孔河,而为什么只提到了恺撒呢?
为什么两千多年来,全世界都重视凯撒在公元前四十九年渡过了卢比孔河这一简单的事实呢?
这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我只告诉你们事实本身和它的简单轮廓,没有提到和它连在一起的线索,此外,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们,而且,如果我是一个诚实的人,那末我就应该说明为什么没有什么可告诉你们,为什么全然没有。
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但它对我们却是毫无意义的。
当然,实际情况是:
这个简单的事实是有线索牵着的,这就是两千年来它一直受人重视的原因所在.它受到无数其它事实的牵制以致于除非它抛去那个清晰的轮廓,否则就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
除非把它放进孕育它的复杂的环境网中,否则它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而这个复杂的网,就是在凯撤与庞培、与罗马元老院,罗马共和国以及一切参与此事的人们的关系中组成的一系列事件。
恺撒接到罗马元老院的命令,要他辞去在高卢担任的指挥官的职务,他决定不服从,不仅不辞去指挥职务,反而向罗马挺进,并一举夺取了罗马共和国的统治权,最后正如别人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俨然成了统治这个狭小世界的一世之雄。
不错,这条河恰恰位于高卢和意大利的交界,因此凯撤及其军队渡过卢比孔河这一举动已是既成事实,而且随后又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抛开这些重大事件和复杂的关系,横渡卢终孔河这件事就毫无意义了,严格说来,它就根本不成为一个历史事实了。
就事件本身而言,它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它之所以对我们具有某种意义,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由于它作为另外一些事情的象征,是代表一连串事件的象征,而这些事件不得不涉及一些最难以确定的和无形的现实,即恺撒与千百万罗马人之间的关系。
这样,这个简单的历史事实终子证明并不象砖头那样是轮廓分明的、可以测出重量的、某种坚硬的、冷冰冰的东西。
就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来看,它仅仅是一个象征,一个概括许许多多简单事实的叙述,而这些简单事实我们目前还无意加以利用,而且我们不能利用这种概括本身,如果撇开它所象征的一些更为广泛的事实和概括的话。
一般说来,一个历史事多越简单,越清楚,越明确和越可以证实,那么从其本身来说,对我们用处就越少.比较复杂的事实同样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甚至效果会更好。
例如:
“1517年在德国出售赎罪券”这一事实就可以得到彻底证实。
任何人也不会怀疑它.但就事实本身来说,它微不足道,没有任何意义。
它也只是许许多多事实的概括,只是无数遍及德国的赎罪券的买者和卖者在不同时期的许许多多活动的概括,只有把它和其它事实以及更广泛的概括联系起来时,它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还有比这些更不确定、更不明显的事实。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的史学家们(以及其他人)在研究日耳曼原始部落的风尚时,发现了他们称之为日耳曼或条顿民族的乡村公社(Mark)的一种公社体制。
德国的日耳曼乡村公社是当时一位德国史学家受了凯撤所写的《高卢战纪》一书中几段话的影响,以及受塔西佗——一个不满现状的罗马人(他试图通过使原始的德国人理想化来摆脱一种复杂的心情)写的《日耳曼志》一书中某几节的影响,并通过丰富的想象所得到的产物。
这些史学家所写的日耳曼乡村公社,基本上是神话,与现实不符。
尽管如此,日耳曼乡村公社却是历史事实。
德国史学家们关于日耳曼乡村公社的观念在十九世纪思想史中也是一个事实,而且是重要的事实。
很早以前,我就把我在大学里精心整理出来的关于日耳曼乡村公社的笔记转移到了档案箱里。
这些档案箱里装着我研究十九世纪历史的笔记。
我把有关日耳曼乡村公社的笔记与关于俄国乡村公社(Mir)的笔记,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笔记,关于孔德的实证主义的笔记,关于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论述的笔记,关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以及关于当时的其它一些错误想法的笔记都放在一起。
那么历史事实是什么呢?
我决不会去解释这个虚幻的、捉摸不定的名词。
但我暂且可以这样说,史学家感兴趣的就是与过去人们的生活有关的一切事情,也就是一切活动或事件,人们所表达的各种各样的感情,以及人们有过的种种思想,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的确,这类事件就是史学家的兴趣所在。
但是由于这些事件已不复存在,所以,史学家也就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
他所能接触的仅仅是参二事件的有羊谬攀。
简单说来,他接触的不是事件,而是证明曾经发生过这一事实的有关记载。
当我们真正严肃地考虑这些铁的事实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仅是一份证实发生过某个事件的材料。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差距,即:
已经消失了的、短暂的事件与一份证实那一事件的、保存下来的材料之间的差距。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构成历史事实的正是这个关于事实的证明。
如果确实如此,历史事实就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可以使人们想象地再现这一事件的一个象征。
既然是象征,说它是冷酷的或铁一般的,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
甚至评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是危险的,最安全的说法是说这个象征或多或少.是适当的。
因此,这就让我接触到第二个向题,即历史事实在哪里?
不管听起来多么刺耳,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历史事实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柯地方。
我愿意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解释这个说法。
“亚伯拉罕•林肯于1865年4月14日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被暗杀”。
这在事情发生的瞬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件,事变和事实。
但我们在1926年却说它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不能说它过去是一个历史事实,因为那将暗示说它不再是一个历史事实了。
我们说它过去是一个真实事件,而现在则是一个历史事实。
不管真实事件和历史事实两者联系多么紧密,它们却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那么林肯被暗杀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事实现在又在何处呢?
林肯不是现在在“福特剧院”或某个地方被暗杀的(除了在宣传性的文学作品中可能出现以外!
)。
这个真实事件发生在过去,并且永远消失了,决不会再现于现实之中,再也不会为活着的人所经历和证实。
而史学家所关心的恰恰就是诸如此类的永远消失了的事件、活动、思想和感情。
那么,史学家又如何能叙述已经消失了的客观事实呢?
他所以能这样做,就是因为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客观事实被关于它们的暗淡的反映和模糊的印象或观念所代替,而目这些触摸不到的、暗淡模糊的反映和印象都是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所留下的全部东西。
所以这些就是史学家所叙述的,这些就是他的材料,而他不得不对这些感到满足,最根本的原因是,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
这些暗淡的反映和难以捉摸的印象究竟在何处呢?
这些事实又在何方?
如前所述,它们存在于他的头脑中,或者存在于某些人的头脑中,否则它们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可是,我听到有人这样说:
它们在记载里,在原始资料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
林肯被害这一历史事实就是在记载里,在当时的报纸上,在书信中,在日记中,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是在那里,但到底是指哪种意义呢?
记载毕竟是些纸张,在这些纸张上用墨水按照一定格式写了一些东西而已。
甚至这些格式也不是当时就由象林肯被害这类事件构成的。
格式本身只是事件的“历史”,是由某些头脑中还保留林肯被杀时的印象和概念的人写出来的。
当然;我们,你和我,通过看这些白纸黑字的格式,使我们能够在头脑中或多或少地形成一种象作者头脑中一样的印象和概念。
但是如果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种文字格式的记载,或原始资料中的含义,那么林肯被害这一事实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事实了。
你也许会称它为死的事实,但是,一个事实,不仅现在已是死的,而且人们不知道它曾经存在过,或者甚至不知道现在已是死的,肯定称不上是一个事实。
总而言之,历史事实僵死地躺在记忆中,不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
而只有当人们,你或我,依靠真实事变的描写、印象或概念,使它们生动地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时,它才变成历史事实,才产生影响。
正是这样,我才说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子任何地方。
因为,当它不是再现于人们的头脑中,而是躺在毫无生气的记载里的时候,就不可能在世界上产生影响。
可是,你也许要说林肯被害这一事实在世界上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在目前很大,即使在片刻、一小时成一个星期之内,世界上没有人对这个真实事变具有什么印象。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是为什么呢?
非常清楚,因为自从事件发生以后,人们记住了它,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断地想起它,在人们的头脑中反复形成了对它的印象。
如果美国人民不能保持记忆,比方说,象狗那样(我只是这样假定;因为我不是狗,就不敢肯定),那么林肯被杀这一事实是否能在当今世界上产生影响呢?
如果所有的人在四十八小时之后完全忘记了这个意外事变,那末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它还会发生什么形响呢?
十分清楚,恰恰是因为人们有持久的记忆,而且不断地在他们头脑中形成林肯被害的印象,所以宇宙不但包含着保存下来的历史事实,也包含着没有保存下来的真实事件。
但是对我们现在产生影响的,不是短暂的、真实的事变,而是保存下来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之所以产生影响仅仅是因为它至今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现在谈第三个问题——历史事实是指何时?
如果你同意人们一直持有的、十分值得怀疑的观点,那末答案似乎还是相当简单的。
如果历史事实生动地展现在人们头脑中,那么此刻它就是现在的一部分。
但是现在这个词叫人难以捉摸,而且这件事情本身则比这个词更糟糕。
现在是时触一个不确定的点,当你能够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
此刻我头脑中关于现在的印象或概念转眼之间就溜进了过去的行列。
而过去事件的印象或概念却也许总是与将来的印象和概念分不开的.我来举个实例。
我今天早上醒来时,发现在那些使我得到启发或使我感到痛苦的记忆中,有一个模糊的念头,这就是一些我想记起而又记不起来的事情——我肯定这是人们共有的一种体会。
我想不起来我需要记住的究竟是什么;可是我能想起,为了唤起自己的记忆,我曾经作过一些关于此事的笔记。
于是我查阅了我的那本小小的袖珍备忘录——我随身携带的小小的“私人档案局”,里面装满了历史资料。
为了搞一点历史研究,我取出我的备忘录,在第一卷第20页上,找到了这个死的历史事实,“今天付史密斯先生煤费帐1016美元。
”现在备忘录的印象从我头脑中消失,而被另一种印象所代替。
一种关于什么东西的印象呢?
这是由三件多少有点不可分割的事情组成的一种印象、一种概念、一幅图象(随你怎么称呼吧)。
第一种印象就是去年夏天,我自己到史密斯先生那里去买煤;第二个就是我自己产生了一个要付清煤费帐这一念头的印象,第三个就是我自已在四点钟到史密斯先生的办公室去付款。
这个印象,一部分是关于过去做过的事情,一部分则是关于将来要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它们却多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印象展现在找的脑海中。
可能有人要问:
“你讲的是历史,还是人们的日常项事?
”是的,也许史密斯的煤费帐单只是我私人的事,毫无疑问,除了史密斯以外,与任何人无关。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现在想到了柏林会议,毫无疑问,那是历史,是一件真实的事件,它生动地展现在我的记忆中。
但我是由于某种目的才想起了关于柏林会议的印象,而且事实上,人们如果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是不会自找麻烦去回忆历史事实的。
我的目的恰巧就是明天下午三点钟我要在C教室把柏林会议的印象讲给历史系42班的学生听。
现在,我发现与这个过去了的柏林会议的印象有关的,就是明天我自己要去C教室把它讲给我的学生听这样一个一掠而过的印象。
我想象着我站在那里单调地讲着。
我听到那些费劲地说出来的不流畅的句子,我想象着根据当时的情况,学生们的面孔或是聚精会神,或是厌倦不堪,以至使这个关于未来的事件的想象与关于柏林会议这一过去事件的形象的描述融合在一起,并使它更加有声有色,以便这个讲演给我带来荣誉,或者使一些幼稚的头脑明白易懂,或者把这个讲演压缩在五十分钟之内,或者达到其它预期的自的。
那么,这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关于这煤费帐单或柏林会议的混杂的印象,究竟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呢?
我不能肯定,也许它象光速一样飞驰而过,并没有时间性。
总之,对我来说,它是真实的历史,我希望使史密斯先生或者C教室的学生们认为它是可信和真实的。
现在,我已经提出了我的三个问题,并且对它们都作了一些说明。
但我不知道你是否认为它们是离题万里的,或者仅仅是显而易见的,或是新奇的。
如果其中有任何新的东西,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把历史领域看作是外在世界的,部分,并把历史事实看作是真实的事件那种长期形成的习惯造成的。
实际上,客观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历史领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领域,它只是形象地被再创造,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
按照我的想法,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从这里就可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如果你没有感到疲劳的话,我倒愿意谈到其中的一些启示,我将用“第一”、“第二”以及依此类推的方法来论述,就象布道时分几点来讲一样,而不打算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
第一个启示是:
史学家不可能展现某个事件的全过程,即使最简单的事件也不可能,你也许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也是这样看的;但是关于这一点还需要不断加以重复,因为十九世纪的史学家们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之一就是认为:
一个史学家,一个“科学的”史学家将要做的正是“展现所有的事实,让它们为自己辩护”。
一个史学家,除了他头脑中的感光底片以外,他本身将没有什么作为,反映在他感光底片上的客观事实会显示出它们本身的无可怀疑的含义。
尼采以他无与伦比的措词极其确切地描迷了十九世纪的“客观的人”。
事实上,客观的人是一面镜子:
习惯子服从他想要知道的每一件事、希望只是知道它并反映它,他等待着,直等到有些事情出砚了,他就敏感地把自已这面镜子展开,即使那些精灵的轻橄的脚步和一闪而过的动作也不至于成在他的表面和底片上消央。
无论他还具有什么样的“个性”,对他来说似乎都是一种妨碍。
他已经完全把自己看成是外部形式和事件的通道与反映了••••••不管人们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爱或恨,他总是要做他力所能及的事,并提供他所能提供的东西。
如果他做得不多的话,人们也不应该感到奇怪••••••他正在反映的、不断地自我完善的灵魂再也不知道如何去肯定,如何去否定••••••他只不过是一种工具。
••••••他本身什么都不是(几乎什么都不是)!
这种认为史学家是工具的看法的经典表述,见于据说是福斯太•德库朗惹讲的一句名言。
半个世纪以前,法国知识界强烈反对那种认为政治自由是由早期的德国人带进高卢的荒诞的想法。
而福斯太则是这场反对运动的领袖。
一天,他正在给他的学生讲早期法国的制度,这些学生突然鼓起掌来。
福斯太说:
“先生们,不要鼓掌,这不是我讲,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嘴来讲的。
”在整个讲演中,这位平静的、没有偏见的史学家竭力证明野蛮的德国人和法国文明毫无关系。
这当然就是学生们鼓掌的原因,也就是福斯太为什么要告诉学生们那是历史在说话的原因。
所以,二十年来我一直深信:
任何人再也不会相信这样荒谬的想法了。
但是这种想法却仍然经常出现。
仅在几天前,我乘火车去参加历史协会的会议,在火车上,贝弗里奇先生,一位杰出的、受人尊敬的史学家,却武断地对我说(这可能是武断的):
“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展现所有的事实,并且让事实去为它们自己讲话。
”所以我再重申我的看法——二十年来,我一直讲授的就是:
认为史学家要展现全部事实的论点是荒谬的。
因为,首先展现全部事实是不可能的,第二,即使你能够展现所有的事实,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让我们回到这个简单的事实上来,“1865年4月14日,林肯在华盛顿的雁特剧院被暗杀”。
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它只是全部事实的一个陈述,而且也许是会使某一个史学家感到满意的一个陈述。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另一个史学家却会感到不满意。
他说:
"1865年4月14日,林肯正坐在华盛顿福特剧院的一个私人包厢里看戏的时候,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突然向林肯开枪,然后跳到舞台上喊道,‘sicsampertyrannisi’(应该这样对待暴君!
)”。
这也是关于这个事件的一种真实的断言。
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的话,它也陈述了全部事实。
但是它的形式和内容却不同(在文学表达中则是同一回事),因为它比其它的断言包含了更多的事实。
那么,关健就在于对真实事件可以作出任意多的断言(如果有足够的资料就会有无限多的断言),这些断言都是真实的,都是陈述那个事件的,不过有些断言包含的真实多一些,有些包含的少一些而已。
但是史学家却不可能作出描述全部事实的断言,即描述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一切与此事有关的人的全部活动、思想、感情。
因此,某一个史学家将有必要去选择某些与事件有关的断言,并且以某种可靠的方式来表达它们,同时又反对其它的断言和其它的表达方式。
而另一位史学家必然会作出不同选择。
这是为什么呢?
是什么导致一位史学家从特定事件的所可能真实的断言中作出某些断言,而不是其它断言呢?
原因是:
这位史学家头脑中的某种目的决定着他要这样做。
而且同样地,他头脑中的这种目的将确定他从事件中所得到的确切的意义。
事件本身(即事实)并没有说明任何东西,并没有提供任何意义,而是史学家在谈论,在给这些事件加上某种意义。
从这里可以得到第二条启示:
这就是史学家不能消除个人在观察上的偏差。
当然任何人也不能避免这种偏差,据我看来,即便自然科学家也不能避免。
我们和宇宙打交道仅仅是为了适应我们的需要。
我们可以说,甚至象理论物理学家的那些最客观的解释也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而只是因为这些解释最有利于人类的某些需要和目的。
然而,物理学家比起史学家来,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或者说至少以不同的方式,消除个人在观察上的偏差,因为物理学家直接接触的是外在世界,而史学家却不是这样。
物理学家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事件,而史学家仅仅探索事件的遗迹。
如果我单独一个人在宇宙中,我的手指在一块锋利的岩石上划破了一条口子,我决不会相信,除了我关于岩石和对破了的手指的意识以外,还存在其它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十个人在同一块锋利的岩石上,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划破了手指,通过比较各自的印象,我们可以推断出:
除了意识之外,还有某种东西存在。
有一个外在世界存在。
物理学家可以任意在岩石上一次又一次地划破手指,同时让其他人也这样做,直到他们全都相信了这个事实为止。
正如爱丁顿所说,他能够为了获得某种特定的现象而随心所欲地一次又一次搞出物质世界规则的指针读数,直到他和他的同事满意为止。
当他们都感到满意时,他们就得到了一个解释,即所谓真理。
但是假定一个物理学家不得不根据形形色色的人整理的各种记录来作出关于过去所进行的实验的结论(每一项实验都只做过一次,而且不能重复),那末,他所必须接触的外在世界就只能是这些记录。
史学家的情况也是这样。
因为他所不得不接触的唯一的外在世界就是事件的记录。
他的确可以任意地翻阅资料,他还可以让许多其他史学家翻阅它们。
他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确定某些事件,即某些“事实”,从而达到一致的看法,例如,人所共知的“独立宣言”是在1776年7月4日投票通过的。
但对这一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则不可能用这样方法达成一致的看法,因为这一事实在其中占有一定位置的那一系列事件,不可能因为人们要观察它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而在不同情况下反复发生。
史学家只得根据那仅有的一次行动去判断一系列事件的重要性,而这一行动永不会再现,并且由于资料的不完整而不能完全弄清楚和完全肯定。
这样,个人的因素就掺杂到想象中的事实和它们的意义之中。
任何一个事件的历史,对两个不同的人来说绝不会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人所共知,每一代人都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写同一个历史事件,并给它一种新的解释。
为什么人们一代接一代地对一系列已经消失了的同一些事件产生不同的印象呢?
因为我们对于实际事件所想象的图景总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
(1)由我们所能认识的实际事件本身决定的;
(2)由我们个人的目的、愿望、偏见决定的,这些个人的目的、愿望和偏见都掺杂在我们对它的认识过程中。
真实事件为想象的图景提供了某种东西,但具有这些想象图景的头脑也总是同样地为它提供某种东西。
这就是历史的任何一方面都比不上历史编纂学(历史的历史)那样迷人或启发人的原因:
历史编纂学就是一代一代地想象过去是什么样的历史。
不了解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本身是如何看待历史的,就不可能理解某些伟大事件的历史。
例如:
如果我们知道美国和法国革命的领导人对于古典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