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筹架构企业回归A股首发上市实践与监管研究下.docx
《红筹架构企业回归A股首发上市实践与监管研究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红筹架构企业回归A股首发上市实践与监管研究下.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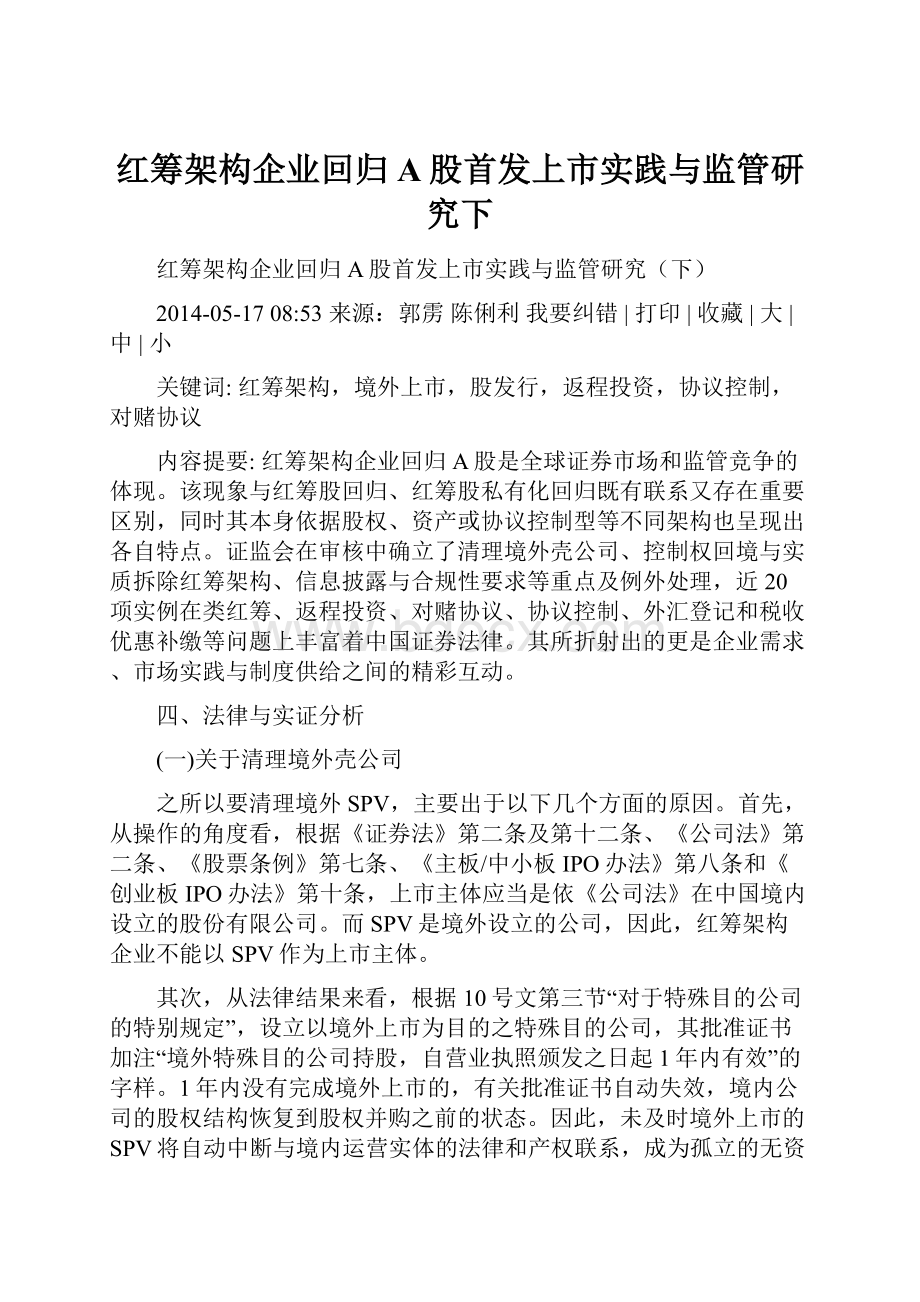
红筹架构企业回归A股首发上市实践与监管研究下
红筹架构企业回归A股首发上市实践与监管研究(下)
2014-05-1708:
53来源:
郭雳陈俐利我要纠错|打印|收藏|大|中|小
关键词:
红筹架构,境外上市,股发行,返程投资,协议控制,对赌协议
内容提要:
红筹架构企业回归A股是全球证券市场和监管竞争的体现。
该现象与红筹股回归、红筹股私有化回归既有联系又存在重要区别,同时其本身依据股权、资产或协议控制型等不同架构也呈现出各自特点。
证监会在审核中确立了清理境外壳公司、控制权回境与实质拆除红筹架构、信息披露与合规性要求等重点及例外处理,近20项实例在类红筹、返程投资、对赌协议、协议控制、外汇登记和税收优惠补缴等问题上丰富着中国证券法律。
其所折射出的更是企业需求、市场实践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精彩互动。
四、法律与实证分析
(一)关于清理境外壳公司
之所以要清理境外SPV,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操作的角度看,根据《证券法》第二条及第十二条、《公司法》第二条、《股票条例》第七条、《主板/中小板IPO办法》第八条和《创业板IPO办法》第十条,上市主体应当是依《公司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而SPV是境外设立的公司,因此,红筹架构企业不能以SPV作为上市主体。
其次,从法律结果来看,根据10号文第三节“对于特殊目的公司的特别规定”,设立以境外上市为目的之特殊目的公司,其批准证书加注“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持股,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1年内有效”的字样。
1年内没有完成境外上市的,有关批准证书自动失效,境内公司的股权结构恢复到股权并购之前的状态。
因此,未及时境外上市的SPV将自动中断与境内运营实体的法律和产权联系,成为孤立的无资产、无业务、无人员的境外壳公司。
其对红筹架构企业的回归而言,没有太大的存在价值。
最后,就法定的发行条件而言,《主板/中小板IPO办法》第十三条和《创业板IPO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有股权清晰的法定发行条件。
而红筹架构下的境外SPV设立在BVI,Cayman等经济法律环境宽松的境外离岸注册地,缺乏透明度,跨境核查难度大。
因此,为了满足境内发行条件,境外SPV应予以清理。
1.类红筹问题(例外A)
尽管如此,上述要求存在例外情况,其中一个便是例外A——外籍控制人。
由于业界人士常将实际控制人(造壳主体)为境外法人或境外自然人所搭建红筹架构称作“类红筹架构”(如图2所示),因此,例外A实际上指:
当具有类红筹架构背景的境内运营实体(以下简称“类红筹架构企业”)拟A股IPO时,与其有关联的境外SPV无须拆除。
(图略)
图2:
类红筹架构(以依顿电子为例)
允许例外A存在具有合理性。
由于类红筹架构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境外自然人或境外法人,因此,类红筹架构企业和境外SPV都属于外资控股。
类红筹架构企业实际上是“真外资”{29}。
对于该企业,因为其注册在境内并拟在境内A股IPO,所以,证监会可依据上市地原则和注册地原则予以管辖[如依据《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外经贸部资发[2001]538号)规定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发行股票的条件进行IPO审核]。
但对于境外SPV,由于其注册在境外且实际控制人为境外自然人或境外法人,注册地原则和属人原则都不适用。
因此,不能过度强调对其的管辖权和我国法律的域外效力,而要求境外投资者将境外SPV全部清理。
然而,如果境外实际控制人是通过境外SPV间接控制类红筹架构企业(拟境内上市主体),证监会仍可基于股权清晰的法定发行条件,核查该企业的境外层次;并建议有关层次尽量简单和透明。
类红筹架构带来的一个监管疑问在于:
如果境内实际控制人变更了国籍或取得了境外居民身份(以下简称“变化身份”),是否将其已搭建的红筹架构视为类红筹架构来监管?
在红筹上市阶段,实际控制人变化身份是为了减少境外上市审批环节。
在红筹架构企业回归阶段,实际控制人变化身份是为了适用例外A保留境外SPV,使红筹架构免予拆除。
如前所述,例外A包括“架构设立后取得境外居民身份”的情形,即境内运营实体的实际控制人(境内自然人)在红筹架构搭建完成后才取得境外居民身份。
由此可见,目前证监会采取“身份外观标准”{30}肯定变化身份行为的影响,换言之,将原红筹架构视为类红筹架构来监管,允许法律意义上现已取得境外身份的实际控制人保留境外SPV并通过境外SPV间接控制境内上市主体。
例外A所体现的监管态度得到了实践中成功案例的印证。
向日葵成功A股IPO即为代表。
向日葵的实际控制人吴建龙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居民。
2007年11月26日,取得R593891(A)号香港居民身份证。
图3为2007年向日葵有限(向日葵的前身0存在的红筹架构,图4为2010年向日葵申请A股IPO时的股权架构。
通过对比可知,在向日葵A股IPO时,吴建龙既直接持有向日葵45.54%的股权,又通过境内公司光华担保间接持有向日葵1.52%的股权,还通过香港优创(境外SPV)间接持有向日葵25.6%的股权。
有关的境外SPV得以保留而没有与上市主体向日葵脱钩,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变化身份以适用例外A的行为得到认可。
当然,为了达到股权清晰的发行条件,有关境外层级得到了简化。
2009年9月1日,SFHCL将其持有的香港优创100%股权转让给吴建龙。
由此,吴建龙直接持股香港优创。
(图略)
图3:
2007年向日葵的红筹架构(类红筹架构)
(图略)
图4:
2010年向日葵申请A股IPO时的股权架构
目前,我国涉及变化身份问题的法律规范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是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的批复:
《关于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的中国自然人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出资者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汇综复(2005)6个号,以下简称“64号文”)。
它规定:
“……中国公民在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前在境内投资举办的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二是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六部委{31}联合发布的10号文。
其第五十八条规定,“境内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变更国籍的,不改变该公司的企业性质”。
这两范性文件都否定变化身份对行为前企业可获得的待遇或企业性质的影响。
显然,证监会在变化身份问题上的态度与上述文件精神相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证监会方面对类红筹架构企业回归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
2.返程投资问题(例外B)
要求一的另一种例外情形是前述例外B:
其控股上市主体的资金来源于境外融资或境外经营自然形成的境外资金,即不存在返程投资问题。
这主要是考虑到实际控制人可以保留境外SPV作为融资平台并通过境外SPV持有境内上市主体的部分股权。
一些业内人士在理解例外B所谓的“不存在返程投资问题”方面存在疑问。
以誉衡药业的成功回归为例说明。
誉衡有限(誉衡药业的前身)的实际控制人为朱吉满、白莉惠夫妇。
2006年,为了在日本上市,搭建了图5的红筹架构。
其中,誉衡国际受让誉衡有限100%股权的资金来源于日本居民井関清对誉衡国际优先股的认购款(放弃日本上市计划后,该款项转为借款)。
2010年,誉衡药业申请A股IPO。
此时,实际控制人朱吉满、白莉惠既通过境内公司恒世达昌间接控股誉衡药业,又通过誉衡国际(境外SPV)间接持股誉衡药业(如图6所示)。
此外,境外SPV作为中间环节,如BRIGHTLUCK,BRIGHTVISION、BRIGHTCAREER和CHINAGLORIA,都与誉衡药业脱钩。
(图略)
图5:
2006年誉衡有限存在的红筹架构(股权控制型)
(图略)
图6:
2010年誉衡药业申请A股IPO时的股权架构
然而,有观点{32}认为,誉衡药业虽能证明誉衡国际收购誉衡有限的资金来自境外借款,但其招股书中明确披露,誉衡国际“为公司董事长朱吉满等设立在中国境外的返程投资公司”,因此,不属于例外B所谓的“不存在返程投资问题”的情形,理应清理SPV。
但誉衡药业在2010年6月23日境内上市时,其实际控制人却,保留了境外SPV(誉衡国际)升通过其持有股权,令人费解。
解答这一疑惑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例外B中的“返程投资”。
从横向上看,目前,跨境监测统计方面对返程投资的定义主要有: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的定义——“返程投资指一个经济体内某实体的资金在投资于另一经济体的某个居民实体后,又投资于第一个经济体内的另一实体。
第二个经济体内的实体本身通常只有有限的业务。
(返程投资可能有两个或其他中间经济体。
)”{33}
(2)IMF统计部《协调的直接投资调查指南》的定义——“返程投资是指,一个经济体(东道国经济体)内某实体的资金被投资于第二个经济体(中转经济体)内的某居民实体,然后重新投资于第一个经济体内的某实体。
就中转经济体内的实体而言,其本身所开展的活动通常有限”。
{34}从字面上看,这两种定义都将返程投资界定为一种存量资本往复运动的行为,无法反映红筹架构企业返程投资时因境外融资而导致增量资本入境的情形。
事实上,根据返程投资目的的不同,返程投资可分为融资性返程投资和非融资性返程投资两大类。
前者以境外融资为目的,并通过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来完成,融资完成后会导致增量资本入境。
后者涉及过渡性资本外逃{35},一般不涉及增量资本入境,只是纯粹的境内资本存量的往复运动,其目的主要有:
政策寻租(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在诸多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财产保护与非法转移(获得国外更好的财产保护或进行跨境洗钱)和金融投机(利用境外更多的投资避险工具)等{36}。
可见,从资金来源上看,融资性返程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境内资金和境外融资的结合,而非仅来源于境内资金,即俗称的“假外资”。
红筹架构下两类返程投资的结构基本相同,均是境内自然人先出境设立境外SPV(第一步)再通过该境外SPV对境内企业进行投资与控制(第二步),唯一的区别就是返程时(即第二步)的资金来源不同。
因此,对于红筹架构企业回归而言,当返程时的资金仅来源于境内资金时(属于非融资性返程投资),其既不是真正的“走出去”,也不是真正的“引进来”,境外SPV只是中间环节,没有太大的存在必要,加上其目的比较复杂(如政策寻租等),回归A股IPO时理应清理掉。
而当返程时的资金中还有部分来源于境外融资{37}时(属于融资性返程投资),如果境外SPV仍有必要存在(境外VC/PE仍愿继续投资或境外融资协议尚未履行完毕等),回归A股IPO时可继续保留境外SPV作为境外融资平台,但要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资金来源为境外资金。
因此,红筹架构企业回归时境外SPV可免予清理的应是融资性返程投资,例外B所指的“不存在返程投资”应理解为不存在非融资性返程投资(假外资)。
对例外B作上述理解,区别对待两类返程投资不仅是证监会审核要求的应有之义,也符合我国最新的立法趋势。
从纵向上看,我国法律关于返程投资的规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一网打尽到区别对待的过程。
2005年以前,我国并无关于返程投资的专门规定。
2005年1月24日和4月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出台了《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11号,以下简称“11号文”)和《关于境内居民个入境外投资登记及外资并购外汇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29号,以下简称“29号文”),开始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管理监控的范围。
其中,11号文不区分目的地对境外投资和跨境换股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管。
如11号文第二条规定,跨境换股行为要取得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
29号文第八条则首次定义了特殊目的公司:
“特殊目的公司系指境内居民个人为其实际控制的境内企业权益在境外筹资目的而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结束了原先特殊目的公司无境内法律身份的状况。
法律对融资性返程投资的认可和保护初见雏形。
2005年10月23日颁布的75号文(停止执行11号文和29号文)重新定义了特殊目的公司并首次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界定了受法律保护与规范的返程投资(即融资性返程投资):
本通知所称“特殊目的公司”,是指境构居民法人或境内:
居民自然人以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在境外进行股权融资(包括可转换债融资)为目的而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
本通知所称“返程投资”,是指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对境内开展的直接投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购买或置换境内企业中方股权、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及通过该企业购买或境内资产、协议购买境内资产及以该项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向境内企业增资。
同时,根据75号文,设立或控制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跨境换股等行为只需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表明法律对融资性返程投资的规范由堵到疏、由严到宽。
2005年至2011年,75号文配套的操作规程陆续出台。
其中,2011年出台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舍理操作规程〉的通知》(汇发[2011]19号,以下简称“19号文”)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的表述并对其进行严格的监测和管控。
如19号文规定:
将境内居民个人不属于75号文所指“特殊目的公司”性质的境外企业对境内进行的直接投资,在如实披露其境内控制人信息后标识为“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
由此可知,19号文的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实际上即是本文所述的非融资性返程投资。
2013年5月11日出台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及配套文件的通知》(汇发[2013]21号,简称“21号文”,其废止了19号文)明确界定了受法律保护的“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
如其规定:
境内个人未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的,但可提交能证明其境外权益形成合法性的证明材料(境外权益形成过程中不存在逃汇、非法套汇、擅自改变外汇用途等违反外汇管理法规的行为),可为该外国投资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办理基本信息登记,并在外汇局相关业务系统中将其标识为“个人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
(“返程投资情况”选项含义)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本企业外方股东直接或间接地被境内居民持股或控制,但是该外方股东不属于特殊目的公司。
本企业保证外方股东直接或间接地被境内居民持股或控制的过程符合中国和注册地法律规定,不存在逃汇、非法套汇、擅自改变外汇用途等违反外汇管理法规的情况(或相关违规行为已接受外汇管理部门查处)。
至此,我国初步构建了针对融资性返程投资和非融资性返程投资不同的监管框架。
尽管从理论上可以对融资性返程投资和非融资性返程投资进行定性,但要从量上区分这两类返程投资却不太容易操作。
如前所述,两类返程投资在红筹架构下的唯一区别是返程时资金来源不同。
其中,融资性返程投资的资金来源是境内资本和境外资本的结合。
但要融入多少境外资本,发生多少增量才属于融资性返程投资,进而区别于非融资性返程投资,并在红筹架构企业回归时适用例外B?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参考10号文关于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方面的规定。
10号文第九条第三款规定:
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但该境外公司认购境内公司增资,或者该境外公司向并购后所设企业增资,增资额占所设企业注册资本比例达到25%以上的除外。
根据该款所述方式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以外的外国投资者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高于25%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据此,可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的是认购增资和“实际控制人以外的外国投资者”出资的行为且增(出)资额占注册资本至少(高于)25%的情形。
这些情形下带来了至少25%的增量资本,当然属于融资性返程投资。
相反,如果无增资或出资或增量资金低于25%,则在法律上视为非融资性返程投资,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因此,可以25%的比例为参考,对两类返程投资进行量上的区分。
在誉衡药业的案例中,正如其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其确实存在返程投资,但很明显属于融资性返程投资,因为其返程投资的资金来源于日本居民井関清对誉衡国际优先股的认购款(后转为借款)。
由于有关融资协议尚未履行完毕(誉衡国际仍欠井関清本金333.34万美元及相应利息),因此,其实际控制人保留境外融资平台誉衡国际,并通过誉衡国际间接持有誉衡药业的部分股权,符合例外B免予清理特殊目的公司的情形。
实践中成功过会的案例并未与证监会的审核要求相违背。
(二)关于控制权回境与红筹架构的实质拆除
为了还原上市主体真实的股权状态,控制权要转回境内。
但同时为了不增加红筹架构企业回归A股上市的负担,允许其保留部分外资股权,以享受有关的优惠待遇。
实践中,红筹架构企业回归时往往已引进境外VC/PE进行融资性返程投资。
因此,控制权转回境内意味着境外VC/PE的退出或以其他方式(如通过境内人民币基金)参股境内上市主体。
然而,由于境内外法律和上市政策不同,引入VC/PE时当事方约定的一些受境外法律保护、为境外上市政策允许的特殊权利安排,未必会得到境内法律的认可以及证监会的核准,很有可能会对红筹架构企业的回归构成实质性的障碍。
这方面以对赌协议最为典型。
1.对赌协议问题
“估值调整机制”(ValuationAdjustmentMechanism,以下简称“VAM”)是私募投资中常见的合约安排,在引入我国时被译为“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的产生是为了弥合投资者与被投资公司(或其实际控制人、管理层等)在投资决策当时对公司估值的差异,促成融资交易的发生。
由于公司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处于信息劣势一方的投资者对公司的估值比较低,处于信息优势一方的被投资公司(或其实际控制人、管理层等)则对公司的估值比较高。
因此,在达成投资协议时,投资当事人先搁置争议,约定一种估值进行投资。
同时,约定附条件的估值调整机制。
以投资者先按高估值进行投资的情形为例。
在这种情形下,估值调整机制(对赌协议)一般规定如下:
如果被投资公司在约定的时间未能达到约定的经营收入、利润等业绩目标(业绩对赌)或未能成功上市(上市时间对赌),则投资者有权获得现金补偿(现金对赌),或获得股权补偿或有义务以一定价格售出其持有的股份(股权对赌)。
{38}
在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赌协议是被认可的。
如2011年10月4日,美国法院肯定了中华网投资集团(CDCCorporation,以下简称“CDC”){39}与美国一家对冲基金EvolutionCapital(以下简称“EC”)的对赌协议,并裁定对赌失败的CDC需向EC支付高达6540万美元的赔偿。
据CDC提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的20-F文件{40}披露,2006年11月,CDC发行可转换优先债券时,与EC签订了债券购买协议。
该协议约定了对赌条款:
若CDC软件和CDC游戏(均为CDC旗下子公司)不能在2009年11月13日前完成IP0,EC将有权要求公司赎回债券,赎回价格须加上应计及未付利息,利息按2006年11月13日至赎回日支付,惩罚性年利率为12.5%。
2009年8月,只有CDC软件赶在了协议规定的11月之前登陆纳斯达克,募资5760万美元。
CDC游戏上市最终未果。
2010年3月,EC起诉CDC违约并索赔。
2010年11月12日,纽约高等法院宣布批准EC针对CDC的初步禁制令。
根据法庭判决,CDC不得在诉讼进行期间单方面废除高级可转债的债券购买协议,也不得对相关条款做出任何肯定或否定。
2011年10月4日,法院裁定CDC必须向EC支付高达6540万美元的赔偿。
由于截至2011年二季度,CDC的现金及短期投资仅8067万美元,因此,CDC向美国破产法院提交了破产保护申请。
2012年9月6日,美国乔治亚州北部地区破产法院下达了判决书,确认执行CDC第二次修订的联合重组计划。
{41}
相比之下,对赌协议在我国的合法性却一直饱受争议。
2012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终于对首例私募对赌纠纷案件“海富案”{42}作出再审判决{43},就对赌协议的合法性问题落槌:
一方面,否定了股东与公司之间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对赌条款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认可股东与股东之间对赌条款的合法有效性。
而此前,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认定涉案的对赌条款因违法而无效。
“海富案”中涉及的《增资协议书》约定,海富公司以现金2000万元人民币对众星公司增资,占众星公司增资后总注册资本的3.85%,香港迪亚公司占96.15%。
案争的对赌协议是《增资协议书》的第七条第
(二)项内容——如果众星公司(后更名为世恒公司)2008年实际净利润完不成3000万元:
A.海富公司有权要求众星公司予以补偿(以下简称“A约定”);B.如果众星公司未能履行补偿义务,海富公司有权要求香港迪亚公司履行补偿义务(以下简称“B约定”);C.补偿金额=(1-2008年实际净利润/3000万元)×本次投资金额(以下简称“C约定”)。
关于上述对赌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海富公司(股东)和世恒公司(被投资公司)之间的A约定和C约定“使得海富公司的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世恒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对于一审法院、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八条关于“企业净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的规定”之规定认定海富公司和世恒公司之间的A约定和C约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是正确的。
同时,其认为二审法院将海富公司18,852,283元(=2000万-计入注册资本的115万)的投资定性为“名为联营,实为借贷”没有法律依据。
另外,香港迪亚公司对于海富公司的补偿承诺(即股东之间的B约定和C约定)“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
判决颁布后,一系列引人关注的问题随之而来。
例如,司法实践在对赌协议合法性问题上的最新进展会不会影响证监会绝对禁止上市主体存在对赌协议的态度?
境外VC/PE通过对赌协议获得的合同权利是否有望在红筹企业架构回归过程中得以保留?
长期以来,证监会通过窗ロ指导、中介机构培训和会议发言等多种非书面形式要求拟上市公司车申请上市前终止所,有的对赌协议。
{44}红筹架构企业当然也不例外,引进境外VC/PE时约定的对赌条款,也必须在A股IPO前清理完毕而不能保留。
(图略)
图7:
日海通讯的红筹架构(资产控制型)
日海通讯的回归验证了证监会的上述态度。
图7为日海通讯实际控制人王文生搭建的红筹架构。
在引入境外VC时,王文生、周展宏以及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IDGTECHNOLOGYVENTUREINVESTMENTS,LP)于2003年7月26日签订了《日海投资协议》,并约定上市时间对赌条款:
“发行人成立之日起四年内,若公司仍不能成功上市,IDGTECHNOLOGYVENTUREINVESTMENTS,LP和周展宏均有权要求王文生为首的经营队伍回购其持有的日海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份,回购价格为提出回购时相关股份所对应的资产净值,王文生先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若王文生先生拒绝购买周展宏先生的股份,周展宏先生有优先购买IDGTECHNOLOGYVENTUREINVESTMENTS,LP股份的权利。
”
图8为日海通讯申请A股IPO时的股权架构。
王文生通过境内公司海若技术、易通光间接控制日海通讯,符合控制权回境的审核要求。
此外,境外SPV作为中间环节,如AllfmeMetrovision,Dotcom和日海国际,都与日海通讯脱钩,符合清理境外壳公司的审核要求。
另外,境外VC(1DGVCII.IDGVCIII)并未退出而是通过IDGVC(HK)参股日海通讯。
同时,境外VC放弃通过上述对赌协议获得的股份回购权(因日海国际未能在规定时间实现海外上市,因此境外VC获得要求王文生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的权利),“《日海投,资协议》中关于回购日海国际出资的相关约定亦不再执行”。
可见,日海通讯在上市之前,有关的对赌协议已终止,符合证监会方面的要求。
(图略)
图8:
日海通讯申请A股IPO时的股权架构
根据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