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磨坊 13 图鲁斯劳特雷克传.docx
《红磨坊 13 图鲁斯劳特雷克传.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红磨坊 13 图鲁斯劳特雷克传.docx(3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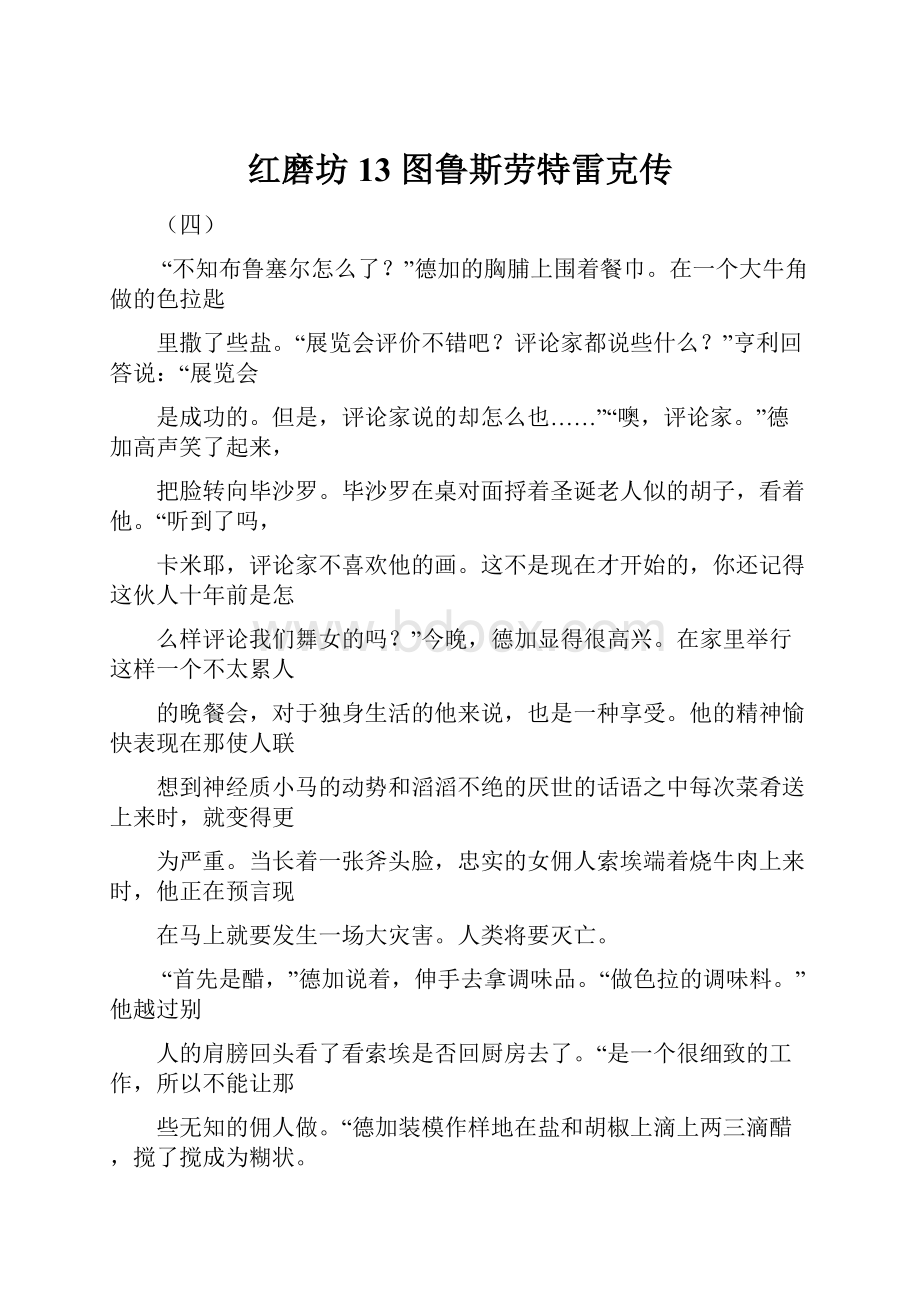
红磨坊13图鲁斯劳特雷克传
(四)
“不知布鲁塞尔怎么了?
”德加的胸脯上围着餐巾。
在一个大牛角做的色拉匙
里撒了些盐。
“展览会评价不错吧?
评论家都说些什么?
”亨利回答说:
“展览会
是成功的。
但是,评论家说的却怎么也……”“噢,评论家。
”德加高声笑了起来,
把脸转向毕沙罗。
毕沙罗在桌对面捋着圣诞老人似的胡子,看着他。
“听到了吗,
卡米耶,评论家不喜欢他的画。
这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你还记得这伙人十年前是怎
么样评论我们舞女的吗?
”今晚,德加显得很高兴。
在家里举行这样一个不太累人
的晚餐会,对于独身生活的他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他的精神愉快表现在那使人联
想到神经质小马的动势和滔滔不绝的厌世的话语之中每次菜肴送上来时,就变得更
为严重。
当长着一张斧头脸,忠实的女佣人索埃端着烧牛肉上来时,他正在预言现
在马上就要发生一场大灾害。
人类将要灭亡。
“首先是醋,”德加说着,伸手去拿调味品。
“做色拉的调味料。
”他越过别
人的肩膀回头看了看索埃是否回厨房去了。
“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所以不能让那
些无知的佣人做。
“德加装模作样地在盐和胡椒上滴上两三滴醋,搅了搅成为糊状。
“现在是油。
”他的态度变得一本正经起来。
“卡米耶,你是怎样加调味汁的?
满满的,还是一点儿?
”“怎么都行,鹰是不会为了一棵莴苣而吵个不停的,是吧。
”
毕沙罗笑了。
德加又转过脸来看着亨利。
“喂,听到了吗?
我为什么要花一些时间讲调味汁
的事呢?
说印象派画家不懂是说不过去的。
在盐里放些大蒜,再加上些油,搅和一
下就算了,放多少都没关系?
印象派是不是都是那种人呢?
那么,是不是不在意素
描、解剖学,那些细致的地方呢?
没有辛辛苦苦地苦练技巧吗?
如果他们说,印象
派的印象就是饱蘸颜料,在画面上涂上粉红色和蓝色,就算完成了。
那又有什么不
好呢?
”“喂,喂!
德加,你不要那么兴奋嘛!
”用安慰似的口吻说话的是毕沙罗。
“你把莴苣弄得满桌都是了。
“谁兴奋了?
我是这样镇静!
”德加高声地说着,同时把莴苣叶扔向两边。
德加装出副高傲、毫不在意的样子,把脸转向客人,对亨利说:
“你讲给我听
布鲁塞尔的事。
你自然已经看到过圣·格德乌尔和布鲁盖尔的祭坛了?
很不错吧?
但是,你有时间去美术馆吗?
所谓完美的画就是指这个。
你,没有
一点错!
无论是那只手,还是那美丽的衣裙,如果有人比这画得还要好的话,那就
成了神了。
我个人觉得,就是神也不过如此。
不过不是听说你决斗了吗?
你不要一
声不吭地坐着,给我们讲一讲吧。
”亨利早有被询问的思想准备,因为蒙马特尔正
流传着他参加决斗的流言蜚语。
“还没到那种地步,德加先生。
”亨利的脸红了。
“不过我向名叫德·格鲁的
人挑战了。
他说了凡·高的坏话,我实在难以容忍。
是在展览会的讨论会上,大家
干杯时发生的。
”亨利边叙述着当时的情景,也想起了那热闹的宴会。
铺着白布的
长桌,闪闪发光的酒杯,衬衫胸前徽章的亮光,谈话声中搀杂着刀叉声。
不过,突
然,德·格鲁引起了亨利的注意。
他是个有着一头金发、面色苍白的唯美主义者。
他在桌子的左侧,挥舞首戴着紫石英戒指的手,主张展览会不该邀请凡·高。
“为
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疯子。
疯到竟可以削落自己的耳朵。
关于他的作品,是的,
对于一个原来就是精神病患者抱有期待,这难道不可笑吗?
”亨利拼命地抑制自己,
然而,不知不觉这种忍耐输给了愤怒。
“德·格鲁先生!
”亨利在桌面上猛击一拳,由于用力太大,桌上的酒杯都发
出了丁丁冬冬的声响。
连得侍者都拿着香槟酒瓶呆立在那儿不动了。
“攻击一个不
能保护自己的人只能是卑鄙的小人。
伟大的天才都被你这样的傻瓜唤成了疯子!
凡·高如果在这儿的话,会把你打倒在地的,当然也许会原谅你。
这,我不清
楚。
但是,我是他的朋友,因此我不原谅你。
我真想和你用剑决一胜负,砍下你两
只耳朵。
如果愿意的话,哪怕是枪也无妨……”“如果是吐鲁斯·劳特累克丧命的
话,我就继续挑战!
”修拉喊着站了起来。
一下子哗然起来。
德·格鲁结巴着辩解似地说着什么。
但是俱乐部会长大发雷
霆,并不好言相劝地把他赶了出去。
“因为这,才没有决斗成。
”亨利看着德加,不好意思地微笑着结束了叙述。
“德·格鲁把餐巾往桌上一扔,大步地走了出去。
会长代表俱乐部表示了歉意,
事情这才解决。
”“太精采了!
”德加大为感动地说。
“你的话使我想起了《奥林
匹亚》,由于这幅画,引起了很多地方发生了争执,有的人天才蒙蒙亮就起床,去
布洛涅的森林里决斗,结果得了感冒死了。
你还记得吗?
卡米耶,说起《奥林匹亚
》,那位做模特儿的姑娘也不知怎么样了?
真是个可爱的姑娘。
叫什么名字来着?
”
“维克托里努,叫维克托里努·缪兰,现在都有一个孩子了吧。
”“胸部长得那么
好的女人可不常见啊。
”德加追忆着,臀部也是梨子形的,长得很可爱。
她的举止
绝不是一个小姑娘……”德加看了看表,“唉呀,已经八点了!
我和迪奥兄妹约好
晚饭后去听音乐的,克莱曼蒂内说要为我弹莫扎特的曲子。
音乐要数莫扎特的最棒
了,他可真是个天才呐!
”吃完饭,亨利夸放了糖的桔子好吃,上了年纪的佣人高
兴得脸都红了。
“但是不合我的口味”,德加离开公寓时说:
“本人对于自己的杰作很有自信,
一年里没有一天不做菜的。
女人一旦自信自己有本领了,她的眼里也就不考虑别人
的爱好了,所以真可怕。
”毕沙罗在马路拐角处告了别。
他把圆圆的黑帽沿拉到眼
眉处,朝北站方向走去。
德加和亨利决定步行到迪奥兄妹住的弗罗肖街。
正值寒风
凛冽的一月的傍晚。
偶然吹来的一阵大风吹得每家的百叶窗都咯嗒咯嗒响。
水坑里
的水掀起了波澜。
刚踏上楼梯,就传来了德杰莱·迪奥那低音笛奏出的深沉的琶音和着弟弟弗鲁
特吹的轻快的音阶。
这种乐器可以使人联想起在森林尽头玩得正酣的母子。
德加按了电铃,马上所有的声音都突然停了下来。
“请,快里面请。
”德杰莱·迪奥满面笑容地开门迎接他们:
“来得正好,我
们刚开始演奏一支非常好的曲子。
”德杰莱·迪奥留着威严的八字胡,鼻子青筋暴
出,给人的印象,与其说他是歌剧院有名的低音笛演奏家,还不如说他是好喝酒的
马夫。
他从两人手中接过帽子和外套,挂在化妆室,一边说:
“克莱曼蒂内正在厨房
准备咖啡。
咖啡和音乐很融洽,啤酒也行。
对了,排练丹霍伊扎时,瓦格纳像灌水
似地喝啤酒,那个歌剧让排练了一百五十次,那人也够厉害的。
因此,在初演时,被扔了臭鸡蛋。
这下可不合算了呀。
”他一边说着,把客人
请到了会客厅。
装饰稍有些过度的屋子里,已有了人在那儿。
刚跨进屋子,几乎同
时克莱曼蒂内快步地走了进来。
由于厨房炉子的热气,脸通红通红,她很快地环视
了一下屋子,脸色变得忧郁起来,把盆子往桌上一放。
“唉呀!
大概是不知道地址
吧。
我给他写过地址,但是他干什么都是心不在焉的,真让人担心。
常常是脑子里
只有音乐,大概是把笔记搁在哪儿了吧。
”这时,她才注意到德加和亨利。
“啊!
德加先生,欢迎欢迎。
吐鲁斯先生这么晚了也光临寒舍,欢迎。
”她寒
暄着,焦急不安地往上拢了拢散开的头发,瞧着壁炉台上套着玻璃罩的台钟。
“唉呀!
已九点了。
”她自言自语着,“一定是迷路了。
那就开始吧。
首先演奏已同德加先生讲定的莫扎特的奏鸣曲。
”刚要开始演奏,门铃响了。
弟弟急忙走到门口,带进来一个矮胖子、圆脸的男人,这人留着浓密的白色络腮胡。
嘴角上露出一丝歉意的微笑。
“我想你大概是迷路了吧。
”说着,克莱曼蒂内展开双臂,奔了过去。
“是迷路了”,老人紧紧握住她的手上下摇晃着。
“我确有一张你写地址的纸,
可不知放哪儿了。
请原谅。
上了六十八岁,记忆也就差了,……有时,连学生的住
址也会丢失。
这些就不谈了。
在我来你家的路上,上帝给了我优美的变调。
这实在
是太优美了。
七度音减去半音,只不过是有些逆对位法,为了不被忘记,我在路灯
下写了下来。
”克莱曼蒂内没听他辩解完,怕他逃走似的,拉着他的袖口,把他介
绍给了客人。
“塞扎尔·弗兰克先生……”这天清晨三点,亨利累极了。
他浑身湿透地坐在
污秽的酒店,眯着近视眼,注视着不太熟悉的大街。
他想这儿究竟是哪里呢?
这么
晚了,怎么回家去呢?
他看着玻璃里映出的自己的面庞,低声嘟噜说:
”怎么找马车呢?
”然而,这
没关系,这儿又暖和又安静,……实在太静了……煤气取暖炉发出了丝丝的响声。
苍蝇弄脏了的日历上美丽的贵妇人穿着夜礼服在饮着味美思。
荣幸的是能完全逃脱危险,这是多么危险,而且出于意外的事啊。
那是个愉快的演奏会。
克莱曼蒂内弹了莫扎特奏鸣曲。
演奏令人觉得像是酒杯
玻璃相碰时发出的清脆声。
然后,有人拿来了小提琴,弗兰克先生坐在钢琴前,伴
奏了自己的奏鸣曲。
是支格外动听的曲子。
以后就发生了那件事。
克莱曼蒂内带着鼻音,请他演奏一首什么曲子。
“弗兰克先生,求你了。
”应邀弹的曲子竟是德尼兹演奏的前奏曲。
多么奇怪,几个月来,我竟然一点没想到自己是个残废。
然而现在,突然从正
面猛击了一下亨利的面颊。
你不能毕直走了,没有一个女人会爱你的。
无论何时,你都会感到孤独,这些昔日的回忆……。
朝柜台一望,脸长得像黄鼠狼似的店主人正和接客的在窃窃私语。
接客的穿着
合身的套装,戴着顶茶色的小礼帽。
“这条街叫什么名字?
”“拉利埃街,老爷。
”
店主人肉滚滚的脸上浮起了和蔼的笑容。
“这儿离克利西大街远吗?
”“不,很近。
这条街的尽头往左拐就到了。
”
“谢谢!
再来一杯科涅克白兰地。
”亨利又向前久了欠身子,看清了黑暗的大街。
雨已经停了,大风还在刮着。
这是一个怎样的夜晚啊!
到了克利西大街,就找得到
马车了吧,坐马车回去吧。
他不时地瞅一下扇型的煤气取暖炉。
煤气一流动就窜出了火焰,就像扑在蜘蛛
窝上的蝴蝶似地吧嗒吧嗒地拍打着翅膀,摇动着身子。
火焰是多么美丽的东西啊!
角落里,穿着平纹白布衬衣的妓女伏在桌上睡着了,脸埋在胳膊肘里,摆在面前的
葡萄酒酒瓶已经空了,帽子掉在地上,沾上了脚下的木屑,呼吸像孩子似的很有规
律,还不时地响起了低低的打呼噜声。
店主对接客的说:
“对不起,我离开一会儿。
”吧达吧达地走到了女人跟前,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摇晃着,让她醒过来。
女人深深地叹了口气,转动了一下身子,抬起肥胖的大脸庞,
心情舒畅地笑了笑。
用睡眼惺忪的眼睛瞧着。
店主挥着手背扇了女人一个耳光“吵
死了,醉鬼!
你不知道我讨厌打呼噜吗?
首先,这是无礼的行为。
今后再打呼噜,
我就赶你出去。
”他费力地回到了柜台,对接客的说。
“对不起,在这儿睡着了,可不好办呐。
”“的确,”戴着茶色小礼帽的男人
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亨利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
他感到一股就要爆发的怒火,多么厉害的家伙。
如果我是个高个儿,对自己的体力
充满自信的话,就一定要揪住他的脖子,朝他那傻呼呼的脸上揍上几拳。
然而在这
种想法下,萌发了一种别的感情使他克制了激愤。
女人被这一击,打得目瞪口呆,
一动也不动。
过了一会儿,用手捂住面颊,漠然地盯着空瓶。
由于酒力,神志恍惚
的脸显得苍白。
这真是画上画的落魄情景。
亨利飞快地从口袋里取出短铅笔和纸。
女人只要保持一分钟这种姿势……请千
万别动……亨利抱着祈祷的心情,飞快地画着,再过几秒钟,蓬乱的头发和盯着空
瓶的漠然的双眼就画好了。
但是,杰出的模特儿忽然垂下头,邋遢地张着嘴,一会
儿就发出了微弱的声音,伏在桌上又睡着了(这幅素描几天之后完成了,成了劳特
累克的代表作《两日醉》)。
亨利付了酒钱又说:
“再给她一瓶葡萄酒。
”等到新瓶灌满之后,拖着脚离了
酒店。
寒冷的空气吹得背上索索发抖。
亨利立起了天鹅绒的领子,一只手压着小礼帽,
避着风走着。
高高的天空中,暗白色的月亮在孕育着暴风的云间忽隐忽现。
他走到
马路拐弯处,朝四周骨碌碌地张望了一下,寻找着马车。
然而,平时热闹的大马路
上阒无一人,简直静得令人难以置信,亨利靠着手杖使身子向前倾了倾,呼吸艰难
地又走了起来。
他知道就这样,他一步不停地可以走二十英尺,有时可以走三十英
尺左右。
也就是说,走到床边,还需要二十分钟。
红磨坊就像烧焦了的废墟,黑呼呼地沉默着。
亨利就像划船渡过急流似地一步
一步走在阒无一人的大街上,这时,从背后传来了吧哒吧哒的轻轻的追赶脚步声。
一会儿,一位年轻女子追了上来和亨利并肩行走。
女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嗫嚅:
“先生,求您了,请您说声我是和你一起的。
”不大工夫,又传来了另外的脚步声。
这时,从黑暗中伸出了一个男人的手,揪住了女人的脖子。
“出示一下许可证!
”女人抬起脚就踢,用手指甲挠,打算咬男人的手。
男人
含糊不清地臭骂着,猛地拧女人的手臂。
女人大声地惨叫着,忍受不了的疼痛,蜷
曲着上身。
“给我老实一点,如果不听我就强行把你拉走。
”“放开她的手。
”亨利插嘴
说。
”难道你不知道她痛吗?
”男人转过身子,”我看到她拉行人的袖子。
在街上
接客一定要有许可证。
你为什么要插嘴呢?
”“她一直和我呆在一起,怎么会去拉男人的袖子呢?
”
谎话一句接一句地从嘴里溜了出来。
“一直在一起?
”男人侮蔑地学道。
“你想用
这来骗我,可是大错特错了。
我清楚你是一个人……”男人说到这儿,突然闭口不
言。
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亨利的脸。
然后问:
“难道你是吐鲁斯·劳特累克先生吗?
”
声音完全变了,含有一种敬重的心情。
“是的,如果你纠缠不清,做出可笑的举动的话,我要告诉警察。
”“警察?
警察就好了,我就是干这一行的。
”“谁相信,你又没穿制服,给我看一下你的身
份证。
”男人慢慢地放开了女人的手腕,开始解上衣的钮扣。
“我是执行严肃风纪
的巴尔塔扎·帕特警官,因为工作的性质而不穿制服的。
”“那就相信你吧。
你的
事我在爱丽舍·蒙马特听人谈起过,说你是这一带最有良心的警官。
像你这样的人
再多一些就好了。
但是,关于这个女人你却错了。
今晚,从一开始她就和我在一起。
”
可是,我是亲眼看到的啊。
”“这么暗,你能说就一定没看错人吧。
给你这么一说,
倒是有个女人朝那儿走了。
”亨利指了指马路的前面。
”你在找的是不是那个女人?
”
“你看到脸了吗?
”“怎么会看到呢?
一眨眼功夫她就跑没了。
”对于这充满自信
的回答。
帕特惊慌失措了。
“你说她是朝那儿走了?
”“是的,确实跑到弗罗曼坦
街去了。
”亨利说着,回过头去对女人:
“你也看到了吧?
”“是的,看到了。
”
女人抚摸着手腕,噘着嘴,昂然地向后仰着头补充说:
”去那儿了。
”警察好像难
以下决心似地捋着胡子,看着两人,自言自语他说:
“如果是逃到弗罗曼坦街去了的话,那是怎么也追不到了。
”“对不起,给你
添麻烦了,吐鲁斯-劳特累克先生。
可是,我是按上面的指示办事,为了保护市民
的健康,必须要取缔妓女。
”“那当然,这我也清楚。
那么帕特先生,再见。
”亨
利转身对女人说:
“那,我们走吧,时间已经很晚了。
”两人意识到警官的视线,默默地走了。
亨利拼命地走着,他意识到身旁的女人奇怪地缠着自己,并没有离开;他从女
人那像蹦似的步子中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愤恨。
我究竟为什么要编出这么一番话来呢。
“嗳!
能再走得快一点吗?
”亨利第二次停住脚步时,女人低声地催促说,”
你的脚怎么了?
”女人的声音里不用说没有同情和厌恶,连好奇心也没有。
有的只
是对于他的缓步行走感到焦虑不安。
听了这话,亨利勃然大怒,她只差没说那句潜台词了。
“你不喜欢我的走法,
就赶快走好了,警官已经走了,没必要再在一块。
他也不会追上来的。
”女人沉默
了一会儿,用同样不感兴趣的语调问:
“是天生的,还是受伤,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以前我认识一个被机器断了手的
人,不过,从保险公司拿的五百法朗,所以还是运气好的。
”女人越过肩膀回头说
:
”嗳,快一点。
”“我不是已经走得这么急了嘛!
”亨利呼吸困难,气喘嘘嘘地
说。
“我不是说了你可以先走嘛。
你放心好了,警察不会再来追你了。
”“我真想
打断他的牙齿,啐他一口唾沫!
”女人语词激烈,好像吐掉什么似他说。
“可是,你不是逃脱了吗?
”“那是没错,但是警察是不会变的。
我一看到他
们,就恶心。
就想踢他一脚”这话赤裸裸地充满敌意,包含着被追者对于追者的憎
恨。
”不过,你很妙地骗过了他。
骗警察可是很难的事呀。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
了句奉承话。
”你的脑子不错呀。
”然而语调还是那么冷冰冰的。
女人既没有感激
之情,也不会有什么赞赏之意,仅仅是觉得他脑子不错,才这么说的。
一会儿功夫,到了土拉克街的拐角处,亨利在路灯下停了下来,指着一盏有点
污秽的大楼门灯说:
“瞧,这儿就是旅馆。
这儿是通宵经营,他们会让你留宿的,
有钱吗?
”“我可不想住在旅馆。
”女人别扭他说。
“没有许可证不让我住的,就是让住也要收两倍的住宿费,而且到了早晨,为
了得到十个法朗的赏金,会向警察告密的。
”亨利这时才看了女人一眼。
一头金发,
比估计的要年轻,大概十八,最多不过十九岁吧。
在黑暗处,眼睛的颜色呈土绿色
如果是在白天的话,也许是明亮的棕色吧。
宽宽的嘴上笨拙地抹着口红,没带帽子,
也没穿外套。
亨利想,衣服下面不要是裸露的吧。
薄薄的衣料,正好盖在乳房突出
的地方,使人想到希腊雕刻的线条。
女人显得有些肮脏,但有着女性的丰腴和温柔
的形体曲线,这使亨利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危险。
亨利突然不希望其它任何东西来替
代了。
“你,是住在这一带吗?
”“噢,沿着这条街往前走一会儿有一个画室。
”
“你能让我住下吗?
”这时,女人的声音第一次带着献媚,亨利感到肯上一阵动荡
的战栗。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到了早晨,我就离开。
”女人低垂着眼帘,给亨利送
了个秋波。
“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不要钱。
真的,一生丁也不要。
有烟吗?
”
亨利递给女人一只金盒。
女人反复看着金盒,用手指摸了摸,拿了一支,然后还给了亨利。
”是真金的
吧?
曾有人给过我金耳环,不过找不到了。
有火柴吗?
”亨利划了根火柴递了过去。
于是,女人躬着背,用手心围住了火焰。
“唉呀,这么丑陋的男人!
”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吸着,含糊不清地说了句,并
透过眼睫毛瞧了亨利一眼。
亨利的脸一下变得苍白。
“回去!
你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
我不要你!
”“要想却……”女人镇定地吹
灭了火柴,很内行地吸了一口。
”你的脸上写着你想要。
”“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
会吧。
”亨利拽着脚走了起来。
”你再强词夺理的话,我就把你交给警察了。
”女
人追了两三步。
“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我不过说了句请你让我住一夜嘛,我不会
偷东西,如果行的话,你也可以抱抱我。
不管你是侏儒,还是脚部萎缩也好,都没
关系。
我会让你舒服的。
”女人又是一副献媚的样子。
“我,心血来潮时,会使劲、周到地为你服务的。
这是真的。
”亨利没有回答,
他避开淡淡的月光照耀下的水洼,蹒跚地走在万籁俱寂、不见人影的街上。
旁边,
女人吸着烟,合着他的节拍,时而停下,时而行走。
“你有个画室,那就是个画家吧。
”过了一会儿,女人说。
“说起画家,我以
前也认识一个在汤盘上画丘比特的人。
”女人的声音里有着对昔日的怀念。
走过了鲁贝夫人管理室的屋子,开始上楼。
油灯发出丝丝声燃烧着,墙上火焰
的影子在摇曳。
“你,不锁门?
”亨利转动门把手时,女人问。
“没这个必要,因为没什么可偷的东西。
我去开灯,你等着。
”亨利在早已习
惯的黑暗中走到画桌旁,点上煤油灯。
过于宽阔的屋子在灯光下泛出琥珀色,可以
望到天花板。
映出了沿墙置放的画布和画架四方的剪影。
屋子中间,取暖炉在熊熊
燃烧着。
女人环视了一下画室。
“这屋子真大呀。
取暖炉已点了火,不过是一直这么烧
着的吗?
”女人的眼睛睁得圆圆的。
她走到窗边,在长椅上坐了下来,毫不踌躇地
开始脱衣服。
亨利纹丝不动地盯视着。
手指摇着还没燃尽的火柴,这是在我画室过夜的第一
个女人。
多么美的躯体啊!
就连放大了的映在墙上的投影也是美丽的。
既然如此,这个女人为什么会惹我生气的呢?
是因为没有谢我吗?
不,不是的。
是她的直率以及那异常的充满自信的镇静自若。
她说从我脸上看出了欲望,果真如
此吗?
她到这儿还不到五分钟,就开始脱衣了,宛如回到自己家中那样的旁若无人。
佩罗克·格里的女人们是边说边脱衣的,招呼主人时总要说:
“喂!
你。
”当然这
是一种虚假,是一种做爱的伪装。
可是,眼前女人连伪装都没有。
女人扬起与猫相似的双眸,问:
“你一动不动地在看什么呀,从没见过女人脱
衣服吗?
”她取下夹在嘴里尚未吸完的烟蒂,扔在地上踩灭了。
“你虽是个画家,
可不爱说话呐。
”见亨利没有答话,她又接着说:
“我刚才说过的画汤盘子的那人,
他是个爱说话的人。
唠唠叨叨不停他说着各种事情,还说笑话逗人发笑。
”这时,
亨利对于那个知道怎样逗女人发笑的画家充满了嫉妒,不仅是画家,对那些曾经详
细地看到这个女人脱衣并搂抱过她的数不清的男人感到难忍的妒忌。
这个女人在那
些从未见过的男人面前,经常这样卷下长袜,在从未住过的屋里,从未睡过的床上,
睡过不知多少次吧。
……才十九岁的年轻轻的……。
女人站了起来,很快地脱去衣服。
真如想象的那样,没穿衬裙,然后,又飞快
地脱去裙裤。
这样。
女人只穿着一件廉价的,嵌有花边的薄衬衣,站在亨利的面前。
“厕所在哪里?
”怎么能让你用我那高级的浴室呢,让她在家里到处找找,患
上伤风感冒!
那样,她就会稍微懂得一点儿什么是礼貌了吧……。
“在走廊尽头。
”“同一层吗?
”女人吃惊地叹了口气。
“我们爬了两三级台阶了……”亨利盯着女人的脸想,以前,你爬过的都是些
破公寓肮脏不堪的走廊吧,你已经卖了几年春了。
一定是从小就站在街头了。
“能不能借我用一下火柴?
”她有些游移不决似的说,声音里有着淡淡的恳求。
”
我不熟悉这里。
”“你就拿着这灯去吧。
”“话刚出口,亨利后悔了。
她只穿着一
件衬衣,光着脚站着的姿势,看上去挺可怜的。
自己应该抑制冲动,轻轻地把火柴
扔给她。
在汤盘上画画的画家及那些买这女人的男人们一定都是这么做的。
他们把
妓女当妓女看待。
不让这个女人看出自己的担心。
首先她并不习惯温柔的关切,也
不会理解这些的。
女人一声不吭地拿过灯,朝门口走去。
站在蓝色的黑暗中,亨利想,如果动作快一点,可以在女人回来之前钻到床上
去。
这样她就看不到脚了。
幸好床已经整理好了。
亨利很快地解开鞋带,把衣服扔到扶手椅上,钻了进去。
刚钻进去就听到了叭
哒叭哒的脚步声。
“已经钻进被窝了?
你钻的太快了。
”女人把灯放在桌上,从头上脱去衬衣。
“灯就这么点着吗?
”“不,吹灭了。
”女人朝前倾着身子,用手掌围着灯罩。
刹
那间,亨利看到了番红花似的侧面,喉部线条丰满柔和,乳头就像玫瑰花蕾。
又是
个刹那间,在深蓝色的黑暗中消失了。
“你不想让我看到脚吗?
”声音中潜在着的讥讽激怒了亨利。
“滚!
穿好衣服快滚!
我不想要你,我又没让你来!
”啊!
如果我的个子再高
些,有力气的话,能搧她个巴掌,像帕特那样扭拧她的胳膊的话!
“你是说从没和侏儒睡过吗?
不是不管是谁都睡的吗?
”女人镇静地揭去盖被,
很快地滑进了被窝。
亨利感到了滑溜溜的肌肤触到了自己的身体。
“不要那么大声地嚷嚷。
”女人的声音格外地轻,格外地温柔。
”家里人会被
吵醒的,我不过问了声你不想让人看到脚吗?
与你的脚没任何关系。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如让我住下的话,我会让你留
下愉快的记忆的。
你,不也希事我留下的吗?
难道不是吗?
”于是,除了突然贴了
上来的舌头和柔软的身子的接触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窗外,高高的天空中挂着一轮明月。
醒来时,取暖炉里生着火,显然是鲁贝夫人来过了,而且来了又走了。
连鸟叫声都没有的寂静,充满着她的责备。
窗外的牛毛细雨,使人觉得有点冷
飕飕的。
今天又是静寂的冬天的一日。
亨利悄悄地扭过头去,看了一眼旁边的女人。
女人的面颊压在手臂上,嘴巴舒
服地张开着,睡得正香,一边的胸部坦露着,嘴唇上抹着口红,眉毛描得浓浓的。
然而却使亨利想起了格瑞兹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