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docx
《论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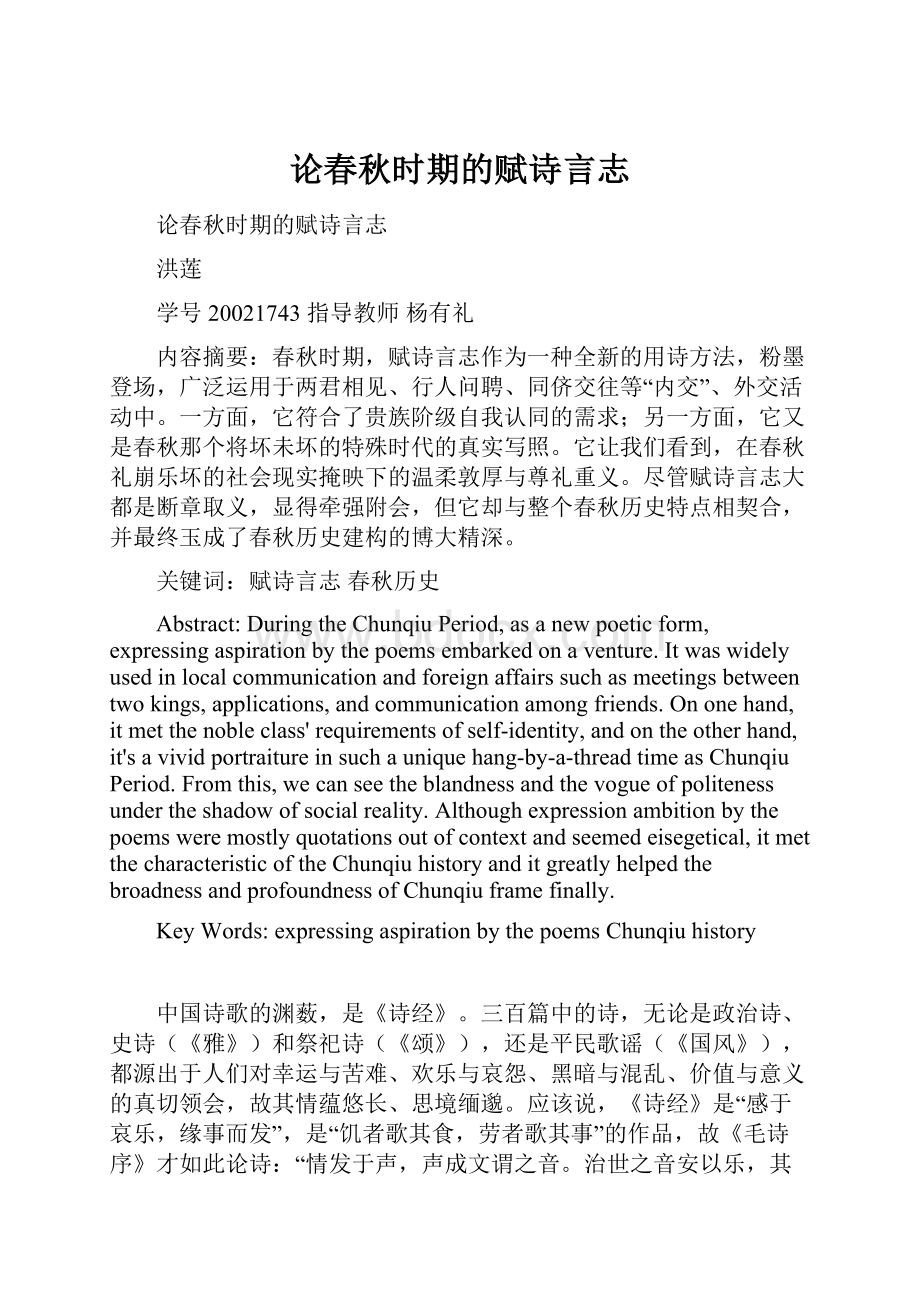
论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
论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
洪莲
学号20021743指导教师杨有礼
内容摘要: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作为一种全新的用诗方法,粉墨登场,广泛运用于两君相见、行人问聘、同侪交往等“内交”、外交活动中。
一方面,它符合了贵族阶级自我认同的需求;另一方面,它又是春秋那个将坏未坏的特殊时代的真实写照。
它让我们看到,在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掩映下的温柔敦厚与尊礼重义。
尽管赋诗言志大都是断章取义,显得牵强附会,但它却与整个春秋历史特点相契合,并最终玉成了春秋历史建构的博大精深。
关键词:
赋诗言志春秋历史
Abstract:
DuringtheChunqiuPeriod,asanewpoeticform,expressingaspirationbythepoemsembarkedonaventure.Itwaswidelyusedinlocalcommunicationandforeignaffairssuchasmeetingsbetweentwokings,applications,andcommunicationamongfriends.Ononehand,itmetthenobleclass'requirementsofself-identity,andontheotherhand,it'savividportraitureinsuchauniquehang-by-a-threadtimeasChunqiuPeriod.Fromthis,wecanseetheblandnessandthevogueofpolitenessundertheshadowofsocialreality.Althoughexpressionambitionbythepoemsweremostlyquotationsoutofcontextandseemedeisegetical,itmetthecharacteristicoftheChunqiuhistoryanditgreatlyhelpedthebroadnessandprofoundnessofChunqiuframefinally.
KeyWords:
expressingaspirationbythepoemsChunqiuhistory
中国诗歌的渊薮,是《诗经》。
三百篇中的诗,无论是政治诗、史诗(《雅》)和祭祀诗(《颂》),还是平民歌谣(《国风》),都源出于人们对幸运与苦难、欢乐与哀怨、黑暗与混乱、价值与意义的真切领会,故其情蕴悠长、思境缅邈。
应该说,《诗经》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作品,故《毛诗序》才如此论诗: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然而,这些极为率真、质朴,甚至有时有些“放荡”的诗歌何以能成为后世儒家的神圣经典呢?
这真是让我们惊叹不已。
从先民的歌唱到后世的经典这一发展过程至少说明:
《诗》的功能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诗》以前那种个体情感宣泄与审美愉悦性质越来越被人们淡化了。
而在此过程中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便是于春秋时期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用诗方法——赋诗言志。
一、赋诗情况及其作用
(一)赋诗情况: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作为一种人际交往沟通的特殊方式,普遍存在于两君相见、行人问聘、同侪交往、甚至是日常生活中。
从典籍记载可知,《左传》中的赋诗始于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亡命于秦,秦伯以女妻之。
在遣送重耳回晋继承大统之前,秦伯设宴招待重耳,重耳在赵衰帮助下赋《河水》,取义“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以海喻秦,自比为水,这当然是奉承秦伯,意在表明自己对穆公的尊崇之情。
穆公答赋《六月》,取其“共武之服,以定王国”,勉励重耳有所建树,振兴晋国,并像尹吉甫那样辅佐天子。
杨伯峻说:
“(《左传》记赋诗)始于此,非前此无赋诗者,盖不足记也。
”也即是说,僖公之前的隐、桓、庄、闵诸公间历史,可能早就有赋诗情形,只是水平不高,不足记罢了。
总的看来,僖公及其前实为赋诗发生期。
文公,宣公,成公时,赋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为发展期。
襄公,昭公之时,赋诗勃兴,蔚为壮观,为繁盛期。
定、哀之时,赋诗之风渐衰,终成绝响,为衰落期。
可以说,赋诗几乎与整个春秋历史相始终。
(二)赋诗作用
赋诗在当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在春秋时人眼中,《诗》乃“义之府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以下凡引《左传》只注年数),是道义的府库;并且,据《周礼》、《礼记》及其它典籍记载,在西周的贵族教育中,《诗》是主要内容之一。
春秋之时王室虽趋于式微,但周王朝与各诸侯国大体上仍然继承西周制度。
可见,《诗》在当时不是作为创作与欣赏的精神产品,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贵族文化修养而获得价值的。
那时的卿大夫,十分看重赋诗,所以孔子说: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不懂得《诗经》,不但没法跟别人沟通,而且还会被视为缺乏贵族教养,会遭到讥讽与轻视,如齐国权臣庆封于襄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两次到鲁国去见叔孙穆子。
第一次他衣着华丽、车马光鲜,然而在宴会上吃相颇为不佳,叔孙穆子赋《相鼠》一诗讽刺他: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很明显,这是极为尖酸的讽刺了,可怪的是庆封竟浑然不觉;第二年,庆封由于在国内专权引起内乱而败逃奔鲁,叔孙穆子又设宴招待,席间庆封不懂祭礼,叔孙穆子大为不悦,鉴于庆封不懂赋诗之礼,索性让乐工诵《茅鸱》给他听(按,请乐工诵是为了让庆封听清楚词义)。
这首诗是逸诗,据说是“刺不敬”的,想必是比《相鼠》更露骨的讽刺,庆封听了依然无动于衷。
真是朽木不可雕,难怪叔孙穆子要说他将有“天殃”,将被“聚而歼之”。
能“望其项背”的还有一个华定。
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
宋国的华定出使鲁国,鲁昭公设宴招待他,为他赋《蓼萧》,诗曰:
“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
”意思是:
已经看见君子了,我的心里真欢畅,又饮酒来又谈笑,这真欢乐又荣光。
而华定对鲁昭公的称颂,不知其意,又不答赋,以至昭子骂他“必亡。
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但这在外交上的后果并不算很严重,最严重的是《左传·襄公十六年》中那个因赋诗不当而导致兵刃相见的例子: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
“歌诗必类。
”齐高厚之诗不类。
荀偃怒,且曰:
“诸侯有异志矣。
”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
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
“同讨不庭。
”
孔颖达《毛诗正义》说:
“歌古诗,各从其恩好之义类。
”高厚所歌“不类”,加上又“逃盟”,触怒了晋国君臣,齐国遭到了晋、宋、鲁、卫、郑等诸侯国的联合讨伐。
赋诗不当引起一场大祸,成为一场争霸战争的导火线,这在我们今天看来真是有些匪夷所思。
而成功的赋诗,不仅能表现赋诗者的修养和智慧,甚至可以救国难于危急存亡之间。
例如文公十三年,郑伯背晋降楚后,又欲归服晋,适逢鲁文公由晋回鲁,郑伯在半路上与鲁侯相会,请他代为向晋说情,两方的应答全以赋诗为媒介。
郑大夫子家赋《小雅·鸿雁》,取“之子于征,劬劳与野。
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意思是伯侯哀恤鳏寡,有远行之劳,暗示郑国孤弱,需要鲁国哀恤,代为远行,往晋国去关说。
鲁季文子答赋《小雅·四月》,取“四月维夏,六月徂暑。
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意在说明自己行役逾时,思归祭祀。
这当然是表示拒绝,不愿为郑国的事再往晋一行。
郑大夫子家又赋《载驰》篇第四章,取“控于大国,谁因谁报?
”意思是小国有急,相求大国相助。
鲁季文子又答赋《小雅·采薇》篇之第四章,取其“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鲁国过意不去,只得答应为郑奔走,不敢定居。
赋诗应用之广与作用之巨已如上所述。
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赋诗在中国文化史上仿佛一现的昙花,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只属于春秋。
人们常说:
“存在的历史决定理解的历史”,为什么在春秋那个时代会出现赋诗言志这样一种特殊的活动呢?
在这样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和历史意蕴呢?
二.赋诗言志所隐藏的文化和历史意蕴
(一)贵族自我认同的需求
春秋时期,贵族之所以成其为贵族,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之外,还必须有着文化上、生活习俗上不同于常人而又为常人所认同、所羡慕的地方,必须是时代最高文化价值的承担者,否则即使他在政治上、经济上高高在上,也同样会受到民众的蔑视。
《诗》本来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孔子闲居》中说得明白:
“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
”因此,《诗》本身便具有一种庄严性、高贵性与神圣性,正是这些特征使《诗》可以成为贵族的身份性标志,也使贵族在用这种方式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高贵身份得到了确认。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西周以来的官方学校都以诗教作为主要教育内容之一,因而精通诗就意味着受过良好的教育。
而受过良好教育、熟悉西周以来的文化则是一个诸侯国强盛的标志之一。
所以班固才说: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常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
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汉书·艺文志》)这里的“别贤不肖”与“观盛衰”主要不是从《诗》的内容来看,而是从赋诗者对《诗》的熟悉程度和借《诗》来表达意愿的准确程度来看的。
所以,并不是说赋诗在表达自己意愿时有什么突出的优势,而是这种方式凑巧在当时的语境中成为显示文化修养与实力的身份性标志。
于是,赋诗便成为一种特殊的游戏规则,要进入贵族社会就必须能赋诗,就如同两晋的名士们见面时要以清谈来显示自己的身份一样。
(二)社会过渡时期的写照
1.天子式微,礼崩乐坏
众所周知,在西周时期,人们社会观念里至高无上的东西,便是王权。
《诗经·北山》篇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邦,莫非王臣”是也。
然而,历史的步伐迈入春秋之后,尽管“尊王”的口号震天价响,此起彼伏;可就是在这一片“尊王”的聒噪声中,周天子却如日薄西山般沉沦,周王室也如叶落寒风般趋于凋零。
与此相反,日益强大的诸侯国对周天子桀骜不驯,逐渐形成尾大不掉,本末倒置的局面。
可以说,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王权跌落的伤心史。
随着政治权力的衰落,文化解释权随之下移。
曾经被奉为圭杲的礼乐制度,在各诸侯国手中难免遭厄运。
《左传·襄公四年》中关于晋悼公享鲁穆叔时用乐情况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一点: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
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歌《鹿鸣》之三,三拜。
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
“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
敢问何礼也?
”对曰: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
《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
《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
《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
‘必谘于周。
’臣闻之:
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
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
英哲明达的晋悼公在宴享鲁穆叔,即叔孙豹时,运用了三种乐歌:
《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鸣》之三,以示尊重和友好。
但前二者皆不符合周礼,僭用了天子享元侯和两君相见之礼,超出了他作为上卿应享的礼遇。
因为乐歌不合规范,所以穆叔不拜,不表示感谢。
其实,这种僭礼僭乐的情况,在春秋时已经数见不鲜。
尽管穆叔出自孔子旧乡,深谙礼仪,故而他能对晋侯的许多越礼之举提出批评,并讲得头头是道。
可事实上,就是这个保存西周礼仪、遵守西周礼法最为虔诚的诸侯国——鲁国自己,也早就滥用礼乐了,据《左传·文公四年》载: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
不辞,又不答赋。
使行人私焉。
对曰:
“臣以为肄业及之也。
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則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
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
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
《湛露》、《彤弓》均是《小雅》中的篇章。
《湛露》序云:
“天子宴诸侯也。
”首章云:
“湛湛露兮,匪阳不晞。
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宁武子解此诗,以阳喻天子,天子向明而治,谓之当阳;臣子不当阳而侍,谓之用命。
《彤弓》乃是诸侯讨伐四夷有功,“王亲受而劳之”的诗篇。
这于只是“陪臣”的宁武子来说,确实超出了他应享的礼遇,故宁武子说他不敢犯天子享诸侯之礼来自取罪祸,因而既“不辞,又不答赋。
”
《左传》中的这些赋诗告诉我们:
春秋时礼崩乐坏,人们对西周时制定的那一套严密的、用以规定贵族统治阶级的言行、服饰、车驾、舞乐、宴饮、朝会、祭祀、婚丧等的典章制度,已经渐渐模糊起来,不是那么清楚了;或者说,即使颇明礼仪,也不愿如从前那样严格的恪守它了。
周天子的礼乐制度似乎不太管用了,虽然诸侯国中公然对抗者尚少,可阳奉阴违者颇多。
赋诗中僭礼僭乐的情形,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的政治现实。
孔子说:
“《诗》可以观”,从《左传》的赋诗中,我们观到了春秋时代的王权,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而各诸侯国的霸权,却如一轮初升的圆月,隐然在柳梢之后,预示着无限的生机。
2.温柔敦厚,尊礼重义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春秋时期的周天子尽管威风锐减,失去了往日的尊贵荣华;春秋时期的周王朝尽管衰弱颓败,成了“破落户”,但其天下共主之名却长期保持,周天子始终没有成为某一霸主的附庸。
从这一点来说,它在政治上的优势,乃是所有的诸侯国,包括那些显赫的霸主在内,都不敢小觑的,即使是那个有问鼎之志的楚庄王,也不敢对周天子造次非礼。
各诸侯国的争霸战争确使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几于轰毁,但是人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因此,那些旧有的的文化在形式上仍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顾炎武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
”(《明夷待访录》)黄仁宇先生也这样论述春秋:
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
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
而现在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争伐,仍以道德名义出之。
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
他还说春秋时的战争“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为己不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
”也即是说,中国源远流长的德性文化,在这个时候不是被废弃了,而是再次得到高扬。
外交场合中的赋诗,便体现出春秋政治中这种最富有时代蕴味的高雅雍容的贵族文化和尊礼重信的时代氛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讲周礼,论宗姓氏族,固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
“所谓‘周礼’,其特征确是将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整理,予以系统化、扩展化,成为一整套习惯统治法规(‘仪制’)。
以血缘父家长制为基础(父亲)的等级制度是这套法规的骨脊,分封、世袭、井田、宗法等政治经济体制是它的延伸扩展。
”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自然会发生变化。
所以,春秋霸主中,仍将周礼视为金科玉律,进行顶礼膜拜的,实属稀罕。
但是,他们仍然讲周礼,拥护宗法制度,重视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不允许犯上作乱的行为发生,臣子若对其君主不敬或有取而代之之心,将被视为不得好死。
如《左传·昭公元年》诸侯盟会后的记载:
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
赵孟赋《小宛》之二章。
事毕,赵孟谓叔向曰:
“令尹自以为王矣,何如?
”对曰:
“王弱,令尹强,其可哉!
虽可,不终”。
令尹所赋《大明》为《大雅》中诗,其首章内容是: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
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本是赞美文王明明照于下,故能赫赫盛于上的,但赵孟结合楚国现状——楚王郏敖暗弱,令尹独揽大权,看出令尹“以光自大”,借诗自说,自以为有德,暗示楚王命令不能达于四方,进而显示出令尹有代楚王自立的野心。
赵孟所赋《小宛》,是《小雅》中一篇,第二章内容是:
“人之齐圣,饮酒温克。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各敬尔仪,天命不又。
”言天命一去,不可复还,也即是说,赵孟视令尹僭越之心为不义,并对他提出警告:
即使你称了王,也不会有善果。
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的一场赋诗活动: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
赵孟曰:
“七子从君,以宠武也。
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
”子展赋《草蟲》,赵孟曰:
“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当之。
”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
“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
非使人之所得闻也。
”
在听完各人赋诗后,赵孟告诉叔向说:
“伯有将为戮矣。
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
幸而后亡。
”叔向曰:
“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
”
赵孟根据赋诗推测,伯有必定下场不好。
原因是他所赋诗污蔑了他的国君并公开表示怨恨,并以此作为宾客的光荣。
伯有所赋《鄘风·鹑之贲贲》,《诗序》说是讽刺卫宣姜淫乱的诗,所以赵宣子说:
“床笫之言”。
实际上,此种解释纯属朱熹所谓“以史证诗,牵强附会”,(《诗集传》)并不足取。
但诗中有:
“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之句,是对国君公开表示不满的话。
在赵孟看来,“床笫之言不逾阈”,家丑不可外扬,一家人的矛盾怎么能对外人说及,况且是在这种郑伯宴享宾客的特殊场合。
“志诬其上而公怨之”,有悖做臣子的道德规范。
用叔向的话说是“侈”,即“骄奢”的表现。
就这些不德之处而言,伯有将不得其死。
其二,重和平,讲朝聘盟会,力倡温文尔雅的外事活动。
我们知道,《诗经》首先是被用做伦理道德的教科书使用的,“温柔敦厚,《诗》之教也”。
温文尔雅是《诗经》文化的一贯宗旨。
外交活动中,之所以采取赋诗这种形式,与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特征是分不开的。
无论是请求别人,还是拒绝别人的请求,用赋诗来表达意思都比直接说出来得委婉一些,这样至少不会让对方觉得过于难堪。
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外交活动,不是金刚怒目式的,他们不大讲究“以力服人”,而讲究“以理服人”。
虽然,他们也讲“力”,但从不标榜攻占征伐,不提倡赤裸裸的力争和诡谲的阴谋。
钱穆先生曾盛赞春秋时期贵族文化的灿烂,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这种外交场合的赋诗活动,他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紧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
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是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
(当时往往有赋一首诗,写一封信,而解决了政治上之绝大纠纷问题者。
《左传》所载列国交涉辞令之妙,更为后世艳称——自注)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于富强攻取之上。
(此乃春秋史与战国史决然不同处——自注)《左传》对当时各国的国内政治,虽记载较少,而各国贵族之私生活之记载,则流传甚富。
他们实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
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
可以说,春秋时的政治家是真正的贵族,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讲信义、重荣誉,有一套自觉恪守的行为准则。
赋诗之举在今人看来无疑显得迂腐幼稚,甚至有“掉书袋”之嫌,然而在当时,它却是真正的贵族精神的展现,并且其温文儒雅的风度也确实令人心向往之:
在频繁的朝聘会盟之中,于雍容揖让之间、宴享吟咏之际,卿大夫们常以诗句暗示自己的意向与愿望。
而对方凭借对《诗》的极为熟悉,凭借对诗句的形象与外交情势的联想与比附,可以心领神会,达成彼此的沟通与谅解,甚至化干戈为玉帛,以诗篇消兵燹,使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主动地位。
《左传·文公二年》载,晋国因鲁文公不朝而攻鲁,晋强鲁弱,文公去晋国结盟因而受到侮辱。
一年以后,由于各国形势发生了变化,晋国愿意和好,请求改盟,鲁文公又赴晋,晋侯在宴会上赋《小雅·菁菁者莪》,取诗中“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之意,文公受到善待,马上以小国之礼降阶下拜,赋了一曲《嘉乐》,取“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之句,对晋侯大加恭维,晋侯也降阶而拜。
一场剑拔弩张的争斗归于和平。
难怪雷海宗先生会在其《古代中国的外交》一书中写道:
“赋诗有时也可发生重大的具体作用。
”而《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到:
“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成宾荣,吐纳而成身文。
”在各种外交场合下,赋诗言志,既可在宾主之间灵活斡旋,达到外交的目的,又可充分显示自己的的才华和修养,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三.赋诗言志:
合法的偏见
清人劳孝舆在其《春秋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所作。
……然整理不名,述者不作,何欤?
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
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
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
文中的“变风”,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对本文来说,有意义之处在于这段话一语道破了赋诗情形——“赋诗断章,予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赋诗这种“只取一二章,并且只取一二章中一二句,以合己意,叫做‘断章取义’。
”《左传》中的赋诗,大都是断章取义、即景生情、没有定准的。
我们来看看《左传·昭公十六年》中记述的一段赋诗活动: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
宣子曰:
“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
”子齹赋《野有蔓草》。
宣子曰:
“孺子善哉!
吾有望矣。
”子产赋郑之《羔裘》。
宣子曰:
“起不堪也。
”子大叔赋《褰裳》。
宣子曰:
“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
”子大叔拜。
宣子曰:
“善哉,子之言是!
不有是事,其能终乎?
”子游赋《风雨》。
子旗赋《有女同车》。
子柳赋《萚兮》。
宣子喜,曰:
“郑其庶乎!
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
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
”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
如果不懂诗的言外之义,弦外之音,真是搞不懂这邦人在演什么戏了。
先看看郑六卿诗的意思:
子齹的《野有蔓草》,原是男女私情之作。
子齹却堂而皇之的赋了出来,他只取“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二句,表示欢迎韩起的意思。
上文“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以及下一章,恐怕都是不相干的。
同样,子游赋《风雨》,只取“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之句,表现了他见到韩起时的惊喜和愉快。
子产赋郑之《羔裘》,取“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子旗赋《有女同车》,取其“询美且都”。
二人分别从德、才、貌方面赞美韩起。
子大叔赋《褰裳》,取“子惠我思,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句,这实质上是一种戒谕之辞,杜注云:
“言宣子思己,将有蹇裳之志;如不我思,岂亦无他人?
”意为希望大国晋顾念小国的尊严和利益。
否则,郑将另寻保护国。
显然,这更是与诗的本义风马牛不相及。
子柳赋《萚兮》,取“倡,予和汝”句。
韩起赋《我将》属《周颂》,取其“日靖四方。
伊嘏文王,既右飨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乱而畏惧天威;又取“于时保之”,声称自己会保护小国利益。
整个赋诗活动,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大家都能心照不宣,可谓:
“曲而达,婉而有致”了。
西方哲学家伽达默尔曾宣称:
“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将理解视为“合法的偏见”,认为人类文化就是在理解的“误解”或“合法的偏见”中进行的,并最终走向了历史建构的博大精深。
我们说,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就是这样一种“合法的偏见”。
所有的赋诗,不论是借诗的原有意义来表达赋诗者的某种观点,还是借诗的相近意义来暗示自己的某种要求,或者是完全不顾诗的本意而赋予其某种临时的意义,它们都是断章取义,多数情况下显得牵强附会。
诚如何良俊所说:
“《左传》用诗,苟于义务合,不必尽依本旨。
”(《四友斋从说》卷二)诗在这里只不过是一种表达意见的工具,与诗的审美价值,自然价值关系不大。
但是,赋诗言志却与整个春秋历史特点相契合。
一方面,它符合了贵族阶级自我认同的需求;另一方面,它又是春秋那个将坏未坏的特殊时代的真实写照。
它让我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