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女性的电影.docx
《当代中国女性的电影.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当代中国女性的电影.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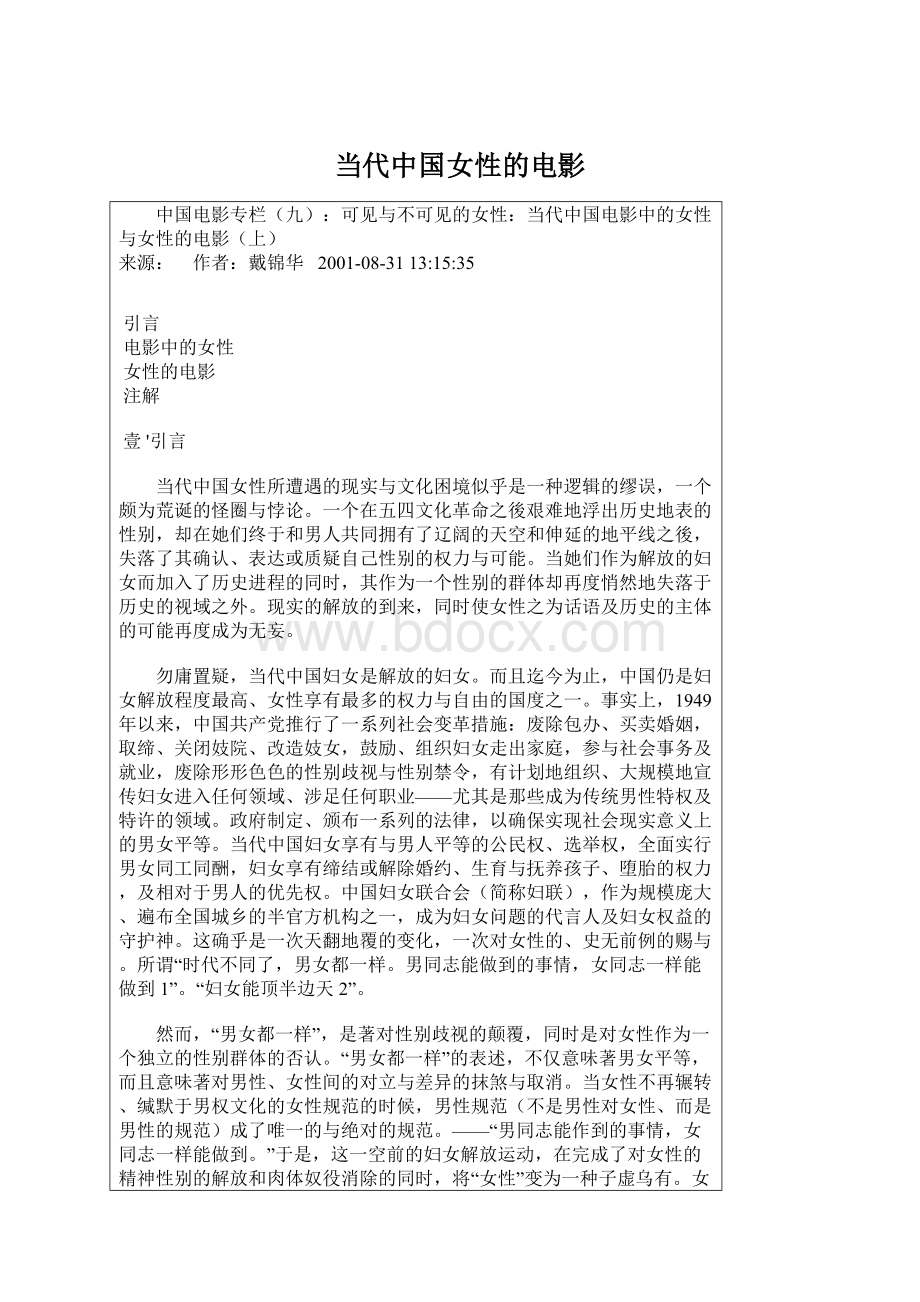
当代中国女性的电影
中国电影专栏(九):
可见与不可见的女性: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上)
来源:
作者:
戴锦华 2001-08-3113:
15:
35
引言
电影中的女性
女性的电影
注解
壹 '引言
当代中国女性所遭遇的现实与文化困境似乎是一种逻辑的缪误,一个颇为荒诞的怪圈与悖论。
一个在五四文化革命之後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别,却在她们终于和男人共同拥有了辽阔的天空和伸延的地平线之後,失落了其确认、表达或质疑自己性别的权力与可能。
当她们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了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之外。
现实的解放的到来,同时使女性之为话语及历史的主体的可能再度成为无妄。
勿庸置疑,当代中国妇女是解放的妇女。
而且迄今为止,中国仍是妇女解放程度最高、女性享有最多的权力与自由的国度之一。
事实上,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行了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
废除包办、买卖婚姻,取缔、关闭妓院、改造妓女,鼓励、组织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及就业,废除形形色色的性别歧视与性别禁令,有计划地组织、大规模地宣传妇女进入任何领域、涉足任何职业——尤其是那些成为传统男性特权及特许的领域。
政府制定、颁布一系列的法律,以确保实现社会现实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当代中国妇女享有与男人平等的公民权、选举权,全面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享有缔结或解除婚约、生育与抚养孩子、堕胎的权力,及相对于男人的优先权。
中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作为规模庞大、遍布全国城乡的半官方机构之一,成为妇女问题的代言人及妇女权益的守护神。
这确乎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次对女性的、史无前例的赐与。
所谓“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1”。
“妇女能顶半边天2”。
然而,“男女都一样”,是著对性别歧视的颠覆,同时是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的否认。
“男女都一样”的表述,不仅意味著男女平等,而且意味著对男性、女性间的对立与差异的抹煞与取消。
当女性不再辗转、缄默于男权文化的女性规范的时候,男性规范(不是男性对女性、而是男性的规范)成了唯一的与绝对的规范。
——“男同志能作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
”于是,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的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
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
女性、女性的话语与女性自我陈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性别差异的消失,而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
在受苦、遭劫、蒙耻的旧女性和作为准男性的战士这两种主流意识形态镜象之间,新女性、解放的妇女失落在一个乌有的历史缝隙与瞬间之中。
这一特定的现实,呈现为历史视域中的悖论:
对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解放成为新的压抑形式。
解放的中国妇女在她们欢呼解放的同时,背负上一副自由枷锁。
应该、也必须与妇女解放这一社会变革相伴生的、女性的文化革命被抹煞、或曰无限期的延宕了。
在为强有力的政权所支持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妇女解放是以完成时态写成的。
一切女性的苦难、女性的反抗、挣扎、女性的自觉与内省,都作为过去时态成为旧中国、旧世界的特定存在。
任何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对女性问题的提出与探讨,都无异于一种政治及文化上的反动。
如果说,女性原本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始终挣扎辗转在男权文化及语言的轭下;而当代中国女性甚至渐次丧失了女性的和关于女性的话语。
如果说,“花木兰式境遇”是现代女性共同面临的性别、自我的困境;而对当代中国妇女,“花木兰”、一个化妆为男人的、以男性身份成为英雄的女人,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女性的最为重要的(如果不说是唯一的)的镜象。
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3。
于是,当代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准分享话语权力的同时,失去了她们的性别身份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後。
在1949——1976年(新中国十七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一特定的历史的情节段落中,存在关于女性的唯一“叙事”是,只有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1949年前)妇女才遭受著被奴役、被蹂躏、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命运,她们才会痛苦、迷茫、无助而绝望。
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加诸女性的特殊命运,而是劳苦大众的共同命运。
所谓“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冬的苦井万丈深。
井底下压著咱受苦人,妇女是最底层”。
于是,对于女性命运的描述便成了劳动人民、受苦人这一共同命运的指称,一个恰当而深刻的象喻。
一旦共产党人的光辉照亮了她(他)们的天空,一旦新中国得以建立,这一苦难的命运便永远成了翻过去的历史中的一页。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而解放的到来并不意味著她们将作为新生的女性充分享有自由、幸福;而意味著她们应无保留地将这自由之心、自由之身贡献给她们的拯救者、解放者——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
她们的必然、唯一道路是由奴隶而为人(女人)、而为战士。
她们将不是作为女人、而是作为战士与男人享有平等的、或者说是无差别的地位。
于是,解放的中国妇女,在一个以男性为唯一规范的社会、话语结构中,承受著新的无名、无语的重负,承受著分裂的生活与分裂的自我:
一边是作为和男人一样的“人”,服务并献身于社会,全力地,在某些时候是力不胜任地支撑著她们的“半边天”;另一边则是不言而喻地承担著女性的传统角色。
新的法律和体制确乎使中国妇女免遭“秦香莲”的悲剧,但却未能解脱、甚或加剧了花木兰式的困境:
一个分裂的空间,双重的、同样沉重而虚假的性别角色。
如果说,当代中国女性之历史遭遇呈现为一个悖论:
她们因获得解放而隐没于历史的视域之外;那么,另一个历史的悖论与怪圈则是,她们在一次历史的倒退过程中重新浮出历史的地平线。
1976以後,伴随著震动中国大陆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思想解放运动,在一个主要以文学形态(伤痕文学、政治反思文学)出现的、有节制的历史清算与控诉之中,女性悄然地以一个有差异的形象——弱者的身份出现在灾难岁月的视域中,成为历史灾难的承受者与历史耻辱的蒙羞者4。
不再是唯一的男性规范中难于定义的“女人”,而是男权文化中传统女性规范的复归与重述。
似乎当代中国的历史,要再次凭借女性形象的“复位”,来完成秩序的重建,来实现其“拨乱反正”的过程。
在难于承受的历史记忆与现实重负面前,女性形象将以历史的殉难者、灵魂的失节者、秩序重建的祭品,背负苦难与忏悔而去。
甚至关于张志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十亿人众之中唯一的勇者、唯一的抗议者、真正的女英雄——的叙事话语也是:
“只因一只彩蝶翩然飞落在泥里、诗人眼中的世界才不再是黑灰色的。
5” 解放女性之自由枷锁在关于性别差异的话语中碎裂了,但这一关于女性的话语却是建立在微妙的性别歧视与女性之为“第二性”的基础之上的。
新的解放伴著“熟悉”的压抑不期然而临。
随著同心圆式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消弱,在社会的现实生活及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在世俗神话及大众传播媒介中,形形色色关于女性的侵犯性、歧视性的行为和话语开始以公然的、或隐晦的形式呈现出来。
而可悲的是,这一关于女性的历史性倒退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女性的默许、甚或配合。
事实上,在漫长的男性规范作为唯一的行为与性别规范的岁月中,在分裂的自我与双重性别角色的重负下,多数妇女已对空泛而虚假的“妇女解放”的现实与话语感到了极度的疲惫与厌倦。
另一方面,由于本应伴随著妇女解放运动而到来的女性的文化革命的“缺席”,以及性别差异的抹杀,使大多数妇女对于自己的精神性别充满了困惑、无知与茫然。
于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诡计与悖论,结束了“男女都一样”的时代,结束了男性规范作为施之于男人和女人的、唯一的规范之後,性别差异的重提使女性写作、女性作为话语主体的重现成为可能;这一倒退与坠落的时刻竟成了女性再次浮出历史地表的契机。
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女性自陈首先以反抗者的声音与形象出现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视域之中。
“女人不是月亮,不靠反射男人的光辉来照亮自己。
6” 继而发展成为在社会反思和社会批评的共存女性的乌托邦式梦想。
相对于此时期其它的社会、文化进程而言,女性的自觉、女性自我的出现是极为艰难、缓慢的,同时充满了误区与歧路。
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女性终于再度浮现,她们在自我质疑、自我陈述、甚或自我否定中困难地开始对自己精神性别的确认与对自己现实遭遇及文化困境的呈现。
她们作为话语主体再度开始对男权文化的黑海和女性的历史雾障的涉渡与穿越。
尽管此间的女性话语仍是混乱杂陈的,女性的本文仍充满了裂隙。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同五四时代的一个偶句,女性的再次觉醒、女性反抗、异己之声音的再次出现,又一次伴随著中国结束封闭、向著世界敞开国门的历史进程。
但是和五四时代不同,尽管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父权、极权时代的牺牲品和反抗者,尽管同是一次“历史性的弑父行为”的参与者;但这一次女性与男性之间并未能如同“少年中国之子”和五四之女那样结为伙伴与同谋。
这一次女性的反抗之声是微弱的,它在空旷的女性原野上播散,几乎没有回声。
甚至对于女性,女性的反抗与女性主义的声音也显得如此怪耽、陌生而异己。
它必须面对的是社会性的无视、冷漠,甚至是敌意与歧视。
如果说1976——1979之间,中国社会经历著一次旧秩序的破坏与新秩序的重建;那么,似乎这一新秩序的内容之一是男权的再确认。
而伴随改革开放及商业化进程的加快,男权与性别歧视也在不断地强化。
女性的社会与文化地位经历著或缓慢、或急剧的坠落过程。
然而,女性的自我与自陈也在这一过程中渐次走向成熟。
事实上,在中国大陆所经历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7”的过程中,女性因其日渐自觉的性别意识与独有的性别遭遇,首先觉悟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困境,正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为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典型情境:
西方世界在其经济与文化渗透的同时,成为一个携带著巨大的历史阉割力的“异己”(the other)者。
在世界文化语境中,种族的遭遇正成为民族视域中女性性别经历的异质同构体。
“解放”之女性的自陈正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之历史遭遇的象喻。
于是,“只有一个太阳”8,但它带来的未必是光耀与辉煌。
自觉或不自觉地,女性写作成了民族文化反抗及其文化的“生死搏斗9”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贰 '电影中的女性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以1949年作为划分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史的年代无疑是准确而恰当的。
因为1949年发生于中国大陆的,不仅是政治的剧变与政权的易主;一系列社会剧变的结果,是使中国历史发生了新的断裂。
1949年以後的中国文化、文学、艺术不复为後五四文化的延续,而成为断裂之後的一次从零开始。
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章。
10”悄然出现在40年代的女性文学同样悄然地消失了,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它们甚至不复出现在文学史上;于30—40年代已然具有成熟形态的中国电影成了一阙断音。
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在其起始处,其参照的唯一蓝本是新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它们是以不同的朴素而幼稚的艺术语言完成的对这一权力话语的重述与再确认。
于是,在由1949——1959年、从无到有、渐趋完善的革命经典电影形态中,逐渐消失了的,不仅是男性欲望视域中的女性形象;而且在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及其一套严密的电影的政治修辞学中,逐渐从电影的镜头语言中消失了的欲望的目光。
如果说,欲望视域和欲望语言的消失,成功地消解了内在于好莱坞式的经典电影叙事机制中的、特定的男权意识形态话语:
即,男性欲望、女性形象、男人看、女人被看的镜头语言模式11;然而这并不意味著这一革命经典电影模式是非男权的、或反男权的。
恰恰相反,它正是经过修正的、由强有力的父权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叙事形态。
一方面,这一新经典电影几乎无例外地呈现为权威视点(当然是男性的、尽管不是男性欲望视点)中的女性被述,而不是女性自陈;另一方面,女性形象不再作为男性欲望与目光的客体而存在,她们同样不曾作为独立于男性的性别群体而存在。
电影叙事中欲望的语言及人物欲望目光的消失,银幕上人物形象呈现为非性别化的状态。
男性、女性间的性别对立与差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物间阶级与政治上的对立和差异。
同一阶级间的男人和女人,是亲密无间、纯白无染的兄弟姐妹。
他们是同一非肉身的父亲——党、人民的儿女。
他们是作为一个共同的叙事形象、或曰空间形象而存在的。
正是这类模糊了性别差异的叙事造成了欲望的悬置,并将其准确地对位、投射于一个空位、那位非肉身的父亲:
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及共产主义事业。
它成功地实现了一个阿尔图塞所谓的意识形态“询唤”12,一种拯救者向被拯救者索取的绝对忠诚。
无性别或非性别的人物形象与叙事同时实现著对个人欲望及个人主义的否定与潜抑,在这一革命经典叙事形态中,任何个人私欲都是可耻而不洁的,都将损害那份绝对忠诚。
在这一高度政治象征化的革命经典叙事中,引人注目的是女性的“新人”形象。
那是翻身、获救的女性,和这些解放的女性终于成长而为的女战士、女英雄。
事实上,这两种女性的“新人”形象出现在新中国最早的电影作品《白毛女》(水华、王滨导演,1950年)和《中华女儿》(凌子风导演,1950年)之中,成为两种基本的女性类型形象,并成了中国当代电影中关于女性叙事(1949——1979年)的基本原型。
其间女性仍置身于为光明王国(共产党人)和黑暗王国(以国民党为代表)所争夺的价值客体的位置上。
她们注定历经苦难,被侮辱、被损害,直到一个男性的共产党人将她们救赎出苦海13。
她们将在一个乌有的历史缝隙中获得她们的精神性别,享有一个解放的妇女、一个新女性的自由与权力。
然而,获得是为了再度奉献,她将成为一个巨大群体中非性化的一员,作为一个化妆为男人的女人,一个消融在群体中的个体而成长、凸现为英雄——一个“女”英雄。
(《红色娘子军》谢晋导演,1959年。
《青春之歌》崔嵬导演,1959。
)这一革命的经典叙事模式,在其不断的演进过程中,发展而为一个不知性别上何物的女性的政治与社会象征。
那时是“铁胳膊、铁腿、铁肩膀”的“铁姑娘”,那时是“站在高坡上,穿著红衣裳,挥手指方向”的“女性”共产党人。
在女性伸展与解放的身体形象下,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潜抑力与整合力。
1965年以後,当代中国电影中充满了鳏、寡、孤、独的人物形象。
此时,遭到潜抑与放逐已不只是女性的精神性别,而且是人物的血肉之躯。
与此同时,一个始终被延用的经典女性原型是母亲、地母。
在当代中国电影特定的编码系统和政治修辞学之中,母亲形象成为“人民”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之核心能指的负荷者,一个多元决定的形象。
在革命经典电影的叙事中,她与另一个核心能指共产党人成为一组相映成趣的被拯救者、拯救者、拯救者、被拯救者的互补关系。
作为“人民”、劳苦大众的指称,她同样置身于苦井的最底层,期待著、盼望著共产党人将她救赎出来,得见天日;同样作为“人民”的指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动力。
”14),她是历史的原动力与拯救力,她是安泰、共产党人的大地母亲。
(《母亲》,凌子风导演,1956年,《革命家庭》,水华导演,1964年)。
她是传统美德——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呈现者。
母亲形象所负荷的无言的承受、默默地奉献,又成为当代中国唯一得到正面陈述与颂扬的女性规范。
事实上,正是母亲形象成了一座浮桥,连接起当代中国两个历史时期(1949——1976年,1976年——至今)关于女性的电影叙事。
事实上,当代中国主流电影正是凭借著女性表象由战士而为母亲的历史性後退动作,完成了其意识形态与叙事模式的转换。
在谢晋影片《啊,摇篮》(1979年)中,一个充分男性化(同时被影片呈现为女性的异化形式)的女军官,因再度复苏、萌动了母爱,而成了一位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人”。
她终于从历史的、画面的前景撤入後景之中,将广阔的前景、历史的空间归还给男人。
尽管出现在影片结局中的仍是异姓的、非血缘的一家人,但作为同一叙事模式的反转,不再是破碎的家庭将女人抛出了传统的轨道、投入了历史的进程;而是通过家庭的重组回收了离轨的女人。
新时期主流电影通过女性表象的复位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拨乱反正”的过程。
再一次,“摇摇篮的手,摇动世界。
”此间,叙事艺术中的女性、母亲、地母形象仍是超负荷的、或曰多元决定的。
她们分别、或同时承担著历史控诉、历史清算(白桦小说《妈妈啊,妈妈》)、历史的拯救与想象性的抚慰(谢晋《天云山传奇》,冯晴岚,1979年,水华《兰色的花》,大娘和妞妞,1979年,谢晋《牧马人》,李秀芝,1981年)、不堪重负的忏悔(《天云山传奇》,宋薇),历史的蒙难者与祭品(冯晴岚、谢晋《芙蓉镇》,胡玉音,1987年)等多重编码。
女性再度成为经典编码与传统意义上的“空洞的能指”,其所指、意义将参照并依据男人来界定。
她们遭劫难、被审判,她们背负、忍受、罹难,这一切都为了男人、历史的获救与赦免。
女性仍未呈现在男性欲望的视野中,她们作为女人出现在历史的视野中,是为了再度被放逐出历史之外,通过这放逐式,人们(男人)将得以放逐历史的幽灵,并在想象中掩埋灾难时代的尸骸。
一如在1949——1976年的主流电影中,女人、性场景始终作为“结构性缺席”,成为影片政治叙事中的“另一场景”;此时,女人、性场景的出演,则成了“另一场景”——现实政治困境的指称,以及对这一困境的想象性解决。
而在1979年前後出现于中国影坛的第四代,则以另一种方式来处理影片中的女性表象。
如果说,第四代的意义正在于对主流电影样式及其艺术——政治工具论的全线突围,而他们孱弱、哀婉的抗议与控诉,终于只成就了一些“大时代的小故事”;那么,在第四代的影片中,女性形象成了历史的剥夺与主人公内在匮乏的指称,成了那些断念式的爱情故事中一去不返的美丽幻影(黄建中《如意》,1982年,“各自手执一柄如意,而始终未能如意。
藤文骥《苏醒》,1981年)。
在那些凄楚的、柏拉图、或乌托邦的爱情故事中,理想的寄寓洗去了欲望的意味;叙境中的女性甚至不曾被指认(杨延晋《小街》,1980年)。
在美丽的女神和美丽的祭品之间,女性表象成了第四代被政治暴力所阻断的青春梦旅、为历史阉割力所造成的生命与人格匮乏的指称。
正当第四代给影坛带来几缕清新的风、几颗清澈、却失落了灵氛的星时,历史、文化反思运动,作为新时期又一次颠覆性的文化革命,以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及其潜在的文化矛盾席卷了中国大陆。
此间中国大陆所经历的结束浩劫时代、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命运,决定了这一历史、文化反思运动是五四文化革命的精神延续,是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潜在参照系展开的、对封建文化、历史惰性的再清算与再批判,以期为现代化进程开路;同时决定了它是对五四运动的悖反,是民族的寻根、传统的再认识,是穿越五四文化裂谷的尝试,是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对西方经济、文化渗透的抵御和反抗。
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在叙事性作品中大量涌现的女性表象,再度成为与女性生存、女性真实无涉的“空洞的能指”、或曰男性历史的“想象的能指”。
作为又一次历史的诡计,它成了再次针对女性的文化倒退与反动。
在历史清算与文化寻根的悖论式努力之中,女性表象将又一次为男权世界偿还历史债务。
寻根作品的基本母题之一是:
干涸、无水的土地、饥渴、无侣的男人,作为叙境中的两个主要角色;寻找水源争夺女人作为民族(男人)生存寓言的情节主部;年长的、有权势的、丧失了生育力的男人、父亲独占了女人的故事,成了东方杀子文化与历史阉割力的象喻,歌声成了水源、女人象喻性的替代。
寻根作品中的一部因之而成了种族死灭的寓言。
而在寻根作品的另一个母题:
象(图象)与字(文字)的对立,表现在文字、语言、历史之外,万古岿然的自然、空间;其中,女人——“宽臀大乳”的女人成了自然的指称,成了原初生命力的象征,成了毁灭性的历史之外的人类(种族)的拯救力。
于是,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中出现了某种人类文化学式的叙事范型,男人间交换(或拒绝交换)女人的故事被再度讲述。
在这一时期(1982——1985年)的第四代作品中,在他们共有的“文明与愚昧”的主题中,女人成了愚昧的牺牲、文明的献祭、历史的演进与拯救;成了第四代文化死结的背负者(丁荫楠《逆光》,1982年,滕文骥《都市里的村庄》1982年,《海滩》,1984年,胡柄榴《乡情》,1981年,《乡音》1983年,吴天明《老井》1985年,颜学恕《野山》1987年。
)此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第四代的导演们将欲望与压抑的故事、将典型的男性文化困境移置于女性形象。
(谢飞《湘女萧萧》1984年,黄建中《良家妇女》1984年,《贞女》1986年),女人又一次成了男人的假面。
第五代于同一时期出现在中国影坛上,几乎立刻进入了世界文化视野。
在其早期创作中,第五代以拒绝女性形象、拒绝叙事(拒绝“时间”,同时拒绝男人与女人的故事),拒绝进入文化、历史的象征式,拒绝与主流电影、主流文化作出任何妥协。
第五代的经典之作由是而成了“子一代的艺术”。
事实上,第五代将文化反思运动的内在矛盾推到了极致。
于是,为了彻底解脱这一困境,第五代在其解体(1987年)的同时,仍必须借助女性表象来重新加入历史、文化与叙事。
正是在第五代的部分作品中,男性欲望的视野终于再次出现,并且因男性欲望的目光将女性指认为一个特定性别的存在。
女性在男人欲望的视域中再度浮现。
部分得益于此,第五代的作品跨越了1949年政治变迁所制造的历史断裂,完成了与中国电影传统的对接,并成功地闯入了世界影坛。
男人之于女人的欲望视域首先呈现在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1987年)之中。
女人的进入,不仅为第五代提供了悬置以久的象征性的成人式,解脱了其“子一代”无名、无语的状态,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叙事之复归的契机。
继而在另一位第五代导演周晓文的商业作者电影《疯狂的代价》(1988年)中,女人出现在男人窥视、渴欲而又恐惧的视域之中。
女性形象的复现是为了完成一次想象性的放逐,完成对男性文化及困境的呈现与消解。
正是在1987年前後,商业化大潮第一次冲击了中国大陆,当代中国文化、电影历史地面临著一种新的“异己”者。
一如当代中国女作家们从自己独特的性别体验中,悟到了後殖民主义文化中,种族与性别命题的同构及相关;中国大陆的艺术电影制作者则在其生存困境中领略了这第三世界文化的“逃脱与落网”之途。
和同时期女作家以性别的叙事作为民族文化的抗争不同,此後第五代的创作呈现为一种文化屈服和民族文化的、“内在的自我放逐”的历程。
他们必须将这一咄咄逼人的“异己者”的视点内在化,同时将民族的历史、经验与体验客体化。
其中,张艺谋的《菊豆》(1989年)、《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 年)、陈凯歌的《边走边唱》(1991年)、《霸王别姬》(1993年)成为这类趋向中的典型之作。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男主角的视觉缺席、多进四合院、古典建筑博物馆式的空间的入主,成群妻妾间的争风吃醋作为中国式的“内耗”与权力斗争的象喻,负荷著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历史反思的内涵;而在西方的文化视域中,却成了欲望主体、欲望视域的发出者的悬置,成了可供西方观众去占据的空位。
东方式的空间、东方故事、东方佳丽共同作为西方视域中的“奇观”(spectacle),在“看”、被看、男性、女人的经典模式中,将跻身于西方文化边缘中的民族文化呈现为一种自觉的“女性”角色与姿态。
中国电影单元(九)可见与不可见的女性: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下)
来源:
作者:
戴锦华 2001-08-3115:
04:
05
参 '女性的电影
作为当代中国女性文化及生存困境最为直接的呈现,是当代中国无疑拥有全世界最为强大、蔚为观止的女导演阵容:
执导了两部以上影片、迄今仍在进行创作的女导演多达三三十余人,成为各大电影制片厂创作主力的十余人,具有不同程度的世界知名度的女导演亦有五、六人之多(诸如黄蜀芹、张暖忻、李少红、胡玫、宁瀛、王君正、王好为、广春兰等);然而在新中国四十余年的电影史上,可以称为女性电影的影片如果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凤毛麟角的。
在大部分女导演的作品中,制作者的性别因素无论是在影片的选材、故事、人物、叙事方式、镜头语言结构上,都是难于辨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