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规0809范事实0806.docx
《正义规0809范事实0806.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正义规0809范事实0806.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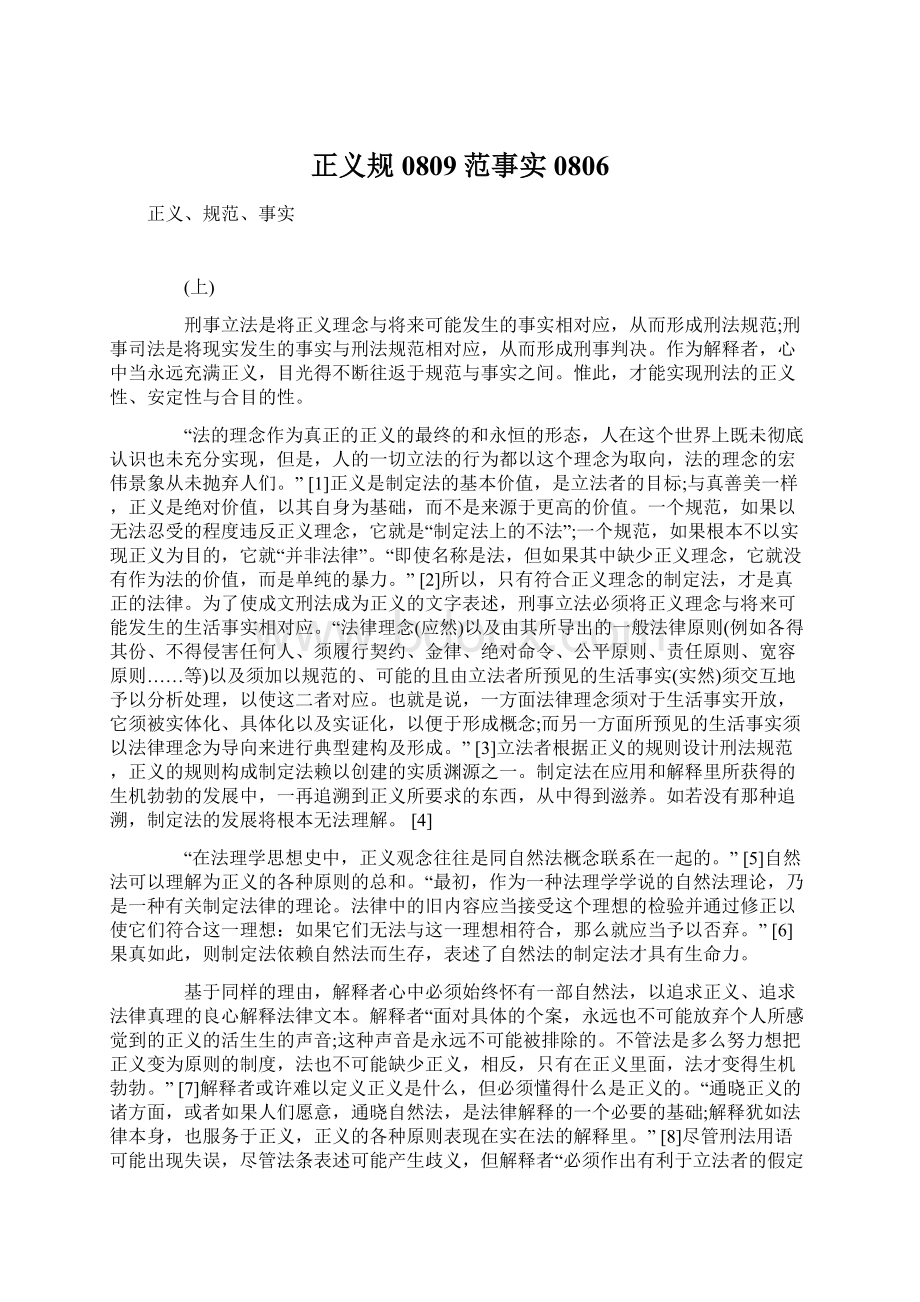
正义规0809范事实0806
正义、规范、事实
(上)
刑事立法是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从而形成刑法规范;刑事司法是将现实发生的事实与刑法规范相对应,从而形成刑事判决。
作为解释者,心中当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得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
惟此,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
“法的理念作为真正的正义的最终的和永恒的形态,人在这个世界上既未彻底认识也未充分实现,但是,人的一切立法的行为都以这个理念为取向,法的理念的宏伟景象从未抛弃人们。
”[1]正义是制定法的基本价值,是立法者的目标;与真善美一样,正义是绝对价值,以其自身为基础,而不是来源于更高的价值。
一个规范,如果以无法忍受的程度违反正义理念,它就是“制定法上的不法”;一个规范,如果根本不以实现正义为目的,它就“并非法律”。
“即使名称是法,但如果其中缺少正义理念,它就没有作为法的价值,而是单纯的暴力。
”[2]所以,只有符合正义理念的制定法,才是真正的法律。
为了使成文刑法成为正义的文字表述,刑事立法必须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生活事实相对应。
“法律理念(应然)以及由其所导出的一般法律原则(例如各得其份、不得侵害任何人、须履行契约、金律、绝对命令、公平原则、责任原则、宽容原则……等)以及须加以规范的、可能的且由立法者所预见的生活事实(实然)须交互地予以分析处理,以使这二者对应。
也就是说,一方面法律理念须对于生活事实开放,它须被实体化、具体化以及实证化,以便于形成概念;而另一方面所预见的生活事实须以法律理念为导向来进行典型建构及形成。
”[3]立法者根据正义的规则设计刑法规范,正义的规则构成制定法赖以创建的实质渊源之一。
制定法在应用和解释里所获得的生机勃勃的发展中,一再追溯到正义所要求的东西,从中得到滋养。
如若没有那种追溯,制定法的发展将根本无法理解。
[4]
“在法理学思想史中,正义观念往往是同自然法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5]自然法可以理解为正义的各种原则的总和。
“最初,作为一种法理学学说的自然法理论,乃是一种有关制定法律的理论。
法律中的旧内容应当接受这个理想的检验并通过修正以使它们符合这一理想:
如果它们无法与这一理想相符合,那么就应当予以否弃。
”[6]果真如此,则制定法依赖自然法而生存,表述了自然法的制定法才具有生命力。
基于同样的理由,解释者心中必须始终怀有一部自然法,以追求正义、追求法律真理的良心解释法律文本。
解释者“面对具体的个案,永远也不可能放弃个人所感觉到的正义的活生生的声音;这种声音是永远不可能被排除的。
不管法是多么努力想把正义变为原则的制度,法也不可能缺少正义,相反,只有在正义里面,法才变得生机勃勃。
”[7]解释者或许难以定义正义是什么,但必须懂得什么是正义的。
“通晓正义的诸方面,或者如果人们愿意,通晓自然法,是法律解释的一个必要的基础;解释犹如法律本身,也服务于正义,正义的各种原则表现在实在法的解释里。
”[8]尽管刑法用语可能出现失误,尽管法条表述可能产生歧义,但解释者“必须作出有利于立法者的假定”[9],相信立法者不会制定非正义的法律。
当解释者对法条作出的解释结论不符合正义理念时,不要抨击刑法规范违背正义理念,而应承认自己的解释结论本身导致不符合正义理念。
当解释者对法条难以得出某种解释结论时,不必攻击刑法规范不明确,而应反省自己是否缺乏明确、具体的正义理念。
所以,解释者与其在得出非正义的解释结论后批判刑法,不如合理运用解释方法得出正义的解释结论;与其怀疑刑法规范本身,不如怀疑自己的解释能力与解释结论。
在经济发展的复杂社会与重视人权的法治时代,不可能直接根据正义理念或自然法认定犯罪。
否则,“尤像18世纪自然法所展示的,走入法的不安定性和任意性。
”[10]因为,正义“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1],而“法律应当是客观的,这一点是一个法律制度的精髓。
”[12]所以,活生生的正义必须具体化、实证化。
换言之,“在论述自然法时,永远不可能是谈论一个完整的、随时随地(hicetnunc)都可以应用的制度,而是仅仅涉及正义的一些原则。
但是,这些原则需要进行某种具体化,才能应用于某些特定的生活情景。
这种必要的改造由实证化(Positiverung)来完成,实证化把那些原则变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法的规则。
”[13]正因为如此,以实现民主与尊重人权(保障国民自由)为己任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以成文的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成文法主义)。
刑法学鼻祖费尔巴哈极力主张罪刑法定主义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克服刑法的不安定性。
18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刑事司法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
一方面,启蒙主义与启蒙时期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已经在理论上与立法上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历来的普通法理论与实务仍然流行。
《加罗林纳刑事法典》在18世纪作为帝国的法律仍然成为普通刑法的基础,但启蒙主义与启蒙时期的自然法思想使得《加罗林纳刑事法典》的宗教基础发生了动摇;法官们为了避免残酷的刑罚,拒绝适用制定法,代之以作为自然法的理性为根据。
于是法的安定性受到了明显损害。
[14]正因为如此,费尔巴哈主张,法官应当受制定法严格且直接的文字规定的拘束;法官的事务应当仅仅在于对于现实的个案以法律规定的文字加以比较:
如果条文规定的文字是谴责,则毋需顾及制定的法的意旨与精神,即应对现实个案判决有罪;反之,如果法律规定的文字是无罪,则应判决无罪。
费尔巴哈还禁止人们对他起草的《巴伐利亚刑法典》进行解释,理由是基于权力分立的法治国的缘故。
尽管如此,费尔巴哈却从未要求法官应当无论如何都遵守制定法;在服从制定法将违反法官之存在仅仅效劳于正义之时,费尔巴哈甚至认为,法官的不服从简直是一项神圣的义务。
[15]费尔巴哈看似矛盾的观点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制定法吸收了自然法,自然法生活在制定法之中,自然法与制定法融为一体。
罪刑法定原则之所以派生成文法主义,是因为文字可以固定法律含义,可以反复斟酌,可以广为传播,成为立法机关表达正义理念的惟一工具。
当然,在所有的符号中,文字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种。
几乎任何用语的意义都会由核心意义向边缘扩展,使之外延模糊;绝大部分用语都具有多种含义;法律制定以后,其所使用的文字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含义;而且言不尽意的情况总是存在。
尽管立法机关在制定刑法时,对许多用语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但是,“一般而论,科学的定义要比词语的通俗意义狭隘得多,因而实际上也不精确得多、不真实得多。
”[16]所以,成文刑法的文字表述总是存在疑问。
在这种情况下,解释者必须以善意将成文刑法规范朝着正义的方向解释,使正义的自然法展示于成文刑法之中。
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现行的法的制度能够仅仅由自身来理解,毋宁说,它必须追溯到现行法之前的或者超过现行法的即此前存在的规则——而后者当中也包括正义的规则。
”[17]法解释学既要以正义理念为指导,又要揭示制定法中的正义理念;不是以正义理念为指导、不揭示制定法中的正义理念的法解释学,只能称为“文字法学”。
所以,解释者必须把握立法者从形形色色的行为中挑选出作为犯罪科处刑罚的实质的、正义的标准,使根据正义的标准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都是犯罪,使相同的行为在刑法上得到相同的至少是相似的处理。
另一方面,不能离开刑法用语、法条文字去追求“正义”。
法学解释的对象是成文的法律,完全脱离法律用语就是推测而不是解释。
刑法通过文字规范人们(包括一般人与司法者)的行为,人们通过文字把握刑法的含义。
如果脱离刑法用语追求所谓“正义”,人们在具体情况下便没有预测可能性,刑法本身也丧失安定性,国民的自由便没有保障,国民的生活便不得安宁。
所以,刑法的正义,只能是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的正义。
解释者所要做的,便是使文字与正义形成一体。
概言之,解释者在解释刑法时,必须根据刑法规定犯罪的实质的、正义的标准,并且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确定犯罪的范围,使实质的、正义的标准与刑法用语的含义相对应,正确界定犯罪的内涵与外延。
惟有如此,才能在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同时,实现刑法的安定性。
虽然成文刑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但并不意味着仅仅根据文字就可以发现刑法的全部真实含义。
事实上,不管是采取主观的解释,还是采取客观的解释,都不是单纯通过法条文字揭示刑法的真正含义。
有的国家刑法制定了近百年。
近百年来,无数的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在解释刑法;而且,只要该刑法没有废止,还将继续解释下去。
无论是披露立法者的原意,还是揭示法条的客观含义,都不至于花费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人们之所以一直在解释现行有效的刑法,是因为“一个词的通常的意义是在逐渐发展的,在事实的不断出现中形成的”[18];活生生的正义还需要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发现;制定法的真实含义不只是隐藏在法条文字中,而且同样隐藏在具体的生活事实中。
即使解释者单纯根据法条文字得出的结论具有正义性,也只是一般正义;而刑法的适用除了实现一般正义外,还必须在具体的个案中实现个别正义。
所以,一方面,任何一种解释结论的正义性,都只是相对于特定的时空、特定的生活事实而言,生活事实的变化总是要求新的解释结论。
“任何一种解释如果试图用最终的、权威性的解释取代基本文本的开放性,都会过早地吞噬文本的生命。
”[19]解释者应当正视法律文本的开放性,懂得生活事实会不断地填充法律的含义,从而使法律具有生命力。
另一方面,“规范必须与生活事实进入一种关系,它必须符合事物。
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解释’:
探求规范的法律意义。
然而这种意义并非如传统法学方法论所说的,仅隐藏在制定法中,隐藏在抽象而广泛的意义空洞的法律概念中,相反地,为了探求此种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某些直观的事物,回溯到有关的具体生活事实。
没有意义,没有拟判断之生活事实的‘本质’,是根本无法探求‘法律的意义’的。
因此,‘法律意义’并非固定不变的事物,它系随着生活事实而变化——尽管法律文字始终不变——,也就是随着生活本身而变化。
”[20]所以,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而且在于生活。
正因如此,刑法分则条文并非界定具体犯罪的定义,而是以抽象性、一般性的用语描述具体犯罪类型。
“形式、抽象性、一般性、以及概念性是对于法律的形成完全不可缺少的,否则法将没有所谓的等同对待,也将没有正义存在。
如果人们在其中不保证将始终变动的生活关系的独有性及特殊性在法律的发现过程中引入,那么纯粹从法律规范演绎出来的‘正义’将会是一种‘永久的、重复相同的’僵化机械论,一种自动化——或者是电脑的——‘正义’,一种非人性的‘正义’。
”[21]刑法分则所描述的犯罪类型是开放的,它虽然有一个固定的核心,但没有固定的界限。
即使立法者当初根本没有想象到的事实,经过解释也可能完全涵摄在刑法规范中;或者相反。
于是,经过解释后的刑法,不再是制定时的刑法;虽然刑法的文字仍然相同,但其内容已经改变。
所以,成文刑法比立法者更聪明。
[22]
__________________
[1][德]H.科殷:
《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日]山田晟:
《法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新版,第72页。
[3][德]亚图.考夫曼:
《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8页。
[4][德]H.科殷:
《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5][美]E.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6][美]罗斯科.庞德:
《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7][德]H.科殷:
《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8][德]H.科殷:
《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
[9]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rancisoSuarez)语,转引自[美]E.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10][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
《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
[11][美]E.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12][英]G.D.詹姆斯:
《法律原理》,关贵森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13][德]H.科殷:
《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2页。
[14]参见[日]内藤谦:
《刑法中的法益概念的历史的展开
(一)》,载《东京都立大学法学会杂志》1966年第6卷第2号,第226页以下。
[15]参见[德]亚图.考夫曼:
《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44页。
[16][法]基佐:
《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页。
[17]德国学者奥菲尔斯(Ophüls)语,转引自[德]H.科殷:
《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18][法]基佐:
《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页。
[19][英]韦恩.莫里森:
《法学理》,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5页。
[20][德]亚图.考夫曼:
《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89页。
[21][德]亚图.考夫曼:
《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22页。
[22]参见[德]亚图.考夫曼:
《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36~237页。
(下)
法律实证主义的典型代表Bergbohm认为,“法律绝不需要从外在加以填补,因为它在任何时刻都是圆满的,它的内在丰富性,它的逻辑延展力,在自己的领域中任何时刻都涵盖了法律判决的整体需要。
”[1]但是,“我们的时代已不再有人相信这一点。
谁在起草法律时就能够避免与某个无法估计的、已生效的法规相抵触?
谁又可能完全预见全部的构成事实,它们藏身于无尽多变的生活海洋中,何曾有一次被全部冲上沙滩?
”[2]“很明显,立法者难以预见到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大量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3]为了使法律满足一个处在永久运动中的社会的所有新的需要,解释者在面对某种崭新的生活事实,同时根据正义理念认为有必要对之进行刑法规制时,总是将这种生活事实与刑法规范相对应,现实的生活事实成为推动解释者反复斟酌刑法用语真实含义的最大动因。
当行为人携带刀具、棍棒等抢夺时,解释者会习惯于将“凶器”解释为一种器具;而当行为人携带含有SARS病毒的注射器抢夺时,便会迫使解释者回答“含有SARS病毒的注射器是否凶器”这样的问题。
要追问立法者当初是否曾经想到过有人会携带含有SARS病毒的注射器抢夺,是不明智的。
所以,当解释者将“携带凶器抢夺”作为判断案件的大前提,而面对行为人携带含有SARS病毒的注射器抢夺的事实时,必然不断地对构成要件要素(“凶器”)进行解释,不断地对现实事实进行分析。
换言之,判断者的目光应不断地往返于大小前提之间,使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交互作用,从而发现法律、做出判决。
具体地说,“法学家必须把他应当判决的、个别的具体的个案与组成实在法的法制的或多或少是抽象把握的各种规则联系起来。
规则和案件是他的思维的两个界限。
他的考虑从案件到规则,又从规范到案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权衡。
案件通过那些可能会等丰拿来应用的、可能决定判别判决的规则进行分析;反之,规则则是通过某些特定的个案或者案件类型进行解释。
”[4]换言之,在刑法解释、适用的程序中,必须对刑法规范与案例事实交互地分析处理,一方面使抽象的法律规范经由解释成为具体化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要将具体的案例事实经由结构化成为类型化的案情;二者的比较者就是事物的本质、规范的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构成要件与案例事实的彼此对应。
即“规范成为‘符合存在的’,案件成为‘符合规范的’。
并且逐步地规范变成较具体的、较接近现实的,案件变成轮廓较清楚的,成为类型。
”[5]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将生活事实与规范相拉近,另一方面将规范与生活事实相拉近。
二者是一种同时且连续发展的由事实自我开放的向规范前进和规范现事实前进。
“只有在规范与生活事实、应然与实然,彼此互相对应时,才产生实际的法律:
法律是应然与实然的对应。
”[6]
例如,构成要件的内容是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当解释者面临的案情是,甲将他人的电视机从楼上摔至楼下,导致电视机不仅物理上毁损,而且丧失其本来用途时,他可能将“毁坏”解释为:
“通过财物的全部或者一部分进行物质性破坏、毁损,以致全部或者部分不能遵从该财物的本来用途进行使用”。
进而得出甲的行为符合毁坏要件的结论。
但是,当解释者面临的案情是,乙故意将他人价值1万元的戒指扔入大海中时,上述“毁坏”的定义会导致乙的行为无罪。
当解释者认为他人戒指值得刑法保护、乙的行为值得科处刑罚时,必然重新解释“毁坏”。
解释者可能将“毁坏”解释为:
“对财物行使有形力,毁损财物或者损害财物的价值、效用的行为”,并且将乙的行为抽象为:
对他人财物(戒指)行使有形力,导致他人丧失财物(显然不能将乙的行为抽象为“使他人戒指转移于大海中”),从而使乙的行为符合毁坏要件。
可是,当解释者面临的案情是,丙故意将他人的鸟笼打开,使他人价值1万元的鸟飞走时,上述两种“毁坏”定义都将导致丙的行为无罪。
当解释者认为他人的鸟值得刑法保护,丙的行为值得科处刑罚时,必然再次重新解释“毁坏”。
解释者可能将“毁坏”解释为:
“导致财物的效用减少或者丧失的一切行为”,并且将丙的行为抽象为:
使他人丧失了财物的效用(显然不能将丙的行为抽象为“使鸟回归大自然”),从而使乙的行为符合毁坏要件。
解释者之所以反复定义“毁坏”,是因为面临着不同的生活事实;之所以并不简单地以第一个定义否认乙、丙行为的可罚性,是因为解释者认识到他人的戒指与鸟值得刑法保护。
规范与事实之所以能够取得一致,是由于存在一个第三者,即当为与存在之间的调和者——事物的本质。
“从法律意义上说,‘事物的本质’这一概念并不指派别之间争论的问题,而是指限制立法者任意颁布法律、解释法律的界限。
诉诸事物的本质,就是转向一种与人的愿望无关的秩序,而且,意味着保证活生生的正义精神对法律字句的胜利。
因此,‘事物的本质’同样断言了自身的权利,是我们不得不予以尊重的东西。
”[7]“‘事物本质’是一种观点,在该观点中存在与当为互相遭遇,它是现实与价值互相联系(‘对应’)的方法论上所在。
因此,从事实推论至规范,或者从规范推论至事实,一直是一种有关‘事物本质’的推论。
”[8]之所以认为将他人的戒指扔入大海与毁坏他人财物相对应,是因为刑法规定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目的在于保护他人财产,保护的方式是禁止毁坏他人财物;而将他人的戒指扔入大海的行为本质,是毁坏了他人财产。
如果不是从这一“事物本质”出发,毁坏他人财物的构成要件与将他人戒指扔入大海的行为,是难以相互对应的。
由此可见,只有通过生活事实解释规范,才能实现刑法的合目的性。
总之,刑法的解释就是在心中充满正义的前提下,目光不断地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的过程。
当然,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判断者一定要达到有罪结论才罢休。
无论如何不能通过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歪曲案件事实得出有罪结论。
换言之,在既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又不歪曲事实的前提下,如果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彼此对应,则应得出有罪的结论。
另一方面,不要以为,越是能“设定”刑法漏洞,就越有学术成就。
因为刑法学的任务并不是设定漏洞,相反应当合理地填补漏洞。
没有人会认为,能将谋杀解释为无罪,是学术上的辉煌成就和罪刑法定主义的伟大胜利。
因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恣意地将根据普遍的正义标准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解释为刑法没有规定的行为,必然不利于保护法益,必然违反民主主义,因而从根本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通过事实解释规范,与将某些事实强加于规范、以某种事实限制规范大相径庭。
“将熟悉与必须相混淆”是人们常犯的错误。
[9]人们在解释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时,习惯于将自己熟悉的事实视为应当的事实,进而认为刑法规范所描述的事实就是自己熟悉的事实。
例如,当人们熟悉了二者间的诈骗时,便习惯于认为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只包含二者间的诈骗,而将三角诈骗(诉讼诈骗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排除在外。
当人们熟悉了秘密窃取财物的盗窃行为时之后,便习惯于认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不包括公开盗窃的情形。
这显然混淆了事实与规范,而且使规范处于封闭状态。
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新的犯罪,即使是传统犯罪,也不乏新的手段与方式。
所以,人们所熟悉的只是部分有限的事实。
而构成要件所描述的是犯罪类型,只要属于某犯罪类型,就被描述该类型的构成要件所涵摄。
所以,将规范的涵摄范围限定为解释者所知的有限事实,并不合适。
综上所述,刑法的解释就是正义理念、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的相互对应。
这里首先遇到的疑问是,由于解释者的价值观不同,对于同样的解释结论,有人认为是正义的,有人可能认为是非正义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应当如何取舍?
这虽然是一个难题,但并不意味着解释者无能为力。
第一,对于一般的、基本的正义原则,解释者之间不会产生明显分歧。
第二,“使法律之间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Concordarelegeslegibusestoptimusinterpretandimodus.)。
因为正义被实证化,正义的核心是平等,它要求对所有的人都应用一种统一的标准,所以,对刑法分则进行体系解释,使刑法条文之间保持协调,使相同的犯罪得到相同的处理,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
例如,倘若解释者将招摇撞骗解释为包含骗取财物,就会形成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协调:
一方面,当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时,因为行为人所犯的并非诈骗罪,不能适用刑法第269条,进而出现不公平的现象:
采用其他方法骗取财物的,可能转化为抢劫,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财物的,不可能转化抢劫。
[10]另一方面,采取其他方法诈骗公私财物的,最高可以判处死期徒刑;而采取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方法骗取财物的,最高只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
[11]既然如此,解释者便不应认为招摇撞骗罪包含骗取财物。
易言之,只要将招摇撞骗解释为不包含骗取财物,便可以使处罚公平合理,也不会出现处罚上的漏洞。
第三,一致的价值经验是认识正义的基础。
正义“原则是从在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定的、反复出现的基本境况和基本事实方面法的理念和事物本质的社会道德内涵引申出来的。
只要它们与某些特定的境况有关系,并且从人类本性或者事物本质的某些特定的状况出发,它们就在它们的伦理的基础里,即先验地包含着经验的要素。
它们属于人的世界;它们的适用局限在人的这个世界上。
”[12]解释者应当善于观察一般人的生活与心理,准确了解人类本性与事物本质。
“人文科学的‘业务’是了解人类的表示。
‘最重要的不是单纯地观察,毋宁是对被观察到的、有意义的人类生活表现的解释’。
这点既适用于历史学家,也适用于法学家。
”[13]第四,在解释刑法时,不仅要想象“如果自己是当初的立法者,会得出何种结论”,而且还要想象“如果自己是当今的立法者,会得出何种结论”。
第五,当然,“只有自己是正义的,才能认识正义的事情”[14],才能揭示刑法的正义理念。
“学者的良心是追求真理、阐述真理的良心。
”[15]只有凭着良心解释刑法,才不至于违反刑法的正义理念。
疑问还在于:
如何使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相对应?
这便需要反复、合理地运用各种解释方法,准确分析生活事实,正确理解规范与事实的本质,直至得出符合正义的结论。
“相对于裁判的字义,法官在案件中有着先前判断与先前理解。
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