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学民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docx
《戚学民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戚学民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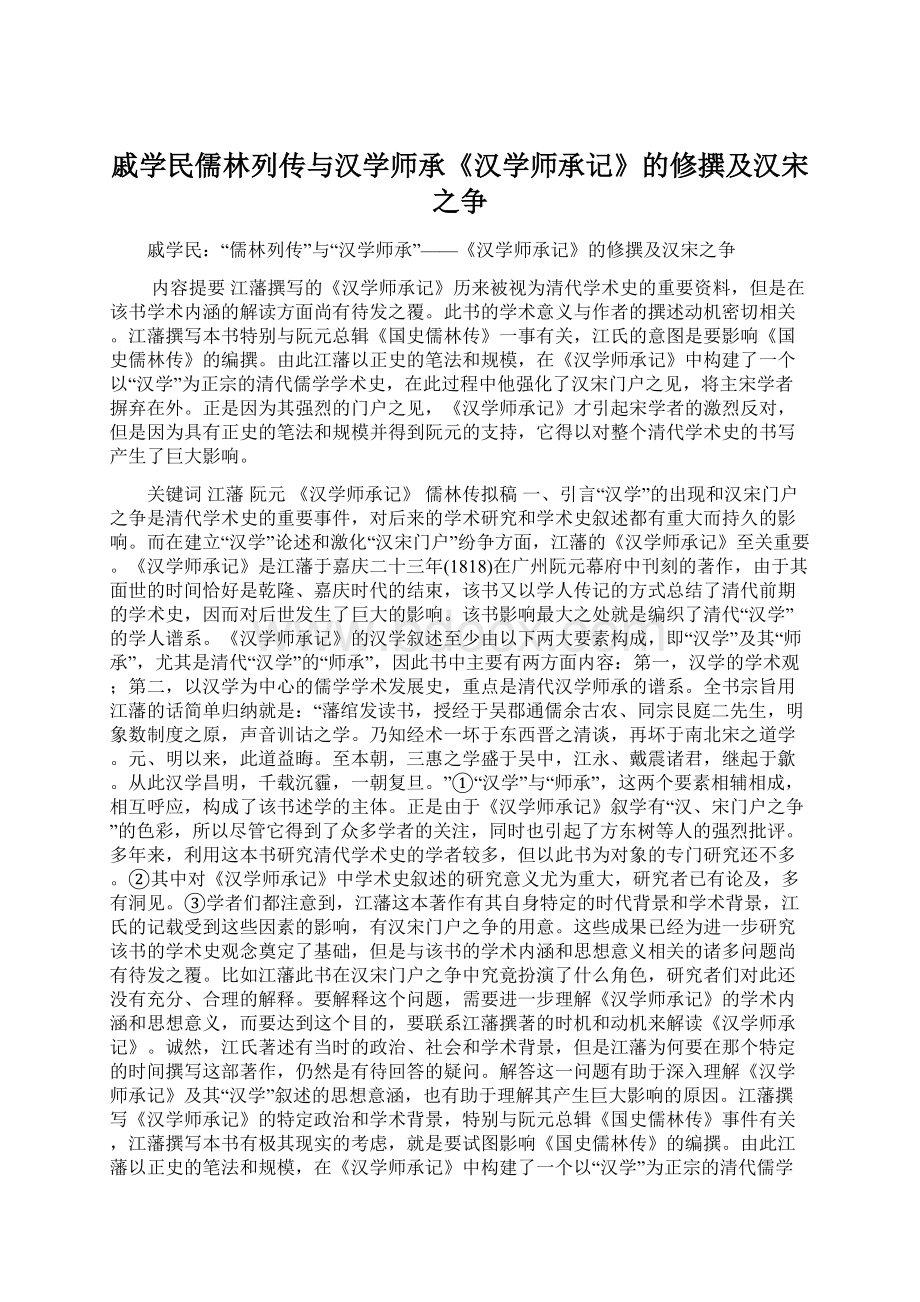
戚学民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
戚学民:
“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
内容提要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
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
江藩撰写本书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图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
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
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江藩阮元《汉学师承记》儒林传拟稿一、引言“汉学”的出现和汉宋门户之争是清代学术史的重要事件,对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史叙述都有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而在建立“汉学”论述和激化“汉宋门户”纷争方面,江藩的《汉学师承记》至关重要。
《汉学师承记》是江藩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广州阮元幕府中刊刻的著作,由于其面世的时间恰好是乾隆、嘉庆时代的结束,该书又以学人传记的方式总结了清代前期的学术史,因而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该书影响最大之处就是编织了清代“汉学”的学人谱系。
《汉学师承记》的汉学叙述至少由以下两大要素构成,即“汉学”及其“师承”,尤其是清代“汉学”的“师承”,因此书中主要有两方面内容:
第一,汉学的学术观;第二,以汉学为中心的儒学学术发展史,重点是清代汉学师承的谱系。
全书宗旨用江藩的话简单归纳就是:
“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
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
元、明以来,此道益晦。
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
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①“汉学”与“师承”,这两个要素相辅相成,相互呼应,构成了该书述学的主体。
正是由于《汉学师承记》叙学有“汉、宋门户之争”的色彩,所以尽管它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方东树等人的强烈批评。
多年来,利用这本书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者较多,但以此书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还不多。
②其中对《汉学师承记》中学术史叙述的研究意义尤为重大,研究者已有论及,多有洞见。
③学者们都注意到,江藩这本著作有其自身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江氏的记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有汉宋门户之争的用意。
这些成果已经为进一步研究该书的学术史观念奠定了基础,但是与该书的学术内涵和思想意义相关的诸多问题尚有待发之覆。
比如江藩此书在汉宋门户之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研究者们对此还没有充分、合理的解释。
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理解《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内涵和思想意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要联系江藩撰著的时机和动机来解读《汉学师承记》。
诚然,江氏著述有当时的政治、社会和学术背景,但是江藩为何要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撰写这部著作,仍然是有待回答的疑问。
解答这一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汉学师承记》及其“汉学”叙述的思想意涵,也有助于理解其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
江藩撰写《汉学师承记》的特定政治和学术背景,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事件有关,江藩撰写本书有极其现实的考虑,就是要试图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
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
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备国史之采择要明了江藩编撰《汉学师承记》的动机,④该书编撰工作的起止时间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汉学师承记》修撰的启始时间,因为缺少直接的证据,以往没有明确的意见。
而其成书时间是能够确定的,根据汪喜孙跋和《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卷末江钧《跋》所记,“家大人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的时间是“嘉庆辛未良月既望”,则该书正文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前已经成稿,至少在年底前全书已经完稿。
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版本证据,但是这一记载应是可信的。
《汉学师承记》中多处文字也可以印证这个成书时限的确切。
该书收录的人物大体是按照生年先后为序的(卷八是例外),其中大多已经去世。
而这些人物很多卒年都在嘉庆十年左右,如钱大昕逝于嘉庆九年,纪昀、王昶卒于嘉庆十一年,《汉学师承记》始撰时间当不早于此。
而洪亮吉、凌廷堪去世时间最晚。
洪氏卒于嘉庆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凌氏卒于嘉庆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汉学师承记》均记载其身后事,可证修撰时间当不早于嘉庆十五年。
至于嘉庆十六年后事,该书多无记载,如臧镛于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于北京,《汉学师承记》未见提及。
《汉学师承记》所记阮元职衔也足为修撰时间佐证。
所称阮元职衔有三处,同在卷七,两处称为侍郎,一处称为詹事府少詹事。
阮元曾多次任侍郎,但均不晚于嘉庆十六年。
关于阮元的正式记载见于《凌廷堪记》附记,内称阮元“乾隆丙午举人,乙酉进士,授编修,官至浙江巡抚,今官詹事府少詹事”。
阮元授詹事府少詹事有两次,一次在乾隆五十六年(1792),一次在嘉庆十六年,其本事见于《清史稿》本传及《雷塘庵弟子记》。
前一次显然与《汉学师承记》的写作时间不合。
后一次《雷塘庵弟子记》嘉庆十六年谱记:
“七月二十三日,阮元奉旨补授詹事府少詹事。
”这一次任詹事府少詹事的时间仅有数月,同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旨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事并见《清史稿》《清史列传》本传,《仁宗实录》,但据研究,阮元未实授礼部侍郎)。
其后阮元又逐渐得到拔擢,嘉庆十七年五月初八,奉上谕“阮元补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事务”(《仁宗实录》卷二五七“五月戊寅,以内阁学士阮元为工部右侍郎”);八月十四日,上谕“以漕运总督许兆椿为工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阮元为漕运总督”,两天后,阮元奉到此谕。
⑤因此,《汉学师承记》内称阮元“今官詹事府少詹事”,时间断限极为明确,应在嘉庆十六年底之前。
有关阮元的记载已经到了《汉学师承记》第七卷的终了,而第二年即嘉庆十七年五月,汪喜孙即看到本书并作跋,因此可以推断,该书在嘉庆十六年底就已完稿。
闵尔昌《江子屏年谱》也将《汉学师承记》系于此年。
⑥根据以上多条限制,可以推定《汉学师承记》的集中编撰应始于嘉庆十五年六月以后,而完成于嘉庆十六年底之前。
以《汉学师承记》的篇幅,在这一段时间内编辑完成是完全可能的。
为什么江藩要在嘉庆十五年至十六年间编撰《汉学师承记》,在嘉庆十六年底前完稿?
主要是因为这一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机缘,促使江藩起意编写《汉学师承记》。
这个事件就是阮元在嘉庆十五年自愿出任国史馆总辑。
嘉庆十四年九月初三日,阮元因受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而被革去浙江巡抚之职,解京发落。
阮元于九月二十三日到京,旋获嘉庆帝恩赏编修衔,在文颖馆行走,是年冬重入翰林。
此后一直到嘉庆十七年八月被皇帝任命为漕运总督为止,接近三年的时间,阮元基本留在北京。
在这段时期内,他从事了很多学术活动,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嘉庆十五年十月至嘉庆十七年)他自愿出任国史馆总辑,编辑《儒林传》和《文苑传》。
据称,此议原发于前任编修陈寿祺,但是他丁父忧去职,因此阮元自告奋勇继任。
到嘉庆十七年阮元任漕运总督离京前,《儒林传》已经纂办粗成并交付国史馆。
⑦把儒林传作为史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正史编撰的一个特色和传统。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学说。
《史记》为此单设一篇,专记儒家代表人物的活动和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的传授过程。
《史记》这一创设为后代史家所继承,《汉书》、《后汉书》等都有儒林传,此后更成为修史的一个惯例,其主要内容都是记载儒生的经术和事迹。
而《文苑传》记载的更多是文学家(不一定是儒生)的事迹,其创设的时间也较晚一些。
虽然司马迁已经在《屈原贾生列传》等传记中记载了文学家的事迹,并且后来的史家也将此作为历史记载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范晔的《后汉书》才有《文苑传》这样一个名目。
而从对国家的重要性来说,《儒林传》是要高于《文苑传》的,特别是宋代科举以经义取士之后,儒学的内涵中“经义”的地位更高。
清代学者更加尊崇儒学,对于《儒林传》的修撰历史及其意义更有自觉性。
而清初学者对此的认识往往是与对理学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黄宗羲认为:
“夫《十七史》以来,止于《儒林》。
以邹、鲁之盛,司马迁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孟子列传》而已,未尝加以道学之名也。
《儒林》亦为传经而设,此处夫不及为弟子者,犹之传孔子之弟子也。
历代因之,亦是此意。
周程诸子,道德虽盛,以视孔子,则犹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为允当。
”⑧朱彝尊也认为:
“《儒林传》者,自司马氏、班氏以来,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禹偁《东都事略》更名儒学,而以周张二程子入之。
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学》析而为两,言经术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别之为道学;又同乎洛闽者进之《道学》,异者置之《儒林》。
其意若以经术为粗,而性理为密,朱子为正学,而陆杨为歧途。
”⑨并且,清代学术的风气总体趋向崇古尊经,儒生们普遍重视经术,不仅认为经术是人才的根柢,而且认为辞章之学也应以经术为基础。
而在尊经的学者中,有一种轻视文士的风气。
因此,在当时儒生的心目中,《儒林传》的地位比《文苑传》高,并且列入国史的《儒林传》还体现了国家对某种儒学观念的正统地位的承认和对某种儒学人才的尊重。
因此,《儒林传》的编撰是涉及多方利害的大事。
所以我们看到在编辑《儒林传》的过程中,阮元曾向其姻亲和弟子们征求意见。
根据有限的资料,可知他曾向焦循、臧庸、张鉴等人征求撰写《儒林传》和《国史文苑传》的建议,或托张鉴和江西地方官员代为搜集学者遗书;另外阮元曾与其关系较为接近的官员或学者,如王念孙、朱锡庚等在北京讨论编撰问题,由此产生了一批知情者。
⑩而这些人和在国史馆任职的其他史官会将此消息透露给其他有关人。
如汪喜孙就由王念孙、焦循告知其父汪中将会被列入《儒林传》,(11)而由朱咏斋来信得知其父被列入的是《文苑传》。
(12)因此,《国史儒林传》的修撰一事在北京和扬州等地的官员及学者圈子内应有相当数量的知情者。
焦循等对《儒林传》编选原则和方法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七点意见:
“计拟七则:
一曰征实,二曰长编,三曰兼收,四曰鉴别,五曰详载,六曰公论,七曰附见。
”(13)他还提出自己眼中的《儒林传》人选,“儒林、文苑两传既分,则各隶者不宜讹杂,盖经生非不娴辞赋,文士或亦有经训,是必权其轻重,如量而授”。
(14)阮元弟子张鉴也是这样。
嘉庆十六年七月,阮元编写的《儒林传》部分稿已成,并交送其弟子张鉴校对,张校阅后提出了修撰的建议:
蒙示史馆顾、陈诸列传,伏读再四,具见审择之精,裁断之妙。
以顾作传首,而附吴、梁以下,此千古不刊定论……至来稿陈传叙事处略有未明晰者,附签上方,未知当否。
鉴谓近时如钱宫詹等作经学诸儒私传,往往取其生平、著述之书表章之。
杭堇浦之传梅定九、戴东原之传江慎修,其著也。
其实《汉书·儒林传》中赵宾说《易》,辕固治《诗》,以汤武为受命,即是此意。
吾朝学者踵顶相及,若辟青州梅勿庵之天算,顾景范、胡胐明之地理,惠松崖、万季野之经学,其他横厉一时,凌铄百代者,所在多有。
吾师表章绝学,自必取其原书,沈潜反覆,一一摭其大旨,勿仅拾取提要一二,庶几为后学者得以有所考见,尤深伫企。
(15)然而,在为公的同时,有些学人也有为私的一面,即为自己的先人或先师能列入《儒林传》而设法。
如果被列入《国史儒林传》,对于清代学人而言将是非同一般的荣誉。
因此除了编撰原则等技术问题,《儒林传》的人选很受重视。
而某些相关者特别关注自己的父祖能否入选。
臧庸就是公私兼有的立场。
一方面他积极协助寻找并向阮元提供有关人物的著述资料,“接谕,知欲览孙夏峰、汤文正书,谨奉上《洛学编》、《潜庵遗稿》二种。
闻先生近人已录张皋文矣,如卢学士(文劭)、王光禄、钱少詹事(大昕)、江叔沄、钱学原、刘端临、凌次仲、汪容夫诸君,亦得著录否?
庸未得见邵学士(晋涵)、任侍御(大椿)、孔检讨(广森)其学”。
(16)另一方面,臧庸也设法让自己的祖父臧玉林被收入《国史儒林传》。
阮元本拟将臧玉林列入《国史儒林传》(今日所见《国史儒林传拟稿》中确有《臧玉林传》,臧庸附见),但是当时存在反对意见,认为臧玉林著述乃经其子孙润色。
嘉庆十六年三月,臧庸特为此致书阮元,力辩此为谣言,力争其高祖当入《国史儒林传》:
又先高祖当入《国史儒林传》,此陈编修充纂修官时自言之,有手书可据。
《尚书集解案》亦编修由舍间索取,郎君为邮寄,意欲采其精者入列传,不幸传未成,而编修遭大故,犹幸大人续为总裁,其相知之深,有过之无不及也。
乃客冬忽述外人子孙润色之言,阁下岂为之惑耶?
此书在当时有阎徵君序,丁教授辑录遗文并见徵君于稿,在康熙丁丑。
卢学士修《常州府志》,采入《儒林传》,及校勘《经典释文》,撰入考证,在乾隆乙酉、庚戌间。
时庸年二十有三,亡弟年始十四五,谁能为润色。
且此书先为学者流传已久矣。
此必有嫉怨之士诬以不根之谈……阁下仁人君子也,孝子慈孙也,爱庸而重其先人者也。
庸之事先生终始不欺者也,抑此固千古之公论也。
先生秉笔当为一代信史,邱氏九分已虚,犹恐有一分之实,先人之书刊于子孙,即间有一二删订,亦校字者之责也,可因此疑其全体乎?
《尚书集解案》如无所用之,希发还,尊处需《经义杂记》,示之呈上。
自去冬闻命,寝食不宁,趋谒又未敢面请。
(17)汪喜孙是这种情况的另一个例证。
他也为其父汪中能被列入《儒林传》而设法,他始从焦循和王念孙处得知其父汪中被收入《儒林传》,后从史馆得知乃父被改入《文苑传》,大为焦虑,于是致信王念孙,请求其出面关说。
(18)今日阮元《国史儒林传拟稿》钞本内有《汪中传》,不过是补录。
而由《国史儒林传拟稿》中黜落的人物确有汪中。
(19)汪喜孙后多方搜集乃父资料及各方评论,辑为《汪氏学行记》刊行,与此当大有关系。
在此情况下成书的《汉学师承记》与《国史儒林传》有直接的联系,是对阮元修撰《国史儒林传》的一种形式独特的反应,以成稿的传记向阮元提出编选的学术原则和具体入传人选的建议。
首先,江藩应该较早得知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
虽然截止目前还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表明,江藩曾经被邀参与讨论《国史儒林传》的修撰,但是《汉学师承记》中的片断言辞透露他知道个中消息。
《汉学师承记》卷一自述撰述缘起说:
“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
”这里提及的“国史”,并非一般的国史,因为《汉学师承记》本身是儒者传记,与上文提及的《国史儒林传》正相合,而此一时期恰由阮元为史馆总辑,修撰清代《国史儒林传》。
(20)江藩与阮元是同乡兼同学,在阮元入仕后两人仍时有学术交往,(21)与阮元当有联系。
但是很多情况显示,他起初似乎并非阮元倚重的幕友。
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多次邀请其姊父焦循前往杭州帮忙,编撰《经籍纂诂》等重要学术著作时也没有请江藩任事。
(22)到嘉庆十七年阮元被任命为漕运总督后,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江藩很快就被聘请掌教淮安丽正书院,算是正式入阮元幕府。
其后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江藩远赴广州,阮元并拟请其协助编辑《皇清经解》,这一时期阮元似乎很看重这位老同学。
上年阮元主持辑录《儒林传》,江藩虽非其心腹,但是以他在扬州学者圈子中的崇高地位(江藩与焦循并称为二堂),很可能从其他扬州学人处得知《国史儒林传》修撰一事。
从《汉学师承记》对阮元短期任职“詹事府少詹事”的准确记载来看,江藩对阮元的动向很关注,而且消息相当准确,对阮元担任詹事府少詹事时撰修《国史儒林传》和《文苑传》一事当能知情。
扬州地处南北交通要道,除了扬州籍的学者,江藩还可能从其他学者那里得知修撰《儒林传》的消息,比如凌廷堪的弟子张其锦。
嘉庆十六年,张其锦为搜集凌廷堪的遗文,南走歙县,北走海州。
江藩在《校礼堂文集序》中记述此事道:
“《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亡友凌君次仲之文也。
次仲殁于歙,受业弟子宣城张文学襞伯,南走歙,北走海州,捃拾次仲之著述及诗古文词,编次雠校,先刊《燕乐考原》六卷。
又手写文集,渡江至淮壖,就正于阮侍郎。
”这篇文章虽然写于1812年漕运总督阮元的驻地淮安,但是扬州是凌廷堪长期客居之地,江藩又是凌氏好友,且对凌氏学问有极高评价,(23)张氏搜访凌之遗文时,极有可能会找到他,从而使江得知《儒林传》修撰的消息。
江藩如此急于在嘉庆十六年底之前编成《汉学师承记》,正是对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的回应。
具体情形为,此年秋阮元任职国史馆,主持修撰《国史儒林传》不久,江藩就从焦循或者其他扬州学者以及其他途径如张其锦等人处得知此事。
而阮元并没有直接向江藩征求意见,这就是今天在江藩的著作中没有直接与阮元讨论《国史儒林传》修撰问题的信件的原因。
没有机会像焦循那样直接向阮元进言,为修撰国史提供参考意见,对自负的江藩而言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正因为如此,像修撰《国史儒林传》这类对于所有儒生都意义重大的事情,江藩决不会由于没有得到老同学的眷顾而甘于袖手旁观,他开始独立以具体行动来参与这次撰修国史。
这就是编写一部模拟史馆笔法和具备正史规模的儒林传记,具体提出自己的编撰意见,此应即江氏所言“以备国史之采择”的含义。
这部儒林传记就是《汉学师承记》。
三、以汉学为儒学正宗《汉学师承记》和《国史儒林传拟稿》之间,在编撰原则及体例等方面存在诸多重要特征的相似或者相近之处,可以进一步佐证上述推断。
首先是在编撰体例上,《汉学师承记》和《国史儒林传拟稿》两书都是以列传集合成文,且卷首都有长篇的序论。
《汉学师承记》卷一启首是一长篇论述,少有学者注意其意义。
各代《儒林传》启首都有一篇序论,而在《国史儒林传拟稿》卷首,阮元也撰写了一篇《拟国史儒林传序》,(24)由此可以了解《汉学师承记》卷首文即相当于“序论”。
《汉学师承记》卷首语的结构也和阮元的《拟国史儒林传序》大致相似(虽然具体表述有一些差别),即首先叙述根本的儒学观念,其次叙述历朝的儒学学术史,随后转入对“国朝”儒学学术的称颂,等等,由此可见两者在各自的文字序列中执行着相似的功能。
《汉学师承记》和《拟国史儒林传稿》中的每一传记,都是辑录众书而成。
研究者已注意到《汉学师承记》博采诸家记载,但是对具体某篇传记取材的渊源尚存争议。
其中体现了江藩对传主思想和学术的认识,此为别一问题,暂且存而不论,从编撰角度而言,可以理解为江藩是在刻意模仿正史的做法。
关于辑录之法,阮元说:
“凡各儒传语,皆采之载籍,接续成文,双注各句之下,以记来历,不敢杜撰一字。
”(25)《研经室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后有阮福案语:
“家大人撰儒林正传、附传共百数十人,持汉学、宋学之平。
群书采集甚博,全是裁缀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
因馆中修史,例必有据,儒林全无案据,故百余年来,人不能措手。
”证以《儒林传拟稿》和后来的《清史稿》,可知阮福所言非虚。
《清史稿》《儒林传二》就基本是在阮元的《儒林传拟稿》基础上删改而来。
今日可见的《儒林传拟稿》正是严格按照史馆修史的成例,“裁缀集句”而成。
《汉学师承记》取材广泛,且少有自撰,也可以认为是“裁缀集句”的做法。
这方面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26)这些能够说明江藩独立编撰的《汉学师承记》是在模仿史官的笔法。
其次是两书立场相同,都极力颂扬清朝统治者。
《汉学师承记》卷一相当于序论的长篇文字,自“我世祖章皇帝握贞符,膺图篆,拨乱反正,罚罪吊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以下,不惜笔墨地缕述清朝历代皇帝刊行经解的“文治”,最终是为了颂扬“盖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
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可谓千载一时矣”!
同时该书在学者传记中也时时记载他们受统治者的褒奖或重视,比如对于阎若璩记其得到世宗的优礼。
此外,《汉学师承记》安排诸学人传记时,将清代学术的开山人物黄宗羲、顾炎武置于全书之末,江藩此举颇为人所诟病,(27)但是如果考虑到该书是竭力模仿国史,就能明白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做法。
阮元的《儒林传拟稿》也是如此,一定要说明“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
御撰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
人物列传安排的顺序,不是以黄宗羲、顾炎武为始,而是顾栋高为首,其理由是“因高宗纯皇帝谕办儒林传,奉为缘起也”。
(28)在传记取材方面,《汉学师承记》和《国史儒林传》也有共性,即材料大都来自钱大昕、王昶等曾任官职之人的著述。
阮元的做法可能来自焦循的建议,(29)但无疑也是一种政治姿态。
他辑撰的人物列传,主要依据钱大昕、王昶、万斯同等人所著传记,而对于传主的学术贡献,主要依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一做法引起其弟子张鉴委婉的批评,认为他应该多参考原著。
(30)其实,从阮元搜集材料的范围和态度来说,他不是看不到原著,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除了方便以外,更主要的是出于政治考虑。
《汉学师承记》多引钱大昕的著述,除了江藩对钱大昕学术的推崇,显然是为了使其著作更容易得到官方的认可。
这个相似的政治立场也说明《汉学师承记》是在有意模仿国史。
编辑原则和政治立场这两点相似之处可以进一步揭示“以备国史之采择”的含义,也佐证《汉学师承记》追摹国史的用心。
《汉学师承记》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汉学”立场,而《儒林传拟稿》则表面维系了汉宋折衷的学术立场。
《汉学师承记》和《儒林传拟稿》在入选人选上也有很大不同。
这两点是两书最重大的差别,而这些差异颇能说明江藩的用心,也揭示了本书的学术内涵和思想价值。
如前所述,《汉学师承记》的主要内容是儒学学术观和以汉学为中心的儒学学术发展史,重点是清代汉学师承的谱系。
“汉学”与“师承”,这两个要素是该书的主体。
联系江藩的用意可知,这不仅仅是简单为汉学者立传,而是要在《儒林传》里为“汉学”争得儒学的正统地位,并且将汉学人物列入国史。
正因此,当可理解《汉学师承记》中护教意味十分浓厚的“汉学”观念,因为批驳当时已经无势力的释老二教,正是为了表明“汉学”为血统纯正的儒学,信奉“汉学”的人物才是“醇儒”。
这是“政治正确”的一种曲折表达。
江氏的“汉学”立场,直接来自其祖师惠栋。
惠栋最鲜明的汉学表述见于其《易汉学序》:
“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火,传于汉。
汉学之亡久矣。
独诗礼二经犹存毛郑两家。
春秋为杜氏所乱。
尚书为伪孔氏所乱。
易经为王氏所乱。
杜氏虽有更定,大较同于贾服。
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
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
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矣。
故宋人赵紫芝有诗云:
辅嗣易行无汉学,元晖诗变有唐风。
盖实录也。
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闵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
天崇之际,遭乱散佚,以其口说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说》六卷。
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
栋趋庭之际,习闻余论,左右采获,成书七卷。
自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异流同源,其说略备。
呜呼!
先君子即世三年矣。
以栋之不才,何敢辄议著述?
然以四世之学,上承先汉,存什一于千百,庶后之思汉学者,犹知取证,且使吾子孙无忘旧业云。
”正是因为有存亡续绝的心理,惠栋有此门户之见,成为清代“汉学”的主将。
惠栋的汉学观念,不仅仅表示汉代学者所研究的对象,还包括他认为的汉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口耳相传的“家法”和“古训”: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
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
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
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
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守专室,呻稿简,日有省也,月有得也,岁有记也。
顾念诸儿尚幼,日久失其读,有不殖将落之忧。
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吾子孙其世传之,毋隳名家韵也。
”(31)在惠栋的其他文章中,我们能看到类似的表述。
(32)惠栋对于其自身学术的强烈信心,来自于他认为是“独得之契”的汉代易学价值的再发现。
(33)而汉代儒学的价值,就在于其真正能够经世致用。
他借用阎若璩的话来描述其心目中的儒术:
“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