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部的兴盛与扬州地域文化.docx
《花部的兴盛与扬州地域文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花部的兴盛与扬州地域文化.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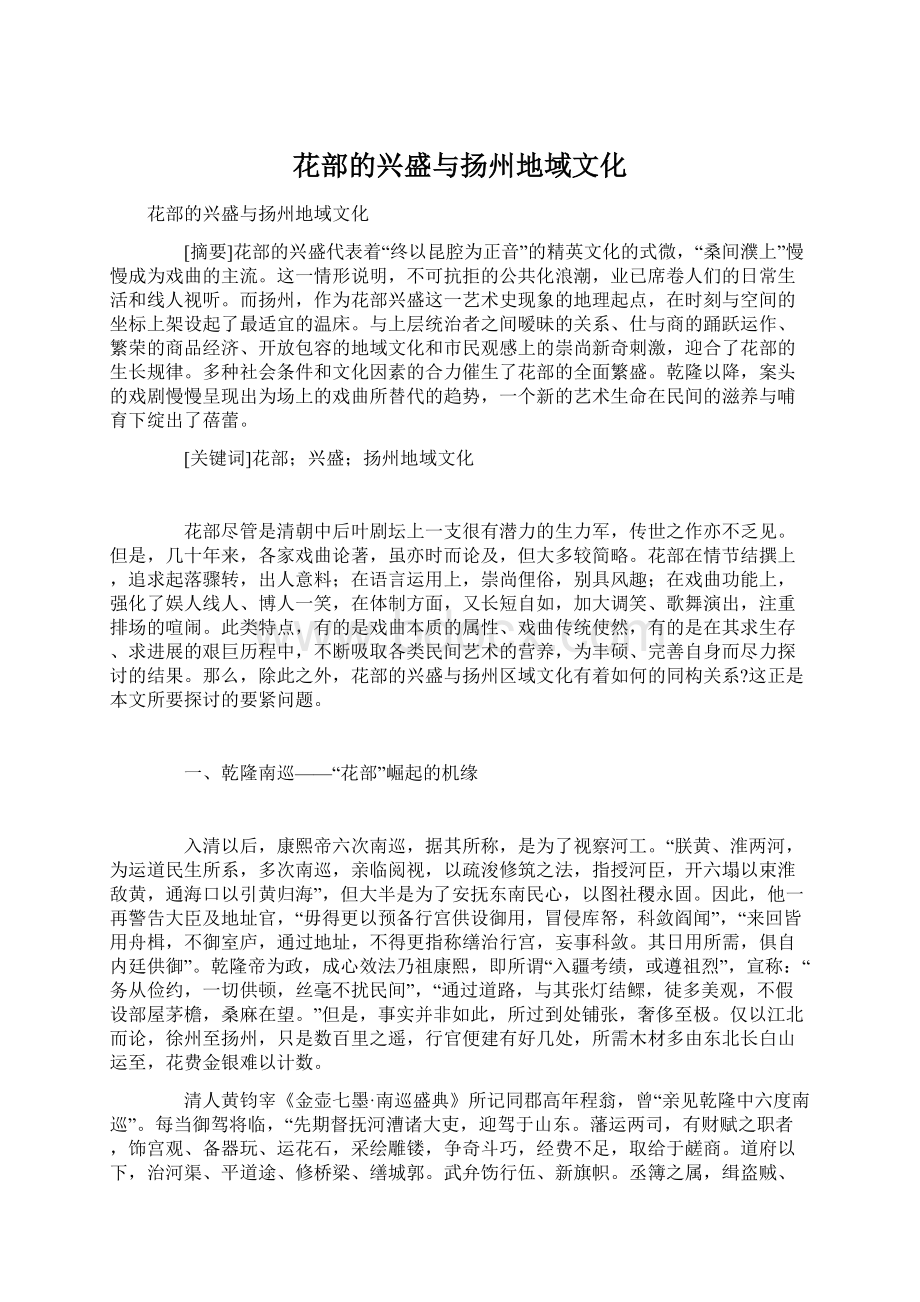
花部的兴盛与扬州地域文化
花部的兴盛与扬州地域文化
[摘要]花部的兴盛代表着“终以昆腔为正音”的精英文化的式微,“桑间濮上”慢慢成为戏曲的主流。
这一情形说明,不可抗拒的公共化浪潮,业已席卷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线人视听。
而扬州,作为花部兴盛这一艺术史现象的地理起点,在时刻与空间的坐标上架设起了最适宜的温床。
与上层统治者之间暧昧的关系、仕与商的踊跃运作、繁荣的商品经济、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和市民观感上的崇尚新奇刺激,迎合了花部的生长规律。
多种社会条件和文化因素的合力催生了花部的全面繁盛。
乾隆以降,案头的戏剧慢慢呈现出为场上的戏曲所替代的趋势,一个新的艺术生命在民间的滋养与哺育下绽出了蓓蕾。
[关键词]花部;兴盛;扬州地域文化
花部尽管是清朝中后叶剧坛上一支很有潜力的生力军,传世之作亦不乏见。
但是,几十年来,各家戏曲论著,虽亦时而论及,但大多较简略。
花部在情节结撰上,追求起落骤转,出人意料;在语言运用上,崇尚俚俗,别具风趣;在戏曲功能上,强化了娱人线人、博人一笑,在体制方面,又长短自如,加大调笑、歌舞演出,注重排场的喧闹。
此类特点,有的是戏曲本质的属性、戏曲传统使然,有的是在其求生存、求进展的艰巨历程中,不断吸取各类民间艺术的营养,为丰硕、完善自身而尽力探讨的结果。
那么,除此之外,花部的兴盛与扬州区域文化有着如何的同构关系?
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要紧问题。
一、乾隆南巡——“花部”崛起的机缘
入清以后,康熙帝六次南巡,据其所称,是为了视察河工。
“朕黄、淮两河,为运道民生所系,多次南巡,亲临阅视,以疏浚修筑之法,指授河臣,开六塌以束淮敌黄,通海口以引黄归海”,但大半是为了安抚东南民心,以图社稷永固。
因此,他一再警告大臣及地址官,“毋得更以预备行宫供设御用,冒侵库帑,科敛阎闻”,“来回皆用舟楫,不御室庐,通过地址,不得更指称缮治行宫,妄事科敛。
其日用所需,俱自内廷供御”。
乾隆帝为政,成心效法乃祖康熙,即所谓“入疆考绩,或遵祖烈”,宣称:
“务从俭约,一切供顿,丝毫不扰民间”,“通过道路,与其张灯结鳏,徒多美观,不假设部屋茅檐,桑麻在望。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过到处铺张,奢侈至极。
仅以江北而论,徐州至扬州,只是数百里之遥,行官便建有好几处,所需木材多由东北长白山运至,花费金银难以计数。
清人黄钧宰《金壶七墨·南巡盛典》所记同郡高年程翁,曾“亲见乾隆中六度南巡”。
每当御驾将临,“先期督抚河漕诸大吏,迎驾于山东。
藩运两司,有财赋之职者,饰宫观、备器玩、运花石,采绘雕镂,争奇斗巧,经费不足,取给于鹾商。
道府以下,治河渠、平道途、修桥梁、缮城郭。
武弁饬行伍、新旗帜。
丞簿之属,缉盗贼、赡穷困,以示太平。
銮辂既及河上,留从骑之半于东省,乃御舟渡河而南,于是萍翳涤道,勾芒扇芳,神人协欢,鱼鸟偕畅,那么有属车霆击,列校云驰,羽盖捎星,霓旗晃日,扈从文武,络绎河干。
罐发黎氓,红女黄童之众,匍匐瞻望,唐集而无哗。
然后苍龙负舟,赤刘夹岸,楼船先引,文鹤偕征,但见一片黄旗,安流顺发罢了。
翁又日:
‘予以年强力健,幸逢钜典,不欲遽归,同人步往扬州,以观临江之盛。
至那么固阁高敞,旌旆远张,逵途锦帷,阑阑绣幕。
文鹈云雾之绮,金蚕蓝碧之绨,步障非金谷可方,亭幔岂武夷所拟。
箫籁既发,榷歌远扬,金石铿锵,宫商缥缈,五湖四海,扳耄提孺者,莫不袂帷汗雨,山朝而海归,此第观乎道路之光景,而离宫别馆当中,固不可得而拟议也。
’”浪费无度、骄奢淫逸可见。
相传,“御舟过广陵,竟遣妇女百人为之挽纤,而每班各二十五人更番上。
故事,官吏始得入侍天颜,平民无直接近御座者,有陈词者,须经多数人传导而后达,而帝独于挽舟之妇女不然。
”乾隆帝前三次巡幸,“扬州之供给皆以缛丽受赏,后以上意耽于禅悦,乃专饰梵宇,土木大兴,又延聘名僧,研求内典,以备奏对,所费亦不资”。
赵瓯北《万寿重宁寺五十韵》就曾表达,“翠华将南来”,扬州地址仕绅为“邀天颜喜”,“于兹创兰假设,瞬息幻绀紫”,遂建成上摩云天、“飞鸟避而过”、“缁流养千指”的大寺院。
为装点倚中景物,还“垒土屹冈阜。
凿地辟沼沚”,“割峰灵鹫飞,驱石湖鼋徙。
连根移乔松,合抱植文梓”,“一木一雕镂,一砖一磨砥。
”并感慨道:
“传言庀工材,不吝费倍蓰。
宵作万枝烛,午膳千斛米。
始信钱刀力,直可役神鬼。
”听说,扬州瘦西湖上的喇嘛塔,即是为“邀天颜喜”而鸠集工匠挑灯通宵一晚上而建成。
而且,乾隆帝所到的地方,必有歌舞供奉。
这是因为,“圣意颇好剧曲,辇下名优常蒙恩召入禁中,粉墨登场,天颜有喜,假设一径宸赏,那么声价十倍”。
《礼记·缁衣第三十三》引孔子语谓:
“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
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
”因此,凡乾隆“所驻跸之地,倡优杂进,玩好毕陈”,“扬州菊部之盛,本以乾隆问为最,其由于鹾商之奢华者半,而临时设备为供奉迎驾之养者亦半”,那么道出真实消息。
地址官绅、富商明知皇帝“恒以禁制倡乐为言”,但又深知其“嗜女乐”的内幕,为了讨得皇帝欢心,曾进献“集庆班”、名伶荟萃的“四喜班”和“训练之熟,假想之奇,当世无两”的如意班人行宫演出,所演剧目有《绣户传》、《西王母献图》、《华封人三祝》、《东方朔偷桃》等多种。
其中,如意班主“所特制之剧场,能随御舟而行,其布置一切,与陆地上行宫无异,令皇上几不知有水上程”。
另一戏班之演出那么更奇,初那么一鲜红可爱之蟠桃渐近御舟,忽又上升数丈,下呈根干枝叶之形。
再那么桃落巨盘之上,“假设有人捧之献寿者”,后那么桃开两面,各垂其半,中为一剧场,男女老幼数十人演出于场上,出“寿山福海”四字,最后由一光艳女子翩跹出场,上龙舟膜拜,献酒果等物。
果然博得乾隆龙颜大悦。
其实,乾隆帝爱看戏,当是实情。
闻名文人赵翼曾在《蘑曝杂记》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谓:
“内府戏班,子弟最多,袍笏甲胄及诸装具,皆世所未有。
”他曾随驾秋季至热河行宫,亲见为庆贺乾隆帝生辰,持续演大戏十天之事,称:
“所演戏,率用《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中神仙鬼魅之类。
取其怪诞不经,无所触忌,且可凭空点缀,排引多人,离奇变诡作大观也。
戏台阔九筵,凡三层。
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乃至两厢楼亦化作人居,而跨驼舞马,那么庭中亦满焉。
有时神鬼毕集,面具千百,无一相肖者。
”乾隆二十六年,为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仅沿途所设置景物的准销银,即为七万八千余两。
并安排许多承应彩戏:
大班十一班,每班雇价二百两,计二千二百两;中班五班,每班雇价一百五十两,计银七百五十两,加上小班、杂耍、扮演彩戏的砌末添置、工饭零星费用等,竟用银达一万七千余两。
乃至“演剧设乐”、经费报销,均由皇帝亲自过问,说明乾隆喜好戏曲,由来已久,并非仅仅发生在南巡之时。
又据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载述:
“每一年坤宁宫祀灶,其正炕上设鼓板。
后先至,高庙驾到,坐炕上自击鼓板,唱《访贤》一曲。
执事官等听唱毕,即焚钱粮,驾还宫。
盖圣人偶当游戏,亦寓求贤之意。
”足见《南巡秘史》所述不虚。
乾隆既有此癖好,那时“遍地绅、商,争炫奇巧,而两淮盐商为尤甚,凡有一技一艺之长者,莫不重值延致。
”加上“南巡时须演新剧,而时已匆促,乃延名人数十辈,使撰《雷峰塔传奇》,然又恐伶人之不习也,乃即用旧曲腔拍,以取演唱之便利,假设歌者偶忘曲文,亦可因依旧曲,含混致之,不至与笛板相迕。
当御舟开行时。
二舟前导,戏台即驾于二舟之上,向御舟演唱,高宗辄顾而乐之”。
而且,“自京口启行,逦邋至杭州,途中皆有极大之剧场,日演最新之戏曲,何尝中断”。
淮扬固然更是如此。
如此众多之戏班,究竟如何治理,那么成了各类有关官吏所应考虑的问题,因此才有“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之事。
不仅如此,他们还组织文士修改戏曲。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丁酉(四十二年,公元1777),“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
历经图思阿及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
总校黄文旸、李经,分校凌廷堪、程枚、陈治、荆汝为,委员淮北分司张辅、经历查建珮、板浦场大使汤惟镜。
”黄文旸受命“修改古今词曲”。
又“兼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因得尽阅古今杂剧传奇”,遂以此为契机,撰就《曲海》(二十卷)一书。
这恰说明,戏曲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艺术样式,已开始名正言顺地为官方所认可,由初始的乱而无序的民间之状态,已堂而皇之境界人皇室贵族的殿堂,成了那时社会各阶级人物即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一起追捧的对象。
在以往,戏曲尽管也时而演出于王公贵族的宫室、厅堂,但似乎还未如此风光过。
作为封建统治者来讲,醉心于戏曲,自然是为了知足豪侈生活的需要,以求得感官上的愉悦,但在客观上却为戏曲的进展制造了便利条件,为花部这一“才露尖尖角”的艺术“小荷”,提供了展现自我、完善并丰硕自我的最正确契机。
二、仕、商运作——“花部”生存空间的拓展
地址戏以其浓重的乡土气,早就不为“文人墨客”所喜。
明代闻名散曲家陈铎,精通音律,有“乐王”之称,并曾撰有杂剧、传奇,是一个热心于通俗文学的风雅之士。
但在他眼里,流入金陵的“川戏”,只是是“把张打油篇章记念,花桑树声调攻习”,“提起东忘了西,说着张诌到李,是个不南不北乔杂剧”。
“也弄的些歪乐器”,“乱弹乱砑”、“胡捏胡吹”,加上扮相的不雅。
“礼数的跷蹊”,无非是“村浊人看了喜”,只只是“专供市井歪衣饭”。
上不得大台面,难以供奉官员府第。
“新腔旧谱欠攻习,打帮儿四散求食”,显然对地址戏很是轻视。
但是,陈铎所云,也道出地址戏的一些特点,一是“不南不北”,恰说明那时的川剧并非严守南、北曲之宫调,仅取其上口、便唱罢了。
徐渭在论及“永嘉杂剧”(即南戏)时说,“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富调,亦罕节拍,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罢了。
……间有一二叶音律,终不能够例其余。
”川戏“不南不北”何尝不是如此?
恰表现出民间艺术的特色。
其二是“村浊人看了喜”,恰说明川剧所搬演的剧作,内容活泼生动,贴合基层百姓心理,为一般民众所喜好。
至明代中后叶,随着昆山腔的流播,其阻碍愈来愈大,慢慢被尊为正声,时人目之为“时曲”。
传唱北曲者渐稀,“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今皆废弃不问,只剩弋阳腔罢了”,然“弋阳腔亦被外边俗曲乱道”,改变了其原先的声调。
这说明弋阳腔在与其他戏曲声腔的竞争、碰撞的进展进程中,不断吸取着“外边俗曲”以丰硕、充实自身。
由此可知,其声腔体系不是封锁、保守的,而是以开放的态势,不断融汇相邻艺术之长,为其自身的成长注入活力。
这或许是弋阳腔一变再变,某些唱法至今仍保留在全国许多剧种中的重要缘故。
清朝至康熙时,宫庭仍在唱弋阳腔,只是用该腔演唱的剧目,仅占十分之三,远远比不上昆山腔。
尽管如此,苏州织造员外郎李煦,为“博皇上一笑”,欲“寻得几个女小孩”。
“寻个弋阳好教习,学成送去”,说明弋阳腔在清初内廷,仍有必然的进展空间。
稍后,情形那么发生了转变。
雍正帝禁止官吏蓄养优伶,大半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
他以为,外官蓄养优伶,“非倚仗势力,扰害平民,那么送与属员乡绅,多方讨赏,乃至借此交往,夤缘生事”,故称“家有优伶,即非好官,着督抚不时访查”。
督抚假设访查不力,或故意循隐,将“从重议处”。
乡间演戏,或禁或准那么区别对待。
乾隆初年,所禁者乃充满“媒亵之词”的淫戏,“忠孝节义”、历史掌故、神仙传奇那么不在禁之列,且“凡各节令皆奏演”,并非时用演戏招待域外宾客,故“内廷内外学伶人总数超过千人”。
但对地址戏却采取压制之政策,称:
“城外戏班,除昆弋两腔,仍听其演唱外,其秦腔戏班,交步军统领五城出示禁止。
此刻本班戏子,概令改归昆弋两腔。
如不肯者,听其另谋生理。
倘有怙恶不遵者,交该衙门查拿惩处,递解还乡。
”直至嘉庆初年,“苏州钦奉谕旨给示碑”尚称:
乃近日倡有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狭邪蝶亵,即怪诞悖乱之事。
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
此等声调虽起自秦皖,而遍地辗转流传,竞相仿效。
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
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
在此前后,查禁地址戏,每每显现于各级官吏的奏折中,如两淮盐政伊龄阿于乾隆四十五年所上奏折:
查江南苏、扬地址昆班为仕宦之家所重,至于乡村镇市和上江、安庆等处,每多乱弹。
系出自上江之石牌地址,名目石牌腔。
又有山陕之秦腔,江西之弋阳腔,湖广之楚腔,江广、四川、云贵、两广、闽浙等省皆所盛行。
所演戏出,率由小说鼓词,亦间有扮演南柬、元明事涉本朝,或竞用本朝服色者,其词甚觉不经,虽属演义虚文,假设不严行禁除,那么愚顽无知之辈信以为真。
亦殊觉非是。
同年,苏州织造全德于所上奏折中亦称:
奴才前在九江时闻有秦腔、楚腔、弋阳腔、石牌腔等名目词曲,更涉不经,恐其中不无亦有违碍语句、扮演过当者,自应一概查办。
同年,直隶总督袁守侗于所上奏折中摘上谕曰:
再壹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督抚查办等语,自应如此办理。
江苏巡抚闵鹗元亦谓:
臣查曲本流传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所演剧本多数本之弹词鼓儿词占多数,较之昆腔演本,尤多怪诞不经。
其他如广东巡抚李湖、湖南巡抚刘墉、江西巡抚郝硕、继伊龄阿以后的两淮盐政图明阿,均曾于奏折中申明此意。
这一较为集中的剧作内容清查与地址戏之查禁,大致有两方面的缘故;一那么与人清以来严酷的文字狱相呼应,追查戏文中有否“关涉本朝”的“违碍的地方”。
二是地址戏运用“方言俗语”,“鄙儇粗浅”,系“乡邑随口演唱”。
“任情捏造”,“怪诞不经”,“奸淫邪道,悖伦乱常”。
“非比昆腔传奇出自文人之手”。
较存雅道。
那时,演唱秦腔的名优魏永生,至京师后不久便“名动京师,观者日至千余”,许多王公贵族、朝中贵吏,“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以致其它声腔的戏剧门前冷落,无人过问。
但是,以其所演多男女情事,娇媚调笑,“极诸亵贱”,不久,便受到查禁。
昭楗《啸亭杂录》卷八,曾描述这一情形说:
“近日有秦腔、宜黄腔、乱弹诸曲名,其词淫亵猥鄙,皆街谈巷议之语,易入市人之耳。
又其音靡靡可听。
有时能够节忧,故趋附日众。
”然终因朝廷的查禁,使花部戏在京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尽管“其调终不能止”,但毕竟受到极大限制,以致阻碍到在各地的传播。
上层统治者既喜爱戏曲,同时,又对戏曲存有戒心。
这是因为,“在任何戏剧中,都能够感觉到必然的标准和对标准的破坏”,“戏剧主人公也确实是恍如始终综合着这两种相反的激情——标准的激情和破坏标准的激情的戏剧性格”,“悲剧主人公是用最大的力量同绝对的、不可动摇的法那么进行斗争,那么,喜剧主人公一样地确实是反对社会法那么,而闹剧主人公那么是反对生理法那么”。
而且,艺术的真正本性,往往“老是包涵有改变克服一般情感的某种东西”,凸显出与现实秩序、法那么的不相谐和,何况崛起于民间的花部?
它所表现的,不是“叫人膜拜的古典世界,而是有现实人情味的世俗日常生活”。
其间有“对人情世俗的津津玩味,对荣华富贵的钦羡期望,对性的解放的企望欲求,对公案、神怪的普遍爱好,……尽管那个地址充满了小市民各类庸俗、低级、浅薄无聊,尽管这远远不及上层文人士医生艺术趣味那么高级、纯粹和优雅,但它们却是有生命活力的新生意识,是对长期封建王国和儒家正统的侵袭破坏”。
自然对封建秩序存在着潜在的要挟,统治者的下令禁止那么是意料中之事。
但是,面临诸多的政治高压,花部却兴盛于扬州。
人称:
“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讲明。
”扬州濒临长江,金陵、镇江又近在咫尺,正所谓“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自古以来即为重要的通商口岸。
至明、清,更是盐业巨子聚集之地,富豪贵吏流连之所。
人称扬州“大略有业者十之七,无业者十之三。
而业鹾务者任职不重,是以士耽乐逸,甚于他地”,竞尚豪奢之风由来已久。
“郡中城内,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扬郡着衣,尚为新样”,以时兴为荣。
且追求口腹之欲,“烹饪之技,家庖最胜”,“风味皆臻绝胜”。
“扬州盐务,竟尚奢丽,一昏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
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妻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那么更易其他类”,“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还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瞬息而散。
沿沿草树之间,不可收复。
又有三千金买尽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
这种人既有钱又清闲,自然想寻求精神的愉悦,就观众中的“大部份人而言,吸引他们到剧场来的东西中没有比想取得娱乐的欲望更强烈的”,戏剧“是从聚集观众开始”、“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
观众是戏剧存在的前提。
扬州既然是富豪贵吏聚集之地,与之相适应的效劳行业自然取得进展,市民阶级人物大为增多。
如此一来,便大大刺激了艺术市场的拓展与文化娱乐的消费。
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那时的扬州,除人们所熟知的评话、小唱及各类戏曲演出外,仅杂耍之技就有竿戏、饮剑、“壁上吹火、席上反灯”、走索、弄刀、舞盘、风车、簸米、踩高跷、飞水、摘豆、大变金钱、顶竿、摆架子、西洋镜、猴戏、肩担戏等数十种。
富商、仕绅为了装点门面,炫示财富,蓄养戏班或请优伶来唱堂会,那么是习见之事。
假设果禁戏,他们那空寂无聊的生活自然难以打发。
而且,他们占有相当多的物质财富,连皇帝对他们都另眼相看。
所谓禁戏,在他们那里全然起不到作用。
他们不仅看戏,而且还想方设法让皇帝随时随地能看上戏。
如商总江春,本为诸生,却被赏布政使衔,曾筑康山草堂,延揽名士,“奇才之士,座中尝满”,“曾奉旨借帑三十万,与千叟宴”。
乾隆帝南巡,“绅商咸推江鹤亭者为领袖,总司供奉事宜,议以女乐博天赏”,可知,江春曾直接组织女乐参与接驾之事。
据《扬州画舫录》载:
“扬州御道,自北桥始。
乾隆辛未(1751)、丁丑(1757)、壬午(1762)、乙酉(1765)、庚子(1780)、甲辰(1784),上六巡江、浙”,均曾住扬州。
正所谓“早晨解缆发秦邮,落照淮扬驻御舟”。
而且,辛未、丁丑南巡,扬城之蜀冈三峰及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田、郑、巴、余、罗、尉诸家园亭,均是乾隆帝必临幸之地。
“道旁或搭彩棚,或陈水嬉,共达呼嵩诚悃,所过皆然”。
上述各大姓,大多为业盐巨商。
这便为富贾陈献戏乐提供了方便。
新河本为运草人城便道,为迎圣驾,才数次疏浚,以直达天宁门行宫。
两岸设档布景,名其景日华祝迎恩,自高桥起,至迎恩亭止,由“淮南北三十总商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接圣驾。
所设香棚,装饰华丽,“上缀孩童,衬衣红绫袄挎,丝绦缎靴,外扮文武戏文,运机而动”,且有锣鼓、乐器伴奏。
乾隆帝尽管有些厌其喧闹,但毕竟盛情难却,倒也乐意观赏,并赋诗云:
“夹案排当实厌闹,殷勤难却众诚殚。
”那时行宫建有四处,一在金山,一在焦山,一在天宁寺,一在高曼寺。
天宁寺行官就建有戏台及御花园。
梨园子弟并佩有巡盐御史署所发的腰牌。
在南巡期间,他们凭牌出入于园亭寺观,与工商、亲友一例看承。
这那么在客观上提高了优伶的地位。
该书卷五《新城北录》下又载:
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嫠之地。
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风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
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
两淮盐务倒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
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
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
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班。
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迭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
春台为外江班。
今内江班归洪箴远,外江班隶于罗荣泰,此皆谓之内班,因此备演大戏也。
这无疑为花部的传播拓宽了途径。
商总江春,钟爱戏曲。
伶人刘亮彩以演《醉菩提》全本而得名,人江班,但“江鹤亭嫌其吃字”,后闻有“戏忠臣”之称的朱文元来投,遂“喜甚”。
江春爱名伶余维琛风度。
“令之总管老班,常与之饮及叶格戏”。
四川魏永生,“年四十来郡城投江鹤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
尝泛舟湖上,一时闻风,妓舸尽出,画桨相击,溪水乱香”。
花部既然取得官商大贾的扶植,且同昆腔一样,均被组织进“备演大戏”以迎圣驾的演出队伍,无疑大大提高了花部的声望,增进了花部的兴盛与进展。
本地乱弹勃起,“至城外邵伯、宜陵、马家桥、僧道桥、月来集、陈家集人,自集成班”,“间用元人百种”,纷纷演出。
尽管“音节、衣饰极俚”,但一样可演出于祷祀等极严肃的场合。
“迨五月昆腔散班,乱弹不散”,成心与昆腔争雄,占据演出市场,“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安庆有以二黄调来者,弋阳有以高腔来者,湖广有以罗罗腔来者,始行之城外四郡,继或于暑月人城,谓之赶火班”。
同时,为博取重利,刻印戏曲者亦不乏见,“郡中剞劂多刻诗词、戏曲为利。
近日是曲翻板数十家。
远及荒村、僻巷之星货铺,所在皆有”,这又进一步加速了戏曲传播。
由此可知,商人的运作,虽意在“博天赏”,但在客观上对花部的繁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为花部自身的完善、艺术上的精进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还拓展了它的生存空间,很值得咱们去从头凝视。
后来。
乾隆帝虽多次示意查禁花部,但关注的多是京师一方的文化市场,而对扬州却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以致当两淮盐政图明阿欲将“各类流传曲本尽行删改良呈”时,他斥之为“稍涉张惶”,“办理未免过当”,“致滋烦扰”。
这一文化政策的调整,或与其多次在扬观剧的经历有关。
三、剧坛争雄——完善自身的良机
乾隆之时,是花、雅争胜的时期。
这在多种文献中均有反映。
剧作家蒋士铨在所著《西江祝嘏·升平瑞》一剧中,叙及提线傀儡班将演出于江西南丰。
当他人问及“你们是什么腔,会几本什么戏”时,班主回答:
“昆腔、汉腔、弋阳、乱弹、广东摸鱼歌、山东姑娘腔、山西卷戏、河南锣鼓戏,连福建的鸟腔都会唱,江湖十八本,本本皆全。
”蒋氏为江西铅山人,所言或有所据。
清人徐孝常,在为“江南一秀才”张坚《梦中缘》传奇作的“序”中亦谓;“长安梨园称盛,管弦相应,远近不绝;子弟装饰,备极靡丽;台榭辉煌,观者叠股倚肩,饮食者吸鲸填壑。
而所好惟秦声啰弋,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朋然散去。
”说明花、雅之争胜,非扬州一地个别现象,已涉及全国许多地域,且昆腔已呈衰微之势。
尽管如此,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爱惜和扶植,昆山腔的正统地位,仍然没有动摇。
对花部持有成见者,不胜列举。
即以张坚而论,“为文不阿时趋尚。
试于乡,几得复失者屡屡”,乃“穷困出游”,郁郁寡欢。
但是,当有人把其所作《梦中缘》购去,“将以弋阳腔演出之”时,他却“盛怒,急索其本来归,曰:
‘吾宁糊瓿。
’”便很能说明问题。
在扬州,花部尽管被编入“备演大戏”之戏班之列,且有握有财力的盐商支持,但仍以流播于城外乡间者占多数,“本地乱弹祗行于祷祀,谓之台戏”,“音节、衣饰极俚”,仅仅“取悦于乡人罢了,终不能道官话”,因“各囿于土音乡谈,故乱弹致远不及昆腔”。
“假设郡城演唱,皆重昆腔”。
花部这一艺术新芽,生长在上有统治者排斥、下有相邻艺术形式挤压的夹缝中,究竟如何进展,倒成了它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依照有关资料来考察,花部在谋求进展上,大致做了三方面的探讨。
一是剧作题材上的翻新。
昆山腔由乾嘉至清朝中叶,传唱二百余年,上演剧目“十部传奇九相思”,陈陈相因的题材,面目相似的俗套,极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难怪他们“闻歌昆曲,辄明然散去”。
而且,才子、佳人故事毕竟与乡间百姓生活相去太远,也难以激起他们的观赏爱好。
而花部那么不然。
如《铁丘坟》(一名《打金冠》)叙薛家将事,因薛刚打死武氏私幸薛怀义所生伪太子。
被夷三族。
徐勋“自以子而易薛之子而抚育之”。
此情节“生吞《八义记》”。
此子即薛交,后长大成人,“之韩山,起义师”,“为国讨乱”。
据焦循称,“韩山者,邗上也”。
薛交起兵讨乱,实徐敬业事也。
如此错乱史实,看去似“无稽之至”,“及细究其故,那么妙味无穷”。
妙就妙在以本地土班,演述本地曾发生之事,令观众易产生认同感。
小戏《上街》中姑嫂之韵白:
“家住在维扬,两脚走忙忙。
赚些钱共米,家去过光阴”,花面上场后的自报家门:
“自家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