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和《牡丹亭》褚友翠1.docx
《汤显祖和《牡丹亭》褚友翠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汤显祖和《牡丹亭》褚友翠1.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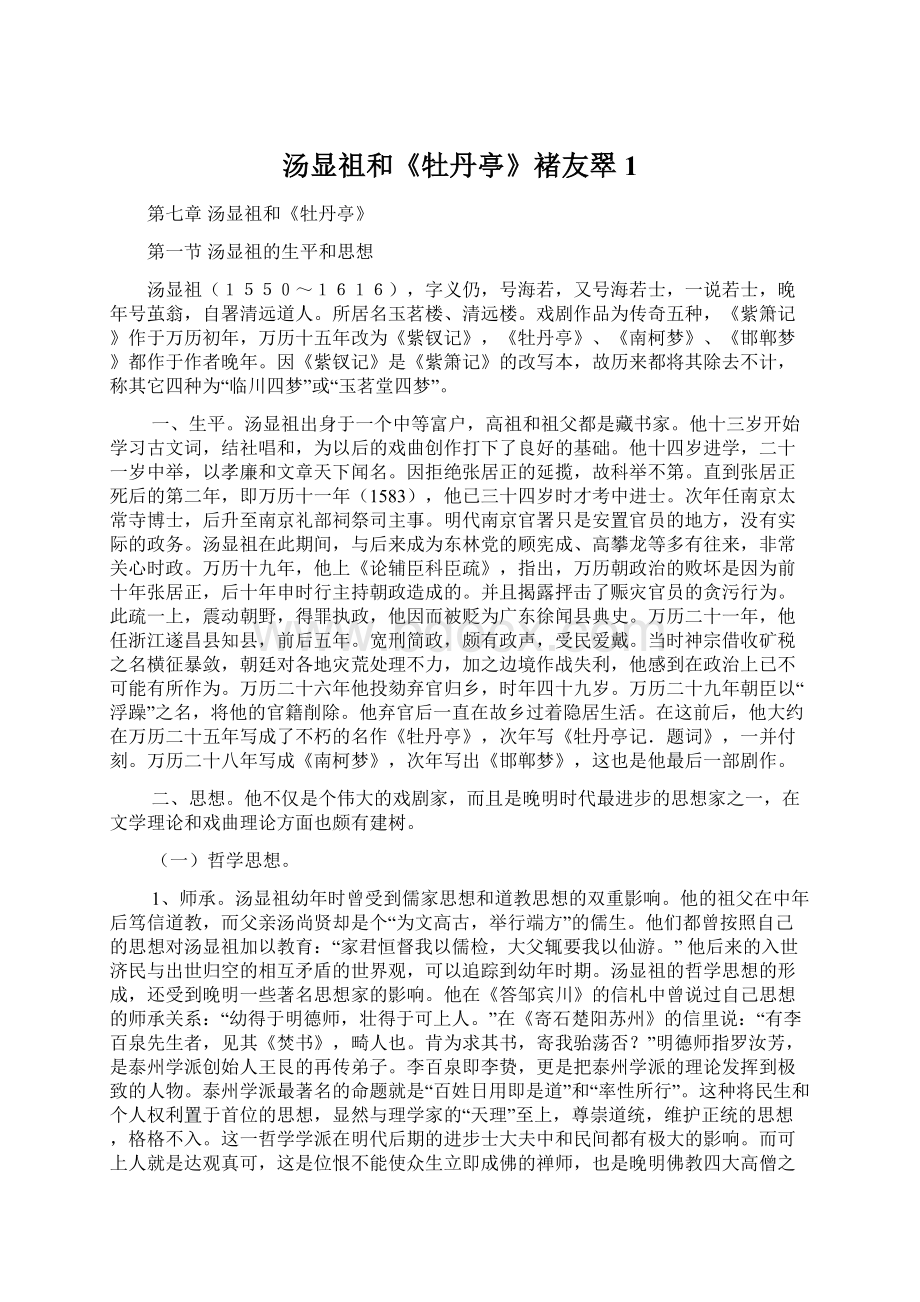
汤显祖和《牡丹亭》褚友翠1
第七章汤显祖和《牡丹亭》
第一节汤显祖的生平和思想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又号海若士,一说若士,晚年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
所居名玉茗楼、清远楼。
戏剧作品为传奇五种,《紫箫记》作于万历初年,万历十五年改为《紫钗记》,《牡丹亭》、《南柯梦》、《邯郸梦》都作于作者晚年。
因《紫钗记》是《紫箫记》的改写本,故历来都将其除去不计,称其它四种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
一、生平。
汤显祖出身于一个中等富户,高祖和祖父都是藏书家。
他十三岁开始学习古文词,结社唱和,为以后的戏曲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十四岁进学,二十一岁中举,以孝廉和文章天下闻名。
因拒绝张居正的延揽,故科举不第。
直到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他已三十四岁时才考中进士。
次年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后升至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
明代南京官署只是安置官员的地方,没有实际的政务。
汤显祖在此期间,与后来成为东林党的顾宪成、高攀龙等多有往来,非常关心时政。
万历十九年,他上《论辅臣科臣疏》,指出,万历朝政治的败坏是因为前十年张居正,后十年申时行主持朝政造成的。
并且揭露抨击了赈灾官员的贪污行为。
此疏一上,震动朝野,得罪执政,他因而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
万历二十一年,他任浙江遂昌县知县,前后五年。
宽刑简政,颇有政声,受民爱戴。
当时神宗借收矿税之名横征暴敛,朝廷对各地灾荒处理不力,加之边境作战失利,他感到在政治上已不可能有所作为。
万历二十六年他投劾弃官归乡,时年四十九岁。
万历二十九年朝臣以“浮躁”之名,将他的官籍削除。
他弃官后一直在故乡过着隐居生活。
在这前后,他大约在万历二十五年写成了不朽的名作《牡丹亭》,次年写《牡丹亭记.题词》,一并付刻。
万历二十八年写成《南柯梦》,次年写出《邯郸梦》,这也是他最后一部剧作。
二、思想。
他不仅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而且是晚明时代最进步的思想家之一,在文学理论和戏曲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
(一)哲学思想。
1、师承。
汤显祖幼年时曾受到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的双重影响。
他的祖父在中年后笃信道教,而父亲汤尚贤却是个“为文高古,举行端方”的儒生。
他们都曾按照自己的思想对汤显祖加以教育:
“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
”他后来的入世济民与出世归空的相互矛盾的世界观,可以追踪到幼年时期。
汤显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还受到晚明一些著名思想家的影响。
他在《答邹宾川》的信札中曾说过自己思想的师承关系:
“幼得于明德师,壮得于可上人。
”在《寄石楚阳苏州》的信里说:
“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
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
”明德师指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
李百泉即李贽,更是把泰州学派的理论发挥到极致的人物。
泰州学派最著名的命题就是“百姓日用即是道”和“率性所行”。
这种将民生和个人权利置于首位的思想,显然与理学家的“天理”至上,尊崇道统,维护正统的思想,格格不入。
这一哲学学派在明代后期的进步士大夫中和民间都有极大的影响。
而可上人就是达观真可,这是位恨不能使众生立即成佛的禅师,也是晚明佛教四大高僧之一。
他也是位反理学的斗士,勇于献身和无所畏惧的思想家。
他曾说过“生死关头须直过为得”。
当时有人比其说法为狮子吼。
汤显祖在南京任官的后期结识了他,深表敬慕,将其视为师友。
这些人的思想代表了那个时代思想界的最高成就,受到时人的推崇,李贽和达观甚至被时人称作“两大教主”。
总之,他们的思想有两个鲜明的倾向,一是极端重视个人内心的体验,反对权威,反对传统;二是关怀民生,重视普通人的权利。
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些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因此他们都受到当局的残酷迫害。
李贽和达观相继下狱,受迫害而死。
汤显祖的进步哲学思想受到了他们的巨大影响。
2、哲学思想。
他哲学思想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尊情反理。
情和理的含义是什么?
汤显祖显然是从两个互有联系的角度来解析情和理这一对范畴的。
一是主要从心理学角度。
他说:
“是非者理也,爱恶者情也。
”认为情与理本身并无善恶属性,是人类不同的心理活动。
理是推理判断这种理性的心理活动,来区分是非。
从根本上来讲,这种心理活动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尽量排除个人的感情倾向,不以己之好恶来确定事物的真假属性。
因此,其结果往往是符合科学的。
二是主要从伦理学角度。
陈继儒在《批点牡丹亭·题词》中曾记载了汤与他的老师张位的一段对话:
张新建相国尝语汤临川云:
“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
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矜所笑!
”临川曰:
“某与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
师讲性,某讲情。
”张公无以应。
张位认为,以汤之才学,完全可以与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并驾齐驱,成为理学大师,但现在却只知在戏子们中混日子,批评他不务正业。
而汤显祖则鲜明的提出,他与老师的区别是“师讲性,某讲情”。
这里的性的含义指的是程朱理学中的人之本性。
程颐说:
“性即理也。
”宋代理学家说的理指先验的客体精神,它支配决定着自然界和人世间的各种事物的发生发展。
而在人间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上下尊卑有序的等级和秩序,所谓“君臣父子,天道当然”。
而人之本性,正是与这种天理一致的,所以人们应“格万物,致良知”即从对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观照中,认识到这种等级和秩序的万古不移,自觉的认同并遵从。
也就是要自觉的服从三纲五常之类的道德教条,泯灭人的自由的天性。
张位正是这样要求汤显祖的。
而汤显祖则明确的提出,自己与老师不同,不讲性而讲情。
可知他是坚决站在情的一边。
这种情,与程朱理学中的理是截然对立的概念。
它不是先验的精神,而纯属一种个人内心的体验,这种体验,基于人的生理本能,“是指生命的欲望、生命活力的自然与真实状态”。
他认为这种个人体验才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绝对的,除此之外没有更高的原则。
它具有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
“噫而风飞,怒而河奔,世能厄之于彼,而不能不纵之于此。
”这种情甚至可以脱离人的肉体而激荡于世间,所谓的天理是无法限制它,人的死亡也不能使它消失,它可以永远存在。
甚至将情强调到了可以脱离现实生活的程度。
《牡丹亭》中杜丽娘生而死,死而生的过程,就是对他所谓的情的形象化体现。
他认为情与理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互不相容。
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
“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他的朋友兼老师达观批评他的观点是: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
”而他回答道:
“谛视久之,并理亦无。
”这是说,理是无足为道的,他实际上坚持了“情之所必有”的观点。
他认为“情在而理亡”,从而高举起情的大旗。
在明代,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连科举考试都只能以“四书”“五经”作为法定教材,封建礼教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将情与理对立起来,极度尊情的主张,实际上具有极大的个性解放的意义,其历史进步性是无庸置疑的。
他将情分为真情和矫情,肯定真情。
他认为,“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
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
固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
”真情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是一种天性,所以它的极致应与宇宙的本原是一体;而真情的极致同样可以不通过语言来表达,但是,语言作为媒介,必定会将真情或显或隐的表现出来,无论圣贤还是英雄,都不可能没有真情。
然而,即便是真情,他也有所分析,区别看待。
他在《复甘义麓书》中说:
“性无善无恶,情有之。
”此处所说的性,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人性,这种人性是无所谓善恶的,完全由后天的环境和教育决定。
而情则可分成善情与恶情两种。
问题是既然情分善恶,那么首先就得有个标准,以此来衡量其善恶属性。
标准是由个人来确定的,凭什么某个人确定的标准要让别人遵从?
既然情是个体的欲望和追求,它并不是科学的结论,可以经过严格检验,而情绪体验的结果肯定会因人而异,每个人的欲望和追求都不会相同。
并且,个人欲望追求的满足实现往往要以牺牲别人为代价。
这样,为情确定善恶的标准就难乎其难了。
那么如何确定何者为善情,何者为恶情呢?
汤显祖用的是有利于人的正常生存成长的标准,即他自己所说的“贵生”。
他说:
“天地之性人为贵”,“大人之学,起于知生。
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
”这是重视人的生命的价值的认识。
他认为生存权是最重要的。
由此,他又引申出每个人都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进而为社会作出贡献。
“人生大患,莫急于有生而无食,尤莫急于有才士而蒙世难。
”这倒有点类似马斯洛的人生需求层次说了。
总之,善情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人生观,首先有利于人的生存成长,进而有利于社会公众。
可见他所说的情并非是个体欲望的无限膨胀,可以不惜一切,不管他人的利益和他人的存在,一意孤行。
个人之情的抒发和表现,必须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社会的伦理要求。
他据此要求统治者“能为天地大生、广生。
”即要爱民。
这可看出儒家仁者爱人和民为重说以及佛教慈悲重生说的影响,故道德伦理的色彩很浓。
如此,这种情才可以称为是善情。
而恶情则是不利于人的正常生存成长的和社会健康有序的人生观。
如放纵和贪图酒色财气,以及在官场中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等。
正因为他确定的善情与恶情的标准是以公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因此,可以很容易的被人们所认可接受。
矫情也可分为两种。
假情是矫饰的,虚伪的感情。
它并非是人的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而是为了某种现实功利的目的,伪装出来的情绪。
例如他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评价当时的士大夫,“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行俯立,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
”这显然是针对当时那些貌似彬彬有礼的伪道学家而言的。
这种感情,显然是他所不屑一顾的。
宗教感情虽然也是经过修饰的感情,但对此他并不持否定态度。
他早年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
他早年在乡试秋举的那一年,坠簪于抚州(今南昌)云峰寺的莲池,写诗曰:
“虽为头上物,终是水云心。
”若干年后,达观游寺见到后,大加赞赏,并因此才与汤结成亦师亦友的关系。
汤后来受其影响非常之大。
万历二十六年冬《牡丹亭》付刻后,达观与汤显祖在临川相遇,两人围绕着情与理的关系有一场激烈的辩论。
他的观点是:
“理明则情消,情消则性复,性复则奇男子能事毕矣!
”当然,达观强调的理是佛理,性指的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佛性。
虽说与程朱的性理并非一体,但是认为理高于人出自本能欲望的情,则是一致的。
当时汤显祖并未被说服,但是,这种观点却对晚年的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深了他的出世思想。
他在《江中见月怀达公》一诗中写道:
“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
”情到了极致时,反而消失了,所达到的是无欲无望,四大皆空的佛教境界。
显然他已经在宗教中寻找情的最终归宿了。
这种出世思想在他后来写的《邯郸梦》和《南柯梦》中可以明显看出。
由于晚明时代,佛教禅宗盛极一时,禅宗中特别强调“明心见性”,“我心即佛”,认为人心向佛完全由每个人自己的愿望和修持决定的,不必通过偶像崇拜,甚至呵祖骂佛成为时尚。
这样,禅宗与崇尚天理的理学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所以汤显祖的皈依佛教不能看作是与礼教的妥协,而应看作是由于他“情”与禅宗强调个人精神自由方面本身就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才会产生的行为。
(二)政治思想。
他的政治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有着统一之处。
他将尊情反理和为天地大生贵生的原则贯穿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之中,主张仁民爱物,认为做官的人必须能为人民办事,“不要钱,不怕死”,“因百姓所欲去留”。
所以无论是评论时政,还是从事政务,都能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甚至有时打破一些僵硬的规定。
不是事事从法律出发,而是从人之常情出发。
他在浙江西南部贫困山区遂昌当知县时,曾在除夕放囚犯回家过年,正月十五放囚犯上街观灯。
他对朋友赵仲一没收土豪数千顷地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的事赞不绝口。
虽然他的政治思想还没有达到人人平等的高度,还不能摆脱尊卑有序的传统伦理观,但其中已有了免除贫困和人压迫人的因素,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羞富贵而尊贫贱,悦皋壤而愁观阙”。
他的政治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理想,这是很可贵的。
(三)文艺思想。
汤显祖把自己哲学思想中对于情的极端重视,应用于文学实践中,强调了情在文学中至高无上的作用。
他说: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
”认为情是人世间的事物的原动力,而诗歌应表现这种情。
诗歌是缘情而生的,其能否被读者认可,取决于是否有神。
情是诗歌的原动力,属于诗歌有没有,能不能产生的问题,当然是第一位的;而神指神韵,这是诗艺的范畴,解决诗歌好不好的问题,当然其重要性比不上情了。
一切文学作品,也都与诗歌一样,是因情而生的。
在具体创作中,汤显祖的重情论变而为灵气论。
因为只有情,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但却不一定可以成为文学家,而文学家还需要很好的文学创作才能“灵气”,以及“尚奇”的艺术追求。
他认为,灵气与尚奇是互为因果的。
“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
怪怪奇奇,莫可名状。
非物寻常得以合之。
”只要有了这种灵气,自然就会在头脑中形成各种前所未有的形象,形成独特的艺术世界。
而另一方面,对于艺术的独特性的追求也有其独立的意义,有了这种追求,也可以促使灵气的生成。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
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
”这里侧重强调作家追求新奇的意愿,认为只有主动的追求独特的艺术世界,摆脱各种陈陈相因观念的束缚,才会有灵气,才可以真正自由的驰骋想象,上天下地,无所不至,无所不能。
这种灵气不管多么奇诞,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即这种灵气是来自于文学家的发自内心的真情。
它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而与经验、学识及规则等外在的的约束是没有关系的,也不可以常理来要求它。
在灵气与尚奇之间,汤显祖更重视的显然是灵气。
这种灵气并不神秘,他说:
“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
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
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
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
”这可以看作是他对灵气构成因素的阐说。
灵气是由意念、情趣、神气和形象组成的,他特别重视四者的协同作用,即必须是四者之间构成了协调一致的关系,才可能写出具有艺术独创性的好的文学作品。
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没有提到学理规则等后天形成的理论认识。
在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汤显祖主张内容是第一位的,内容决定形式,而不能为了追求所谓完美的形式,以文害意。
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吴江派的沈璟有过非常激烈的论战。
沈璟立论的出发点是“合律依腔”。
即作品的音乐形式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他显然是针对汤显祖,在《博笑记》所附的《词隐先生论曲》的[二郎神]套数中写道:
“何元朗,一言儿启词宗室宝藏。
道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
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
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
”汤显祖对这种观点持激烈的反对态度。
沈璟的信徒吕天成在《曲品》中曾记载了汤显祖与沈璟二人的一场激烈的争论。
“乃光丞(沈璟曾官光禄寺丞)尝曰‘宁律协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
’奉常(即太常,汤显祖曾官南京太常寺博士)闻之,曰:
‘彼恶知曲意哉!
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
’此可以观两贤之志趣矣!
”汤显祖在《与宜伶罗章二》这封书信中说,“《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
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
”对吴江派诸人为了追求舞台演出的效果而改动自己的作品表示出极大的反感,认为这种篡改实际上是阉割了自已作品的内容。
他坚决主张,在剧本的文学语言与音乐语言发生冲突时,音乐语言应为文学语言让路。
这里因为,文学语言体现的是作者真实的感情,而音乐语言体现的不过是一种人为的规则。
表面上看来,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文字语言为先还是音乐语言为主,但归根到底,这还是反映了戏剧理念中的内容与形式之争。
沈璟理论看来是要求依腔合韵,可以不顾文字,认为文字语言形式不如音乐语言形式重要,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应舍弃语言形式而保留音乐形式。
言为心声,而音同样是心声。
这看起来好像是用一种形式反对另一种形式。
但实际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因为沈璟所说的律腔,并非是作曲家创作的音乐。
在这种音乐中,作曲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感情形成其自己独特的音乐语汇。
而他所说的律腔,都是前人传下来的已经固定化程式化的宫调。
剧作家的合辙依韵,对其感情的抒发有规范制约的作用。
而相对这种音乐语言来说,文字语言的束缚作用显然要小得多。
文字总要自己写出,不可能像已程式化的音乐那样完全利用现成的模式,只要循规蹈矩就行。
所以两者相较而言,文字语言显然能够更多的与内容取得沟通。
这样,他的音乐语言的重要性高于文字语言,骨子里就是形式至上,只不过有点儿变形而已。
正因如此,他对剧本的形式因曲谱、句法、平仄、阳阳、用韵都特别考究。
形式的因素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位的,就这一点来说,他是个地地道的形式主义者。
当然,如果单就戏曲形式本身来看,他的这种理论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为传奇当时有另一种重形式的骈偶典雅,文辞华美,句意艰深,甚至句句有对,难以听懂。
这就脱离了戏曲艺术的根本要求,使戏曲严重脱离舞台实践,影响到其演出。
但他所说的宁合腔而不惜害文,亦即害义,则把合乎戏曲音乐形式提高到不恰当的高度了。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把这种理论与他的理学家思想结合起来考查,就不难看出这也曲折地反映了“理”在戏曲创作中的应用。
即戏曲也同任何事物一样,受着其天理,即先验存在某种模式的制约。
理学家是不会让任何事物没有规矩的。
由此看来,双方围绕着文字语言和音乐语言何者为先的论战,实质上就是内容与形式何者为重之争。
戏剧的本色当行是临川与吴江争论的又一个焦点。
双方或自我标榜,或受他人推崇,皆称“本色当行”。
陈继儒在《批点牡丹亭·题词》中说:
“独汤临川最称当行本色。
”而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也认为:
“汤显祖的戏剧语言,继承有元剧语言本色的传统。
”而《词隐(沈璟号)先生手札二通》里,沈璟也提出了自己“僻好本色”。
两人都号称本色当行,是否没有区别呢?
在元代,戏曲有所谓本色派与案头派之分。
本色与当行是一个意思,都指语言自然朴素,适合舞台演出。
但是细加辨析,则可以发现,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本色侧重于语言,指语言自然,不矫揉做作,不刻意雕饰;而当行则指符合戏剧本身特点,即要直接面对观众,能够吸引他们,从而取得良好的舞台演出效果。
这个问题在元人那里不是问题,因为只要做到了一点,另一点也就有了。
但是到了明代,这个问题就凸现出来。
戏剧家片面追求某个方面,对戏曲的创作和演出已经发生了影响,这就迫使戏曲理论家不得不辨析两者的涵义,注意到两者的异同及其关系。
如吕天成《曲品》中说:
“殊不知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
”虽然两者之间互有重合,但毕竟不能等同。
可见这个问题当时所受到的关注,已经到了非弄清不可的地步了。
这样,临川与吴江在本色当行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陈继儒所说的汤显祖的当行本色,并非是就其本义而用的,指的只是真诚地道的感情流露而已。
因此,如果就语言和剧情而论,他的剧作更应放在以表现个人情绪和追求华美语言为长的案头派的作品中,与人们公认的本色派戏剧杰作如关汉卿等的作品的风格,大相径庭。
他的剧本,确实不是为舞台演出而写的,这从他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和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的嗓子的说法中,都可得到证实。
为了表达他所说的真情,他并不在乎语言规范和戏剧规律的种种限制。
王骥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故在《曲律·杂论》中说:
“《紫箫》、《紫钗》,第修藻艳;语多琐屑,不成篇章。
”而在其代表作《牡丹亭》中,其运用华美语言的能力,已经完全成熟。
他对语言的雕琢并不是以舞台为中心来考虑的,而是以能否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理念与情绪为准的。
他过分地强调真情的至高无上,反对用任何形式加以限制,所以只要与其情合拍,他便会对语言本色的要求置之不顾。
而沈璟的观点,倒是更接近本色论。
但是要注意的是:
首先,他所说的本色更偏指对民间俚俗语言的利用,使作品语言的通俗易懂方面。
其次,他的本色不是像元杂剧的本色派和早期南戏那样,要求贴近民众,即一切从舞台演出的效果出发,以期当行;而是理论上的本色。
他先是根据自己对本色的理解,弄出一套创作的模式,然后再用这种理论指导自己的创作。
而也就到此为止,缺乏实践检验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所以他的本色未必当行,在语言和戏剧结构上,也许都中规中矩,自然本色,但是舞台演出的效果上,则成就不高。
当然,他的戏曲理论在从后期南戏以来南曲系统的典雅化,骈俪化,而越来越脱离舞台实践的倾向来说,自有其积极意义。
故在戏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因此在当时以至清代都有人推重他。
第二节《牡丹亭》
这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戏剧中又一部伟大的作品。
又名《还魂记》。
他本人也为此自豪:
“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
当时就有“家传个颂,几令西厢减价”的说法,与西厢记同被誉为古代戏剧中爱情题材的最高典范,曾打动了一代以一代青年男女的心灵。
一、故事来源和梗概。
它的故事来源于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明末刊本《重刻增补燕居笔记》里收入。
据作者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
“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
予稍为更而演之。
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
”所谓“传杜太守事”的说法,证明当时民间已流行这个话本了。
他所说的李仲文与冯孝将儿女事,分别见于陶潜《搜神后记》和刘敬叔《异苑》;而收考谈生事,载于干宝《搜神记》。
他认为民间话本的来源是这几处。
作品的主要情节虽然源于话本,但作者充实了很多新的内容。
剧作的梗概是,南宋福建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因梦中与少年书生柳梦梅幽会结合,此后为相思所苦,终于一病而亡。
三年后,书生柳梦梅前去都城临安应试,经过杜丽娘坟茔,拾到杜丽娘临终前的自绘象,一见钟情。
他在其旁的屋舍中夜宿,杜的鬼魂出来和他相会。
他挖开坟墓,杜丽娘终得再生,二人结为夫妇,一起前往临安。
可是升任为宰相的杜宝坚决反对他们的结合。
杜丽娘不改初衷。
柳梦梅考中状元,由皇帝作主赐婚,杜宝才认可了这门亲事,与女儿女婿重归于好。
二、主题和意义
(一)作品的主题。
作者以人鬼幻化的浪漫过程表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
虽说从情节上看,杜丽娘缺乏一个贯穿始终的对立面,因此全剧没有形成集中的戏剧冲突,但是戏剧冲突仍然存在。
这就是以杜宝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势力与以杜丽娘为代表的争取爱情自由的力量之间的斗争。
杜宝等长辈要求杜丽娘一丝不苟地按封建礼教行事,强烈压制她的青春意识,以至于她忧闷而死。
杜丽娘为了复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虽说斗争的对象不再是父亲,但是仍属与封建礼教的斗争。
而杜宝在杜丽娘复生后,仍然从封建礼教的立场出发,固执地封杀其自由生活的权力,不认女儿女婿,强迫他们分开。
而杜丽娘则要冲破封建牢笼,争取自由,死后仍不放弃反抗,因爱而生。
生后不顾父亲残暴的压迫,甚至上朝亲自与其斗争。
作者通过描写这场生死冲突和杜丽娘的奇特遭遇,批判了封建礼教的残酷和不合理,歌颂了青年一代争取自由恋爱理想婚姻,反抗礼教的不屈不挠的斗志,赞扬了他们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
这个主题与《西厢记》很类似,但在表现上比《西厢记》感情更为强烈,更有时代特色。
(二)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时代精神
1、作者以反封建礼教作为创作目的,把戏剧冲突提炼到情与理对立的高度,用情与理的冲突贯穿全剧。
情在作品中表理为杜丽娘对柳梦梅的爱情,理则是主流社会对杜丽娘爱情的扼杀,其内核是程朱理学。
“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作者正是通过杜丽娘与杜宝、甄夫人和陈最良等封建正统势力的矛盾冲突,用杜丽娘这一形象包含的全部艺术魅力,表达了情与理之间不可调合的矛盾冲突。
同时,作者的扬情抑理,尊情反理,表现了他情高于理,情胜于理的理想。
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都显得异常的自觉。
可见作者将杜丽娘这个人物作为了情的化身,用她与理对抗。
情之所以不能伸张是由于理的压抑,而情大于理,甚至可以超越生死界限,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战胜的。
他已经将情的作用神化了,可以说将情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极度尊情的主张,是晚明社会上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这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不顾一切的热情,就像狂风巨浪一样,具有摧垮封建伦理堤防的强大力量。
作品的完满结局,则是情能战胜一切理的象征。
2、作品用情与理的冲突和尊情抑理的主张,表现明代社会生活中传统观念与新生思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
这是当时市民社会的萌芽和封建社会的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再现。
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