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docx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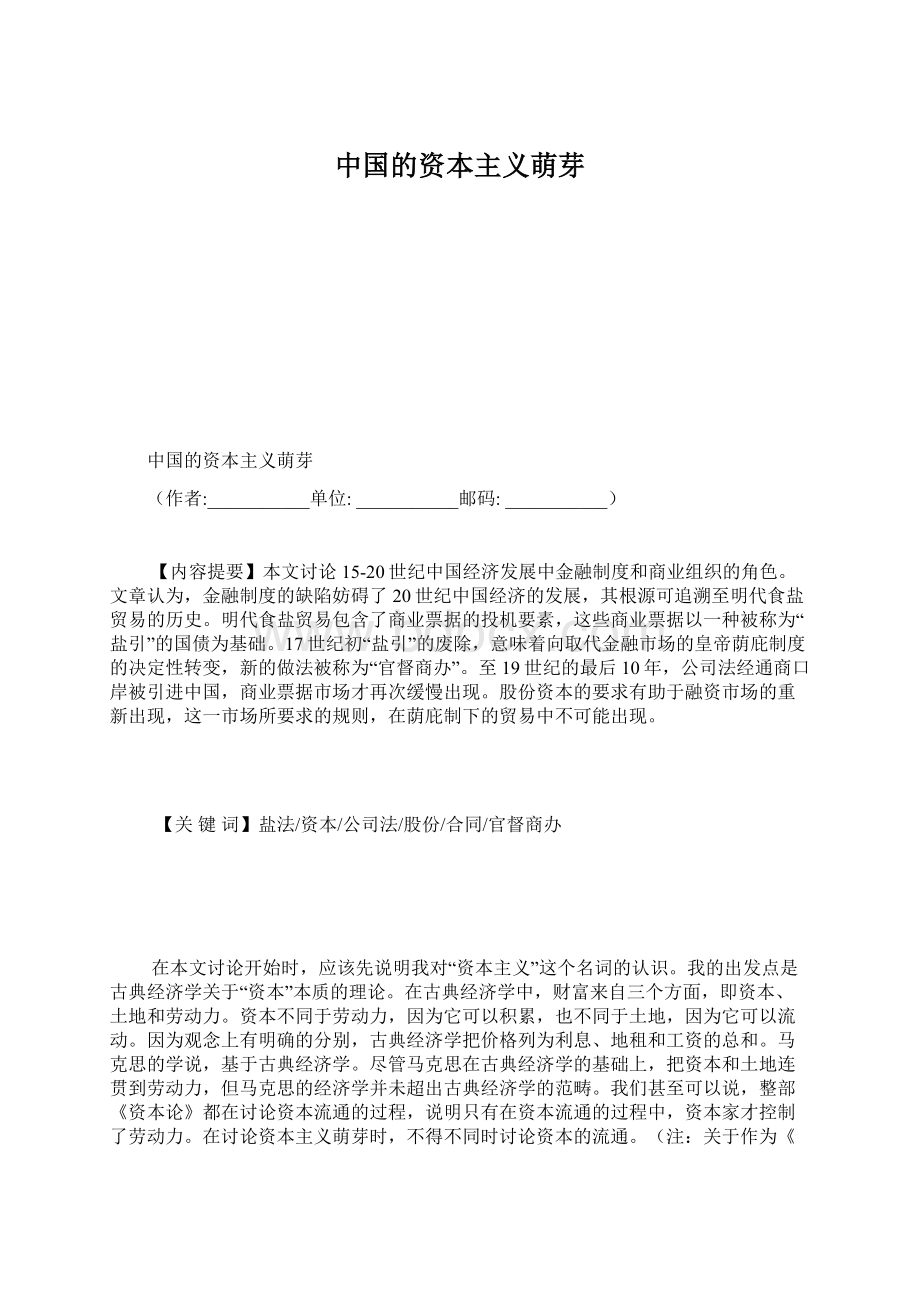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作者:
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码:
___________)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15-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中金融制度和商业组织的角色。
文章认为,金融制度的缺陷妨碍了20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根源可追溯至明代食盐贸易的历史。
明代食盐贸易包含了商业票据的投机要素,这些商业票据以一种被称为“盐引”的国债为基础。
17世纪初“盐引”的废除,意味着向取代金融市场的皇帝荫庇制度的决定性转变,新的做法被称为“官督商办”。
至19世纪的最后10年,公司法经通商口岸被引进中国,商业票据市场才再次缓慢出现。
股份资本的要求有助于融资市场的重新出现,这一市场所要求的规则,在荫庇制下的贸易中不可能出现。
【关键词】盐法/资本/公司法/股份/合同/官督商办
在本文讨论开始时,应该先说明我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认识。
我的出发点是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本质的理论。
在古典经济学中,财富来自三个方面,即资本、土地和劳动力。
资本不同于劳动力,因为它可以积累,也不同于土地,因为它可以流动。
因为观念上有明确的分别,古典经济学把价格列为利息、地租和工资的总和。
马克思的学说,基于古典经济学。
尽管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把资本和土地连贯到劳动力,但马克思的经济学并未超出古典经济学的范畴。
我们甚至可以说,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的过程,说明只有在资本流通的过程中,资本家才控制了劳动力。
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时,不得不同时讨论资本的流通。
(注:
关于作为《资本论》背景的这一古典经济学解释,参见LouisDumont,fromMandevilletoMarx,theGenesisandTriumphofEconomicIdeology,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7.)
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说明资本为什么可以流通。
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说,资本是在以贸易为主体的交换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因为贸易伴随着劳动分工而产生,所以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顺着这一思路,从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考察历史,就会以为,除非遇到人为的阻滞,贸易一定会自然地增长,工业也必定随之而来。
这一论点在本世纪初遭到韦伯(MaxWeber)和朴兰易(KarlPloanyi)的挑战,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说相反,他们认为,不均等的优势(unequaladvantages)并不自然地导致贸易产生,因为贸易只有在适当的制度出现以后,才能进行。
他们所讲的制度就是结算信用(settlementofobligations)的办法,例如货币(特别是纸币)、会计、法律,以及马克思自己也注意到的银行。
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笔下,我们看到了历史上这些使商业得以发展的制度产生的大致情形。
(注:
MaxWeber,EconomyandSociety,anOutlineofInterpretiveSociology,Berkeley: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riginsofOurTime,Boston:
BeaconPress,1957;FernandBraudel,CivilizationandCapitalism15th-18thCentury,transl.bySianReynolds,London:
Collins,1981.)
这些商业制度也溢注到政府和社群之中。
如果这些可以导致资本流通的制度被描述为带有资本性(capitalist)的话,那么,也有理由用同样的词语来描述接受了这些制度的社会。
若将资本主义(capitalism)视为一种理想范式(ideal),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接受这一范式的社会,带有资本性的制度就是使这一理想范式成为可能的制度。
这不是说,社会必然受什么统一的规律所支配——实际上,有哪个社会只是受到一个标准支配的?
事实上,韦伯社会学的基本点就在于,社会制度并不总是相得益彰的,而正是在社会制度发生冲突之时,结构才开始变化。
中国并不需要向西方学习有关贸易的价值。
当19世纪上半期西方前来敲击大门之时,留心国计的中国官员都充分认识到贸易为“互通有无”所必需。
商人活动活跃,钱币通常都被放贷生息,中国文献也常常表达“利从本出”的思想。
占统治地位的是农本思想,即使如此,19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思想中,正很快地发现市场的重要性。
这一发现的后果之一,就是最终导致了引发鸦片战争的重银主义(bullonism)的信念。
(注:
关于市场独立性,以及银价与鸦片出口间的关联的认识,可参见包世臣:
《庚辰杂俎》,见赵靖、易梦虹编: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北京:
新华出版社1982年,上册,第3-13页。
有关包世臣结交的高级官僚的政治及其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关系,可参见JamesM.Polachek,TheInnerOpiumWar,Camb.Mass:
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HarvardUniversity,1992.)战后不久的1853年,当咸丰皇帝准备让钱币贬值时,户部侍郎王茂荫已上奏警告说,尽管朝廷有权力和办法降低币值,但却没有同样的权力与办法防止百姓抬高物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同样的结论,并在一个注脚中提到王茂荫。
然而,少数官员偶尔表露的对市场独立性的认识,并未扭转王朝的抑商倾向,清政府仍然拒绝承认开放海外贸易的必要,并贬低商业活动。
王茂荫因为提议发行完全可兑换纸币,而受到朝廷的斥责,在朝廷看来,这样做保护的是商人,而不是国家的利益。
(注:
KarlMarx,Capital,ACriticalAnalysisofCapitalistProductions,London:
WilliamGlaisherLtd.,1920,p.103n.1;吴晗:
《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史辑刊》1937年。
)19世纪中国的落后,我们又可以归咎于这个拒绝从商人的观点去看待市场的强有力的王朝。
(注:
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参见韩大成: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02页。
)
可惜,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办法,可以把中国的经济落后归结于政府统治。
18世纪以及更早以前的中国,政府也同样地实行高压统治,但是为什么前几个世纪的经济是繁荣的,而19世纪以后是没落的。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就是被设计出来回应这一问题的。
(注:
“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最重要的论文,收录于尚钺:
《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其续编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6年;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60年。
)把早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说成是“萌芽”的想法,既重视中华帝国的富庶,又同时强调19世纪工业化的失败。
这种观点认为,最终在西方引致实现资本主义的制度,尽管明清时代在中国也显露过,但它们没有能象在西方一样开花结果。
由此引申出来,亦有论者认为,如果中国的历史进程不被西方人侵打断的话,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也可以把中国带入机器时代。
(注:
关于对尚钺观点的意识形态性的批评,可参见刘大年:
《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
)
明代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但是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并不在于某些论者所认为的源于手工业的发展和雇佣劳动较以前普遍。
明朝皇帝散发着专制君主的独裁气息。
(注:
关于明朝皇帝作风的出色描述,可参见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但在明代,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官僚体制的出现,长时间的和平,引人瞩目的思想自由的风气,先是来自日本、后又来自欧洲的白银的大量流入,以及令人注目的经济繁荣,这种繁荣不仅表现在生产丝织品和陶瓷的城市,而且也出现于拥有商品性农业和新世界高产作物支持的乡村地区。
没有疑问,明代的作坊主使用雇佣劳动,但是,认为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就远远离开了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原则相联系的图象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描述的核心。
以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萌芽象征的历史学家必须回答,劳动力的雇佣是如何反映出资本经营的方式的,手工作坊的背景下资本是如何流通的,一个作坊主能够雇佣多少工人?
如果说雇佣劳动的存在都会创造出早期资本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发现,从古代的战国时期就存在着这种方式。
(注:
傅筑夫:
《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傅筑夫:
《中国经济史论丛》,北京:
三联书店1980年,第669-708页。
)然而,从这个出发点来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再不需要问初期资本主义是否曾经在中国存在,而是要问,如果这些制度2000年里都保持不变的话,那为什么它们没有延续更长的时间。
我认为,在明清的作坊中寻找早期资本主义的论著,混淆了作坊(workshop)与工厂(factory)的界线。
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引致资本主义的原因。
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变而来,而是19世纪上半期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
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佣劳动,还把会计的方法用于生产的管理。
(注:
SidneyPollard,TheGenesisofModernManagement,AStudyoftheIndustrialRevolutioninGeratBritain,Harmondsworth:
Penguin,1968.)这一点是中国的作坊生产完全欠缺的。
中国的作坊和其它场所对劳动力的管理方式,未能提供直接雇用大量工人的办法。
从文献记载看,尽管中国曾利用行政命令,成功地雇用大量人工从事劳动密集的工程,但没有一个兴办较大规模的商业企业的个案是成功的。
中国官营丝织品和陶瓷的生产作坊,在设计时规模巨大——诸如官营丝业织造工厂准备拥有数百台织机——但几乎从未成为一个统一管理的企业。
替代的办法,就象我们在香港所熟悉的生意运作方式一样,官营的工厂被分包给熟悉技术的工头,这些工头各自办他们自己只用一两台织机的企业。
(注:
彭泽益:
《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彭泽益:
《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的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PaoloSantangelo,”TheimperialfactoriesofSuzhou:
limitsandcharacteristicsofstateintervention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inS.R.Schram,ed.TheScopeofStatePowerinChina,LondonandHongKong:
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andChineseUniversityPress,1985,pp.269-294.)根据文献记载,类似的碎裂经营的情况,也见于采矿业和陶瓷工场。
矿井和瓷窑归私人所有,但承包给一小组工匠,这些工匠在自己工头的带领下工作。
(注:
有关文献可参见邓拓:
《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论证》,《历史研究》1956年第5期;胡铁文:
《试论清前期景德镇制瓷业中官窑、行会同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5辑,1983年,第205-224页;梁淼泰在《清代景德镇一处炉寸窑号的收支盈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中讨论的两个帐本,也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在官营的铸币厂,政府保持对机械的所有权,但工头雇用他们自己的工匠。
(注:
彭泽益:
《清代宝泉宝源局与铸钱工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5辑,1983年,第179-204页。
)可以猜想,由于没有某种形式的生产会计,监管的费用一定很高,分包所需的管理费用会比直接雇工低。
直至1920年代,中国的工厂主还是通过包工头来管理其工人,包工头领取一笔总费用后,自行招募、监管工人,并给他们薪水。
近代的工厂在同一个厂房内聚集着许多工人,但其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沿用传统的分散监管的路子。
以后发生的情况,与其说是由于管理思想的有意识改变,不如说是传统的行为方式,对新引进机器所要求的前提条件的勉强适应。
动力织机、卷烟机和水泥厂,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们能够使用非熟练工人去取代传统工场所必需的熟练工人。
到了1920年代,中国工厂的经营者才致力于管理合理化,开始以受薪的管理人取代传统的包工头,这一过程导致许多劳资纠纷,并驱使包工头在工业行动扩展时,站在他们的劳工一边。
因此,把作坊与工厂联结起来的论点,忽视了伴随着动力机械使用而来的新纪律的生命力。
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关于工业劳动者与其工作分离的富于洞察力的讨论的基础。
明清时代中国的作坊不仅不能产生大规模生产所必需的管理工具(managementtools),而且也无法提供一个架构(framework),为向蒸汽动力转变准备条件。
可以肯定,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某些方面的技术领先于西方。
直到蒸汽动力出现之前,西方工业革命中发明的所有棉纺织的新机械,都可以在明代的农书中找到。
然而,这不等于说,中国已经掌握了蒸汽机所必需的机械基础。
而蒸汽机的发明,才是制造业使用机器的基础性革命。
我们无须讨论发明的偶然性问题,发明这种机器所要求的决定性技术不是关于蒸汽可以推动连杆的知识,而是有没有象钻床和车床这样的能够精确地把五金材料加工成不同形状的工具。
(注:
关于威尔金森空心钻床对瓦特蒸汽机的重要性,参见L.T.C.Rolt,ToolsfortheJob,AShortHistoryofMachineTools,London:
B.T.BatsfordLtd.,1965,pp.49-50,53-54.)
中国没有象西方那样强的使用机器工具(machinetools)的传统。
钻床和车床在西方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制造火枪,这是一个在中国没有太大进步的技术领域。
(注:
车床的另一个用途是制造螺丝,而中国不使用螺丝。
)当然,还是可以争辩说,只要中国的工匠看到制造蒸汽机的要点,他们是能学会使用车床的。
(注:
李约瑟和WangLing认为,蒸汽机的要素在中国已经被发现,但这并不未改变这些要素没有加起来变成蒸汽机这一事实。
参见JosephNeedhamandWangLing,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vol.4,PhysicsandPhysicalTechnology,Part2,mechanicalInvention,Camb.:
CambridgeUinversityPress,1965,pp.135-155and380-387。
PeterMathias认为,与其说蒸汽机的发明源于新的动力原理的出现,毋宁说是由于现有技术的灵巧应用,这一观点,对认为只要有证据说明一种技术在书本上存在,它就自然会被应用的预设性结论,是一个批评。
PeterMathias关于车床在蒸汽机发明中的应用的论点,参见其TheFirstIndustrialNation,AnEconomicHistoryofBritain1700-1914,London:
Methuen,1983,p.127.)然而,这是一个与历史的时间选择问题密切相关的观点。
推动工厂机器的蒸汽机并不是一个容易移动的产品。
可以移动的轮船和火车头,并没有带来在工厂中应用蒸汽机的观念。
(注:
JosephNeedhamandWangLing,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vol.4,pp.387-390。
)中国对新技术的掌握和西方新技术的发明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到1890年代,甚至连官员们自己都很清楚在工业方面必须追赶技术差距时,西方的技术进步已经超越了蒸汽机,而到了大规模生产化学制品、钢铁和应用电力的阶段了。
这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明不是工匠创造的,而是由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完成的。
从此,以往可以从师傅处学到的手艺,让位给只有通过严谨的小学教育才能掌握的工程技术。
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和迅速的文化变迁,这个过程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此,在考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时,我们一定要把与技术进步的制度性基础(institutionalbases)有关的若干问题分开讨论,不能把这些问题混为一谈。
如果问题是,在明清时期已经存在的技术基础上,中国人能否发明工厂和蒸汽机,答案是几乎不可能,因为中国的作坊完全没有使用机器工具和进行生产核算的传统。
如果问题是中国人能否在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刚发明时就掌握它们,或许可以说,在19世纪早期是可能的,但还得补充说,技术转移被延误的时间越久,技术也就越先进,越是从工匠的手艺转变为学者的技术。
除非有制度化的基础教育的改革,否则,中国人普遍地掌握技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但是,第三个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在有关中国的技术引进的讨论中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因素,那么,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发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规模使用新技术所必需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核心所在。
相比之下,作坊中雇佣关系的性质只不过是一个侧面的问题。
要回答有关19世纪后期有没有可应用的金融制度(financialinstitutions)这个问题,既惨痛又明显。
直至19世纪末,尽管中国本身的金融机构有能力提供小工厂所需求的资本,但除了政府以外,还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提供建设铁路和开发大矿山所需的资金数额。
没有疑问,金融帝国主义(financialimperialism)有助于西方银行控制工业融资,但是,中国本身的金融机构也很明白,假如想参与资本密集的金融市场的竞争的话,他们也不得不象近代银行一样运作。
说真的,如果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萌芽的话,那么,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本地的金融机构发展如此受阻,以致于在西方银行可以向中国提供大笔贷款之前,在中国本土的环境下,没有出现可以提供大额工业贷款的资本家。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在中国手工业作坊的经营中找到。
这一方面的历史,我们可以在贸易和土地经营的历史中寻找。
关于明清时代的贸易活动情形,我们的了解基本来自第二手的描述,而非第一手的商业记录。
(注:
有一些例外,参见邓拓:
《从万历到乾隆》;MadeleineZelin,”CapitalaccumulationandinvestmentstrategiesinearlymodernChina:
thecaseoftheFurongsaltyard”LateImperialChina9:
1,1988,pp.79-122;ChoiChi-cheung,”Competitionamongbrothers:
theKinTyeLungCompanyanditslianhaos[associatecompanies],”inRajeswaryAmpalavanarBrown,ed.ChineseBusinessEnterpriseinAsia,London:
Routledge,1995;梁淼泰:
《清代景德镇一处炉寸窑号的收支盈利》。
)不过,我们所知的情况足以拼出一幅暂时可用的粗略图象。
例如,我们知道,明清时期财产转移时,经常使用契约文书。
中国史学家大量利用这些被分别称为“合同”、“契”或“合约”的契约文书进行研究。
它们被用于土地、房产和人口买卖,借贷、投资,建立生意伙伴关系,以及汇款等等场合,也在包括订婚、结婚以及祭祀神灵等多种仪式活动中被使用。
(注:
Fu-meiChangChenandRamonH.Myers,”CustomarylawandtheEconomicGrowthofChinaduringtheCh’ingperiod,”Ch’ing-shihwen-t’i3:
5,1976,pp.1-32;3:
10,1978,pp.4-27,JamesHayes,”Specialistsandwrittenmaterialsinthevillageworld,”DavidJohnson,AndrewJ.NathanandEvelynS.Rawski,edsPopular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5,pp.75-111;MyronL.Cohen,”FamilypartitionascontractualprocedureinTaiwan:
acasestudyfromsouthTaiwan,”DavidC.Buxbaum,ed.ChineseFamilyLawandSocialChangeinHistoricalandComparativePerspective,Seattle:
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78,pp.176-204,andRosserH.Brockman,”Commercialcontractlawinlatenineteenth-centuryTaiwan”,inJeromeAlanCohen,R.RandleEdwardsandFu-meiChangChen,eds.EssaysonChina’sLegalTradition,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0.pp.76-136.)事实上,这些文书被使用的广泛程度,可见于民间流行的刊印或手抄的各种手册,因为它们都以这类文书的格式作为其基本内容。
到了晚清,商业书信可能也逐渐变得与契约文书同样重要。
邮局的建立降低了送信的成本,这也许就是那个时期有那么多“尺牍指南”之类的书籍保留至今的理由。
(注:
许舒(JamesHayes)搜集了大量这一类文书,现收藏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通过书信可以订货、供货、报价,有时还涉及到复杂的付款安排。
中国人在生意中使用文字工具(writteninstruments),就象在社会活动的其它领域使用文字一样平常。
明清时期订立的契约,基本上属于私人(private)契约的性质,讲明签约者彼此的责任,几乎没有牵涉社群和国家的参与。
还不清楚的是,是否所有契约在法律上都有同等的强制力。
明清的法律根据是刑法,虽然《大明律》、《大清律》某些条款可以扩展到商业事务,但从当时的记载看,县官处理最普遍的是婚、户和田土方面的纠纷,明显地没有包含合伙和银钱借贷在内。
这种局限,要从地方行政的角度来理解。
明清时期的知县,由于其儒学的传统,对家礼有相当的认识。
作为地方官,他对税收和田产登记负有责任,所以也就必须熟悉田地的交易。
商业不属于其经验范围,追求利润的德性本身也受到质疑,所以地方官通常对做生意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既不敏感,也缺乏同情。
明清时期的商业仲裁者是行会,而不是衙门。
行会制定行规,也代表其成员与外人和官府打交道。
现存的文献远不足以弄清行会解决其成员之间纠纷的能力到底如何,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其地位和影响力与此很有关系。
(注:
台湾的资料显示,提交给知县的案件中,约20%是民事案件。
这表明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