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刚这样回忆恩师季羡林不薄西方爱东方.docx
《梁志刚这样回忆恩师季羡林不薄西方爱东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梁志刚这样回忆恩师季羡林不薄西方爱东方.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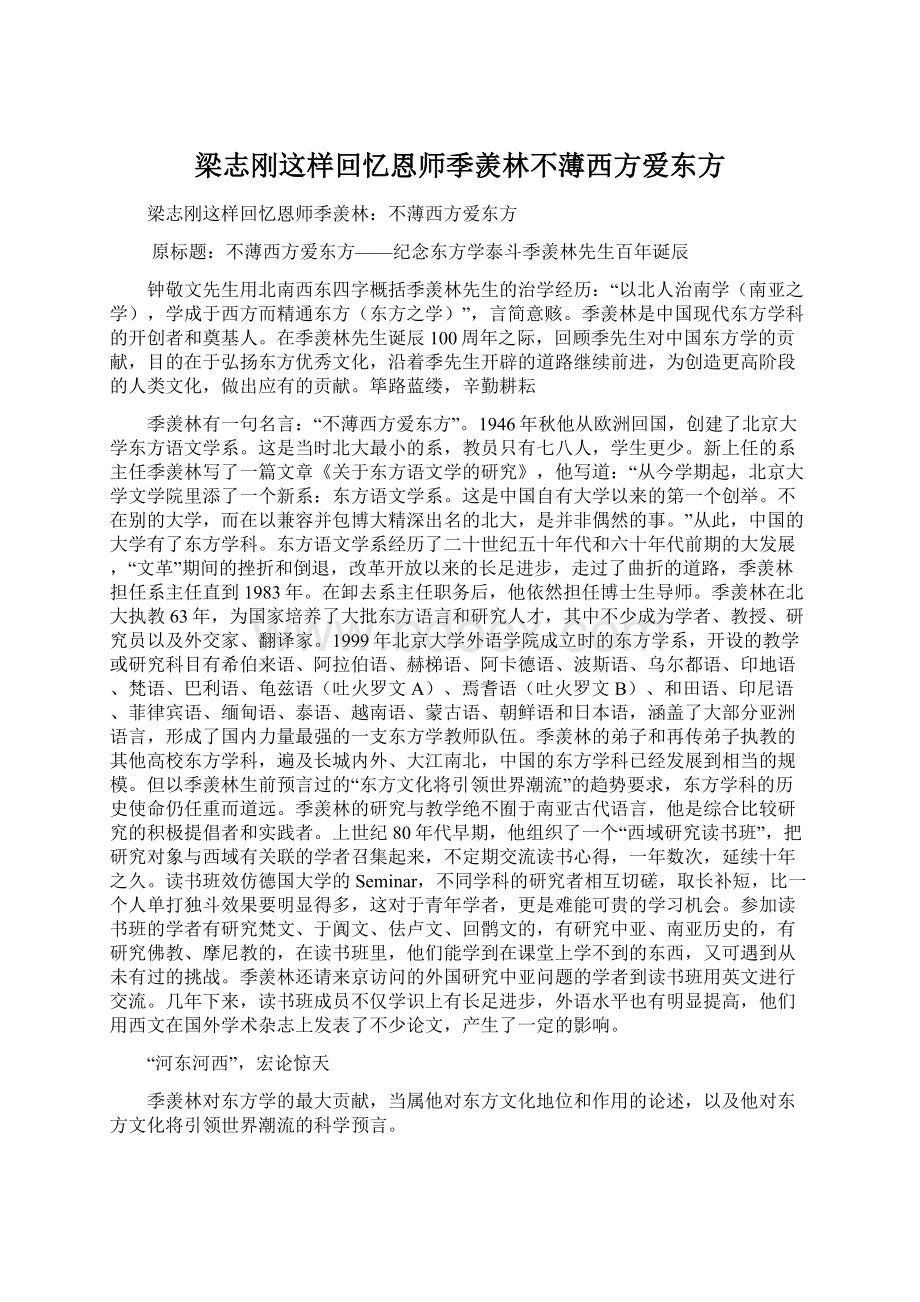
梁志刚这样回忆恩师季羡林不薄西方爱东方
梁志刚这样回忆恩师季羡林:
不薄西方爱东方
原标题:
不薄西方爱东方——纪念东方学泰斗季羡林先生百年诞辰
钟敬文先生用北南西东四字概括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经历:
“以北人治南学(南亚之学),学成于西方而精通东方(东方之学)”,言简意赅。
季羡林是中国现代东方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在季羡林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回顾季先生对中国东方学的贡献,目的在于弘扬东方优秀文化,沿着季先生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创造更高阶段的人类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筚路蓝缕,辛勤耕耘
季羡林有一句名言:
“不薄西方爱东方”。
1946年秋他从欧洲回国,创建了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
这是当时北大最小的系,教员只有七八人,学生更少。
新上任的系主任季羡林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东方语文学的研究》,他写道:
“从今学期起,北京大学文学院里添了一个新系:
东方语文学系。
这是中国自有大学以来的第一个创举。
不在别的大学,而在以兼容并包博大精深出名的北大,是并非偶然的事。
”从此,中国的大学有了东方学科。
东方语文学系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的大发展,“文革”期间的挫折和倒退,改革开放以来的长足进步,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季羡林担任系主任直到1983年。
在卸去系主任职务后,他依然担任博士生导师。
季羡林在北大执教63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东方语言和研究人才,其中不少成为学者、教授、研究员以及外交家、翻译家。
1999年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成立时的东方学系,开设的教学或研究科目有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赫梯语、阿卡德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印地语、梵语、巴利语、龟兹语(吐火罗文A)、焉耆语(吐火罗文B)、和田语、印尼语、菲律宾语、缅甸语、泰语、越南语、蒙古语、朝鲜语和日本语,涵盖了大部分亚洲语言,形成了国内力量最强的一支东方学教师队伍。
季羡林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执教的其他高校东方学科,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国的东方学科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
但以季羡林生前预言过的“东方文化将引领世界潮流”的趋势要求,东方学科的历史使命仍任重而道远。
季羡林的研究与教学绝不囿于南亚古代语言,他是综合比较研究的积极提倡者和实践者。
上世纪80年代早期,他组织了一个“西域研究读书班”,把研究对象与西域有关联的学者召集起来,不定期交流读书心得,一年数次,延续十年之久。
读书班效仿德国大学的Seminar,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比一个人单打独斗效果要明显得多,这对于青年学者,更是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
参加读书班的学者有研究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回鹘文的,有研究中亚、南亚历史的,有研究佛教、摩尼教的,在读书班里,他们能学到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又可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
季羡林还请来京访问的外国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到读书班用英文进行交流。
几年下来,读书班成员不仅学识上有长足进步,外语水平也有明显提高,他们用西文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论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河东河西”,宏论惊天
季羡林对东方学的最大贡献,当属他对东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以及他对东方文化将引领世界潮流的科学预言。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热在中国悄然兴起。
随着国门的打开,一些人产生了近乎病态的崇洋心理,全盘西化的主张一时甚嚣尘上。
在严重地甚至病态地贬低自己文化的氛围中,人们有意无意地抬高西方文化,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只有外来的和尚才会念经。
季羡林感到深深的忧虑。
经过慎重思考,他在1989年写了一篇重要文章《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他提出:
探讨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几十年近百年,也不能局限于我们居住于其中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我们必须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才能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全貌,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
总之,我们要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探骊得珠。
(《季羡林回忆文集:
此情犹思》卷四,第229页)
文章说:
人类文化产生是多元的,决不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单独创造出来的。
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是,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贡献又不完全一样。
有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对周围的民族或国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积之既久,形成了一个文化圈或文化体系。
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总共形成了四个大文化圈:
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国家的闪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
文化圈内有一个主导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民族或国家又是互相学习的。
在各文化圈之间也是互相学习的。
这种相互学习就是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
倘若从更大的宏观上来探讨,这四个文化圈又可以分成两大文化体系:
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三、四个文化圈构成了东方大文化体系。
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学习的。
仅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
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可以用一句俗语来概括,这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历史上,东方文化曾经辉煌过,引领过世界潮流。
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文化逐渐占了上风。
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如果还想存在下去,就必须跟上世界潮流。
想振兴中华,必须学习西方,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今天要向西方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
如果固步自封,回到老祖宗走的道路上去,那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人类历史证明,全盘西化,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
季羡林赞成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万岁的观点。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自己应该避免两个极端:
一不能躺在光荣的历史上,成为今天的阿Q;二不能只看目前的情况,成为今天的贾桂。
”
季羡林认为,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原因何在呢?
从总体上看,东方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
从伽俐略以来四百年中,西方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
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分析下去的。
自然科学界和哲学界发生了一场争论:
物质真是无限可分吗?
赞成这个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反对物质无限可分观点的人,只占极少数。
金吾伦的《物质可分析新论》可以作为后者的代表。
他认为,当代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新进展表明,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无限分割的方法与整体论是相悖的。
无限可分论是机械论的一种表现。
季羡林赞成金吾伦的观点。
同时,季羡林从一种方兴未艾的新学说——混沌学受到启发。
美国学者格莱克写了一本书:
《混沌:
开创新科学》。
混沌学是关于系统的整体性质的科学。
它扭转了科学中简化论的倾向,努力寻求整体,寻求复杂系统的普遍行为,揭示了有序与无序的统一,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是过程的科学而不是状态的科学,是演化的科学而不是存在的科学。
其覆盖面之广,几乎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为什么在西方文化如日中天光芒万丈的时候,西方有识之士竟然开创了与西方文化背道而驰的混沌学呢?
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
这些有识之士已经痛感,照目前这样分析是分析不下去的。
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人类文化才能重新洋溢着活力,继续向前。
季羡林得出结论:
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它的对立面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
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
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将看出分晓。
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里所说的“取代”,并不是“消灭”,而是继承西方文化之精华,在这个基础上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季羡林的“河东河西”论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争论逐渐平息,并非季羡林的辩才占了上风,而是历史发展本身,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看清了端倪。
“天人合一”,东方瑰宝
季羡林经常考虑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他想:
21世纪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1998年3月他在为郑彝元的《道统论》作序时写道:
我平生为不中不西而又亦中亦西之学,偏考据而轻义理,此盖天性使然,不敢强求也。
迨至耄耋之年,忽发少年之狂,对义理问题,妄有所论列;但局促门外,有若野狐,心情介于信疑之间,执着则逾意料之限。
数年前曾写一长文《“天人合一”新解》,意在唤起有志之士正确处理人与大自然之关系。
盖谓西方科技文明,彪炳辉煌,为时已久。
造福人类,至深且巨。
然时至今日,际此上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其弊害渐趋明显,举其荦荦大者,如环境污染,臭氧出洞,人口爆炸,疾病丛生,淡水匮乏,生态失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此皆大自然对人类征服之报复,而芸芸众生,尚懵懵懂懂,使人不禁有“错把杭州作汴州”之慨叹。
此诸弊端,若其中任何一方阻止无方,则人类生存前途必处于极大危害之中,事实如此,非敢危言耸听也。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问题产生的根源。
季羡林通过长期研究和观察,发现根源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搞错了。
这是以分析思维为基础的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结果,是与自然为敌的后果。
西方科学技术在带给人类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要害是以为自然是个奴隶,是可以征服的。
这种想法与事实不符。
事实证明自然是不能征服的。
出路何在?
季羡林认为,只能到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中寻求解决之道。
他发掘出“天人合一”这个东方的古老命题,加以新解,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1992年,他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天人合一”新解》,文章说:
谈到“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大多数学者认为源于儒家的思孟学派。
其实这是一个相当狭隘的理解。
广义的理解是“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
宋代大哲学家张载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话: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简称“民胞物与”,“与”就是“伙伴”的意思。
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涵义深远。
中国古代也有征服自然的想法,荀子想制天,能够战胜自然。
不过这种观点不是主流。
而事实证明,你想制天,必定为天所制。
印度古代文献《奥义书》论述梵我关系常使用一个词儿“梵我一如”。
意思是说:
真正实在的惟有最高本体梵,而作为现象界的我(小我)在本质上就是梵,二者本来是同一个东西。
无非是说梵我合一,也就是天人合一,中印两国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天人合一”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
“天人合一”是讲人与大自然合一。
这个思想非常值得注意,非常值得研究,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因为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
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
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
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
“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表述。
东方文化曾在人类历史上占过上风,起过导向作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时移势迁,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
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秉持征服自然的方针。
对人类的得寸进尺永不餍足的需求,大自然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在限度以内,它能够满足人类的某些索取。
超过这个限度,则会对人类加以惩罚,有时候是残酷的惩罚。
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
有。
季羡林开出的药方就是以东方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
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生存下去。
这个主张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石破天惊,季羡林的“新解”一出,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
反对者认为只有发展科学,发展技术,发展经济,才有可能最后解决环境问题。
决不能为保护环境而抑制发展,否则将两俱无成。
季羡林认为,为了保护环境决不能抑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大前提绝对是正确的。
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脑筋里必须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只能是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尽最大的努力,对弊害加以抑制,决不允许空喊:
“发展!
发展!
发展!
”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梦想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挫败弊害。
事实早已证明了:
科学决非万能。
十几年前的这场争论,现在已经看到结果了。
我国的发展战略已经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了。
还是这四个字,可是顺序变了,标志着重点的转移、认识的深化。
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同十几年前相比也大不相同了。
人们不得不佩服季羡林老先生的远见卓识。
坚持“拿来”,提倡“送去”
季羡林说:
对西方文化,鲁迅先生曾主张“拿来主义”,这个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今天,在拿来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而且应该定为重点。
为了全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把东方文化的精华送去。
季羡林指出,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时代性。
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
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
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
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来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
所以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个问题是贯彻始终的。
所有文化都是以民族性为纬线、以时代性为经线交织在一起的,因而呈现五光十色的特点。
所以说“全盘西化”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
几乎是从一有文化开始,中国文化中就有外来文化的成分。
中国人向来强调“有容乃大”,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只要有利就吸收。
海纳百川,成就了中国文化之大。
中外文化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
最大的两次是佛教的传入和西学东渐。
季羡林主张,拿来要以我为主,决定取舍。
要拿来的无非是三个层次:
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心的部分,都要拿。
“物”的部分,我们拿来的真不少,好的坏的都拿来了,连艾滋病也拿来了,这是不应该的。
心、物结合的部分,比方说制度,也可以学习。
最重要的还是心的部分,要拿价值观念、民族性格。
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不能马马虎虎,得把弱点克服掉,要不克服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就发展不了。
季羡林从长期的历史研究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在我们国力兴盛,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
如果见到外国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这往往是我们国势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
中华文化不仅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而且有天下为公的胸怀。
我们的好东西,向来主张与其他民族分享,决不保守,决不吝啬。
汉唐时期,世界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在中国。
在明末清初以前确实有过“东学西渐”。
人类文明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中国人做出了自己伟大的贡献。
如果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文化的发展,会推迟几百年。
为什么季羡林特别强调“送去”呢?
这同前边讲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论和“天人合一”论有关。
因为近几百年以来,西方文化产生的弊端颇多,如不纠正,人类前途岌岌可危。
对于“送去主义”,季羡林不仅大声疾呼,而且身体力行。
20世纪90年代,季羡林担任主编组织了一套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已经出书100多部,还远未完成,目的在于和全世界分享东方智慧。
季羡林还和王宁合编了一套《东学西渐丛书》,这套丛书,可以增强我们变革和发展的信心。
读者可以发现:
文化交流向来是相互的,从来就不是什么“单行线”。
季羡林主张,首先要送去的是汉语。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中华民族古代和现代的智慧也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
外国人要想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首先必须掌握汉语。
作为语言学家的季羡林发现,汉语具备一些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优点。
这就是:
汉语是世界上最短的语言。
使用汉语,可以花费最少的劳动,传递最多的信息。
坚持“拿来”、提倡“送去”,季羡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他在治学方面,拿来了“德国的彻底性”,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度;而在送去方面,他发掘出中国的、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为贵”理念,用以济西方的“征服自然”、“物择天竞”之穷,为创造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表现出天覆地载、海纳百川的情怀。
2011年2月26日初稿3月19日改写梁志刚,季羡林的学生,曾任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司长,主要著作有《季羡林大传三部曲》《人中麟凤季羡林》《我的老师季羡林》,经季老授权选编《此情犹思:
季羡林回忆文集》《季羡林谈义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