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殷红作家印象二.docx
《胡殷红作家印象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胡殷红作家印象二.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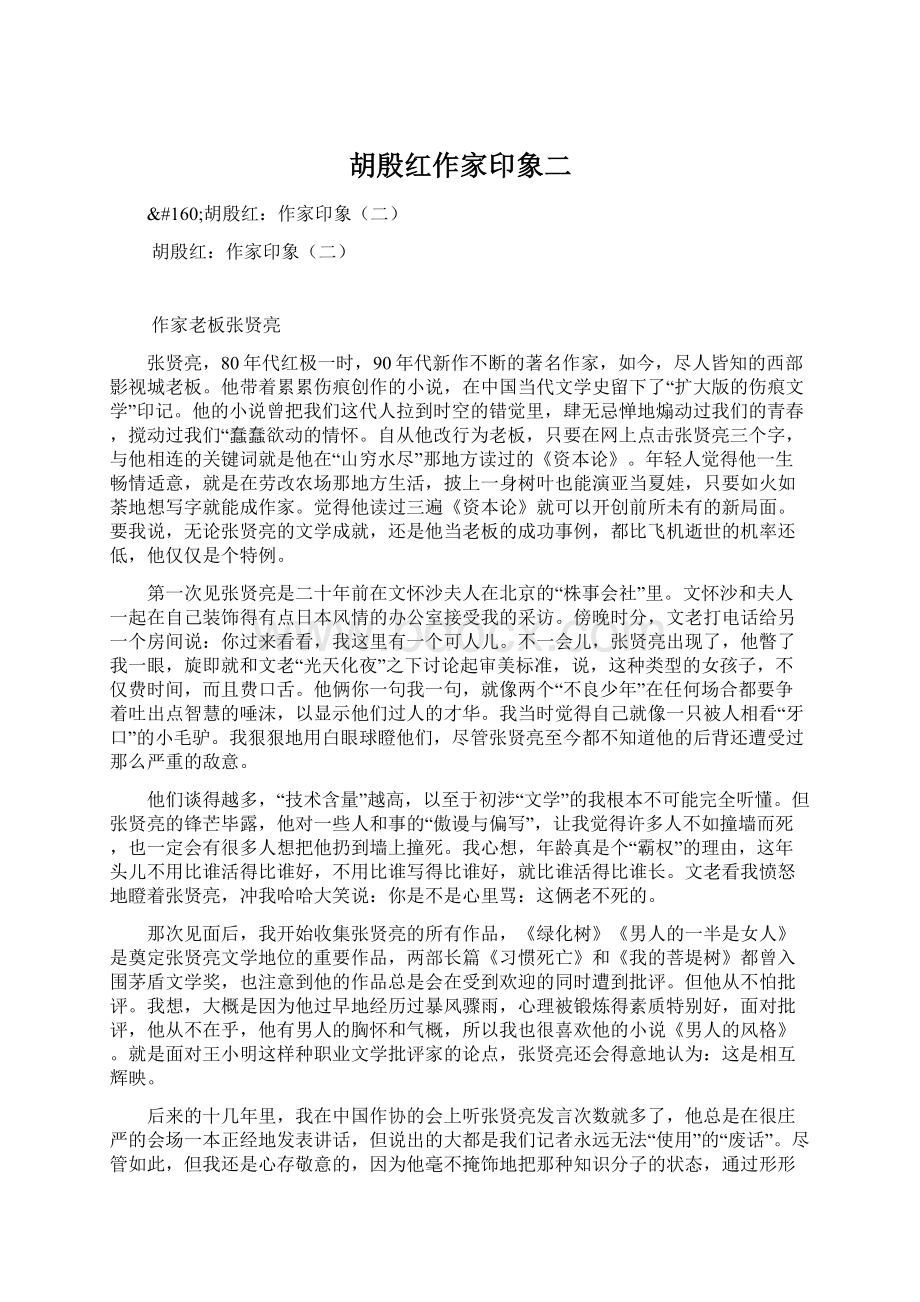
胡殷红作家印象二
胡殷红:
作家印象
(二)
胡殷红:
作家印象
(二)
作家老板张贤亮
张贤亮,80年代红极一时,90年代新作不断的著名作家,如今,尽人皆知的西部影视城老板。
他带着累累伤痕创作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扩大版的伤痕文学”印记。
他的小说曾把我们这代人拉到时空的错觉里,肆无忌惮地煽动过我们的青春,搅动过我们“蠢蠢欲动的情怀。
自从他改行为老板,只要在网上点击张贤亮三个字,与他相连的关键词就是他在“山穷水尽”那地方读过的《资本论》。
年轻人觉得他一生畅情适意,就是在劳改农场那地方生活,披上一身树叶也能演亚当夏娃,只要如火如荼地想写字就能成作家。
觉得他读过三遍《资本论》就可以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要我说,无论张贤亮的文学成就,还是他当老板的成功事例,都比飞机逝世的机率还低,他仅仅是个特例。
第一次见张贤亮是二十年前在文怀沙夫人在北京的“株事会社”里。
文怀沙和夫人一起在自己装饰得有点日本风情的办公室接受我的采访。
傍晚时分,文老打电话给另一个房间说:
你过来看看,我这里有一个可人儿。
不一会儿,张贤亮出现了,他瞥了我一眼,旋即就和文老“光天化夜”之下讨论起审美标准,说,这种类型的女孩子,不仅费时间,而且费口舌。
他俩你一句我一句,就像两个“不良少年”在任何场合都要争着吐出点智慧的唾沫,以显示他们过人的才华。
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人相看“牙口”的小毛驴。
我狠狠地用白眼球瞪他们,尽管张贤亮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后背还遭受过那么严重的敌意。
他们谈得越多,“技术含量”越高,以至于初涉“文学”的我根本不可能完全听懂。
但张贤亮的锋芒毕露,他对一些人和事的“傲谩与偏写”,让我觉得许多人不如撞墙而死,也一定会有很多人想把他扔到墙上撞死。
我心想,年龄真是个“霸权”的理由,这年头儿不用比谁活得比谁好,不用比谁写得比谁好,就比谁活得比谁长。
文老看我愤怒地瞪着张贤亮,冲我哈哈大笑说:
你是不是心里骂:
这俩老不死的。
那次见面后,我开始收集张贤亮的所有作品,《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奠定张贤亮文学地位的重要作品,两部长篇《习惯死亡》和《我的菩堤树》都曾入围茅盾文学奖,也注意到他的作品总是会在受到欢迎的同时遭到批评。
但他从不怕批评。
我想,大概是因为他过早地经历过暴风骤雨,心理被锻炼得素质特别好,面对批评,他从不在乎,他有男人的胸怀和气概,所以我也很喜欢他的小说《男人的风格》。
就是面对王小明这样种职业文学批评家的论点,张贤亮还会得意地认为:
这是相互辉映。
后来的十几年里,我在中国作协的会上听张贤亮发言次数就多了,他总是在很庄严的会场一本正经地发表讲话,但说出的大都是我们记者永远无法“使用”的“废话”。
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心存敬意的,因为他毫不掩饰地把那种知识分子的状态,通过形形色色的谈话表现出来。
他嘲弄与自嘲的风格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状态。
每当听他让会场爆发笑声时,我都会想:
生活真是充满严酷的讽刺,它可以让有张贤亮这种历经磨难的人还能保持一种具有生命色彩的躁动不安,并不断产生“兼济天下”,心向往之的追求,真是太奇特了。
我从不怀疑张贤亮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的重要位置,和他对一代作家产生过的巨大影响,但他投资西部影视城的举措我当时并不看好。
早些年《文艺报》银根吃紧,广告部想找张贤亮给我们点儿资助或广告。
广告部主任就想让我给他做一个整版专题报道,先期做点事,然后再张口。
报选题时领导们一致认为,采访和拉广告没关系,张贤亮肯定不会出一分钱。
广告部坚持认为不能放掉这条大鱼,又派了别人去写张贤亮,最终报社也没拿到他一分钱。
我说,张贤亮是照着《资本论》经营的,咱们这套“骗钱”的方法就像过了期的天气预报和去年的台历,他才不“买单”呢!
事实上张贤亮的确接受不了这种方式。
换了作家们去采风、中国作协去开会,他真像个阔绰的老板,决不吝啬,而且热情周到。
张贤亮是一位能说出文学之秘密的作家,但张贤亮在文学之外,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是一位懂得保持秘密的老板。
有一次谈到作家怎样当老板,张贤亮告诉我他使的“绝招儿”:
在影视城,张贤亮只管他该管的,不该管的绝对不管。
比如个人隐私,在中国的企业里张贤亮是第一个将个人隐私权制度化的,而且写进规章制度:
任何人不得干涉、揭发别人的隐私。
张贤亮说,我们影视城有位女职工跟外面的一个有妇之夫好上了,有一天她突然失踪了,搞得我很焦急,派了所有的员工去寻找也没找到,只好向派出所报案。
过了三天,她回来了。
我没过问她去干什么,那是她个人的事,要管就由道德、社会、法律来管。
但是她违反了影视城的纪律,我必须罚款。
至于她的隐私谁也不许问,谁也不许传。
现在这小姑娘跟当地的一个小伙子结婚了。
看张贤亮为自己的“创举”得意,我说,你这叫顺理成“张”,一个作家深知水道渠成的结果才是生活的常态,这就是作家的优势嘛。
张贤亮作为作家,积累了他的名气和人气,但搞企业仅靠个人的名气肯定是不行的,没准还把他的那点名气全赔进去了。
当然,张贤亮的名气对影视城也是一种宣传,起码读过张贤亮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下海搞了个西部影视城。
张贤亮从不炫耀低调,所以他总是高调地让别人去替他炫耀。
他让周星驰、张曼玉、巩俐、林青霞、张艺谋替他做广告,他们用过的道具全部收藏起来展览。
游客手机不小心掉进厕所,水一冲就进了化粪池。
明知捞出来也肯定报废,但张贤亮硬是叫3个员工花半天时间在粪池里掏,洗得干干净净退还游客,这位游客对影视城感激不尽。
我说,这就是你的广告理念,难怪不在我们《文艺报》做广告。
旅游是什么?
旅游就是找感觉。
旅游经济是什么?
旅游经济赚的就是感觉的钱。
张贤亮身为作家却抓到了“赚钱”的门路,大会小会“煽乎”得不少写字之人误以为有感觉就能当老板,有想法就能赚大钱。
我心想,对钱的感觉好的多着呢,不还是得靠写字赚点散碎银两嘛。
不服张贤亮不行,他的过人之处别人学不来的。
其实王安忆随和得一塌糊涂
从读王安忆的小说,到认识她这个人,把手指头和脚指头捆在一起数年头儿,怎么也超过了这个数,但真正走近她,是我们前不久一起到港澳的那些天。
在我平日的印象中,王安忆衣着并不讲究,她的理论是:
天天在家里,用不着买太多的“工作服”,再贵的衣服,一年也不一定能穿一次。
但是她有“礼服”,一袭丝绸旗袍,淡淡海蓝之色,在香港作联二十周年隆重的庆典晚会上,她确实给中国作家代表团增了彩。
而且王安忆受欢迎的程度也出乎我的预料,她的“粉丝”比这个团的男作家多多了,请她签字、合影的男男女女追着她,围着她。
特别是有一天她穿了一件“香樵领”,蓝印花布的“短坎”,“民族”而时尚,凡到有人拉她拍照,她都特别配合,镜头一对准她,她脸上就绽开灿烂的笑容,昂首挺胸地往那儿一站,高而挺拔的身材还带着点模特的“范儿”。
我夸赞这件衣服与她穿旗袍的两种味道,王安忆悄声告诉我,这是她母亲的“遗物”。
我更为认真地打量这位茹志娟的爱女,体味着这对文坛母女的审美情趣。
王安忆从不主动和人搭讪,显得挺孤傲。
这不用我说,有目共睹。
这么多年里,她无论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亦或她参加什么著名作家活动啥的,我们总有很多机会见面。
她从来脖子挺着,头昂着,面无表情。
当她一以贯之地从主席台走上走下的时候,我脑子里一定会想,她肯定把台下的人都假设成服装模特的教练啦:
上了T台就不许笑。
当然,年头多了,日子长了,我也看惯了她那没有表情的表情。
有时我会主动地朝她呲一下牙,她一定会还我一个有点羞涩的微笑。
工作需要时我也会往她家里打电话,她的声音听来还热情,只是问一句回一句,想和她“煲”电话粥是不可能的。
凡到这时我就在心里问自己,一个不愿与人交流的人怎么写小说啊?
想解答这个百思不解的问题我从没指望王安忆本人。
但是,天赐良机,这个疑问终于由她亲口给了我解答。
王安忆说,这么多年她有“工作单位”必须上班的时间就三五年,其余时间都是“独立生活”,基本是待在家里写作,即便调到大学里工作,也是有课去上,无课在家,很少参加应酬。
这样的状况使她不太会,也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了。
她至今不上网,不会收发邮件,最大的消遣和信息来源是一份《新民晚报》。
我所担心的是,王安忆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会受到环境条件制约,从而影响她个人生活感受之外的创作。
王安忆说:
写小说,没有经验做想象的出发点,就没有办法去写作。
我最担心的局限性问题,王安忆却不以为然。
她认为,相对地封闭可以把她的立足点圈起来,圈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
她说,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能够自圆其说。
当然,这也是取决于作家自身的生命力,生命力旺盛,生态就平衡,重要的是要经营好这块园地,而不要妄想去超越经验的局限。
我笑说,我原以为小说家都是“私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可你的确是把“经营”的好手,经营创作的园地,经营生活的家园。
所有读过王安忆作品的人都不能否认,王安忆作品中对人物心理描写的到位是她非常突出的特点,这说明她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不仅对人的内心观察是细微的,而且能够摆脱个人的局限去理解别人。
读王安忆的作品,我总为王安忆那双能看入骨髓、令人颤栗的眼睛兴奋。
我说,王安忆,你虽不爱说话,但你的眼睛特别好使,就好比失聪的人往往心明眼亮一样。
王安忆写了很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我也读了不少。
但从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入围那天,我就开始收藏她长篇小说的各种版本了,只是直到今天也没找她签过一本。
不知道为什么,她那明察秋毫的眼情和性格,好像“抑制”我的热火朝天。
那些年,我们总是远远的、淡淡的相视一笑,无话可说。
但在我心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长恨歌》的获奖,不仅仅是对王安忆文学创作的肯定,也是茅奖自身的一次突破。
在此之前的四届茅奖获奖作品里,是没有她这种类型的作家和作品的。
这让我想起颁奖的当天,所有在现场的人都跟打了鸡血似的亢奋,王安忆却在他丈夫的陪同下拒绝了很多记者的采访,闭门“歇”了。
我当然不会上赶着非要求采访她不可,只是暗自佩服她的自信、淡定和决非做作的低调。
一晃十年又过去了。
这期间她写了很多作品,每次都是先在刊物上发表不久,新书就跟着上市了。
唯《月色撩人》这篇是先在报纸上连载后,才在《收获》五期发表,这种发表方式对王安忆是个特例。
我揣想,这也许和作品的内在品质有关?
也许表示某种转向?
也许是为了面向大众?
我不否认《月色撩人》是一部好小说,只是怀疑有多少人能静心读下去呢?
关于《月色撩人》评论界和网上评价不一,但我想,别人怎么评价对王安忆都不会有任何影响,她从来不太在乎别人的评论。
她说过,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所做的劳动无法向别人传达,我根本不期待别人完全理解。
我自己阅读的经验也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很难找到一个特别合适发表意见的人。
王安忆这话我以前听过,而当她面对我再次谈到时,还真觉得她说得实在,没有假装谦虚。
王安忆也是水做的女人,肉长的心,她一定喜欢听表扬,但我理解了她决不是抵触批评,她觉得批评要真的读了作品,真的有分析,才有交流的可能。
在香港和澳门,我们朝夕相处,有很多话题可聊,我发现,只要能有机会走近她,就会觉得她特别随和,无论吃、住,无论讲话、拍照,无论什么场合,她一点不拧巴,随和得一塌糊涂。
不管事先是否通知了她发言,临时拉上场她也有话可讲,头头是道。
无论她累还是不累,想不想购物,喊她逛街她就陪着。
出门前她还会轻声问一句:
海风凉,你带外衣了吗?
她的每一次关心和提醒都让我想到“上海女人”,想到专门研究她的人对她这个人的评价和对她作品的归类。
有学者或文学评论界将她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把她放在“海派文学”的传统中来评说。
我想,如果不探讨“籍贯”,只论写上海写得好,写得透彻,写得细致入微,张爱玲和她是我读到的作品中,最好的海派作家了。
但我又觉得她俩不可比,生存状态不同,生活的时代不同,历史责任不同。
可我最终这样想:
评价王安忆的文学创作,最好别给她“撮堆”分类,也最好不用“责任”二字,应该用:
“生活、生命”这四个字最妥贴。
我也非常喜欢王安忆的《心灵世界》那部讲课稿结集。
这个集子里的每一课都体现出她极强的表达能力,而且很显文学专业水准,很有理论素养,真想表扬她是文学方面的“全才”。
她从作家到教授的漂亮转身,日常生活中的她与讲台上的她的变化与反差令我惊诧。
走近她也没能解开这个谜。
和王安忆聊她的创作,不可能不谈她标志性的作品“三恋”。
但当读者和评论界认定了“三恋”的风格之后,她并未行成所谓“王式风格”,而是不断在变。
王安忆似乎是刻意“创新”,这也是我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八、九十年代,各种文学思潮涌动,王安忆的吸纳性又特别强,在各个思潮中都有代表作。
那个时期,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热情都是“相当澎湃”。
可如今,已不是文学风起云涌的年代,文学思潮消失了,作家如何写作,从哪个维度关注现实,进入现实的通道在哪儿,精神支点在哪儿,如何确立创作方向,就开始令人堪忧了。
我提了一大串问题,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只好约定另谈了。
王安忆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对待的那种人,这真不是因为她“情商”高,而是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在于她的真诚。
我们在香港时就约好回来的第二天,一起到杭州参加叶文玲大姐的新书发布会,并到叶大姐的家乡去采风。
她说叶大姐是她的同学,别的会可以推,这个会是一定要去的。
遗憾的是我们到杭州的当天,叶大姐突发高血压住院。
王安忆和我商量怎么办,是否还要再到她的家乡去。
我说,人都住院了,我们再去“采风”一是给人家添麻烦,二是还有心情“疯”吗?
王安忆沉重地表示:
那就不去了。
其不知,叶大姐的家乡仍然非常希望这个活动继续下去,浙江省作协的领导也千方百计动员王安忆去。
我先走了,王安忆执拗地坚持说:
胡殷红说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她说让我别去了。
后来浙江方面打电话责怪我不出好主意,王安忆当天就回了上海。
我心想,这就是王安忆,当她接受你、信任你时,你就是她的一部分,当她爱你的时候就一定爱你。
她不装。
北京姑奶奶叶广芩
叶广芩虽然在陕西好几十年了,但她“身在曹营心在汉”,因为她毕竟是我们北京的姑奶奶。
15年前我采访她时,她说我不像汉族人。
我心想,你还一点不像满族人呢,明明一个大家闺秀装成个陕西婆姨。
今年春节前北京热播叶广芩同名小说《采桑子》改编的电视剧,正巧她回北京过年。
叶广芩按老理儿拜谒了七大姑八大姨、老哥和老姐。
他们个个早已是平头百姓,可个个还都放不下皇亲国戚、遗老遗少的谱儿,请他们到老字号用膳,出租车断然不肯坐,叶广芩就天天高价雇“黑车”,让人家装成专车司机,背人下楼,扶人上车,鞠大躬,行“蹲礼”,直闹腾到正月十五。
受雇的车主说,姑奶奶,你们家亲戚要是都这么排场,给多少钱我也侍候不了啦。
在叶广芩身上,老北京人的“讲礼数”和“满不吝”都有突出表现。
她那大家闺秀的“范儿”一般人还真端不起来:
进电梯她从来侧身让步,右手伸出,礼让他人。
开会入座,她决不第一,也从不迟到。
任何人讲话,她都是“凌腰”而坐,双手对握放在腿上。
和朋友聊天,她一定注视对方,从不插话打断。
这些从“丫丫”时代就养成的规矩,让她身上散发着时髦女性们少有的气派和独特味道。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这毛病,对自己要求严,对别人要求更严。
比如叶广芩带女儿到青海湖去旅游,一对20来岁的恋人迟到一个多钟头,车上骂不绝耳。
待那两人手拉手上了车,叶广芩用腿往通道上一横,非要他俩向全车人道歉,小伙子像被激怒的公牛高声嘶吼。
叶广芩脾气也上来了,双方居然动手打将起来,直打得司机把车停下来说:
等你们打完了再走。
全车人没一个说话,也没人劝架。
我听得过瘾,叶广芩说得更来劲。
我说,你就不怕打出人命?
叶广芩得意地说,我有数,那小两口不是打架的人,要不我也不敢招呼啊。
她还号召我参加她组织的打架旅游团,走一路打一路,打那些不守规矩的、不主持正义的、不说人话的。
我说,那我的医药费得你出。
我一点规矩不讲地坐在桌子上和叶广芩聊天,听她讲她在西藏要饭的事,乐得我差点翻掉地下。
当年,叶广芩听说“一卡在手走遍全国”,赶了回时髦,到了才知西藏根本没时兴一卡通。
兜里那点散碎银两用光后,饿得坐在马路边上冒金花,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人现眼地拿碗要饭啊。
一抬眼看见“天府大酒楼”,她想出个馊主意:
进去点它个四碟四碗,饱饱吃上一顿,然后用卡结账,人家肯定说不行,正好在那儿免费打长途让家里汇款。
盘算得不赖,可饭店快打烊了,不再接待客人,就剩两个出差模样的人还没吃完,叶广芩急中生智,搬个椅子往两人中间一坐说,我遇到麻烦了。
那俩人说,你这样的我们见多了。
叶广芩又拿出牡丹卡、身份证,那俩人说,这玩意儿假的就更多了。
她再拿出招待所房门钥匙和记者证,那俩人说,就你这样也就冒充记者。
费了半天口舌叶广芩先急了:
让你们多添一碗饭有什么难的?
那俩人觉得也是,又没骗别的。
叶广芩见人家突口了,就顺竿爬:
一碗饭哪儿顶得到晚上啊,再加一碗饭添两个菜。
吃完,谢过,告辞。
到晚上,那俩“赏”饭的散步到叶广芩住所附近,就便想验证一下“女骗子”。
叶广芩见他俩来了,噌地一下从床上蹦到地下,得了理似地大声说,我没骗你们吧?
那你们得借我1000元,到成都马上寄你们。
俩小伙子跟自己犯了错似的,乖乖交出钱走了。
当然,他们三天后就收到了叶广芩的汇款。
没多久,他俩到西安出差,试着打叶广芩留下的手机号。
见面时叶广芩正在电视剧拍摄现场呼风唤雨呢,她那大着嗓门掳胳膊挽袖子统筹全局的架式让他们目瞪口呆:
这就是在西藏要饭吃的大姐!
在外要饭的事叶广芩不觉着丢人,回家当“总管”她也觉得满有成就。
买房、修车、换灯炮,事事都是叶广芩说了算,件件也就得她自己干了。
有几年叶广芩家闹耗子,耗子们大庭广众之下出来溜跶时,老公两腿一抬让耗子们过去,然后大喊:
你给我把它们打死!
赶上叶广芩出差几天,回来准能看到家里地上、桌上到处摆着一小堆一小堆的吃食。
老公说,我给耗子吃的,它们有吃的就不偷吃我的饭了,等你回来再处理它们。
看着老婆整天家里家外上了弦似地折腾,老公常常冷嘲热讽地问叶广芩:
你什么时候当总理啊?
叶广芩挂职县委副书记有十来年了,把自己混同于当地老百姓,深入于他们之中已不是问题,但说当领导,她就是上不了道。
有一次县委通知下午开会研究提拔干部,上午就有一个婆姨得了消息,拿着五捆香椿找到叶广芩,张嘴就说:
我想当乡长,我要当了乡长,决不允许滥砍滥伐。
叶广芩收了“贿”,也觉得这人直爽,想干事。
开会时先说收了人家香椿,然后提议让这个婆姨当乡长,结果是惹来哄堂大笑,弄得书记连连说,这是选一乡之长啊,你有点谱行吗?
叶广芩的大名,在小小的县城妇孺皆知。
夏天她为了凉快,穿个自制的花布旗袍满县城跑。
书记想说却不好说,比她这副书记职务低的也没法开口。
琢磨半天,组织上让县文化馆馆长找她说:
你的穿戴要注意,干部最好穿正装,你这样别人会觉得不正经。
叶广芩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第二天全县开大会,叶广芩就穿着旗袍上了台,从那以后小县城旗袍盛行。
叶广芩打小就爱吃烤白薯,见了烤白薯非吃不可,县城里卖白薯的没有不认得她的。
县委办公室主任委婉地找到叶广芩说:
叶副书记,您有啥需要就对我们说,我们去给您办。
叶广芩意识到吃烤白薯的事影响了干部形象,第二天再见到烤白薯的,买了揣进怀里就往办公室跑,先吃白薯,再去医务室处理肚皮上烫出的大泡。
上上下下都知道她还在偷吃,但谁都窃笑不语了。
叶广芩在那里挂职是配了专车的,但一元钱跑遍县城的三轮车是她最得意的交通工具。
她嫌叫车等车浪费时间,从来自己坐三轮东跑西颠。
我说,你可真行,坐三轮,穿旗袍,啃白薯,真有咱北京姑奶奶的派——满不吝!
叶广芩写了一系列家族小说,其中《采桑子》曾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们给予很高评价,但终因这部作品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长篇小说的结构,评委们对这部作品能否称为长篇小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没能摘取桂冠。
《青木川》是叶广芩以她的第二故乡陕西农村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文字还是一以贯之地优雅和耐读,那淡淡的情调,优雅的文笔,回味甘长。
叶广芩是可爱的作家,优秀的女人,她把大家闺秀气、姑奶奶派、陕西婆姨劲儿糅合于一身,那叫一个和谐。
范小青这女同志
早就想写范小青,因为她是我的“酒友”。
可一提笔,黄蓓佳的样子就如影随行地在我眼前晃,她俩在中国数得上名的女作家中算是挺“养眼”的一类。
这两位江苏省作协的副主席不仅文学成就匪然,一个个杨柳细腰、袅袅婷婷不说吧,还“花枝招展”,最重要的是她俩都不扭怩作态,不装大尾巴狼,该啥样就啥样。
有一次,范小青乐嘻嘻对我说,我们俩都有“粉丝”啊,黄蓓佳的“粉丝”叫黄瓜,我的“粉丝”叫“饭(范)桶”。
有了范小青的如是说,我想到黄蓓佳就会想到纤细、清爽的“黄瓜”形象。
前些年我到南京,会后和范小青、黄蓓佳同桌吃饭,饭一开局,一拨又一拨人过来敬酒,敬到黄蓓佳,她微微欠起身,酒杯轻碰双唇,算是回应,再会劝酒的人到了她那儿也似乎没了词。
敬到范小青,人家酒杯没伸过来,她早早站起来热情地说:
干了吧!
刚清净会儿,范小青忍不住,歪着头与我们商量:
咱们去回敬一下吧。
其实范小青也知道我们不可能跟着“饭桶”去当“酒桶”,就自嘲地、一边走一边说:
我自己去吧,就这坏毛病。
看着她在各桌之间“热情酒溢”,我“气愤”地说:
范小青哪儿是“作协”的,分明改“足协”了,把自己当球往外踢。
范小青说自己是“饭桶”也不是瞎讲。
范小青和黄蓓佳常常一起出场,一桌美酒佳肴,人家黄蓓佳挑着精细的素食吃点儿。
范小青可好,见了美食决不嘴软,吃饱了举着杯飘然而去,喝得美滋滋踏云而归。
凡到这时我们大家都会被范小青一一拥抱,礼毕,她还可以挑着爱吃的再吃,那劲头儿就如同往饭桶里倒,急急忙忙像是补足了“给养”再去战斗似的,全然没了酒前苏州女人的精致优雅,也全然没了素日里的矜持与安静,一副“欲与酒公试比高”的男子气慨。
我说,你写小说真不比男作家差,可以和他们论论英雄,这种场合你就只能论雌雄啦,别跟他们叫劲儿。
范小青连声说,是啊,是啊,他们一点都不爽气,还是我主动先喝了,他们才喝。
我扭头和旁边的人小声说:
看范小青这样,小时候脑袋肯定摔坏过。
范小青眼睛朦胧了,听力不差,抓住我解释说,你说对了,我小时候狠狠地摔过一次,小学以前的事都记不住了。
听她舌头都不打弯的醉话,看着她喜气洋洋的模样,在座的一致认为,范小青小时候不是从棕床上大头朝下摔过,就是掉到“苏州河”里脑袋进了点水。
还有一次也是我到南京参加会议,报到后把行李放进房间就被朋友拉去喝酒,夜半三更回到房间,跌跌撞撞地去开灯,忽听有人嘻嘻发笑:
喝多了吧。
吓得我酒醒了一半,看看两张床都平平整整,人在哪儿说话呢。
嘿,本来就苗条得像柳叶似的范小青笔直地躺在床上,被子一丝不苟,里面跟没睡人似的。
定神一看,范小青没枕枕头,只枕了一件衬衣。
关了灯范小青还不停地笑话我,我问她,你的枕头呢?
她好像是说,因为天天趴在电脑桌上,有挺严重的颈椎病。
我说,傻了吧,那叫积劳成疾。
她说,不写更难受。
我笑她“痴”,她说我啥,我没记住。
反正谁也看不见谁,你一句我一句“瞎说”了半宿。
但她对写作的痴迷对文学的执著,由于她“低枕有忧”让我记住了。
第二天一早,我满房间找我昨夜不知甩到哪儿去的鞋,边找边问她,你这身份怎么混得跟我“同居”?
范小青呵呵呵呵地笑:
我昨天从苏州赶过来就很晚了,被塞在你的房间,能看看你酒后的样子挺好玩的。
我说,你看我现在赤着脚,就想起你笔下那个脑膜炎的赤脚医生万泉和了吧?
大不了你把我当“赤脚记者”,反正什么时代、什么环境就有什么产物。
范小青听出我“会意”了她新作《赤脚医生万泉和》里的那个笨得不称职的医生,所以她忽然显得比昨夜看我笑话还开心。
说心里话,我确实和她作品里那个“笨人”有共鸣,因为我也经历了那个有“赤脚医生”的时代,我喜欢范小青倾全部爱恨描写的那个“不正常”的人。
我对范小青说,你用一个脑子有毛病的赤脚医生的一辈子,把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几十年中的中国农村医疗问题以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带出来了,这让我觉得你聪明绝顶。
范小青听我夸她的作品,像小孩儿吃糖一样甜笑,真比我见别人夸她漂亮时高兴多了。
她说,你的感觉很对,要谈写小说,我是努力把生活化开来,小说应该将“政治”放在小说背后,只有人物是永远的,政治和历史在人物身上。
这是我们清醒时的对话。
后来的日子,范小青醉酒的“糗”事不时有捷报传来,听得我把耳闻当目睹似的高兴。
范小青为人随和,我们平日里联系不热络,但只要我张口,她不管多忙还是有求必应,耐心地回复和处理。
有一次中国作协开全委会,我带着还差十几页没读完的《女同志》在开会时读。
我对范小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