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师善诱法》清唐彪.docx
《《父师善诱法》清唐彪.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父师善诱法》清唐彪.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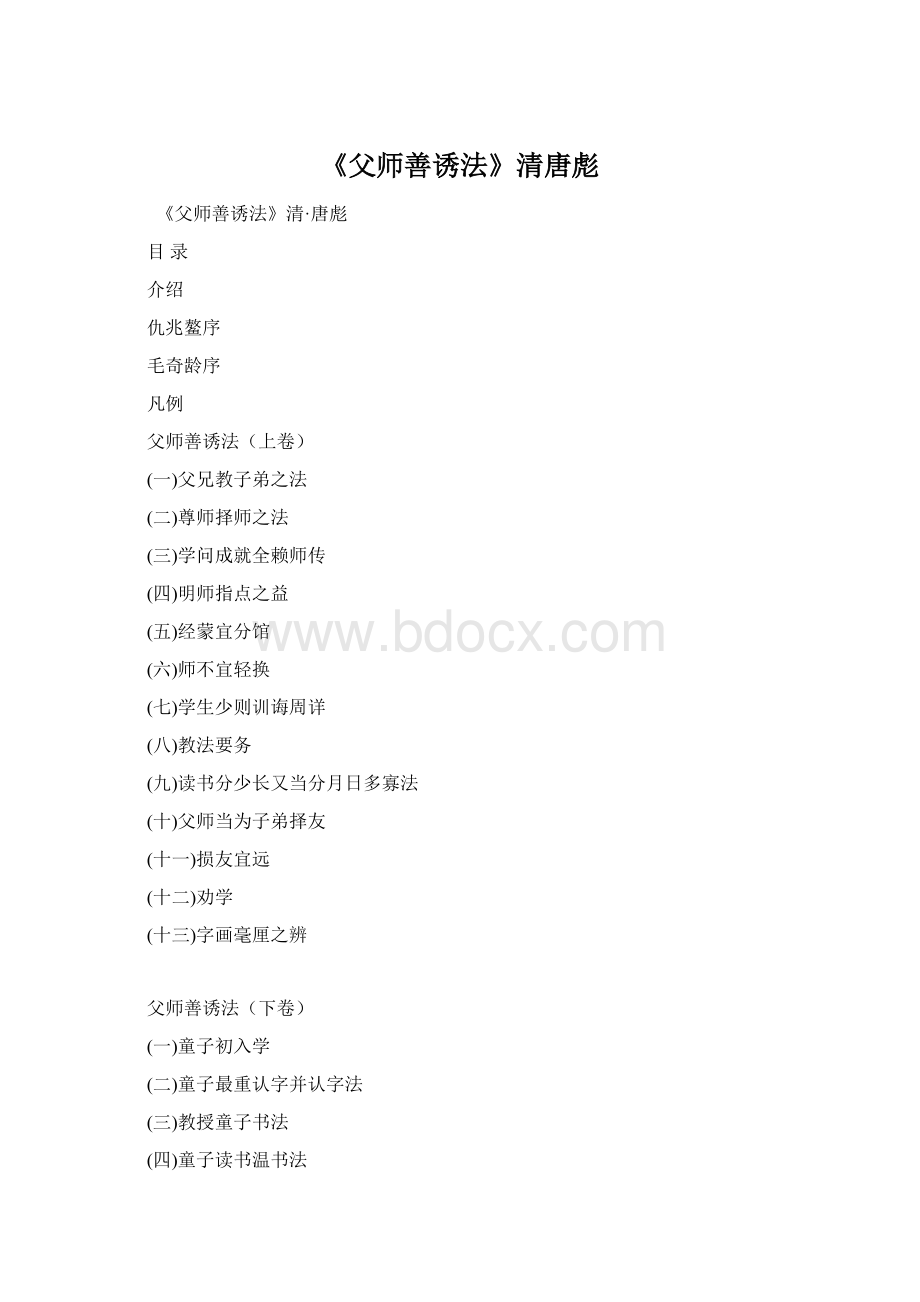
《父师善诱法》清唐彪
《父师善诱法》清·唐彪
目录
介绍
仇兆鳌序
毛奇龄序
凡例
父师善诱法(上卷)
(一)父兄教子弟之法
(二)尊师择师之法
(三)学问成就全赖师传
(四)明师指点之益
(五)经蒙宜分馆
(六)师不宜轻换
(七)学生少则训诲周详
(八)教法要务
(九)读书分少长又当分月日多寡法
(十)父师当为子弟择友
(十一)损友宜远
(十二)劝学
(十三)字画毫厘之辨
父师善诱法(下卷)
(一)童子初入学
(二)童子最重认字并认字法
(三)教授童子书法
(四)童子读书温书法
(五)读书讹别改正有法
(六)童子读注法
(七)附古人大文与注分读法
(八)附《四书》正文大注小注字总数
(九)觅书宜请教高明
(十)背书宜用心细听
(十一)读书总要
(十二)童子学字法
(十三)童子宜歌诗习礼
(十四)童子讲书复书法
(十五)童子读古文法
(十六)童子读文课文法
(十七)改文有法
(十八)童子宜学切音
(十九)教学杂条
附:
不习举业子弟工夫
附:
村落教童蒙法
介绍
清人唐彪,号翼修,浙江人,辑著有《父师善诱法》、《读书作文谱》、《身易》等。
唐彪初以《父师善诱法》名其书,合刻重印后则常称为《家塾教学法》,毛奇龄序中提到“其书旧名《家塾教学法》,吾愿受其书而求其法者”。
仇兆鳌序
古之养士者,习之以《礼》、《乐》、《诗》、《书》,而复娴之于射御书数,盖道德才艺,本末相须,而不可以偏废也。
今世竟尚文艺,而于《少仪》、《内则》、《弟子职》诸条,漫不加意,此人心所以日放而人材所以日降欤。
近经部议颁行朱子《小学》,俾童子有所取则,日孳孳于明伦正身、嘉言懿行,诚朝廷育才盛事也。
自此家读其书而敦本尚实,可谓得所先务矣。
倘于游艺一途犹然荒疏,涉猎不能竟委穷源,又安所得华国文章,振风会于日上哉?
此唐子翼修教法、书文谱二书之所由作也。
翼修金华名宿,胸罗万卷,而原本于道。
向者秉铎武林,课徒讲学,人士蒸蒸蔚起,其所著学规二书,详而有法,自延师受业以还,先令穷究经史,次及秦汉唐宋之文,莫不有条绪可依,而循途易致。
且于执笔临池,吟诗作赋,兼能旁通,曲畅其指。
而于制举之文,尤注意焉。
盖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
不汲汲于为文而文愈工,此唐子辑书之大意也。
今日学堂中诚得二书,以资教学,则文有根抵,不为一切影响恍惚之谈,其有功于文艺,不已多乎!
余谓是书当与《小学》并行,一则砥行饬躬,以养其德性;一则博学多能,以扩其才华,异日立乎庙堂之上,言吐经纶而文垂金石,则唐子之所以造就学者,又岂浅鲜乎哉!
康熙戊寅岁孟夏月甬江年家眷弟仇兆鳌顿首拜题
毛奇龄序
古者教子弟之法,师以三行,保以六艺,未尝专主呫哔课诵及授简橐笔之事,惟天子诸侯及乡大夫元士之适子,则有六书九数典文简策诸务,行于虎门,令其娴习之,以为他日用世之籍也。
今世则不然,学校之造士,文衡之选士,全以是物之优劣为进退,则又无分贵贱少长,皆为最急之务矣。
濲水唐先生献策长安,出为师氏者若干年,历东西两浙人文会萃之所,皆座拥臯比,令馆下诸生执经北面,其为三物六德兴起后学者,既已习之有素,且艺文灿然,见诸法则,所至省课诸生皆视效之,此真见诸行事,未尝仅托之空言者尔。
乃睥睨之间,拂衣归里,复取平时所为《读书作文谱》、《父师善诱法》二书梓以行世,其间讲求之切,择取之精,一字一注,皆有绳检,所谓哲匠稽器,非法不行者非与!
夫弓冶之后,必有箕裘,世家子弟,皆有承授。
先生席累世勋贤之裔,守其青箱,传之不坏,今即以其所世嬗者,公诸海内,盖不自私其美,而教化乃广大焉。
或疑先生以师保之尊,久历庠序,兴德兴行,归田而复取呫哔课诵之法,谆谆留意,似非要务。
尝读伏生《大传》及班掾《食货志》,知乡大夫归田,每出而为闾党师,谓之上老,终日居里门右塾,以掌诰诫。
先生之著二书,抑亦乡大夫居塾之遗情也乎?
故其书旧名《家塾教学法》,吾愿受其书而求其法者,由此渐进于诚正修齐,以为治平之本,安见二书不为大学之先资也乎!
康熙己卯季春月年家眷弟毛奇龄顿首拜撰
注:
橐音tuó
凡例
一、古人之言,有一篇合发数理者,难以混入一类,愚为之分析隶于各类之中,非敢轻为割裂,盖欲分类发明,不得不如此也。
一、天下之理有归一者,亦有两端者。
归一者易见,两端者难明,大舜、孔子每加意焉。
是书于古人之议论有不同者,必两存之,更为之分析其理,而斟酌取中,知偏见不可以为法也。
一、凡一人立言,不无遗漏,惟集众美补其欠缺,汇集成编,庶几详备。
故二书不欲尽出于已,而多引他人之言也。
一、凡书分类成卷,则事理会于一处,可以比拟而识其理之深浅,言之纯疵,存精去粗,所集之书始能简约。
二书初所集古人成语与自己所著共二十五万馀言,类聚一处,比其高下而删汰之,仅存九万馀言。
故欲书详备而仍简约,必不可不分类也。
一、凡书虽极明极浅,然初学必不能解,须父师为之讲明,乃能领略。
不然,虽列在案头,亦如无有二书。
虽不敢云佳,然颇有可采。
父师能破除俗见,虚心细阅,择紧要者另作标记,另加圈点,与子弟讲究,则读过经书,一经解说,便能触类推广,悟所未言,可省却数数讲求也。
至于文章,则不但易解,而且易做矣。
信如此,则讲解似属不可已也。
一、凡古人片言只字,必有所为而发。
殚思竭虑,始笔于书,引用其言,安可没其姓氏?
近见辑书者,一书之中,无非他人议论,而卷首但列己名,使未见原书者,竟以为是其所著。
噫!
窃人之长以为己有,盗名诚巧矣,亦思作者精灵不灭之神,岂肯甘心。
而冥冥之报密且严乎!
管登之曰:
“名根未尽,慎毋著书,人间之墨迹未干,天上之罪案已定。
”盖谓其以穿窬之心,行穿窬之事。
盗人学问才名,为上帝所深恶,玄律所不宥也。
愚于二书,凡引古人之言,或词晦、或语俚者,每为之润色,间有润色过半者,必仍列其姓名,不敢奄为己有也。
一、世风不古,坊间但见一书既行,即请人将书改头换面,挪东入西,或全偷,或半窃,或剿袭三四,称纂称辑,或称辑补,称纂著,没人之名,冒为己有,刻成庸陋之书,以欺世觅利。
不数年间,效尤叠出,原书面目杳然无存。
兴言及此,深可痛心。
二书不禁人之翻刻,但禁人之盗窃。
倘有蹈此者,无论目前后日与年代深远,必以盗窃鸣究,更将其盗名丑态著之于书,遍告四方也。
一、徐伯鲁《文体明辨》,毛西河、朱竹垞二先生俱谓不宜纂入书内,以其言多有未当也。
余悉改去之,纂其是者,取其有裨于浅学也。
父师善诱法(上卷)
(一)父兄教子弟之法
唐彪曰:
父兄教子弟,非仅六七岁时,延塾师训诲,便谓可以谢己责也。
必多方陶淑,于幼稚时即教以幼仪,稍长择明师与之斟酌尽善课程,某书为正课,某书为兼课,某书读毕,某书继之,文在其中。
通体定其正兼、先后,使确有成规可守,则所学自然允当矣。
更择良朋切磋夹辅,必不使亲近狡仆损友,导之以色声,并诱其嬉游博奕。
如此则子弟之学必有成,庶可谓克尽父兄之职也。
唐彪曰:
父子之间,不过不责善而已,然致功之法与所读之书,不可不自我授也,故孔子与伯鱼,亦有读《诗》读《礼》之训。
今怠忽之父兄,不能设立善法教其子弟,又不购觅好书与之诵读,事事皆委之于师,不知我既无谆切教子弟之心,师窥我意淡漠,恐亦不尽心训诲矣。
唐彪曰:
父兄于子弟课程,必宜详加检点。
书文间时当令其面背,文艺间时当面课之。
如己不谙于文,当转质之于人,始知所学之虚实也。
(二)尊师择师之法
唐彪曰:
富贵之家姑息子弟,必欲他人来家附学,不欲子弟外往,又多存尔我之见,与人稍不相合,明知其家延有明师,不屑令子弟从游。
甘心独请先生,不思一人独请,束修未必能厚,应请者未必名师,偶或名师曲意俯就,然终岁所入,不能给其一家之需,虽欲精勤严厉,尽心教迪,不可得矣。
故诚心欲教子弟者,必不可姑息子弟,更不多存我见,宜与亲朋联络,虚心延访,同请名师,彼此互相趋就,虽所居少远,往来微艰,不可辞也。
古人千里寻师,尚不惮远,何况同乡井乎?
唐彪曰:
人仅知尊敬经师,而不知尊敬蒙师。
经师束修犹有加厚者,蒙师则甚薄,更有薄之又薄者;经师犹乐供膳,而蒙师多令自餐,纵膳亦亵慢而已矣。
抑知蒙师教授幼学,其督责之劳,耳无停听,目无停视,唇焦舌敝,其苦甚于经师数倍。
且人生平学问,得力全在十年内外。
《四书》与本经宜熟也,馀经与后场宜带读也,书法与执笔宜讲明也,切音与平仄宜调习也,经书之注,删读宜有法也。
工夫得失全赖蒙师,非学优而又勤且严者,不克胜任。
夫蒙师劳苦如此,关系又如此,岂可以子弟幼小,因而轻视先生也哉!
唐彪曰:
子曰: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是师必以学问优为胜也。
今人第谓蒙师贵勤与严,不必学优,皆属偏见矣。
惟于三者兼备,乃明师也。
人无择师之识,欲为子弟择师,不宜止询一人,恐其人以所亲所友荐,或过揄扬,未必得实,必再加体问,果学优而又严且勤者,方令子弟从游,庶几其可乎。
又毛稚黄曰:
大抵举子业求正于先达最善,先达举业过来人也。
若为子弟择师,自己不能别其贤否,以其人之文质诸先达,先达赞其文,则知其造诣正矣。
此亦择师一法也。
(三)学问成就全赖师传
唐彪曰:
师之关系至重也,有孔子而后有七十二贤,有二程而后有三十高弟,有朱吕讲学于丽泽(书院名),而后金华诸贤哲后先相继迭出而不已,非得师成就之明验乎!
古人云:
得决归来好读书。
人亦曾细玩此言否也。
(四)明师指点之益
唐彪曰:
人之为学,第一在得明师。
明师不必同处一堂讲解经义、改阅文章者也,或经年一晤,片言数语指点大概,谓某经讲说好,某史评断好,某古文时文佳选也,不可不读,某古文时文庸选也,不必著眼,则一日指点,受益已在终身。
故明师不必同堂,亦有益也。
然宇宙之内,不乏名贤,时加廉访,必得其人。
千里问业犹嫌其晚,乃人或畏其名高而不敢近,或以地远而惮从游,或吝小费而不欲就正,宁甘学术卑陋,老死而无成。
呜呼!
此岂天之限人乎哉!
(五)经蒙宜分馆
唐彪曰:
予观少年,未尝无天资胜者,亦未尝无勤学者,然皆学问荒落,无所成就,因反复细思,而知其弊。
由于已冠、童蒙同一馆,而先生兼摄两项学徒也。
吾婺往时经蒙分馆,经师无童子分功,得尽心力于冠者之课程,故已冠者多受益;蒙师无冠者分功,得尽心力于童蒙之课程,故幼童亦受益。
今则不然。
经蒙兼摄,既要解《四书》,解《小学》,解文章,选时艺,改会课,又要替童子把笔、作对,写字样,教读书,听背书,虽有四耳目四手足者,亦不能矣。
况今时有习武一途,馆中或间一二习武者,更增解武经、选策论诸事矣。
而犹未尽也,先生与试者又要自己读书,则虽有八耳目八手足者,亦不得完诸课程矣。
于是先生尽置大小学生课程于度外,亦势不得不然也。
是以学生虽至二三十岁,或己进学,而本经未及解,安望其学有成就乎?
至于诸经、《通鉴》、古文诸要书,学生亦未经目睹可知矣。
然则为父兄者,欲教已冠子弟,必多方觅已冠之友为一馆;欲教幼童,多方觅幼童为一馆。
为人师者,亦当以成就学徒为心,倘得子弟课程完全,父兄亦必加厚束脩,得名得利,有何不美,而必欲苟且从事,使名利两失,且误人子弟哉。
(六)师不宜轻换
毛稚黄曰:
凡欲从师,始须加慎,如既得其人,则不可轻换,数换师者烦而鲜功。
盖彼此习业章程互异,而后师亦多翻前师之案以自见长,纷更不一,将使学者工夫愈纷错也。
古人每一师以终其身,虽千里负笈而不惮远者,良为此也。
(七)学生少则训诲周详
唐彪曰:
塾师教授生徒,少则工夫有馀,精神足用,自然训诲周详,课程无缺,多则师之精力既疲,而工夫亦有所不及,一切皆苟且简率矣。
故生徒以少为贵也。
虽然,生徒既少,必当厚其束修,使先生有以仰事俯育,始能尽心教诲,不至他营矣。
(八)教法要务
唐彪曰:
教法严厉,乃至烦苦之事,实先生所不乐为。
然先生欲求称职,则必以严为先务,不然,学问虽优,而教法过于宽恕,使弟子课程有缺,终非师道之至也。
唐彪曰:
凡书随读随解,则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有所开悟。
若读而不讲,不明其理,虽所读者盈笥,亦与不读者无异矣。
故先生教学工夫,必以勤讲解为第一义也。
唐彪曰:
凡同馆所读之书文,一半相合,则诸人可以同解同听,先生自然工夫有馀。
若所读之书文人人各异,每人需一番讲解,则不特先生工夫无暇,却力量亦有所不及。
然此必先生虚心细察,与有学识者商量,确知何书何文当读当解,宜先宜后,确有成见,然后使学生课程不甚参差,庶几讲解简省,而学生受益多也。
唐彪曰:
先生教童子之法,其根基全在正二月间,此时宜屏绝外务,专心致志开导督责,令学生读书字句分明,课程悉循法度,此后训诲工夫俱易为力矣。
又曰:
学生前师手中所读之经书全不成诵者,后师多不令其温习,此甚非教诲之善法,亦非忠厚长者之道也。
必也于初入学时,悉令其开明前此读过之书于每册中,或令学生背半或令背三分之一,以验其生熟。
《四书》本经半日皆可背毕,甚不费工夫,不当以难视之也。
生则先宜令其温习,不必授生书。
一则能知学生之底蕴,则教诲易于成功;二则可免不肖子弟避难就易,止温其熟者,竟置其生者,以致长大经书不能成诵;三则经书既熟,可免学生终身之怨;四则我乐补前师之所不足,后日之师亦必乐补吾之所不足,此又感应必然之理也.唐彪曰:
教法严厉,乃至烦苦之事,实先生所不乐为。
然先生欲求称职,则必以严为先务,不然,学问虽优,而教法过于宽恕,使弟子课程有缺,终非师道之至也。
唐彪曰:
凡书随读随解,则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所开悟。
若读而不讲,不明其理,虽所读者盈笥,亦与不读者无异矣。
故先生教学工夫,必以勤讲解为第一义也。
唐彪曰:
凡同馆所读之书文,一半相合,则诸葛亮人可以佩解、同听,先生自然工夫有馀;若所读之书文,人人各异,每人需一番讲解,则不特先生工夫无暇,却力量亦有所不及。
然此必先生虚心细察,与有学识者商量,确知何书何文当读、当解,宜先宜后,确有成见,然后使学生课程不其参差,庶几讲解简省,而学多益也。
唐彪曰:
先生教童子之法,其根基全在正二月间。
此时宜屏绝外务,专心致志,开导督责,令学生读书字句分明,课程悉循法度。
此后悉循法度。
此后训诲工夫俱易为力矣。
又曰:
学生前师手中所读之经书,全不成诵者,后师多不令其温习,此甚非教诲之善法,亦非忠厚长者之道也。
必也于初入学时,悉令其开明前此读过之书,于每册中,或令学生背半,或令背三分之一,以验其生熟(四书本经半日皆可背毕,甚不费工夫,不当以难视之也),生则先宜令其温习,不必授生书,一则能知学生之底蕴,则教诲易于成功;二则可免不肖子弟避难就易,只温其熟者,竟置其生者,以致长大经书不能成诵;三则经书既熟,可免学生终身之怨;四则我乐补前师之所不足,后日之师亦必乐补吾之所不足,此又感应必然之理也。
此项系为师者至要工夫,不可忽视也。
唐彪曰:
夫子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父兄苟不购觅好书与子弟诵读,先生必宜再三开导鼓舞之,令之购觅,无刻本者必宜令其借抄。
不然,当读者既无其书,将以何者为资益学问之具?
此实先生必不当漠视者也。
(九)读书分少长又当分月日多寡法
唐彪曰:
童蒙初入学,先令读《孝经》、《小学》,继读《四书》本经。
如资钝,或父师教无善法,本经读毕,年已长大,不得不读时文,以图进取,馀经俟文艺明通后补读可也。
如资颖,本经读毕,年尚幼冲,则当如古人分月用工之法,以一月读诸经,一月读时艺,读文读经,每日俱当带三进或五进,每进当加读遍数,如幼时带书之法始佳。
每日带记表判,或记诗。
俟时艺读少充,再将经与史分月读之,古文与时艺分日读之。
所以宜如此者,以时艺多虚词,经史乃实义,惟胸中有实义,乃能发为虚词。
又古文法详笔健,远过时文,故读经史古文,则学充识广,文必精佳;不读经史古文,则腹内空虚,文必浅陋。
且经史之益,更在身心,读之其用又不止于作文已也。
人之不读经与史者,每汨没于多读时文,若不多读时文,自有馀力及诸经史,其理固甚明也。
徐聚五曰:
近见习举业者,本经之外,馀经皆用删读法:
《尚书》删十之二,《诗》、《易》删十之三,《礼记》、《春秋》删十之五。
虽不应如此,然举予以取功名为急,力不能多读,势不得不从乎简乎简约也。
唐彪曰:
子弟七八岁时,正课之馀,宜令读判。
其读之法,一判日读十遍,期以十日之后始背,必能成诵,数年诸判可读毕矣。
继此又当读表,一表日读三遍,期以一月后始背,必能成诵,数年诸表可苟完矣。
至于温法,则三日一判,十日一表,循环温习,未有不记者。
凡事刻期求熟则难,纡缓渐习则易。
且幼时记性优,能永记,乘时早读,至为良法。
况读此则平仄明,音调熟,诗赋之理半在其中矣。
策论读法,亦当推此行之。
(十)父师当为子弟择友
唐彪曰:
人知成人之士,咸赖朋友切磋,而不知童蒙无知,尤须朋友训诲。
如一馆之中,得一勤学学长,先生工夫精力不及之处,学长少佐助之,则诸生多受其益,而每日之课程皆不虚然。
此学长非先生与父兄有心招致之,恐不能得也。
(十一)损友宜远
唐彪曰:
一堂之中偶有一极不肖弟子,或博奕纵饮,或暗坏书籍,或离间同堂,或己不肯读书,而更多方阻人致功,一堂之中皆为其扰乱。
子曰:
“毋友不如己者”,不如己者尚宜远之,况如此之甚者乎!
为父兄者,当时加觉察,如有此,必宜求先生辞之。
父兄或不知,同堂之士宜会同上白父兄,转求先生辞之。
不然,宁避之而他学,盖所害不止一端,不得不远之矣。
(十二)劝学
《迪幼录》曰:
“凡事乘少年鞭功,事半功倍,年过二十,功倍而效止半矣。
”陈白沙曰:
“今人姑息自恕,不思进学,乃谓过今日尚有明日,殊不知过一日无一日也,徒至老大而伤悲,岂不晚哉!
”
郭开符曰:
维昔之人笃志好学,囊萤映雪,何惜阴若此;悬梁刺股,何牢苦若此。
今有明窗净几之乐,而无负薪挂角之劳;有朝饔夕飧之供,而无三旬九食之苦。
昼则宴游,夜则鼾卧,嗟嗟!
白驹过隙,老大徒悲,追悔壮龄,恨无及矣。
《警枕书》曰:
“有志之士,纵不能日新,犹当月进,不能月进,犹当岁益。
”
柳屯田《劝学文》云:
“父母爱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
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
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
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
徐白谷曰:
骐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枥而不驰,则蝼蚁过之矣。
鹍鹏天下之捷飞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奋,则鹪鹩过之矣。
士之当学,何以异是。
诸匡鼎曰:
匡衡好学,邑有富民,家多书,衡为之慵作而不取其值,日愿借主人书读耳,遂得博览群书。
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抄写,每日自课必五十纸,纸数不足则不止。
予谓古人贫而好学,或慵作借读,或假借抄写。
每见今之世家子弟,家藏书籍汗牛充栋,而狗马声妓饮博交游之好,往往从而闻之,四子之书经年不及一披览,真可叹哉!
丁菡生曰:
徐广好读书,年八十犹岁读《五经》一遍。
若夫少年,经书一岁尚不能周,可愧极矣!
张师云:
有家务人,当择古文一册,时艺一册,经书二册,偷闲便读一过。
若期拟闭户一月二月,一意读书,如何能得。
恐“期拟”二字,瞬息间又了一年也。
丁菡生曰:
记性日拙,家事日多,三复斯言,仰天浩叹。
注:
饔音yōnɡ飧音sūn嗟音jiē戢音jí鹩音liáo
(十三)字画毫厘之辨
字画之辨,介在毫发,形体虽同,音义迥别。
揭其相似者并列相形,俾一目了然,庶免鲁鱼之谬矣。
父师善诱法(下卷)
(一)童子初入学
王虚中曰:
六岁且勿令终日在馆,以苦其心志,而困其精神。
书易记、字易识者,乃令读之,其难者慎勿用也。
初间授书四句,若未能尽读,且先读前两句,稍熟令读后两句,稍熟然后通读四句。
初时如此,日久则可以不必矣。
(二)童子最重认字并认字法
唐彪曰:
凡教童蒙,清晨不可即上书,须先令认字,认不清切,须令再认,不必急急上书也。
何也?
凡书必令学生自己多读,然后能背。
苟字不能认,虽欲读而不能,读且未能,乌能背也?
初入学半年,不令读书,专令认字,尤为妙法。
唐彪曰:
先生教读书不过五六遍,至多不过十馀遍止矣,而童蒙心散,不会用心,先生教彼时,彼心已不在书,不过随先生之口述而念之。
资性钝者,既到案头,一句且不记,任先生催促,彼终不读,非不欲读也,不识字也。
在童蒙幼稚无知,但畏书之难读,疾书如仇,而不知由于不识字之故,在先生更不深思,但咎学生之顽拙,骂詈仆责交加。
而不知由于己不教令识字之故。
噫!
所谓方枘音锐,榫也圆凿孔也,两不相入也。
若先教令认字,字既能认,虽教三遍四遍,彼到案头,亦能按字口诵,读至百遍外,虽甚拙者,亦能记能背矣。
唐彪曰:
余子正心,自六岁入学,因书不成诵,三岁历三师,至四年无可如何,不复易矣。
其岁则甲寅也,因兵乱避居山中,适有朱雨生设帐其地,因令就学从游。
至五月,所读新书不减于前三载,且于前三载不成诵之书,无不极熟。
彪敬问其故,答曰:
“吾无他术,惟令认字清切而已。
令郎非钝资,止因一二句中字认不清,故不敢放心读去,则此一二句便不熟。
因一二句不熟,通体皆不成诵矣。
”又尝试验之,童蒙苟非先生强令之认字,必不肯认。
认过而仍忘者,苟非强令之来问,必不肯问。
止皆先生所当知者也。
彪思读书在认字,甚为浅近,何以前三师皆见不及此,乃知甚明之理,未经人指出,未易知也。
唐彪曰:
教童蒙泛然令之认字,不能记也。
凡相似而难辨者,宜拆开分别教之。
......如戍戍臣臣微微之类。
凡见易混淆之字,即当引其相似者证之,曰此宜分别熟记者也,如此始能记忆,无讹误遗忘之患矣,此教认字之法也。
更有令彼复认之法:
将认过之字难记者,以厚纸钻小隙,露其字,令认之;或写于他处令认之。
倘十不能认六者,薄惩以示儆,庶可令其用心记忆云。
注:
詈音lì
(三)教授童子书法
唐彪曰:
教授童子书,遍数虽少,无害也,但宜极缓,令童蒙听得句句分明,看得字字周到,到案头未有不能读者。
若授之急疾,如自己读书之状,学生不但眼看未到,耳听亦且未明,勉强随声,既不知字句为何物,安望其到案间能自读也。
唐彪曰:
每见童蒙读书,一句之中,或增一字,或减一字,二段书或上截连下,或下截连上,此皆先生未曾与之讲明句读与界限道理,以致学生颠倒混乱读之。
若先生将句读道理讲明,则自然无增字减字之病;将界限处用硃笔画断,教令作一截读住,则自无上截连下、下截连上之病。
又有极长之句,原不可加读点,但学生幼小,念不来,亦须权作读句加读点,则易念也。
一册书中,定有数处至难念者,然能知其中有界限,有差别,则亦易读。
苟不能知,纵读多遍,亦不成诵。
如“子路问闻斯行诸”一章,每见童蒙读此章,多混乱不清,因不能记。
为先生者,遇此等书教读时,宜细细开示学生:
前是夫子教由求之言,次是公西华问夫子之言,后是夫子教公西华之言。
第一界限是“闻斯行之”止,宜划断作一截读住;第二界限是“敢问”止,宜划断作一截读住;第三界限是“故退之”止,宜划断作一截读住。
又如“知虞公之不可谏”一节,原分六段,有六界限,可指划断作六段读之,自然易记。
苟不分清,求其不错乱也难矣。
差别者如两孟书中,“五亩之宅”凡三见,而三处字句不同;“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一章,万章述问与孟子所说,字多不同;“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一章,舜荐禹之辞与禹荐益之辞,文义大段同而字多不同。
此等不同处,有学识者方能分别,在童蒙则不能,愈读愈乱,不开示之,无由明白,开示之,自然易读易记矣。
(四)童子读书温书法
屠宛陵曰: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
量其资能读二百字者,止可授一百字,常使精神有馀,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唐彪曰:
古人读书,必细记遍数,虽已成诵,必须满遍数方已。
故朱子云:
“读一百遍时,自然胜五十遍时;读五十遍时,自然胜三十遍时也。
”
唐彪曰:
欲学生书熟,必当设筹以记遍数,每读十遍令缴一筹。
一者书之遍数得实,不致虚冒;二者按期令缴筹,迟则便可催促督责之;三者筹不容不缴,则学生不得不勤读,以早完课程。
殆一举而三善备矣。
唐彪曰:
凡幼学,本日所读书但随其资之高下,令读之若干遍,必满其数,能背固佳,即不背,亦可次日加读若干遍,亦必满其数始背,背毕,将二日前书加读若干遍,三日前书加读若干遍,均令满数,然后总背。
生则示儆,讹别字以角圈标记之,然后授生书。
此读书带理书之法也。
凡书倩朋友先背,后送先生背,则纯熟而无讹误生涩矣。
资有高下,授书有多寡,故遍数之繁简,宜因人而定,不能尽拘一例。
斟酌变通,必使与资相合,方善也。
王中虚曰:
凡书中有难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