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应该用重典.docx
《乱世应该用重典.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乱世应该用重典.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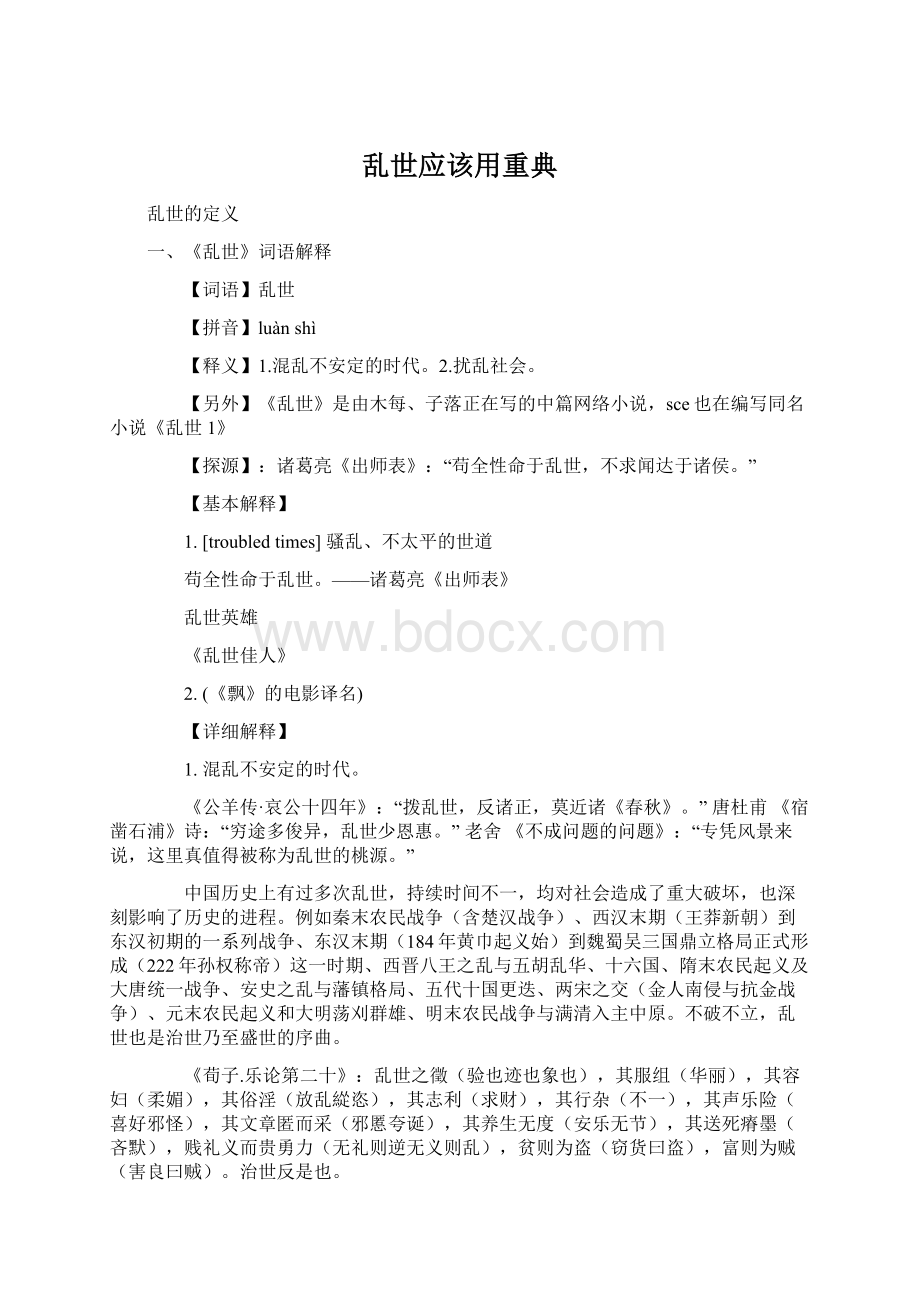
乱世应该用重典
乱世的定义
一、《乱世》词语解释
【词语】乱世
【拼音】luànshì
【释义】1.混乱不安定的时代。
2.扰乱社会。
【另外】《乱世》是由木每、子落正在写的中篇网络小说,sce也在编写同名小说《乱世1》
【探源】:
诸葛亮《出师表》: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
【基本解释】
1.[troubledtimes]骚乱、不太平的世道
苟全性命于乱世。
——诸葛亮《出师表》
乱世英雄
《乱世佳人》
2.(《飘》的电影译名)
【详细解释】
1.混乱不安定的时代。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唐杜甫《宿凿石浦》诗:
“穷途多俊异,乱世少恩惠。
”老舍《不成问题的问题》:
“专凭风景来说,这里真值得被称为乱世的桃源。
”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乱世,持续时间不一,均对社会造成了重大破坏,也深刻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例如秦末农民战争(含楚汉战争)、西汉末期(王莽新朝)到东汉初期的一系列战争、东汉末期(184年黄巾起义始)到魏蜀吴三国鼎立格局正式形成(222年孙权称帝)这一时期、西晋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十六国、隋末农民起义及大唐统一战争、安史之乱与藩镇格局、五代十国更迭、两宋之交(金人南侵与抗金战争)、元末农民起义和大明荡刈群雄、明末农民战争与满清入主中原。
不破不立,乱世也是治世乃至盛世的序曲。
《荀子.乐论第二十》:
乱世之徵(验也迹也象也),其服组(华丽),其容妇(柔媚),其俗淫(放乱緃恣),其志利(求财),其行杂(不一),其声乐险(喜好邪怪),其文章匿而采(邪慝夸诞),其养生无度(安乐无节),其送死瘠墨(吝默),贱礼义而贵勇力(无礼则逆无义则乱),贫则为盗(窃货曰盗),富则为贼(害良曰贼)。
治世反是也。
2.扰乱社会。
燕谷老人《续孽海花》第四七回:
“他曾经弹劾过强学会伪学乱世,所以反对主张变法的人.”
乱世用重典
释义
1.[crueltorture;severepunishment]:
严厉的刑律(区别酷刑与苛刑)
如治乱国用重典2.[importantclassics]:
重要的典籍
"乱世用重典"基本信息
“乱世用重典”,“乱世”是指中国古时各朝代社会出现凌乱及差劣局面的情况,与“盛世”相反;“重典”是指严苛的惩罚。
全句指,为了整顿好社会上凌乱的局面,迫不得已唯有使用严苛的惩罚。
而整体上,“乱世用重典”用于社会上的定义为,透过严苛的法律效果惩罚犯罪,来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
最常被举到的例子是,“日治时代,台湾的治安很好,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不用关窗户”,就是因为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和强而有力的警察制度。
理论基础
基于应报思想,任何有同理心的人,对于犯罪者造成受害者和受害者的亲人的伤害有所体会。
当伤害是如此深刻难以磨灭时,为什么反而对犯罪者如此宽大,难道不该给这些犯罪者应得的惩罚?
当社会情势混乱的时候,采用较重的刑罚比较容易达到威吓的效果,进而降低犯罪的比率以实现稳定重建社会秩序的目的的。
批评与反思
从技术层面:
乱世用重典,强调透过威吓的法律制度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是那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而且过度地依赖法律制度,代表一厢情愿地认为法律制度不会有缺失、不会有疏误的可能,当警察抓错人、法官误判、冤狱发生的时候,透过重典只不过是凸显政府治理社会的失责,并且使得冤狱变成难以挽回的遗憾。
从政府权利过大的流弊层面:
受害者与其家属固然值得同情,但是重典不是协助他们的合适方式。
如果我们期待政府,可以效率地、有力地、明智地抓到真凶,但是给予政府过大权力,往往适得其反,并且反过来箝制人民思想自由或是透过监控系统侵犯个人隐私。
重典治国论
重典治国论
传统社会以降,“重典治国”在各朝不同时期备受统治者青睐,似乎成为稳定政治经济局面,实现长治久安惯用且重要的政治运行和法制工具。
但重典治世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往往难以完成统治者的决策预期,收效了了,最终难以逃脱成为历史陈迹的命运。
在认清辨明重典给传统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的同时,不应妄自断言仅是法典之严苛性造成了社会动荡,阻碍了社会进步的步伐。
反之,应当透过制度体表剥离并审视导致重典失效的权力结构、社会文化氛围、法文化为背景等要素群体,反思而进取,此乃是国人不可偏废的重要任务。
传统社会以降,历代统治者依赖“以刑为主”的东方本土式法制路径,而“重典治国”现象在各朝不同时期也备受青睐,似乎成为稳定政治经济局面,实现长治久安惯用且重要的政治运行和法制工具。
而由中国特有的政治、法制土壤所孕育的“重典论”,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具备的意蕴是有差别的,对社会的作用力也趋于殊途。
剥离纷繁的表象,抽取各式重典背后承载的法文化,“重典论”思潮似乎也并没有随着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更新换代而彻底消褪,却成为隐性的法制因素,供给着目的论化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着国人今日的法治进程。
故而,在不断辩证借鉴、汲取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思想经验,兼顾吸纳国外优秀法律制度的今天,归纳、总结重典治世所发挥之效用,使之浮于水面,愈加明确化,继而认清利弊,抽取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扶正法治化轨道,乃是国人不可偏废、僭越的社会工程。
一、重典治国理论之解构
(一)重典论之源流概要翻阅中国历史,即可发现“重典治国”理论拥有厚重的人文底蕴。
上古伊始,发端于礼、刑之中国法,在刑始于兵,刑、法并无二致的年代,实则反映着一部古人类社会群落逐步发展壮大的演化史。
国家产生后,统治者为建立统治,维持秩序,启用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之道:
邢之目的即为树立权威,使“民不敢犯”[2],“禁奸止过”以确保有条不紊。
从人类演进学的角度审视法源于刑之事实,也能窥见人类发展史乃至法律制度发展史的诸多共性。
但中国法之流变有其自身的轨迹。
重刑亦非万能,当鉴于史上因滥施刑罚适得其反,遭至民众反抗而湮灭统治权的事例,统治者蹒跚般学会,应在可控的范围内掌握权力行使的适当性,提出了以轻刑、仁政为表征的“以德配天”、“德主刑辅”、“一准乎礼”“礼法合一”的施政方针,缓和了阶级矛盾,为国家政治较为安定、经济得以渐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创造了有利的成长期,达到盛世。
但是“约法省刑”之国策并非彻底游离于重典论设置的框架之外独立生存。
于此相反,由于中央国家的形成从始便依靠着集权化的政府万能主义,决定了盛世亦当在此框架项下适度发挥而变形、衍化——其始终不能也不愿摆脱“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的行为范式,遵守“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5]之法则。
看似重典论在法则中位居下位,然而其在较短时期内针对特定对象或为实现特定目标,从重从快,善于高速营建起“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的初始局面,在稳定秩序方面,拥有毋庸置疑的高效性和合目的性,以至于可作为实施其他后续统治行为的有力保障……这些均是轻、中二典在“运行——收益”坐标系中考察时间占用、整体行为效率上无法比拟的。
是故,重典治世绝非单纯仅在“乱国”发生,而有着更广大的作用空间和运行范畴。
(二)传统社会重典治国理论之解构在对重典治国理论进行实践考察,剥除历代对重典不一的执行理念或表达方式,寻找其中共性时,实则在明确两个概念:
重典面向的对象群体和“重典”概念本身。
其一,重典面向的对象群体。
学者指出,古中国所谓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即官僚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简言之,系由公权力国家行政执法规则和相应治理罚则构成的制度体系。
其始终难以超脱“法自君出”、“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模式,生长出如同西方那样弱化集权条件下独立完备的私法系统。
造成此种局面,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也自然非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但必定成为考察重典治世效用时不可或缺的历史土壤和理论基石。
中国法制结构决定了法制之锋芒为“士制百姓于刑中”:
通过对统治者治下的社会下层进行公法为主要形式的法律约束达到治世的目的。
但这并不是说,国人不曾受到统治者施加的私法色彩法律准则的控制。
自古便存在的“家族法”、民事习惯,为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而推行的官办、督办经济法律制度,经济发达时期培育的民事法律大量出现,在推翻有学者认为中国“无私法”论断的同时,确也说明这些法律措施相较刑事公法而言,不太能淋漓尽致的展现古中国法的特点。
故而,“夫法,所以兴功惧暴也”[9]的“典民”结论即定,统治者所关注的刑控社会下层对象,自然为广大的底层人民,以及为其所用的庞大行政官员机构、被皇权所弃不予保护的贵族群体等(在本文考察中可视为微量化特殊对象),而对最为底部百姓的操控,很多时候是在对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过程中完成的。
易言之,高位统治集团以法治官,打造较为高效的官僚结构便能实现统治目的。
若假设统治者单纯要求重典在适用于底部群体时达到“禁暴止奸”之效果,而由于官僚实质上也应归属于统治集团,便在适用法律时会产生与适于民众有别的效果,则对重刑结果的追求也会不再纯粹。
其二,重典之界定。
传统社会末期,统治者对封建法度的意义作有如下总结:
“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
而其中“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可达到“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之功效。
似乎重典所传达出的意味仅停留于严刑峻法、用刑苛重,能够从刑种的严酷和刑度的不着边际来体会。
实际上,要准确给“重典”下一个定义,应当首先建构于整个法律体系层面,顾及其应当具备的下列特征:
1)其体系严密,适用领域深广,并经过历代不断修正而得到完善发展。
以刑事法为例,不论上古,且从先秦战国时代之始奴隶制五刑以降,经历后世各代“轻刑”之改革而达成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再到封建社会中后期部分苛刑的复兴及至滥用、重新入律,形成了体制严谨、“疏而不漏”的宏观体系,甚至甚多行政、民事法律责任都会被施以刑罚制裁,如唐律中有“凡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的规文。
后世欲了解各代法律制度及政治经济环境,大致也可从所立刑罚和具体规文中窥视一二。
2)其成文法范式呈现严苛性,同时存在大量特别“法”细胞,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弹性。
奴隶制五刑之严苛被逐步改良而更新为封建制五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人类蛮荒时代具有的同态复仇、肉刑充斥的现象,代之以较为文明的刑罚,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但其中依旧保留了“罪人以族”、充军、刺字、枷号等罪,明清时代更以凌迟入律,彰显了传统重典的严酷性特征。
同时,肉刑残余在一定时期以镇压、整肃、争权为目的被滥用而肆虐兴盛,但往往不存在成文的法律依据,被归为法外酷刑。
但因注意到法自君出,大体也可将其视作某种意味上的特别“法”,只是缺失了常规法律制度所应具备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被赋以较大的伸缩性和随意性补充了重典实施的威力。
其弹性还表现为,存在大量同罪异罚的情形构成重典体系中较为重要而特殊化的组成环节:
按受罚主体待遇的迥异程度可将此环节作一二分:
一方面被免除部分乃至全部的法律义务,诸如赎刑之适用;另一方面则可能承担重于律文规定的刑罚,抑或被施以特别“法”所定的极端刑罚。
3)其类型繁复,具有强烈的合君权目的性,决定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具不同的内涵,并伴有些许理想主义色彩。
依据制定和运行重典的统治需要不同,区别出即如学者归纳的几种模式:
极端重典主义、重重轻轻主义、相对弱化重典主义及其他特殊化重典主义[12]。
极端重典主义以秦朝刑法为典型,以繁于秋荼而著名于史。
重重轻轻主义以北宋中期颁行重法地法和“盗贼重法”、明代相较汉唐法制的“重其重法、轻其轻法”的刑法特点为代表。
相对弱化主义则以主张“约法省刑”为代表,刑罚中正,多出现于国家初创或社会经济遭受重大破坏,需要长久时期修养生息之时。
至于特殊化的重典推行,不宜归纳为上述任何一列,多是统治者为达到某种目的、由个人好恶及注意力之转移而发生,诸如明太祖时期颁行《大诰》、重典治吏,便具有强烈的政治整肃目的。
同时,统治者通过施用重典欲达到社会秩序长治久安,万世为君的目的在史上不乏个别,惩治奸党、屠戮权臣,往往渗透了许多道德衍生的理想主义情调,而大多却事与愿违,此留待后文详述。
故而,由上可以简单描绘出有关传统社会重典的轮廓:
即一种为实现统治目的服务,依据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理想化设置而架构的,以统治权治下所有社会群体、机构建筑为施用对象,运用刑事法律为主体并结合特殊化制度工具所形成的全社会严密、灵活而具备相当弹性的法律制度体系。
二、重典治国理论之效用考察与合理性分析
(一)重典论之效用考察本文给出的重典论之意义界定系以整个传统社会法制结构的发展承继为背景,就某个历史时代为考量目标,由于统治者对重典的理解正如上文中学者给出的诸多分类方式那般所异,其欲施用达成的目的也有不同,从而在后世对重典论的绩效考察过程中,需要略作抽样区别。
从较为狭隘的范畴入手,中国传统社会传承的人治氛围里,历来将开明专制主义奉为经典兴国政策,重典适用也自是以较为低级化的工具姿态非独立性存在于此制度土壤之中。
故而,欲对重典制度的绩效得出相较合理与理性的结论,必须首先区分出较为适合开明专制统治生长的政治经济条件。
作为既成事实,今日对重典的分类方式便在社会形态的选取中比作相应参照系。
亦由此,上述分类中较为明显的,如同有秦一代等典型的极端重刑主义在考量该理论效用时,予以参照似属不妥。
其次,相对弱化重典主义以使国家修养生息为立足点,多为修复脆弱的自然经济而设立。
统治者总结历史,普遍考虑到暴刑荼重致使民众反抗、社会动荡,给统治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后适度反省,能够识知“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此环境中,重典用为上层建筑,由其本身性质与较为脆弱的社会资源条件相左,决定了其不宜作为长久制度存在。
于是乎当约法恤刑,弱化对广大民众适用的重典因素。
此种政策多发于封建国家权力初创但保有较强的统治力,抑或公权力所能调配的社会资源数量尚处于上升趋势中的时期,经济政治制度本身还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通过法制变革易于释放被前不合理桎梏所封闭的发展动力。
此种重典制度的推行,一方面使得民生得以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易导致在重典治理对象中,可能对官僚群体的监控力度松散不足而日益滋生并加速此群体的溃烂。
在此也应说明的是,在传统社会中盛行的诸如“八议”、官当、请、减、赎、免等制度,并非统归于相对弱化主义,正如上文所提及,是重典制中较特殊的同罪异罚环节的组成部分,它具有对重典制度的较强“离心力”,但囿于皇权权威的维护始终未能游离,但确对重典所达之效用有抵销之反作用。
这样一来,衡量重典治世绩效较为上佳的样本,即剩下区分对象的重重轻轻主义和特殊化重典主义。
重重轻轻主义重典模式有着纵横二向有别的不同意域:
从纵向而言,以规范性法律文件传承的角度,指出后世重典较前期规文在适用对象和程度上的区别,这是历史差异的显示,如有明一代较唐律所作出的改进;从横向而言,是对当期使用法制时对象和程度的差别性规定。
易言之,即同罪异罚环节中扩大受动主体承担义务的可能性部分,即如宋代“盗贼重法”“重法地法”之推行。
传统社会笃信“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北宋时期,由于立国未经过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改革、外患深重、加强中央集权而形成的冗官弊政等因素,客观上塑造了一个阶级对立相对严重的时代,以至于统治中期便较早的开始显现危机,盗贼之患即是表征之一。
对此,由北宋仁宗嘉佑6年始历经英宗、神宗、哲宗三代以恶治恶、加重打击贼盗力度而扩大施用的重法地法、盗贼重法等,依据今日传世的大料史料,似乎其从未能有效发挥统治者预期的治理效果。
不但如此,还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社会混乱。
如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京东、河北盗贼不禁,至白昼杀人于市,攻略镇邑,执缚官吏”;元丰年间(1078-1085年),李常知齐州,“齐多盗,论报无虚日”,在其治下,“盗贼遂清”。
而到哲宗末年(1086-1100年),齐地“群盗昼掠涂巷”……即便在京都附近,“盗贼充斥,劫掠公行”,作为执法主体的军队、官员多是“势力怯弱,与贼不敌”,“纵能告捕入官,其余徒党辄行仇报,极肆惨毒,不可胜言”。
特殊化重典模式之特异,在于其非但不能彰显统治者所谓“审慎刑罚”,也不是出于如同北宋王朝那样严酷的统治环境,导致统治集团“被迫”推行严酷的法度,整肃社会秩序——决策者在主客观方面都未遭遇“窘境”。
客观上,其时常处于较为安定的统治时期,甚至万象更新、盛世之状初见端倪;主观上,决策的制定并非外部因素推动的应激反应,而很大程度上是己身深思熟虑的结果。
更确切地说,是依照自己的人格信仰和对自己利益的检讨。
此种模式时常被筛选出的例子,即明太祖重典制贪之几十年风云历程。
亲历社会底层疾苦的明太祖,对元末官员贪渎、政治腐败而遭灭亡感触颇深,故严厉法度,重典治贪,对封建官吏的严罚可称空前绝后。
最为重要的是,其空前的完成了将久已存在的、体现各代统治者严苛色彩的法外酷刑即特别“法”因素转换为真正意义的制定法模式,使传统社会的重典体制更加完备化,尽管这些成文法实际发生效力的时间极为短暂。
但应看到,终洪武之世,其也未能助太祖达成事先所勾勒的清明政治的目标。
凡举一例即可:
洪武十八年,吏部考核全国布政司及府、州、县来京朝谒官员几千,其中所谓称职者仅435人。
对此太祖晚年也认识道:
“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至成祖永乐初年废建文仁政而沿用《大诰》收效不佳后束之高阁,《大诰》之刑渐渐弃用后数载,贪官污吏已遍布内外,显示了挣脱重典之束缚后强劲的反弹力。
(二)适用重典之合理性分析由上,传统社会无论何种重典治世模式,收效均属了了,呈现整体低效甚至无正效用但却有长久活力的奇怪姿态。
对此进行合理性解释的角度可有多个,但欲以单向的、法律制度模型的路径为切入点,应把握法文化、制度建构与发展史及其客观运行评价作为突破关键。
首先,重典发挥的阶段性正效益对维护统治具有强吸引力,统治者可将其作为改变行使统治权不利局面,寻求优化时的博弈行为。
中国古来之重典是成系统的,规范严密,且表现为某种封闭性的独立发展结构,立法和策略之行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
同时中国自古而来较西方强烈甚多的集权型治理模式,也能将资源集中到足以确保由上而下执行某种制度初始阶段所要求的严格性,甚至严苛、残暴性。
故而,重典推行在短期时间确实可如史料所描述的那样“彰善瘅恶,激浊扬清”。
虽然只是违法者受到重惩造成社会相关主体感到自危后,所受规制的社会反常暂时停滞甚至隐蔽的反应。
然重典的最初作用力越强,其受用波及越广,影响便越深,停滞症状维持时间便较长久,虽然不乏孕育着更剧烈反弹的可能。
但这不能不给统治者以想象的空间,继续预期所深恶痛绝的受动主体自觉进行良性转变,以至设想能秉承重法之效,最终消弭不安定因素,“以刑去刑”,长治久安。
而在传统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社会呈现多元化趋势和统治者所欲维护的简单生产基础下社会治理手段产生冲突,更凸现了无法与时俱进的一般法典修正补充技术的落后地位。
为摆脱此种不利局面,采用有别于一般法制制约力的重典,不能不说体现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被迫放手一搏的无奈。
其次,适用重典是统治者认可的,永葆国家机器运转动力所必需赋加的“托宾税”。
在传统社会这架巨型机器运转二千余年的过程中,官吏始终作为统治者实现统治效能,控制普通民众不可缺失的组成利器。
官吏集团与最高统治者之间本质上存在的是一种特殊雇佣关系:
因为高度集权社会中权力之行使,实际亦是建立在地方权力为中央权力直接控制,却也过分集中的情况下。
故各级官僚机构在中央之下扮演的角色,即为雇员也为在局部受制的大领主,系一种具有人格化的工具。
故“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是古人对官之于国重要性的认识,于是坚守不放“治国莫大于惩贪”、“治天下首在惩贪治吏”之圭臬。
时时用重法剔除国家机器中不合理因素,整肃行政纪律,即如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学家所言为齿轮良好运转而不时放入细沙般效果的课税雷同,治理官员腐败懈怠而致阶级矛盾过分扩大化,促进行政效能的提升、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
再次,适用重典反映了传统社会“礼法合一”条件下泛道德化的“和谐”行为预期。
两汉以降,法律道德化色彩逐步加强,隆礼重法成为中华法系一大特色。
引礼入法,一方面为统治者鼓吹“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宣扬仁政和统治地位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善用礼中丰富的道德规范培育发达的家法族规,使社会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金字塔状结构,也有利于减轻维护统治所需耗费的成本,“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惟“以德化天下”,“明刑制以齐之”,国家可长久矣。
应该说,决策者乃至国民均在一定程度上采纳并预设了人性向善的儒学基点,努力以道德化行为范式来改造既定的不合理因子,其中一方通过隆礼以导民向善,减少不必要的统治开支;另一方则企盼上为政以德、匡扶正义——权力义务极不对称两方群体在社会构建中共享着基于不同认识形成的“和谐”雏形表征之向往。
但由于传统社会局限性,社会矛盾无法消解,人们注定长久面对大同理想和严酷现实之冲突。
于是乎统治者每每“痛下决心”,对人性论稍作一修正,试图以灭除恶之人性的刚猛之法以恶治恶,树立权威,瓦解法制运行不畅的阻碍;国民也时常希冀青天在世,向给自己带来深重苦难的官僚腐败集团表达失望和愤慨情绪之时,事实上也早已偏离了人性善之预期,复燃原始复仇主义之观念,同时却也清楚意识到民众分散力量之孤立弱小,被迫对善治之论尚存遐想,有通过接受由上至下的重典洗礼来达到社会革新,重建“和谐”的心理准备和要求。
作为传统社会法文化的标志之一,尚不能忽略法自君出、权尊于法的事实。
重典之存,如果排除社会性因素而单独从研究决策者入手,时常可以发现重典适用的轨迹与君主自身对外部环境的应激及心理状态的描绘极其相符。
正是统治者“口含天宪”,不受权力约束,决策之合法性历来没有适格的评价标准,而合理性则可在决策定立时由下而上反馈得以损益,但依旧无法摆脱深烙有统治者自身对历史、社会现状、皇族利益思考和抉择之泥淖,甚至表达了其对以往自身经历“辛酸”面的反思或抵触、逆反情绪,重典的抛出也不外如是。
乱世应用重典
“治乱世用重典”,以重刑威慑阻遏犯罪的思想,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法家一派的法律思想家们奉为预防犯罪、治理国家的经典。
按照近代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人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只要刑罚有可能带给犯罪人足够的痛苦,他就不会选择犯罪。
死刑能够带给犯罪人的痛苦是最大的,当然就对犯罪人有着最大的心理强制,对犯罪行为有着最有效的威慑力。
然而,思想家们却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道理:
乱世并不是轻典的结果。
犯罪人实施犯罪,特别是某些重大犯罪,主要原因也不是他权衡后认为刑罚不重才选择的结果。
因此,重典治不了乱世,死刑也吓不住重罪。
首先,从犯罪产生的根源来看。
犯罪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观念、家庭关系等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根源,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
中国清末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律改革家沈家本就曾指出:
“苟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罹刑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
”“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
”。
另外,朱元璋是典型的乱世用重典: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
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
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杀掉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
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
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
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
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
此后,当廷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
终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