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纽扣与红裙子高三作文.docx
《蓝纽扣与红裙子高三作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蓝纽扣与红裙子高三作文.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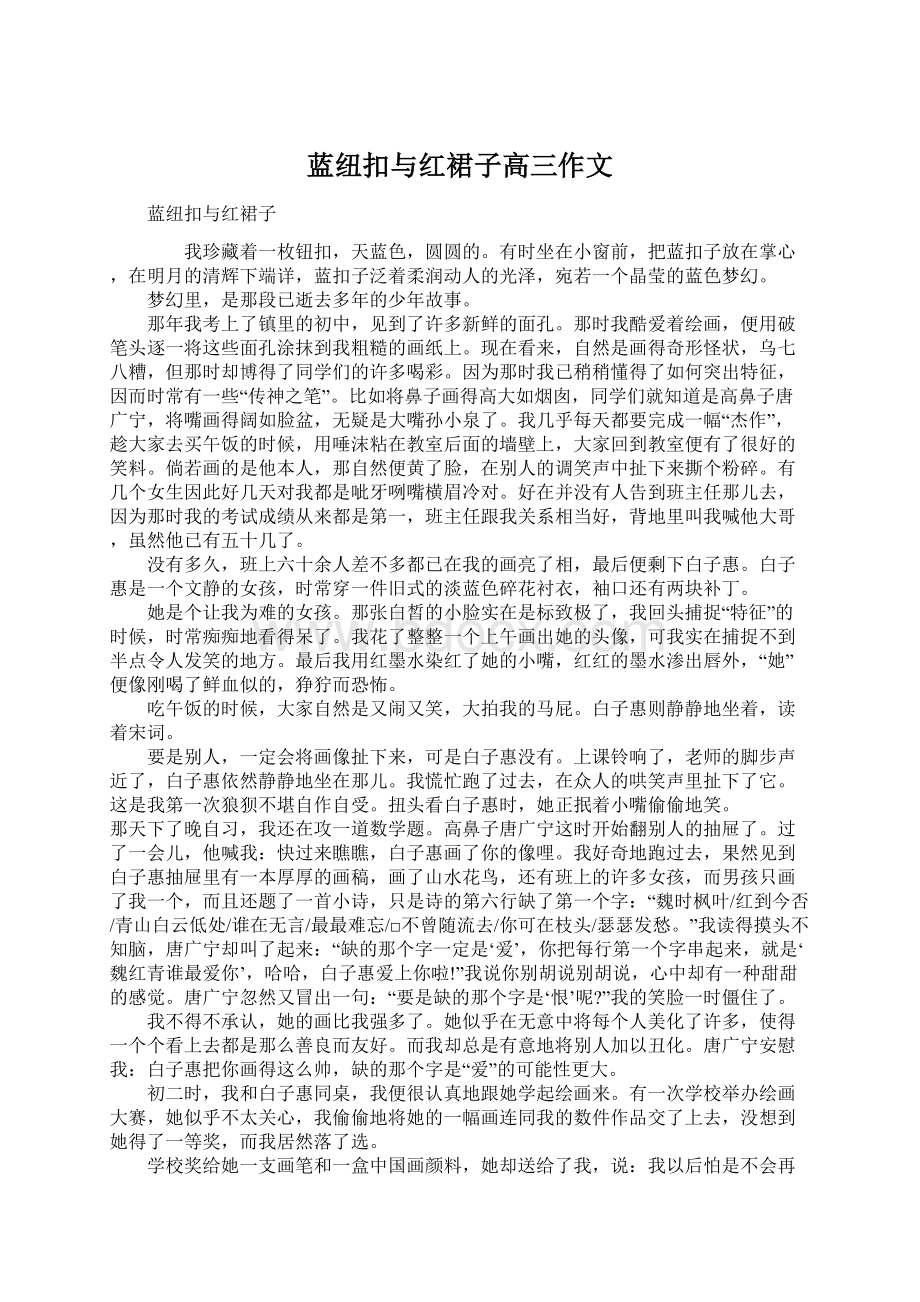
蓝纽扣与红裙子高三作文
蓝纽扣与红裙子
我珍藏着一枚钮扣,天蓝色,圆圆的。
有时坐在小窗前,把蓝扣子放在掌心,在明月的清辉下端详,蓝扣子泛着柔润动人的光泽,宛若一个晶莹的蓝色梦幻。
梦幻里,是那段已逝去多年的少年故事。
那年我考上了镇里的初中,见到了许多新鲜的面孔。
那时我酷爱着绘画,便用破笔头逐一将这些面孔涂抹到我粗糙的画纸上。
现在看来,自然是画得奇形怪状,乌七八糟,但那时却博得了同学们的许多喝彩。
因为那时我已稍稍懂得了如何突出特征,因而时常有一些“传神之笔”。
比如将鼻子画得高大如烟囱,同学们就知道是高鼻子唐广宁,将嘴画得阔如脸盆,无疑是大嘴孙小泉了。
我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幅“杰作”,趁大家去买午饭的时候,用唾沫粘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大家回到教室便有了很好的笑料。
倘若画的是他本人,那自然便黄了脸,在别人的调笑声中扯下来撕个粉碎。
有几个女生因此好几天对我都是呲牙咧嘴横眉冷对。
好在并没有人告到班主任那儿去,因为那时我的考试成绩从来都是第一,班主任跟我关系相当好,背地里叫我喊他大哥,虽然他已有五十几了。
没有多久,班上六十余人差不多都已在我的画亮了相,最后便剩下白子惠。
白子惠是一个文静的女孩,时常穿一件旧式的淡蓝色碎花衬衣,袖口还有两块补丁。
她是个让我为难的女孩。
那张白皙的小脸实在是标致极了,我回头捕捉“特征”的时候,时常痴痴地看得呆了。
我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画出她的头像,可我实在捕捉不到半点令人发笑的地方。
最后我用红墨水染红了她的小嘴,红红的墨水渗出唇外,“她”便像刚喝了鲜血似的,狰狞而恐怖。
吃午饭的时候,大家自然是又闹又笑,大拍我的马屁。
白子惠则静静地坐着,读着宋词。
要是别人,一定会将画像扯下来,可是白子惠没有。
上课铃响了,老师的脚步声近了,白子惠依然静静地坐在那儿。
我慌忙跑了过去,在众人的哄笑声里扯下了它。
这是我第一次狼狈不堪自作自受。
扭头看白子惠时,她正抿着小嘴偷偷地笑。
那天下了晚自习,我还在攻一道数学题。
高鼻子唐广宁这时开始翻别人的抽屉了。
过了一会儿,他喊我:
快过来瞧瞧,白子惠画了你的像哩。
我好奇地跑过去,果然见到白子惠抽屉里有一本厚厚的画稿,画了山水花鸟,还有班上的许多女孩,而男孩只画了我一个,而且还题了一首小诗,只是诗的第六行缺了第一个字:
“魏时枫叶/红到今否/青山白云低处/谁在无言/最最难忘/□不曾随流去/你可在枝头/瑟瑟发愁。
”我读得摸头不知脑,唐广宁却叫了起来:
“缺的那个字一定是‘爱’,你把每行第一个字串起来,就是‘魏红青谁最爱你’,哈哈,白子惠爱上你啦!
”我说你别胡说别胡说,心中却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唐广宁忽然又冒出一句:
“要是缺的那个字是‘恨’呢?
”我的笑脸一时僵住了。
我不得不承认,她的画比我强多了。
她似乎在无意中将每个人美化了许多,使得一个个看上去都是那么善良而友好。
而我却总是有意地将别人加以丑化。
唐广宁安慰我:
白子惠把你画得这么帅,缺的那个字是“爱”的可能性更大。
初二时,我和白子惠同桌,我便很认真地跟她学起绘画来。
有一次学校举办绘画大赛,她似乎不太关心,我偷偷地将她的一幅画连同我的数件作品交了上去,没想到她得了一等奖,而我居然落了选。
学校奖给她一支画笔和一盒中国画颜料,她却送给了我,说:
我以后怕是不会再画画了。
我听不明白,糊里糊涂地接受了。
渐渐地我发现我去买午饭时白子惠总没有离开教室,而我买了饭回到教室时她却已捧着一缸凉开水在慢慢地喝。
再后来,我怀疑她总没有吃午饭,问她,她却说早吃过了。
有好几次天并不热,我却看见她白皙的脸上渗出汗来,下午上课时便昏睡在课桌上,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老师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她也常回答得丢三拉四。
后来,我便多买了一份午饭,放在她的桌上。
她坚决不肯吃,我便说用饭来换她的画稿。
她便吃一顿午饭,给我两张画稿。
这样没多久,那本画稿便几乎全部放进了我的抽屉,只有画着我头像的那张画稿,她还保存着。
那天后排的唐广宁正在吸墨水,我不小心猛地靠了一下,那墨水瓶便从书堆上倒下来,溅了白子惠一身。
我立即表示说要买一件新的赔她。
她说不必了不必了,后来便穿了一身更旧的衣服。
那一定是她姐姐穿过的。
那时街上流行红裙子。
我想,白子惠穿上红裙子一定更加漂亮。
我暗暗地筹钱,先是卖了新凉鞋,后来又半价处理了新华字典。
14岁生日那天我并没有声张,我珍藏着一枚钮扣,天蓝色,圆圆的。
有时坐在小窗前,把蓝扣子放在掌心,在明月的清辉下端详,蓝扣子泛着柔润动人的光泽,宛若一个晶莹的蓝色梦幻。
梦幻里,是那段已逝去多年的少年故事。
那年我考上了镇里的初中,见到了许多新鲜的面孔。
那时我酷爱着绘画,便用破笔头逐一将这些面孔涂抹到我粗糙的画纸上。
现在看来,自然是画得奇形怪状,乌七八糟,但那时却博得了同学们的许多喝彩。
因为那时我已稍稍懂得了如何突出特征,因而时常有一些“传神之笔”。
比如将鼻子画得高大如烟囱,同学们就知道是高鼻子唐广宁,将嘴画得阔如脸盆,无疑是大嘴孙小泉了。
我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幅“杰作”,趁大家去买午饭的时候,用唾沫粘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大家回到教室便有了很好的笑料。
倘若画的是他本人,那自然便黄了脸,在别人的调笑声中扯下来撕个粉碎。
有几个女生因此好几天对我都是呲牙咧嘴横眉冷对。
好在并没有人告到班主任那儿去,因为那时我的考试成绩从来都是第一,班主任跟我关系相当好,背地里叫我喊他大哥,虽然他已有五十几了。
没有多久,班上六十余人差不多都已在我的画亮了相,最后便剩下白子惠。
白子惠是一个文静的女孩,时常穿一件旧式的淡蓝色碎花衬衣,袖口还有两块补丁。
她是个让我为难的女孩。
那张白皙的小脸实在是标致极了,我回头捕捉“特征”的时候,时常痴痴地看得呆了。
我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画出她的头像,可我实在捕捉不到半点令人发笑的地方。
最后我用红墨水染红了她的小嘴,红红的墨水渗出唇外,“她”便像刚喝了鲜血似的,狰狞而恐怖。
吃午饭的时候,大家自然是又闹又笑,大拍我的马屁。
白子惠则静静地坐着,读着宋词。
要是别人,一定会将画像扯下来,可是白子惠没有。
上课铃响了,老师的脚步声近了,白子惠依然静静地坐在那儿。
我慌忙跑了过去,在众人的哄笑声里扯下了它。
这是我第一次狼狈不堪自作自受。
扭头看白子惠时,她正抿着小嘴偷偷地笑。
那天下了晚自习,我还在攻一道数学题。
高鼻子唐广宁这时开始翻别人的抽屉了。
过了一会儿,他喊我:
快过来瞧瞧,白子惠画了你的像哩。
我好奇地跑过去,果然见到白子惠抽屉里有一本厚厚的画稿,画了山水花鸟,还有班上的许多女孩,而男孩只画了我一个,而且还题了一首小诗,只是诗的第六行缺了第一个字:
“魏时枫叶/红到今否/青山白云低处/谁在无言/最最难忘/□不曾随流去/你可在枝头/瑟瑟发愁。
”我读得摸头不知脑,唐广宁却叫了起来:
“缺的那个字一定是‘爱’,你把每行第一个字串起来,就是‘魏红青谁最爱你’,哈哈,白子惠爱上你啦!
”我说你别胡说别胡说,心中却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唐广宁忽然又冒出一句:
“要是缺的那个字是‘恨’呢?
”我的笑脸一时僵住了。
我不得不承认,她的画比我强多了。
她似乎在无意中将每个人美化了许多,使得一个个看上去都是那么善良而友好。
而我却总是有意地将别人加以丑化。
唐广宁安慰我:
白子惠把你画得这么帅,缺的那个字是“爱”的可能性更大。
初二时,我和白子惠同桌,我便很认真地跟她学起绘画来。
有一次学校举办绘画大赛,她似乎不太关心,我偷偷地将她的一幅画连同我的数件作品交了上去,没想到她得了一等奖,而我居然落了选。
学校奖给她一支画笔和一盒中国画颜料,她却送给了我,说:
我以后怕是不会再画画了。
我听不明白,糊里糊涂地接受了。
渐渐地我发现我去买午饭时白子惠总没有离开教室,而我买了饭回到教室时她却已捧着一缸凉开水在慢慢地喝。
再后来,我怀疑她总没有吃午饭,问她,她却说早吃过了。
有好几次天并不热,我却看见她白皙的脸上渗出汗来,下午上课时便昏睡在课桌上,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老师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她也常回答得丢三拉四。
后来,我便多买了一份午饭,放在她的桌上。
她坚决不肯吃,我便说用饭来换她的画稿。
她便吃一顿午饭,给我两张画稿。
这样没多久,那本画稿便几乎全部放进了我的抽屉,只有画着我头像的那张画稿,她还保存着。
那天后排的唐广宁正在吸墨水,我不小心猛地靠了一下,那墨水瓶便从书堆上倒下来,溅了白子惠一身。
我立即表示说要买一件新的赔她。
她说不必了不必了,后来便穿了一身更旧的衣服。
那一定是她姐姐穿过的。
那时街上流行红裙子。
我想,白子惠穿上红裙子一定更加漂亮。
我暗暗地筹钱,先是卖了新凉鞋,后来又半价处理了新华字典。
14岁生日那天我并没有声张,我珍藏着一枚钮扣,天蓝色,圆圆的。
有时坐在小窗前,把蓝扣子放在掌心,在明月的清辉下端详,蓝扣子泛着柔润动人的光泽,宛若一个晶莹的蓝色梦幻。
梦幻里,是那段已逝去多年的少年故事。
那年我考上了镇里的初中,见到了许多新鲜的面孔。
那时我酷爱着绘画,便用破笔头逐一将这些面孔涂抹到我粗糙的画纸上。
现在看来,自然是画得奇形怪状,乌七八糟,但那时却博得了同学们的许多喝彩。
因为那时我已稍稍懂得了如何突出特征,因而时常有一些“传神之笔”。
比如将鼻子画得高大如烟囱,同学们就知道是高鼻子唐广宁,将嘴画得阔如脸盆,无疑是大嘴孙小泉了。
我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幅“杰作”,趁大家去买午饭的时候,用唾沫粘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大家回到教室便有了很好的笑料。
倘若画的是他本人,那自然便黄了脸,在别人的调笑声中扯下来撕个粉碎。
有几个女生因此好几天对我都是呲牙咧嘴横眉冷对。
好在并没有人告到班主任那儿去,因为那时我的考试成绩从来都是第一,班主任跟我关系相当好,背地里叫我喊他大哥,虽然他已有五十几了。
没有多久,班上六十余人差不多都已在我的画亮了相,最后便剩下白子惠。
白子惠是一个文静的女孩,时常穿一件旧式的淡蓝色碎花衬衣,袖口还有两块补丁。
她是个让我为难的女孩。
那张白皙的小脸实在是标致极了,我回头捕捉“特征”的时候,时常痴痴地看得呆了。
我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画出她的头像,可我实在捕捉不到半点令人发笑的地方。
最后我用红墨水染红了她的小嘴,红红的墨水渗出唇外,“她”便像刚喝了鲜血似的,狰狞而恐怖。
吃午饭的时候,大家自然是又闹又笑,大拍我的马屁。
白子惠则静静地坐着,读着宋词。
要是别人,一定会将画像扯下来,可是白子惠没有。
上课铃响了,老师的脚步声近了,白子惠依然静静地坐在那儿。
我慌忙跑了过去,在众人的哄笑声里扯下了它。
这是我第一次狼狈不堪自作自受。
扭头看白子惠时,她正抿着小嘴偷偷地笑。
那天下了晚自习,我还在攻一道数学题。
高鼻子唐广宁这时开始翻别人的抽屉了。
过了一会儿,他喊我:
快过来瞧瞧,白子惠画了你的像哩。
我好奇地跑过去,果然见到白子惠抽屉里有一本厚厚的画稿,画了山水花鸟,还有班上的许多女孩,而男孩只画了我一个,而且还题了一首小诗,只是诗的第六行缺了第一个字:
“魏时枫叶/红到今否/青山白云低处/谁在无言/最最难忘/□不曾随流去/你可在枝头/瑟瑟发愁。
”我读得摸头不知脑,唐广宁却叫了起来:
“缺的那个字一定是‘爱’,你把每行第一个字串起来,就是‘魏红青谁最爱你’,哈哈,白子惠爱上你啦!
”我说你别胡说别胡说,心中却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唐广宁忽然又冒出一句:
“要是缺的那个字是‘恨’呢?
”我的笑脸一时僵住了。
我不得不承认,她的画比我强多了。
她似乎在无意中将每个人美化了许多,使得一个个看上去都是那么善良而友好。
而我却总是有意地将别人加以丑化。
唐广宁安慰我:
白子惠把你画得这么帅,缺的那个字是“爱”的可能性更大。
初二时,我和白子惠同桌,我便很认真地跟她学起绘画来。
有一次学校举办绘画大赛,她似乎不太关心,我偷偷地将她的一幅画连同我的数件作品交了上去,没想到她得了一等奖,而我居然落了选。
学校奖给她一支画笔和一盒中国画颜料,她却送给了我,说:
我以后怕是不会再画画了。
我听不明白,糊里糊涂地接受了。
渐渐地我发现我去买午饭时白子惠总没有离开教室,而我买了饭回到教室时她却已捧着一缸凉开水在慢慢地喝。
再后来,我怀疑她总没有吃午饭,问她,她却说早吃过了。
有好几次天并不热,我却看见她白皙的脸上渗出汗来,下午上课时便昏睡在课桌上,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老师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她也常回答得丢三拉四。
后来,我便多买了一份午饭,放在她的桌上。
她坚决不肯吃,我便说用饭来换她的画稿。
她便吃一顿午饭,给我两张画稿。
这样没多久,那本画稿便几乎全部放进了我的抽屉,只有画着我头像的那张画稿,她还保存着。
那天后排的唐广宁正在吸墨水,我不小心猛地靠了一下,那墨水瓶便从书堆上倒下来,溅了白子惠一身。
我立即表示说要买一件新的赔她。
她说不必了不必了,后来便穿了一身更旧的衣服。
那一定是她姐姐穿过的。
那时街上流行红裙子。
我想,白子惠穿上红裙子一定更加漂亮。
我暗暗地筹钱,先是卖了新凉鞋,后来又半价处理了新华字典。
14岁生日那天我并没有声张,我珍藏着一枚钮扣,天蓝色,圆圆的。
有时坐在小窗前,把蓝扣子放在掌心,在明月的清辉下端详,蓝扣子泛着柔润动人的光泽,宛若一个晶莹的蓝色梦幻。
梦幻里,是那段已逝去多年的少年故事。
那年我考上了镇里的初中,见到了许多新鲜的面孔。
那时我酷爱着绘画,便用破笔头逐一将这些面孔涂抹到我粗糙的画纸上。
现在看来,自然是画得奇形怪状,乌七八糟,但那时却博得了同学们的许多喝彩。
因为那时我已稍稍懂得了如何突出特征,因而时常有一些“传神之笔”。
比如将鼻子画得高大如烟囱,同学们就知道是高鼻子唐广宁,将嘴画得阔如脸盆,无疑是大嘴孙小泉了。
我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幅“杰作”,趁大家去买午饭的时候,用唾沫粘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大家回到教室便有了很好的笑料。
倘若画的是他本人,那自然便黄了脸,在别人的调笑声中扯下来撕个粉碎。
有几个女生因此好几天对我都是呲牙咧嘴横眉冷对。
好在并没有人告到班主任那儿去,因为那时我的考试成绩从来都是第一,班主任跟我关系相当好,背地里叫我喊他大哥,虽然他已有五十几了。
没有多久,班上六十余人差不多都已在我的画亮了相,最后便剩下白子惠。
白子惠是一个文静的女孩,时常穿一件旧式的淡蓝色碎花衬衣,袖口还有两块补丁。
她是个让我为难的女孩。
那张白皙的小脸实在是标致极了,我回头捕捉“特征”的时候,时常痴痴地看得呆了。
我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画出她的头像,可我实在捕捉不到半点令人发笑的地方。
最后我用红墨水染红了她的小嘴,红红的墨水渗出唇外,“她”便像刚喝了鲜血似的,狰狞而恐怖。
吃午饭的时候,大家自然是又闹又笑,大拍我的马屁。
白子惠则静静地坐着,读着宋词。
要是别人,一定会将画像扯下来,可是白子惠没有。
上课铃响了,老师的脚步声近了,白子惠依然静静地坐在那儿。
我慌忙跑了过去,在众人的哄笑声里扯下了它。
这是我第一次狼狈不堪自作自受。
扭头看白子惠时,她正抿着小嘴偷偷地笑。
那天下了晚自习,我还在攻一道数学题。
高鼻子唐广宁这时开始翻别人的抽屉了。
过了一会儿,他喊我:
快过来瞧瞧,白子惠画了你的像哩。
我好奇地跑过去,果然见到白子惠抽屉里有一本厚厚的画稿,画了山水花鸟,还有班上的许多女孩,而男孩只画了我一个,而且还题了一首小诗,只是诗的第六行缺了第一个字:
“魏时枫叶/红到今否/青山白云低处/谁在无言/最最难忘/□不曾随流去/你可在枝头/瑟瑟发愁。
”我读得摸头不知脑,唐广宁却叫了起来:
“缺的那个字一定是‘爱’,你把每行第一个字串起来,就是‘魏红青谁最爱你’,哈哈,白子惠爱上你啦!
”我说你别胡说别胡说,心中却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唐广宁忽然又冒出一句:
“要是缺的那个字是‘恨’呢?
”我的笑脸一时僵住了。
我不得不承认,她的画比我强多了。
她似乎在无意中将每个人美化了许多,使得一个个看上去都是那么善良而友好。
而我却总是有意地将别人加以丑化。
唐广宁安慰我:
白子惠把你画得这么帅,缺的那个字是“爱”的可能性更大。
初二时,我和白子惠同桌,我便很认真地跟她学起绘画来。
有一次学校举办绘画大赛,她似乎不太关心,我偷偷地将她的一幅画连同我的数件作品交了上去,没想到她得了一等奖,而我居然落了选。
学校奖给她一支画笔和一盒中国画颜料,她却送给了我,说:
我以后怕是不会再画画了。
我听不明白,糊里糊涂地接受了。
渐渐地我发现我去买午饭时白子惠总没有离开教室,而我买了饭回到教室时她却已捧着一缸凉开水在慢慢地喝。
再后来,我怀疑她总没有吃午饭,问她,她却说早吃过了。
有好几次天并不热,我却看见她白皙的脸上渗出汗来,下午上课时便昏睡在课桌上,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老师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她也常回答得丢三拉四。
后来,我便多买了一份午饭,放在她的桌上。
她坚决不肯吃,我便说用饭来换她的画稿。
她便吃一顿午饭,给我两张画稿。
这样没多久,那本画稿便几乎全部放进了我的抽屉,只有画着我头像的那张画稿,她还保存着。
那天后排的唐广宁正在吸墨水,我不小心猛地靠了一下,那墨水瓶便从书堆上倒下来,溅了白子惠一身。
我立即表示说要买一件新的赔她。
她说不必了不必了,后来便穿了一身更旧的衣服。
那一定是她姐姐穿过的。
那时街上流行红裙子。
我想,白子惠穿上红裙子一定更加漂亮。
我暗暗地筹钱,先是卖了新凉鞋,后来又半价处理了新华字典。
14岁生日那天我并没有声张,我珍藏着一枚钮扣,天蓝色,圆圆的。
有时坐在小窗前,把蓝扣子放在掌心,在明月的清辉下端详,蓝扣子泛着柔润动人的光泽,宛若一个晶莹的蓝色梦幻。
梦幻里,是那段已逝去多年的少年故事。
那年我考上了镇里的初中,见到了许多新鲜的面孔。
那时我酷爱着绘画,便用破笔头逐一将这些面孔涂抹到我粗糙的画纸上。
现在看来,自然是画得奇形怪状,乌七八糟,但那时却博得了同学们的许多喝彩。
因为那时我已稍稍懂得了如何突出特征,因而时常有一些“传神之笔”。
比如将鼻子画得高大如烟囱,同学们就知道是高鼻子唐广宁,将嘴画得阔如脸盆,无疑是大嘴孙小泉了。
我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幅“杰作”,趁大家去买午饭的时候,用唾沫粘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大家回到教室便有了很好的笑料。
倘若画的是他本人,那自然便黄了脸,在别人的调笑声中扯下来撕个粉碎。
有几个女生因此好几天对我都是呲牙咧嘴横眉冷对。
好在并没有人告到班主任那儿去,因为那时我的考试成绩从来都是第一,班主任跟我关系相当好,背地里叫我喊他大哥,虽然他已有五十几了。
没有多久,班上六十余人差不多都已在我的画亮了相,最后便剩下白子惠。
白子惠是一个文静的女孩,时常穿一件旧式的淡蓝色碎花衬衣,袖口还有两块补丁。
她是个让我为难的女孩。
那张白皙的小脸实在是标致极了,我回头捕捉“特征”的时候,时常痴痴地看得呆了。
我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画出她的头像,可我实在捕捉不到半点令人发笑的地方。
最后我用红墨水染红了她的小嘴,红红的墨水渗出唇外,“她”便像刚喝了鲜血似的,狰狞而恐怖。
吃午饭的时候,大家自然是又闹又笑,大拍我的马屁。
白子惠则静静地坐着,读着宋词。
要是别人,一定会将画像扯下来,可是白子惠没有。
上课铃响了,老师的脚步声近了,白子惠依然静静地坐在那儿。
我慌忙跑了过去,在众人的哄笑声里扯下了它。
这是我第一次狼狈不堪自作自受。
扭头看白子惠时,她正抿着小嘴偷偷地笑。
那天下了晚自习,我还在攻一道数学题。
高鼻子唐广宁这时开始翻别人的抽屉了。
过了一会儿,他喊我:
快过来瞧瞧,白子惠画了你的像哩。
我好奇地跑过去,果然见到白子惠抽屉里有一本厚厚的画稿,画了山水花鸟,还有班上的许多女孩,而男孩只画了我一个,而且还题了一首小诗,只是诗的第六行缺了第一个字:
“魏时枫叶/红到今否/青山白云低处/谁在无言/最最难忘/□不曾随流去/你可在枝头/瑟瑟发愁。
”我读得摸头不知脑,唐广宁却叫了起来:
“缺的那个字一定是‘爱’,你把每行第一个字串起来,就是‘魏红青谁最爱你’,哈哈,白子惠爱上你啦!
”我说你别胡说别胡说,心中却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唐广宁忽然又冒出一句:
“要是缺的那个字是‘恨’呢?
”我的笑脸一时僵住了。
我不得不承认,她的画比我强多了。
她似乎在无意中将每个人美化了许多,使得一个个看上去都是那么善良而友好。
而我却总是有意地将别人加以丑化。
唐广宁安慰我:
白子惠把你画得这么帅,缺的那个字是“爱”的可能性更大。
初二时,我和白子惠同桌,我便很认真地跟她学起绘画来。
有一次学校举办绘画大赛,她似乎不太关心,我偷偷地将她的一幅画连同我的数件作品交了上去,没想到她得了一等奖,而我居然落了选。
学校奖给她一支画笔和一盒中国画颜料,她却送给了我,说:
我以后怕是不会再画画了。
我听不明白,糊里糊涂地接受了。
渐渐地我发现我去买午饭时白子惠总没有离开教室,而我买了饭回到教室时她却已捧着一缸凉开水在慢慢地喝。
再后来,我怀疑她总没有吃午饭,问她,她却说早吃过了。
有好几次天并不热,我却看见她白皙的脸上渗出汗来,下午上课时便昏睡在课桌上,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老师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她也常回答得丢三拉四。
后来,我便多买了一份午饭,放在她的桌上。
她坚决不肯吃,我便说用饭来换她的画稿。
她便吃一顿午饭,给我两张画稿。
这样没多久,那本画稿便几乎全部放进了我的抽屉,只有画着我头像的那张画稿,她还保存着。
那天后排的唐广宁正在吸墨水,我不小心猛地靠了一下,那墨水瓶便从书堆上倒下来,溅了白子惠一身。
我立即表示说要买一件新的赔她。
她说不必了不必了,后来便穿了一身更旧的衣服。
那一定是她姐姐穿过的。
那时街上流行红裙子。
我想,白子惠穿上红裙子一定更加漂亮。
我暗暗地筹钱,先是卖了新凉鞋,后来又半价处理了新华字典。
14岁生日那天我并没有声张,
初二时,我和白子惠同桌,我便很认真地跟她学起绘画来。
有一次学校举办绘画大赛,她似乎不太关心,我偷偷地将她的一幅画连同我的数件作品交了上去,没想到她得了一等奖,而我居然落了选。
学校奖给她一支画笔和一盒中国画颜料,她却送给了我,说:
我以后怕是不会再画画了。
我听不明白,糊里糊涂地接受了。
渐渐地我发现我去买午饭时白子惠总没有离开教室,而我买了饭回到教室时她却已捧着一缸凉开水在慢慢地喝。
再后来,我怀疑她总没有吃午饭,问她,她却说早吃过了。
有好几次天并不热,我却看见她白皙的脸上渗出汗来,下午上课时便昏睡在课桌上,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老师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她也常回答得丢三拉四。
后来,我便多买了一份午饭,放在她的桌上。
她坚决不肯吃,我便说用饭来换她的画稿。
她便吃一顿午饭,给我两张画稿。
这样没多久,那本画稿便几乎全部放进了我的抽屉,只有画着我头像的那张画稿,她还保存着。
那天后排的唐广宁正在吸墨水,我不小心猛地靠了一下,那墨水瓶便从书堆上倒下来,溅了白子惠一身。
我立即表示说要买一件新的赔她。
她说不必了不必了,后来便穿了一身更旧的衣服。
那一定是她姐姐穿过的。
那时街上流行红裙子。
我想,白子惠穿上红裙子一定更加漂亮。
我暗暗地筹钱,先是卖了新凉鞋,后来又半价处理了新华字典。
14岁生日那天我并没有声张,我珍藏着一枚钮扣,天蓝色,圆圆的。
有时坐在小窗前,把蓝扣子放在掌心,在明月的清辉下端详,蓝扣子泛着柔润动人的光泽,宛若一个晶莹的蓝色梦幻。
梦幻里,是那段已逝去多年的少年故事。
那年我考上了镇里的初中,见到了许多新鲜的面孔。
那时我酷爱着绘画,便用破笔头逐一将这些面孔涂抹到我粗糙的画纸上。
现在看来,自然是画得奇形怪状,乌七八糟,但那时却博得了同学们的许多喝彩。
因为那时我已稍稍懂得了如何突出特征,因而时常有一些“传神之笔”。
比如将鼻子画得高大如烟囱,同学们就知道是高鼻子唐广宁,将嘴画得阔如脸盆,无疑是大嘴孙小泉了。
我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幅“杰作”,趁大家去买午饭的时候,用唾沫粘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大家回到教室便有了很好的笑料。
倘若画的是他本人,那自然便黄了脸,在别人的调笑声中扯下来撕个粉碎。
有几个女生因此好几天对我都是呲牙咧嘴横眉冷对。
好在并没有人告到班主任那儿去,因为那时我的考试成绩从来都是第一,班主任跟我关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