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关于八十年代的几本书.docx
《李泽厚关于八十年代的几本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李泽厚关于八十年代的几本书.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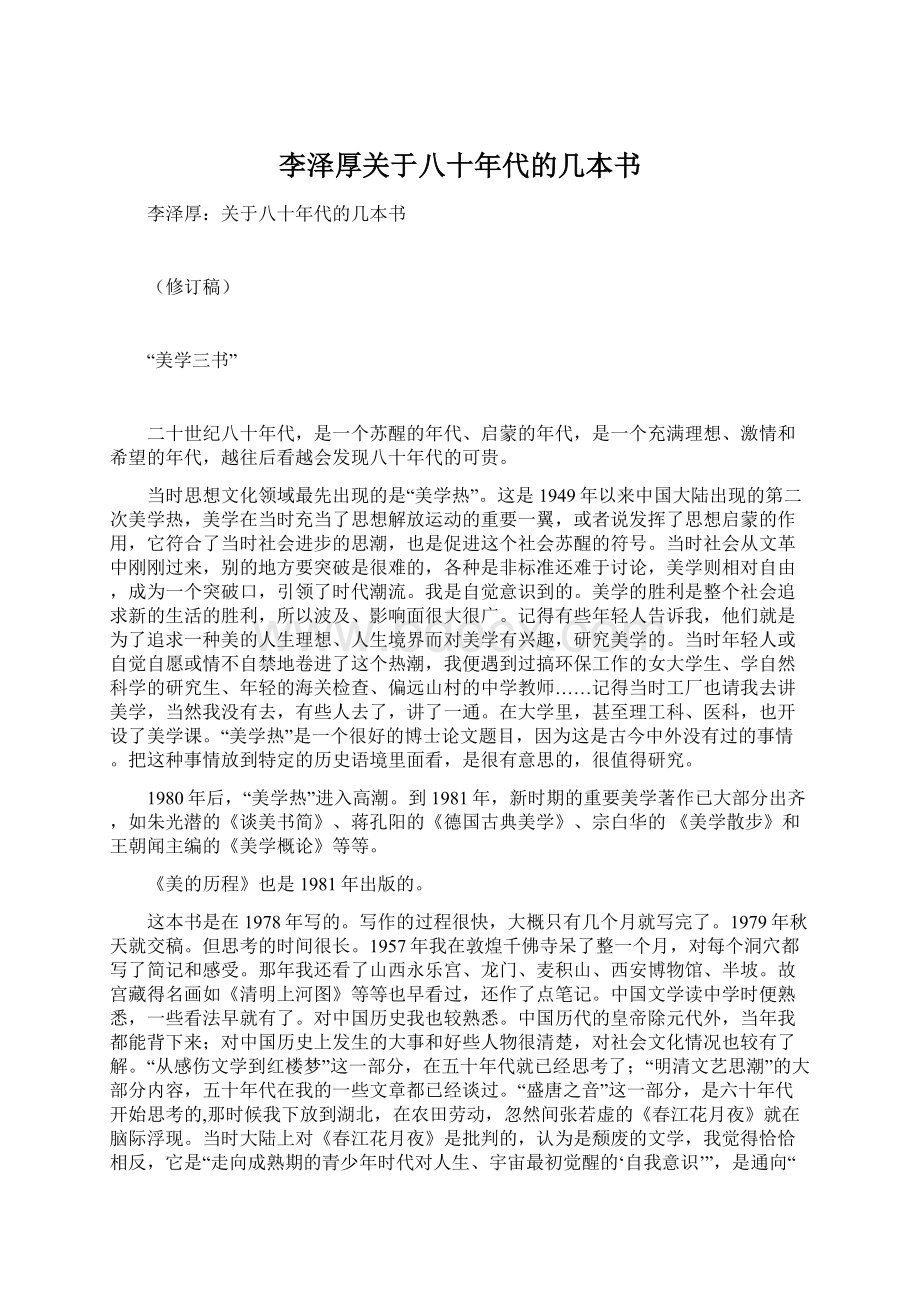
李泽厚关于八十年代的几本书
李泽厚:
关于八十年代的几本书
(修订稿)
“美学三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苏醒的年代、启蒙的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和希望的年代,越往后看越会发现八十年代的可贵。
当时思想文化领域最先出现的是“美学热”。
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二次美学热,美学在当时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翼,或者说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它符合了当时社会进步的思潮,也是促进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
当时社会从文革中刚刚过来,别的地方要突破是很难的,各种是非标准还难于讨论,美学则相对自由,成为一个突破口,引领了时代潮流。
我是自觉意识到的。
美学的胜利是整个社会追求新的生活的胜利,所以波及、影响面很大很广。
记得有些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就是为了追求一种美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而对美学有兴趣,研究美学的。
当时年轻人或自觉自愿或情不自禁地卷进了这个热潮,我便遇到过搞环保工作的女大学生、学自然科学的研究生、年轻的海关检查、偏远山村的中学教师……记得当时工厂也请我去讲美学,当然我没有去,有些人去了,讲了一通。
在大学里,甚至理工科、医科,也开设了美学课。
“美学热”是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因为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事情。
把这种事情放到特定的历史语境里面看,是很有意思的,很值得研究。
1980年后,“美学热”进入高潮。
到1981年,新时期的重要美学著作已大部分出齐,如朱光潜的《谈美书简》、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等。
《美的历程》也是1981年出版的。
这本书是在1978年写的。
写作的过程很快,大概只有几个月就写完了。
1979年秋天就交稿。
但思考的时间很长。
1957年我在敦煌千佛寺呆了整一个月,对每个洞穴都写了简记和感受。
那年我还看了山西永乐宫、龙门、麦积山、西安博物馆、半坡。
故宫藏得名画如《清明上河图》等等也早看过,还作了点笔记。
中国文学读中学时便熟悉,一些看法早就有了。
对中国历史我也较熟悉。
中国历代的皇帝除元代外,当年我都能背下来;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和好些人物很清楚,对社会文化情况也较有了解。
“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这一部分,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思考了;“明清文艺思潮”的大部分内容,五十年代在我的一些文章都已经谈过。
“盛唐之音”这一部分,是六十年代开始思考的,那时候我下放到湖北,在农田劳动,忽然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在脑际浮现。
当时大陆上对《春江花月夜》是批判的,认为是颓废的文学,我觉得恰恰相反,它是“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时代对人生、宇宙最初觉醒的‘自我意识’”,是通向“盛唐之音”的反映。
“青铜饕餮”是七十年代,也就是文革期间写的……许多年断断续续的思考,许多年陆陆续续的写下来的笔记,在短时间里积累完成了《美的历程》。
我主要的兴趣在哲学,我认为哲学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命运,离不开“历史”。
经过“文革”的浩劫,我更不满足于当时大陆“僵化”及“割碎”的美学和文学史、美术史,《美的历程》就在这样的心情下动笔了。
这本书,每章每节都是我想出来的,都有些新东西,在当时都是特意“标新立义”,很多提法、观点等等,都是以前没人谈过的。
包括如“龙飞凤舞”,本来现成词语,用来讲远古,却是我想出来的。
“儒道互补”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词。
写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有意义,是会有影响。
现在看来,这本书好象都只是常识,但在当时,每章每节都不是常识,都是跟当时的“常识”即主流意见相反的,这可以拿当时的那些书、文章对照。
在材料运用上,有人说《历程》引的材料都是大路货,我当时是自觉这样去做的,我就是要引用大家非常熟悉的诗词、图片、材料,不去引那些大家不熟悉的,就是要在普通材料、大路货中,讲出另外的东西来。
大路货你讲出一个新道道,就会觉得更亲切,有“点石成金”的效果。
《历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艺术史论著,而是讲哲学美学,是“审美趣味史”,是从外部对艺术史作些描述,但又并不是对艺术史作什么研究。
有人把《历程》当作讲艺术史的专著,那就完全错误了。
我只是讲美学而且是哲学美学而已。
它并非艺术史著作,而只是一本欣赏书,而且是“鸟瞰似的观花”的“笼统”(见该书“结语”)粗略之作,因此便不可能作任何细部分析。
《历程》小书十余万言,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从文学、各类艺术到历史和哲学),涉及人物、作品、事件、思想百十,自己并非专家(也不可能“专”那么多家),实自不量力,姑妄言之。
书中各项主题如雕塑、绘画、文学(诗、词、曲)三类型三境界说、两种盛唐说、楚汉浪漫主义、魏晋文的自觉、汉唐艺术比较、明清文艺思潮、龙飞凤舞、青铜饕餮(“狞历的美”)等等等等,虽自矜属于创见,却可能贻笑方家。
但均为美学欣赏,而非艺术概括。
由于是趣味史,所以我从历史、社会、思潮等讲起。
也的确没有人这样把文学、美术、考古,统统放到一锅煮。
有文学史、艺术史等各个门类的史,以及美学史,就没有《美的历程》这样的审美趣味史。
书中那些照片是我挑选的,那时文物出版社给了很多照片,我挑了一些。
文物出版社最初联系的编辑不敢出,觉得这书卖不掉,但另一个编辑说:
你卖不掉就堆到我办公室,结果很快就卖掉了,而且赚了钱。
那编辑室有很好的一位编辑,可惜他过早去世了。
有一事,略感遗憾,起初《美的历程》篇幅较大、资料也很多,如在明、清部分写了很多的内容,但出版社要求字数压缩,只好压掉了,很多材料没有用上。
书出版后,影响很大,销路很好。
但也招来大量的攻击、责难、批评,认为《美的历程》“属于基本史实的常识性错误就够怵目惊心了”、写法也是“不伦不类”,根本不该出版这种书,等等等等。
总之就是惹恼了不少人。
记得当时蔡仪主办的美学杂志便用整版封面刊登了一幅有大字的赵佶的花鸟画,配合专文批判我犯了“常识性大错”。
刘再复讲:
“八十年代有人嘲笑说,《美的历程》算什么,既不是文学史又不是艺术史。
有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对我说,李泽厚这本书一锅煮。
我说,它的好处就是一锅煮。
”的确,《美的历程》说不清该算什么样的著作,专论?
通史?
散文?
札记?
……都是,都不是。
但这也正是它的特点所在。
冯友兰先生不搞美学,却是最早给予我的《美的历程》一书最高评价的人,我非常感谢他。
他写信给我说:
“《美的历程》是一部大书(应该说是几部大书)是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一部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文化史,这些不同的部门,你讲通了。
死的历史,你讲活了。
”(此信以《谈〈美的历程〉——给李泽厚的信》为题刊于《中国哲学》第9辑1983年)此外,胡绳、刘纲纪、包遵信、章培恒等学者也都说了好话,海外也有评论说《历程》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后的又一部名著,但大多数学者则保持沉默。
最近有人还给我看一些材料,除了一些学者,一些著名作家、音乐家等,也说受过此书影响,如:
“著名作家陈忠实自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集中读过李泽厚的著作,当时一起掺和着读的,还有另一位学者谈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本书。
这两本书,陈忠实自称让他看到了文学的另一种表述可能。
”“(著名作曲家)叶小纲特别说明了《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经历。
‘这首作品是我青年时代迈向音乐的第一步。
它的灵感来自于对敦煌古乐谱的研究以及魏晋南北朝佛像雕塑。
当时,李泽厚《美的历程》出版,他提出,佛像洞察一切的微笑是对苦难最大的蔑视,这给了我无垠的想象力。
’”这些是我所没有想到的,颇感意外。
1987年我到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讲学,在那里我完成并出版了《华夏美学》(1988年)。
这本书在搞《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时已经写了一半,是和《美的历程》配套的,在构思上也是交错的。
这是我一开头便承诺的谈中国美学的“内外篇”,内篇讲美的观念,外篇讲趣味流变。
《华夏美学》提出中国美学仍以儒学为主流,这是颇有异于许多中外论著的。
在渐次论述了远古的礼乐、孔孟的人道、庄生的逍遥、屈子的深情和禅宗的形上追索后,得出结论:
中国哲学、美学和文艺,以至伦理政治等等,都是建基于一种心理主义上,这种心理主义不是某种经验科学的对象,而是以情感为本体的哲学命题。
这个本体,不是上帝,不是道德,不是理智,而是情理相融的人性心理。
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感性,是为审美的形上学。
这种哲学—美学思想对今日和未来,对设想更为健康更为愉悦的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生活和人生境地,希望仍有参考价值。
本书结语部分明确提出了“情本体”思想:
“什么是本体?
本体是最后的实在、一切的根源。
……这本体只能是人。
……这个人性也就是心理本体,……心理本体的重要内涵是人性情感。
……这个似乎是普遍性的情感积淀和本体结构,却又恰恰只存于个体对‘此在’的主动把握中,在人生奋力中,在战斗情怀中,在爱情火焰中,在巨大乡愁中,在离伤别恨中,在人世苍凉和孤独中,在大自然山水花鸟、风霜雪月的或赏心悦目或淡淡哀愁或悲喜双遣的直感观照中,当然也在艺术对这些人生之味的浓缩中。
去把握、去感受、去珍惜它们吧!
在这感受、把握和珍惜中,你便既参与了人类心理本体的建构和积淀,同时又是对它的突破和创新。
因为每个个体的感性存在和‘此在’,都是独一无二的。
”
在新加坡,我还完成和出版了《美学四讲》(1989年),我的美学观点主要在这书里。
这之前的1980年,我曾出版过《美学论集》,收录了我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论文,还有几篇七十年代末的。
五十年代的美学文章相当幼稚、不能再看,特别是文字嚣张浅陋,用词激烈,自己看来都觉得汗颜之至。
今日看来,如强调从本质论、反映论谈美学、典型、意境等等,似多可笑;但过来人则深知在当年封脑锢心、万马齐喑下理论挣扎和冲破藩蓠之苦痛艰难;斑斑印痕,于斯足见。
从而,其中主要论点又与后来之变化发展有一脉相沿承者在。
《美学论集》一出来,刘再复第一个说:
“你是有体系的。
”我当时听到时印象很深,因为还没有人这么说过,只我自己心里知道。
后来讲这话的人就比较多了,但都只是在口头上讲的。
《美学四讲》由四次演讲记录稿加以调整连贯,予以修改补充,裁剪贴之而成,一应读者要求“系统”,二践出版《美学引论》之早年承诺。
本书对美学是什么、美是什么、美感是什么、艺术是什么这四个问题作了一些基本的说明。
有些思想和提法与五六十年代有变化,但主要观点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本书主要是从哲学讲美学,还是讲哲学问题的。
其中吸取了一些现代的成果,像分析哲学、格式塔的心理学等等。
对存在主义、弗洛依德,我在书里都作了哪些赞同哪些不赞同的说明。
香港版的书店做广告说,它“回应了现时流行的中外各美学流派”。
2010年《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NortonAnthologyofTheoryandCriticism)第二版收的就是《四讲》第四章第二节“形式层与原始积淀”。
我讲我的美学没有变化,是说基本观点没有变化,但就美在我的思想中的地位而言,就美学在我的理论结构中的位置而言,那是有变化的,因为后来我的美学思想成为我的哲学思想的一部分。
这种变化与我后来研究康德哲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有关系。
有人说,你又搞中国古代思想史、又搞康德哲学、又搞美学,弄不到一起呀。
我呢,恰恰是思考哲学的根本问题时,三位一体了。
所以,讲美的本质,后来就发展了。
美与人密切相关,那么,回到康德的那些问题,它的哲学意义自然就增强了。
再有美学的地位问题。
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宗教的那个境界,所以我把美学提得很高。
这些思想慢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西,一个哲学结构。
在西方,美学本身就是哲学嘛。
我谈具体美学问题很少,但把美学摆的地位很高。
我在书的结尾讲:
“于是,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本体、感性和偶然吧。
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everydaylife)中来吧!
不要再受任何形上观念的控制支配,主动来迎接、组合和打破这积淀吧。
……于是,情感本体万岁,新感性万岁,人类万岁。
”这即是“情本体”思想了。
《四讲》以后,我就告别美学了。
我只是在哲学上概括一些美学问题,不做具体的实证的研究。
我也只能停在这里,无法多言。
我讲过,要么做艺术社会学研究,要么做审美心理学研究,但我自己不打算搞,所以就告别美学,搞别的东西了。
相比《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在学理上更重要,但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这两本书产生影响,那已是很晚了。
八十年代出版的这三本美学书,后来被人们冠以“美学三书”名,不断重印,并都译成英文,有的还译为德文、日文、韩文等。
这里,可顺便讲一下八十年代我做的三件事,都与美学有关:
一是,主编《美学》杂志。
因为开本较大、每期字数多、影响大,人们称之为“大美学”,一年一期或两期。
挂的名是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办,实际没有什么编辑部,就我一个人在干,从策划到组稿到审稿到发稿。
我那时只看质量,不看人,无名小卒,只要文章好,我都用。
大名人的文章,倒不一定。
“大美学”当时大家的反映还是比较好的。
“大美学”从创刊到停刊,历时八年,出版七期。
后来感觉文章太一般化,而要深入下去,也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于是就停办了。
还有,就是出了一套“美学译文丛书”。
是我和滕守尧共同主编的,原计划出一百种,实出五十种。
那套丛书是在所有丛书里最早的,但进度却是最慢的。
当时翻译西方的东西是禁区,可能会是一个罪名,因为你是在贩卖资产阶级的东西嘛。
就有人警告我,说你不能搞这个。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理解。
我感到高兴的是,许多搞美学、搞艺术的人都买了,好些有关美学、文艺理论、批评以及其他论著中,常常见到引用这些丛书中的材料。
这说明,尽管有缺点、毛病,这套丛书毕竟还是有用的。
但这里我想说明的是,这主要是滕守尧的功劳,没有他,便不会有这套丛书。
许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也一直不吭声。
我要他共署主编,他因顾虑客观环境,坚决不肯,这对我倒形成了“掠人之美”的心理负担,今天一吐为快。
第三件事,是与刘纲纪合作写《中国美学史》。
1979年哲学所成立美学室时,我提议集体编写一部三卷本的《中国美学史》,因为古今中外似乎还没有这种书。
后来,我又请刘纲纪先生共同主编,出版社起初不赞同,经我说服同意了。
此书由我与刘商定内容、观点、章目、形式,由刘执笔写成,我通读定稿。
因是刘执笔写成的,所以我始终不把这部书列入我的著作中,尽管我提供了某些基本观点。
在通读定稿时,我从内容和文字进行了某些修改,但不多,因亊先已作了许多商定。
也不强求全书必须完全贯彻我的观点。
我认为《中国美学史》是一部知识的书,许多部分是为了解释材料、分析材料,与《美的历程》有所不同。
“思想史三论”
八十年代颇为热闹,“美学热”之后,又出现了“文化热”。
从广义上说,“文化热”里头也包括了“美学热”,或者说“美学热”是“文化热”的前奏或一部分。
从“美学热”过渡到“文化热”,便不是偶然的,是有线索可求的。
八十年代中期产生了三大民间文化机构: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
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
可以说是“文化热”的标志。
我和三个文化机构都有联系,但都未深入参与。
既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成员,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
《文化:
中国与世界》创刊前和我讨论过,这个名字还是我最后和他们确定的,但我没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写了“思想史三论”。
最早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年出版,与《批判》同年,但晚几个月。
收的十篇文章,实际写于两个不同时期。
三篇《研究》(1958年以《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次略有增改)和孙中山文写成、发表于五十年代大跃进运动之前,其他各篇写成和发表于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后。
尽管二者合成此书时作了一些统一修改,但毕竟各自带有时代的不同印痕。
写于五十年代的大体坐而论道,从容不迫,分析较细,材料较全,一些人如王元化先生就很喜欢。
哈佛大学的一位德国博士生曾将谈谭嗣同一文译为英文。
他当时说佩服我分析得那么细,认为我应该搞分析哲学,当时那是哲学主流。
而写于七十年代的则又失之过粗,基本是些提纲性的东西,但搞现代思想史的金冲及先生,当时却跟我说:
你最近的几篇文章,比过去好。
时值毛刚去世,人们思想似一片茫然,这书通过近代思想人物的论述,提出了一些看法,其中好些的确是有所指而发,只是相当含蓄,点到为止。
我并没有影射,只是指出历史的“客观规律”使类似现象重复出现。
这里可提一下黎澍先生。
当时的《历史研究》是黎澍主编的。
那时《历史研究》思想是非常解放的,应该算一面旗帜,可惜现在大家都不提,许多人不知道黎澍,太不公平了。
我七八十年代文章发得多,各刊物报纸都有,但主要在《历史研究》。
黎澍思想解放的比较早,比李慎之早。
黎澍对我的文章特别喜欢。
我写辛亥革命的文章他就是作为刊物头条登出来的。
我的文章极少作头条,所以这篇(就是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这一篇)记得特清楚,当时有哲学所的同事提起,我也挺高兴。
现在看来《近代》就是很普通一本书,但在当时却颇为轰动,在“思想史三论”中影响最大,此已难为今人理解了。
出版者曾亲口说,假如差半年这本书就出不来了。
就可以见到当时整个气氛是什么情况。
当时人家认为我离经叛道已经很远了。
在当时封闭多年、思想阻塞的年代里,这本书算是起了开风气先的作用。
所以对今天读者是如此平淡无奇的普通常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非同小可的危险话语。
我吃惊地听到一些作家、艺术家说,这本书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记得获奖小说《拂晓前的葬礼》的作者王兆军还到过我家,说谈太平天国文,对他创作小说有启发和具体的指导意义。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此书已经彻底“过时”,它的好些历史观察和价值描述是至今仍然有其意义的,其中也的确有意蕴含了后来在《現代》等书中展开以及至今尚未展开的好些思想、观点、看法。
如《论严复》(1978年),就提出“法国式”与“英国式”之分。
我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方式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这些看法现在看起来实在平淡无味,但记得当时写时,还不免胆战心惊。
时春寒尚重,“凡是”尤存,“革命气氛”仍然浓烈。
我想,不要被人识破话中有话就好。
所以,不止这一处,这本书好些地方都是“点到为止”,不多发挥。
后来一些人告诉我他们还是“侦破”了。
遗憾的是,现在年轻人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情况似已相当隔膜,完全不能体会和了解此书和其他一些事、一些书的真实情况和作用,因此他们的评论就抓不住要害。
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就已经在考虑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对中国古代思想也形成了一些看法,如庄子反异化等观点就酝酿成熟在自己六、七十年代大读西方存在主义时期。
我的第一篇古代思想史文章是写于1976—1978年、1980年发表的《孔子再评价》。
我在日本讲《孔子再评价》(当时尚未发表),他们一个个都在记,认真记要点,印象极深,使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他们都是日本一些最大的学者。
桑原武夫跟我说,大师级的学者还是出在中国。
这里还有个插曲,黎澍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号称中国最高学术刊物,本来要将《孔子再评价》和顾准的文章一起发在创刊号上的,后来有人反对,是一些老先生,王明、容肇祖、张岱年等等,他们说唯物唯心此文一字未提,阶级斗争也未提,大有问题,创刊号就没发成。
发在第二期上。
顾准的遗文后来就一直没在那刊物上发出来。
《孔子再评价》这篇文章发表之初,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是情况很快也就改观了,也变得比较能够接受了。
文章提出“仁的结构”中的“心理原则”,突出的是“情”而非“理”。
人性是人心的情理结构,而不只是理性。
我至今仍然坚持“仁”是这个四方面的结构体,即由“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所形成的人性结构,也就是我后来《论语今读》所提出的“情理结构”(emotio-rationalstructure)即“情本体”(emotionassubstance),其中的情理交会既区别于禽兽动物,也区别于理性机器,这是我数十年没有变动的人性论的观点圆心。
文章还初步提出了“巫史传统”观念,一开头就讲这个“巫术礼仪”的问题,并与当年对少数民族鄂温克人调查研究相比较,认为周礼是通过“祭神(祖先)”的礼仪扩而成为社会组织、生活规范的整套规范。
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制度、贵族生活规范、社会等级规则等等。
1999年发表的《说巫术传统》更具体地展开了一些。
《孔子再评价》实际标志着以原典儒学来吸收融会康德和马克思以眺望未来。
当时反传统高涨,未能多说。
《中国社会科学》还刊载了我的《宋明理学片论》(1982年)、《秦汉思想简议》(1984年)、《漫述庄禅》(1985年)。
谈庄禅玄的那篇发表后,钱学森先生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立了功!
”,并把这篇文章收到他主编的《关于思维科学》书中。
1985年我将八十年代陆续发表的有关古代思想的文章汇集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并以《近代》为前导。
这本书我试图改变一下几十年来中国哲学史只是简单地分割、罗列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的陈陈相因的面貌。
我想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等角度进行研究,我希望这种研究能略有新意。
比如孔子吧,有多少哲学史就可以说有多少位孔子,每个人都有他所理解的孔子,并且都认为这才是那个“真正的”孔子思想。
我的兴趣却不在这里,而主要是想探究一下两千多年来已融化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行为中的孔子,看看他给中国人留下了什么痕迹,给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带来了些什么长处和弱点。
这个孔子,倒是个活生生的,就在你、我、他以及许多中国人中间。
因为集中在这个概括性的主题之上,我就只能选择一些最有代表性、最有实际影响的人物和思潮,弃而不论许多比较起来属于次要的人物、学派和思想。
例如先秦的名家以及其他好些非常著名甚至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也舍弃了所论述的人物、思潮中离这一主题关系较远的方面、内容和层次,当然更完全舍弃了一些属于考证范围的问题如人物生平、史料源流、版本真伪等等。
总之,本书所作的只是一种十分粗略的轮廓述评。
我丝毫不想以齐备为目的,只望能在舍弃中更突出所要研讨的主题:
即在构成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起了最为主要作用的那些思想传统。
同时在论述中也尽量注意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以避开重复。
本书上下数千年,十几万字就打发掉了,自己写作时,便深感底子太薄,功力不够,知识太少,不可能也不应该驾驭这么大的场面,甚至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写这种东西了”。
但结果居然还强如人意,这书在海内外的反应都不坏,不断被人提及甚至还受到赞赏。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本。
原因是尽管材料少,论述粗,但毕竟是企图对中国整个传统作某种鸟瞰式的追索、探寻和阐释,其中提出的一些观念和看法,如“乐感文化”、“实用理性”、“文化心理结构”、“审美的天地境界”等等,我至今以为是相当重要的。
我自认对中国思想史除了对荀子的评估、说庄子哲学是美学等等次要成果外,至少有三个重要创获,它们都是假说,有待以后科学论证其真伪:
一是“巫史传统”(巫的理性化),二是“情本体”,三是“兵家辩证法”。
我希望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文化传统在东西方人文世界进行真正深入的对话中,能有自己的立场和贡献。
因此,此书之作,似乎比《近》、《现》二册,便有更深一层的目标和涵义了。
这本书在当时没什么影响,真正有影响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有更多的人引用和赞同。
由于《古代》对传统文化作了相当多的肯定,与新儒家有相近的地方,不少青年学子认为它背离了《近代》反传统的批判精神,说我“转向”了、倒退了,认为我自相矛盾:
《近代》、《现代》二书反封建、反传统,《古代》却大说传统的好话。
其实不然。
简单说来,这正是今日中国现实的深刻“吊诡”和关键所在:
中国要进入现代化,当然要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意义上反掉某些前现代的传统;但今日中国又应该是在看到后现代的前景下来进入现代,从而才可能尽量避免或减轻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灾难、弊病和祸害,因此,注意保存传统又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也许这样,才能尝试去走出一条既现代又中国、既非过去的“社会主义”又优越于今日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的道路来。
我写了一篇《关于儒家与“现代新儒家”》,阐释了《古代》与港台“新儒家”的区别。
但那时正是反传统的高潮,几乎都在反孔。
当时有四大名将,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刘某某,各从启蒙主义、科学主义、基督教、尼采来批孔和反传统。
于是,有人就说:
“孔子死了。
李泽厚老了。
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
”我被视为保守、陈旧,成为被某些青年特别“选择”出来的批判对象。
从此,我便需要两面应战,一面是正统“左派”,一面是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