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docx
《《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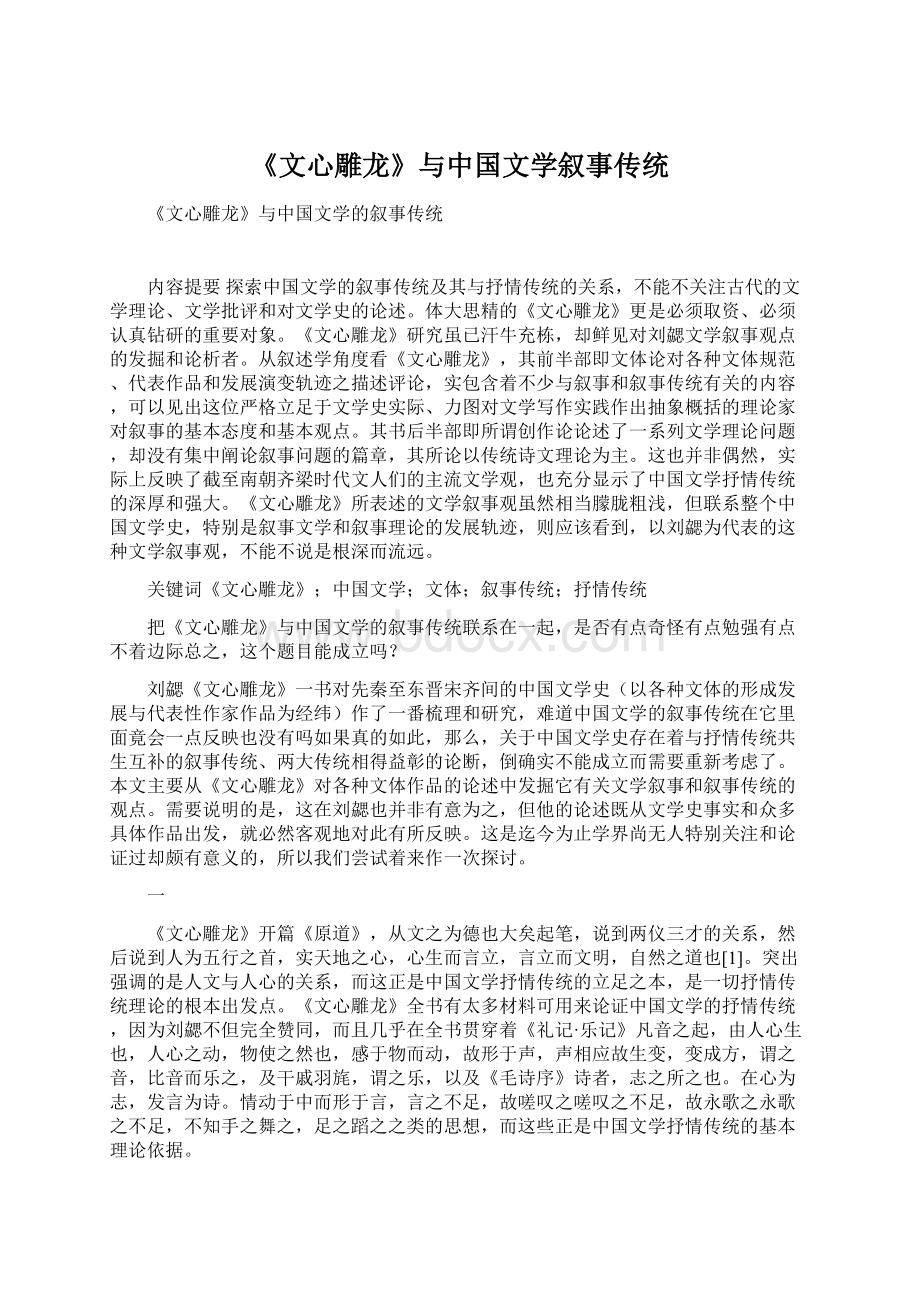
《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
内容提要探索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及其与抒情传统的关系,不能不关注古代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对文学史的论述。
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更是必须取资、必须认真钻研的重要对象。
《文心雕龙》研究虽已汗牛充栋,却鲜见对刘勰文学叙事观点的发掘和论析者。
从叙述学角度看《文心雕龙》,其前半部即文体论对各种文体规范、代表作品和发展演变轨迹之描述评论,实包含着不少与叙事和叙事传统有关的内容,可以见出这位严格立足于文学史实际、力图对文学写作实践作出抽象概括的理论家对叙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
其书后半部即所谓创作论论述了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却没有集中阐论叙事问题的篇章,其所论以传统诗文理论为主。
这也并非偶然,实际上反映了截至南朝齐梁时代文人们的主流文学观,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深厚和强大。
《文心雕龙》所表述的文学叙事观虽然相当朦胧粗浅,但联系整个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叙事文学和叙事理论的发展轨迹,则应该看到,以刘勰为代表的这种文学叙事观,不能不说是根深而流远。
关键词《文心雕龙》;中国文学;文体;叙事传统;抒情传统
把《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联系在一起,是否有点奇怪有点勉强有点不着边际总之,这个题目能成立吗?
刘勰《文心雕龙》一书对先秦至东晋宋齐间的中国文学史(以各种文体的形成发展与代表性作家作品为经纬)作了一番梳理和研究,难道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在它里面竟会一点反映也没有吗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中国文学史存在着与抒情传统共生互补的叙事传统、两大传统相得益彰的论断,倒确实不能成立而需要重新考虑了。
本文主要从《文心雕龙》对各种文体作品的论述中发掘它有关文学叙事和叙事传统的观点。
需要说明的是,这在刘勰也并非有意为之,但他的论述既从文学史事实和众多具体作品出发,就必然客观地对此有所反映。
这是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人特别关注和论证过却颇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尝试着来作一次探讨。
一
《文心雕龙》开篇《原道》,从文之为德也大矣起笔,说到两仪三才的关系,然后说到人为五行之首,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
突出强调的是人文与人心的关系,而这正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立足之本,是一切抒情传统理论的根本出发点。
《文心雕龙》全书有太多材料可用来论证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因为刘勰不但完全赞同,而且几乎在全书贯穿着《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以及《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类的思想,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基本理论依据。
但是,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毕竟是从中国文学实际出发的,当他面对文学史事实、面对形形色色的文章体裁和具体作品时,就会很自然地涉及中国文学的叙事问题,或者是无法回避的文学叙事问题。
而这也必然要反映到他的论述之中,为我们观察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提供许多信息和资料。
《文心雕龙·原道》篇在述及中国文学的源头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后,马上就提到
炎皡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代渺邈,声采靡追。
《三坟》这部传说中的上古佚书,在刘勰描述中应该是一部记事之书,它叙述的是炎皡(炎帝、太皡,即神农、伏羲,代指三皇)时代的遗事。
我们追溯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不能不从中国人的叙事思维和叙事能力讲起。
先民们由口头传承所表现和积累的叙事经验和叙事才能姑且不论,仅据刘勰所言,《三坟》既是记载炎皡遗事的(用了怎样的文字、记了些什么事虽然并不清楚),自然可视为(或推想判断为)上古先民的叙事之作。
此书作为理想中的经典,应该显示出先民们当时所能达到的叙事水平——此书和与之齐名且性质类同的《五典》《八索》《九丘》等虽今皆不存或被视为伪书,而且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实际上是将《尚书》《春秋》作为最早史书,但他和许多古人,如深受他影响的刘知几[2]对《三坟》之类古史的追忆和遐想,该不是空穴来风,故仍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退一步,即使从《尚书》《春秋》算起,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也就够邈远的了。
既要探寻《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关系,查一查事字在《文心雕龙》各篇出现过多少次和它的具体用法,不失为一种方法。
当然,绝非书中每次用到事字均与叙事有关,如《征圣》篇有事迹贵文、徒事华辞二句,即与叙事无甚关系。
但《宗经》篇论到《易》《系》称旨远辞近,言中事隐,论到《礼》以立体,据事制范,这两个事字,就都与经书的叙事有点瓜葛了。
同篇还有论《书》实记言,论《诗》主言志,诂训同《书》,和论包括《春秋》在内的五经的总体特征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实际上就把五经与叙事联系了起来——五经所记述的虽都是古圣当时种种事情(所谓事近指那些事与古圣生活时代为近),但那些事所喻指的意义却远至后世直到今日仍然有效,这就是刘勰强调后人著文必须宗经的理由。
[3]按照刘勰的看法,五经是后代一切文章的源头和楷模。
这说法固然笼统牵强,纪昀就曾给予批评。
[4]但由此而引出的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之论,却代表着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纲领
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这纲领既涉及抒情文学,也涉及叙事文学,而其中的第三条和第一条,再明白不过地说出了文学与事、与情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都离不开事,世上哪有无事的文学文学的抒情也总是因事而起,并须托事而行才不直白空虚、单调乏味。
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状况看,文学之事既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表现于作品之中(即下文所谓事在诗中),也可以作为背景而存在于作品之外(即下文所谓事在诗外)既可叙述得原原本本、完整细致,也可表现为神龙不见全体而只现鳞爪。
而刘勰不但认为文学离不开事,并且还明确提出要求事信而不诞——真实可靠乃是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重要内涵,此论渊源有自而影响极为深远。
同时,文学又怎能无情就算作者拼命把情感砌没在叙述、描写或咏叹的壁垒里面,读者仍然会透过可见的文字符码感受到并发掘出其深藏的情意。
对此,刘勰的提法是情深而不诡,其最根本要义仍然是真实深沉、不伪不虚。
需要说明的是,《宗经》篇所提的六义,每一条都是对着文学的总体而言,在刘勰的概念里并不存在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之分(岂但无抒情叙事之分,就连文学与非文学都与今人的认识差异颇大)。
是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向我们显示文学作品从表达的层面看,确有侧重抒情还是侧重叙事的不同,也由此而才产生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可以并且应该二分的看法。
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这两大传统,我们的认识过程大致是由模糊混沌渐趋明辨清晰,逐步地发现并掌握了它们的差异,觉得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但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让这两大传统分庭抗礼,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论证它们的关系——它们本来是既有所区别又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但又毕竟你是你我是我的关系,把这种关系论证清楚,将有助于更深刻地揭示中国文学的特质和中国文学史的真实面貌。
二
《原道》《征圣》《宗经》之后,是《正纬》《辨骚》两篇。
刘勰在说明写作宗旨的《文心雕龙·序志》篇说,这篇是全书的纲领,阐论的乃是具有根本性的文之枢纽问题。
所谓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前三者属于执正,后二者则是驭奇,合之,便是刘勰极力提倡的文学创作最佳方式。
但在我们看来,纬书和楚骚其实也都是古代文类之一,如果将《正纬》《辨骚》两篇和《明诗》以下篇,都当文体论视之,虽似有违刘勰的自述,却也未必全然无理。
而从刘勰对各种文体名称的解释、规范的描述,对各类范文的分析和文病的批评,我们正可以具体而微地觅见和体察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某些斑痕乃至轨迹。
在人们印象中,纬常与谶合称为谶纬,是古人迷信思想、荒诞谬说的大杂烩,它在隋代遭到禁绝,从此不再流传。
《文心雕龙·正纬》主要以经书为准绳批判纠正谶纬的作伪和无稽,所谓按经验纬,其伪有四云云。
其实,据历代学者研究,谶与纬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谶多托古圣贤而言符命灾异,其说确实诞妄纬则为配经而作,虽亦多附会凿空之谈,但正如刘勰所说若乃羲农轩皡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鸟之符,黄银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可见也不尽是废物,特别是对于文学来说。
上引文中事丰二字,很值得注意。
这说明纬书颇具叙事性质,而且所叙之事甚为丰富,有助于扩展作文所需的想象。
刘师培《谶纬论》曾说纬有五善,可以用来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征礼。
从他所列举的例子,可知纬书中包含着上古神话、各类传说、历史遗闻,乃至地理天文知识等等,而且往往出之以华丽繁缛的辞藻。
[5]在学术史上纬书常常充当被批判的对象,今天我们也无意为之翻案,然而从叙事视角、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观之,则应指出因其本身属于文学历史的一环而应有它的研究价值。
纬书与叙事有关,楚骚又如何以屈原的《离骚》而言,当然是抒情之作,一向是被放在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中来论述的。
可是,刘勰在《辨骚》篇论及它在内容上具有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面时,举例道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恕之辞也。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
仅从这些例子,不是就能看到《离骚》所叙到的种种故事吗《离骚》正是通过对种种史事、神话、传说和对政治现状充满感情色彩与褒贬倾向的叙述(其具体手法又是多种多样的)才得以将胸中积郁的忠君爱国和强烈愤懑之情抒发出来。
在论到屈骚继承者的创作时,刘勰写道自《九怀》(西汉王褒作)以下,……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
这里说的是《九怀》以下一批作品的内容。
请注意刘勰所用的动词叙述、论、言。
当然,我们不可望文生义,以为一见叙字,便是叙事。
叙情怨如果是指直接描叙作者主观的感情,这种叙其实是抒情。
而所谓叙事,则指对作者主观心灵以外任何客观事物、事件事态的描述。
文学作品少不了描写和叙述,描叙的对象有主观(心)、客观(物、事、状态、过程等等)之分,前者通常也称为直陈胸臆,即通常所谓抒情(含议论)后者则与之相对,可概称之为叙事。
叙情怨也就是抒情怨,那么,述离居、论山水、言节候呢所写对象均为客观的事或物,故无论是述、论还是言都应归入叙事一类。
由此看来,楚辞系列的作品,就绝非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无关,而是抒、叙结合的典范,只是我们以前很少从这个视角加以考察罢了。
[6]
《明诗》《乐府》两篇论诗歌,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次序,集中而承上启下地阐发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方方面面。
承上,是说其对诗歌起源、本质、功能、评判标准等基本问题的看法,与《尚书·尧典》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及《毛诗序》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等等经典性言论,完全一致。
启下,是说它的有些说法,特别是对自先秦至晋宋历代诗歌的评论,又成为后人常常引用的名言,如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创作动因物感说,如叙诗歌从四言到五言的发展,对曹丕、曹植及王、徐、应、刘等建安诗人风格特色的概括,对正始、西晋、江左诗风演变轨迹的描述,直到对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的判断,均成为后世论者(直至今日文学史研究者)依凭的准绳。
在刘勰心目中,诗与歌皆纯系抒情之具,故《明诗》《乐府》两篇均无从叙事角度观察分析的论述。
这两篇可以说是论中国文学抒情传统集中而经典的文字。
而且,由于文学观的关系,刘勰对文学叙事颇存偏见,对叙事性强的诗歌比较歧视,说得轻一些,起码也是缺乏应有认识。
故《乐府》篇对那些叙事色彩鲜明、为后来文学史十分重视的乐府和文人拟乐府作品,如汉乐府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和南朝民歌(吴声歌曲、西曲歌),如曹操《苦寒行》、曹丕《燕歌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等,要么根本不提,要么评价不高。
倘与时代相近的《玉台新咏》相比,刘勰对乐府民歌的轻视就更显突出来。
王运熙先生分析这一现象,认为原因在于刘勰认为民间色彩浓郁的乐府诗内容浅陋,艺术上过于质朴鄙俗,缺乏文采,即所谓直而野。
这是南朝正统文人的普遍观点,不惟刘勰如此,钟嵘、萧统也是一样,《玉台新咏》则是个例外。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从《明诗》《乐府》两篇的行文仍能发现诗歌与叙事及叙事传统的某些线索。
如《明诗》篇论及建安诸子的作品(主要指公宴诗),有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语,其中述恩荣,叙酣宴,就明白地用了叙、述二字,说明刘勰实不能回避他们诗中所含的叙事成分——事实上,如无对恩荣、酣宴的具体描写叙述,又怎能表现出对风月的怜和对池苑的狎呢接下去,刘勰概括建安诸公共同的诗风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这里的造怀指事就又和创作中对某些事情的叙述有关,有的研究者就把它解释为述怀叙事[7]。
而驱辞逐貌要达到昭晰即生动鲜明的程度,也不能不对身外事物做出客观细腻的描述。
当然,叙事也好,描写也好,归根到底,目的仍在于抒情言志,刘勰以及历代诗论家因此强调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色和传统,自有其道理,只是把叙事一节撇过不论,现在看来却也欠妥,故我们需要特别拈出。
富于叙事色彩本是乐府诗的一大特色,但《文心雕龙·乐府》篇对此也无论析。
该篇说凡乐辞曰诗,咏声为歌。
在本篇中刘勰着重论述的是乐府的音乐而不是歌词,故不细辨其叙事特色也无可厚非。
可是这也再次说明他对乐府诗的叙事特色的轻忽,因为哪怕有一点点重视,以刘勰思路的缜密严谨,也绝不会在全文中毫不论及此点。
只是乐府诗歌毕竟与事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班固就曾说过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艺文志》刘勰在本篇末引班语,但行文中对此还是不能不有所触及。
请看他说
至于轩、岐《鼓吹》,汉世《铙》《挽》,虽戎丧殊事,而并总入乐府。
这里举例性地提到乐府几种曲辞,属于鼓吹曲辞的铙歌和属于相和歌辞的挽歌。
据沈约《宋书·乐志》鼓吹,盖短箫铙哥(歌)。
蔡邕曰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
(《乐志一》)而挽歌则是丧葬时用的哀乐悲歌。
这两种乐府的音乐和歌词分别与戎、丧二事有关,是为此二事而作,为此二事所用的,虽事情不同,但都纳入了乐府。
我们从保存于《乐府诗集》的歌辞来看,这些戎丧之歌即使未曾描绘具体事件,也应属于事在诗外之列,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为事而作。
而与文学叙事传统关系更为密切的事在诗内的情况,也有例可寻。
试看《汉铙歌十八曲》之一的《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
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或者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当风扬其灰。
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君绝!
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
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感情都很强烈,但那感情不是直接呼喊出来,也不是借用比喻象征(比兴)表达,而是通过一定的情节展示(虽然并不复杂)、场景描绘、人物对话、心理独白等,即在叙事的框架中完成抒情。
就连《上邪》这样抒情性极强的小诗,读来也足以使人想象出男女二人对话当时的情景,甚至不难进一步构想出二人交往的某些情节。
总之,叙事性成为它们显眼的特征,其语言则通俗明快而接近口语。
刘勰绝不会没有发现这些,可惜他不欣赏,甚至视之为弊病,故不予肯定,也不多加论述而已。
赋是诗歌的近亲,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8],就说明了它们的关系。
所以在《明诗》《乐府》之后,就轮到赋了。
《诠赋》篇开头就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写志即抒情,体物是多方面地描绘物象,当然还不是叙事,却又与叙事脱不了干系。
因为体物写志与中国诗学之物感说有关,而物感说与事感说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又有前后相承继之谊,钟嵘《诗品序》就显示了二者混一的情景。
钟嵘对赋比兴的认识是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由此谈到诗歌创作的动力,乃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离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这就超越了笼统的物感说而进入了与文学叙事传统关系更密切的事感说。
物与事都是外于人的客观存在,而物的范围似乎更大,当然也更笼统。
因泛泛的物之动而感于心,而发为诗,这是文学抒情传统的理论基石,历代论者已将其义发挥殆尽。
事是外于人又因人而生的(看上引钟嵘所举种种就很清楚),把它作为文学创作的动力源,显然比物感说更具体,也更切近文学的本质和历史实践。
而从事感说出发,则文学与事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学含事、咏事(歌谣诗词曲赋等擅长)、述事(小说擅长)乃至演事(戏剧擅长)的演化轨迹和承传统系就可清晰呈现。
钟嵘能够提出事感说,与他对赋法直书其事,寓言写物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而《文心雕龙·诠赋》篇对赋义的解释还停留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程度。
故刘勰既没有从理论上看到赋(包括赋法和赋篇)与事的关系,也没有从京殿苑猎,述行叙志(指汉代大赋)和荀结隐语,事数自环(指荀卿赋)的文学创作实际中发现赋体文在想象、内容、谋篇结构和铺写行文中所表现的叙事性特征,当然更不可能看到赋体文这些特征的创新意义。
[9]
三
自《诠赋》篇后,《文心雕龙》的文体论进入合论阶段,每篇不是论述一种文体,而是合论两种文体,如《颂赞》《祝盟》《铭箴》等。
再往后,更有一篇论述多种文体的,如《杂文》《诏策》《书记》等篇。
从我们的眼光看来,自《辨骚》至《诠赋》诸篇所论,大抵接近于后世所谓的纯文学类作品,而《颂赞》篇以下所论则属各种应用文类,其写作都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用途,文学性似乎比不上诗赋那么纯粹。
此类文章在当日种类多数量亦夥,颇受重视,故陆机、挚虞、刘勰、萧统均有所论列。
但在近代某些极端的纯文学论者那里,却将它们判为非文学,甚至将其彻底革出文学之门。
在他们编写的文学史中,此类文章自然绝无踪迹可寻。
经过对文学史百年的反思,我们觉得旧的泛文学观固然不够精密,需要更新,但舶来的纯文学观也不适合中国文学的实际。
而且就文论文,此类文章虽具应用性却也绝非毫无文学价值,《文心雕龙》罗列并加论述,《昭明文选》亦颇多采录,都是对它们文学价值的肯定。
对于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且影响深远的文学和文学观不应视若无睹,我们的文学通史应给此类文章适当的地位和篇幅,至于断代史、文体史和文学史专题研究就更可以将它们作为重要的对象来处理。
现在我们从叙事视角重审中国文学史,就发现此类文章实与文学叙事传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构成中国文学叙事传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撇除了它们,就切掉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一个环节,从而破坏了中国文学史的完整性。
我们还是看《文心雕龙》怎样论述颂、赞、祝、盟、铭、箴这几种文体吧。
“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颂体文章原是为颂扬人的功德以告于神明而作。
可想而知它必定要这样那样地涉及对人和人事的描述。
“赞者,明也,助也。
远古时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
”点出了赞文(言)与已然之事迹的关系。
后来像《史记》《汉书》以及《文心雕龙》各篇末尾的赞语,是对全文的简约小结,功用是表明作者的观点和用意,因为多置于史文之末,涉及相关的人与事也是必然的。
祝文系向神灵或祖先祷祝祈求佑护之辞,“所以寅虔于神祇,严恭于宗庙也”。
这里,有着人向神诉说之意味,而诉说,就不能是纯粹抒情,表达愿望也须在叙述一番状况(事情)之后。
盟文则是两造订立盟约时的誓词,所谓“盟者,明也”,“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其中“序(叙)危机”,即描述双方面临的共同危机,是其余一切的基础。
至于铭箴,“铭者,名也”,铭文所记述的内容,为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总之是天子诸侯大夫们的事迹功勋。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
刘勰说,箴的文体要求是“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
不但指出了箴体文章与事有关,而且对箴的取事提出了核以辨的要求。
在对种文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之后,便是选文以定篇,即举出范文,进行文章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敷理以举统,即作出理论概括,梳理文统。
刘勰上面的论述已经显示,这种文体均为当时的实际事务而作,其文总是与一定的事有关,这些事自然也要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表现在文章之中——这在我们看来,正是形形色色的叙事。
从刘勰所选的诸多文例也足以证实这一点,下面略举例证,以见一斑。
《颂赞》选文以定篇举出的第一个例子是周公所作的《时迈》,此文现存《诗经·周颂》之中。
毛序、郑笺,特别是孔颖达《正义》对本诗作者、主题和创作背景有所说明。
孔疏根据《左传》《国语》对此颂的记载,云:
“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柴望之礼。
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业,故述其事而为此歌焉。
”(6)可见《时迈》乃是周公向昊天陈述武王克商,威震天下,从此干戈弓矢均可藏而不用,而在全国施行美政,特求昊天保佑。
祈求保佑是目的,而叙事陈情则是这篇颂诗所用的手段。
以下举出的,如屈原的《桔颂》、李斯为秦皇巡行所制的诸多刻石文,直到子云(扬雄)之表(赵)充国,孟坚(班固)之序戴侯(窦融),武仲(傅毅)之美显宗(东汉明帝),史岑之述熹后(东汉和帝皇后),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但都还算颂体的范文。
刘勰在这里所用的动词表序(同叙)、美、述,即多与叙事有关。
可见颂体本是具有叙事性的——当然,颂文的叙事要求是高度概括而无需具体,不铺叙,更不描写,所以像《北征颂》(班固)、《西征颂》(傅毅)、《广成颂》(马融)、《上林颂》(马融),以及崔瑗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等就因叙述成分过重而受到刘勰的批评。
[10]刘勰的文体观比较明确,力求划清各种文体的界限,但过于强调文体的规定性,不赞成交叉和突破。
殊不知文体之交叉互渗必不可免,文人们的创作实践不会受既有规定的限制牢笼,他们面对不同的对象、需要,从实际出发,又喜逞才,爱创新,就一定会对文体规范有所突破。
结果他们的作品在文体性质上便不免时存模糊,难分彼此——这其实也说明这些文体本身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所谓文体的名称及其规范绝非不能通融,更非一成不变。
而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我们发现,乃是各种文体的叙事成分都呈逐步增加之势,而叙事与抒情议论的关系则愈益密切,且叙事愈益成为抒情议论的基础。
颂文如此,其他几种文体也是如此。
史赞曾因其一定的叙事性而被称为“史述”,[11]当然,这在刘勰看来是不对的。
东汉王延寿的《梦赋》以赋为名,其实是一篇祝文,其序云:
“臣弱冠尝夜寝,见鬼物,与臣战。
遂得东方朔与臣作骂鬼之书,臣遂作赋一篇叙梦。
后人梦者,读诵以却鬼,数数有验。
”范文澜注据《艺文类聚》引录了此赋的残篇,从中可看出其明显的叙事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还是虚构的、想象的叙事。
对于祝文,刘勰还指出其同类或变种很多,像某些祭文和哀策文,义同于诔,而文实告神,诔首而哀末,颂体而祝仪,太史所读之赞,固周之祝文也,这些文章既皆涉及人事,也都不同程度地含有叙事成分。
盟文所举的如臧洪歃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