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docx
《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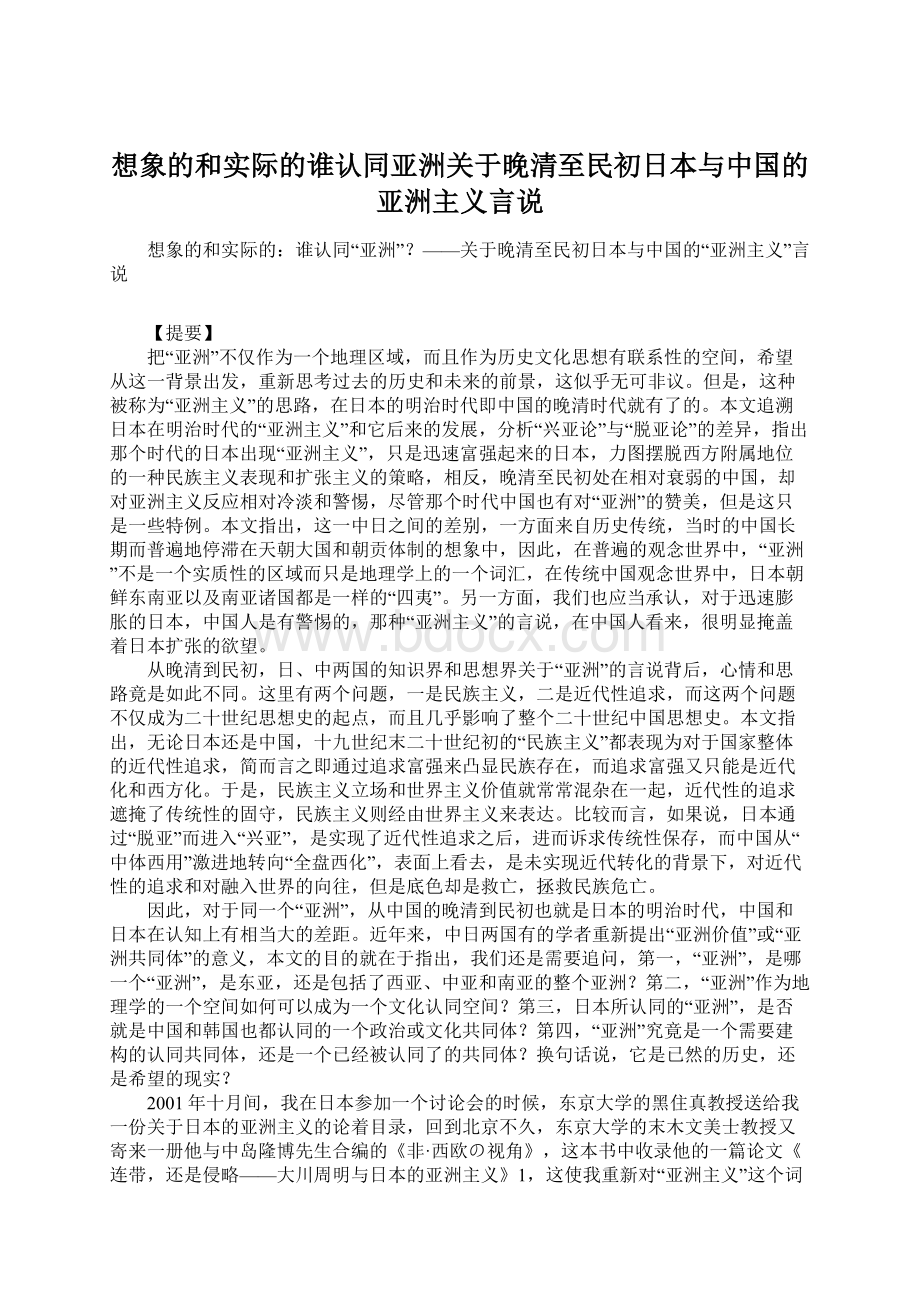
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
想象的和实际的:
谁认同“亚洲”?
——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
【提要】
把“亚洲”不仅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而且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重新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这似乎无可非议。
但是,这种被称为“亚洲主义”的思路,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即中国的晚清时代就有了的。
本文追溯日本在明治时代的“亚洲主义”和它后来的发展,分析“兴亚论”与“脱亚论”的差异,指出那个时代的日本出现“亚洲主义”,只是迅速富强起来的日本,力图摆脱西方附属地位的一种民族主义表现和扩张主义的策略,相反,晚清至民初处在相对衰弱的中国,却对亚洲主义反应相对冷淡和警惕,尽管那个时代中国也有对“亚洲”的赞美,但是这只是一些特例。
本文指出,这一中日之间的差别,一方面来自历史传统,当时的中国长期而普遍地停滞在天朝大国和朝贡体制的想象中,因此,在普遍的观念世界中,“亚洲”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域而只是地理学上的一个词汇,在传统中国观念世界中,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南亚诸国都是一样的“四夷”。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对于迅速膨胀的日本,中国人是有警惕的,那种“亚洲主义”的言说,在中国人看来,很明显掩盖着日本扩张的欲望。
从晚清到民初,日、中两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关于“亚洲”的言说背后,心情和思路竟是如此不同。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民族主义,二是近代性追求,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成为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起点,而且几乎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
本文指出,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族主义”都表现为对于国家整体的近代性追求,简而言之即通过追求富强来凸显民族存在,而追求富强又只能是近代化和西方化。
于是,民族主义立场和世界主义价值就常常混杂在一起,近代性的追求遮掩了传统性的固守,民族主义则经由世界主义来表达。
比较而言,如果说,日本通过“脱亚”而进入“兴亚”,是实现了近代性追求之后,进而诉求传统性保存,而中国从“中体西用”激进地转向“全盘西化”,表面上看去,是未实现近代转化的背景下,对近代性的追求和对融入世界的向往,但是底色却是救亡,拯救民族危亡。
因此,对于同一个“亚洲”,从中国的晚清到民初也就是日本的明治时代,中国和日本在认知上有相当大的差距。
近年来,中日两国有的学者重新提出“亚洲价值”或“亚洲共同体”的意义,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指出,我们还是需要追问,第一,“亚洲”,是哪一个“亚洲”,是东亚,还是包括了西亚、中亚和南亚的整个亚洲?
第二,“亚洲”作为地理学的一个空间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文化认同空间?
第三,日本所认同的“亚洲”,是否就是中国和韩国也都认同的一个政治或文化共同体?
第四,“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建构的认同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
换句话说,它是已然的历史,还是希望的现实?
2001年十月间,我在日本参加一个讨论会的时候,东京大学的黑住真教授送给我一份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的论着目录,回到北京不久,东京大学的末木文美士教授又寄来一册他与中岛隆博先生合编的《非·西欧の视角》,这本书中收录他的一篇论文《连带,还是侵略——大川周明与日本的亚洲主义》1,这使我重新对“亚洲主义”这个词语产生了兴趣2。
自从六十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好等人开始集中讨论“日本的亚洲主义”以后,陆陆续续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似乎新的一轮讨论又在日本开始,根据手边的资料举一些例子,追溯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如1997年小路田泰直的《日本史的思想:
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的冲突》,直接讨论这一问题的像1996年古屋哲夫编的《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间接用这种视角来思考历史的如1992年荒野泰典等合编的《亚洲中的日本史》3,特别是在当代中国也相当有影响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宫岛博史所编的丛书《从亚洲出发思考》,更是再一次在九十年代引起了这个话题4。
把“亚洲”不仅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区域,而且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似乎无可非议,我也曾经在一次会议论文中,以近代佛教为例指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应当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是互为背景与资源的5。
但是,什么时候它却成了“亚洲”而且是“共同体”?
尽管我们承认,日本、韩国、中国的一些学者重提“亚洲”,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重新建构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但是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者什么时候成为过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的“他者”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
且不说亚洲的西部和中部现在大体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也不说文化和历史上与东亚相当有差异的南亚诸国,就是在所谓东亚,即中国、朝鲜和日本,何时、何人曾经认同这样一个共同空间?
竹内好以及相当多的学者当年都曾经指出,这种产生于日本的亚洲主义,在日本“脱亚”入欧追寻近代化的努力已经成功的背景下,引出了“兴亚”并与欧洲分庭抗礼的心情,这使日本一方面重建与亚洲的“连带”关系,另一方面又滋生了凌驾与指导亚洲的“侵略”心情6。
对于这一分析框架,现在尽管有很多学者以为已经相当陈旧,但我以为仍然相当有说服力。
那么,现在重提“亚洲”或者“亚洲共同体”的旧话,如果已经超越了竹内好所说的“连带与侵略”,那么,其背景和心情又是什么呢?
特别是日本所认同的“亚洲”,是否就是中国和韩国也都认同的一个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想象和建构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却还是一个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别从历史上看尤其有疑问。
一、关于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
按照桂岛宣弘氏说法,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潮要追溯到十九世纪前半叶甚至十八世纪末期,当西洋的天文与地理之学改变了面前的世界,使日本人意识到万国的存在和“东洋”、“西洋”的地图时,传统的以中华为文化中心的华夷观念便开始瓦解7,这种世界图像的瓦解成了日本重新建构新的政治地图和文化地图的契机。
而按照山室信一的说法,日本的“亚洲观念”之确立,更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当西川如见作《增补华夷通商考》中的《地球万国一览之图》凸显了“亚洲眼光”、新井白石在《西洋纪闻》中区分了“西洋”和“东洋”,其实已经改变了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8。
不过,尽管历史渊源还可以向上追溯,但通常学者注意到的是日本迅速近代化的明治时期的很多言论,因为,不仅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观念,以及“兴亚论”和“脱亚论”,甚至一切后来的思想史变化,都可以在这个时代找到其原因。
有的学者指出,“兴亚论”与“脱亚论”的差异,是前者以“东洋-西洋”为认同的基础,强调地缘性的作用,而后者以“文明-非文明”为认同的基础,强调近代性的意义。
但是,实际上“亚洲主义”并非单纯强调地缘的作用,它也在凸显一种价值的认同取向,而“欧化主义”也并非仅仅注意到追求欧洲的近代性,它也曾经要求日本在亚洲作为表率,使整个东亚一同摆脱大清帝国中心与传统中国观念世界的笼罩。
因此,像脱亚论的主张者中,最具代表性的福泽谕吉,也曾经在强烈呼吁“脱亚”的时候,其实并不忘记亚洲的连带性9,很多人都注意到,明治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他发表在《时事新报》的《脱亚论》中就有这样的话:
我日本国土在亚洲东部,但国民之精神已经摆脱亚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
然而……为今日谋,我国不能不等待邻国之开明,一道振兴亚洲,与其脱离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度共进退,还不如接引支那、朝鲜……10
当然,同时他也说到,这个亚细亚的同盟,当然不能不以日本为盟主,因为日本在东洋的文明化进程中已经是当然的盟主和领袖11。
这恐怕不是一个福泽谕吉的个人私言,据芝原拓自对日本明治时期中央五大报纸舆论的调查和研究,即使是在一般的民间,也可以看到,自从明治维新以来的十年,已经浸透了骄傲自满的开化日本观和充满蔑视的亚洲观念12,而伊藤之雄则指出,在明治维新到1884年,无论在藩阀还是在民间,日本都已经开始确立了自己东亚盟主的意识,从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深感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和俄国在东亚的渗透,产生了“过剩”的警戒之心,而中日战争日方的胜利,则强化了亚洲盟主的观念13,当然可以补充的是,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这种盟主的意识就膨胀成了霸主的野心。
因此,这种观念蕴涵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却又以对抗西洋的侵略为旗帜,以所谓追求普遍的亚洲文明为口号。
当然,在这样的人中间,除了像福泽谕吉这样以西洋文明为亚洲共同追求,以近代性观念作为合理依据之外,当然,还有的人是直接强调东方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同时也由于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共同性,而同样强调地缘的亲和感,像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关于“东方为日出之所,主发育和亲,其神青龙,其德慈仁,亚洲在欧洲之东,日本朝鲜在最东,故受木德仁爱之性,清明新鲜之气煦然,其性情风俗,与西北染肃杀之风者不同,盖自然之理也”,所以,他凸显的是“其土唇齿,其势两轮,情同兄弟,义均朋友”的同文同种14。
简单地说,“亚洲主义”的呼声渐高,与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关,而明治维新的成功,一方面使日本从根本上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的羁绊,摆脱了中国文化的笼罩,重新确立了日本的自我和他者,一方面也使日本产生了摆脱西方,从西方边缘的尴尬地位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希望再度确立一个地缘与政治、经济、文化重叠的“自我”15。
这个时候,对近代化以来的强盛与进步的自豪、对自身所处的东方传统的依恋感、以及地缘上的认同习惯,加上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对日本的颐指气使,就构成了日本近代相当复杂的心情,脱亚是脱不了的,入欧也是入不了的,于是,一些日本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视线转向了自身所在的同一空间,本来在中国和日本都不曾把它作为近邻的“亚洲”,却突然成了具有天然亲和感的远亲,仿佛本来它就是和自己一门出身,和“欧洲”没有血缘的自家人。
平石直昭在《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中列举了福泽谕吉的“东洋连带论”、樽井藤吉的“大东连邦国构想”、近卫笃■和“同人种同盟论”到冈仓天心的“解放者日本像”,指出这个时代亚洲主义的依据,一是同文同种为基础的连邦国家构想、二是东洋门罗主义的理念,三是将日本视为以文化同一性为基础的亚洲的解放者。
第一点是来自历史与文化同一性的想象,第二点是将地理空间与政治空间重叠的设想,第三点则建立在以“进步与落后”的近代理念上的16。
但是,且不说最后这一点中所包含的危险倾向,就以第一点论,其实,所谓同文同种也罢,文化同一性也罢,在文化认同上,在族群认同上,根基都不那么可靠。
比如,把中日韩算在一门当然还有汉字文化圈的依据,而把中日印也算在一个认同空间,却主要靠了佛教信仰,尽管中国从来就不能算是一个佛教国度,而印度的佛教在近代已经早已风光不再,但是在提倡亚洲主义的人那里,曾经产生过或流传过佛教,就是沾亲带故的理由,而在把“西方”作为“他者”的背景下,建构一个“东方”似乎也顺理成章,因此在着名的冈仓天心的笔下,喜马拉雅山不再是划分两个文明区域的屏障17:
亚洲是一个。
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的共同社会主义中国文明和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分开,但雪山并不是障碍,它不能将追求普遍性的‘爱’的思想割断,而这种‘爱’是所有亚洲民族共同的思想遗传,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区分开了自身与偏好寻求人生手段而非目的的地中海沿岸诸民族18。
这种把“亚洲”的历史和日本连在一起,又在“日本”身上寄托亚洲理想的思路,在日本战胜中国,又战胜俄国之后,似乎变得更加高涨起来19。
近一百年以后,当一个西方人柯能回忆当时欧洲人的普遍焦虑时这样说道,“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时,它可能还自许为亚洲的扞卫者。
某位西方作家预言,世界的未来将决定于亚洲,他引述大隈谈论萎退的西方,并指出日本将会替亚洲人驱逐西方,……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大也可自许是欧洲文明的扞卫者,……一名旅居圣彼得堡的英国人写道:
如果日本打赢了,它可能很快结合黄种民族,从此不可一世”20,事实正是这样,在这以后,“亚洲”才成了日本政治与文化想象中需要“提携”和“连带”的一个空间。
二、晚清至民初中国对“亚洲主义”的复杂反应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年里,快速膨胀的日本似乎确实有一种“提携支那”的热情和“同文同种”的想象。
其中,大久保利通和“振亚会”、《太阳》杂志、东亚同文会及《东亚时论》、日本人在中国所创办的各种东文学堂,在一些学者眼中就是某种“亚洲主义”的象征。
也有人过高估计当时中日接近的程度,把这段时间看成是中日关系的所谓“黄金十年”,似乎让人觉察到一些“亚洲一体”的端倪21。
不过,这都忽略了当时中国人真正的心情和感情,更误看了当时历史,把表面热情掩盖了背后蔑视。
其实,仿佛老话说的“剃头挑子一头热”,那个时代“亚洲一体”的构想更多地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
作为一个已经充分近代化,而且在日中、日俄两次战争中初尝胜果的国家,日本很容易由于自我地理的边缘性而感到世界格局的不公平,也特别容易刺激它自命“盟主”甚至充当“霸主”的心情。
但是,对于仍然处于传统与近代转换期间的国家如中国,却未必愿意接受这种日本的“亚洲主义”。
本来中国的地理观念中,就没有“亚洲”或“亚细亚”的意识,而只有“中朝”与“四裔”的观念,直到近代接受西方地理学的空间说法,才有“亚洲”的意识,但是这种地理学意义上的认知,却与政治学意义上的认同无关,这除了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的历史记忆滞留外,现实的原因很简单,在以国族为基础的思考框架下,既不愿意作为被日本牵着鼻子走的附庸,又不能认同这种想象的、没有历史与文化基础的“亚洲”为政治与文化的共同空间。
毋庸讳言,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国知识人中也曾经有过对日本相当亲切的议论,确实看上去也颇吻合“亚洲主义”的口径22。
最早如曾纪泽,就曾经和日本驻英国公使吴雅娜谈到,欧洲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得“合纵”之意,所以中日两国“皆在亚细亚洲,辅车依倚,唇齿毗连……吾亚细亚洲诸国,大小相介,强弱相错,亦宜以公法相持”,这样可以成为与欧洲抗衡的“亚洲”23。
到了1895年以后,这种言论更多,像当时在日本的章太炎、梁启超等等,章氏曾经在1897年2月在《时务报》第十八册上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的文章,主张“互相依存为东亚之利”,并且在文章中把俄国作为假想敌,甚至可以认同日中战争为日本的自救,这几乎全是日本方面言论的翻版,1901年又在《国民报》第四期上所写的反驳梁启超的《正仇满论》末尾,甚至认为对于汉族而言,“日亲满疏”,“自民族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而满非同族”24,而1907年更在日本组织“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25,而梁氏则不仅在东亚同文会的刊物《东亚时论》上发表不少文字,而且有一段时期内确实也有过相当认同亚洲的口号,1898年在他主编的《清议报》第一册上,他所提倡的一共只有四条宗旨,其中三、四条就是“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26。
至于稍后的孙中山,更是提到亚洲主义的人必定要举的例子,他在1913年访问日本的时候,曾经有过提倡中日携手、维持亚洲和平的说法,也有过“亚细亚为吾人之一家”,甚至“中日两国协力而行,则势力膨胀,不难造成一大亚洲,恢复以前光荣之历史”等等与日本方面相当一致的说法27。
问题是,这种话语的出现背景仍然需要仔细地分疏,一方面可以看到,它的出现语境,常常是因为对西方列强侵略的警惕,换句话说,是由于“西方”或“欧美”的压力而被逼出来的一个“东方”或“亚洲”。
至于联日的具体心情,或是在处于困境时对日本支持的感铭在心,如梁启超,或是出于反满的汉族民族主义或者出于反观中国时的痛心疾首,如章太炎,或是访问日本时的外交辞令,如孙中山,其实都未必真的对所谓“亚洲”有真心的认同28;另一方面,这也只是处于积贫积弱状态下的中国知识人,对日本迅速“富强”与“文明”的艳羡,这种艳羡的价值基础恰恰是对西洋文明以及近代性的认同,并非来自对日本民族与文化的认同。
毫无疑问,在晚清一直到民国初年间,相当多的中国知识人对于日本是相当佩服的,日本明治维新给中国的刺激,现在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它激起了传统中国自强的心情,特别是在甲午一战之后,尽管战败耻辱的感情始终纠缠着中国人的理智思索,但似乎很多人都从此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日本比中国更接近西洋式的“文明”,而西洋式的“文明”就等于是近代国家和民族的“富强”。
所以,步日本的后尘,追求文明进步,在这方面很少有人提出疑问。
举几个人们熟悉的例子,像1896年,汪康年在《中国自强策》上里大声疾呼,中国要自强,“我苟能自振,则西人之于我,亦犹其与日本耳”,打败了中国并给中国带来耻辱的日本,现在成了中国效法的对象,尽管过去日本只是一个附属的“岛夷”;而日本之所以可以效法,也是因为明治维新29,1898年,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载,他读了《明治新史》很有感慨30;特别可以看出中国知识人的心情的,是1899年12月30日宋恕在《与孙仲恺书》中的感慨,他称赞“今之日本,文明之度胜中国,非但亿兆之与一比例也……日人之评中国曰:
‘文明早已过去,六经早已扫地之国’见鄙薄如此,真可怜矣”31。
就连现在被斥为保守派的王先谦,也从另一角度看到日本的意义,在光绪二十八年刻《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曾撰序指出,日本的兴盛,在于其“藉口攘斥西人,责之归政,耸动群藩,纳上户土,亿兆一心,拱戴王室”,而中国则否,日本成了中国自强的镜子32。
但是,这种观念与心情的巨变,多少有些无奈。
说它是卧薪尝胆也罢,说它是隐忍图强也罢,需要分疏的是,努力学习和效法的对象,未必是认同和亲切的对象,之所以有这种变化,主要是战败的刺激,像光绪十七、十八年间,在日本担任公职的郑孝胥还对日本的维新不以为然,讽刺伊藤博文学西法,“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甚至对日本的偶尔内乱兴灾乐祸地说,是“天败之以为学西法者戒”33,但是到了光绪二十到二十一年间,中国被日本打败,包括李鸿章,也得在中日谈判时向伊藤博文承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应当以日本为榜样,特别是说到,中日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34,那么,仅仅几年的时间,历史和传统遗留下来的天下观念和四夷意识,被日本打败的切肤之痛,会那么快地遗忘么,感情和观念真的能变得这么快么?
三、世界图像的各自想象:
中日之间的差异
1862年,日本人高杉普到中国上海访问,回国后写下的《游清余话》中轻蔑地断言“支那固陋而自灭”,但是,他也提到日本应当强化东亚的一体性,并用了“唇亡齿寒”的中国成语。
这种轻蔑和连带的双重意识,后来确实长期并普遍存在于日本上下,到了明治二十年代,随着维新的成功和国力的增强,日本迅速膨胀的大日本主义,就把中国看成是“半开化”的、“落后的”,对现实中国的轻蔑多过了对古代中国的依恋35,前引芝原拓自对日本舆论的调查就表明这一点。
而中国人其实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像李筱圃《日本纪游》记载东京博物院拿中国烟具、破灯、旧兵器等作为“中国物”展览、黄庆澄《东游日记》记载长崎商人所说的日本当时对中国尊敬之风的消歇和蔑视之风的开始,都清楚地表明了相互的警觉36。
然而中国对日本也一样有着莫名其妙的蔑视,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文化传统相当固执的帝国,它长期而普遍地停滞在天朝大国和朝贡体制的想象中,在它的历史记忆中,日本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国家而是“蕞尔岛夷”,同样,在普遍的观念世界中,“亚洲”也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域而是地理学上的一个词汇,毕竟在传统中国观念世界中,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南亚诸国都是一样的“四夷”。
古代中国遗留的历史记忆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它使得清帝国在未战败时对日本充满了毫无理由的自负和骄傲,在已战败后对日本又充满了相当深刻的忌惮和艳羡。
不过,这种记忆是历史的存在,它使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压力时,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它在价值和文化上的认同空间是“中”或者“西”,并不很会考虑建构一个相对于西方的“亚洲”,或者建构一个可以互相认同的“同文同种”。
因此,亚洲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而不是中国的“亚洲主义”,这个作为西方的“他者”的“亚洲”,也只是日本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共同体。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日本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并没有被作为感情上认同的对象,就连对日本的理智学习和仿效,也只是因为日本既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折射的却是西洋的文明和富强,又是一个转运站,转手贩运的是西洋的新知。
因此,尽管日本成了学习和效仿对象,可是中国人却并不觉得日本和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天然的血缘关联,也不觉得“亚洲”是一个有连带性的空间,中国知识传统中的“天下”观念,使中国知识人有一种世界主义或普遍主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他们倾向于认同一个中心和一种真理,而且中国很习惯于把自己的视野扩展到整个天下,因此,当西洋以其富强崛起,那么,中国又很容易就承认西洋的途径就是普遍适用的途径。
然而,对于日本的兴盛,他们觉得这只是因为日本比中国早一步接受了西学西法而已。
薛福成《筹洋刍议》已经指出日本“仿行西法,颇能力排众议,凡火轮、舟车、电报及一切制造贸易之法,稍有规模,又得西人之助,此其自谓胜于中国也”,但是他还是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器物械具和人口三方面都超过日本,只是“自强之权在中国,即所以摄服日本之权,亦在中国”37。
梁启超在维新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也只是说日本学习西方变法,可以是中国效法的对象,“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38。
后来,裘廷梁的《白话丛书》中的《日本志略》也说道,中国儒教书说的,都是古时事迹,对现在的事情论说极少,但是日本却处处学泰西,对现在的事情有办法,十三页上说到,“凡欧洲所读的书,日本人没有不读的,从此以后……万万不会受别国的欺侮”。
怎么办?
就是像日本一样,学习西方,一时不能迅速地学习西学,那么也可以权宜方便地从日本转手贩来,仿佛“假道灭虢”那个典故一样。
而顾鸣凤在1900年所写的《三十年来吾华人崇尚各种西艺》一文中,提到中国自强应以日本为师,因为学习西文很难,“中日两国既属同文,华人之学东文,较学西洋语言文字事半功倍”,又说“日本维新而后,凡西政西艺各种有用书籍,均经译为东文,大称美备”39。
到了再晚些的贺铸,就对朋友说道,“日本维新之初,醉心欧化,几经冲突,乃成为今日之日本。
中国风气初开,正所谓醉心欧化之时,乘其机而利用之,而慎防其弊,使东西政法皆得效用于我,以自成为中国之治”,还劝另一个朋友的五公子“既通东文,当专习欧文,欧文为群学根本,通欧文乃能乘酣呈怪,大放厥词,专恃译书,局促如辕下驹”40。
那个颇出名的王闓运并不懂这个道理,倒在光绪二十九年的一份奏折上批评时人,“名为西学,实倭学也”,其实说起来,这话应当反过来说,当时看上去虽然满眼都是倭学,其实都只是转手从日本贩来的西学41。
到了更多的人可以直接从西文学习真正的近代之术时,就仿佛老话里说的“过河拆桥”或古语中说的“舍筏登岸”,这个借力的桥板和摆渡的舟楫,就可以不要了。
中国知识人可能也有根深蒂固的天下主义。
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这种历史渊源极深的天下主义,可能转化为接受普遍真理和普遍价值的世界主义,引申出价值上的一元主义,把西方“先进”、“文明”和“富强”当做全球普遍追求的路向,从而迅速地认同另一种文化和制度,但也可能延续着鄙夷四裔唯我独尊的民族主义,却引申出通过近代化而富国强兵,从而俯视天下的雄心。
在这种历史记忆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尽管有些人对于原为“虾夷”、“倭寇”或“岛夷”的日本,会有权宜的亲和之心,会有热烈的学习之意,但是从根本上却不会有所谓“同文同种”的心底认同42。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丁日昌上书告诫朝廷,“日本国变峨冠博带之旧习,师轮船飞炮之新制”,要中国注意这种变化,而翁同龢则只是说,“阴而有谋,固属可虑,穷而无赖,则更可忧”43,从鼻子里哼出的是不屑。
何况在甲午之前,中国知识人中,一方面对日本还残存了“倭寇”的历史记忆,像薛福成就不仅在《筹洋刍议》中指出“日本人性桀黠,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