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抒情诗.docx
《政治抒情诗.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政治抒情诗.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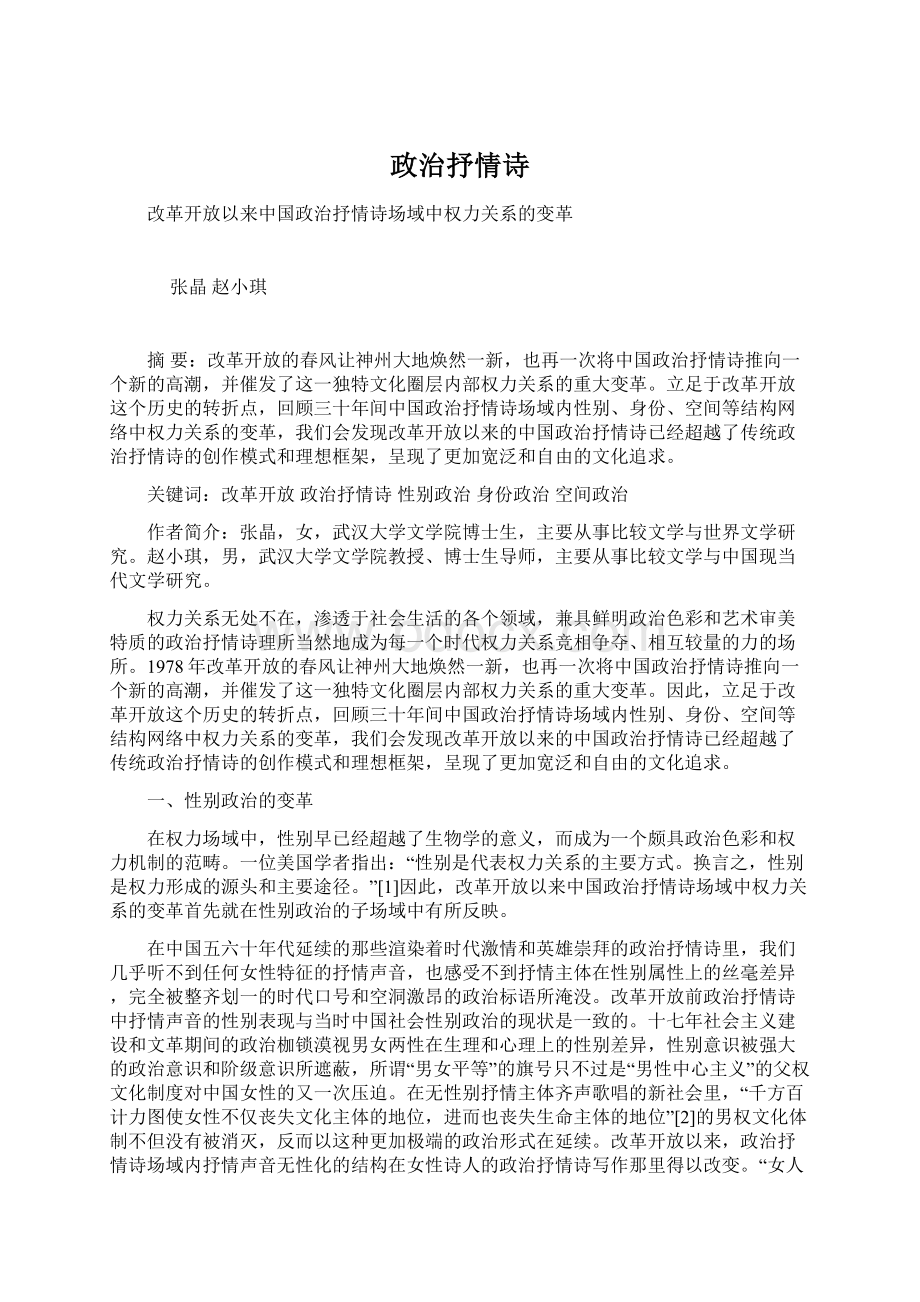
政治抒情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抒情诗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变革
张晶赵小琪
摘要: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神州大地焕然一新,也再一次将中国政治抒情诗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并催发了这一独特文化圈层内部权力关系的重大变革。
立足于改革开放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回顾三十年间中国政治抒情诗场域内性别、身份、空间等结构网络中权力关系的变革,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抒情诗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模式和理想框架,呈现了更加宽泛和自由的文化追求。
关键词:
改革开放政治抒情诗性别政治身份政治空间政治
作者简介:
张晶,女,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赵小琪,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权力关系无处不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兼具鲜明政治色彩和艺术审美特质的政治抒情诗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个时代权力关系竞相争夺、相互较量的力的场所。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让神州大地焕然一新,也再一次将中国政治抒情诗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并催发了这一独特文化圈层内部权力关系的重大变革。
因此,立足于改革开放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回顾三十年间中国政治抒情诗场域内性别、身份、空间等结构网络中权力关系的变革,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抒情诗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模式和理想框架,呈现了更加宽泛和自由的文化追求。
一、性别政治的变革
在权力场域中,性别早已经超越了生物学的意义,而成为一个颇具政治色彩和权力机制的范畴。
一位美国学者指出:
“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
换言之,性别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主要途径。
”[1]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抒情诗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变革首先就在性别政治的子场域中有所反映。
在中国五六十年代延续的那些渲染着时代激情和英雄崇拜的政治抒情诗里,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女性特征的抒情声音,也感受不到抒情主体在性别属性上的丝毫差异,完全被整齐划一的时代口号和空洞激昂的政治标语所淹没。
改革开放前政治抒情诗中抒情声音的性别表现与当时中国社会性别政治的现状是一致的。
十七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文革期间的政治枷锁漠视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性别差异,性别意识被强大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所遮蔽,所谓“男女平等”的旗号只不过是“男性中心主义”的父权文化制度对中国女性的又一次压迫。
在无性别抒情主体齐声歌唱的新社会里,“千方百计力图使女性不仅丧失文化主体的地位,进而也丧失生命主体的地位”[2]的男权文化体制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以这种更加极端的政治形式在延续。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抒情诗场域内抒情声音无性化的结构在女性诗人的政治抒情诗写作那里得以改变。
“女人和男人应去关注民族、国家、社会,关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和整个人类的命运。
女性诗人的写作,如果和某些男作家一样,表现出很大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都是一种写作的失败。
”[3]改革开放初期,女诗人舒婷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暴风雨过去之后》、《这也是一切》等诗歌里细腻地展现了女性抒情主体在与时代情绪交融之下真实的个体感受,既有迷惘的痛苦也有欢欣的希望:
“我是贫困,/我是悲哀。
/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在舒婷之后,以翟永明为代表的女性诗人则抛弃了传统政治抒情诗男性抒情主体惯用的抒情策略,从平凡人的日常生活着手以小见大,抒发她们对自由生命的歌颂、对弱者的同情和对世界的关爱,充满了母性慈爱的光辉和人文主义的温情。
翟永明将眼光投向年幼的《雏妓》,投向依然贫穷靠卖血维生的《老家》,表现了诗人对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同情与人文关怀;深圳女诗人刘虹则在《笔》、《小车时代》等诗作里抒发了对现代工业社会和电子时代人性失落、民风不古的担忧。
近年来更多女性抒情声音在一些关注社会时政、表现民生疾苦、感时伤逝、忧国忧民的诗歌作品里响起是觉醒了的中国女性诗人对男权传统在政治抒情诗歌领域的挑战,也是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
准确地说,中国至今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政治抒情诗人,但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政治抒情诗场域中女性抒情声音的强大还是显现了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轨迹。
八十年代初以舒婷为代表的女性抒情声音,面对着刚刚过去的苦难岁月和充满期许的未来,更多的是反思和憧憬:
“不要告诉我这样做,而让我想想为什么和我要怎样做。
让我们能选择,能感觉到自己也在为历史、为民族负责任。
”[4]八十年代中期后,以翟永明为代表的女性诗人则以更具内心化和个体化的声音抒发了对传统性别权力体系的反叛,从而强化了政治抒情诗场域中女性抒情主体的力量,翟永明在为组诗《女人》作序中写道:
“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
这就是诗……黑夜的意识使我把对自身、社会、人类的各种经验剥离到一种纯粹认知的高度,并使我的意志和性格力量在种种对立冲突中发展得更丰富成熟,同时勇敢地袒露它的真实……”[5]。
相对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政治抒情诗场域女性抒情声音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中的觉醒和凸显,世纪之交的女性抒情主体又重新有意追求抒情声音的无性化,诗人刘虹说:
“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
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
”[6]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抒情诗中女性抒情声音的高涨并非完全是女性抒情主体有意识地将性别书写作为男女两性权力关系中性别文化反抗的工具和手段,而只能看作是女性抒情主体在性别政治斗争中所采取的一种被动和临时性的文化策略。
二、身份政治的变革
身份政治是一种“既以差异和压迫为基础又以同一性或团结为基础”[7]的特殊权力关系。
政治抒情诗场域中身份政治的变革绝不仅仅是抒情主体在身份角色上的简单替换,更是身份关系背后政治抒情诗在抒情立场与诗歌精神上的深层演变。
在五六十年代延续的政治抒情诗传统里,抒情主体是国家意识与革命风暴的传声筒,“大我”以绝对的优势淹没了“小我”的声音,二者之间是抑制与被抑制的一元权力关系。
但改革开放以来,“小我”的抒情声音逐渐凸显,“大我”却也从未消失,政治抒情诗场域中抒情主体在自我身份认同的政治表达方式上呈现了二元对立统一的新型权力模式。
改革开放之初,代表着时代精神与人民意愿、具有强烈现实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大我”依然是政治抒情诗场域中身份权力关系的主要身份形式。
这一时期,无论是曾经遭受政治迫害的“归来诗人”,还是在“潜写作”中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都一齐登上诗坛为祖国和时代献歌:
《光的赞歌》、《老水手的歌》、《献给历史的情歌》、《为高举和不举的手臂歌唱》、《生命的欢歌》、《小草在歌唱》、《颂歌》……这些充满了喜悦的欢歌一时间又让中国的政治诗坛再次响起了整齐高昂的民族大合唱。
艾青、绿原、牛汉等七月派诗人依然坚持为人民写作、为时代呐喊,勇敢地走出历史阴影、盛赞新时代的光明;军营诗人李瑛、张志民、周涛、雷抒雁纷纷以军人饱满的政治激情,关注社会现实、歌唱时代的英雄、赞颂新生的美好;年轻诗人杨炼、江河、杨牧、张学梦纷纷唱起了青春的赞歌,鼓励新时代的青年们以火热的激情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重新发现我自己》中“从庄严的汉白玉石的裂罅中走出”的“我”、《我骄傲,我是一棵树》中的“我”、《我是青年》中“是鹰、是马、是骨、是汗”的“我”都是改革开放初期以“人民代言人”身份自居的抒情主体最生动的写真。
在改革开放最初几年抒情主体以“大我”身份欢欣鼓舞的同时,政治抒情诗场域中身份政治的变革也在悄然酝酿,具有更多反思意识和主体特征的“小我”正在迅速地成长壮大。
在“复出诗人”创作的“归来”诗歌中,除了有时代大合唱的“我们”,还有“自白式”吟唱中深沉而真挚的“我”:
“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
”抒情主体代表了一群从过去走来、独具个性的沉思者,他们在历史的沉思中思索现实,在艺术的抒写中理性批判。
同时,朦胧诗潮向政治抒情场域的漫延也让“大我”的身份愈来愈模糊,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鲜明的“小我”真正开始了与“大我”在政治抒情诗场域内的权力之争。
年轻的朦胧诗人们在诗歌中公开凸显自我形象,充满生命意志的“人”得以高扬,抒情主体以个体身份承担起了时代和民族的苦难,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大胆的怀疑与叩问。
北岛诗歌中“我是人”、“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的呼唤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抒情主体对自我权力的维护与追寻,对集体政治压抑的抵制与反抗。
改革开放为中国人解除了沉重的思想枷锁,随之而来的是商品经济无休止的消费与欲望,是社会急剧转型的阵痛和信仰的失落……这样的时代情绪也必然会在政治抒情诗场域中身份政治的权力斗争中有所体现。
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政治抒情诗场域内身份政治的斗争进入白日化阶段,关于“大我”与“小我”、宏大身份与个体身份的争论愈演愈烈,以至于在九十年代臻于顶峰。
其后政治抒情诗场域内有关身份政治的权力斗争表现得更为复杂与隐蔽,抒情主体的政治身份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特征。
第一类是以传统身份出现的抒情主体,他们继续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者和时代的歌唱者的共同身份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力话语中对现实历史作统一的叙述。
诗人朱子奇在“政治抒情诗100首”——《星球的希望》中为我们描绘了这一类身份的抒情主体:
“我站在海特公墓的高地上/依傍着伟人的大理石碑像/举目向多云的远天眺望……五月的风吹得我两眼晶亮晶亮……撩开海雾的帏帘重重,我向在远方红场的墓中人致敬”。
传统身份的抒情主体置身于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中,将时代集体的政治理想与革命信念抽象化、符号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共同象征,而社会个体的生命体验和主观感受则被完全放逐。
第二类是与传统身份相对立,以叛逆姿态出现的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精神进行大胆解构与反思的批判者,其精神资源来自于西方的解构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
同时,在这一类抒情主体的身份结构内部还存在着民间与精英两种不同抒情立场的分化:
一部分抒情主体立足民间,将崇高的阶级意识消解为真实的个体欲望,把时代的英雄主义掩埋于日常琐碎的平庸: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风景/然后再下来”[8];而另一部分抒情主体则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坚守着着历史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对社会现实给予人文主义的关怀: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在弥撒曲震颤中相逢的灵魂/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自己的土地!
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在风中燃烧的枫叶/人民胃中黑暗、饥饿,我怎能/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
”[9]无论是民间立场还是精英立场,显然以叛逆身份出现的抒情主体已经实现了对传统政治抒情诗里“大我”身份的超越,成为了当代政治抒情诗场域中既与时代、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又对社会现实深度介入的完全独立的“人”。
在传统身份与批判身份之外,九十年代政治抒情诗场域内还存在着第三种政治身份,即一种融合的身份,抒情主体始终没有放弃对历史的记忆与时代的书写,但却将这种宏大的政治传统以一种颇具现代性的日常姿态和个人立场予以展现。
被誉为“后政治抒情诗人”的胡丘陵在其诗集《拂拭岁月》中正是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身份来重新审视新中国建国五十年的历史岁月,其中既包含了抒情主体丰盈独特的生命感受,也反映了现代视角对于历史与时代的深刻透视:
“一颗螺丝钉/将一位戴着冬帽的/士兵头像 / 钉在全国/所有的教室……国家与集体,塞满了/记忆的仓库/ 忘记的/ 只有 /‘私’字和自己…… 世界所有的专家/ 还不能克隆羊的时候/ 共和国的领袖 /已经掌握了 /克隆优秀国民和思想的技术”[10]。
在九十年代之后政治抒情诗的权力谱系中,传统、批判、融合三种身份形态的多元并存是当代中国文化多元与价值多元的时代特征在政治抒情诗场域内的必然反映,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民主与自由进程影响当代文艺创作的一个典型,通过不同身份形态的抒情声音传达出了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转型与历史变革中复杂多元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动态。
三、空间政治的变革
空间政治在政治抒情诗场域中的变革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抒情诗歌文本中有关地域形象的变化,二是政治抒情诗创作主体现实生活地域的变迁。
政治抒情诗场域中空间政治的这些变革又都与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
诗歌中很多的地域意象都不仅仅是方位空间的概念,往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政治抒情诗中的地域意象尤其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抒情诗场域中空间政治的变革首先就体现为对地域意象的重新选择。
颂歌是传统政治抒情诗最繁荣的抒情样式,歌颂党、歌颂领袖、讴歌红色革命和新中国政权都是经典的主题,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以及大西北等中国北方农村和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心脏——北京,这些与中国革命与红色政权密切相关的地域空间自然也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传统政治抒情诗中常见的诗歌意象。
但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抒情诗中,红色革命圣地、首都北京以及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形象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以上海、深圳为代表的南方都市及城市文化意象。
秋天的十月,城市里没有庄稼等待/收割。
只有各色树木跳着习惯的脱衣舞/大街上车流如织,带着腰别手机的人们/奔驰。
如果手机能割来香香的五谷/如果手机能散发炊烟和草垛/多好。
……这是我巴掌大的与国际接轨的城市/钢筋结构,灰石所砌/盛产金钱和利润,大款和白领/机器运转,工人繁忙/口音杂乱,磁卡电话畅销/书店频频倒闭,饭店愈益豪华……”[11]
显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是政治抒情诗场域空间政治变革的根本原因。
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这些时代风潮的转变都促使了政治抒情诗在意象选择上由革命气息的乡土空间转向了充满现代气息的都市空间。
其次,在政治抒情诗创作主体的地域分布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抒情诗场域也表现出了这种由南自北、由乡村到城市的空间变革趋势。
政治抒情诗是一种与政治关系相当密切的文学样式,这就要求从事政治抒情诗创作的诗人要有敏锐的政治直觉和快捷的信息渠道来把握时代的风云变化。
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理所当然地成为改革开放之前诗人创作政治抒情诗的云集之地。
诗人黄翔道出了当时外省青年诗人对北京的向往:
“我之所以选定北京,因为在那里,立于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
放个屁也是响雷!
”[12]而这一切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人们对北京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政治的崇拜心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重心的转变悄然实现了南移,沿海特区淘金的热潮和城市文化迅速的崛起让一种全新的空间政治观念在中国政治抒情诗场域中诞生。
四川、南京、上海、深圳相继成为诗歌的故乡,在这些原本被权力系统边缘化的城市上空也响起了风格各异的政治抒情声音。
上海诗人发出了他们的“撒娇”宣言:
“我们都是中国人,试试看,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在我们国家容易活一些。
社会主义制度好,我们撒娇;风花雪月江山无限好,我们撒娇。
”四川诗人李亚伟在《我的中国》一诗中用粗野莽汉的方式穷尽日常生活的全部琐碎形象后终于顿悟地发出了“我是中国”的感叹,这无疑是对之前所有政治抒情诗里中国形象的彻底颠覆。
经济是文化的物质基础,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由城市到乡村、由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到欠发达内陆地区的空间发展趋势也必然会对政治抒情诗创作主体的创作心态和生活方式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抒情诗在空间政治场域内的变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然产物。
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重心的转移让在经济浪潮中兴起的都市文化成为政治抒情诗新的时代焦点和现实主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社会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让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主体拥有更广阔的抒情空间。
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
“对陈述的分析是一个历史的分析,但它无需任何的解释……它寻求的是它们以什么方式存在,它们被表现出来意味着什么”[13],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抒情诗场域中性别、身份和空间等权力关系的变革,我们不仅要作出“一个历史的分析”,更重要的还要思考这样一种变革趋势“被表现出来意味着什么”?
在性别政治的权力关系中,我们倾听到越来越多女性抒情声音对政治抒情诗场域内男权中心文化的挑战;在身份政治的权力关系中,我们目睹了抒情主体在政治抒情诗场域中由无我到有我、由大我到小我、直至多元身份共存的崭新模式;在空间政治的权力关系中,我们见证了新兴都市文化空间取代红色革命乡村的历史变迁。
在历史分析中“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将政治抒情诗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变革放在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考察。
由此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转型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抒情诗场域内权力关系变革的根本动力和深层缘由,而政治抒情诗也正是在这一全新的社会语境下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实现了对传统政治抒情诗固有抒情模式和审美范式的超越,呈现出更加宽容的诗歌精神、多元的审美形态和深厚的文化质感。
(赵小琪,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张晶,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发表于《诗歌月刊》2009年第2期)
[1]琼·斯科特:
《性别:
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转引自李银河主编:
《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0页。
[2]周力、丁月玲:
《女性与文学与艺术》,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3]吴思敬:
《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诗潮》2000年3-4月号。
[4]舒婷:
《梅在那山》,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
[5]翟永明:
《黑夜的意识》,《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142页。
[6]刘虹:
《为根部培土》,《诗刊》2004(6)上半月刊。
[7]约翰·罗、王逢振、谢少波:
《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约翰·罗访谈录》,《文艺研究》2001年第一期。
[8]韩东:
《有关大雁塔》。
[9]王家新:
《帕斯捷尔纳克》。
[10]胡丘陵:
《1963年,雷锋》,《拂拭岁月》,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1]君儿:
《秋天的减法》。
[12]黄翔:
《狂醉不醒的兽性》。
[13]福柯:
《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
政治抒情诗札记
作者:
想念汪晖 2008-03-0912:
03星期日晴
政治抒情诗札记
——以对《时间开始了》的阐释为中心
摘要:
在政治抒情诗的代表性文本《时间开始了》之中,人称的使用纷繁而灵活,处于极其自由的转化中。
这体现出个人性话语在集体性话语中的消泯。
诗歌对于战争心态的真诚抒写也留下了足够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
政治抒情诗人称分析革命
一、小引
在谈及中国当代诗歌的进程时,谢冕将之比喻为“一支小号引出了一部雄伟的奏鸣曲”。
作为引子的小号,“它的高亢、嘹亮,传达了以战争和建设的凯歌为基调的充满自信和乐观的音响。
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整整五十年代,我们的诗中就响彻了这种充满天真和透明的单纯感的声音。
”
(1)50年代是政治抒情诗成熟的年代,近年来,胡风写于1949年11月——1950年1月间的长篇抒情诗《时间开始了》被纳入了政治抒情诗的考察视野中。
陈思和在《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对之做了单节叙述,将之作为胜利者的歌谣来加以阐释。
赵金钟的《<时间开始了>:
胡风的生命之歌》明确提出,这首诗的出现客观上把新中国政治抒情诗的成熟期提前了几年,考察当代政治抒情诗不把它算在内是不客观的。
(2)一般来讲,取材的强烈政治性、时事性,艺术形式上政论性和激情的结合,强烈的政治鼓动性和感染力是政治抒情诗的重要特征。
《时间开始了》毫无疑问也具有这三个特征。
除了第三曲《青春曲》外,其余四个乐章都由具体的重大政治事件所触发,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作者真诚的、喷涌的激情。
然而今天更为重要的并不是为胡风在政治抒情诗人群体中争得一席之地,而是通过考察时代语境在诗歌深层结构中所留下的或深或浅的痕迹,达到对政治抒情诗这一重要的诗歌样式的恰切把握。
胡风站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所创作的《时间开始了》包含着诸多丰富、敏感的信息。
关于《时间》一诗,有一个重要的描述:
“……他沉醉地彻夜不眠地写着,写出了巨型交响乐般的史诗长卷《时间开始了》。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他仿佛在履行自己对历史所负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他不得不写这几篇长诗,不得不唱出亿万人所想唱的歌,同时这几篇长诗也似乎不得不由他这位‘曾经沧海’的诗人来写。
”(3)这是又一个以音乐术语来作比喻的描述,它与谢冕的“小号”构成了对照。
“交响乐”意味着它包含着多种声音,表现着复杂的、变化多样的感情,犹如交响乐中主旋律的出现,消失、复现。
“史诗”则意味着它传达了一种集体性的经验,即“唱出亿万人所想唱的歌”,那么这位“曾经沧海”的诗人的个体经验是否与之产生了排斥?
这一描述出自胡风的密友,“七月派”著名诗人绿原,他与胡风等人对于诗歌的理解是否有着不同于当时主导性潮流之处?
这样的推断可以从一些当代文学史事件来加以证明。
胡风在1949年11月11日写完《时间》的第一章《欢乐颂》,11月20日即在《人民日报》刊出。
但是接着创作的《光荣赞》、《英雄谱》和《胜利颂》的发表则遭遇了困难,得以出版后则很快遭到了何其芳、黄药眠、安海等人的批判。
在一个文艺界思想被全面整合的年代,我们确乎可以从《时间》的命运反证出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异端性,尽管它对领袖和人民的歌颂,对革命激情的宣扬与同时代的诗歌并无二致。
通过以上的简短分析,我可以将本文的主要观点与写作意图概括如下:
与后来的朦胧诗在思想内涵上的丰富性、艺术手法上的繁复性相比,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确实是一支单纯明朗的小号,但是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也不是单一的存在,它的构成是有差异的。
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就是包含着异质性因素的政治抒情诗。
而正如赵金钟所言,由于它“无论是从视野的高阔、内涵的深邃、感情的浓密,还是从形式的活脱,风格的奔放等方面来考察”,“都是政治抒情诗中的佼佼者”,(4)因此,对《时间》一诗进行深入审视是必要的。
同时,应当避免将这种异质性强调到极端而丧失了本文对政治抒情诗进行论述所应具有的包容性,而是尽力凸显50、60年代有代表性的政治抒情诗在话语方式、结构特点等方面对《时间》一诗的继承与偏移。
并且希望50、60年代的文艺生态环境能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透视。
二、人称分析:
政治抒情诗的话语秩序
现代社会学知识表明,“非现代国家要试图变成‘现代’国家的话,它的首要任务就是
叙事,即把处于自然状态的社会组织到一个按照“我们”与“他们”的划分有序、层次分明的现代话语中去。
”(5)而文学作为叙事的一种形式,从中可以分析出现代话语的组构方式。
而进行这种分析的一个契入点便是进行人称分析。
关于对诗歌写作进行人称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姜涛曾有过如下论述:
诗歌写作中的人称意识与叙事性作品一样,不仅构成写作者观物方式转换的中轴点,而且与文本中主体性的生成有关。
依照一些学者的论述:
“这种‘主体性’不管在古典抒情诗里(‘我你’或‘我她’)或现代诗(自我消匿)的论述过程里,均不断形成,和他人产生对立、接触,以了解本身的处境,一再修正自己,一方面描述自我与外在世界(你、她或它)的种种关系,一方面便以这些关系组构自身。
”而这种主体与他者微妙共生的关系也即应和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在他人的帮助下我才展示自我,认识自我,保持自我。
最重要的构成自我意识的行为,是确定对他人意识(你)的关系。
于是,人称分析、主体确立及发现他者,这三者就在说者“我”,听者“你”及被谈论者“他”的冲突溶合之间,达成了一种内在的一致性。
(6)
从初入解放区起,胡风的思绪始终处于复杂的起伏与冲撞状态。
面对新的文化秩序,他试图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面对新的时代,他充满了热情与真诚。
在给绿原的信中,他说:
“你所欢呼的时代来了。
来时,希望能带来一卷作品。
希望我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