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丝绸路上的敦煌.docx
《第二章 丝绸路上的敦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二章 丝绸路上的敦煌.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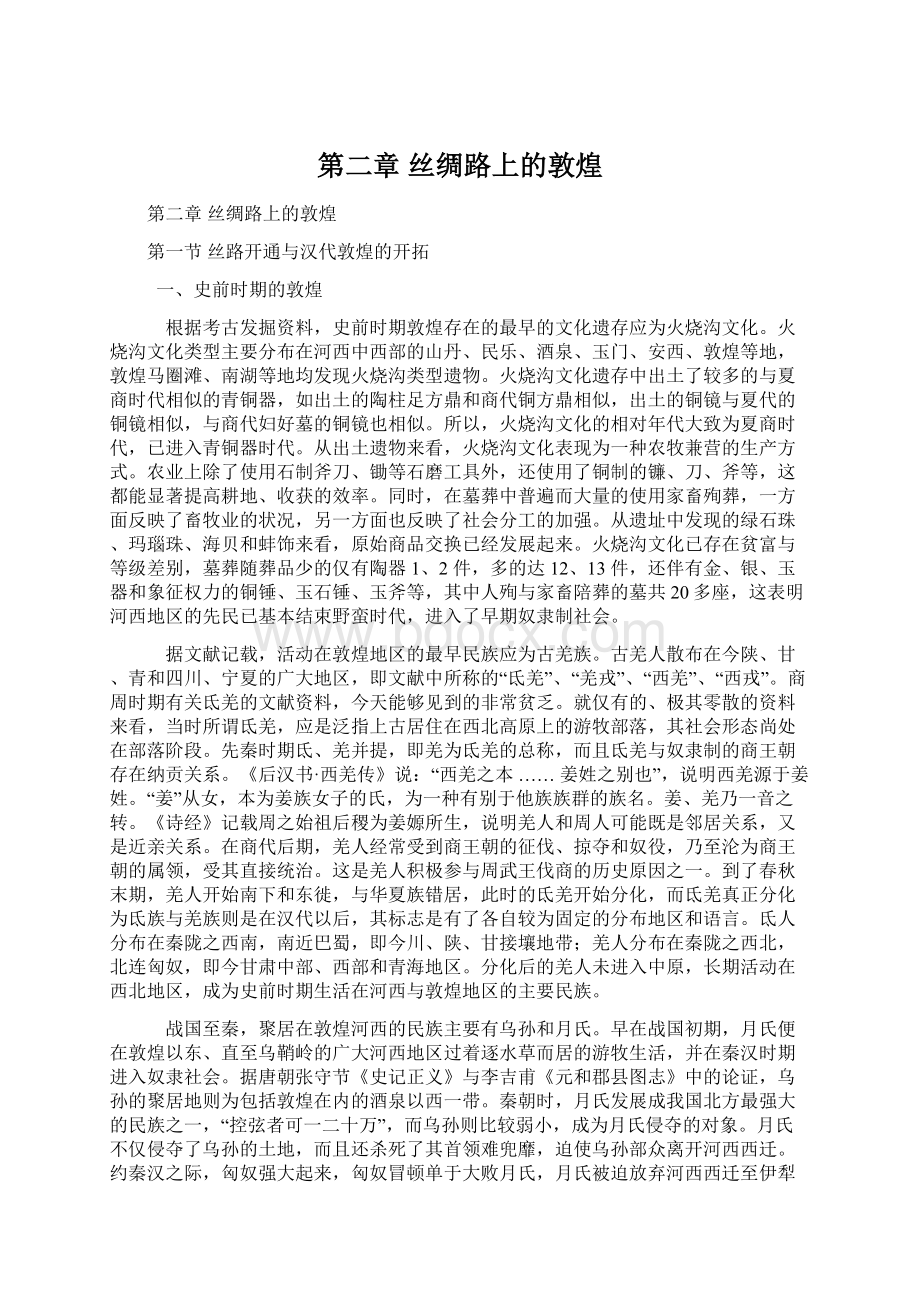
第二章丝绸路上的敦煌
第二章丝绸路上的敦煌
第一节丝路开通与汉代敦煌的开拓
一、史前时期的敦煌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史前时期敦煌存在的最早的文化遗存应为火烧沟文化。
火烧沟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河西中西部的山丹、民乐、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敦煌马圈滩、南湖等地均发现火烧沟类型遗物。
火烧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较多的与夏商时代相似的青铜器,如出土的陶柱足方鼎和商代铜方鼎相似,出土的铜镜与夏代的铜镜相似,与商代妇好墓的铜镜也相似。
所以,火烧沟文化的相对年代大致为夏商时代,已进入青铜器时代。
从出土遗物来看,火烧沟文化表现为一种农牧兼营的生产方式。
农业上除了使用石制斧刀、锄等石磨工具外,还使用了铜制的镰、刀、斧等,这都能显著提高耕地、收获的效率。
同时,在墓葬中普遍而大量的使用家畜殉葬,一方面反映了畜牧业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分工的加强。
从遗址中发现的绿石珠、玛瑙珠、海贝和蚌饰来看,原始商品交换已经发展起来。
火烧沟文化已存在贫富与等级差别,墓葬随葬品少的仅有陶器1、2件,多的达12、13件,还伴有金、银、玉器和象征权力的铜锤、玉石锤、玉斧等,其中人殉与家畜陪葬的墓共20多座,这表明河西地区的先民已基本结束野蛮时代,进入了早期奴隶制社会。
据文献记载,活动在敦煌地区的最早民族应为古羌族。
古羌人散布在今陕、甘、青和四川、宁夏的广大地区,即文献中所称的“氐羌”、“羌戎”、“西羌”、“西戎”。
商周时期有关氐羌的文献资料,今天能够见到的非常贫乏。
就仅有的、极其零散的资料来看,当时所谓氐羌,应是泛指上古居住在西北高原上的游牧部落,其社会形态尚处在部落阶段。
先秦时期氐、羌并提,即羌为氐羌的总称,而且氐羌与奴隶制的商王朝存在纳贡关系。
《后汉书·西羌传》说:
“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说明西羌源于姜姓。
“姜”从女,本为姜族女子的氏,为一种有别于他族族群的族名。
姜、羌乃一音之转。
《诗经》记载周之始祖后稷为姜嫄所生,说明羌人和周人可能既是邻居关系,又是近亲关系。
在商代后期,羌人经常受到商王朝的征伐、掠夺和奴役,乃至沦为商王朝的属领,受其直接统治。
这是羌人积极参与周武王伐商的历史原因之一。
到了春秋末期,羌人开始南下和东徙,与华夏族错居,此时的氐羌开始分化,而氐羌真正分化为氐族与羌族则是在汉代以后,其标志是有了各自较为固定的分布地区和语言。
氐人分布在秦陇之西南,南近巴蜀,即今川、陕、甘接壤地带;羌人分布在秦陇之西北,北连匈奴,即今甘肃中部、西部和青海地区。
分化后的羌人未进入中原,长期活动在西北地区,成为史前时期生活在河西与敦煌地区的主要民族。
战国至秦,聚居在敦煌河西的民族主要有乌孙和月氏。
早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敦煌以东、直至乌鞘岭的广大河西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并在秦汉时期进入奴隶社会。
据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论证,乌孙的聚居地则为包括敦煌在内的酒泉以西一带。
秦朝时,月氏发展成我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控弦者可一二十万”,而乌孙则比较弱小,成为月氏侵夺的对象。
月氏不仅侵夺了乌孙的土地,而且还杀死了其首领难兜靡,迫使乌孙部众离开河西西迁。
约秦汉之际,匈奴强大起来,匈奴冒顿单于大败月氏,月氏被迫放弃河西西迁至伊犁河流域。
匈奴占据河西后,将今武威一带划归休屠王统辖,张掖及其以西的酒泉、敦煌划归浑邪王统辖。
可见在汉武帝统一河西之前,河西地区一直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先后生存着羌族、乌孙、月氏与匈奴等族,史前时期的敦煌历史与这些民族的发展史密切相关。
二、张骞“凿空”与丝绸之路的开通
西域一名,始于前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就其广义而言,我国新疆及其以西的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皆可称之为西域;就其狭义而言,则主要是指我国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即葱岭以东、甘肃敦煌以西之地。
匈奴占据河西、西域及我国北方的大片土地后,经常侵掠中原,不仅中断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阻塞了中西陆路交通,还与居住在青海高原的西羌相连接,并联合起来,对西汉王朝的西北地区形成了包围之势,威胁着汉朝的安全。
然而,西汉建国之初,国势虚弱、经济残破,无力抵御匈奴的进攻,只得采取“和亲”政策。
汉武帝即位后,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大增强,已经具备了抗击匈奴的物质基础。
据《汉书》记载此时的汉王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决心抗击匈奴。
此前,他听说为匈奴所迫而西迁的大月氏,与匈奴有世仇,心怀怨恨,常思报复,于是决定选拔有胆识的人,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等民族,共同抗击匈奴,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
汉武帝公开召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以汉朝使节的身份率团第一次出使西域。
他们从长安出发,进入河西走廊后,便被匈奴扣押。
匈奴单于对张骞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起初对其威吓,继而又用高官利禄诱惑,并迫使张骞娶匈奴女为妻,试图以此来泯灭他的意志。
但是,张骞坚贞不屈,牢记使命。
在被软禁十年以后,终于趁匈奴不备,和随从甘父等人一起逃脱。
张骞逃出匈奴后继续西行,越过葱岭,先后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城)、康居(乌兹别克之撒马尔罕),又到达大月氏(阿姆河北岸一带)。
张骞到达大月氏后,那里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月氏所占阿姆河一带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从事生产,生活安定。
安居乐业的大月氏人无意东归,已不想再找匈奴报仇了。
张骞在大月氏停留一年多,都未说服大月氏王,于是只好东返长安。
在返回长安途中,为避免再次被匈奴抓获,打算取道昆仑山北麓,沿祁连山脚进入青海羌中地,然后东出河湟返回长安。
但不幸再次被匈奴擒获扣留一年多,元朔二年(前126年),张骞趁匈奴内乱逃出,回到长安。
张骞一行一百余人,历经13年,历尽艰险,回到长安时仅剩二人,为了褒奖其功劳,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张骞此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为汉代解决匈奴大患,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征河西,重创匈奴。
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兵两路,大败匈奴。
为了将匈奴彻底击溃,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再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的目的是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
此时,由于河西已为汉朝辖地,张骞一行不仅顺利到达乌孙,而且使团规模也比上次大得多,人数达三百人,还带了大量的牛、羊及价值巨万的金、帛等物。
张骞到达乌孙后,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地进行友好活动。
由于乌孙内部分裂,未能统一,所以此次出使并未能实现同乌孙联盟共同攻打匈奴的目的,但乌孙表示愿与西汉建立密切的关系。
当张骞返汉时,乌孙王昆弥派遣数十名亲信大臣为专使,带着几十匹著名的乌孙马为礼物,到长安向汉王朝致谢。
张骞前后两次出使西域,行程万余里,历时近二十年,倍尝艰辛,为丝绸之路的开通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骞的出使,以其亲身经历考察了被匈奴中断与阻塞了的丝绸之路,为我国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
张骞还以其亲身经历证实和订正了过去对西域诸国的传说和零散记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使汉朝政府了解到了丝绸之路上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真实情况,并由此与他们建立起了友好关系,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奠定了基础。
据《汉书·西域传》和《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汉代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陇西,穿过河西走廊,到达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然后分为两路:
南路:
由敦煌西南行,出阳关,沿南山(昆仑山脉)北麓,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且末、精绝(今新疆民丰县尼雅)、于阗(今新疆和田)、沙车到疏勒(今新疆喀什),然后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向南到达大月氏、大夏、罽宾、身毒等国。
北路:
由敦煌西行,出玉门关到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又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到疏勒,越过葱岭可达大宛、康居、奄蔡(在里海、黑海间)等国。
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是汉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经丝绸之路,西汉政府把内地的丝织品、钢铁、竹器、漆器、陶器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西方,而西方的葡萄、苜蓿、胡麻等物产,以及音乐、绘画、宗教也随之传入中国。
张骞通西域沟通了被中断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使汉族与边疆各族,使中国与周边各国建立起了友好关系,因此史书将张骞出使西域誉为“凿空”。
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地处丝路要冲的敦煌也随之发展成为中西交通的枢纽。
三、汉代对敦煌、河西的开拓经营
河西归入汉朝版图后,为了建立制匈奴、通西域的强大根据地,便在河西地区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郡县的设置就是其中之一。
汉在河西置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的敦煌郡共统辖6个县,即:
敦煌(今敦煌市西沙州故城)、冥安(今瓜州县锁阳城)、效谷(今敦煌市东北)、渊泉(今瓜州县四道沟)、广至(今瓜州县破城子)、龙勒(今敦煌市南湖破城)。
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地区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与其在中西交通中的咽喉地位,遂成为西汉政府经营西域的前哨与基地。
而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要冲与枢纽,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西汉对河西、敦煌主要的经营措施有:
首先,移民实边,增加人口。
向河西地区移民的对象主要是一些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即史书所说之“下贫”之人,同时也包括一些罪犯和少数民族等。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已有61270户,282110口。
其中敦煌郡有户11200,有口38335。
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但促进了河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在加强边防、防御匈奴入侵等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随着移民与设立郡县,汉王朝将内地实行的封建经济与政治制度推行到了河西,从而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发展。
其次,西汉政府积极在河西、敦煌地区实施屯田。
屯田的组织形式有军屯和民屯。
见于史书和汉简记载,负责屯田的官员及有关人员有农都尉、护田校尉、候农令、仓长、仓佐、仓曹吏等,而具体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戍卒称为戍田卒、事田、田卒等。
屯田的收获,不仅解决边防供给,还可在市场出售。
汉代在河西及敦煌地区的屯田生产,使得边郡粮库充足,家给民足,大大减轻了国家由内地向边塞运粮的负担。
同时增强了边塞的武备力量,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尤其在农业与畜牧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从而为汉王朝经营西域与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节魏晋北朝时期的敦煌
一、魏晋北朝时期敦煌的历史状况和军事建置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各豪强势力集团,拥兵自立,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214年,曹操进军陇右,消灭马超集团,整个关陇地域遂成为其势力范围。
曹丕代汉建魏,继续推行西汉以来的河西屯戍政策。
公元227年(太和元年),仓慈继任敦煌太守,他治理清正廉明、管辖有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敦煌商业与社会生产的发展。
首先他面对“大族田连阡陌,小民无立锥之地”的状况,采取“随口割赋”的办法,将大户多余的田地按人口分给无地的农民,赋税按田亩和人口分摊。
其次,严格法治。
仓慈到任后将各县衙门积压的案件一一查究处理,宽严相济,严禁滥刑,使社会风气好转。
同时,仓慈以民族平等的态度,保护和鼓励西域人来敦煌经商,对过往客商给予优待,并公平市价,促进了敦煌商业的发展。
齐王嘉平元年(249年),皇甫隆出任敦煌太守,在敦煌改进和推广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即耧犁耕作技术。
并实行了严整土地、分畦灌溉的“衍溉法”,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防止了土地板结。
使敦煌的农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
西晋在河西设凉州刺史部,敦煌属凉州。
当时的敦煌郡所辖各县,有史料可考者为:
昌蒲(今肃北蒙古自治县一带)、敦煌、龙勒、效谷、广至、宜禾、冥安、深泉(即汉渊泉)等8县,郡治敦煌。
有户6300户,人口约3万余人。
晋初,东吴降将吾彦出任敦煌太守。
吾彦在其任期内躬耕力行,劝民生产,促进了敦煌农业经济的持续繁荣。
西晋末年,爆发了“八王之乱”,形成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
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统辖。
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前凉张骏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与西域都护、戍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设置为沙州,治所为敦煌,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沙州”之名始于此。
前凉在敦煌兴办学校,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促进了敦煌地区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发展。
其中有名的阳开渠、阴安渠、北府渠等水渠,就是在此时开凿
前秦建元21年(385年),苻坚徙江汉之民万余户,中州之人七千户到敦煌,这是继汉武帝之后,对敦煌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促进了敦煌农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麟嘉七年(395年),后凉内乱,武威、张掖百姓数千口涌入敦煌与晋昌,从而为敦煌输送了人力。
据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西南的“孟授渠”就是在此时修成,成为造福敦煌人民的重要水利工程。
公元400年,李暠称凉王,建都于敦煌,敦煌遂成为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
西凉建国之初,敦煌地区经济比较繁盛,李暠采取诸多措施发展了敦煌的农业、教育与文化等事业。
在农业上他动员流民归田,从事农桑,并在玉门、阳关一带屯田,采取“寓兵于农”的措施,发展当地农业。
同时李暠还注重振兴敦煌文教事业,在敦煌南门外建造一座“靖恭堂”,作为议论朝政、检阅武事、听取意见的地方,并在敦煌设立县学、州学和医学,宣扬儒家学说,促进了敦煌的教育事业发展。
然而自405年,李暠东迁都城至酒泉,同时带走了两万多户人口,大大削弱了敦煌的实力。
421年,北凉沮渠蒙逊攻破敦煌。
沮渠蒙逊系张掖卢水胡人,汉化程度很深,在他治理敦煌期间采取了一些富国强兵的政策,如鼓励人民努力耕作,发展农业生产,并重视汉族文化的发展,如敦煌学者宋繇、阚骃等都为他所重用。
442年,北凉沮渠无讳逃离敦煌后,西凉李暠孙李宝趁机返回,并派其弟李达向北魏请降,北魏遂任命李达为敦煌太守,任李宝为镇西大将军、领户西域校尉、沙州牧、敦煌公。
从此敦煌归属北魏统辖。
正光五年(524),北魏北方边镇爆发“六镇起义”,孝明帝下诏将边镇“镇改为州”。
敦煌因盛产美瓜而取名“瓜州”,领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治所为敦煌。
孝昌元年(525),北魏派元荣任瓜州刺史,永安二年(529),又封元荣为东阳王。
元荣任刺史历北魏、西魏两代,为时近20年。
在元荣治理敦煌的近20年中,他团结豪强大家,发展当地经济,并大修佛窟,使敦煌经济文化不断发展。
北周取代西魏后,继续在敦煌设置瓜州,并任命建平公于义继任瓜州刺史(约565~576年)。
于义与东阳王元荣一样,十分佞佛。
在其任职期间,大兴修窟造像。
也正是在东阳王、建平公等的带动下,敦煌的佛教日益兴盛。
二、佛教活动的兴盛
早在西汉末东汉初,佛教便经由西域传入祖国内地,敦煌遂成为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
而佛教在敦煌民间的大流行则开始于西晋末年、十六国时期。
此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祈求来生的幸福,人们纷纷求助于佛教。
同时,一些社会上层人士的崇佛也对佛教在敦煌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前所述元荣与于义等人。
十六国时,河西地区的佛教以译经与讲经为主,同时石窟寺的开凿也兴盛起来。
被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自晋武帝时便游历西域诸国,通晓36国语言,世居敦煌,在敦煌组织了自己的译场。
《开元录》载其共译经175部354卷,《高僧传》称他为“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的人。
这之后的鸠摩罗什与昙无谶亦是著名的译经大师。
鸠摩罗什(344~413),龟兹(今新疆库车)人,前秦建元二十年(384)苻坚派大将吕光进攻西域得胜东归时,带鸠摩罗什到达凉州,据传罗什一行途经敦煌时,所乘白马病死,遂葬马并在其上建塔,今敦煌仍遗留白马塔胜迹。
罗什在凉州从事译经多年,此后又入长安,继续译经。
后人将他和唐玄奘、义净并称为古代的三大翻译家。
北凉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昙无谶亦对敦煌的佛教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原为印度僧人,后辗转经龟兹、鄯善来到敦煌,并在此熟悉了汉语。
由昙无谶翻译的佛经共有11部一百多卷,主要有《大般涅槃经》、《悲华经》、《金光明经》等。
他在《大般涅槃经》中,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还进一步提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可成佛。
这一提法,突破了佛教的原有思想,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在译经上取得较大成就外,河西佛教的兴盛还体现在石窟寺的大量建造上。
河西地区现存的石窟寺之多,在全国是十分罕见的。
这些石窟寺许多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尤其是著名的莫高窟,就是在十六国时期开凿的。
据武周圣历元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一个叫乐僔的禅僧云游到敦煌,忽然看见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僔认为是佛的昭示,于是他便开凿了第一个石窟。
此后不久,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禅师,在乐僔所开石窟旁又开凿了一窟。
然而,由于时代久远与风沙侵蚀,这两个石窟已无法考求。
据今人研究,现存确知为十六国时期的洞窟大约有九个,它们的编号分别为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
北魏时期,敦煌石窟与寺塔继续兴建。
《魏书·释老志》言:
“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反映了敦煌石窟寺修建的兴盛。
太武帝拓拔焘时虽有灭佛事件,但对敦煌佛教的发展似乎影响不大。
北魏后期,元荣任瓜州刺史期间大兴佛事,出资造经两百多部,并在莫高窟掀起了造窟高潮。
莫高窟现存北魏末年至西魏时期佛窟10个,都与元荣有直接关系。
北周时期瓜州刺史建平公于义,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他在任期间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
其中北周修建的最大石窟428窟,就是于义所建。
三、莫高窟的早期建造
敦煌石窟艺术的内容可分为建筑、雕塑和壁画三方面。
石窟建筑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
僧房、塔庙和佛殿。
僧房也称禅窟,是僧侣坐禅修行的地方。
主室为长方形或方形,顶部为平棋倒斗藻井,正壁开龛塑佛像,四壁布满壁画。
如268、487等窟。
塔庙,即中心窟,洞库平面呈长方形,前部为“人字披”屋顶,后部有中心方柱,供僧侣和善男信女绕塔观像。
如254、257等窟。
佛殿,即倒斗藻井窟,正壁开龛造像,是群众礼拜供养之所,如272、249等窟。
塑像是石窟的主体。
敦煌现存彩塑2415身,其中北魏塑像318身。
早期的塑像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有佛、菩萨像。
佛像一般都有侍从菩萨,形成一佛二菩萨的形式。
北周时期增加了佛弟子,一铺像最多可达五身。
早期洞窟多以弥勒(菩萨或佛像)为主尊像,一般都塑在中心柱和南北壁上层阙形龛中,表示弥勒高居“兜率天宫”。
据段文杰等先生的研究,早期塑像大多造形朴拙,色彩淳厚,人物比例适度,面相丰圆略长,鼻隆眼鼓,脖颈细长,衣服折波,紧贴身体。
北魏晚期人物造像面貌清瘦,眉目开朗。
北周时则出现了面短而艳的风格,人物高鼻深目,具有西域民族某些特征。
敦煌壁画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是经变画,即佛经故事画,它是莫高窟壁画中的最主要部分。
如五百强盗成佛图、月光王以头施人、九色鹿拯救溺人等。
二是佛像画,主要是以佛为主体的说法图。
早期洞窟一般都有说法图,如420窟中的《群鸟听法图》,描绘了释迦牟尼坐在柳树之下说法,各种禽鸟围绕宝座听法,整个画面生动活泼。
三是民族传统神话图,如西王母驾车西游、女娲补天等故事。
四是装饰图案,主要是用于顶部装饰的平棋与藻井。
除此之外,还有龛楣、边饰和椽间图案,主要纹样有莲荷纹、忍冬纹、云气纹、火焰纹、棋格纹、鸟兽纹等。
五是供养人画像,供养人是指那些出钱修窟的人,他们修好窟之后,便将自身及家人的像画在主要壁画下方,排列成行,并将个人的姓名、官品等写于像旁。
供养人画像少则十数身,多则成百身。
在绘画技法上,十六国及北魏前期多采用凹凸晕染法并多使用土红地色,可形成人物的立体感与整个画面温暖浑厚的色调。
北魏晚期突破了土红地色所形成的浓重淳厚的基调,出现了爽朗明快的中原风格。
北周时代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民族的融合,南北两种艺术风格逐渐融合。
在绘画上,中原式染色法与西域式明暗法相互结合,产生了富有立体感的新晕染法,人物表现更加生动形象。
第三节隋唐时期的敦煌
一、东西交通的兴盛
隋炀帝即位后,为打通丝路,进一步经营西域,多次派兵出击吐谷浑与西突厥,取得全胜战绩,西突厥归降了隋朝。
大业初年隋炀帝派裴矩前往张掖,主持同西域的贸易。
裴矩到达张掖后,往来于敦煌与张掖之间,积极了解西域各国的地理形势、民风物产,撰写《西域图志》3卷,上呈炀帝,引起炀帝的重视,亲自接见了裴矩,详细询问了西域的情况。
裴矩回到张掖后,对进入敦煌的过往客商,给予优待,提供各种方便。
在隋政府的支持下,河西诸地的商贸活动日益繁荣兴盛起来。
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亲自出巡张掖。
在张掖召见西域27国的使者。
据《隋书·裴矩传》记载,使者们佩兰玉、被锦罽,焚香奏乐,尽情歌舞。
当地百姓也都盛装观看,人群长达数十里,充分显示了隋王朝与河西的繁盛。
隋炀帝在张掖举行了盛大的商品交易会,扩大了西域与内地的商贸、文化往来。
隋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有北中南三条,分别为:
北道(又叫新北道):
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再经蒲类(今巴里坤)、铁勒部,度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今地中海),大致沿天山北麓而至中亚。
中道:
出敦煌至高昌(今吐鲁番),经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再经费尔干纳等地而至波斯(今伊朗),在我国境内大致是沿天山南麓而行。
南道:
出敦煌至鄯善(今若羌),经于阗、朱俱波(今叶城南)、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再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
在我国境内是大致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而行。
这三条道路都“发自敦煌”,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在中西交通中具有枢纽地位。
唐朝初期,西域处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为了肃清边患,开通丝路,贞元九年(635)唐太宗派大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分兵出击吐谷浑,伏允可汗兵败自杀,其子慕容顺率部归降,从而解除了其对河西的威胁。
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率军平定高昌,唐在高昌设西州,不久又在此设安西都护府,镇守西域。
接着,唐朝分别于贞观18年(644)与22年(648)攻下焉耆与龟兹,从此西域各族纷纷内附。
此后迁安西都护府至龟兹,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即安西四镇。
高宗初年,西突厥灭亡,公元702年,唐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北庭都护,管理西突厥故地,从此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保证了敦煌商业贸易的繁荣。
唐代的敦煌,既是西域交通的枢纽,又是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都会。
在这里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商贩、西行求法的僧侣等人,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于西域与中原、中国与西亚之间。
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等通过敦煌输送至世界各地,西域、中亚的珠宝、香料、宗教等也经由敦煌传布内地。
二、敦煌社会经济的发展
隋朝建立以后,基于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视对河西及敦煌地区的经营。
隋中央政府通过移民与屯田,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到敦煌和河西。
如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到,隋代敦煌地区使用的耕犁,已由魏晋嘉峪关画像砖墓中所描绘的长辕长床犁,变成了长辕无床犁,这种犁结构简单,既可翻土又可破土。
隋朝对河西畜牧业也很重视,在河西及敦煌设置了牧马监,每年养马十余万匹,隋朝的军马基本上是由此地供应的。
到了唐代,中央政府充分认识到河西乃中原王朝“强兵足食之本”,所以对河西及敦煌的开发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