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族群结构与族际关系.docx
《人口流动族群结构与族际关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口流动族群结构与族际关系.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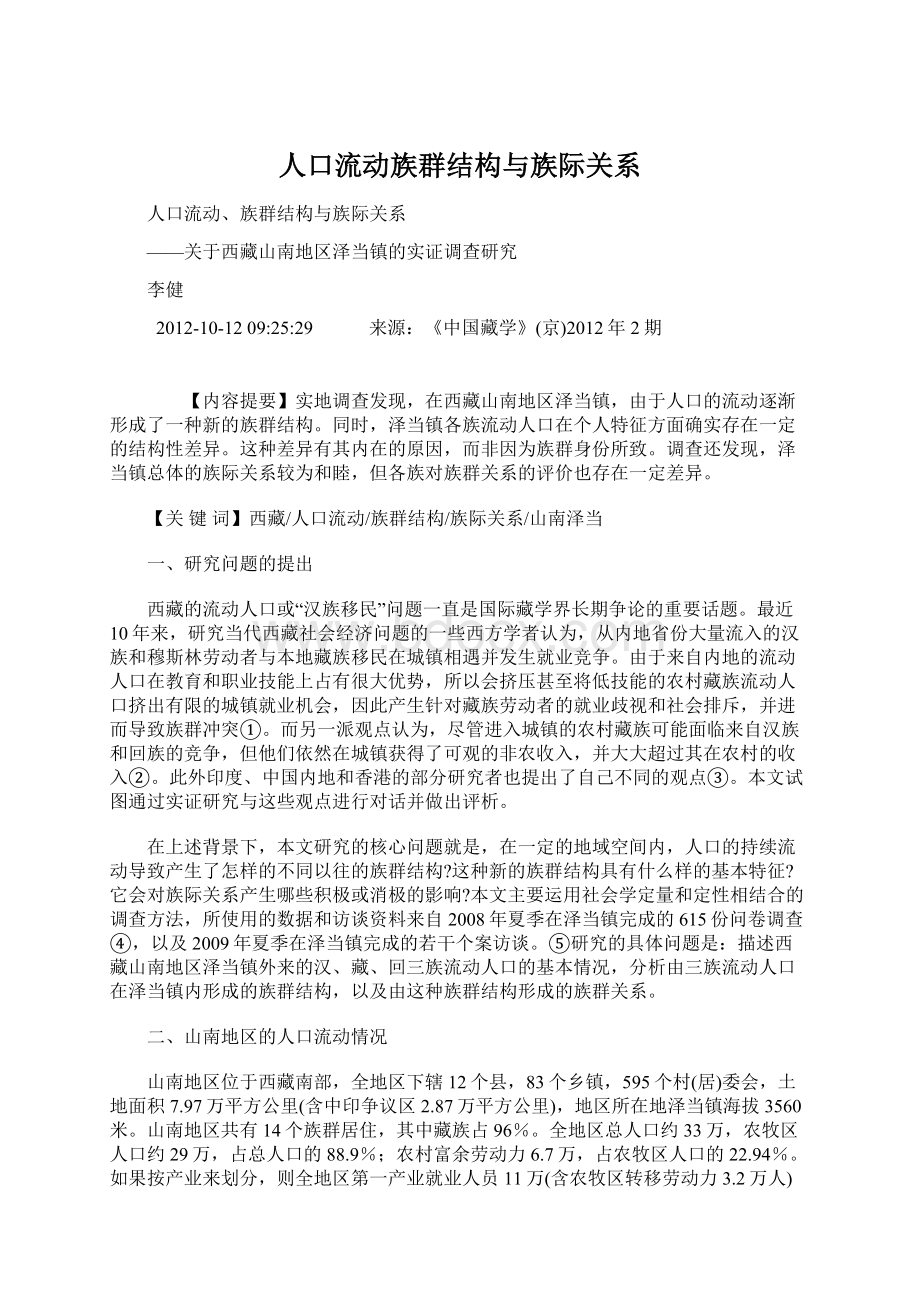
人口流动族群结构与族际关系
人口流动、族群结构与族际关系
——关于西藏山南地区泽当镇的实证调查研究
李健
2012-10-1209:
25:
29 来源:
《中国藏学》(京)2012年2期
【内容提要】实地调查发现,在西藏山南地区泽当镇,由于人口的流动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族群结构。
同时,泽当镇各族流动人口在个人特征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差异。
这种差异有其内在的原因,而非因为族群身份所致。
调查还发现,泽当镇总体的族际关系较为和睦,但各族对族群关系的评价也存在一定差异。
【关键词】西藏/人口流动/族群结构/族际关系/山南泽当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西藏的流动人口或“汉族移民”问题一直是国际藏学界长期争论的重要话题。
最近10年来,研究当代西藏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从内地省份大量流入的汉族和穆斯林劳动者与本地藏族移民在城镇相遇并发生就业竞争。
由于来自内地的流动人口在教育和职业技能上占有很大优势,所以会挤压甚至将低技能的农村藏族流动人口挤出有限的城镇就业机会,因此产生针对藏族劳动者的就业歧视和社会排斥,并进而导致族群冲突①。
而另一派观点认为,尽管进入城镇的农村藏族可能面临来自汉族和回族的竞争,但他们依然在城镇获得了可观的非农收入,并大大超过其在农村的收入②。
此外印度、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部分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③。
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与这些观点进行对话并做出评析。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人口的持续流动导致产生了怎样的不同以往的族群结构?
这种新的族群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
它会对族际关系产生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本文主要运用社会学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所使用的数据和访谈资料来自2008年夏季在泽当镇完成的615份问卷调查④,以及2009年夏季在泽当镇完成的若干个案访谈。
⑤研究的具体问题是:
描述西藏山南地区泽当镇外来的汉、藏、回三族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分析由三族流动人口在泽当镇内形成的族群结构,以及由这种族群结构形成的族群关系。
二、山南地区的人口流动情况
山南地区位于西藏南部,全地区下辖12个县,83个乡镇,595个村(居)委会,土地面积7.97万平方公里(含中印争议区2.87万平方公里),地区所在地泽当镇海拔3560米。
山南地区共有14个族群居住,其中藏族占96%。
全地区总人口约33万,农牧区人口约29万,占总人口的88.9%;农村富余劳动力6.7万,占农牧区人口的22.94%。
如果按产业来划分,则全地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11万(含农牧区转移劳动力3.2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73.5%。
⑥(见表1)可见,该地区人口城镇化率极低,农村人口比重大,富余劳动力多,为农牧民外出打工提供了条件。
一般来讲,西藏的流动人口包括来自区内外的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及外来朝佛人员、旅游观光人员等。
在本文中,流动人口主要指以赚钱谋生为目的,离开本乡外出务工经商的人员,短期的朝佛者和游客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山南地区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数量相对稳定。
据不完全统计,在2008年之前,长期办理暂住证的有3万余人。
由于受拉萨“3.14”事件影响,2008年上半年,流动人口数量有所减少,全地区暂住人口1.7万,其中泽当镇暂住人口9108人。
⑧
泽当镇是西藏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流动人口较多,是山南地区各县农牧民进城务工的重要目的地。
2008年,全镇拥有户籍人口7010人,其中农业户口6708人,非农业户口302人。
⑨泽当镇下辖6个社区居委会,其中有3个位于泽当镇城区⑩。
泽当镇流动人口主要由以下三部分构成:
(1)来自西藏区内各地农村的藏族中青年农民,以山南地区的为主;
(2)来自自治区外其他藏区的农村藏族中青年农民,人数较少;(3)来自其他省区的汉族、回族等人员,以农村中青年劳动者为主,人数较多。
组成泽当镇城区的泽当、乃东、结莎3个社区居委会是泽当镇本地人口主要的居住区。
根据2008年的数据,泽当镇区的流动人口在各居委会都超过了当地人口,在结莎居委会,外来流动人口几乎达到了当地人口的3倍。
这还是由于“3.14”事件的影响,导致外来流动人口大幅减少。
(12)乃东居委会所在地区是山南地区和乃东县党政机关及单位的集中地,流动人口相对较少。
从表3中可发现,进入泽当镇的外来人口,男性与女性的数量差别并不大,分别占55%和45%。
不过这是总的性别比例,看不出族群间的差异。
从族群构成来看,汉族是外来流动人口的主体,占66.24%,将近2/3,这与2005年拉萨调查的比例是相近的(14)。
其次是藏族,占到了总数的1/4强,但以区内藏族为主,区内藏族占了藏族流动人口总数的68.40%,而区内藏族又以来自山南地区各县的为主。
进入泽当镇的区外藏族人数与回族相当,比例都接近8%。
三、泽当镇的族群结构
1.被访流动人口的族群与性别构成在被调查的615名流动人口中,男性占54.8%,女性占45.2%。
这与泽当镇暂住人口中男性占55%的比例几乎完全一致。
在被访者的族群构成方面,由于课题设计的需要,主要是想了解流动人口中藏族的具体情况,在被调查流动人口中,藏族378人,占61.5%;汉族162人,占26.3%;回族70人,占11.4%;其他民族5人,占0.8%。
(15)
从两性比例来看,三个族群各不相同。
藏族流动人口是女性略多于男性,汉回两族是男性远多于女性,其中回族的男女比例最为悬殊。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汉回两族流动人口几乎全部是由区外远距离迁徙进藏谋生者,从事自主经营的比例较高,对西藏的高原环境适应性差。
从选择性迁移的角度看,男性更倾向于迁移。
而藏族绝大部分来自山南本地,离家较近,从事服务业的比例更高,因此妇女的迁移可能性就要大得多。
2.被访流动人口的迁出地分布调查流动人口的籍贯或迁出地,有助于我们了解流动人口的来源和流向,有助于把握流动人口本身的特征。
由表5可知,本次调查的泽当镇流动人口来自全国16个省区,其中区内以西藏山南各县的为主,超过了一半,区外以甘肃、四川为主。
汉族162个流动人口中,四川汉族86人,占被调查汉族总数的53.1%;居二三位的甘肃和河南汉族分别为21人和19人,占13.0%和11.7%,三省合计占77.8%。
可见泽当镇汉族流动人口的来源地比较集中。
同样,藏族378个流动人口中,来自山南本地区的345人,占藏族总数的91.3%,区外藏族的比例很低。
回族的来源集中度最高,来自甘肃的回族68人,占被调查回族70人中的97.1%。
以上分析说明赴泽当镇的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地缘性特征。
四川汉族、甘肃回族和山南藏族分别是泽当镇三族群流动人口的主体。
3.被访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年龄是流动人口的一个基本结构特征,从年龄的分布即可看出外出人群是以哪一年龄段为主。
一般来说青壮年是最倾向于流动的人群。
在被访者中,20岁至29岁的青年人最多,占45.7%。
如果将20岁至39岁的人算作青壮年人口,则青壮年所占的比重为72%。
不同族群的年龄结构差异往往与其他结构性差异相关。
在20—29岁和30—39岁这两个关键年龄组里,三个族群的情况各不相同。
汉族中30岁组的比例比20岁组还要高,说明泽当的汉族流动人口很可能拥有更多的资本和更丰富的社会经验,结婚成家的比例会更高。
相反,藏族流动人口的年龄明显更加年轻,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未婚的外出打工者。
回族年龄结构居中。
在泽当的青壮年流动人口中,藏族以青年为主,汉族和回族以壮年为主,反映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必然是汉族和回族要高于藏族。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
4.被访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在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影响个人职业、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关键性因素。
考察流动人口中不同族群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藏、回3个族群的受教育程度差异非常明显。
其中汉族受教育程度最高,藏族次之,回族最低。
就文盲率而言,汉族为3.7%,藏族为19.8%,回族则是44.0%。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以往调查的经验,西藏流动人口中藏族的文盲率要远大于回族。
本次调查中拉萨的数据也显示,藏族的文盲率为42.2%,回族则为24.6%。
日喀则的数据分别是,36.8%和29.4%。
为什么唯独山南的数据显示的正好相反呢?
除了调查样本选取的原因外,在泽当的访谈资料可以提供一定的解释。
来自甘肃的26岁回族虫草商M先生说:
我没上过学,我们那时家里穷嘛,我很想上学,但上不起,现在只会写自己名字。
……写字的话我们反正是汉字也不会写,藏字也不会写,我们自己的那个经文也不会写。
……这个院子里住的人(几乎全部是回族)90%都没上过学。
汉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远远高于藏回两族,这也使汉族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可能要好于藏族。
回族因为自身善于经营的传统、强有力的族内社会资本支持和对藏语的掌握,即使文化程度不高,其收入也可能远高于藏族。
M先生的话印证了这一点,他说:
我藏话70%都会说,学也没学,反正慢慢就会了。
这边做生意的回族基本都会藏语,有的百分之百都能懂。
……做生意就是脑子灵活一点,不用看文字。
……我们回族互相帮忙,只要你不特别坏的话。
假如我们两个人合伙借钱做20万的生意,我们连欠条都不打,到时说好什么时候还就还了。
我们欠了钱不能不还。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发现,泽当镇的流动人口中,藏族、汉族、回族之间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均有结构性的差异。
特别是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汉族流动人口远远高于藏族和回族。
总的趋势是,藏族流动人口在泽当镇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这种相对弱势地位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藏族务工者自身的社会特征,如大部分年龄较小,从小在几乎是纯藏族的社区环境中长大,对城镇里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并不熟悉,汉语能力较差,职业技能不足,社会经验欠缺,竞争意识不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之后,外来的汉族回族需要经过竞争和淘汰,只有技能高或各种资本较多的人最后能留下来。
显然,这种族群结构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客观原因,并不是西方一些学者所谓的是由于政府推行的制度性歧视和排斥的结果。
事实上,调查发现当地政府也一直在为改变藏族务工人员的弱势状况而努力,如举办各类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进行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在乃东县的部分农村,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当然,实际效果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族际关系
1.问卷调查结果族群关系一直是族群社会学中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较难测量的一个变量,需要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分析。
本次调查显示,泽当镇内族群间关系总体良好,但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从表6可见,总体上每个族群对与其他族群关系的评价都较高,其中回族评价最高,汉族居中,藏族相对最低。
通过卡方检验,说明三个族群对与其他族群关系的评价确实存在差异。
与藏族相对的汉回两族基本都是区外流动人口,国外的研究认为这两个群体间存在相当紧张的关系,但调查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只能说藏族流动人口对泽当的其他族群评价相对较低。
超过1/3的藏族和超过3成的汉族认为与其他族群关系一般。
这部分持中间态度的外来人员很关键,如果生活中遇到族群纠纷或矛盾,他们很可能转而对族群关系评价不好,反之,也可能转向好的评价。
认为与其他族群关系不好的人比例极低,但是鉴于在调查中,敢于公开表露自己对族群关系不满的人肯定要少于实际,对这一极少部分人也应给予关注。
泽当镇的本地居民主要是藏族,通过测量与本地人的关系(表7),也可以间接发现各族流动人口与本地藏族之间的关系。
总体上,各族流动人口对这一关系评价很高。
回族对本地藏族评价最高,这可能与回族和本地藏族交往多有关。
回族做的虫草、皮革等生意主要同本地藏族发生联系,范围也会超出泽当镇,遍及整个山南地区。
外来藏族对本地人评价也很高,接近回族,这显然与他们同属一族有关。
汉族流动人口从事职业较杂,人数又最多,很可能对本地人形成一定压力,因此,汉族对本地人评价明显低于其他两族,但是公开认为关系不好的也没有。
卡方检验显示,三族对与本地人关系的评价确实存在差异,但藏族和回族差异很小。
2.个案访谈分析本文选取了3个典型个案,分别是汉族、回族和藏族的外来经商者。
从中可以窥见一个更深入的族际互动模式和族群关系面貌。
3个个案都从事自我雇佣式的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个案一:
废品收购点的女主人(17)
W女士,汉族,39岁,河南商丘人,泽当镇私人废品回收点女主人。
在泽当生活了4年的W女士对于与周围人群的接触交往深有体会,对镇里不同族群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在这生活跟周围的本地人关系很好,人都是好的。
哎呀,我们那房东(藏族)最好了,我们跟他们藏族最合得来,感觉比跟这里的汉族还合得来。
他们实在得很,善良得很。
不像我们老家那些过来做生意的,钩心斗角。
我们跟回族交往不多,还是跟藏族、汉族交往最多了,跟回族一般不打交道,就是他卖东西,我们给钱,就这些话。
平时不交往,主要是不喜欢,就感觉没那个心想去跟他们交往,感觉没有像跟咱们这些人打交道舒服一些。
在这位女主人眼里,与镇里的藏族老百姓是最好交往的,甚至互相帮助,评价远远高于对同样来自河南商丘的老乡,同乡群体反而因为行业竞争的原因而关系紧张。
当地管理废品收购的派出所民警也证实说,他们老乡群体内部的关系很紧张,不怎么来往。
其次,他们与回族并无利害冲突,但交往仍然很少,主要源于心理上的距离感和个人方面的原因。
最后,被访者反复提到“汉藏就是一家人”,“不要老分汉族还是藏族”,对藏族老百姓的亲近感溢于言表,对他们淳朴善良的性格非常认同和称赞。
当然,与藏族偶尔的小争吵也是有的,被访者提到:
像他们(藏族)有时候也“挺坏”的,说点难听的话,像“把你们赶出西藏”。
有的调皮嘛,就这样说一句,对吧。
其实他就是说一下。
像那天,有一个就对我们说,“哎呀,你们起来,这是我们的地盘。
”……年轻人有的还是说那个嫩话,上了年纪的都不会。
好还是挺好的,要是不好我们马上走了,早就走了,现在再干五年还不想回去呢!
偶尔的小争吵并不影响被访者对当地藏族老百姓总体的好感,而且她对此也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并没有将这种小争吵与族群身份挂上钩。
被访者表示“再干五年还不想回去”显然不仅是因为在西藏能够谋生,而是表现出对当地良好的汉藏关系的信心,对当地社会环境和与当地人的关系表示满意。
在访谈中,W女士不赞同老是强调汉族藏族的区分,认为也没啥区别,这至少反映了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族群区分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偶尔的小争吵都是发生在被访者同藏族青年人之间。
虽然次数不多,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部分年轻一代藏族对外来的经营者存有抵触情绪。
这与问卷中关于族群关系的调查结果较吻合。
个案二:
年轻而老道的回族虫草商
M先生,男,26岁,回族,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马集镇人。
我们这儿回族和藏族通婚的很多,主要是回族男的娶藏族女的。
……反正藏族跟我们回族打交道比较好一点,交往也多,成婚也比较配。
我们就是一般跟汉族交流得少,跟藏族一般哪个村子里都有认识的人。
主要是因为我们做生意和藏族接触得多。
挖虫草的地方,纠纷抢劫案件比较多……现在我们白天出去没什么危险,到桑日这一带沟里去很安全,人基本上都认识,我们的名字他们(当地藏族)都知道,那边也有工作组嘛,一般都没问题。
M先生也表现出了对藏族较高的认同度。
藏回通婚多是一个重要指标,对藏回通婚的认可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藏回关系并不一定就如外界所认为的那么紧张。
从被访者与当地藏族的熟识程度看,显然他在当地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网,这种关系网虽然主要是商业性的,但它也为被访者提供了很好的人身安全保护,所以才使他很有信心的认为自己从事高危险的行业却很安全。
另一方面,下到基层的回族虫草商与虫草产区的藏族老百姓实际上也结成了一定的利益共同体,缺了任何一方的信任,另一方的利益都会受损。
访谈说明,至少这一类型的较良好的藏回关系是存在的。
西方的研究一般认为,在西藏的城镇中,藏回之间的矛盾冲突更为严重。
该个案所代表的群体显然并不支持这一点。
个案三:
LM的往事
LM,女,藏族,35岁,拉萨市曲水县人,泽当镇某藏茶馆老板。
以前在隆子县那边开做汉族菜的餐馆,“3.14”以后那边生意不太好就来这里了。
这边生意还凑合,主要是藏族老百姓进来喝茶。
……平时也不和周围的人来往。
一般周末的时候,汉族打工的喜欢来喝茶,工地上的四川人来的比较多。
跟汉族交流没什么问题。
回族从来不来,也从不交往。
受到“3•14”事件影响的不仅是外来的汉族和回族,当隆子县的汉族因此返回内地后,LM的餐馆也就很难经营下去,才搬到泽当。
市场经济是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并不适宜用族群的边界强硬分割。
在访谈中,可以观察到LM的汉语讲得不错,只是跟回族没有来往。
LM的藏茶馆并不是只有藏族顾客,打工的汉族也时常能给她带来一些生意。
五、结束语
泽当这样一个中国西南边疆的小镇,无论是镇区面积、常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如果放在内地可能微不足道,但其人口流动与族群结构呈现的特征完全不同于内地。
国内外学者对西藏流动人口问题有过很多争论,但从实证调查的角度看,现实的情形往往要比想象的更为复杂。
调查数据显示,泽当镇各族流动人口在个人特征及收入等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是基于个人技能、拥有资源或职业类型的不同,这种不同又是西藏与内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致,而非因为族群身份的差异。
在当地获得的深度访谈资料有助于加深对微观层面上族际交往的了解,其结果进一步证明流动人口之间并不存在基于族群身份的社会排斥,各族外来者更多地集中在自己擅长和具备社会网络的不同行业中。
在泽当,汉回两族经济收入接近,但关系相对冷淡;汉藏和藏回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关系反而较好,甚至对他族群的正面评价超过了对本族群的评价。
可见,族群间经济收入差距大并不必然导致族群关系差。
另一方面,尽管泽当镇族群关系总体和睦,但外来藏族对族群关系的评价较汉回两族低,应当引起重视。
在看待西藏城镇流动人口问题时,既不能因为局部的族群关系和睦就忘记了在总体上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识,也不能因为存在可能引发族际矛盾的隐患就否定了长期形成的各族群和睦共处的事实。
在西藏流动人口与族际关系问题上,应采取宏观和微观相贯通的研究视角,不断通过实地调查来推进专题研究和学术对话的深度,本文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尝试。
注释:
①参见Fischer,AndrewMartin,2005a,StateGrowthandSocialExclusioninTibet:
ChallengesofRecentEconomicGrowth,Copenhagen:
NIASPress.
②Goldstein,Melvynetal.2006,“DevelopmentandChangeinRuralTibet:
ProblemsandAdaptations”,BarrySautmenandJuneT.Dreyer,eds.ContemporaryTibet,NewYork:
M.E.Sharpe.
③DawaNorbu,2006,EconomicPolicyandPracticeinContemporaryTibet,BarrySautmenandJuneT.Dreyer,eds.ContemporaryTibet,NewYork:
M.E.Sharpe;Sautman,Barry,2001,Tibet:
DevelopmentforWhom?
ChinaInformation,2001.2;马戎、旦增伦珠:
《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报告》[J],《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④该调查是由北京大学马戎教授主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旦增伦珠研究员具体负责的“西藏流动人口管理对策研究”课题调查的一部分。
2008年7月,课题组部分成员在山南泽当镇进行了为期数天的座谈、访谈和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点主要有龙马市场、贡布路废品收购户、泽当老村新村出租房、雅砻河酒店、白日街工地、萨热路工地、建材市场、蔬菜基地、粮贸中心出租房等,最后完成有效问卷615份。
调查员是经过专门培训的西藏大学学生和山南地区中学教师,他们辛苦而认真的工作保证了问卷的质量,在此表示感谢。
⑤此次访谈主要在泽当镇内,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索朗央宗担任翻译,特此致谢!
⑥山南地区行政公署:
《向西藏流动人口管理与对策研究调研组的汇报材料》[N],2008年7月28日。
⑦同上。
⑧同上。
⑨不包括居住在泽当镇的山南地直和乃东县直机关的3万多人口,泽当镇虽然是地区的首府,但本镇所辖的6个居委会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属于农牧业户口,城市化还处于低水平。
⑩泽当镇共辖6个社区居委会,其中3个居委会远离镇区,不涉及流动人口问题。
(11)泽当镇政府提供,2008年7月18日。
(12)从全地区来看,2008年办理暂住证的人数比往年减少将近一半。
(13)乃东县公安局:
《流动人口调研汇报提纲》[N],2008年7月18日。
(14)参见马戎、旦增伦珠:
《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报告》,《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15)以下分析数据均来自2008年的问卷调查,不再一一标出。
(16)因此次调查并非专门针对族群关系,在问题设计时未细化到每两个族群间的关系。
(17)废品收购业是一个外来汉族相对集中的行业。
个案一中的女主人笔者曾在2008年7月和2009年8月分别作过访谈,此资料是对第二次访谈的整理。
个案二和三是2009年8月作的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