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公共卫生史上的胜利肝炎防治.docx
《台湾公共卫生史上的胜利肝炎防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台湾公共卫生史上的胜利肝炎防治.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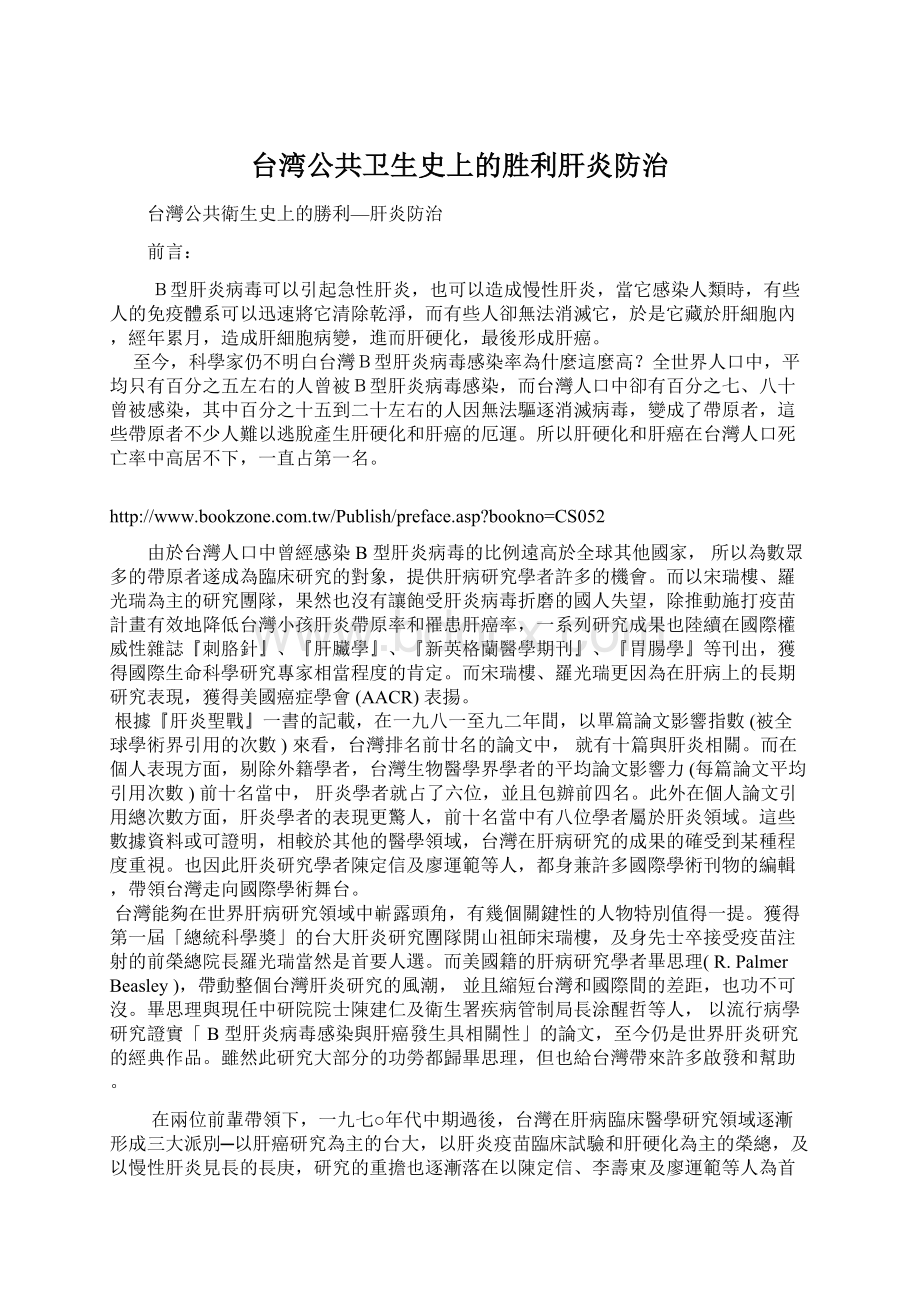
台湾公共卫生史上的胜利肝炎防治
台灣公共衛生史上的勝利—肝炎防治
前言:
B型肝炎病毒可以引起急性肝炎,也可以造成慢性肝炎,當它感染人類時,有些人的免疫體系可以迅速將它清除乾淨,而有些人卻無法消滅它,於是它藏於肝細胞內,經年累月,造成肝細胞病變,進而肝硬化,最後形成肝癌。
至今,科學家仍不明白台灣B型肝炎病毒感染率為什麼這麼高?
全世界人口中,平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人曾被B型肝炎病毒感染,而台灣人口中卻有百分之七、八十曾被感染,其中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的人因無法驅逐消滅病毒,變成了帶原者,這些帶原者不少人難以逃脫產生肝硬化和肝癌的厄運。
所以肝硬化和肝癌在台灣人口死亡率中高居不下,一直占第一名。
.tw/Publish/preface.asp?
bookno=CS052
由於台灣人口中曾經感染B型肝炎病毒的比例遠高於全球其他國家,所以為數眾多的帶原者遂成為臨床研究的對象,提供肝病研究學者許多的機會。
而以宋瑞樓、羅光瑞為主的研究團隊,果然也沒有讓飽受肝炎病毒折磨的國人失望,除推動施打疫苗計畫有效地降低台灣小孩肝炎帶原率和罹患肝癌率,一系列研究成果也陸續在國際權威性雜誌『刺胳針』、『肝臟學』、『新英格蘭醫學期刊』、『胃腸學』等刊出,獲得國際生命科學研究專家相當程度的肯定。
而宋瑞樓、羅光瑞更因為在肝病上的長期研究表現,獲得美國癌症學會(AACR)表揚。
根據『肝炎聖戰』一書的記載,在一九八一至九二年間,以單篇論文影響指數(被全球學術界引用的次數)來看,台灣排名前廿名的論文中,就有十篇與肝炎相關。
而在個人表現方面,剔除外籍學者,台灣生物醫學界學者的平均論文影響力(每篇論文平均引用次數)前十名當中,肝炎學者就占了六位,並且包辦前四名。
此外在個人論文引用總次數方面,肝炎學者的表現更驚人,前十名當中有八位學者屬於肝炎領域。
這些數據資料或可證明,相較於其他的醫學領域,台灣在肝病研究的成果的確受到某種程度重視。
也因此肝炎研究學者陳定信及廖運範等人,都身兼許多國際學術刊物的編輯,帶領台灣走向國際學術舞台。
台灣能夠在世界肝病研究領域中嶄露頭角,有幾個關鍵性的人物特別值得一提。
獲得第一屆「總統科學獎」的台大肝炎研究團隊開山祖師宋瑞樓,及身先士卒接受疫苗注射的前榮總院長羅光瑞當然是首要人選。
而美國籍的肝病研究學者畢思理(R.PalmerBeasley),帶動整個台灣肝炎研究的風潮,並且縮短台灣和國際間的差距,也功不可沒。
畢思理與現任中研院院士陳建仁及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長涂醒哲等人,以流行病學研究證實「B型肝炎病毒感染與肝癌發生具相關性」的論文,至今仍是世界肝炎研究的經典作品。
雖然此研究大部分的功勞都歸畢思理,但也給台灣帶來許多啟發和幫助。
在兩位前輩帶領下,一九七○年代中期過後,台灣在肝病臨床醫學研究領域逐漸形成三大派別─以肝癌研究為主的台大,以肝炎疫苗臨床試驗和肝硬化為主的榮總,及以慢性肝炎見長的長庚,研究的重擔也逐漸落在以陳定信、李壽東及廖運範等人為首的青壯派身上。
而從這個時期開始,有越來越多優秀人才投入肝病臨床研究領域中,賴明陽、陳培哲、許金川、蔡養德、朱嘉明、丁令白、吳妍華、胡承波、蘇宗笙、周成功、羅時成、施嘉和、吳肇卿、李發耀、林漢傑等各領域的人士都相繼在肝病研究上做出貢獻,其中以陳定信為首的台大研究團隊,由於資源及人才都充沛,整體而言,近來表現最搶眼。
.tw/237/23759.htm
歷史回顧
時代背景
日據時代,日本人發現台灣的肝炎以及黃膽性肝炎特別多,黃膽性肝炎當時叫做加達爾性黃疸。
那時曾懷疑黃膽性肝炎可能為傳染病,當時曾著手採集病患血液、大小便進行細菌培養,未能找到任何細菌,但卻注意到患者白血球數目減少的現象。
因而開始懷疑此病源體是否為病毒?
但日後所做黃疸一連串動物試驗,如老鼠、兔子都不成功,始終未能找到神秘的黃疸病毒(人類B型肝炎病毒只感染人類和黑猩猩靈長類)。
當時日本肝病患者已遠較歐美為多,但卻又不如台灣。
主持日本帝大醫學部第三內科的日本教授澤田藤一郎來到台灣後,很驚訝發現台灣竟有如此多肝病患者,尤其是肝癌,此盛況在日本是沒見過的。
澤田藤一郎專供人體解毒作用,用生化學方法來研究如何解毒,因看到如此多肝病患者,開始想辦法加強肝功能檢測,但因檢測工作須親自執行相當辛苦,加上檢測技術不純熟,因而中斷,此工作於是落在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第三屆畢業生宋瑞樓肩上,。
此時期另一位重要人物為羅光瑞,因隸屬軍方系統,在服從命令之天職下,進入陸軍八0一醫院胃腸科,進而與「肝病」結緣。
當時到病房時,也幾乎是肝硬化,黃疸腹水之病人。
ㄧ九五0年代末期,羅光瑞擔任住院醫師期間,對肝病造成原因的推測與寄生蟲有關,如中華肝吸蟲等,中國人肝病多是因寄生蟲盛行,再加上營養不良所造成,但羅光瑞懷疑此說法,因六0年代以來生活經濟、醫藥衛生改善,傳染並降低,但肝病仍不斷增加。
羅光瑞因而想赴美進修研習肝炎相關研究,但因美國大多為酒精性肝炎,故此次留學在肝炎探究方面並未有預期的進展,但他卻體會到ㄧ件事,自己的問題,只能靠自己解決。
肝炎病毒的發現
1965年,布侖伯格(B.S.Blumberg)在澳洲進行研究時,於當地士著的血液中發現一種新的抗原,稱為澳洲抗原(Australiaantigen)。
此抗原的出現與肝炎有關,後來經過各地區之研究,確認是B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抗原,故現在通稱為B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Bsurfaceantigen,HBsAg)。
這一肝炎抗原的發現,使得全世界對肝病的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此後幾種與B型肝炎病毒有關的標記亦紛紛為人發現,已知的有核心抗原(hepatitisBcoreantigen,HBcAg)、e抗原(hepatitisBeantigen,HBeAg)及相對的抗體。
這些抗原抗體的出現,使醫學家開始重新對肝炎、肝硬化及肝癌加以研究,至今短短十五年間,全世界的研究論文如雨後春筍,而台灣地區的肝炎感染及肝癌盛行情形也開始受到全世界醫學界的重視。
引起肝炎的因素很多,有病毒、細菌、藥物、酒精、寄生蟲等多種。
病毒中主要的是所謂的肝炎病毒,目前已知者有A型、B型及非A非B(或C)型病毒。
由國內外專家在台灣地區的研究中,已確知B型肝炎病毒是引起台灣地區急慢性肝炎、肝硬化或肝癌的主要罪魁禍首。
台灣地區B型肝炎病毒的感染率究竟有多少?
感染途徑如何?
肝炎、肝硬化與肝癌間之關連如何?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http:
//163.14.136.54/science/content/1981/00030135/0004.htm
B型肝炎病毒在台灣地區的流行現況
1970年,布侖伯格又報告了澳洲抗原(亦即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在世界各地正常人口中的地理分布情形。
台灣竟幾乎高居世界之冠(13%),也就是100個正常人口中,有13人體內攜帶有B型肝炎病毒,同研究中的其他地區感染率皆相當低。
1975年玆穆斯(W.Szmuness)的流行報告亦同。
布侖伯格的報告是有關台灣B型肝炎病毒感染流行的首次研究報告,台灣B型肝炎的盛行方才廣受重視。
1971年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的M.J.Tong與榮民總醫院合作,對943個正常的中國人及55個肝癌病人檢查B型肝炎表面抗原,其陽性率分別為14.6%及80%,再度證實了正常中國人B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盛行。
這一篇報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肝癌病人合併出現陽性抗原的比率特高,達80%,遠比一般常人為高,使人聯想到B型肝炎病毒感染與肝癌間是否有密切的關係存在,當時提出報告時頗令醫學界驚異與難信。
同年台大醫學院的施炳麟及宋瑞樓等醫師亦有類似之發現。
http:
//163.14.136.54/science/content/1981/00030135/0004.htm
畢斯里炫風
1968年畢斯里(受僱於華盛頓大學預防醫學研究所)到台灣來調查德國麻疹的流行及疫苗注射情況。
他當時在想,要在台灣研究傳染病,該選擇哪一種?
1960年代澳洲抗原已初步證明和肝炎有關,公衛調查又顯示台灣澳洲抗原帶原率偏高,經特意蒐集相關資料後,發現肝癌在台灣的確很普遍。
心中因此產生疑惑:
台灣澳洲抗原感染率為何如此高?
肝癌和它到底有無關係?
畢斯里已瞄準B型肝炎之研究。
結束四個月的短期研究返回美國後進而認真蒐集B型肝炎最新研究資料(楊&羅,1999)。
1960年代末。
病毒性肝炎已被區分為傳染性肝炎及血清性肝炎,表示已知道肝炎可以透過血液來傳染。
由於國人喜歡打針,ㄧ度懷疑打針是肝炎感染猖狂之原因,但畢斯里卻懷疑打針是近代文明,不可能短期間牢牢札根於一個族群中?
因而提出傳染途經可能為母親和嬰兒之間的垂直感染之假設,然後ㄧ代傳ㄧ代留存於族群中。
1972年他再度前來台灣研究B型肝炎(楊&羅,1999)。
由1972年十二月到次年十一月,經由檢測及追蹤嬰兒的血液後,畢斯里證實由母親直接把B型肝炎傳染給嬰兒的垂直感染在台灣非常盛行,同時在探討垂直感染的相關研究中,亦發現垂直感染途徑非母乳,也非子宮內感染。
他提出「生產過程中」假說:
大部分帶原孕婦的嬰兒都是在生產時感染。
此假說因而暗示B型肝炎應該是可以預防的,可努力看是否能切斷母子垂直感染途徑(楊&羅,1999)。
其後畢斯里開始著手研究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的臨床試驗,ㄧ方面證明垂直感染的確是發生在生產階段,ㄧ方面基於公衛考量找出預防方法。
之後與榮總小兒科及婦產科合作進行雙盲實驗三年,結果並不理想。
在眾多學界大老鼓勵下開始計畫第二次臨床試驗,但卻被榮總拒絕。
轉而與婦幼衛生中心(謝豐舟)合作第二次「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預防垂直感染臨床試驗」,結果發現注射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等於是透過被動免疫來對抗感染,新生兒在受到現成抗體保護下,有機會自己產生抗體,且劑量愈多,對抗肝炎機會愈大(楊&羅,1999)。
疫苗風波
B型肝炎疫苗史的發展
1968年布倫伯格在『自然』期刊發表一篇論文指出,澳洲抗原不含核酸,可以純化作為疫苗。
1969年布倫伯格利用帶原者血液所分離出之抗原,在美國申請B型肝炎疫苗專利,1971取得專利,在費城與墨克藥廠合作進行血漿疫苗試驗。
之後十年於法國美國針對高危險群如醫護人員、同性戀男及B型肝炎盛行地非洲塞內加爾進行臨床試驗,於初步分析結果證明有效後,於1980年著手準備在台灣大台北地區進行墨克藥廠B型肝炎疫苗之兒童組臨床試驗。
當時的台灣尚未訂定臨床醫學試驗法規,畢斯里便以口頭方式,取得相關單位同意,然後再以臨床試驗藥劑名義進口疫苗。
初步試驗對象為幼稚園四至六歲小孩,分發注射說明書給家長,要家長決定是否讓小孩參與。
後來引起媒體報導指責畢斯里拿台灣小孩當天竺鼠,亦指責衛生署失職,讓洋人跑到台灣做「這種事情」。
當時衛生署長因而下令:
未拿到執照的疫苗不准用。
研究因而停擺。
透過衛生行政官員之友人牽線,畢斯里認識蔣彥士,因而透過蔣彥士認識李國鼎。
當時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之李國鼎很快就連絡行政院長孫運璿,有了行政院長的支持,疫苗臨床試驗的第一個障礙算是通過了。
此後衛生署對肝炎疫苗的注射態度轉為積極,但是當時媒體炒的很大,反對和贊成的意見各持ㄧ方。
榮總羅光瑞這邊對B型肝炎疫苗很有興趣,但當時全球有能力生產B型肝炎疫苗的廠商,只有法國巴斯德和美國默克,但都還沒有拿到銷售執照,廠商間彼此也互相較勁,某次會議上,羅光瑞碰到作疫苗實驗的法國學者莫帕斯,因此向他請教疫苗之相關事情,莫帕斯因而向羅光瑞承諾,想辦法叫巴斯德藥廠送肝炎疫苗樣本。
但此想法仍受到當時衛生署所屬肝炎防治委員會的反對,畢斯里、羅光瑞同時須承受媒體及同僚的壓力。
當時法國這種病人很少,因而至非洲地區收案,這點被當時認為「法國在落後民族身上做試驗,難道我們台灣人也跟非洲人ㄧ樣囉?
」畢斯里則被抨擊「洋人要拿中國人做試驗品」,當時大部分免疫學家反對、小兒科醫師反對,甚至台大很多肝病學家也反對(楊&羅,1999)。
1981年二月十六日,衛生署正式核准墨克藥廠進行B型肝炎幼兒臨床試驗。
又掀起一股激辯,反對理由包括接受過嚴謹科學訓練之學者,因了解免疫學上的潛在危險,故對於取自人體血清疫苗極不放心,加上當時愛滋病異軍突起。
更嚇壞ㄧ般學者。
除疫苗安全性外,另一被批評的是臨床試驗對象的年齡問題;廖運範認為試驗目的在於解決肝炎問題,台灣肝炎問題在新生兒,若阻斷新生兒感染,其餘問題即可解決,因此他認為試驗ㄧ至六歲健康幼兒是不適當的,應該選擇高危險群之新生兒。
但反對者認為如此做違反醫學倫理,根據規定,疫苗試驗順序應為大人殘障者,然後才小孩,逐漸降低年齡。
後來因廖運範依然堅持:
台灣疫苗臨床試驗要不從大人做起,要不從高危險性新生兒,他因此被人誤以為是「反對疫苗」。
此外,另一種反對理由則牽涉到民族主義:
怎麼可以打台灣小孩子?
但蘇益仁認為B型肝炎垂直感染是台灣很嚴重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怎麼可能讓美國小孩先做試驗,證明沒問題後,再拿給台灣檢便宜,我們須訂定一套周延的疫苗試驗法規,以便有所依循。
此主張與監察委員不謀而合,因而展開調查,最後要求衛生署應該嚴格要求臨床試驗主持人防止受試者發生嚴重副作用,也因此,醫政處開始草擬台灣自己臨床試驗規範,使我國在臨床醫學研究上跨出重要一步。
B型肝炎臨床試驗部分後來是等到它們拿到本國銷售執照才進行,亦即通過三期人體臨床試驗,動物實驗、人體免疫力試驗、與人體保護效益試驗(楊&羅,1999)。
1980年,奉行政院長孫運璿之命,李國鼎大力邀月當時在WHO任職的許子秋擔任衛生署長。
原本婦產科醫師後改走公共衛生的他,全力推動B型肝炎疫苗。
1981年行政院核准通過「肝炎防治計劃」,鑒於B型肝炎疫苗紛爭不斷,李國鼎想出典子舉辦一場國際肝炎會議,將國際最有權威之肝炎學者ㄧ網打盡,集邀台北,在肝炎權威學者一致認為B型肝炎臨床試驗值得在台灣做的聲音下,終將台灣B型肝炎疫苗施打試驗的紛爭告一段落(楊&羅,1999)。
高危險新生兒臨床實驗只是肝炎防治計劃之ㄧ部份,下ㄧ目標則是推動B型肝炎預防注射。
B型肝炎預防注射
1983年8月:
行政院通過科學技術發展方案,正式把肝炎防治列入重點科技,內容分為六大項:
(一)衛生教育
(二)肝炎研究(三)推動使用拋棄式注射針管,加強檢驗預防水平感染(四)發展檢驗試劑及檢驗品管(五)疫苗生產供應(六)成立肝炎患者資訊中心。
1983年11月:
奉院核定B型肝炎預防注射十年實施計畫
1984年開始自高危險群新生兒開始實施B型肝炎疫苗注射
1985年開辦民眾自費接種
1986年於台北市試辦幼稚園學童自費接種
1987年擴大免費施打對象至所有新生兒、未感染醫護人員及全面推動學齡前幼兒自費接種
1990年學齡前幼兒及國小新生納入免費接種對象
1992年推動大專青年、成人自費接種
1998年推動警消外勤人員自費接種
http:
//203.65.72.7/WebSite/%E9%A0%90%E9%98%B2%E6%8E%A5%E7%A8%AE/%E9%A0%90%E9%98%B2%E6%8E%A5%E7%A8%AE%E6%88%90%E6%95%88/%E5%8F%B0%E7%81%A3%E5%9C%B0%E5%8D%80%E9%A0%90%E9%98%B2%E6%8E%A5%E7%A8%AE%E5%8F%B2.htm
B型肝炎疫苗注射的成就及影響
台灣自從1984年七月開始針對B型肝炎帶原者母親所生嬰兒施打疫苗,更漸次擴及到高中,大學,到目前為止已有相當好的效果;根據衛生署針對全台灣六歲初入學兒童抽血分析顯示:
B型肝炎帶原率已經從1989年的10.5%降至1993年的1.7%;另外台大張美惠教授的調查更顯示孩童肝癌的盛行率已經從疫苗注射前的每十萬人口0.52,下降到每十萬人口0.13,相信這樣的成效在不久的將來應該會漸次及於青少年乃至於成年人,使國人肝癌的盛行率逐漸下降。
http:
//www2.cch.org.tw/GI/%E8%A1%9B%E6%95%99%E8%B3%87%E6%96%99/%E8%98%87%E7%B6%AD%E6%96%87-B%E5%9E%8B%E5%8F%8AC%E5%9E%8B%E8%82%9D%E7%82%8E%E4%B9%8B%E6%B2%BB%E7%99%82%E7%8F%BE%E6%B3%81.htm
B型肝炎疫苗歷史之省思
醫療政策與政治人物
如果說肝炎防治政策是台灣公共衛生史上的大勝利,那麼除了學者專家的努力之外,當時的政治體制與政治人物也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如果換作今日台灣的政治環境,「恐怕五個李國鼎也沒有用,」白壽雄感嘆。
雖然威權體制不是現代人歡迎的政治體制,但是不可否認,它有利於政府政策的推動,尤其是牽涉高度專業領域的政策。
「公共衛生政策常帶有濃厚的專業色彩,而它本身也是一種專制。
只不過我們認為它有科學根據,所以就認為自己站得住腳,」前衛生署防疫處處長張鴻仁以衛生行政人員的經驗來解釋:
「但是如果從民主角度來看,即使你有科學根據,也並不代表就擁有正當的理由。
」
或許,許多人認為因為政治落後促成肝炎防治政策成功,讓台灣意外地成為世界的領先者,但作者認為當時的政治環境不只是威權體制所影響,其應該還有更重要的因素- 擁有有理想、有風骨、肯做事的政治人物與官員。
當時的政治體制固然有影響,但政治人物與官員的影響更深遠。
例如,民國七十年二月十六日,衛生署正式核准默克藥廠進行 B型肝炎幼兒臨床試驗時,曾引起一場爭議。
當時這場紛擾也驚動了柏台大人,派出黃榮爵和尤清兩名監察委員,出面調查整個疫苗事件的始末。
兩名監委查完後,並沒有在情緒性的爭論上打轉,而是很扼要地切入問題核心。
他們告訴衛生署:
你們應該要根據赫爾辛基規定的臨床實驗精神去做,而且衛生署也應該要有自己的臨床實驗規範。
另外,他們也建議:
不應該拿健康的幼稚園小朋友做試驗,而是應該要拿帶原者小孩。
此外,衛生署也應該嚴格要求臨床實驗主持人防止受試者發生嚴重副作用。
類似這樣合理、理性的政治決定似乎比較難在今日台灣的政治環境中看到。
從威權體制走到民主體制,理論上我們應該擁有更多參與、討論的空間,但是這樣的機制卻在惡質化的政治環境中被犧牲了。
每當醫療政策發生爭議時,立法院一定是一片責怪聲,並在事實未調查清楚前就要求某些官員下台以示負責,監察院也在政治角力與利益糾葛中草草做出決議及懲罰,而這些決議與懲罰可能無法反映問題之癥結,也無法解決問題。
同樣地,在醫療政策的制訂上也是如此,政治人物擁有愈來愈大的權力,卻不用負擔責任。
目前台灣科技發展經費大多掌握在非專業政治人物手中,卻是不爭的事實。
曾幾何時,下決策不再需要專業知識,而已定案的決策也可朝令夕改,「知識即權力」,在台灣早已經退變成「權力即知識」。
許金川舉了一個荒謬絕倫的例子。
幾年前,衛生署本來有一個肝癌篩檢計畫,可是案子到了立法院,有立委說:
中醫很重要,為什麼不去研究中醫?
又有一個立委說:
喝尿現在很重要,為什麼不去研究喝尿?
「結果,錢就這樣被拿光了,而那個計畫也就停了,」許金川忿忿地說道。
政治人物,尤其是民意代表,不需要再為自己的發言或決策負責,無論後果為何都是由全民來共同負擔。
這才是醫療政策碰到政治人物最大的困難。
如果政治人物願意針對政策方向、內容做討論與辯論,才是真正走入民主時代。
然而,目前台灣僅是空有民主之外像,官員與民意代表之作為並不真正以人民之利益為出發點。
因此,任一政策的產生與制訂,其背後可能隱含著許多的政治角力與利益交換。
而這樣的風氣是因為我們的姑息、放任所營造出來的。
希望找回真正做事的年代,或許需要的不是威權,而是嚴謹的態度與耿介的風骨。
http:
//www2.mmh.org.tw/gi/others/amoeba01.htm
醫界與媒體
現代人幾乎是無法避免傳播媒體的介入,尤其是對於專業知識的傳播。
在《肝炎聖戰》中曾經提到媒體的報導:
「美國人拿台灣小孩當實驗品?
」
「台灣小孩是天竺鼠嗎?
」
一個個觸目驚心的標題出現在各大報紙頭版,矛頭都指向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的畢思理小組。
輿論炒響之後,各界批評聲浪也接續湧至,一波接一波地,把台灣社會搞得熱騰騰。
一時之間,原本沒沒無聞的「B型肝炎疫苗」忽然走紅起來;大家都在問:
B型肝炎疫苗是什麼東西?
那些美國人到底在搞什麼鬼?
為什麼有學者說安全,也有學者說不安全?
誰說的才準?
在醫藥新聞裡,許多發生爭議的問題是涉及發展中的科學,本身即充滿不確定性。
所以,如何在不確定的科學中做平衡報導是相當不容易的事,好像不應該只是陳述正反兩方意見而已,整個事件的起始與發展、爭議的關鍵、依據的理論,甚至背後的政治角力,媒體工作者如果能追究清楚,或許即使是發展中的科學問題,也可以透過公眾的辯論與思考,得到更好的解決方式或共識,而不是讓更多的政治角力、權力介入,模糊爭議的焦點,使問題複雜化。
正如《肝炎聖戰》中所提到的另一件事: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十日,省議員張溫鷹嚴厲質詢省府衛生處長林克紹:
敢不敢百分之百保證血漿疫苗的安全性?
而事實上,生物製劑根本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安全。
林克紹只好據實答稱:
不敢保證。
這些質詢內容透過各種平面、電子媒體,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呈現出諸多負面印象:
「血漿疫苗是危險又落伍的」、「保生公司是國民黨獨佔企業」、「主張施打血漿疫苗的學者專家都是不顧國民福祉的惡人」。
這會兒,不只保生公司的股東,連推動 B型肝炎防治的官員和學者專家,也全都被罵進去了。
曾為了落實肝炎疫苗注射計畫而全省奔波的許須美,很難接受這樣的指控:
「他們罵說你們這些壞人哪,把我們全都罵進去了。
那時壓力真的很大,每天報紙都在報導。
」
或許媒體工作者應該對於這類爭議性大、影響力深遠的醫療政策或醫藥新聞做更深入的討論與報導,開創更多公眾參與辯論的空間與機會。
http:
//www2.mmh.org.tw/gi/others/amoeba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