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法律的一些问题.docx
《学习法律的一些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学习法律的一些问题.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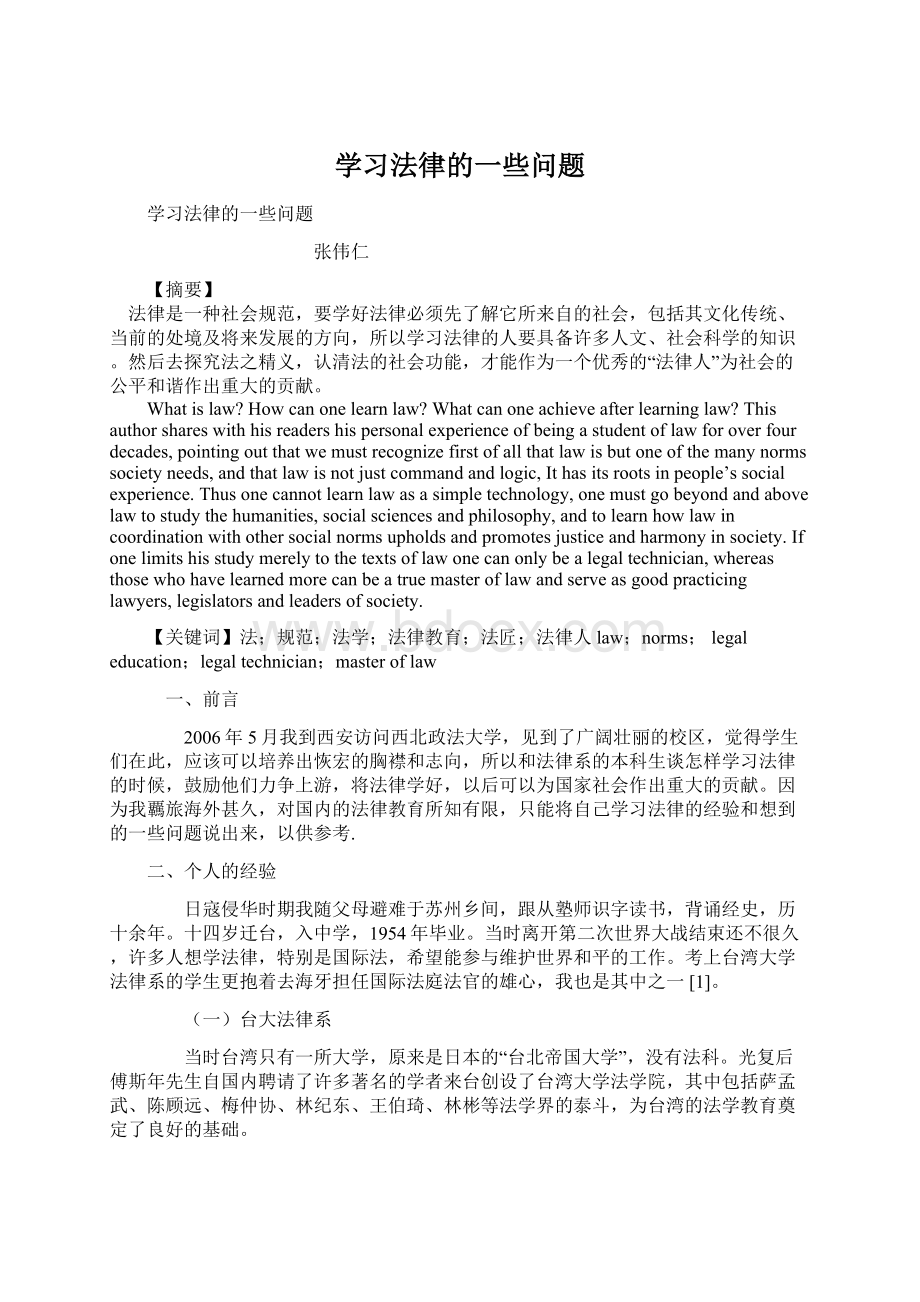
学习法律的一些问题
学习法律的一些问题
张伟仁
【摘要】
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要学好法律必须先了解它所来自的社会,包括其文化传统、当前的处境及将来发展的方向,所以学习法律的人要具备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然后去探究法之精义,认清法的社会功能,才能作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为社会的公平和谐作出重大的贡献。
Whatislaw?
Howcanonelearnlaw?
Whatcanoneachieveafterlearninglaw?
Thisauthorshareswithhisreadershispersonalexperienceofbeingastudentoflawforoverfourdecades,pointingoutthatwemustrecognizefirstofallthatlawisbutoneofthemanynormssocietyneeds,andthatlawisnotjustcommandandlogic,Ithasitsrootsinpeople’ssocialexperience.Thusonecannotlearnlawasasimpletechnology,onemustgobeyondandabovelawtostudythehumanities,socialsciencesandphilosophy,andtolearnhowlawincoordinationwithothersocialnormsupholdsandpromotesjusticeandharmonyinsociety.Ifonelimitshisstudymerelytothetextsoflawonecanonlybealegaltechnician,whereasthosewhohavelearnedmorecanbeatruemasteroflawandserveasgoodpracticinglawyers,legislatorsandleadersofsociety.
【关键词】法;规范;法学;法律教育;法匠;法律人law;norms;legaleducation;legaltechnician;masteroflaw
一、前言
2006年5月我到西安访问西北政法大学,见到了广阔壮丽的校区,觉得学生们在此,应该可以培养出恢宏的胸襟和志向,所以和法律系的本科生谈怎样学习法律的时候,鼓励他们力争上游,将法律学好,以后可以为国家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因为我覊旅海外甚久,对国内的法律教育所知有限,只能将自己学习法律的经验和想到的一些问题说出来,以供参考.
二、个人的经验
日寇侵华时期我随父母避难于苏州乡间,跟从塾师识字读书,背诵经史,历十余年。
十四岁迁台,入中学,1954年毕业。
当时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很久,许多人想学法律,特别是国际法,希望能参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工作。
考上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更抱着去海牙担任国际法庭法官的雄心,我也是其中之一[1]。
(一)台大法律系
当时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原来是日本的“台北帝国大学”,没有法科。
光复后傅斯年先生自国内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来台创设了台湾大学法学院,其中包括萨孟武、陈顾远、梅仲协、林纪东、王伯琦、林彬等法学界的泰斗,为台湾的法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台大法律系开设的绝大多数是狭义的法律课目,如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等。
但是一二年级的学生还须修习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理则学、国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及外语,大约与现在国内的情形相似。
一般学生的注意之点当然在法律课程,成日捧着“六法全书”和各科目的教材、书刊,像绕口令似的将许多法律术语搬弄着,觉得很是新鲜有趣。
但是稍久之后,我发现所学的东西似乎与现实社会没有很大的关系。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显然有另外一套准则在指导他们的行为,解决他们的问题,很少有人谈法律,用法律。
当我提到法律里的若干规定如“夫妻分别财产制”,亲友邻居们听了都觉得匪夷所思。
当时社会比较安定,重大的刑案较少。
人们有了民事的纠纷大多经由亲邻和社区内的公正人士调停,很少诉诸于法,几乎没有听说闹到法院去的事。
既然如此,法律究竟有多少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想起“思而不学则殆”这话,便决定去找些书来看。
听说有一种学问叫做“法律社会学”,但是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是一门比较新兴的东西,台大图书馆还没有这方面的书刊,只有一些日文翻译的Weber,Durkheim等人讨论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著作。
我因曾经眼见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而拒学日文,无法阅读那些书,所以对于为什么法律会与社会现实脱节这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
另外使我对于当时台大的法学教学感到困惑的有两点:
一是那时流行的“注释法学方法”将法律条文一词一句地加以注释。
虽然这是研读任何专业性文书资料必须做的第一步基本工作,但是这一步只能使人懂得法律的文义,而无法使人明白为什么法律应该有这样的规定,尤其是在法律的规定似乎与实际社会生活脱节的情形,这种研讨文义的工作就更少实益了。
幸好在三、四年级时我觉得这种注释已没有太大必要,但那时候又有了另一个困惑:
老师们对于法律的条文往往引用了许多外国的学说加以阐述,甲乙丙丁诸说纷纭,但与中国的国情常常风马牛不相及。
其说愈精,愈显得那些条文不是为中国而制订的。
这一困惑在四年级时学习中西法史和中西法理之后更为加深了。
许多极为博学的老师们如陈顾远、萨孟武等对此也有很多感慨。
(二)台大政研所
我的法律系毕业论文写的是一些关于国际条约的问题,内容已记不清楚,因为在三、四年级时我的兴趣已不在狭义的法律了,在应付课业的要求之外,化了比较多的时间找了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书来看。
当时台湾的出版业已渐复苏,重印了许多旧书,也发行了一些新着。
我读到了不少在台学者的著作(当时国内学者的作品在台湾都列为禁书),很喜欢看萨孟武老师的书,特别是若干观点新颖,分析精妙的,如《西游记与中国政治》,使我极为钦佩他对中国文化通盘、深入的悟解,所以1958年毕业后考进了台大政治研究所,主修中国和西方的政治思想史。
入学不久便经萨老师的介绍认识了文学院的许多老师,听了不少历史系和哲学系的课,其中以毛子水老师的经学、沈刚伯老师的史学和殷海光老师的理则学给我的启迪最深。
殷老师有许多西方哲学的书,很慷慨地借给学生们看,我也借阅了不少[2],最喜欢的是罗素(BertrandRussell)的著作,看了六七本[3],后来就以他的政治思想为题写了我的硕士论文,内容十分肤浅,回想起来仍汗颜不已。
但在这段时间里的确读了不少书,虽然一知半解,但对法律以外的知识增加了一些,好像为一间密室打开了一些窗子,使我看到了比较广阔的世界。
(三)南卫理大学
1962年研究所毕业并服过兵役后,我考取了Fulbright奖学金,被派到美国德州的南卫理大学(SouthernMethodistUniversity)学“比较法”。
此校不大,也没有什么名气,而且并没有开设什么特别的比较法课程。
我和美国本地的学生一样,修习美国宪法、刑法、契约法、侵权行为法等课,所以起初不免有些失望,后来才发现此校有许多优点,主要的是学生不多,师生的关系比较密切,校方对于像我那样来自三十个不同国家的外籍学生照顾得很周到,所以大约在一年之后,我们的英语都大有进步,对美国的社会也增加了许多认识。
在学业上则有二项收获,一是学得了不少美国法,自然地与本国法作比较看出两方面的若干问题,二是因为该校所用的普通法系教学法与国内用的大陆法系教学法差异极大(大致而言,前者自判例出发,分析许多案件的判决要旨,找出一个原则,供给司法者处理同类案件时作为参考;后者自原则出发,依据逻辑推出可以适用于具体案件的细则作为判决的依据),使我学会了对归纳和演绎两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四)耶鲁
1964年在南卫理大学取得比较法学硕士后,觉得所获有限,便申请延长居留继续就学,得到了耶鲁和哈佛二校的入学许可。
由于两个原因我选择了耶鲁:
一则因为HaroldLasswell在那里。
我在台湾时曾经读过一些他的著作,对于他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去观察、分析法律的方法很感兴趣。
二则因为我仍念念不忘要去海牙,应该学国际法,而当时美国一位著名的国际法学者MyresMacDougal也在耶鲁执教。
在耶鲁两年修习了不少为研究生开的课程,其中最为特殊的便是这两位老师的国际法及法理学。
由于他们认为法律是一种具有价值导向、政策导向的规范,所以他们的学说被称为“valueoriented”或“policyoriented”的jurisprudence,也称为“policyscience”。
这种学说指出法律并非一种中性的、纯理性的规范,对我的帮助不小,因为在台大时虽然已经知道学习法律还应该注意它与社会的关系,但一直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产物,有它自己的内在理则和外在的目的,几乎可以说有它自己的生命,可以独立存在,对于与它不合的社会情事可以加以匡正,而不是仅仅反应社会现实而已。
这种想法当然是受了老师们的影响,而他们似乎是受了注释法学派和相近的“形式法学”(legalformalism)及“实定法学”(legalpositivism)的影响。
记得当时曾读过一本与这种想法相关的重要著作:
HansKelsen的PureTheoryofLaw,但没有看懂。
耶鲁的policyscience似乎使我茅塞顿开,见到了法律的非理性的一面。
然而这种看法当时并没有在美国普遍流行。
哈佛法学院似乎仍有不少教授采取比较传统的态度,重视法律的内在理则。
所以耶鲁的学生常常说:
“WestartatwhereHarvardstops”,很引以自傲。
(五)哈佛
虽然在耶鲁学到不少法理,我的法学硕士论文仍在国际法领域,探讨一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问题。
1966年毕业,又得了个硕士学位,旋即进入了国际法的博士班。
开学前的暑假里我去波士顿看在哈佛读国际法的台大同窗丘宏达。
他介绍我认识了JeromeA.Cohen教授。
那时Cohen才开始研究中国法,觉得要了解当今中国的法律,必须对传统的中国法制有一些认识。
他可以看中国的白话文,但不能读传统法学资料所用的文言文,须要有人帮助。
丘宏达推荐了我,说我的中文比较好。
Cohen觉得很奇怪,因为一个美国人不会说另一个美国人英文比较好。
丘宏达花了一点时间才向他解释清楚因为我幼时读私塾,熟悉古文经典之故。
Cohen此后每次介绍我时都提起此事,认为很有趣。
暑假三个多月Cohen和我常常在一起读大清律例和相关的资料,除了读通文义外,他常常会问为什么会有某种的规定或理论。
对于他的许多问题,我都瞠目不知所对,感到十分惭愧。
另一件使我惭愧的事发生于DerkBodde的一次演讲之时。
Bodde是宾州大学的教授,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享有盛名。
那年暑假到哈佛来演讲“ChineseTraditionalLegalSystem”,谈清代的司法。
讲到“勾决”,他说那是皇帝用硃笔在死罪人犯的名单上画一个大圈,名字被硃笔扫到之人便该处死[4]。
讲到这里,他问道:
清代刑事程序从传讯、初审、覆审,一步一步十分严密,为什么到了最后竟由皇帝如儿戏似的决定了罪犯的生死?
在座的听众约四五十人,面面相觑,其中有些认识我的,转头看我,因为我是听众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然而我也答不上来,被大家这么一看,使我涨红了脸,不知所措。
Bodde接着又问中国人真是神秘莫测(inscrutable)吗[5]?
然后又自行作了一番解释,似乎说公平正确的判决是极为难得的,最后的决定常常含有一些偶然的成分在内。
这话听来很是玄妙,但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
我则羞惭得无地自容,不仅因为答不出他的问题,更因为对于他所说的清代刑事程序也不甚了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如此膧朦,贻笑于外邦,实在可耻!
由于上述两事,我发愤去探究中国传统法制,天天去哈佛燕京图书馆埋头苦读清律和有关的典籍,希望能尽快弥补自己的阙佚。
原来想到波士顿访友渡假的,结果却做了三个月的密集学习。
Cohen对我的努力印象苌睿栽谑罴俳崾拔饰乙灰粼诠鸺绦芯恐泄撤ㄖ啤N宜滴胰韵胙Ч史āK笛Ч史ǖ娜撕芏啵弥泄撤ㄖ频娜思伲绻芙獠糠种泄幕パ镉谑溃热ズQ郎罄砑父霭讣墓毕状蟮枚唷K庑┗凹由衔乙蛭杂谥泄澄幕奈拗械角苛业男卟眩刮掖鹩α怂:
罄垂鸱ㄑг旱母痹撼avidSmith与博士生谈话时对我说:
“啊!
你终于来了!
”我听了觉得莫名其妙,愣了一会才想起来,当年决定去耶鲁时忘了写信辞谢哈佛的入学许可,很是失礼。
哈佛大约也很少这样获得它的入学许可而不去入学的先例,但是显然还保存着我的记录,因为哈佛与耶鲁一直在竞争,所以Smith说那句话,大约有点高兴吧。
在哈佛时一方面继续研读中国传统法制的典章,将一部分大清律例和成案译成英文给Cohen作为教材,并和他一起上堂为学生解释;一方面修习了若干课目,包括SamuelThorne的英国法史、ArthurvonMehren的欧洲法史、LonFuller的法理学、JohnFairbank的东亚文化史等。
Thorne花了一个多学期讲英国的feudalsystem,vonMehren也对欧陆诸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作了精要的分析。
显然他们都认为要了解一国的法制必须深入地了解其背景。
Fairbank以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文化,并将它与周围诸国的文化比较,显出我以前没有见到的许多中国文化的长处和缺点。
上Fuller的课获益最多,因为那时他才结束和英国牛津大学的法理学教授HerbertLionelAdolphusHart反复辩论关于自然法与实定法之间的种种问题。
他们的文章使我对西方当时这两个重要的法学派增加了一些认识[6]。
此外我也看了若干西方法理发展史的书,对于各学派如何形成和演变有了较深的了解。
(六)中研院史语所
1967年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许倬云先生到哈佛来,听说我在学中国法制史,告诉我史语所藏有清代的“三法司”档案,是研究清代法制的原始资料。
我听了十分高兴,便经他的推荐于次年冬返台进入了史语所。
返台后去拜访了几位老师,他们都欢迎我回来工作,因为当时许多出国读书的人都千方百计设法留在国外,回国的人极少。
他们都对我讲述了不少做人做事的道理,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林纪东老师的话。
那天我才在他研究室坐定,他劈头问道:
你在美国学到了些什么?
对于中国有什么用吗?
我一时答不出来,他便提到许多在国外留学三五年,对于专修的科目只学得了一点皮毛,对于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所知更少,但在回国之后便在学校里及社会上卖弄那一点点洋货,招摇撞骗,误人误国,希望我千万不可蹈此覆辙,要好好地将所学的一点东西,放在自己的社会文化里,仔细比较研究,引发出一些自己的见解[7]。
他这番话犹如当头棒喝,使我的骄妄之气消减不少;又如醍醐灌顶,让我见到了一条此后该走的路。
史语所有一个极好的研究工作的环境。
初到之时,所长李济先生和历史组主任陈槃先生都教我多读书、多思考,不要急急乎写作、发表。
我当时已很清楚自己的浅薄,知道要花很多时间去札根,听了他们的话,便如服了一颗定心丸,就放心地去各个图书馆寻找有关中国传统法制的书刊来看,随手将心得写在卡片上。
后经所长屈万里先生的鼓励录出了2352种书籍的基本资料,出版了《中国法制史书目》三册[8]。
在此期间我也开始看“三法司档案”。
据前辈李光涛先生说那是原存于清代内阁大库的文件,清末被盗卖给纸厂去做“还魂纸”,经当时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筹款买还,共八千麻袋,经初步整理后,因日寇入侵,将比较完整的三十一万件随史语所播迁至四川,战后又运到台湾,由李光涛先生继续整理。
在他的指导下我选出了若干与清代法制有关的文件,开始了我的研究工作。
1980年后我又接下了通盘整理那三十一万件档案的担子,将残破杂乱的文件逐渐修复、分类、摘要、保存,前后花了二十多年[9]。
其间还帮助台大法律系戴炎辉老师整理了一些台湾的淡新档案,又协助台湾文献馆的王世庆先生搜集了三千六百多件台湾公私藏自明清到日据时代的古文书[10]。
史语所的“三法司档案”其实不只是“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文书,而包括了京师各衙门及地方大员呈给皇帝的题本、衙门间的移会和皇帝的谕旨等等资料,内容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各方面,与法制有关的大多是处理重大刑案的纪录。
由于它们残缺太甚,无法用来通盘地做各种实体法的研究,但是因为许多文件都详细陈述了案件如何发生以及地方、省、中央各级官司和皇帝处理该案的措施,所以是研究程序法的极佳素材[11]。
这一发现使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程序法的研究比较重要,理由有二:
1.虽然实体法规定了权利、义务和赏罚,但必须有程序法才能使这些规定付诸实现,而且妥善的程序还可以保障人们基本的权益,使其免于不当的实体法的伤害[12];2.实体法可以说只是静态的规定,程序法则规定当事人、律师、检察官、司法官之间的互动,所以研究程序法有助于对整个司法制度的组织和运作,取得一种通盘的认识。
基于这种看法,我分析了数千个史语所保存的文件,探究清代民刑案件当事人如何呈诉、上控;基层司法人员(州县官、幕友、代书、书吏、衙役、保甲等)如何受词、勘查、检验、传拘⑸罄怼⒛馀小⒊氏辏恢胁闳嗽保ㄖ⒌涝保┤绾闻怠⑸笞皇〖度嗽保ǚ尽Ⅳ尽⒆芏健⒀哺В┤绾胃采螅庾啵恍滩咳绾我樽铮蝗ㄋ尽⒕徘洹⑼豕蟪既绾胃春耍皇〖爸醒敕ㄋ救绾吻锷螅换实廴绾尉龆希绾喂淳鏊雷锶朔福桓髦中谭H绾沃葱械鹊任侍狻!
?
/p>
在这一个探究的过程中见到了许多以前没有人谈过的细节,例如“勾决”一事,档案中有不少题本对“勾”前的程序有详细的叙述[13],而“勾”这一动作并非皇帝以硃笔在死刑人犯名单上画一个大圈,而是将每个应予处死之人的姓名上个别地作一“勾”号[14],然后又在勾到本的首幅以硃笔写明“这所勾的某某某、某某某〔将被勾之名一一抄录出来〕著即处决,余著牢固监候”[15]。
这些步骤当然是为了确切防止误行勾决而设计的,十分谨慎细密,绝非儿戏。
看到了这些文书之后又想起Bodde的话,不禁哑然失笑。
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胡适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是许多西方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不能满足于这样谨慎的做法,而喜欢推论(extrapolate),从一个有据之点推到一些相关之点。
这样的做法可能流于过份,推论会变成臆想(speculation)甚至幻想(imagination),犹如盲人摸象,所得的结论不免贻笑大方。
除了找到这类细节问题的答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通盘探究清代法制的动、静两面之后,我突破了自清季至今的一种流行的(受了东西洋人及中国崇洋之人影响的)看法——清代,甚至整个中国传统的法制弊端重重,几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我发现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一片黑暗。
固然清代法制在设计上及实践中确有许多缺陷,但是其咎并不全在法制本身。
它的许多劣迹实系当时政治、经济、教育、种族、战乱等等外在因素造成的。
此外更引我注目的是:
在此恶劣的环境里仍有许多人,自书役、幕友、地方官吏以至中央大员,甚至几个皇帝,都曾在司法程序中努力寻求社会的公平和谐。
在清代许多档案、成案汇编及官员的判牍里特别可以看出他们的这种奋斗,可惜那些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法制的人似乎都无见于此。
基于研究清代法制档案的心得,我在1983年出版了《清代法制研究辑一:
盗案之初步处理及疏防文武之参劾》[16]。
原来的计划是继续写以下数辑,逐步将清代司法制度及实践仔细析述出来,后来因为两个目的,决定先写一本概论性的书:
一、描绘出一幅虽然不很精细,但是能呈显出清代法制轮廓的鸟瞰图,供给想要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法制的人作为参考,让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研究的问题在这图中处于那一个部位,以及它与其它问题的关系。
二、纠正人们由于无知而对中国传统法制的误解与偏见。
因为促使我研究中国传统法制的是Cohen和Bodde,此后又有许多欧美的朋友、学生提出无数相关的问题,为了回答他们并纠正他们的若干成见,我决定将此概论先用英文写出来,名之为StruggleforJusticeinLateImperialChina[17]。
我这么做,多少是为了一雪当时的羞惭,然而也可以算是对Cohen多年前劝我将中国法律文化播扬于世的一点小小的回应吧。
(七)教学、研究
自美回台之初,戴炎辉老师知道我要去中研院工作,问我要不要到台大兼课。
我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直到1980才开始去教中国法制史。
因为台湾的法制是民国成立后订立的,与传统的法制差异极著,一般学生对于以往某一朝代曾有某一法律兴趣不大,所以我决定将课程的重点放在传统的法律思想上,强调法条和制度虽然容易改订,新的法制很难使一般人的行为模式在短期内产生重大的变化。
行为模式是由传统思想塑造成的,要了解现代人的行为,尤其是涉及法制的行为,必须对传统的法律思想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基于此一想法,我选录了若干前人的法学著述作为教材,其中当然以先秦的比较多,因为那时正是思想最创始、最蓬勃的时期。
我发现除了《商君书》、《韩非子》等一般认为是法家的著作外,《诗经》、《书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论语》、《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书中也有许多比狭义的“法律思想”更宽广、高深的政法理论——例如社会上存在着许多规范,包括道德、礼俗、各种血缘、地域和职业团体的规章等等,为什么还要有“法”?
什么是“法”?
“法”与其它社会规范有什么区别,什么关系?
“法”来自何处?
如果它是人制订的,什么人可以有立法的权威?
谁有司法的权威?
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何在?
“法”有良窳吗?
如果“法”与其它规范发生冲突该怎么办?
如果立法者或司法者滥用其权威该怎么办?
这些都是极重要的法学(尤其是法史学和法理学)的问题。
它们又必然地与更基本的许多问题,如社会的起源、人性、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等等相关。
中国历代都有许多思想家加以思索,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但未必都用今人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因而一般人不易看出。
对我而言这个困难并不大,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我对西方的法史学和法理学略知一二,很熟悉上列的那些问题;二是我自幼诵读经史,当时对其内涵虽然一知半解,但是后来再读诸子之书,常常看到一段便想起同一书或其它书内相关之处,众端参观,互相比较,其意义便容易了解了。
总之,我觉得在那些著作里看到了许多前人似乎没有看到并讨论过的东西,很是高兴,就将那些资料录出,以上列那些问题为标题右苑掷啵喑闪艘徊拷滩模谔ù蠓上凳杂谩:
罄葱薅┕啻危⑷恳氤捎⑽模米髟诿拦鶸CLA、NYU、哈佛、康乃尔等校及法国法兰西学院(CollegedeFrance)讲述“ChineseLegalThought”的资料。
为了适应美国法学院流行的问答教学法(SocraticMethod),又在资料后加上了许多法理学的问题,促使学生去思考并在教材中去探索中国古代思想家对那些问题的答案。
1999-2000年在清华及北大授课时又将资料再整理一番,将问题译成中文。
2003年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的陈金全教授来信说我对那些资料的分类编排“富有新意”,问我是否可以由他加以注释后出版,以便学生阅读。
我最初的反应是那些资料的原著俱在,不必再灾加梨枣;但是想到如他所说现在的学生大多不易阅读古文,所以就同意了。
经过他多年的努力,那些资料终于以《先秦政法理论》为名,于2006年五月由北京人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