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隐私阿尔帕西诺深度访谈.docx
《绝对隐私阿尔帕西诺深度访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绝对隐私阿尔帕西诺深度访谈.docx(6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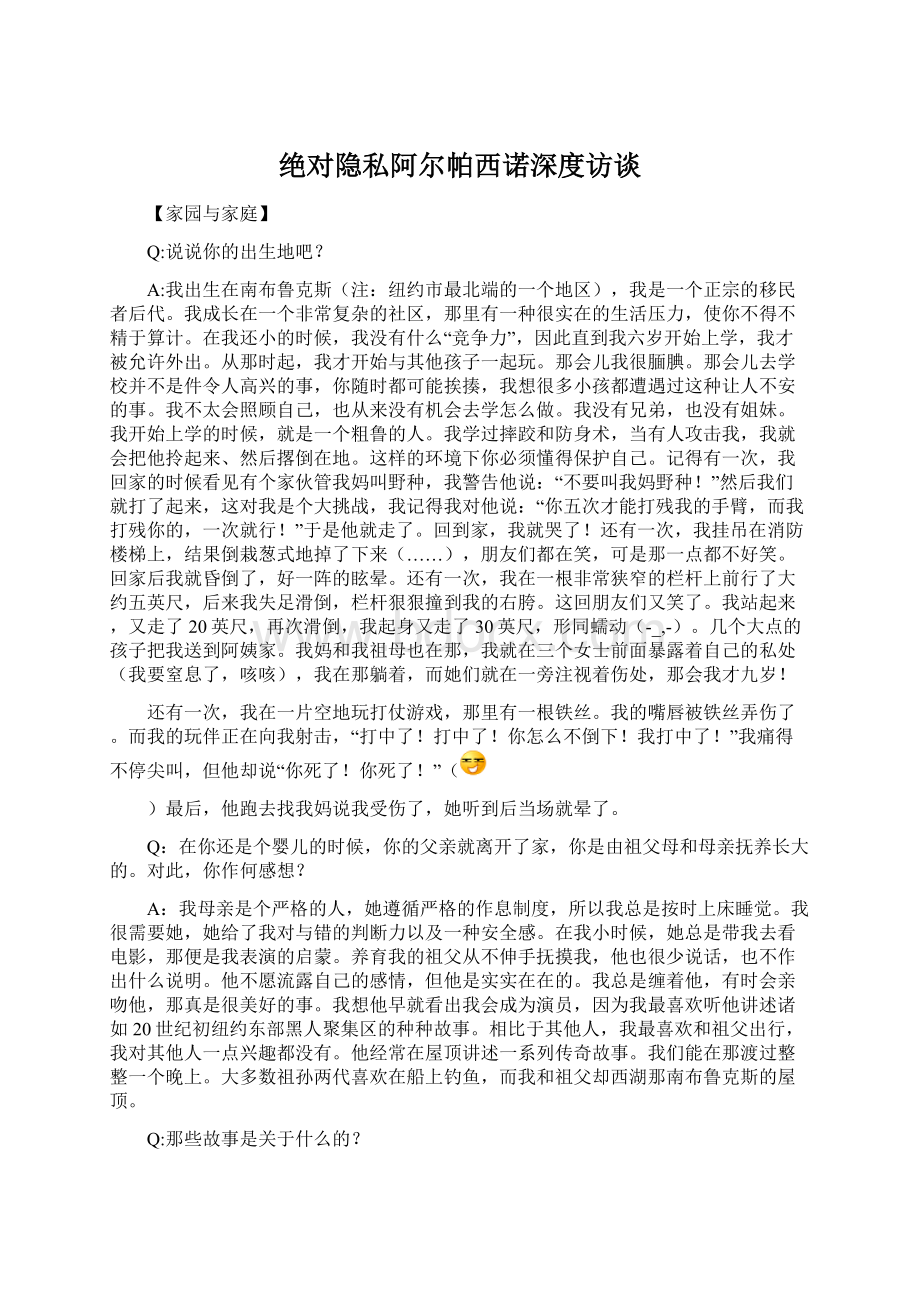
绝对隐私阿尔帕西诺深度访谈
【家园与家庭】
Q:
说说你的出生地吧?
A:
我出生在南布鲁克斯(注:
纽约市最北端的一个地区),我是一个正宗的移民者后代。
我成长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社区,那里有一种很实在的生活压力,使你不得不精于算计。
在我还小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竞争力”,因此直到我六岁开始上学,我才被允许外出。
从那时起,我才开始与其他孩子一起玩。
那会儿我很腼腆。
那会儿去学校并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你随时都可能挨揍,我想很多小孩都遭遇过这种让人不安的事。
我不太会照顾自己,也从来没有机会去学怎么做。
我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
我开始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粗鲁的人。
我学过摔跤和防身术,当有人攻击我,我就会把他拎起来、然后撂倒在地。
这样的环境下你必须懂得保护自己。
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看见有个家伙管我妈叫野种,我警告他说:
“不要叫我妈野种!
”然后我们就打了起来,这对我是个大挑战,我记得我对他说:
“你五次才能打残我的手臂,而我打残你的,一次就行!
”于是他就走了。
回到家,我就哭了!
还有一次,我挂吊在消防楼梯上,结果倒栽葱式地掉了下来(……),朋友们都在笑,可是那一点都不好笑。
回家后我就昏倒了,好一阵的眩晕。
还有一次,我在一根非常狭窄的栏杆上前行了大约五英尺,后来我失足滑倒,栏杆狠狠撞到我的右胯。
这回朋友们又笑了。
我站起来,又走了20英尺,再次滑倒,我起身又走了30英尺,形同蠕动(-_,-)。
几个大点的孩子把我送到阿姨家。
我妈和我祖母也在那,我就在三个女士前面暴露着自己的私处(我要窒息了,咳咳),我在那躺着,而她们就在一旁注视着伤处,那会我才九岁!
还有一次,我在一片空地玩打仗游戏,那里有一根铁丝。
我的嘴唇被铁丝弄伤了。
而我的玩伴正在向我射击,“打中了!
打中了!
你怎么不倒下!
我打中了!
”我痛得不停尖叫,但他却说“你死了!
你死了!
”(
)最后,他跑去找我妈说我受伤了,她听到后当场就晕了。
Q:
在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你的父亲就离开了家,你是由祖父母和母亲抚养长大的。
对此,你作何感想?
A:
我母亲是个严格的人,她遵循严格的作息制度,所以我总是按时上床睡觉。
我很需要她,她给了我对与错的判断力以及一种安全感。
在我小时候,她总是带我去看电影,那便是我表演的启蒙。
养育我的祖父从不伸手抚摸我,他也很少说话,也不作出什么说明。
他不愿流露自己的感情,但他是实实在在的。
我总是缠着他,有时会亲吻他,那真是很美好的事。
我想他早就看出我会成为演员,因为我最喜欢听他讲述诸如20世纪初纽约东部黑人聚集区的种种故事。
相比于其他人,我最喜欢和祖父出行,我对其他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经常在屋顶讲述一系列传奇故事。
我们能在那渡过整整一个晚上。
大多数祖孙两代喜欢在船上钓鱼,而我和祖父却西湖那南布鲁克斯的屋顶。
Q:
那些故事是关于什么的?
A:
他的移民经历、他的母亲诸如此类的故事。
在他四岁那年,他的母亲去世了。
他不得不辍学,到了九岁时他就开始干拉煤这样的工作了。
等我出生后,他每天下班回家都会和我玩一阵。
我还会请求他帮我寻找小玩具。
他总是一边抱怨个不停,一边深深地弯下腰,好像要钻进他的鞋里去,他总是能找到那些小玩具,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Q:
你说过他是你的榜样!
A:
我认为他是,没错。
我的祖父是一个榜样。
在他的生活中,任何工作都是快乐的。
因此当我长大之后,我对工作有一种特别的热忱,我做的事总是我渴望的。
Q:
在[伸张正义](1979)中有一场戏,你去看望由李·斯特拉斯堡演的祖父,你对他说:
“你关心我,你爱我,看你的儿子只是一堆狗屎。
”这不是跟你的生活经历特别接近?
A:
那不过是剧本而已。
不,当我扮演这个角色时我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想法。
有些人感受真实的能力很强,他们对诚实真挚有很强的鉴别力。
李·斯特拉斯堡如此,我的祖父也如此。
Q:
你觉得这句台词怎么样?
在真实生活中你的父亲就是一坨屎么?
A:
不,不。
我和他的关系属于并不亲密的那种,但是他一直都会来看我。
他会来拜访、探望、问候我。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和他呆过一段时间。
而有时我们也会四五年才能见一次面。
但是,他总是努力保持与我联系。
Q:
你母亲43岁那年去世时,你多大?
A:
我22岁。
我母亲的死是对我们全家的打击。
她是因为贫血症而住进医院的。
她忍受着我无法想象的痛苦。
一年后,我的祖父也去世了。
母亲的死应该是导致他去世的原因之一。
他是很强健的一个人。
他一生都没有得过病。
母亲的死显然让他变得脆弱了。
谈论这些事令人非常难过。
Q:
那是你跟母亲的关系如何?
A:
那段时间我们之间的确有一些沟通的困难。
生活不顺利的时候总是不幸的,特别是和你母亲的关系又不太好时。
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低潮的时期。
而她的去世对我更是一个打击,我变得更加脆弱。
Q:
那你一个人住了?
A:
我祖父死后,我就和别人合住了。
我每周四为报摊送一趟报纸。
那就是我当时的工作。
送报的路线让我经常路过百老汇和第48大街。
后来我的视力有点问题,医生帮我看了看,测量一下脉搏,然后告诉我一切正常,并建议我到贝尔福莱姆的门诊部再看看。
Q:
家人的离去有没有让你亲近你的父亲?
A:
没有,实际上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能跟他正常交流。
Q:
你回到过布鲁克斯的老社区吗?
A:
我怎么回去呢?
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那个社区已经消失,已经完结。
那个世界已经没了。
【学校与梦想】
Q:
你的学校生活怎么样?
你是否有过惹是生非的时候?
A:
有一段时间我的确是那样的。
Q:
你都做了什么?
A:
一些恶作剧。
我经常做些举止不当的行为,比如把老师的眼镜放在他的座位上,当老师坐下时,眼镜就被压坏了。
有时我在图书馆呆着,我把立着的书推到,让倒下的金属书发出巨大的声响。
如果我做得太频繁,就会有人把我撵出来。
我曾经被送到一个“留级班”,不过我并没有在那呆很长时间。
Q:
你有没有想过长大以后做什么?
A:
说真的,我想过当一名篮球运动员,但是在这方面我不够出色。
我并不清楚我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我只是有一股活力!
我还算是个快乐的孩子,虽然在学校我有点麻烦。
在我八年级的时候我的戏剧老师给我妈写了封信,让她多鼓励鼓励我!
我经常背诵柯勒律治的诗作《古舟子吟》。
我也经常在礼堂里阅读《圣经》。
在那,我第一次知道了马龙·白兰度这个名字。
在我表演的时候如果有人说:
“嘿!
那小子演得真像白兰度!
”并非怪事。
我那会儿也就12岁。
我觉着他们这么说是因为我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厌恶感,事实上我在每次演出这戏的确感到厌恶。
我真正的偶像是詹姆斯·迪恩。
是他的经历伴随我的成长。
我母亲喜欢他。
他有一种横扫一切的感染力。
[无因的反叛]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还记得那件红色夹克衫吗?
那会儿人手一件。
我爱这句台词:
“生活并不美好。
”
Q: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上了演艺高中?
A:
我去那里只是因为只有哪所高中愿意招收我。
我的成绩挺糟糕的。
我记得进了学校后我加入了西班牙语班,然后我就开始学西班牙语了。
Q:
但是你依旧学习表演?
A:
其实我并不是非常热衷于表演,它并没有让我特别兴奋。
如果还能再来一次从头选择的机会,也许我会干翻双筋斗或只是瘫坐在地板上。
我是用表演来反表演。
别人是过量吸毒我是过量表演。
那所学校传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技法。
那就是一整套技法和一连串动作,要我说感觉的话,那实在有点疯狂。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哪里颇有趣味等等,我对此感到非常厌倦。
有一回,我必须在课上表演一系列的行为,以展示当我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时的活动。
虽然我从来就没有过属于自己的屋子,我还是得把它演出来。
Q:
你住的屋子里会有多少人?
A:
一般而言,我们家就个人睡在三间房里。
我跟婶婶和舅舅他们家在一块。
为了这段表演,老师还找来我的母亲,并与她谈论这个事情。
我母亲认为表演时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干的,而我应该找一份工作。
为了赚钱养活自己,两年后我离开了学校,但是我始终记得老师对我讲过的“自然的”表演。
因此我哦总是努力保持自然的表演。
虽然我不清楚自然的与真实的有什么不同。
我能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得到什么呢?
他是一个俄国人,而我,来自布鲁克斯。
【性、哥们、独立】
Q:
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次吗?
A:
我的第一次?
在九岁的时候(
),我遇见一个女孩。
她脱掉了上衣,在我面前袒露着。
也许她比我大点,或者我比她大点。
我把手放在那上面,她就傻傻地笑。
她就站在弹簧床垫的前面。
当我推到她,她就被床垫弹起一下,我们这样反复了三四次(
)。
我觉得我想要了,于是我立马跑出去拿回来一包避孕套。
一般它们都被放在钱包里,其实我们当时也不太清楚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Q:
你是说你和你的朋友对这种事都不怎么懂?
A:
有一个,克里菲,我最好的朋友。
他长得有点像理查德·伯顿和马龙·白兰度的混合体。
他还是一个犹太人,却想成为一个天主教徒。
他是我认识的最凶恶、粗暴的家伙。
他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他是一头野兽。
他也是我们当中最先有性经历的。
在他14岁的时候他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然后他对我讲述那些小说有多恐怖。
有一件事我始终铭记在心。
我目睹他试图猥亵我的母亲,当时他只有14岁。
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古怪的家伙。
Q:
你母亲怎么做的?
A:
她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还多少有几分讥笑他。
她对此似乎显得无法理解。
Q:
你现在还跟他们见面么?
A:
他染上了毒瘾,最后死了。
我听说死的时候只有30岁。
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在19岁的时候也死于吸毒。
Q:
你从来没有注射过毒品么?
A:
是的,从来没有。
正是毒品让我和他们分开了。
他们走入了另一个世界。
我答应母亲要好好活着,我甚至都不碰针头。
我从不想毒品,我看到毒品给无数人都带来了什么。
我认为那就是一条绝路。
有时我会畅饮一番。
做这事的时候我差不多13岁,这也是大多数年轻人做的事。
长大一点了,你会看到他们在街上向你售酒。
自大我能记事那一刻起,流连于杯盏与香烟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喝点酒吧。
我九岁的时候开始吸纸烟,十岁开始嚼烟草,11岁时我就开始抽烟斗了。
但是像我朋友克里菲所作的那些事,却是我闻所未闻的。
Q:
例如?
A:
当我们长大一点了,他向我保证他再也不沾毒品,我们便不在私下里谈论这个事了。
有一次他抢劫了坐满了乘客的公交车。
要么就是偷盗垃圾车又或者阻止它停在我家门前。
还有一次他次着实让我卷入了一个麻烦,他为了给我弄双鞋,不停地踢商店的窗户。
一个巡警抓住了他,你可以想象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有多尴尬,我的祖母急忙把我带走了!
我还记得又一次他被叫到教室前面。
老是被他气疯了,她开始抓他、打他。
他只是不停地笑,因为他觉得特有劲。
最后老师把他赶出去继续上课。
我也笑了,所以我也被赶了出去。
那真是美妙的日子(……)。
我经常回想那段纽约街区的生活,那是一段超越其它锁钥的永恒性的记忆,我们总是做出些出人意料的事情。
我们爬上屋顶,以最快的速度跑过街区,那是属于我们的时光。
Q:
听起来你会像你的朋友克里菲一样啊?
A:
我曾经为一个果园主工作过。
我的朋友就在外面玩,而我要把绿番茄从红番茄中挑出来。
果园主在一块木板上画了一幅画,那是一张果园树木与路径的分布图。
他向我走过来说:
“人生有两条路:
一条是正确的,一条是错误的。
你正在错误的路上。
”我以为这话是针对我挑番茄的活的,但其实它是针对我外面的朋友的。
他说:
“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跟他们一样。
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对果园主:
谁派你来的
)
Q:
你是否介意还是孩子时就得工作?
A:
谁想工作呢?
但是我又不想去学校,为了我自己和我母亲,我不得不工作。
我的祖父母在我15的时候搬走了。
17岁那年,我母亲的祖父母住在一起,只留下我一个人。
换做今天这没什么,但这事可是20年前的事。
Q:
你是否想过自己很年轻就死了的情况?
(主持人想象力挺丰富啊
)
A:
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你会有一个对死亡可能性的认识,你审视死亡。
从这种审视中你会对周围的人有全新的理解。
我现在就对此有所感触。
人们常说这种情况发生在你35、36岁之时。
我会有一种幻想,我的尸体被放进箱子里,人们哀悼我,说:
“我们不该那么恶劣地对待他!
”最近我的左脚趾长了根骨刺。
我对医生说:
“已经好多了吧?
”他说不,我突然意识到当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任何事都不会自行好转了。
如果我死了,墓志铭可以这样写:
“他正开始下决心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在10——15年中,他过得挺快乐。
他已经改变了很多!
”
Q:
你做过什么古怪的行当么?
A:
我做过邮递员、看门的、卖鞋的;我在水果铺、药店、超市干过;我搬过家具——那是我做过的最辛苦的工作。
作为一个搬运工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书。
每个人都有书,甚至数千本。
它们放在盒子里。
这相当有迷惑性。
其实那起码有五千本平装的书(XDDDD我看出来了,本来想挑个盒子去搬,结果拿上手就知道糟糕了)。
我开始做搬运的时候是在车里等候,他们一喊“过来帮忙!
”我就迅速从车里出来,帮他们拖着钢琴上楼,我每小时可以挣三美元。
我也搬过艺术品。
当你拿着价值连城的雕塑撞到墙上,那真是有趣(这小子果然不是好鸟啊
)。
我就遇到过,雕像的头部掉落碰到它的肩部。
因此我知道的一句关于艺术工作的名言就是:
你得赔!
我也做过引座员。
人们总是问:
“表演什么时候开始?
”“最后一部分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问各式各样的问题,人们总是听从我说的任何话。
所以我跟其他引座员打赌,说我能够让他们列队穿过街道,然后我对他们说,他们就排在布鲁闵戴尔的大街上了。
(XDD)
Q:
你赢得了赌注,得到了什么?
A:
我被解雇了。
Q:
哪个工作你做的最久?
A:
做的最久的一次试在一家新闻评论杂志。
我在那干了几年。
主要做些递送之类的事,我挺喜欢在那干的。
【表演工作室的岁月】
Q:
那会儿你也表演吧?
A:
我参加了赫伯特·伯格霍夫的表演工作室。
在那我认识了查理·拉夫顿。
我当时18岁,而他29岁。
他正在教授一个表演班。
我想多了解了解他,因为我觉得与他有某种关系。
查理将我带入了另一个世界,那是我从未触及到的生活的某些领域。
他把我介绍给作家,让我知道了与表演相关的方方面面的事。
我依旧记得有一回我睡在店面门口,身上只有15美元的情景。
我那晚一定是喝醉了,但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身上一个子都没了。
我知道查理家就在“远方马车”大道的海滩。
但是去那需要25美分,为了弄到车费,我只能用一大堆贝拉蒂尼淡啤酒做抵押,向搬运公司的老友借钱。
然后我上了火车去找查理。
他和孩子和妻子就在海边,他看见我。
而我,正朝他走过去,穿过一路上的遮阳伞。
我穿着深黑色的衣服和裤子。
他注视着我,我说:
“我身无分文了。
”他给了我5美元。
我转身穿过人群,进了他家,上了楼,我知道查理会收留我的。
于是我们成了一家人。
他是一个伟大的演员,但是他从来不看重这点。
在表演班他没有把我当学生。
就好像他把教导我视为自己的责任一样。
(对查理:
谁派你来的+1)
Q:
他就如同你的父亲?
A:
我把他想象成父亲。
他既是慈父,也充当我的兄弟和密友。
他总是和我一起做每件事,我无法想象没有查理能做什么。
Q:
拉夫顿是第一个认识到你明星潜质的?
A:
绝对是——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
在我19岁时我住在布鲁克斯的出租屋。
在我下楼的时候,查理正好从我身边经过。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
“你会成为明星的!
”这种事在布鲁克斯是难以置信的,怪异的,后来他和我再也没有谈论过这个事。
Q:
在进入伯格霍夫前,你没有想过进入李·斯特拉斯堡的表演工作室?
A:
我参加过试演,但落选了。
我对自己说,他们错了。
我总是保持一个健康的态度对待这种事。
当年年轻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源源不断的活力、力量在涌动。
四年后,我再次试演,被录取了。
他们甚至从詹姆斯·迪恩纪念基金拿出50美元让我付房租。
达斯汀·霍夫曼和我是同一年进去的:
我总能听到人们不断谈论他,他真是太棒了!
Q:
表演工坊对你有多重要?
A:
它对于我的人生有太多意义。
实际上李·斯特拉夫斯堡的表演工作是并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声誉。
白兰度没有给工作室带来声誉,相反还让它有了个坏名声。
【主角与经纪人】
Q:
在第一部由你担任主角的影片[毒海鸳鸯]里的角色比你的真实年龄大不少,你对这部片子有什么感想?
A:
我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有点喝醉了(XDDDD)。
我对自己说:
“这里有一个有天赋的演员,他需要工作和实践。
”
Q:
为什么选择这个影片?
A:
在我接受这个片子前我拒绝了11部片子的邀请。
我想是时候开始我的电影事业了,但是我不知道会演什么。
这时[毒海鸳鸯]出现了,马蒂·布莱格曼努力帮我争取加入到这个片子。
我有五部电影的角色是他直接搞定的,这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巨大。
Q:
他是怎么成为你的经纪人的?
A:
他看了我一出百老汇戏剧演出,然后他找到我,表示愿意为我争取任何我想做的工作。
我一开始没弄明白,他又说,我打算赞助你。
但我还是没搞清楚他想做什么!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他想做我的经纪人(
)。
这对我非常重要。
是他鼓励我出演[教父],[赛皮科]也是他的工作成果。
还有那部[热天午后]。
Q:
你和他有比较正式的合约吗?
A:
是,那可是一分昂贵的合约。
但是非常值得。
Q:
你现在还跟他共事吗?
A:
不,几年前,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最终导致我们散伙了。
他变成了一名制片人。
一切都不一样了。
【[虎口巡航]的非议】
Q:
说说[虎口巡航]吧。
它的上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激进的同性恋组织甚至宣称这个故事是反同性恋的?
A:
我不能理解这种事。
这是我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情况,我很困惑。
不过有一点不得不承认,这是部粗暴的电影。
Q:
你扮演的是一名追查同性恋谋杀案的警察。
电影中许多场景所展现的是出于非主流的性河蟹虐同性恋,而不是主流同性恋生活!
A:
这是关键点。
当我初次阅读剧本时,我甚至都不知道这种非主流生活的存在。
这不过是这类同性恋社团生活的一小部分。
就像黑手党是意大利裔美国人生活的一小部分一样。
Q:
你怎么评价这部片子?
A:
它是多重情感交织的一部片子。
我觉得剧本的某些部分像哈罗德·品特,有些部分像希区柯克。
它是一部惊险刺激的小说,一个冒险故事。
Q:
显然纽约的同性恋社团并不这么想。
传发的小册子称这部电影为“一次诈骗”,这个关于一名同性恋杀人犯的故事中,用得无非是同性恋电影中非常老套的一些东西作为背景!
A:
在没有看这部片子前他们不该这么说。
Q:
他们说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表示同性恋被描绘成性错乱者,他们是易受死亡和暴力侵害的对象。
这部电影不是关于我们怎么生活的,而是关于我们为什么被杀的!
A:
这真是一段强有力的声明。
令人非常不安。
Q:
你对这些指控有何看法?
A:
我觉得太糟了。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当我读到剧本,我从来没有过反对同性恋的想法。
我始终没有弄明白这部影片怎么会煽动起这样的情绪。
我对这方面的事并不是很敏感,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境遇却非常敏感,因此,我不能过多辩解什么。
但是我觉得,不该把现实与电影混为一谈。
Q:
[虎口巡航]是你最富争议的片子吗?
A:
是的,没有哪一部片子的争议更胜于它了。
我以为[热天午后]会惹麻烦,但是没人来打扰我们的拍摄。
我不喜欢这些麻烦事。
我从未置身政治舞台,这不关我的事。
对于我而言,电影中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向来不重要。
电影毕竟只是一个故事,一些角色。
电影获得国际关注,媒体对片子进行讨论,这些都是围绕电影主题而不是我。
而主题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无限发挥的东西。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谬误:
电影没有我照样会被拍出来。
Q:
也许吧。
不过这个剧本在你接受之前已经被三个制片公司拒绝了。
A:
但这不是我的电影!
它不是我筹备的,是他们找上我的。
Q:
的确,不过一旦你接受剧本,它就变成了一部阿尔·帕西诺的电影了!
你不觉得应该对电影中的某些观点负责人吗?
(这个主持人鬼打墙了么,好欠揍
)
A:
你把它当成一部阿尔·帕西诺的电影?
在这部电影中,阿尔·帕西诺只是一个演员,不能因为我的名字在其中就将这种强大的压力施加在我身上,责任是相对的。
我的责任就是按照剧本塑造好我演的人物,而不是我没资格评论的电影主题!
Q:
但是我们最终都是对我们做的事有责任的,而不像你说的可以逃避一部分。
A:
这不是一部反同性恋的电影。
而我重申一点,我的责任只是尽力拿出最好的表演状态。
我接着这个角色是因为他很让人着迷。
他是一个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很暧昧的人,他既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又是一个煽动者。
我有机会去塑造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又带有污点的人物。
我是以演员的身份与公众交流的。
无论是同性恋社团、意大利裔美国人社团、警察社团、政治社团,或是其它我在银幕上描绘的社团,我根本不曾想过对它们造成伤害。
我只能以我演员的才能做出回应。
Q:
自从你中途接手这个片子,迄今为止你对影片做如是观?
A:
影片有一种力量,一种特定的戏剧风格。
当我读剧本时就有这样的感觉。
我相信威廉·弗莱德金的活力通过剧本实现了。
因为它让你振奋。
在这一点上他非常像科波拉。
【科波拉与[教父]的故事】
Q:
那么谈谈科波拉吧?
A:
我记得我去旅馆见弗朗西斯,与他探讨[教父Ⅱ]的剧本。
当我离开时,充盈着他的灵感。
他给我补充了能量。
我本不打算出演[教父Ⅱ]。
这里有一件趣事,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我赚的第一笔大钱。
在他们打算付给我那笔钱之前,科波拉其实还没有说服我。
Q:
那是怎么回事?
A:
他们准备给我十万拍第二部,我没有答应,他们又说那15万怎么样?
我还是说不,他们说如果让普佐来写剧本呢?
我答应了,不过在我读了普佐写好的剧本后,其实我觉得很不错,但是我又说了不,于是他们把价码提高到20万,我还是说不。
他们把报酬一路飙升到35万。
最后报出了45万,我还是拒绝了。
之后他们邀请我倒纽约的办公室继续谈。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说笑,制片人拉出他的抽屉,打开一个盒子。
我就坐在对面,他将盒子的开口对着我,说:
“如果我告诉你这里有100万现金,你会怎样?
”我说:
“那不意味着什么——这不过是个抽象的概念!
”实话实说,我对于最终也没有拿那100万,还对那位制片人抱有一丝歉意!
Q:
那么什么使你改变主意的?
A:
弗朗西斯跟我谈了剧本。
拍这部片子的前景让他非常亢奋,他总能鼓舞他人。
我觉得自己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跟某些导演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常说,如果你想寻找这种感觉,就跟科波拉一起工作吧。
Q:
故事的结局是,你拒绝了100万,但是得到了600万,这是影片票房的十分之一,对吗?
A:
的确如此。
(油,我头发都立起来了!
)
Q:
直到1977年的[夕阳之恋],你再没有得到过100万的报酬吧?
A:
是的
Q:
那么你从教父第一集中得到了多少?
A:
大概是35万。
而最终我的合法收入是15万。
Q:
在完成第一次[教父]试镜的时候,科波拉让你自由发挥,为什么?
A:
他期望我在片中做得更多。
他选取了迈克的戏份中最无趣的部分——也就是第一次婚礼中的一些说明性场景,然后我就演了,但他要求我做更多的事。
但是我不知道他期望我做什么,他经常让你在并非你演的角色的场景中表演,一开始我以为他让我演桑尼,当时我没考虑是否能够得到这个角色。
因为你想得越少,得到的越多。
它意味着什么,就将是什么。
每每我有太多的想法的时候,结果总是做错些什么。
Q:
然而你总是相信自己能得到这个角色,对吗?
A:
有时你只是有一种大致的感觉。
如果你想要实现它,你就会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评估。
这时欲望和贪婪会使你对状况的估计变得困难,但是如果你退一步,你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你就会认识到将要发生什么。
实际上,如果我没有得到教父众的角色,那会使我感到惊讶。
Q:
科波拉先确定了谁的角色,你的还是白兰度的?
A:
我肯定他是先想到白兰度的。
我们在一起参加过一个派对。
他问我:
“你觉得教父应该谁来演?
”我说白兰度。
科波拉在选角方面是非凡的。
他只是试探你。
他是一个奇特的人。
他有点窥视癖。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
像他那样分配工作任务的简直前所未见。
他那中满情绪感染力的行事方式就像迈克·柯里昂。
这就是为什么弗朗西斯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很透彻的原因。
Q:
你扮演迈克的时候,科波拉有没有向你说过他的想法?
A:
有的部分我是按照他的设想来演的,还有的部分是以我认识的几个人为原型的。
Q:
你是说真正的黑手党成员?
A:
是的。
有些人会在私下里给我一些参考。
Q:
你可以观察他们?
A:
是的。
Q:
而且他们也允许?
A:
是的。
Q:
然后发生了什么?
A:
没什么。
Q:
他们都还活着吗?
A这个我不能说。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