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docx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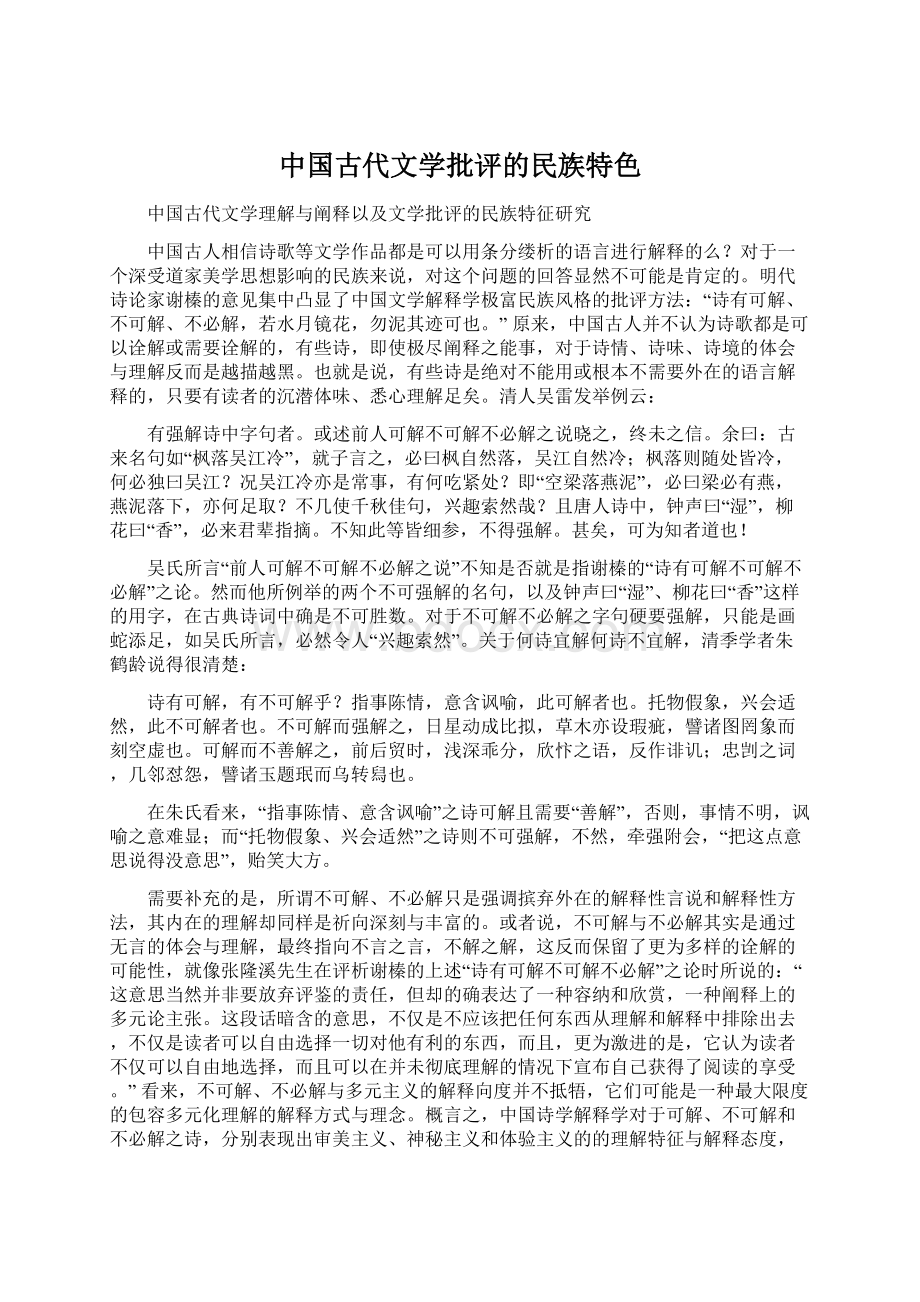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文学理解与阐释以及文学批评的民族特征研究
中国古人相信诗歌等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用条分缕析的语言进行解释的么?
对于一个深受道家美学思想影响的民族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不可能是肯定的。
明代诗论家谢榛的意见集中凸显了中国文学解释学极富民族风格的批评方法:
“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
”原来,中国古人并不认为诗歌都是可以诠解或需要诠解的,有些诗,即使极尽阐释之能事,对于诗情、诗味、诗境的体会与理解反而是越描越黑。
也就是说,有些诗是绝对不能用或根本不需要外在的语言解释的,只要有读者的沉潜体味、悉心理解足矣。
清人吴雷发举例云:
有强解诗中字句者。
或述前人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说晓之,终未之信。
余曰:
古来名句如“枫落吴江冷”,就子言之,必曰枫自然落,吴江自然冷;枫落则随处皆冷,何必独曰吴江?
况吴江冷亦是常事,有何吃紧处?
即“空梁落燕泥”,必曰梁必有燕,燕泥落下,亦何足取?
不几使千秋佳句,兴趣索然哉?
且唐人诗中,钟声曰“湿”,柳花曰“香”,必来君辈指摘。
不知此等皆细参,不得强解。
甚矣,可为知者道也!
吴氏所言“前人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说”不知是否就是指谢榛的“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论。
然而他所例举的两个不可强解的名句,以及钟声曰“湿”、柳花曰“香”这样的用字,在古典诗词中确是不可胜数。
对于不可解不必解之字句硬要强解,只能是画蛇添足,如吴氏所言,必然令人“兴趣索然”。
关于何诗宜解何诗不宜解,清季学者朱鹤龄说得很清楚:
诗有可解,有不可解乎?
指事陈情,意含讽喻,此可解者也。
托物假象,兴会适然,此不可解者也。
不可解而强解之,日星动成比拟,草木亦设瑕疵,譬诸图罔象而刻空虚也。
可解而不善解之,前后贸时,浅深乖分,欣忭之语,反作诽讥;忠剀之词,几邻怼怨,譬诸玉题珉而乌转舄也。
在朱氏看来,“指事陈情、意含讽喻”之诗可解且需要“善解”,否则,事情不明,讽喻之意难显;而“托物假象、兴会适然”之诗则不可强解,不然,牵强附会,“把这点意思说得没意思”,贻笑大方。
需要补充的是,所谓不可解、不必解只是强调摈弃外在的解释性言说和解释性方法,其内在的理解却同样是祈向深刻与丰富的。
或者说,不可解与不必解其实是通过无言的体会与理解,最终指向不言之言,不解之解,这反而保留了更为多样的诠解的可能性,就像张隆溪先生在评析谢榛的上述“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论时所说的:
“这意思当然并非要放弃评鉴的责任,但却的确表达了一种容纳和欣赏,一种阐释上的多元论主张。
这段话暗含的意思,不仅是不应该把任何东西从理解和解释中排除出去,不仅是读者可以自由选择一切对他有利的东西,而且,更为激进的是,它认为读者不仅可以自由地选择,而且可以在并未彻底理解的情况下宣布自己获得了阅读的享受。
”看来,不可解、不必解与多元主义的解释向度并不抵牾,它们可能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包容多元化理解的解释方式与理念。
概言之,中国诗学解释学对于可解、不可解和不必解之诗,分别表现出审美主义、神秘主义和体验主义的的理解特征与解释态度,这三种极富民族诗学个性的解释方式及其话语构成了中国文学解释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我们将分三部分详述之。
第1章中国诗学审美主义多元解释特征
1.1中国诗学审美主义多元解释方式的构成
按照一般的看法,文学解释应该如美国著名文论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言:
“就是通过分析、释义、评论确定作品的意义,通常侧重于对晦涩模糊或者具有比喻意义的段落进行阐明。
”依此定义,文学解释当以论述和说明为主,在语言表征上显然要与文学作品的形象性迥异。
然而,在中国诗学解释学里,我们却看到许多如同诗歌语言一样优美形象的譬喻性解释,这些譬喻性解释运用大量的意象来比况诗歌的艺术风格和文本特征,且有意识地追求一种类似诗歌文体的整齐、对称的形式效果,这使得譬喻性解释自身也变成了富有美感效果的诗性文本。
换言之,中国诗学解释学不喜欢以技术性的手段去对诗歌作条分缕析的解剖,更不擅长用抽象思辨和逻辑分析来诠释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而是主动选择了一种审美主义的诗性方式来批评和诠解诗歌的一切,张隆溪先生称此为“以诗言诗”的方式:
“中国批评家知道自己几乎不可能用诗外之语言谈论诗,因而要么引用一些典范性的句子来证明他们以为精妙或难以言传的性质或特征,要么试图凭借意象和隐喻来暗示这些性质和特征——总之,更多的是展示而不是言说。
中国批评家不去分析和论辩而倾向于以诗言诗,许多有洞见的诗论不是出现在批评文章中,而是出现在诗歌中。
”不错,即使对于那些“可解”之诗,中国古人也并非极尽语言阐说之能事,而是“以诗言诗、以诗解诗”,从而使解释本身如同诗歌文本一样具备了一定的审美价值,这就是中国诗学解释学第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的理解与阐释特征。
利科尔说:
“解释是思想的工作,它在于于明显的意义里解读隐蔽的意义,在于展开暗含在文字意义中的意义层次。
”然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解释不仅是思想的工作,更是艺术的工作,解释也是一项审美性的艺术创作。
而且,在道家言意观的影响下,中国古人似乎不太相信语言对于意义的揭示作用,更何况对于那些“暗含在文字意义中的意义层次”。
他们更偏好用意象譬喻的方法,对诗歌作点到即止的描绘,期于读者自悟自得。
也就是说,解释者说得越多,可能离诗意和诗味越远;相反,利用意象的全息性,引而不发,刺激读者主动参与阐释,可能所获更多。
叶维廉先生说:
“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以不破坏诗的‘机心’为理想,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而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
”用“一种近乎诗的结构”来批评与诠解诗,还有比这更“言简而意繁”的方式么?
诗歌是需要读者“悟”的,而譬喻性解释也需要读者去“悟”,还有比这种双重的“悟”赋予读者多元理解的权力更大的方式么?
本质上,诗是最具美感和生命感的艺术形式,那些概念性的分析只会肢解诗歌的美感和生命感。
狄尔泰说:
“理解和解释始终是这样活跃和活动于生命本身之中,只有通过对富有生命力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在其作者的精神中的联系的合乎技术的解释,理解和解释才达到其完成。
”中国古人想必不会认同这种“合乎技术的解释”,他们会认为技术性的解释反而可能窒息理解和解释的生命性,当然更会压抑乃至湮灭诗歌的生命力。
惟有“以诗解诗”,以审美主义的态度对待诗歌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理解者的审美冲动和生命力,也才能完好地保全和展现诗歌本身的美感与生命感。
中国诗学解释学譬喻性解释方式滥觞于先秦诸子。
《庄子》就是“寓言十九、以寓言为广”之作,而孟子、墨子、韩非子、荀子等人更是善譬、善喻的高手,其精妙的举类说理常常令对方无以言对。
可以说,先秦百家思想的深入浅出、广为流传,某种程度上就与他们多用且善用譬喻、举类的表述方式有直接关系。
《礼记·学记》篇就有“能博喻,然后能为师”之论: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
故君子之教,喻也: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
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
能博喻,然后能为师。
能为师,然后能为长。
能为长,然后能为君。
君子之教,贵在善喻,惟能博喻,方可为师。
而且,判断“喻”之优劣的标准非常明确,即“和易以思”。
尤其是“思”,点出了譬喻之教的要义就是重在使接受者咀而咽之、思而得之,而不是像详尽的分析性解释那样使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全盘吸收。
东汉思想家王符认为,譬喻性解释的形成与发达,不仅在于“喻”能够使听众和读者自悟,更主要是很多事情与道理,非“喻”则不能显,以譬解之,不说而明。
其《潜夫论·释难》云:
“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
”看来,譬喻实有“直告”所不及之处。
刘向《说苑·善说》篇记叙的先秦名家惠施的一则故事很好地道出了譬喻性解释的不可替代的言说作用:
客谓梁王曰:
“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
”王曰:
“诺。
”明日见,谓惠子曰:
“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
”惠子曰:
“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若何?
’应曰:
‘弹之状如弹。
’则谕乎?
”王曰:
“未谕也。
”“于是,更应曰:
‘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
’则知乎?
”王曰:
“可知矣。
”惠子曰:
“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
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王曰:
“善!
”
事实上,惠子的“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无意中为中国诗学解释学指出了一种理想的解释形式,即前为譬喻,后附直言或前为直言,后跟譬喻的言说方式。
二者的巧妙搭配,颇似诗歌创作中的“点染”手法,前染后点或前点后染,言简意赅,相得益彰。
例如,《世说新语·文学》中一段广为称引的作品评鉴:
“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钟嵘《诗品》“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条则反其道而行之:
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
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对这种以优美的意象来喻示诗歌的艺术风格、气味神韵的方法,罗根泽先生称之为“比喻的品题”,郭绍虞先生以之为“象征的批评”,而张伯伟先生则名之“意象批评”,他说:
“意象批评法,就是指以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的理念,以揭示作者的风格所在。
其思维方式上的特点是直观,其外在表现上的特点则是意象。
”这些显然都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着眼。
邓新华先生则从诗学解释学的视域出发,称上述譬喻性解释为“象喻”式的诗性阐释方式。
针对《诗品》“宋光禄大夫颜延之”条引汤惠休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他说:
“这些评语并不是直接对作品作出理性的分析和评价,而是用‘象喻’的方式给读者描绘出一幅幅构象新奇、诗意盎然的画面,让人们通过联想和想象去体会作品的情趣和韵味,并使读者在一种审美的愉悦当中自然了悟阐释者所要表达的观点和态度,这就是‘象喻’这种诗性的阐释方式的基本特点之所在。
”此论切中肯綮地点出了“象喻”阐释方式的要妙不仅在于对理性分析和抽象演绎的放逐,更在于它能使读者在一种审美愉悦中去了悟阐释者的观点与态度。
在我看来,以诗性的方式去解诗,希冀读者能获得对诗歌文本和阐释文本的双重审美愉悦,正是譬喻性解释的特殊魅力和价值所在。
大致而言,譬喻性诗学解释形成于魏晋六朝,以钟嵘的《诗品》为代表。
“钟嵘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他善于精心选择和提炼一些生动具体、含蓄隽永的自然美意象和形象来喻示解释对象的内在风格和整体韵味,同时又借这些意象和形象委婉含蓄地传达出解释者对解释对象整体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解。
这样一来,这些比喻象征性的意象和形象在诱发读者审美联想和想象、给读者以审美的享受的同时,其自身也显示出浓郁的诗意。
”但钟嵘时期的审美性和诗性批评与解释所运用的意象还显得单薄,描述还比较拘谨,对作家作品的风格与特征的认识还只限于单一视角。
到了唐代,在唐诗创作高度繁荣的熏染下,譬喻性解释变得更加摇曳多姿、铺张扬厉,其唯美色彩更浓,表意也更为丰赡。
这是中国诗学解释学审美主义解释特征的定型与成熟期。
我们来看杜牧对李贺诗歌的意象阐释:
贺,唐皇诸孙,字长吉。
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
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
一组由自然物象和社会形象构成的意象群分别从多个侧面和角度对李贺诗歌的各种艺术特色进行全方位的扫描与透视,读此段文字者,不仅对李贺诗歌的理解会更为丰富,其所得之美感也必定更为强烈。
如果这种博喻式的解释所选意象大致相类,则很容易营构出某种富有感染力的意境或境界。
有人就将唐司空图的《诗品》对二十四种不同诗歌风格的意象阐释法称为“境界描述”,罗宗强先生说:
“用境界描述的方法说明一种诗歌风格类型,说明它的境界的多层次的特点,是司空图的创造。
”我们可以随手举出两例司空图所用的这种境界描述法:
绿杉野屋,落日气清。
脱巾独步,时闻鸟声。
鸿雁不来,之子远行。
所思不远,若为平生。
海风碧云,野渚月明。
如有佳语,大河前横。
——《沉著》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
晴雪满竹,隔溪渔舟。
可人如玉,步屧寻幽。
载瞻载止,空碧悠悠。
神出古异,淡不可收。
如月之曙,如气之秋。
——《清奇》
二十四种艺术风格,如果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将它们解释明白,即使写作二十四本专著也难以廓清,且让人看完一头雾水,了无印象。
司空图非常聪明地选用了与每种诗歌风格相一致的系列意象,组成一个视觉效果盎然,使人不由置身其中的意境。
在这种意境里,读者闻花香鸟语,看月落日出,自身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被最大程度地激活、唤醒,所谓的艺术风格其实已与眼前的境界同化,用不着多余的阐述与解释,每种风格所包蕴的丰厚内涵已经了然于胸。
再加上整齐的四言句式,自然成对的组合以及和谐的音韵,没有人不觉得这既是一种对艺术风格的独特解释,也是一首首意象优美、境界浓郁的诗作。
宋代诗话大兴,诗论家对前人诗作的譬喻性解释运用得更加娴熟与灵活,而且这种象喻式的品评方式也逐步扩散到评曲、评词、评画等领域,影响更大。
明人王世贞曾说:
“汤惠休、谢琨、沈约、钟嵘、张说、刘次庄、张芸叟、郑厚、敖陶孙、松雪斋,于诗人俱有评拟,大约因袁昂评书之论而模仿之耳。
其宋人自相标榜,不足准则。
吾独爱汤惠休所云‘初日芙蕖’,沈约云‘弹丸脱手’,钟嵘云‘宛转清便,如流风白雪;点缀映媚,如落花在草’。
”由王氏所说的“独爱”之例,可知宋人竞相“标榜”的就是上述譬喻性的诗性解释与批评方式。
其中所提到的宋人敖陶孙,就有一段颇受后人称道的气势恢弘的意象阐释: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
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
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
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
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暗合音徽。
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
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
……
尽管对二十八家诗风逐一比况,令人叹服,不过,像这样只从诗人作品的一种风格或特征上作喻,毕竟表意单薄,读者美感有余,而所获不足。
因此,宋诗话对前人诗作更多的是运用博喻式的阐释方式,或者是“有喻有评”这种评喻结合的最佳解释方法。
如宋蔡絛所评唐宋十四家诗风:
柳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
王摩诘诗浑厚一段,覆盖古今;但如久隐山林之人,徒成旷淡。
杜少陵诗自与造化同流,孰可拟议,至若君子高处廊庙,动成法言,恨终欠风韵。
黄太史诗妙脱蹊径,言谋鬼神,唯胸中无一点尘,故能吐出世间语;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
……
前评后喻或前喻后评,评喻互证互补,始为一种成熟得当的解释模式。
事实上,宋以后的诗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解诗模式一直占据主流。
随着诗歌批评与解释思想的日渐深入,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过去那种“某人诗如某某”的单纯比拟与罗列,越来越注重将自己的意见直陈于比况的前后,使二者难分主次,相得益彰。
清叶燮曾说:
“夫自汤惠休以‘初日芙蓉’拟谢诗,后世评诗者,祖其语意,动以某人之诗如某某,或人、或神仙、或事、或动植物,造为工丽之辞,而以某某人之诗,一一分而如之。
泛而不附,缛而不切,未尝会于心,格于物,徒取以为谈资,与某某之诗何与?
明人递习成风,其流愈盛。
”的确,如果仅仅是“以某某人之诗,一一分而如之”的形式去解诗,很容易产生“泛而不附,缛而不切”之弊。
需要强调的是,除了以评喻结合的办法来克服单纯譬喻性解释的局限性之外,中国古人还运用“摘句褒贬”的方式来加强批评与解释的针对性和具体性,例如司马光如此阐发杜甫《春望》一诗:
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
他皆类此,不可遍举。
像这样对具体诗句之意的详解,已经接近现代文学解释学的文本阐释。
但多数摘句之法并非如此。
“古代诗学批评中,摘句是相当突出的现象,即不作细致的解说分析,而惟摘录能说明己意的诗句,罗列之,使观者自明。
其思想根源即在于整体直觉。
人们认为诗歌的意味,或佳妙处,往往很难以明确的言辞加以解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读者直接从原作中领会。
”应该说,在整体直觉和期于读者自我领会这两点上,摘句之法与譬喻性解释还是相通的。
由摘句褒贬再往前推进一步,就是以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和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为代表的特殊批评与解释文体——论诗诗。
学界对此研究和论述颇多,这里只想指出,中国诗学在批评与解释的方式上,似乎始终浸淫在一股审美主义的冲动中。
无论是以象喻诗,直接摘取诗句以褒贬之,还是干脆以诗论诗、以诗解诗,都让我们体会到一股浓郁的诗意和美感,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将批评、解释与诗歌创作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1.2中国诗学审美主义多元解释的特征与成因
施莱尔马赫说:
“譬喻性的解释开始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意义在直接的语境中是缺乏的,所以我们需要提供譬喻的意义。
”但是,中国诗学解释学对譬喻性解释的偏嗜与执著主要不是因为意义在直接语境中的阙如,而是首先缘起于古人对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的深度体认。
简言之,诗歌的艺术特质注定了它不宜于采用西方那种抽象的条分缕析式的逻辑推衍,而更适合运用“象喻”的诗性解释方式来与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保持一种契合同构。
清叶燮的一段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诗学对诗歌本质和解诗妙谛的深刻认识:
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
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
若一切以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则能实而不能虚,为执而不为化,非板则腐,如学究之说书,闾师之读律;又如禅家之参死句,不参活句,窃恐有乖于风人之旨。
实际上,叶燮已经说明了为什么诗歌不能“以理概之”,即用抽象的意义分析去诠解诗歌的根本原因。
一言蔽之,对于“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指归在可解不解之会”且“妙在含蓄无垠,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诗歌而言,任何貌似周全的理性解析都只能是一管之见,都有不尽人意之处,而且“非板则腐”,不如索性放弃抽象演绎,以象喻之,将实际的理解与阐释全部交给读者个人去意会,使读者自由徜徉在诗歌与譬喻的双重理解语境中,也许所获更多。
从哲学的层面上看,显而易见,中国诗学对譬喻性解释的青睐和对分析性阐释的疏远当然是道家语言哲学深刻影响的结果。
老庄对语言表意功能的极度不信任不仅在文学创作中被广泛表征,在文学接受和阐释的场域,以意象解释而不是以语言解释为主本身就是对因言求意之法的怀疑。
就像《庄子·天道》篇中轮扁所说的那句千古至言:
“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无论是文本写作还是文本阐释,万物之道和世间真理都不可能凭借语言得以本真的显现与保全。
明人徐祯卿结合诗歌的特质和言不尽意论说得很好:
诗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
若夫妙骋心机,随方合节,或约旨以植义,或宏文以叙心,或缓发如朱弦,或急张如跃楛,或始迅以中留,或既优而后促,或慷慨以任壮,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发奇而似易。
此轮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详也。
《易》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欤!
既然对诗这种特殊艺术文本的解释不能相信因言求意的有效性,干脆反其道而行之,以象释象,以诗解诗,可能在激发读者自身妙悟潜能的同时,增加其双重审美愉悦的效果。
张隆溪先生说:
“对语言的这一激进怀疑,似乎是中国人头脑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见解。
这很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文论为什么大多用诗一般的形象语言来写的缘故。
”这种推测无疑是有根有据的。
对于诗学解释学而言,所谓“诗一般的形象语言”主要体现为譬喻性的解释,一种如同诗歌语言一样唯美的象喻式审美主义解释。
事实上,中国的诗论家和诗歌阐释者多数都是诗人兼之,就像罗根泽先生所言:
“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
”作为诗人的解释者和批评者既不擅长、也不喜欢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待诗歌文本,诗人须臾不离的审美情结以及对意象性语言的天赋注定了他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譬喻性解释与批评,独特的诗人气质也使得他们将解释与批评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诗歌的艺术风格、神韵趣味而不是意义的诠释上。
其实,中国古代的诗歌批评与解释不仅多数是诗人为之,而且是诗人们无意为之,是兴之所至、自然而然的结果,并非有什么预设的理论构架和研究目的,也没有什么很具体的功利目标和现实压力。
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中,“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大多集中在高等院校,由于对高校教师在职称评聘、业绩考核和学术奖惩等方面越来越严格的‘数字化’管理,使得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学术研究成为一种越来越‘规范化’或‘模式化’的文字制作。
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文学批评的写作,无论是文体样式、话语方式抑或语言风格均趋向单一、枯涩甚至冷漠。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那种特有的灵性、兴趣和生命感被丢弃,古代文论批评文体所特有的开放、多元和诗性言说的传统亦被中断。
”当然,我们感到遗憾的并不是规范化的学术研究,而是由此导致的诗性言说传统的断裂。
从“论诗诗”这种诗歌批评与解释的极致追求不难看出,古人完全被裹挟在一种审美主义的时代症候中,他们似乎总在努力把诗歌写作和诗歌评论合而为一,倘不能也要退而求其次——用同样唯美的譬喻性批评来保持与诗歌的美感和诗性相一致。
无疑,任何些许的现实功利目的都会破坏这种自由而又自然的诗性言说。
“与古代西方的文学理论家相比,中国古代文论家既缺少一种对‘理论家’身份的自我确认,也缺少一种理论意识的自觉。
而正是这些‘缺少’成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铸成了古代文论的诗性外观。
”同样,对于诗歌解释而言,没有外在的解释规范束缚,也没有硬性的解释任务要完成,率性而发,随意而成,诗人笔下的诗歌批评与解释不是诗性的象喻方式倒是奇怪的。
美国当代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kLnager)认为,成功的艺术作品表达的是一种“生命意味”,鉴赏者是否把握了艺术文本中的意味或表现性,是不能通过语言来说明的,只能靠“艺术知觉”,即一种艺术洞察力或顿悟能力,从艺术符号排列和组合起来的全部意象中去捕捉艺术品内蕴的“生命意味”。
无疑,中国古代那些兼具诗人和批评家双重才能的解释者既有敏锐的艺术知觉,又深知诗歌所表现的生命意味是不能用分析性的语言去肢解的。
他们非常聪明地选择了一条“以象释象”的诗性批评与诠释的途径,借助读者在长期的诗歌阅读中养成的直觉和顿悟能力来实现对诗歌艺术风格和文本意义的理解。
显而易见,中国诗学审美主义解释得以成立的首要条件就是它自身的具象性和读者的自得性。
依象而得义,悟象而识诗,具象性和自得性也是譬喻性解释的显著特征。
可以说,譬喻性解释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作用的结果。
面对诗歌的各种艺术特性和文本蕴涵,从来没有西方那种主客二分型的分析性思维模式的解释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完整地表达诗歌的神韵,完整地呵护诗歌的生命意味。
实际上,“对于具有含蓄蒙眬、恍惚悠渺、不受道理言语障蔽特点的中国古典诗歌,解释者如果硬用分肌擘理的逻辑方法只能是割裂它、肢解它,而且解之愈细,离之愈远,最后像西方解释学所做的那样使解释对象失却其活泼泼的生命而成为一种僵死的语言堆积。
正是基于对中国古典诗歌含蓄蕴藉、富于暗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有意识地摒弃了概念性的分解活动,而采用‘象喻’这种极富创造性和暗示性的文本阐释方式来传达解释者对于作品风神韵味的心灵体验和整体把握。
”我们可以随手举出一例来展示譬喻性批评和解释对诗歌某种风韵的整体性传递与维护:
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
蕴乎内,著乎外,其隐见异同,人莫之辨也。
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
学者能集众长合而为一,若易牙以五味调和,则为全味矣。
就像这些优美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