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文献论文4600字古代文学文献毕业论文范文模板.docx
《古代文学文献论文4600字古代文学文献毕业论文范文模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古代文学文献论文4600字古代文学文献毕业论文范文模板.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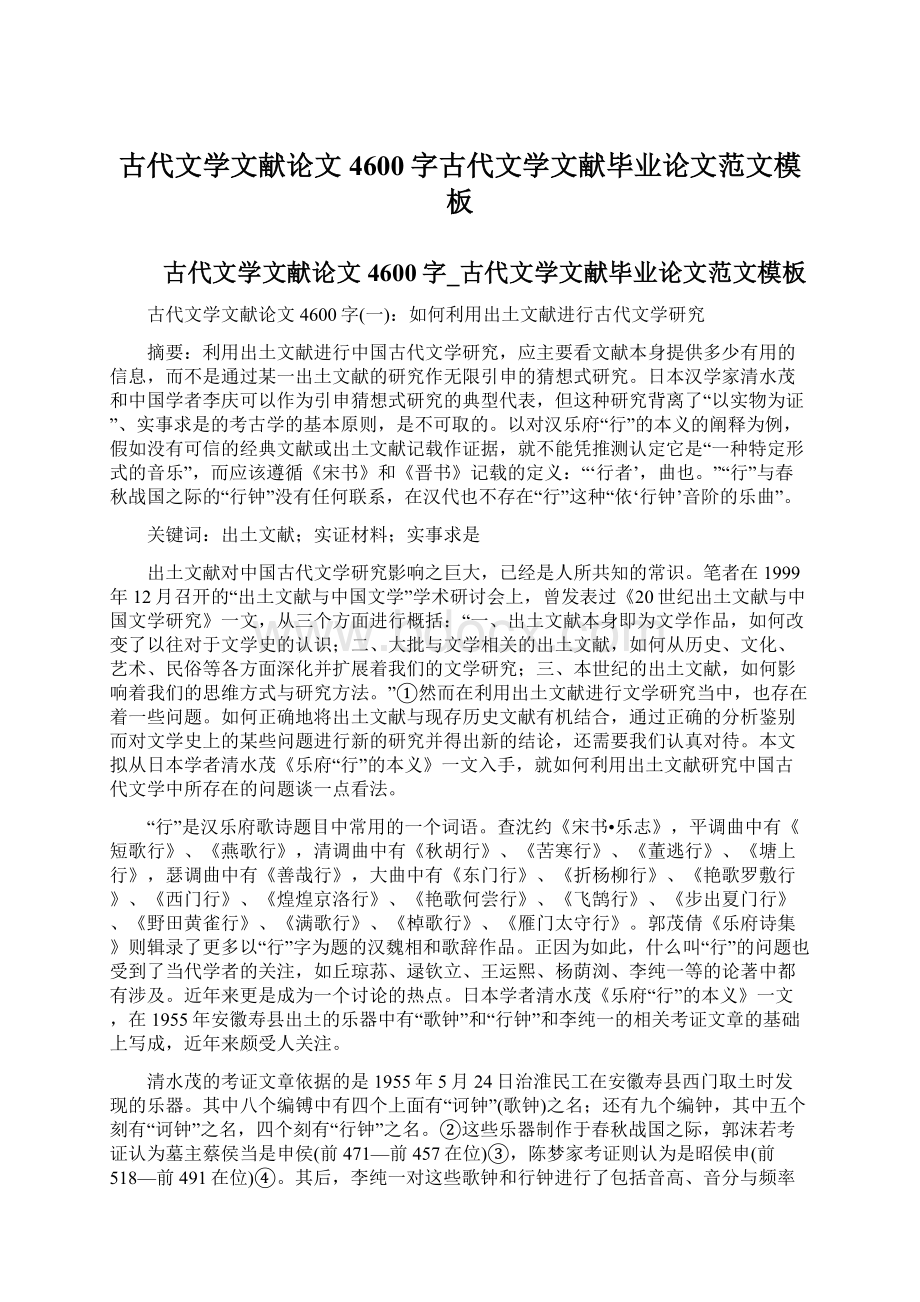
古代文学文献论文4600字古代文学文献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古代文学文献论文4600字_古代文学文献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古代文学文献论文4600字
(一):
如何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利用出土文献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主要看文献本身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而不是通过某一出土文献的研究作无限引申的猜想式研究。
日本汉学家清水茂和中国学者李庆可以作为引申猜想式研究的典型代表,但这种研究背离了“以实物为证”、实事求是的考古学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取的。
以对汉乐府“行”的本义的阐释为例,假如没有可信的经典文献或出土文献记载作证据,就不能凭推测认定它是“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而应该遵循《宋书》和《晋书》记载的定义:
“‘行者’,曲也。
”“行”与春秋战国之际的“行钟”没有任何联系,在汉代也不存在“行”这种“依‘行钟’音阶的乐曲”。
关键词:
出土文献;实证材料;实事求是
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影响之巨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笔者在1999年12月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曾发表过《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如何改变了以往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二、大批与文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如何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深化并扩展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三、本世纪的出土文献,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①然而在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文学研究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何正确地将出土文献与现存历史文献有机结合,通过正确的分析鉴别而对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进行新的研究并得出新的结论,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本文拟从日本学者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一文入手,就如何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行”是汉乐府歌诗题目中常用的一个词语。
查沈约《宋书•乐志》,平调曲中有《短歌行》、《燕歌行》,清调曲中有《秋胡行》、《苦寒行》、《董逃行》、《塘上行》,瑟调曲中有《善哉行》,大曲中有《东门行》、《折杨柳行》、《艳歌罗敷行》、《西门行》、《煌煌京洛行》、《艳歌何尝行》、《飞鹄行》、《步出夏门行》、《野田黄雀行》、《满歌行》、《棹歌行》、《雁门太守行》。
郭茂倩《乐府诗集》则辑录了更多以“行”字为题的汉魏相和歌辞作品。
正因为如此,什么叫“行”的问题也受到了当代学者的关注,如丘琼荪、逯钦立、王运熙、杨荫浏、李纯一等的论著中都有涉及。
近年来更是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
日本学者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一文,在1955年安徽寿县出土的乐器中有“歌钟”和“行钟”和李纯一的相关考证文章的基础上写成,近年来颇受人关注。
清水茂的考证文章依据的是1955年5月24日治淮民工在安徽寿县西门取土时发现的乐器。
其中八个编镈中有四个上面有“诃钟”(歌钟)之名;还有九个编钟,其中五个刻有“诃钟”之名,四个刻有“行钟”之名。
②这些乐器制作于春秋战国之际,郭沫若考证认为墓主蔡侯当是申侯(前471—前457在位)③,陈梦家考证则认为是昭侯申(前518—前491在位)④。
其后,李纯一对这些歌钟和行钟进行了包括音高、音分与频率三个方面的测音,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它们的音乐性能进行了详细研究,最后他说:
“总上所述,暂可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
春秋战国时期的歌钟与行钟的区别不仅在于应用场合之不同,还在于定音和组合的差异。
即:
歌钟用于上层贵族日常燕飨之时,所以它是按照一个完整音阶(或调式)而定音而组合;行钟为上层贵族巡狩征行时所用,因而它的定音和组合是以一个音阶(或调式)的骨干音为根据。
当然,由于目前所能依据的资料十分有限,所以这个初步结论正确与否,还有待于将来新的考古发现和更多的测音结果来检验。
”⑤可见,李纯一虽然对出土歌钟、行钟进行了测音研究,但是,关于这些歌钟和行钟的具体用途以及何以被称之为“歌钟”和“行钟”的问题,因文献资料所限,他只是得出了一个推断性的结论而已。
至于其音高、音阶等之所以会与宴会所用歌钟有差别,则完全是“为了适应出征出行的条件和要求而使然”(李纯一语),并不是一种音乐类型得以命名的原则。
更何况,这些乐器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也不可能与汉乐府的“歌行”发生联系。
但是李纯一的研究却激发了清水茂的联想。
按清水茂的说法,“李纯一论文并没有把这里的‘歌钟’、‘行钟’与乐府的‘歌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但我们却可以由此进一步推论:
依‘歌钟’音阶的乐曲是‘歌’,依‘行钟’音阶的乐曲是‘行’”⑥。
而支持清水茂作出这种联想的根据,则完全是他自己的推测:
我们可以推测,在使用编钟演奏的音乐中,其他乐器也可能同时被使用,但在演奏时,如果使用歌钟,就按歌钟音阶演奏,如果使用行钟,则依行钟音阶演奏。
这样,按歌钟音阶演奏的乐曲,因其具有完整的音阶,就被题名作“歌”,或者不作特别命名;与之相对,用于旅行的音乐,即依行钟简单的大音程跳跃的音阶演奏的乐曲,因其具有旅行音乐的意味,而被题名作“行”,或即使乐曲并非用于旅行,但“行”的名称照样保留了下来。
众所周知,音乐中有不使用某些音阶的乐曲,这就是与西洋音乐的七音阶相对的东方音乐的所谓“4、7不用”的五音阶。
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推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曾经有过一种与五音阶旋律相对的、极其简单的三音阶旋律。
⑦
分析上文我们会发现,清水茂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并没有建立在李纯一关于行钟测音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李纯一关于行钟“可能是因为这些乐器用于贵族们的出行才名之为‘行’”这一推测的基础上。
然而,李纯一的推测是有实物考证为根据的,而清水茂的推论却完全没有汉代出土文献与相关历史记载的支持,成为纯粹的空想。
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汉乐府中的“行”是按照行钟的音阶来演奏,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汉乐府歌行用的是“极其简单的三音阶旋律”。
这种通过某一出土文献的研究而做无限引申的猜想式研究,已经背离了“以实物为证”的实事求是的考古学的基本原则。
可能是由于这种想象过于大胆,所以清水茂在文章中给自己留下了余地。
他说:
“这种三音阶的乐曲,即使依李纯一氏的推测,也仅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与东汉以后出现的乐府诗能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似有疑问。
从战国至汉代的二三百年间,这种三音阶的旋律是否继续留存,因‘文献不足征’,现在只能试作推测。
”在文章的最后他又说:
“本文虽然推测颇多,求证不足,但探求‘行’为‘曲’之本源,与历来的解释相比,可能性似乎较大,故试作假说,以求教高明。
”⑧正是由于清水茂在自感证据不足却又充满自信的这篇文章的引发之下,李庆发表长文支持清水茂的观点。
文章对《乐府诗集》中凡是标有“行”的题目都作了搜集,并且进行了分析,同时又引用了大量的汉代文献来试图证明汉代存在着和先秦行乐相关联的“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
他最后的结论是:
“总而言之,歌行之‘行’,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一种在古代祭祀、宴乐、出行等仪式时演奏的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
‘行’,和歌、引、弄、操、吟、拍等的乐曲,在音阶、使用的乐器,在运用的场合、范围,在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表现形态,都有明显的不同。
随着礼乐制度的变更,到了魏晋时代以后,经一些文人改编的歌行之‘行’,除了音乐之外,还指和这种音乐相对应的诗歌作品。
”⑨但是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李庆的长文里,除了引用李纯一的考证结果之外,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例标有“行钟”字样的出土文献,也没有任何现存纸本文献可以直接证明“行”是“一种在古代祭祀、宴乐、出行等仪式时演奏的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
我们考察现存有关汉代歌诗演唱的记录,都没有发现标有“行”字题的作品之演唱与“行钟”之间有任何关系的直接记载。
反之,我们却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来反驳李庆的观点。
首先是关于相和歌的性质,沈约《宋书•乐志》说:
“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
”郭茂倩《乐府诗集》综合汉魏六朝诸多文献所作的关于相和歌清、平、瑟、楚各调和大曲的解题,详细记载了这些相和歌曲在演奏时所用的笙、笛、篪、筑、琴、瑟、琵琶、筝等各种乐器和演奏方法,不要说没有说到“行钟”,连“钟”都没有提到。
这说明相和歌的特点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其演出根本就不可能用“钟”这种乐器。
其次是关于相和歌的起源,《宋书•乐志》说得很清楚:
“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
”《晋书•乐志》也有同样的说法。
可见相和歌最早的起源当在汉代的街陌谣讴,这与李庆所引录的祭祀四方山川、食举宴乐、君王出行的有关记载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能不对李庆的这一研究结果表示怀疑。
退一步讲,假设汉乐府中“行”的演唱虽然没有用“行钟”类乐器,虽然汉乐府相和歌最初属于“街陌谣讴”,是否仍然会受汉代祭祀燕飨出行之乐的影响,仍然有依“行钟”的音阶来演唱的可能呢?
李庆同样也拿不出出土文献的证据。
反之,我们考察有关汉乐府相和诸调演唱的文献记载,发现只有“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等说法,也没有发现其音阶与“行钟”有关的记载。
《乐府诗集》引《唐?
书•?
乐志》曰:
“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
又有楚调、侧调。
楚调者,汉房中乐也。
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
侧调者,生於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
”《魏书•乐志》载陈仲儒论乐:
“其瑟调以角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宫为主。
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
”以此而言,汉魏六朝清商三调的演奏,并不是以所谓的行钟的“音阶”来进行的。
关于清商三调的音律和调式问题,杨荫浏、冯洁轩等人有过很好的探讨。
⑩所以,无论是李庆的说法还是清水茂的说法,都是与汉魏六朝有关相和歌诗的记载相背离的,因而他们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其实,关于汉乐府中“行”的问题本来很简单,前人已经有过比较简明的解释:
“行”即“曲”也。
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
‘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
’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
”司马贞《索引》:
“乐府《长歌行》、《短歌行》,行者,曲也。
此言‘鼓一再行’,谓一两曲。
”《汉书•司马相如传》:
“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
‘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
’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
”颜师古注:
“行为曲引也。
古乐府《长歌行》、《短歌行》,此其义也。
”又如《文选•饮马长城窟行》李善注:
“《音义》曰:
行,曲也。
”再如《尔雅•释乐》“徒鼓瑟谓之步,徒吹谓之和,徒歌谓之谣。
”郝懿行疏:
“步犹行也。
”可见,乐府诗中的“行”即“曲”,唐以前人无异议。
而清水茂却根据“为鼓一再行”这句话的句法结构,认为“再”是副词,不应该用在名词之前,所以这句话里的“行”应该是动词,自然也就不应该解释为有名词意义的“曲”。
其实,“再”在古代,它的最初意义恰恰是量词,表示第二次的意思。
《玉篇•冓部》:
“再,两也。
”《史记•苏秦列传》:
“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
”所以,《史记》和《汉书》的表述没有问题,司马贞把它解释为“一两曲”也是正确的。
“行”的意义就是“曲”,那么汉乐府清平瑟调与大曲歌辞中有标有“行”字,就可以有很简单的解释,《长歌行》就是“长歌曲”,《猛虎行》就是“猛虎曲”,《东门行》就是“东门曲”,以此类推,本无深义。
它与春秋战国之际的“行钟”没有任何联系,在汉代也不存在“行”这种“依‘行钟’音阶的乐曲”。
在此,我们还要解释清水茂和李庆等人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在汉代歌诗作品里,主要在平调、清调、瑟调、楚调和大曲中的歌辞题目中标有“行”字呢?
逯钦立有一句话富有启发性,他讲:
“我们试从现存的‘相和歌辞’看,凡是‘相和歌’本身不分解,都不叫‘行’。
”(11)的确,如果我们考察《宋书•乐志》,会发现“相和”下面各首歌的题目中均无“行”字,各诗中也没有“解”,而平调、清调、瑟调和大曲下面各首歌的题目上都有“行”字,各诗又全部都有“解”,少则两解,多则八解。
因此我认为,汉乐府相和诸调歌诗中之所以标有“行”字,最初只是为了区分相和曲与清、平、瑟、楚诸调以及大曲的区别。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平、瑟、楚诸调曲和大曲的歌辞大多数都在二解以上,因而才把这些没有“解”的歌曲称之为“行”。
当然,歌辞分解,也就是歌曲分章;歌辞分几解,曲调也就重复几遍,重复乃是其应有之义。
这也正是这些清、平、楚、瑟和大曲在标题上加一“行”字以标示其与相和曲不同的原因。
顺便提一句,李庆在统计《乐府诗集》中标有“行”字的作品时,把从汉到魏的所有作品一样看待,这种做法也有问题。
其实,魏晋以后许多标有“行”字的作品已经属于文人的拟作,它们根本就不入乐,只是沿袭了乐府旧题。
这对于弄清“行”字本义没有帮助,反而容易把问题混淆。
作为现存汉乐府歌诗,最早最可靠的文献记载就是《宋书•乐志》。
其中所辑录的相和曲标题均没有“行”字,而自平调曲以下诸调曲则全有“行”字,并且每一首歌辞都有“解”字。
这正证明了汉乐府相和诸调发展的历史——它由最初不分“解”的相和曲,发展到可以分“解”的平、清、瑟、楚诸调,再发展到前有“艳”曲、后有“趋”与“乱”的大曲,其艺术形式在不断发展。
同时,这些标有“行”字题目的乐府歌诗也代表了汉代歌诗艺术表现的最高形式,所以后人便把由此引申而来的乐府体诗歌也称之为“歌行”,从而成为一种由此而演化出的一种新诗体即“歌行体”的名称。
以上,我们由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一文说起,不但是为了辨析汉乐府“行”的本义,而且想要说明的是:
利用出土文献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要看出土文献本身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而不能把它的文献价值无限扩大,企图解决所有与之相关甚至毫无关系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看重出土文献的价值,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实证材料。
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可能就会变成谬误,因为它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
古代文学文献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二):
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文献”有广、狭义。
广义的“文献”,包括一切知识的载体;狭义的文献,仅指那些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包括地下出土文物上面的文字资料。
我们这里所说的“佛教文献”,主要指佛教各种的藏经和续藏经中的佛典文献,当然也包括敦煌等出土文书中的佛教资料。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除了有自己的经典之外,还包括各种宗教体验、宗教仪规和宗教活动及其活动场所和法器等。
但是,我们今天考察中国古代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主要只能借助现存的佛教文献和文学文献来进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问题;研究“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就是研究“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本身。
近代以来,将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很多,而且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
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郑振铎、季羡林、金克木等老一辈学者,是本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他们的成就令人高山仰止。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学者,其学术的素养虽难以与前辈比肩,但他们各有独特的视野,陈允吉、孙昌武、项楚等人是其代表。
此后,在老一辈学者的启发和带领下,加之日趋自由的学术空气,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该研究领域,而且做了可喜的学术尝试。
在海外,日本学者加定哲地在深浦正文、小野玄妙等人“佛教文学”概念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佛教文学”的范畴。
加定哲地的《中国佛教文学》一书,实际上是将“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更加明晰化了。
因为其中所说“中国佛教文学”的内容,除了“佛典的翻译”之外,主要指中国古代正统文学中的“佛教文学”和俗文学中的“佛教文学”,以及一些佛教僧侣的诗偈创作,而并不包括佛教中的文学性经典或佛教经典的文学性问题。
欧美的学者,则多在“敦煌学”的框架内讨论佛教与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关系,尤其重视对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佛教源头的探讨,如美籍学者梅维恒(Victor.H.Meir)和梅祖麟(Tsu-LinMei)合著的长篇论文《论近体诗的梵文来源》,即是其中一例。
港台学者对佛教文献中的禅诗、变文有较多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结合佛经和敦煌文献,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理论问题做出了全新的阐释,成绩斐然。
综合考察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我认为佛教经典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佛经中的内容、观念渗透到了中国古代文学领域,被中国文学广泛地采用
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题材内容及思想观念的渗透,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小说、诗歌、戏曲及俗文学等许多方面。
中国古代小说的许多情节都取材于佛经,如六朝“志怪小说”刘义庆《宣验记》中的“鹦鹉灭火”的故事、吴均《续齐谐记》中的“阳羡笼鹅”的故事,唐代传奇小说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沈既济的《枕中记》、陈立佑的《离魂记》、张荐的《灵怪录》、李亢的《独异志》、戴君孚的《广异记》等,一直到著名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及其孙悟空的形象和孙悟空与妖怪斗法的情节等,都取材于佛教的经典。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谈六朝小说发达的原因时说:
“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的输入。
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神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
”季羡林先生也说:
“唐代的传奇文虽然从主要方面来说继承和发扬的仍然是六朝以来的中国固有的传统,但是印度的影响却到处可见。
上面谈到的阴司地狱和因果报应仍然继续存在。
此外还添了许多新的从印度来的东西,其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龙王和龙女的故事”,因为“佛教传入以后,‘龙’的涵义变了”。
在诗歌方面,佛教文献对中国诗歌题材内容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催生了六朝的“宫体诗”。
佛教为了破除色欲,阐明色相性空的核心观念,在佛经中有大量描写色相、点明其“性空”本质的内容。
如当时汉译的佛典《法句譬喻经》、《佛本行经》、《普曜经》、《六度集经》等,即多有这方面的内容。
佛教文献的这种观念,首先影响到一批佛教僧侣文人,他们开始创作一些内容淫艳的诗歌,如齐梁时期的释惠休、释道猷、释宝月等人,再继而进一步影响齐梁奉佛佞佛的帝王大臣如萧子良、萧衍、萧纲、萧绎、徐陵、庾肩吾君臣父子,遂形成了所谓的“宫体诗”。
《南史·简文帝纪》云:
“帝辞藻艳发,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
”同书《徐搞传》曰:
“(搞)属文好为新变,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始。
”说的都是这一史实。
在戏曲方面。
近代的许地山和郑振铎等学者既已明确宣称中国的戏曲“完全是由印度传人的”,而事实上,不仅许多中国古代的戏曲,如元杂剧中尚仲贤的《张羽煮海》和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其渊源在于《佛本行集经》、《生经》、《摩诃僧祗律》等佛教文献,而且中国戏曲兴盛的元明时期的许多作家,如写过《半夜雷轰荐福碑》的马致远、明代著名的剧作家汤显祖、沈璟、高明诚,一直到清代名剧《长生殿》的作者洪舁,他们的剧作有的取材于佛经故事,有的在作品中充满了佛经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的思想观念,都直接表明他们受到了佛教经典的深刻影响。
此外,中国古代的散文,特别是其中的议论文,不仅许多的论题,如“神”的是否消灭的问题、“三世”的有无问题、“真空”的关系问题等,皆源于佛典或援引佛典以为论据,而且其辩论的方法,乃至行文的方式,都有很多地方是吸取于佛教文献的。
如宗炳《明佛论》、刘勰《灭惑论》对佛教观点的阐发,韩愈的《原道》、李翱的《复性》分析“道”、“性”、“情”等概念的方法,就实际都是取于佛教经论的。
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学题材内容的重要影响。
二、佛教文献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影响,一是反映在其关于文学的形、神、言、意关系上,二是表现在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特有“境界说”(意境说)上。
中国古代文学中原来也有“言意”、“形神”概念。
《周易-系辞上》曰:
“子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意,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庄子》曰: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秋水》)又说: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这是在讨论“言意”关系,其基本精神是将“言”视为达“意”的工具,而且认为“言”并不能真正达“意”。
对于“形神”范畴,《周易·系辞上》云:
“阴阳不测之谓神。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
”《庄子·天道》云:
“水静犹明,而况精神?
”《庄子·知北游》云:
“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
”《管子·内业》云:
“神也者,气之精者也。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这些言论,主要是把“神”视为人之精神,视为某种“精气”,而形则是一种“粗气”。
佛教的各部派、各宗派对于人(形)轮回的精神主体的看法并不一致,但犊子系的《三法度论》(即《四阿含暮钤解》)则主张有“我”,而且不是“假有”而是“胜义有”(“胜义我”)。
此经翻译到中土之后,道安、鸠摩罗什、慧远、僧睿等人都接受了这一观念。
“形尽神不灭”的观点开始在中土流行。
此后的佛教经典如《涅椠经》、《华严经》等又提出了由具体的事象、到各个幻相、再到实相,这样一种由事物的现象探讨其本质的思维方法,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现象(形)和本质(神)之间的辨证关系。
佛教经典认为:
“有无一切世间法,了达悉如幻。
”但佛陀常以方便说法,让众生“悉令得解真实谛”(《华严经·十忍品》、《贤首菩萨品》)。
《大般涅槃经·菩萨品》也说:
“诸佛如来,亦复如是,随诸众生种种音声而为说法。
为令安住佛正法故,随所应见而示现种种形象。
”佛教文献对“形神”关系的理解,超出了中土固有的认识论,而文人学士也因此对文艺中的“形神”关系的论述达到了一种新的历史高度,并开启了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神轻形、“传神写照”的理论。
如果说顾恺之的“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世说新语·文学》),反映了某种重“神”轻“形”的理论倾向的话;那么,沈约所谓“夫理贵空寂,虽熔范不能传;业动因应,非形相无以感”(《重答李交州书》),则已比较全面地说明了“理”(“神”)与“形相”之间相依相对的关系。
中国的文学理论史上也因而形成了整套“以形写神”的思想理论。
佛经《大智度论》认为:
“一切法实性,皆过心、心数法,出名字语言道。
”故《光赞般若经》又说:
“诸佛之法,亦无实字,但假号耳。
”但这并不等于说佛教也像老、庄那样幻想“处默”、“无言”;相反,佛教总是同时又强调语言的作用:
“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是般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语言能持义亦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是般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语言能持义亦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受佛教文献中这种“言意”观的影响,佛教信徒中的文士首先对文学理论中的“言意”关系做了重新思考。
僧肇曰:
“经云般若义者无名无说。
……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
是以圣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
”(《般若无知论》)僧佑说: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
”(《出三藏记集》卷一)慧皎说:
“借微言以津道,托形象以传真。
”(《高僧传·义解论》)而南朝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由此认为文学创作中的“言意”关系为: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但文学创作的目标又要超越“言”、“文”的逻辑关系,求得“以少总多”。
因此,他提出了“隐秀”的范畴:
“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即文学创作一定要借文字来传意,而且要尽可能选择适应的“辞”来传“意”,但更高的追求则是作品具有“言外之意”,“象外之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言有尽而意无穷”。
佛教文献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促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境界说”或“意境”理论。
佛教瑜伽派的经典把色、声、香、味、触、法叫作“六境”或“六尘”,加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和“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叫“十八界”,统称为“境界”。
如佛教唯识宗经典认为,一切“外境”都是由“内识”转变,故称为“皆有内识,无有境界”(《摄大乘论本》卷二)。
随着唐代佛教唯识宗的传播,唐代诗论家们也开始引入“境界”理论。
释皎然的《诗式》卷一曰:
“夫诗人之诗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逸。
”吕温曰:
“研情比象,造境皆会。
”(《联句诗序》)权德舆则说:
“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
疏导情性,含写飞动,得之于静,故所趣皆远。
”(《左武卫胄曹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