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话语与五四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分析.docx
《民间话语与五四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民间话语与五四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分析.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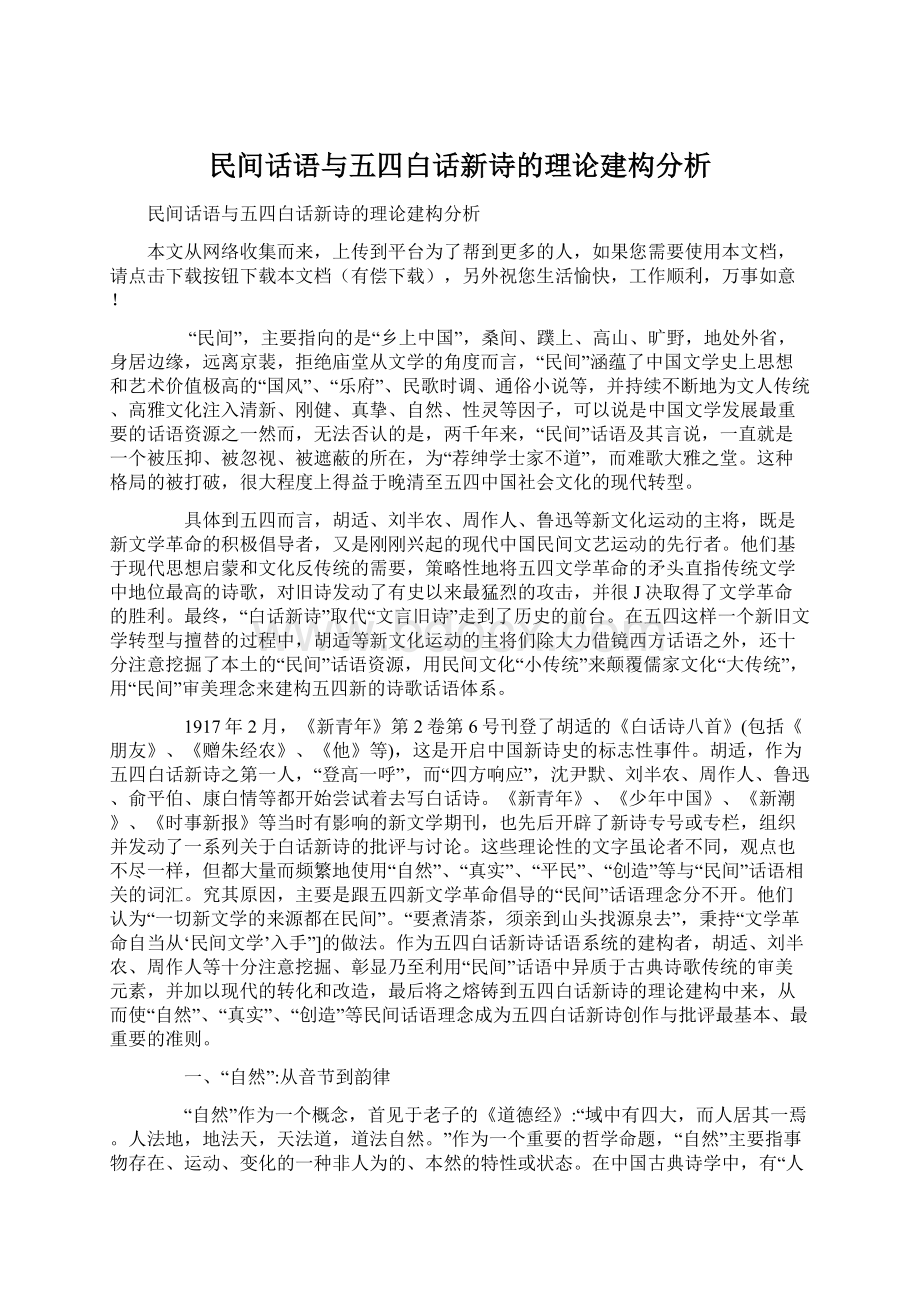
民间话语与五四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分析
民间话语与五四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分析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民间”,主要指向的是“乡上中国”,桑间、蹼上、高山、旷野,地处外省,身居边缘,远离京裴,拒绝庙堂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民间”涵蕴了中国文学史上思想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国风”、“乐府”、民歌时调、通俗小说等,并持续不断地为文人传统、高雅文化注入清新、刚健、真挚、自然、性灵等因子,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话语资源之一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两千年来,“民间”话语及其言说,一直就是一个被压抑、被忽视、被遮蔽的所在,为“荐绅学士家不道”,而难歌大雅之堂。
这种格局的被打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晚清至五四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
具体到五四而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既是新文学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又是刚刚兴起的现代中国民间文艺运动的先行者。
他们基于现代思想启蒙和文化反传统的需要,策略性地将五四文学革命的矛头直指传统文学中地位最高的诗歌,对旧诗发动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攻击,并很J决取得了文学革命的胜利。
最终,“白话新诗”取代“文言旧诗”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在五四这样一个新旧文学转型与擅替的过程中,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除大力借镜西方话语之外,还十分注意挖掘了本土的“民间”话语资源,用民间文化“小传统”来颠覆儒家文化“大传统”,用“民间”审美理念来建构五四新的诗歌话语体系。
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刊登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包括《朋友》、《赠朱经农》、《他》等),这是开启中国新诗史的标志性事件。
胡适,作为五四白话新诗之第一人,“登高一呼”,而“四方响应”,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鲁迅、俞平伯、康白情等都开始尝试着去写白话诗。
《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时事新报》等当时有影响的新文学期刊,也先后开辟了新诗专号或专栏,组织并发动了一系列关于白话新诗的批评与讨论。
这些理论性的文字虽论者不同,观点也不尽一样,但都大量而频繁地使用“自然”、“真实”、“平民”、“创造”等与“民间”话语相关的词汇。
究其原因,主要是跟五四新文学革命倡导的“民间”话语理念分不开。
他们认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
“要煮清茶,须亲到山头找源泉去”,秉持“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的做法。
作为五四白话新诗话语系统的建构者,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十分注意挖掘、彰显乃至利用“民间”话语中异质于古典诗歌传统的审美元素,并加以现代的转化和改造,最后将之熔铸到五四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中来,从而使“自然”、“真实”、“创造”等民间话语理念成为五四白话新诗创作与批评最基本、最重要的准则。
一、“自然”:
从音节到韵律
“自然”作为一个概念,首见于老子的《道德经》: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自然”主要指事物存在、运动、变化的一种非人为的、本然的特性或状态。
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有“人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翩《文心雕龙》“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梦阳《诗集自序沁等说法,还有一批推崇“自然”的诗人,如陶渊明、李白、王维、韦应物等。
“自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学最为重要的创作理念与批评原则。
近人王国维主张“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人间词话》,更是将“自然”视为文学扎匕评的最高境界之一。
在西方,特别是在标举“回归自然”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中,“自然”与“人性”、“天才”、“创造”等同,被视为现代诗学“反传统”、“反理性主义”的一面旗帜。
在谈及浪漫主义崇尚“自然”这一命题时,谁也不能否认其与民间话语的联系。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之于拍西,德国的狂飘突进运动之于赫尔德、格林兄弟,已是文学史的共识。
然而,这样一种以“自然”为中心的美学境界和诗学追求,却在晚近中国雕琢文饰的“文人之诗”中几乎消亡殆尽。
要改变这种局面,则只可回归自然,返求之于“民间”。
1919年10月10日,胡适在《星期评论》的“双十节纪念专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谈新诗》的文章,文中胡适将新诗作为辛亥革命“八年来的一件大事”来看待。
此时,胡适的文学思想,已从五四文学革命初期的“破”转到了新文学建设的“立”上来,重点思考的是如何用“白话”这种民间的语言形式来创造一种“国语的韵文”—“新诗”。
在这篇理论性的文字中,“自然”一词反复地出现,频率极高地被使用。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自然”是胡适白话新诗理论最重要的“关键词”。
胡适认为:
五四所倡导的白话新诗是第四次诗体的大解放,是诗歌发展的“自然”趋势和“自然”演进的结果。
“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
胡适这里所说的“自然”,其实就是“进化”论的哲学观在文学上的表现。
通过”自然”(“进化”论)的文学观,白话新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合法性地位就被确立起来。
五四白话新诗的音节应该是“自然的音节”。
“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
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的自然和谐。
在这里,胡适跳出了传统诗歌音节的外部律,而强调新诗的创作要注重“研究内部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和谐”的“自然的音节”来。
在此之前,胡适就强调,白话新诗创作要真正做到“诗体的大解放”,就得遵循“自然”的审美原则:
“若要作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
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
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
《谈新诗》发表之后,胡适的这篇文章被大量转载和引用,被视为五四白话新诗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
胡适的后来者们更是将“自然”(或相近的“天然”、“自由”、“谐和”等)视为五四白话新诗最高的美学原则和不二的诗学理想。
如,俞平伯认为,“原始的诗,—诗底素质—莫不发乎天籁,无所为而然的”日;宗白华认为,“新诗的创造,是用自然的形式,自然的音节,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等。
诗人康白情在谈及五四新诗时,认为新诗应“排除格律,只要自然的音节”。
何谓“自然的音节”?
康白情指出:
“情发于声,因情的作用起了感兴,而其声自成文采。
看感兴底深浅而定文采底丰歉。
这种的文采就是自然的音节。
他还将“自然的音节”与诗人更内在的“感兴”联系起来:
“我们底感兴到了极深底时候,所发自然的音节也极谐和,其轻重缓急抑扬顿挫无不中乎自然地律吕。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莫知其然而然的。
无韵的韵比有韵的韵还要动人。
……感情内动,必是曲折起伏,继续不断的。
他有自然的法则,所以发而为声成自然的节奏;他底进行有自然的步骤,所以其声底经过也有自然的谐和。
康白情进一步指出:
“诗要写,不要做;因为做足以伤自然的美。
……总之,新诗里音节底整理,总以读来爽口,听来爽耳为标准。
正是鉴于康白情关于“自然”的有关论述,胡适在《尝试集》再版时,将新诗的“自然的音节”论予以发展,阐释为:
“凡能充分表现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诗的最好音节’,古人叫做‘天籁’的,译成白话,便是‘自然的音节’。
按照这样一个再界定,胡适认为自己《尝试集》中只有《老鸦》、《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应该》等十四篇才是真正意义的“白话新诗”。
至此,胡适关于白话新诗“自然的音节”的理论才最终定型,其侧重点也从最初的“诗体”过渡到此时的“诗意”,并成为早期白话新诗“自然”论的阶段性成果。
二、“真实”:
个性之真与社会之实
与五四白话新诗的“自然”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五四白话新诗的“真实”论。
“真”作为一个概念,始于道家,指事物及人的本质、本相、本色。
儒家则以“诚”为“真”,重点指向人的天赋本性,一种自然而又真实的存在状态。
庄子首次将“真”引入文艺美学领域—“真在内者,神动于外”《庄子杂篇渔父》,司空图亦标举诗之“真体”、“真力”、“真迹”,晚明诗人提出“真人”、“真性”、“真诗”之说,从而形成了“真”在中国诗学中独特的审美地位。
在五四白话新诗的倡导期,“真”这一诗学的本体范畴被重新发掘出来。
“人言山惟草树与泉石,未加雕饰何新奇?
我言,草香树色冷泉丑石都自有真趣,妙处恰如白话诗”—沈兼士的这首题为《真》的白话诗,今天读来虽相当瞥脚,却真实地表达出了五四初期白话新诗向民间“真”诗靠拢的美学追求。
作为五四文学革命“闯将”的刘半农,是一个对“真”情有独钟的诗人。
他曾讲:
我爱看的是真山真水,无论是江南的绿畴烟雨,是燕北的古道荒村,在我看来是一样的美,只是色彩不同罢了。
至于假山假水,无论做得如何工致,我看了总觉得不过尔尔。
半农认为:
“作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
为此,他痛斥古代那些所谓的诗人“灵魂中本没有一个‘真’字,又不能在自然界及社会现象中,放些本领去探出一个‘真’字来,却看得人家作诗,眼红手痒,也想勉强胡诌几句,自附风雅。
于是,真诗亡而假诗出现于世”。
在这里,刘半农极为看重诗人思想之“真”和性情之“真”,视“真”为诗歌最高的美学追求:
“《国风》是中国最真的诗,—《变雅》亦可勉强算得—以其能为野老征夫游女怨妇写照,描摹得十分真切也。
后来只有陶渊明、白香山二人,可算是真正诗家。
以老陶能于自然界中见到真处,老白能于社会现象中见到真处。
他认为孔子以“思无邪”的眼光来删诗,“简直是中国文学上最大的罪人了”。
刘半农的新诗“真实”论,显然是受到了晚明“真诗在民间”理念的影响。
在阳明心学和人欲解放思想的影响下,追求“真性真情”的晚明诗人不满于诗坛的“复古”潮流,将目光普遍转向了“民间”和“底层”,在流行于桑间淮上、勾栏瓦肆的“民歌时调”中发现了“真诗”。
其代表人物冯梦龙认为:
为上层文人所不屑的民歌时调,自然而天成,不虚伪,不矫饰,“乃民间性情之响”,是民间性情的真实表达;文人学子应学习民间诗作的赤子情怀,来“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民间诗歌区别于文人之诗的地方就在一个“真”字上,正所谓“情真乃不可废”。
在冯梦龙民间理念的基础上,刘半农将自己的“真”诗理念分为两个层面:
一为诗人个人思想、情感之“真”;一为自然、社会事实之“真”。
正因为如此,刘半农十分羡慕儿童性情之“真”、“你饿了便啼,饱了便嬉,倦了思眠,冷了索衣。
不饿不冷不思眠,我见你整日笑嘻嘻。
你也有心,只是无牵记;你也有眼耳鼻舌,只未着色声香味;你有你的小灵魂,不登天,也不坠地。
呵呵,我羡你,我羡你,你是天地间的活神仙!
是自然界不加冕的皇帝!
”
五四白话新诗的“真实”论,从古代民间诗学中获得某种启示,并服膺于五四新文学的主旨。
一方面,要求诗人真实地表现个人的思想、灵魂和性情,暗合的是五四对“人”的彰显,即“人的文学”。
如郭沫若所言:
“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心琴上弹出来的,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
另一方面,又要求诗人去观察自然与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活情状,如刘半农要求的“在自然界中见到真处”、“在社会现象中见到真处”,暗合的是五四对“民”的重视,即“平民的文学”。
从以上因素来看,五四白话新诗的“真实”论,就带上了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双重色彩,体现了五四文学启蒙的双重诉求。
“人到世间来,本来是赤裸裸,本来没污浊,却被衣服重重的裹着,这是为什么?
难道清白的身,不好见人吗?
那污浊的,裹着衣服,就算免了耻辱吗”(沈尹默《赤裸裸沁;“我们不过是穷乏的小孩子。
偶然想假装富有,脸便先红了”(郑振铎《赤子之心—赠圣陶沁—这是五四白话新诗追求“个性之真”的两个典型诗例。
此外,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康白情、刘大白等早期白话诗人,在展示自己真实个人性情的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同情,并自觉地配合着五四新诗的社会启蒙诉求。
如胡适、沈尹默的同题新诗《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车毯》《学徒苦》《卖萝卜人》、康白情的《“棒子面”》《先生和听差》、刘大白的《田主来》《卖布谣》等,都充分凸显了五四白话新诗的“平民化”品格和民间现实情怀。
“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
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雕凿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逃遁所,与‘真率’的残害者”—这是《雪朝》诗人的真实心声,也是五四新诗的共同追求。
稍晚于刘半农的俞平伯,对民间“真”诗亦感同身受。
他曾讲:
“我平素很喜欢民歌儿歌这类作品,相信在这里边,虽然没有完备的艺术,却有诗人底真心存在。
他还说过:
“其实歌谣—如农歌,儿歌,民间底艳歌,及杂样的谣谚—便是原始的诗,未曾经‘化装游戏’的诗。
他将刘半农关于新诗的“真实”言论发展为两种信念,提出了新诗创作中的“自由”与“普遍”原则:
“自由”,指向诗人真实的个性:
“我相信诗是个性的自我—个人底心灵底总和—一种在语言文字上的表现,并且没条件没限制的表现”、“普遍”,指向群体和社会:
“诗不但是自感,并且还能感人;一方是把自己底心灵,独立自存的表现出来;一方又要传达我底心灵,到同时同地,以至于不同时不同地人类”、“自由”与“普遍”,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相妨”,两者辩证地统一于“真实”。
郭沫若有一个说法,“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可以看作是“自由”与“普遍”关系的最好注解。
新诗如何达到这样的两个方面的“真实”呢?
五四新诗人认为,首先,有赖于诗人人格的培养,包括诗人创作动机的纯正、自由独立个性的养成、艺术品性的完善等等。
因为诗歌的“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感或态度上的“真”,即“感情的叙述”中的“真”。
“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
‘不失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
其次,还得多多接触真实的自然和社会:
“在自然中活动”,“直接观察自然现象的过程,感受自然的呼吸,窥测自然的神秘,听自然的音调,观自然的图画,……在自然中的活动是养成诗人人格的前提”、“在社会中活动”,“诗人最大的职务就是表写人性与自然。
而人性最真切的表示,莫过于在社会中活动—人性的真相只能在行为中表示—所以诗人要想描写人类人性的真相,最好是自己加入社会活动,直接的内省与外观,以窥看人性纯真的表现”。
这样,五四新诗的“真实”论就将五四时期倡导的个性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有机地统一起来,共同指向五四文学的两大主题—“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
三、“创造”:
新诗的精神端在创造
胡适在写作《白话文学史》时指出:
“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
充分肯定了“民间”之于文学的创造性意义。
郑振铎也曾指出,“创造”是民间的一个重要特质,她“勇于引进新的东西。
凡一切外来的歌调,外来的事物,外来的文体,文人学士们不敢正眼儿窥视之的,民间的作者们却往往是最早的便采用了,便容纳了它来”。
民间由于身处边缘,较少受到文化传统和文学体制的约束,其自由自在的品格决定了民间的主体—民众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去表现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1916年7月22日,胡适创作了新文学史上“第一首白话诗”《答梅勤庄》。
该诗虽是一首“打油”之作,甚至被梅光迪本人讽为“莲花落”,但胡适却不为所动,更加坚定了这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题的尝试精神。
7月26日,他在致任叔永的信中说:
“吾志决矣。
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
;8月4日,更是悲壮地说:
“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能新辟一文学殖民地。
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
然我去志已决。
正是胡适有这种敢于尝试的精神以及放胆创造的勇气,才开创了后来五四新诗乃至整个五四新文学全新的局面。
1920年之前,白话新诗的创作还未能形成气候,理论建设更是相当薄弱。
要彻底改变“旧诗”的统治性地位,巩固白话新诗刚刚收获的一点成果并谋其长远发展,新诗必需得有一种开辟洪荒的“创造”精神。
“好凄冷的风雨啊!
/我们俩紧紧的肩并着肩,手携着手,向着前面的‘不可知’,不住的冲走。
可怜我们全身都已湿透了,而且冰也似的冷了,不冷的只是相并的肩,相携的手”—刘半农的这首《我们俩》,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五四新诗人在困难面前相携作战、共同创造新诗美好未来的决心和想法。
刘半农早在“文学革命”的倡导期,就十分重视从民间汲取营养,敢于引进新的东西。
他曾就“韵文”的改良提出了三点建议:
“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认为新诗应从古风、乐府、方言、戏曲中吸取养分,充分发挥民间资源在新诗建设中的作用。
他曾讲:
“彼汉人既有自造五言诗之本领,唐人既有造七言诗之本领。
吾辈岂无五言七言之外,更造他种诗体之本领耶。
;综观刘半农的新诗创作,其《扬鞭集》、《瓦釜集》中的大部分诗作,均章无定节,节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声,诗歌的语言和体式亦相当的自由与随意。
在谈到自己的新诗创作时,刘半农不无得意地说:
“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
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
;在此,仅以他的《拟儿歌》小作分析:
“羊肉店!
羊肉香丫羊肉店里结着一只大绵羊,抬起头来望望铁勾浪丫羊肉店,羊肉香,邓可大阿二来买羊肉肠,三个铜钱买仔半斤零八两,回家去,你也夺,我也抢气坏仔阿大娘,打断仔阿大老子鸦片枪丫隔壁大娘来劝劝,贴上一根拐老杖。
”这首诗模拟儿歌,用江阴方言创作而成。
刘半农从羊面临被宰害」时“苦恼”的叫声和吃羊肉者的“抢夺”中来赋予寓意,寓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明争暗斗、你抢我夺,以及平民老百姓被宰割的命运和无尽的苦恼。
该诗充分运用民间的语言(江阴方言)、民间的形式(拟儿歌)、民间的手法(政治讽刺)等,实现了对民间歌谣的创造性改造。
刘半农在新诗创作中的这种敢于“增多诗体”、“翻新鲜花样”的创造精神,很大程度上与其重视民间文学的“创造精神”有关。
稍后的康白情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新诗的精神端在创造”,他说:
“与其研究关于作品底空论,宁肯观摩古今真正的作品,而与其观摩别人的作品,又宁肯自己去创造。
新诗底精神端在创造。
我愿世间文学的天才,努力探寻宇宙底奥蕴,创造成些新诗,努力修养,创造自己成一个新诗人!
他还说:
“因袭的,摹仿的,便失掉他底本色了。
康白情的诗歌创作以“剪裁时代的东西,表个人的冲动”为原则,很好地将民间的“创造”精神融注其中。
在“创造”这一点上,康白情可能比同时代的其他诗人走得更远。
他敢于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无益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草儿在前,鞭儿在后。
那喘吁吁的耕牛,正担着犁莺,贴着白眼,带水拖泥,在那里‘一东二冬’的走着”—康白情的这首《草儿在前》将古诗音韵的“一东二冬三江……”融入到新诗诗句中,化为耕牛在泥水中走路的声音“一东二冬”。
这种颇有意思的写法为诗人废名所激赏:
“作者将对于旧诗的怨苦很天真的流露出来了,他不是有意的挖苦,只是一点儿游戏的讽刺,因此见他的一种‘修辞立其诚’,比喊起口号来打倒旧诗有趣多了。
”充分肯定了康白情在新诗创作中的“自由意识”和“创造精神”。
俞平伯在为《草儿》作序时,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
“白情做诗底精神,……就是创造。
他明知创造的未必定好,却始终认定这个方法极为正当,很敢冒险放开手做去。
若这本集子行世,能使这种精神造成一种风气,那才不失他底意义。
……如果但取形式,忘了形式后边底精神,那么辗转摹仿,社会上就万不会有新东西了……我最佩服是他敢于用勇往的精神,一洗千年来诗人底头巾气,脂粉气。
他不怕人家说他也不怕人家骂他荒谬可怜,他依然兴高采烈地直直地去。
因而,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草儿》、《冬夜》等早期诗集跟胡适的《尝试集》一样,其意义和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
从胡适最初的“破”,到后来的“立”,五四白话新诗走过了差不多五六年革路蓝缕的艰难历程。
而其间,新诗的倡导者、创作者、诗论家均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民间”,并发出了“喜欢做诗的,必得到民间去学啊”的真切感言,他们希望从中国一切文化的“源头”—民间来寻得足以供新诗话语体系建设发展需要的本土资源。
俞平伯的弟子吴小如谈到这一点时说:
“在‘五四’时期,当时有些作家写新诗就从民族传统的韵文中去寻‘根’觅‘源’,比如刘半农、康白情的作品基本上就走的这条路。
而为了在国内寻根觅源,又不想走五七言古近体诗的老路,于是很自然、也很容易地就找到了我国民间固有的民谣和山歌。
这就是顾领刚、魏建功诸先生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大量采辑并提倡民谣和山歌的真正背景。
而平伯师最后一本新诗集《忆》,走的也正是继承并发展民谣和山歌的道路。
在五四时期,民间话语在诗歌的语言形式、方法技巧、审美理念、思想情感等层面均给予五四白话新诗以重要的借鉴和支持。
五四新诗将从“民间”那里获取的资源,诸如清新活泼的白话口语、和谐自然的韵律节奏、具体直接的写作手法、自由真挚的个性情感以及开拓创新的精神气质等,与五四文学革命从西方借鉴而来的现代诗学理论相掺和、交蜡,充分地融合、搅拌,初步形成了五四新诗“现代性”的理论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建构下,五四白话新诗才取代传统文言旧诗,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
1920年至1922年间,仅出版的新诗集就达十多种,包括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汪静之的《蕙的风》、湖畔诗社的《湖畔》、朱自清等的《雪朝》等。
这些诗集既有力地回击了守旧人士对于白话新诗的讥讽和攻计,也消除了人们对于新诗能否真正取代旧诗的疑虑,充分展示了五四白话新诗的创作实绩。
1922年1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诗歌刊物《诗》创刊,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中国新诗走过了五四艰难的草创期而迈入到更为坚实的发展进程中。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