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到《鬼子来了》讲解.docx
《从《生存》到《鬼子来了》讲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生存》到《鬼子来了》讲解.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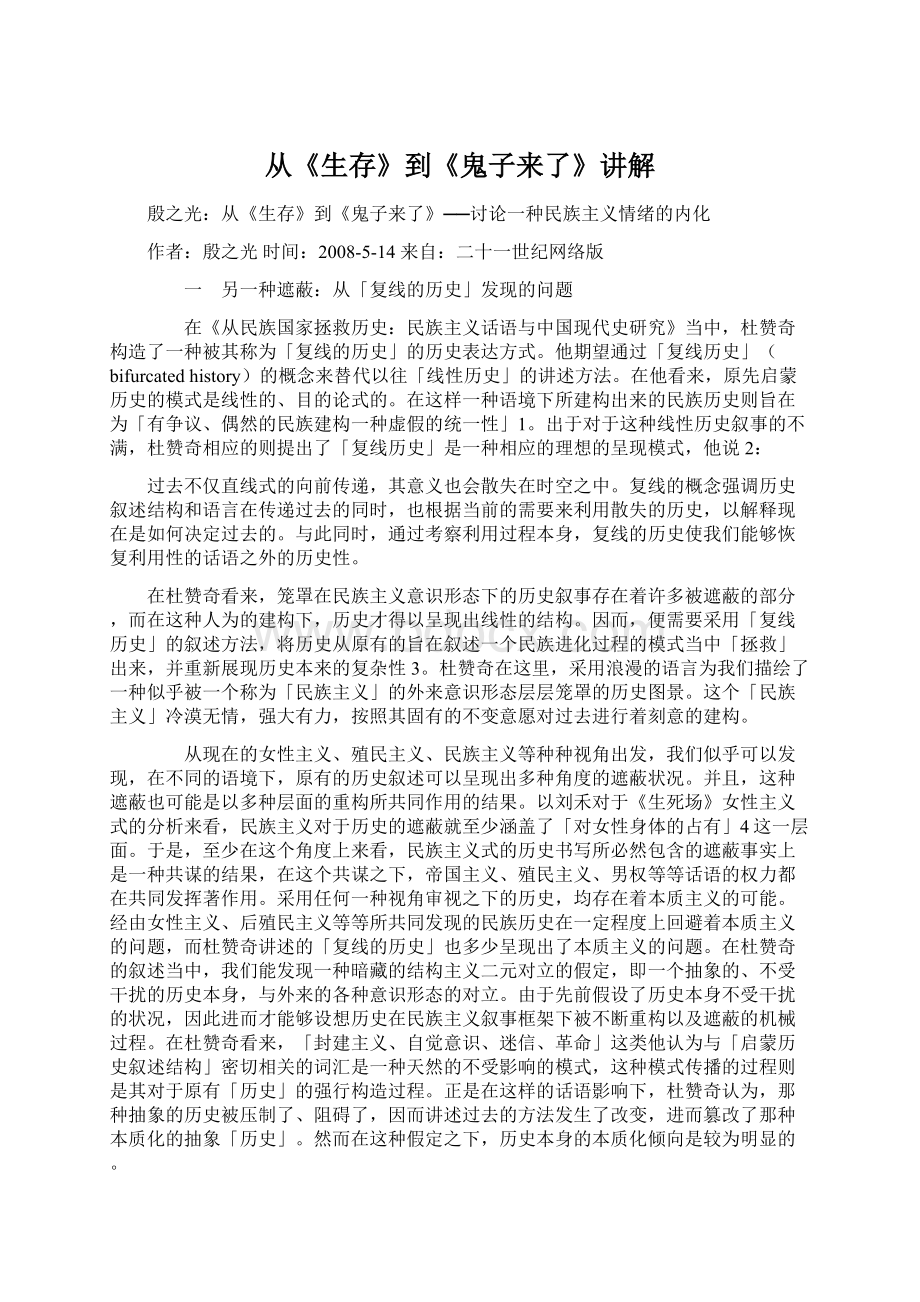
从《生存》到《鬼子来了》讲解
殷之光:
从《生存》到《鬼子来了》──讨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内化
作者:
殷之光时间:
2008-5-14来自: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一 另一种遮蔽:
从「复线的历史」发现的问题
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当中,杜赞奇构造了一种被其称为「复线的历史」的历史表达方式。
他期望通过「复线历史」(bifurcatedhistory)的概念来替代以往「线性历史」的讲述方法。
在他看来,原先启蒙历史的模式是线性的、目的论式的。
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所建构出来的民族历史则旨在为「有争议、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1。
出于对于这种线性历史叙事的不满,杜赞奇相应的则提出了「复线历史」是一种相应的理想的呈现模式,他说2:
过去不仅直线式的向前传递,其意义也会散失在时空之中。
复线的概念强调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以解释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
与此同时,通过考察利用过程本身,复线的历史使我们能够恢复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
在杜赞奇看来,笼罩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历史叙事存在着许多被遮蔽的部分,而在这种人为的建构下,历史才得以呈现出线性的结构。
因而,便需要采用「复线历史」的叙述方法,将历史从原有的旨在叙述一个民族进化过程的模式当中「拯救」出来,并重新展现历史本来的复杂性3。
杜赞奇在这里,采用浪漫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种似乎被一个称为「民族主义」的外来意识形态层层笼罩的历史图景。
这个「民族主义」冷漠无情,强大有力,按照其固有的不变意愿对过去进行着刻意的建构。
从现在的女性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等种种视角出发,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在不同的语境下,原有的历史叙述可以呈现出多种角度的遮蔽状况。
并且,这种遮蔽也可能是以多种层面的重构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刘禾对于《生死场》女性主义式的分析来看,民族主义对于历史的遮蔽就至少涵盖了「对女性身体的占有」4这一层面。
于是,至少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民族主义式的历史书写所必然包含的遮蔽事实上是一种共谋的结果,在这个共谋之下,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男权等等话语的权力都在共同发挥著作用。
采用任何一种视角审视之下的历史,均存在着本质主义的可能。
经由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所共同发现的民族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回避着本质主义的问题,而杜赞奇讲述的「复线的历史」也多少呈现出了本质主义的问题。
在杜赞奇的叙述当中,我们能发现一种暗藏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假定,即一个抽象的、不受干扰的历史本身,与外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
由于先前假设了历史本身不受干扰的状况,因此进而才能够设想历史在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被不断重构以及遮蔽的机械过程。
在杜赞奇看来,「封建主义、自觉意识、迷信、革命」这类他认为与「启蒙历史叙述结构」密切相关的词汇是一种天然的不受影响的模式,这种模式传播的过程则是其对于原有「历史」的强行构造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话语影响下,杜赞奇认为,那种抽象的历史被压制了、阻碍了,因而讲述过去的方法发生了改变,进而篡改了那种本质化的抽象「历史」。
然而在这种假定之下,历史本身的本质化倾向是较为明显的。
毫无疑问,当这一系列词语刚刚进入中国语境的叙述当中时,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是十分明显的,但随着其在中国原有社群当中的流传,这种二元对立则逐渐呈现出互为建构的倾向。
或许民族主义叙事曾经是某种抽象的「中国历史」的绝对的对象,那么,当这种叙事被人们开始讲述并且挪用的时候,它便成为了「他者」而在发挥切实的有机作用了。
事实上,我更加关注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外来物,不断被内化的过程,借用查克拉巴蒂(DipeshChakrabarty)的概念,这样一个过程则可以被表述成为民族主义叙事的「转译」(retranslation)过程5。
如果将这种转译的双方视为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话,那么,在这里,我所关注的这个转译的过程则更大程度上体现在目标语言所在的语境,对于源语言本身的再解释与内化,并随之将这种翻译的过程消解,最终将源语言视为自己语境下自然而然的产物并发挥着文化的作用。
当这样一种转译的过程进行的时候,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二元关系便不那么明确了,而在本文的语境下,则是我们在历史的语境当中,不再那么容易的分辨出来怎样的是民族主义式的叙述模式,怎样是不受民族主义模式的历史叙事。
在《从民族国家发现历史》一书当中,杜赞奇所主要针对的,是民族叙述结构被压制和遮掩的问题6,可以说,在这一点上,这样一种发现是开创性的。
但民族主义叙述在这里相应的却呈现出非历史化的倾向,因此,沿着杜赞奇的思路,我在这里则更加希望讨论一种被历史所重新发现的民族主义叙述模式。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所采用的文本是尤凤伟短篇小说《生存》,以及姜文基于这部小说所改编而成的电影《鬼子来了》。
所选取的两个文本本身都不能被认为是对于「抗日战争」所进行的真正历史学意义上的叙述,因此,两个文本的想象意味则相应被突出,随之所必须负担的「历史真相」的诘问也相应被抽离。
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文本均可以被视为是对于「抗日」的神话式叙述。
无论是尤凤伟还是姜文的叙述,都表现成为一种对于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和时段的想象。
因而,这诸种抗日战争的想象所承载的历史意义是分别作用于它们所处时段的。
并且,我不倾向于单纯讨论《鬼子来了》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对于「抗日」的特别解读方式,我更倾向于将《鬼子来了》与原作小说《生存》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的观察。
无论是《生存》还是《鬼子来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上来看,都并不对于发生于1937-1945年那段时间里作为事件发生过的「抗日战争」发生丝毫的作用,两者都仅仅是站在事件的旁边,而对于「抗日」本身所进行的神话式叙述。
有两种叙述所创造出来的不同神话,仅仅对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间中的民族主义想象具有文化意义。
从《生存》到《鬼子来了》的转变,可以说是「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本身,在两种不同视角审视下、在两个不同时段的转译过程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全然不同的面貌。
二 转型与内化:
两个民族主义文本的分析
(一)民族及其敌人:
一种情绪的形成
关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认同、叙事模式的诞生,经过许多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也已经找到了它作为一种观念的起源。
正如我在前文当中所提及的,杜赞奇对于这样一种单纯追究民族身份认同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的模式提出诘问。
但是,正如他本人也并没有对于这种民族身份认同的起源之初避而不谈一样,关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的起源的讨论,仍旧是提供一种历史语境的必须过程。
在以下的部分当中,我旨在讨论关于民族主义起源及其作用方式的一些共识。
在《想象的共同体》导论之前,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引用了丹尼尔?
笛福(DanielDefoe)《纯正出身的英格兰人》(TheTrue-BornEnglishman)中的一段:
如是从所有人种之混合中起始
那异质之物,英格兰人:
7
在饥渴的强奸之中,愤怒的欲望孕生,
在浓妆的不列颠人和苏格兰人之间:
他们繁衍的后裔迅速学会弯弓射箭
…………
无论怎样,在民族主义认同的内部,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就是一种认同的需要。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共同体毫无目的地被结合到一起。
在大多数民族主义研究者那里,很大程度上,这种认同的基本动力就是在于敌人的存在或者生存的需要。
对于敌人在现代民族主义建构当中的作用,考拉考茨基有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民族主义者想要通过敌对行为和对其他人的仇恨而假定部族的存在,并相信他自己民族所具有的灾难都是外国人侵略的结果8。
在这里,一个基本的共识就在于,抽象的敌人的存在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需要而被想象出来的产物,或许更加确切的说,这里的敌人应当采用一个相对现代一些的字眼来界定,我倾向于采用列维纳斯的「他者」观念,来看待这种认同所产生的基本语境。
安德森极为富有创见的将民族主义揭露为一种「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artefacts)」9在这样的基础上,安德森又指出一系列与现代民族准则有关的民族的有限性、民族所具有的主权等等,均为「想象」的产物。
相应的,在盖尔纳的表述当中,民族主义的形成则更被指责为一种「捏造」和「虚假」10。
虽然这样一种更为激烈的说法被安德森更正成为相对中性的「发明」、「想象」,但是其中所表达出来的某种创造物的倾向仍然是共通的。
无论是盖尔纳还是安德森,还是其它一些民主主义研究者们,都并不否认,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某种「需要」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需要能够令人们所共同崇拜的祖先与模范,同样也需要能够令群体内部所信服的共同的敌人。
而一旦敌人具有了某种公共性之后,其「他者」的特点便被扩大到了可观的地步了。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发现历史》当中提及了在《罗摩衍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邪恶本身被『他者化』」的事实11,以及(《解殖与民族主义》)对于西方世界将伊斯兰国家邪恶化的分析,都很明确的揭示了这样一个建构他者,随之又被他者所建构的过程。
他者在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的过程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恰恰是由于他者本身的特性,在不同需求之下,他者的物质体现相应的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他者不断被发现、被重构的过程在杜赞奇这里,则被视为是民族建构对于历史遮蔽的绝佳体现。
然而,在这种批评之下,被本质化的恰恰是民族主义本身。
由于他者并不是确定的、一成不变的,因此,经由他者而进一步展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也是被重新诠释过的。
怎样一种情感可以被称为是爱国的、民族的边界究竟被划分在哪里、民族的主权究竟应当经由怎样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一系列构成民族主义所必需的元素是随着他者的形象而不断变化的。
或许,正像安德森所说的,我们或许很难想象世界上会有「无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墓」或者是「殉难自由主义这衣冠冢」12。
虽然安德森对此的解释侧重不同,但是根据同样的例子,我们是否也可以相信,这恰恰是向我们表明了,究竟依照怎样一种关系建立起来的群体能够成为一个类似于民族国家那样,具有政治与社会作用的组织呢?
盖尔纳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象,而不是作为民族主义者提出的学说」13。
站在这个基点之上,我们便不至于将「文化的人造物」漫无边际的扩大。
于是我们便可以问,为甚么是在这样一群人当中,这种「文化的人造物」得以成为可能?
为甚么不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不是在「女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中间产生相同的效应?
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的发现也能算作是一种自发的产物。
在以下的部分中,我将对于《生存》与《鬼子来了》及其一系列与《鬼子来了》相关的,发生于2000年左右的事件、评论结合在一起,旨在将其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样本,讨论民族主义本身被重构的状况,主要就是民族主义其敌人与神话书写的转变。
(二)大门外的敌人:
《生存》作为一个战争神话的分析
正如杜赞奇所说的,1936年的中国,「整个史学界都在关注日本的入侵及其给中国历史叙述结构所提出的特殊诉求」14。
抗日战争作为一个事件来说,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极为明确的外部敌人。
一方面,在抗日战争发生的当时,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方面,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民族战争调动,在这之前所存在的国共双方的党派与阶级矛盾被中日之间战争的矛盾所取代。
无疑,民族主义的道德模式在于旧有的道德模式之间所发生的那种转译关系使得民族主义本身具有了某种中国式的走向。
汪晖在其一篇讨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问题的论文当中,便重点论述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互渗关系15。
在这篇论文里,汪晖为我们梳理了在民族建构的过程当中,普遍民族语言超越地方性艺术形式的历史轨迹。
可以发现,在这样的民族建构当中,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仅超越了阶级与党派界限,也超越了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的界限,由于一个突如其来的、在中国大门之外的敌人出现,原本在中国内部分散的势力群体被重新整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敌人的中华民族。
普遍的民族语言的传播,其目的也在于采用一个共有的声音,去讲述一场正在发生的战争故事,以使得无论是身处于战争之内还是战争之外的个体,都对这场战争能够有种共同的想象。
无疑,在这里所谓民族形式的建构同样也面临着旧有秩序,这种在两者之间所进行的转移,其产物便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抗日神话叙述方式。
在《生存》当中,那个故事发生的村庄的地理位置是很有趣的:
曙光里石沟村迎来不凡的一天,揭开村庄抗战史崭新的一页。
在这之前,由于此处偏远贫瘠,交战双方都没将这个猴腚大小的地盘看在眼里,将其排斥于战争之外。
小村人对于战争的体验仅是遥听天边隆隆炮响以及远眺扛膏药旗的日本鬼子从村外过兵。
初时,人们是心惊胆战的,害怕鬼子走着走着一头扎进村里来发疯。
可没有,鬼子坚持对小村的无视与轻蔑,一次也没进村。
久而久之,人们就宽了心,对过兵就不当回事了。
自然,外面战争的消息还是不间断传来,传得最多的是鬼子杀人不眨眼的暴行。
小村人对这些耸人听闻的传言将信将疑。
很明显,那一系列诸如石沟村一般的中国村庄即便在抗日战争时期,正面加入到战争当中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对于中国的军事占领从地图上来看,始终停留在东部沿海、东北地区、以及陇海沿线等一些主要的军事目标上。
事实上,无论是九一八事变时期还是后来中日正式宣战的八年期间,日本扩张主义者在和平条件中也从未打算在中国本部承担直接的行政管理责任。
日本扩张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征服在更大程度上是满足其政治愿望与战争经济需要16。
因此,对于大多数处于战线之外的中国农村来说,较为可信的情况或许确实是如同《生存》当中所描述的,抗日仅仅是一系列传闻、故事的构造物,对于日本军队的情绪因而也更多的表现为是一种本能的恐惧感。
虽然整个石沟村在小说当中被定义为「抗日村」,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整个村子除了协助打狗以防狗在抗日军队夜里进行突袭时暴露目标之外,并没有作任何的与抗日发生关联的其它事情。
相反,在占领区的农村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状况。
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于冀中农村饶阳的调查报告便显示,这些身处抗日战争中心地带的农村表现出了非凡的坚定,积极参与视死如归的精神。
而相应的,这些抗日的故事,即便在当时,也是人们传颂的重点。
抗日英雄的传说经过不断传颂之后,可以成为神话,爱国农民们的行为则成为这类神话的起源或者是受益者。
这样一个神话的过程一方面将抗日战争塑造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神圣的民族战争,一方面也掩盖着战争过程当中那或许占更多数的自私的事实。
在同样是针对饶阳县的调查报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17:
尽管表现对新政权忠诚的传说逐渐取得人们的共识,但事实上,许多人在战争期间仍表现出狭隘、愚昧、背信弃义和自私。
有关安国县的伪军部队、送妇女给日军的村子、不给八路军征兵的领导人、杨各庄及其它地方的汉奸、那些笨拙地试图隐藏粮食的人和取得成功的亲日特务等种种事实,都没有在英雄神话中得到反映。
不难发现,在这各种各样的英雄故事当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对于战争的美化甚至追求的表现,以及对于敌人的恶魔化描写18。
本质上来看,从《生存》当中仍能够清楚地找到这些特点。
而今日,一个鬼子的到来便打破了村子固有的沉寂,小村终于和战争沾上了边儿。
小村将为自己本来平庸无奇的村史绘出闪光的一笔。
在这样一段英雄主义的叙述当中,作者明显对于战争持有某种神话般的向往,在他看来,得以参与战争才能够式的历史本身具有史诗般的意义。
作者以一种神圣的态度将战争为村子的生活所带来的一切简单成为一场英雄主义的演出,在这场演出当中,似乎一切的不快乐都因为这种神圣的色彩而消失殆尽了。
作为叙事者的作者本人,将一种宗教的虔诚从超验的对象转变到完全尘世的对象当中,使得对于民族主义本身的崇拜呈现出了几近狂热的态度。
恰是这样一段叙述与先前除了打狗别的无所作为的抗日村的叙述放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暗示性的效果。
即恰是这样一次将整个村子卷入战争的事件,使得整个村子在民族主义战争的神话叙事当中,得到了犹如宗教般的救赎。
正是在这种救赎的可能性下,作为村长的赵武才别无选择,不得不、并且十分快乐的承担下这一战争强加于他们整个村子的安排。
放在《生存》小说开头的这段内容为之后的所有叙事埋下了神话式的民族主义色彩,因此故事参与者们的主体性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为一个群体为一种抽象的民族目标而服务的需要。
甚至,这样一种本应被视为被迫的要求在实践当中,几乎显现出了一种狂欢式的状态,被迫便成为自主。
神话就此被人们内化为民族主义的动力与模范。
并在以各自的方式来实践着民族主义的情绪。
在这样的情绪主宰下,人与粮食的关系也显出不同的英雄主义色彩:
「对你说啊玉琴,这粮食一半归小鬼子,另一半归你和扣儿。
摊出的第一张煎饼给咱扣儿吃,记住啊!
」赵武临出门时向玉琴叮嘱。
玉琴没言语,泪模糊了她的视线,她看不见赵武怎样出门,只听见了门响。
这是发生在赵武为了让鬼子吃饭而向村里财主万有全借粮之后的事情。
事实上,贯穿于全篇当中的一条主要线索也正是农村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粮食本身构成了小说最后矛盾的所在,赵武作为村长,是出于想要让全村人吃饱肚子的态度而与鬼子俘虏谈判的。
最终谈判的筹码,也是「鬼子」所掌握的秘密藏粮点的粮食。
可以说,在故事开始的时候所发生的这场节粮故事,为之后的故事进程暗示了一种宿命性的结局。
所谓「生存」的意义在这里,同切实的生存与死亡联系在一起,而似乎是故事另一条主线的处决鬼子、汉奸俘虏的问题,则在这里相应的显得并不存在任何重大的冲突。
鬼子俘虏在这个村子里是不显出有任何危机的,在整个《生存》的叙事当中,对于抗日的精神本身毫不怀疑,因此,处决鬼子俘虏在这里所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谁来担任刽子手以及何时处决的问题。
在这个层面上,故事是毫无悬念的,天经地义的。
在更大程度上,鬼子、汉奸俘虏的到来,仅仅是为这个故事当中存在的人与粮食之间的生存联系添加上了一个英雄主义叙事的背景。
就在这一刻,他听到了敲门声。
是那种具有暗号特征的敲门,这敲门声如同一场戏剧的开场鼓点,使他由此进入了角色披挂上场,且从此再难脱身。
于是他就牢牢记住了「民国三十三年腊月十三」这个于他于石沟村都极其不详的日子……
这段略带有马尔克斯味道的开头试图在向故事的读者们传达着一种宿命式的沉重感,作者企图将饥荒为整个村子所带来的恐惧与萧条归结到一个更大的恢宏主题下。
因此,抗日战争,携带着一种民族主义的神圣气度,被放置到了这个闹着饥荒的村子当中来。
可以说,这场战争是被抛至到这个本应当与世隔绝的村子当中的,但是,这种抛至在作者这里,却由于建立起了饥荒与战争的联系,而显得无比神圣与令人庆幸。
在这个故事当中,假如将饥荒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模式化的人物塑造形式。
在这个村子的饥荒事件当中,赵武第一个想到的节粮对象是一个家里有人在军阀部队里当兵的地主万有。
而另一个在饥荒当中还能够吃饱肚子的,则是族长五爷。
前者在整个故事里表现出的极度自私与精明令人很容易就想到,在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学作品当中所固有的地主形象。
而后者作为一名宗族首领,其行为也颇能令人想起在反传统运动当中被平面化,性格化了的族长。
在作者行文当中,不难发现那些启蒙主义的、反传统的叙述。
由于在这里,族长所代表的是那种被启蒙主义、革命者们所否认的就有的宗族领袖,因此,在一种线性的、阶级式的历史叙事当中,他所代表的,也就是与作为「劳苦大众」的石沟村广大饥饿农民所对立的,守旧的、封建的宗族势力。
……五爷连自己的亲生孙女都不管不顾,怎还会可怜别的与他毫无瓜葛的孩子?
作为一族之长,五爷是很让族人心寒的。
许多年前,族人便对他将庙产据为己有而提出过异议。
并指出别的村子庙产收入除祭祀外,所余为族人所共享。
丰收年景村里的庆典以及歉收年景对贫困户的接济都取之于此。
村人觉得别村这种做法合情入理,为何至贫至穷的石沟村却抱着老皇历不放,让一家一户独吞?
五爷也有自己的说法:
别的村族怎样怎样是人家的事情,与石沟村无干,石沟村只能依照自己祖先留传下来的族规行事,不能更改。
这是前些年的事。
在这样的叙事当中,五爷作为一个族长的主体位置被强调了,而随着这种主体位置而来的,则是一系列必然,包括:
自私、冷漠、霸占族产、传统、守旧等等。
正是由于这样的必然存在,因此当全村人陆续饿死的时候,作为族长的五爷才能够毫不作为。
而相应的这种责任则落到了「抗日村长赵武」这一由新秩序产生出来的领导人物身上。
可以说,作者认同,生死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在整个村子里面是一种关键性的目的,遵循怎样一种法则可以生是这种法则合法性的唯一证明,五爷在面对村民陆续死亡的事实上毫不作为的举动责令其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这样一种从旧有宗族领袖到抗日领袖的转变,在这样的故事讲述当中,很大程度上,则表示了一种宗族秩序的合法性丧失与民族主义秩序取而代之的必然性。
作为外来事件的鬼子、汉奸俘虏的出现,则全部目的,则是采用一种民族战争式的神圣必然,为整个新兴秩序取代旧有秩序的过程蒙上一层史诗式的气氛。
事实上,如果将宗族秩序对于祖先的崇拜视为一种形式的有神论模式,那么作为现代性的产物,民族主义所必需要完成的,则是一种从有神向无神的转变。
19而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当中的成分之一,其反传统、反阶级的革命性色彩,也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叙事增添上了某种特有的气质。
《生存》作为一则抗日神化的延续,则是这种特有民族主义气质的又一次体现。
它将共产主义运动下,新兴秩序取代旧有秩序的过程笼罩在民族主义运动的狂热气氛下。
从本质上来讲,它仍旧是「民族形式创造的要求下」20所产生的文艺作品。
传达的,也是革命性的,对于旧有形式的批判。
(三)后现代:
解构战争神话
经由上述的讨论,大体上可以发现,作为抗日神化出现的战争叙事基本上都呈现出了将战争神圣化,绝对化,将战争双方善恶二元化的倾向。
从《生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赵武等人死亡所具有的英雄主义色彩:
春天雪融,山谷由白变黑,当地人在谷中发现了尸体,陆陆续续总共发现了十几具,正是运粮队失踪了的数目。
尸体一点也没有溃烂,完好无损,面目栩栩如生。
但有心人很快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尸体的位置虽很分散,有的相距几里路远,可他们的头都冲着同一个方向,冲着隐于山谷豁口处绿树丛中的一个小村落。
当地人自然知道,那村子是于家夼。
也可以看到对于敌人本能的憎恶:
他(赵武)这是头一遭和日本鬼子打交道,以前曾听人说这些畜生很格色,难斗难缠,这遭他领教了。
可气的是他们做了俘虏还不服软,还和你作对,真他妈该杀该剐!
甚至还可以看到汉奸周若飞对于汉语的热爱:
周若飞说:
「中国的语言如同汪洋大海般广阔无边,我不知道该怎样从中选择。
」
这些明显是作者代言的话,都共同构造出了一个主流的抗日民族主义话语环境。
相应的,对于日本军队的刻画也是邪恶化的:
少尉三十出头年纪,圆脸尖下巴,酷似一个倒置的葫芦,眼光不善,一副桀骛不驯的模样。
这样的仇视的目光贯穿整篇小说,诸种描述与叙事都勾画出了一个在民族主义叙事当中所认可的,日本侵略军人的普遍形象。
在这样一种战争神化里,虽然一方被描述成为出离现实的绝对的正义、真、善、美,另一方也被不合实际的简化成为绝对的邪恶、丑陋,但事实上,对于战争的非人性化渴求使得抗日的情绪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情绪几乎呈现出同样的表现。
这样一种神圣的战争叙事到了《鬼子来了》这里,则成为了主要被责问的对象。
虽然在《生存》中间的这种民族主义式的简单战争叙事仅仅作为整个故事的神圣背景,并没有成为尤凤伟所需要重点刻画的对象;但是,这样一种从前被默认的叙事框架,却成为了《鬼子来了》所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而相应,在小说当中所重点展开的关于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却在《鬼子来了》里面被几乎完全的淡漠了。
虽然电影被认为是《生存》小说的改编,但由于这样一条基本认同的改编,因而使得前后两种对于抗日的改变显得毫不相同。
对于《鬼子来了》这部电影,或许着眼于一些关键的改变的解读更能彰显这部二十世纪末年产生的电影的文化动力。
与《生存》当中名为石沟村的「抗日村」不同,《鬼子来了》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长城脚下名为「挂甲台」的普通村子。
这个村子与战争的关系在地理上并不像石沟村那样遥远不可及,相反,在挂甲台的村口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