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正当性.docx
《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正当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正当性.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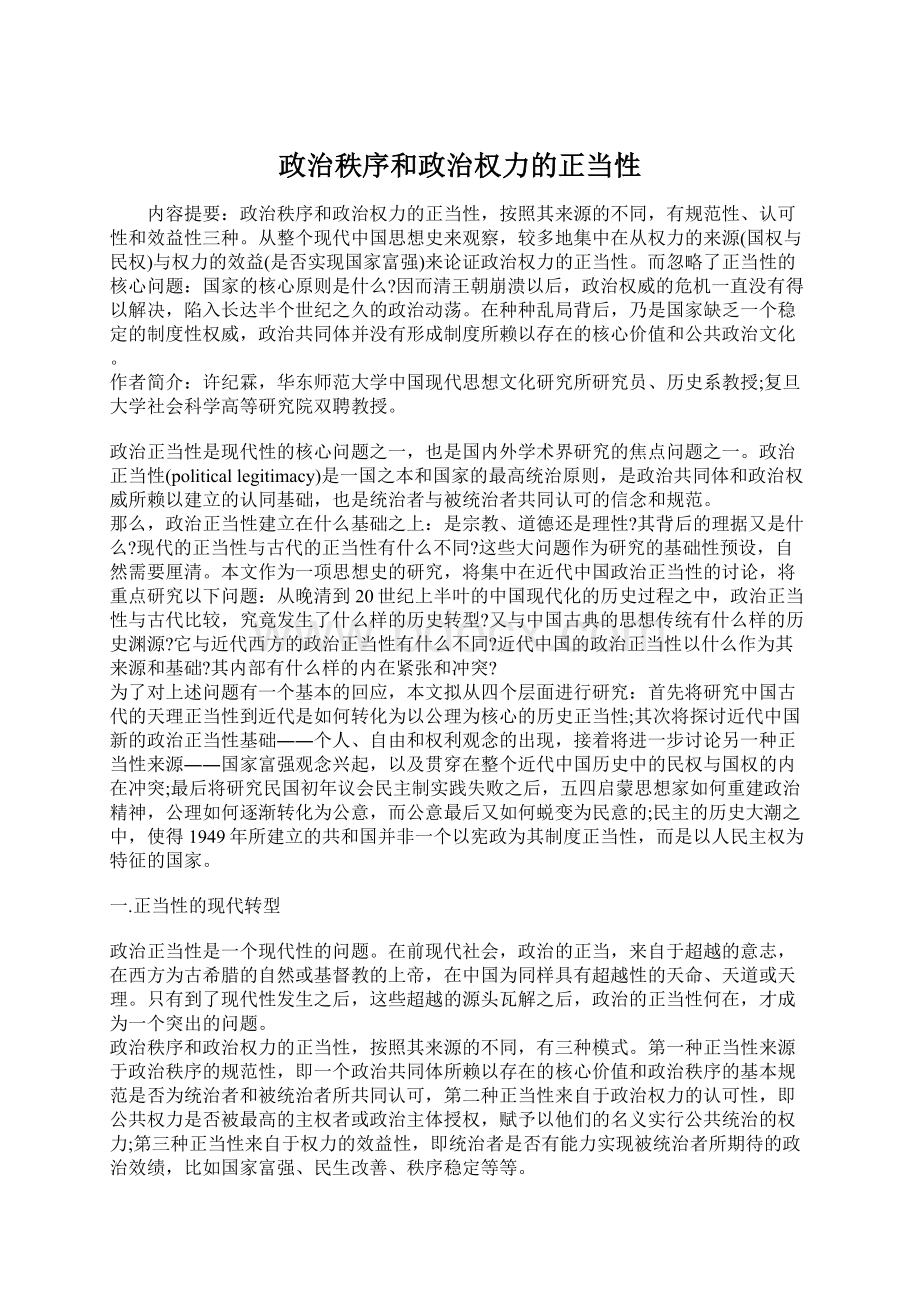
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内容提要:
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按照其来源的不同,有规范性、认可性和效益性三种。
从整个现代中国思想史来观察,较多地集中在从权力的来源(国权与民权)与权力的效益(是否实现国家富强)来论证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而忽略了正当性的核心问题:
国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
因而清王朝崩溃以后,政治权威的危机一直没有得以解决,陷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动荡。
在种种乱局背后,乃是国家缺乏一个稳定的制度性权威,政治共同体并没有形成制度所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
政治正当性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
政治正当性(politicallegitimacy)是一国之本和国家的最高统治原则,是政治共同体和政治权威所赖以建立的认同基础,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认可的信念和规范。
那么,政治正当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是宗教、道德还是理性?
其背后的理据又是什么?
现代的正当性与古代的正当性有什么不同?
这些大问题作为研究的基础性预设,自然需要厘清。
本文作为一项思想史的研究,将集中在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将重点研究以下问题:
从晚清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政治正当性与古代比较,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转型?
又与中国古典的思想传统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
它与近代西方的政治正当性有什么不同?
近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以什么作为其来源和基础?
其内部有什么样的内在紧张和冲突?
为了对上述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回应,本文拟从四个层面进行研究:
首先将研究中国古代的天理正当性到近代是如何转化为以公理为核心的历史正当性;其次将探讨近代中国新的政治正当性基础――个人、自由和权利观念的出现,接着将进一步讨论另一种正当性来源――国家富强观念兴起,以及贯穿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中的民权与国权的内在冲突;最后将研究民国初年议会民主制实践失败之后,五四启蒙思想家如何重建政治精神,公理如何逐渐转化为公意,而公意最后又如何蜕变为民意的;民主的历史大潮之中,使得1949年所建立的共和国并非一个以宪政为其制度正当性,而是以人民主权为特征的国家。
一.正当性的现代转型
政治正当性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在前现代社会,政治的正当,来自于超越的意志,在西方为古希腊的自然或基督教的上帝,在中国为同样具有超越性的天命、天道或天理。
只有到了现代性发生之后,这些超越的源头瓦解之后,政治的正当性何在,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按照其来源的不同,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正当性来源于政治秩序的规范性,即一个政治共同体所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和政治秩序的基本规范是否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共同认可,第二种正当性来自于政治权力的认可性,即公共权力是否被最高的主权者或政治主体授权,赋予以他们的名义实行公共统治的权力;第三种正当性来自于权力的效益性,即统治者是否有能力实现被统治者所期待的政治效绩,比如国家富强、民生改善、秩序稳定等等。
一种政治秩序或公共权力的统治,只要具备了上述某一项条件,就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比如某个公共权力其统治虽然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权力也未经被统治者的合法授权,但其统治的业绩不错,能满足或部分满足被统治者的某些共同愿望,那么这个权力就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即效益的正当性。
不过,这三种正当性在质地是不同的,概括而言,规范的正当性最高,也最稳定;认可的正当性其次,而效益的正当性最低,也最不稳定。
中国古典的思想传统之中,入世的儒家和法家都比较重视政治的正当性。
不过,中国哲人对政治秩序正当性的思考,与西方人是不同的。
根据张德胜的看法,西方哲人考虑的是:
政治秩序之正当为什么是可能的?
而中国哲人思索的是:
如何建立正当性的秩序?
前者问的是“为什么”,是一个智性的问题,而后者问的是“如何”,是一个规范的问题。
[1]西方思想寻找的是政治秩序背后的正当性理据――上帝、自然法或者理性,而中国古典思想更多地集中在:
如何建立一个正当的政治秩序?
他们考虑的不是正当性背后的终极原因,而是如何实现政治秩序之正当化:
德性原则(以民为本)、功利原则(富国强兵)等等。
从正当性的三种模式来看,儒法两家都很少讨论权力的来源问题,皆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的授权,无须得到被统治者民众的制度性认可。
不过,儒家比较重视统治的规范性,即更多地从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出发衡量统治是否合法有道:
是否施仁政?
是否按照德性的原则统治?
是否以民为本?
而法家更强调统治的实际功效,是否可以实现富国强兵?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之中,儒家自然是政治思想的主流,法家是偏支而已,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道义(动机)和功利(效果)简单地二分儒法的政治思想,即使在儒家思想内部,也有从荀子到叶适、陈亮、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功利主义儒家。
[2]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三节中将进一步详细讨论。
从儒家政治思想来看,其正当性有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是超越的,政治统治是否正当,来自于超越的天的意志,二是世俗的,统治是否符合天意,主要通过被统治者民众的意愿和人心表达出来。
超越的天意和世俗的民心不是像西方那样隔绝二分,而是内在相通的:
无论是天意还是人性,都内涵德性,民意与天意都遵循德性的最高原则,内在相通,德性之天意通过民意显现出来。
儒家的这两种正当性来源,为近代以后的转变提供了历史的依据:
超越的天理转化为世俗的公理,传统的民意转化为人民的主权。
晚清的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之所以“三千年未有”,乃是过去中国政治之变化,不过是王朝之更迭、权力之移位而已,虽然统治者不断变化,但统治的基本义理、权力背后的正当性基础,三千年基本未变也。
而晚清开始的大变局,则不同了,不仅老祖宗定下的旧制度要变,而且旧制度背后的义理也发生了危机,也面临着大变化。
综合起来看,晚清以后政治正当性的大变局,体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是对政治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在儒家古典思想中,政治是道德的延伸,内圣外王,政治背后的正当性标准不是政治本身,而是德性,而德性既是民意,又是天道,具有终极性德价值。
而现代性最大的变化,乃是政治与道德分离,公共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分离,政治不再需要道德的源头,不再需要上帝、天命、自然这些超越性源头,政治成为一项世俗性的事务。
于是,政治正当性终于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上帝死了以后,天命、天道、天理式微之后,人成为政治世界的主体,那么,人如何自我立法?
如何为世俗的政治重建正当性的基础?
由此便产生了第二个变化:
超越的正当性变为世俗的正当性。
天理的世界观被公理世界观替代,天德的正当性也转变为历史的正当性。
晚清以后,政治是否正当,不再从超越的天命、天道和天理之中获得其德性的正当性,而转而从人自身的历史,从进化的、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寻找正当性的源头。
晚清出现的公理,虽然从传统的天理演化而来,但已经世俗化了,其背后不再是一个以宇宙为中心的有意义的有机世界,而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机械论的物理世界。
世界是进化的,也是有目的的,现代政治是否正当,要看其是否符合历史演化的法则和目的。
第三个变化是个人、自由和权利成为成为衡量政治是否正当的基本价值和尺度。
古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即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天下归仁的礼治秩序?
因而“仁”和“大同”成为最高的价值理想。
从明代王学中开始萌芽的个体意识和明末的自然人性论到晚清通过西方思想的催化,发酵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新的价值观。
晚清的“仁学”世界观中发展出“自我”和“自由”的价值,“善”的观念演化为“权利”的观念,“个人”伴随着“民族国家”的概念同时诞生。
政治秩序是否正当,在于是否为每个国民提供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个人权利的落实。
于是立宪与否便成为正当性的重要标志,也是上述基本价值的制度性保障。
第四个变化是到近代以后权力的来源成为政治是否正当的核心问题。
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统治才是正当的、符合天意和民心?
而到近代由于民权运动的突起,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革:
政治正当性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如何统治,而是统治者的权力是否得到了人民的授权和同意?
由此从民本的正当性(民本主义)转化为民主的正当性(人民主权论)。
人民从过去只是被代表的客体,成为政治的主体。
不过,人民的意志究竟是什么?
是清末民初所说的公理,还是五四时期流行的公意,或者是后来取而代之的民意?
从公理到公意再到民意的历史演变来看,虽然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但其内涵的客观性和抽象性依次减弱,而主观性和流变性逐渐递增,因此也给了民本正当性一个重新翻盘的空间,统治者只要宣称代表民意,便可以民本正当性冒充民主的正当性,或者以民粹主义的名义行专制主义之实。
最后是国家富强成为政治正当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如前所述,儒家的政治正当性主要建立在统治的动机(义)基础之上,而统治的效用(利)一直是潜伏的支流。
晚清以后,经世潮流大兴,儒家内部的功利主义支流经过洋务运动的刺激,逐渐演化为主流,并进一步以法家的富国强兵作为追求的目标。
效益主义的政治正当性,在近代中国有两个标准,一是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二是建立稳定的统一秩序。
不仅在统治者那里,而且在知识分子内部,这种效益主义的正当性一直有广泛的传播和市场。
在上述晚清以后五大变化趋势之中,可以看到在经历传统正当性危机的同时,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也在逐步重建新的政治正当性轴心。
新的政治正当性以“去道德化”为时代标志,以世俗化的历史主义目的论为知识背景,确立了三个重要的正当性轴心:
自由之正当性、民主之正当性和富强之正当性,并分别形成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和国家主义这三种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潮。
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国家富强,这是三种现代的政治价值,彼此之间有密切的互动和相关关系。
比如,自由主义的民主,便同时包含了自由和民主这两种政治价值。
在晚清,当这些新的价值在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那里出现的时候,彼此之间也是互相包含,尚未分化的。
然而,这些价值毕竟代表了不同的发展取向,很快地民主主义与国家主义便发生了冲突,最后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也分道扬镳。
这些思潮之间的分化,并非自由、民主和富强诸价值的绝对冲突,而是一个当这些价值发生内在冲突的时候,究竟何为优先的选择,国家主义选择的是国家的富强,民主主义看重的是权力的来源,而自由主义更重视的是通过立宪维护个人权利。
从清末到民国,民权与国权的争论一直不绝如缕,而到1940年代后半期,本来一直是结为一体的自由民主主义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形成要宪政还是要民主的大抉择。
在汹涌而起的民主大潮和国家动乱之中,民主压倒了自由,宪政屈从于威权。
从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史来观察,对政治正当性的关注,更多地纠缠在民权与国权的争论中,即不是从权力的来源,就是从权力的效益性来论证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而忽略了正当性的核心问题:
国家的核心原则――立国之本是什么?
政治共同体公认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是什么?
这些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如何通过以宪法为中心的宪政加以制度化和法治化?
由于对正当性这一核心问题的理论探索的匮乏和政治实践的失败,因而清王朝崩溃以后政治权威的危机一直没有得以解决,近代中国从1911年到1949年,陷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动荡,而在种种乱局背后,正是国家缺乏一个稳定的制度性权威,而之所以缺乏权威,乃是政治共同体并没有形成制度所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政治文化。
二.从公共善到个人自由与权利
古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建立在公共善(仁)的基础上,到了晚清之后,逐渐转移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又与西方的现代性过程有什么区别?
要了解这些问题,必须从个人、自由、权利这三个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在中国出现入手。
1,个人
现代性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是个人的出现。
在传统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落实在天下,即以德性为中心的礼治秩序,而到了近代之后,正当性的重心逐渐从天下转移到个人,而与个人密切相关的自由、权利等等,到晚清以后,也成为无庸置疑的正当性词汇。
作为现代性的个人观念是如何出现的?
这固然与晚清西学的引进有关,早期的基督教文献和1900年以后传入的“天赋人权”思潮都有丰富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思想资源,但在晚清,这些外来的观念在尚未崩盘的儒家义理系统之中,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它们只是起了一个外在的“催化”作用,使得在中国思想经典中一些原先并非核心的观念产生“发酵”,在晚清历史语境的刺激下,进入主流。
而个人观念的出现,与晚清出现的强烈的“回归原典”的冲动有关:
儒学和佛学的传统为晚清个人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原始仁学和和宋学之中,人的心性与天道相通,个人在成仁成圣上,内容提要:
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按照其来源的不同,有规范性、认可性和效益性三种。
从整个现代中国思想史来观察,较多地集中在从权力的来源(国权与民权)与权力的效益(是否实现国家富强)来论证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而忽略了正当性的核心问题:
国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
因而清王朝崩溃以后,政治权威的危机一直没有得以解决,陷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动荡。
在种种乱局背后,乃是国家缺乏一个稳定的制度性权威,政治共同体并没有形成制度所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政治文化。
四.政治的精神:
个人、良知和公意
1,国本问题的提出
晚清的思想界对政治正当性的讨论,主要纠缠于以人民主权为核心(权力的认可性)还是以国家富强为目标(统治的效益性),较少考虑到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和精神(秩序的规范性)究竟是什么?
其中的原因恐怕与旧的王权制度依然存在、新的政治共同体尚未建立、政治秩序的规范性原则暂时还没有成为突出的问题有关。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建立了史所未有的共和秩序,但这一秩序又是以政治混乱和重建军事强权为代价,这使得原先被遮蔽的秩序规范性问题变得凸出。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直接渊源于民初知识分子普遍地对政治的失望。
这一失望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以及随之而起的北洋军阀统治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另一个方面,即对民初曾经实践过的议会民主制的变质和腐败的失望。
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在中国统统都归于失败,于是无论是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启蒙知识分子,还是梁启超为领袖的研究系知识分子,都放弃了政治上的努力,重新在文化上为共和政治秩序寻找新的伦理精神和价值规范。
诚如周锡瑞(Josephw.Esherick)所说:
“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
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
”[58]辛亥之后,原先为王权专制所压抑的地方封建势力借民权而崛起,地方绅士权力大大扩张,民初的党争和军阀冲突成为私人、家族和地方利益之争,始终没有发展出统一的宪政制度和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公共文化。
在民国初年,在一个制度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几乎所有的争论,无论是国权与民权之争,还是总统制与内阁制、中央集权制与联邦制的冲突,都是围绕着权力的分配而展开,卷入政治利益冲突的各家各派,却忽略了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的最核心的问题:
政治正当性的规范性基础是什么?
制宪问题虽然也是争论和冲突的焦点问题之一,但焦点却仍然集中在由谁制宪、中央和地方权力如何安排这些权力层面的问题,至于政治秩序的规范性基础、政治共同体的核心原则究竟是什么,却乏人问津。
民初的政治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新的共和制度出现了,却缺乏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宪政;表面的宪法也有了,却无法转换为行之有效的宪政实践。
也就是说,共和制度的背后缺乏制度实践所必须的公共文化,缺乏共和制度之魂――共和精神。
当年思想界最敏感的人物杜亚泉已经注意到,民国成立以后,最令人忧虑的是人心之迷乱。
迷乱表现之一,乃是国是不存也。
所谓国是,“即全国之人,皆以为是者之谓”,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核心价值。
作为核心价值的“国是”,“乃经无数先民之经营缔造而成,此实先民精神上之产物,为吾国文化之结晶体”,清议也好,舆论也好,皆本于“国是”,“虽有智者,不能以为非也,虽有强者,不敢以为非也”。
然而,杜亚泉沉痛地说:
“然至于今日,理不一理,即心不一心,”人心中共同认可的“国是”已经荡然无存,种种庞杂的思想互相冲突,互相抵消。
[59]“国是”不存,强权当道,遂造成民国政治的混乱。
大约从1914年起,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首领风气,开始讨论“国本”(或“政本”)问题。
所谓“国本”,即国家赖以存在之本,即政治共同体最共同的原则、义理和规范。
“国本”讨论的开拓,改变了清末民初只是从权力的来源或统治的效益论证政治的正当性,转而正本清源,从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规范入手,重新建立国家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在《甲寅》杂志诸篇讨论“国本”(或“政本”)的文章中,论述最清晰、分量最重的,要数张东荪的《制治根本论》。
他首先检讨了民初议会民主制度的失败原因,指出“吾国政治上变化虽多,皆属表面,察其根本,按其精神,固仍为清之政治,未尝稍变。
”[60]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皆是从道德本体论而来,张东荪以及后来的陈独秀等五四启蒙思想家从这一思想传统而来,相信精神决定政治,民主政治的失败,要从政治背后的文化和伦理源头寻找根源。
这就是所谓“国本”问题的来由。
张东荪在文章中继续说:
政治制度千变万化,但理一万殊,万殊的制度背后有统一的道,国家的安生立命即在此,文化的基础也在此。
那么,作为现代共和制度背后的“道”究竟是什么呢?
张东荪明确指出:
“政治之精神,惟在使国民自由发展。
”国民之自由发展,从消极方面言之,乃是严格划分国家与国民的界限,国家不得侵犯国民之基本自由;从积极方面来说,国民利用自己的权利,积极监督政府。
[61]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初思想界风气的明显变化:
晚清所弥漫的是国民/国家一体化的国家主义,而到了五四前夕,由于知识分子普遍对国家失望,开始划清国民与国家的界限,防止国家权力对社会和国民的过度干预。
政治共同体背后的自由精神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来了。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甲寅》为核心的一部分思想家的国家观从原来流行的国家有机体论转向了国家工具论。
章士钊指出:
“中国之大患在不识国家为何物,以为国家神圣,理不可渎。
”[62]他说,“国家者,乃自由人民为公益而结为一体,以享其自有而布公道于他人”。
[63]同样在《甲寅》杂志上,陈独秀在那篇引起广泛争论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也明确说:
“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
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64]虽然在《甲寅》杂志和继起的《新青年》杂志之中,章士钊、陈独秀、高一涵等人为了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重要性,其国家观转向了功利主义的国家工具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五四思想界从此国家有机体论消声匿迹。
在五四时期,虽然国家主义潮头有所回落,个人意识空前高涨,既便如此,五四时期的个人也不是原子式的抽象的权利个人,而是在各种“大我”意义中的“小我”,是在人类、社会脉络中的自我,个人与社会具有高度互动性,这也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所信奉的社会有机体论所致。
社会有机体论与国家有机体论只是一步之遥,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1930年代以后,国家有机体论借助“新式独裁论”会再度崛起。
从《甲寅》开始讨论“国本”和“政治精神”,到《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可以看到民初的政治正当性从权力的制度性安排转移到形而上的层面――政治背后的核心价值和伦理精神究竟是什么。
陈独秀明确地表明:
吾人最后的“伦理的觉悟”,乃是确立“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
[65]国本的核心和基础不是国家自身,而是个人的自由。
于是,五四刮起了一股个人解放的狂飙运动。
2,重建个人与重建社会
近代的个人解放,自晚明起源,中经二百年沉寂到晚清又重起波澜,开始冲决网罗,到五四已经蔚然成潮。
如第三节所分析的那样,晚清的个人虽然从各种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但目的是为了归属于国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强盛所要求的新国民。
另一方面,儒家的德性伦理也尚未解体,在仁学世界观下个人的道德自主性依然是自我认同的中心。
但到了五四,情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辛亥以后政治上的王权解体了,社会结构中的宗法家族制度也摇摇欲坠。
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与人的心灵秩序危机同时爆发。
五四对文化传统的激烈批判,不仅使得儒家的规范伦理(三纲五常)崩盘,而且德性伦理(仁学世界观)也受到毁灭性冲击。
五四的知识分子将政治正当性定位于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但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到了五四,却反而没有像晚清那样有明确的答案,变得模糊起来。
经过各种外来思潮的催化,五四思想界对个人的理解是非常多元的,在各种“主义”的旗帜之下,五四思想中所谓的“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典范。
大致而言,可以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流派。
科学主义的个人观将“个人”放在一个科学的、机械主义的宇宙之中加以认识,自我的思想和行动受到客观的因果律所支配,然而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可以通过科学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的法则,或者在自身的历史实践之中积累经验,从而获得个人的自由。
在科学主义的个人观中,又可以分为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不同的类型,胡适、丁文江、吴稚晖等属于前者,而陈独秀则是后者的典范。
[66]五四的人文主义个人观则比较复杂,类型众多,有蔡元培、杜亚泉、吴宓等为代表的、继承了儒家德性传统的“德性的个人”,有周作人的将中国道家、日本传统和古希腊精神结合起来的“自然的个人”,有受到尼采“超人”精神强烈鼓舞的、以鲁迅、李石岑为典范的“意志的个人”,也有朱谦之那样的将“情”视为宇宙和自我之本体的“情感的个人”。
这些个人观由于各自的思想资源和观念繁多不一,很难归于同一个类型,之所以将他们命之为人文主义个人观,乃是它们虽然差异很大,但都对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主流的科学主义个人观有强烈的保留和批评,试图在支配性的科学法则之外,各自通过德性、意志、情感或自然人性,建立现代的个人认同。
尽管五四的个人观非常多元,但继承晚清的思想传统,五四的“个人”依然有其共同的思想预设和时代特征。
陈独秀在《新青年》一文中在谈到个人的人生归宿时说:
“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群”。
[67]这两句话可以说浓缩地概括了五四时期个人观的两大时代特征。
先看“个性之发展”。
五四继承中国宋明理学中人格主义思想传统,又受到德国康德思想的鼓舞,承接晚清的思想命脉,不是在权利的意义上肯定个人,而是将个人定位在个性的充分发展。
胡适将自己大力提倡的“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
[68]不过,与传统的“人格主义”相比较,五四的“个性之发展”已经不限于“为己之学”和道德自主,其个性的内涵不仅包含德性,更重要的是意志的自主。
统一的天理不复存在,公共善也已瓦解,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天性(无论这天性是理性的、德性的,还是审美的,自然的或者唯意志的)设计自我,发展个性,一切取决与个人的自由意志。
五四是功利主义伦理观特别流行的时期,受到约翰·密尔自由观的影响,五四思想家特别相信个性的发展将会给社会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幸福。
个人不仅要发展自己的个性,而且必须对社会和人类担当责任。
胡适在谈到“易卜生主义’时,除了认为“个人有自由意志”自我,还特别强调“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69]这也就是陈独秀所说的“个人“的第二层意思:
“外图贡献于群”。
从内(发展个性)到外(贡献于群),这一“个人“的发展途径依然遵循《大学》的内圣外王模式,只是从共同的德性演变为多元的意志自主。
五四的诸多思想家虽然对人生看法不一,却有一个坚定的共识:
个人无法独善其身,个人无法自证其人生之意义,“小我”只有在“大我”之中才能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之价值。
这“大我”便是群(人类社会或人类历史)。
晚清的“大我”还是有超越的、德性的宇宙,到五四便转化为世俗的人类和历史:
个人的“小我”只有融入人类进化的历史“大我”之中,才能实现永恒,获得其存在的意义。
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丁文江宣称自己的人生宗教是“为万种全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70]胡适根据儒家的“三不朽”思想,将个人的、短暂的“小我”,融入到“永远不朽的历史“大我”的无穷未来。
[71]
傅斯年在《新潮》创刊号上发表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