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帖学大坏论及其影响.docx
《康有为帖学大坏论及其影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康有为帖学大坏论及其影响.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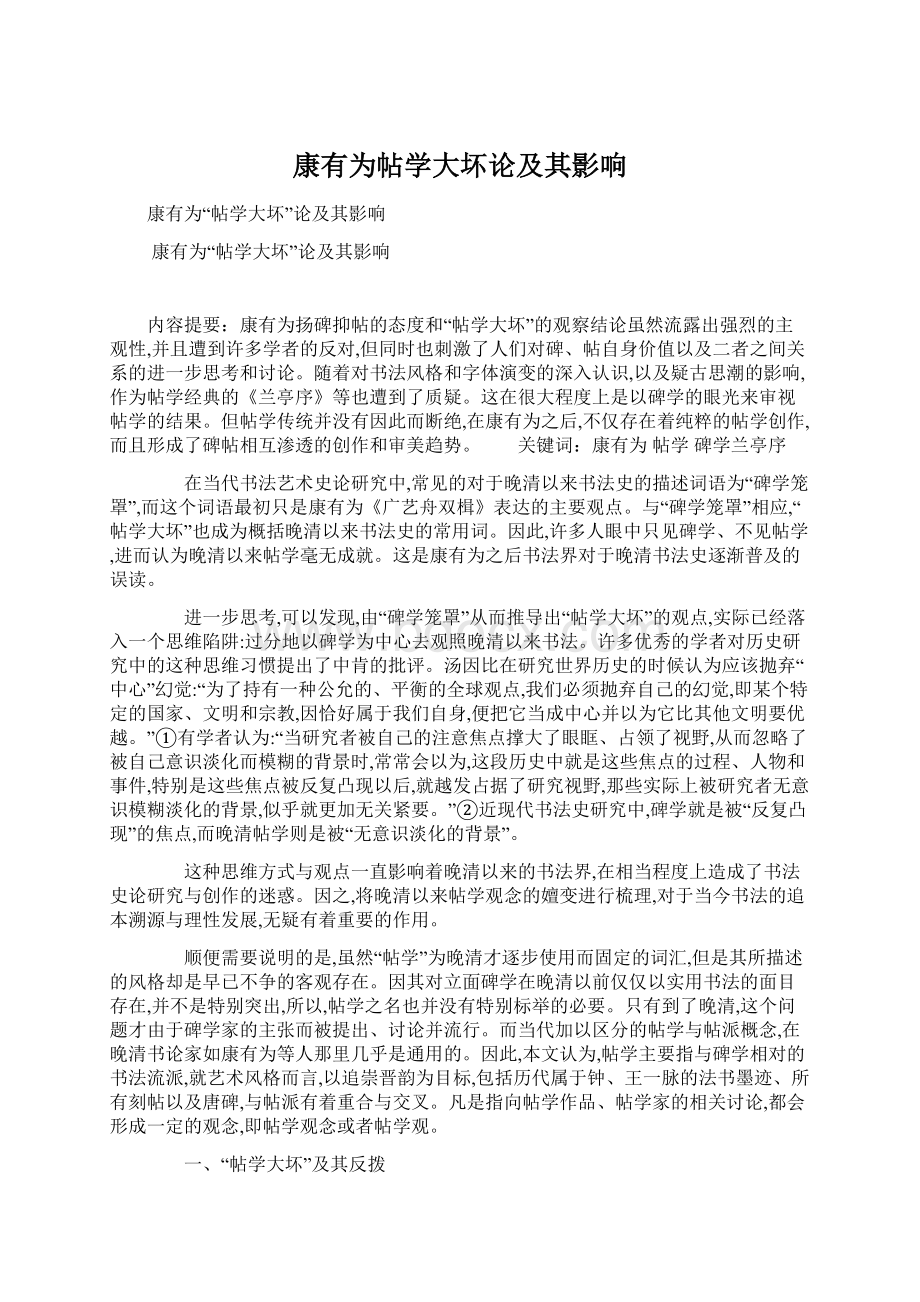
康有为帖学大坏论及其影响
康有为“帖学大坏”论及其影响
康有为“帖学大坏”论及其影响
内容提要:
康有为扬碑抑帖的态度和“帖学大坏”的观察结论虽然流露出强烈的主观性,并且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但同时也刺激了人们对碑、帖自身价值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随着对书法风格和字体演变的深入认识,以及疑古思潮的影响,作为帖学经典的《兰亭序》等也遭到了质疑。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碑学的眼光来审视帖学的结果。
但帖学传统并没有因此而断绝,在康有为之后,不仅存在着纯粹的帖学创作,而且形成了碑帖相互渗透的创作和审美趋势。
关键词:
康有为帖学碑学兰亭序
在当代书法艺术史论研究中,常见的对于晚清以来书法史的描述词语为“碑学笼罩”,而这个词语最初只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表达的主要观点。
与“碑学笼罩”相应,“帖学大坏”也成为概括晚清以来书法史的常用词。
因此,许多人眼中只见碑学、不见帖学,进而认为晚清以来帖学毫无成就。
这是康有为之后书法界对于晚清书法史逐渐普及的误读。
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由“碑学笼罩”从而推导出“帖学大坏”的观点,实际已经落入一个思维陷阱:
过分地以碑学为中心去观照晚清以来书法。
许多优秀的学者对历史研究中的这种思维习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汤因比在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认为应该抛弃“中心”幻觉:
“为了持有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
”①有学者认为:
“当研究者被自己的注意焦点撑大了眼眶、占领了视野,从而忽略了被自己意识淡化而模糊的背景时,常常会以为,这段历史中就是这些焦点的过程、人物和事件,特别是这些焦点被反复凸现以后,就越发占据了研究视野,那些实际上被研究者无意识模糊淡化的背景,似乎就更加无关紧要。
”②近现代书法史研究中,碑学就是被“反复凸现”的焦点,而晚清帖学则是被“无意识淡化的背景”。
这种思维方式与观点一直影响着晚清以来的书法界,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书法史论研究与创作的迷惑。
因之,将晚清以来帖学观念的嬗变进行梳理,对于当今书法的追本溯源与理性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顺便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帖学”为晚清才逐步使用而固定的词汇,但是其所描述的风格却是早已不争的客观存在。
因其对立面碑学在晚清以前仅仅以实用书法的面目存在,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帖学之名也并没有特别标举的必要。
只有到了晚清,这个问题才由于碑学家的主张而被提出、讨论并流行。
而当代加以区分的帖学与帖派概念,在晚清书论家如康有为等人那里几乎是通用的。
因此,本文认为,帖学主要指与碑学相对的书法流派,就艺术风格而言,以追崇晋韵为目标,包括历代属于钟、王一脉的法书墨迹、所有刻帖以及唐碑,与帖派有着重合与交叉。
凡是指向帖学作品、帖学家的相关讨论,都会形成一定的观念,即帖学观念或者帖学观。
一、“帖学大坏”及其反拨
20世纪书法界对于晚清以来帖学的误读很大程度上源于康有为的观点。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论点的本意并不在帖学本身,而且20世纪也有相当多的学者或者帖学家对康有为的观点进行批驳。
1.康有为“帖学大坏”论
康有为所谓“帖学大坏”论,实源于其“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的名句。
标举“帖学之坏”,其目的还在于推举碑学。
毁坏经典之后再重塑经典,是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历代变法者常用的策略。
要达到否定帖学的目的,康有为找到的第一个否定目标就是刻帖。
先来看其对于二王书迹钩摹本及刻帖的评价:
“二王真迹,流传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
方今帖刻日坏,《绛》、《汝》佳拓,既不可得。
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矣。
”③“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
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
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尊碑》)。
这里所谓帖,包括唐摹二王书迹、刻帖,即唐、宋、明三朝钩临翻刻本,均为其所反对者。
所谓“帖学大坏”,主要指刻帖的翻刻日坏。
康有为的“帖学大坏”,除开刻帖翻刻日坏之意外,还包括唐碑的翻刻日坏。
在讨论刻帖的翻刻以后,康有为顺理成章地推论:
“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
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
”(《尊碑》)这里康有为将唐碑与南北朝碑对举,并没有纳入碑学或者帖学。
进一步,康有为将唐碑归入帖学阵营:
“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
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
”(《体变》)古学,即帖学,包括晋帖、唐碑;今学,即碑学,包括北碑、汉篆。
综观康有为全文,后者更符合其本意。
因之,书法界奉为经典的唐碑就成为了他批驳的第二个靶子。
也就是说,如果说前者有着一定的现实依据的话,那么后者则在相当程度上染上了强词夺理的色彩。
试看其夫子自道:
论书不取唐碑,非独以其浅薄也。
平心而论,欧虞入唐,年已垂暮,此实六朝人也。
褚薛笔法,清虚高简……亦何所恶?
良以世所盛行欧、虞、颜、柳诸家碑,磨翻已坏,名虽尊唐,实则尊翻变之枣木耳。
若欲得旧拓,动需露台数倍之金,此是藏家之珍玩,岂学子人人可得而临摹哉!
(《卑唐》)
纵使“平心而论”,欧、虞、褚、薛水平并不差,欧、虞实“六朝”而褚、薛“清虚高简”,但是因为他们毕竟沾了唐代的边,也横遭贬斥。
此处康有为预设了要找出欧、虞、褚、薛弱点的问题,进而提出贬斥唐碑的理由——主要是因为翻刻。
如果说此点理由还算理由,但贬斥唐碑旧拓本则显得过于勉强:
一则因为价昂,二则因为其多属藏家珍玩而不易得。
换句话说,是因为没有普及的基础,而不是唐碑本身的风格或者水平问题。
这显然是一种“酸葡萄”心理!
当然,不可能要求康有为的推理方式都严谨得可以按照形式逻辑的方式演绎,但这里透露出的从自己好恶出发的情感心理逻辑无疑也有着其荒谬性。
或者换个角度讲,康有为的推论有其合理性,这一合理性的特征之一就是推理的情感随意性。
所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专门开辟了《卑唐》一节贬斥唐碑。
在翻刻日坏、不易普及之外,康有为还提出反对唐碑的另外两点理由。
其一,学唐碑者“无人名家”。
首见于《卑唐第十二》:
“自宋明以来,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师两晋。
然千年以来,法唐者无人名家。
”再见于《导源第十四》:
“尝见好学之士,僻好书法,终日作字,真有如赵壹所诮‘五日一笔,十日一墨,领袖若皂,唇齿常黑’者,其勤至矣。
意亦欲与古人争道,然用力多而成功少者,何哉?
则以师学唐人,入手卑薄故也。
”其二,唐人书专讲结构,古意已漓。
《体变第四》:
“夫唐人虽宗二王,而专讲结构,则北派为多……宋称四家,君谟安劲,绍彭和静,黄、米复出,意态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
”《卑唐第十二》:
“(有唐)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
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
米元章讥鲁公书‘丑怪恶札’,未免太过;然出牙布爪,无复古人渊永浑厚之意……唐人解讲结构,自贤于宋、明;然以古为师,以魏、晋绳之,则卑薄已甚。
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
”也许正因为第一点,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只字不提何绍基。
至于批评唐人过于注重结构,无疑也显示出康有为敏锐的洞察力。
基于以上认识,康有为反复申述不学唐碑,而要取法唐以上的观点。
其《购碑第三》云:
“吾闻能书者,辄言写欧写颜,不则言写某朝某碑。
此真谬说。
令天下人终身学书,而无所就者,此说误之也。
至写欧则专写一本,写颜亦专写一本,欲以终身,此尤谬之尤谬,误天下学者,在此也。
”而其所谓被误掉的典型之一就是翁方纲:
“覃溪老人,终身欧、虞,偏隘浅弱,何啻天壤耶!
”
至于行草,他反对学习刻帖中的颜真卿行草,其《行草第二十五》云:
“若师《争座位》三表,则为灌夫骂座,可永绝之。
”但是,他也有与其老师朱九江等帖学家一样的观点,如主张学习孙过庭《书谱》,“尽得其使转顿挫之法”;主张学习李邕《云麾将军碑》等(《述学》)。
大体来说,不学刻帖、不学唐人,这是康有为反复申述的观点。
“帖学大坏”既是康有为眼中晚清书法的现实,也是其推崇碑学的重要原因。
2.20世纪对于康论的批评
康有为的观点在发表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直到今天仍有影响。
但从19世纪末尤其20世纪初以来,有相当多的研究者对其观点进行了批驳。
刘咸炘《弄翰余沈》认为康有为尊六朝而卑唐“染于考据之习。
不知艺术论美丑,不论古近”。
而朱大可《论书斥包安吴康长素》一文堪称批康之经典。
这篇文章直接批驳包世臣、康有为“尊魏卑唐说”,分别批驳魏碑能传蔡卫、魏碑能备诸美、魏碑能开唐法、魏碑能得原拓四说,最后指出包、康实际为得益于唐碑者:
“二氏欲驱天下之人,尽弃唐碑而习魏碑,乃其自叙得力之处,反于唐碑津津道之。
在人则拒之惟恐不严,在己则亲之惟恐不近,古人修辞立其诚,二氏立言矛盾至此,欲取信于后世之士,愚虽不敏,知其难矣。
”④朱大可认为康有为得益于帖学却批驳帖学,自相矛盾。
1936年陈柱《谈书法》一文提出“碑学之兴,书法之衰”。
白蕉《碑与帖》一文认为,“以耳代目的轻信态度,也是古今不肯用心眼脑子的人所相同的。
所以,其实是属于一种研究性的文字,人们便信以为铁案”。
“(包世臣、康有为)两人的学术,既颇且疏,态度又很偏激,修辞不能立诚,好以己意,逞为臆说之处很多。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终欲以石工陶匠之字,并驾钟王……都是偏僻之论”⑤。
近至80年代应成一《碑学与帖学》认为“包安吴虽极力推崇北碑,而于二王书法用功亦深”,“帖学对于碑学从来并无异见,而碑学则往往一方面自视甚高,一方面又鄙视帖学,诋毁指责极尽其词”,同时,他还认为翁同龢为晚清帖学代表,与张旭、怀素以及宋四家等一脉相传⑥。
沙孟海指出碑学发展中掩盖在新型旗号下的两个片面倾向:
1.凡碑皆好;2.无视帖学的优秀传统与成就⑦。
黄惇认为,金农、赵之谦的“稿书”融合碑帖,而杨守敬、沈曾植并不否定帖学,同时提出:
“为什么刻帖漶漫、翻刻失真即当抛弃,而碑刻漶漫、残破模糊,却当备加赞扬呢?
”⑧
以上诸说,都注意到晚清帖学的存在、帖学传统的延续,在相当程度上匡正了康有为在思维方法及推理上的偏失。
晚清以来帖学“坏”与“不坏”的讨论都与康有为的主张有着学术关联,但如何在此基础上厘清晚清以来帖学观念的演变轨迹,梳理帖学书法创作的诸多形态,似乎更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
二、帖学经典的质疑与重新诠释
帖学观念的演变是帖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书家对于帖学经典作品的态度则是帖学观念演变的晴雨表。
所谓“经典”,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兼有“圣典”(scripture)与“古典”(classics)之义,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被崇敬、享有权威,具有无可争议的经典属性”⑨。
书法史上,“书圣”王羲之就是被尊崇的经典书家。
王羲之的“经典化”是在其去世以后的萧梁武帝直到唐初太宗的漫长时期。
几乎同时,他的代表作《兰亭序》也演化成了“经典作品”而影响及于其后的书法史。
更进一步,唐以后各代,被公认为得到王羲之真传的书家也逐渐具有了“经典性”而“经典化”。
然而,到了晚清,“可谓对经典的解说自由度最大的时代”⑩,包括书法经典在内的所有经典,及至圣贤普遍受到质疑。
王羲之《兰亭序》首当其冲,相关解说也显示出极大的自由度。
实际上,对王羲之书法的批评,并非始于晚清。
早在唐代,韩愈有“羲之俗书趁姿媚”的批评,李白也已经有“兰亭雄笔安足夸”、“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等诗句了。
但是,如果从质疑《兰亭》的目的来看,清代以前多为审美判断,而清代以后则多在审美判断之外附加了题外之意。
就拿19世纪来说,否定《兰亭序》的观点主要目的有二:
其一,借否定帖学之最高代表——《兰亭序》来否定王羲之,进而否定帖学;其二,推行碑学主张。
(11)对于碑学家而言,两个目的并非同时达到。
推行碑学在清光绪、宣统年间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而对于《兰亭序》的否定,则是20世纪60年代通过郭沫若之手才达到高潮。
当然,1965年开始的全面否定兰亭的论点并非空穴来风,一如20世纪70年代全面否定孔圣人的风气一样,实际上是中国几百年疑古思潮在当代的变异与反映,其渊源自深。
正如顾颉刚所谓“层累地形成古史”,最初的点滴疑问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不断发展与升级,最后终于变成了全面否定的潮流。
本文选择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几位有着代表性的书法理论家的观点,分析否定《兰亭》的观念嬗变。
19世纪初较早质疑《兰亭》的学者当推阮元(1764—1849)。
阮元在道光初年刊行的《揅经室集》就《兰亭序》提出来的疑问常被后人作为碑派书家否定《兰亭序》的较早例证,如其所谓“《兰亭帖》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化度寺碑》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序》笔法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
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则不知更何境象矣”(12)。
与前人不同,阮元开始强调《兰亭》刻本与“北法”的关系。
“北法为骨”说与翁方纲所谓“雄厚”说相比,更在碑学立场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阮元眼里,仍有一个较大的遗憾:
虽从欧、褚临本可见出其糅合南北法,但《兰亭》真本实则无从知晓。
在此题跋公开之后的道光六年前后,阮元又在晋代残砖拓片后的一段题跋中论及《兰亭》书法特征问题。
阮元认为:
“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
欧、褚二本,直是以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
”(13)其所谓东晋通行字体为隶书的判定以及《兰亭序》非王羲之书的推测,在大约一百四十年后的“兰亭论辩”中被郭沫若作为重要论据。
阮元对《兰亭》风格应与东晋通行隶书接近的推测,在何绍基那里演变为“《兰亭》尤当深备八分气度”。
何绍基认为,《兰亭序》应有八分气度,王羲之行草书全是章草笔意。
这种观点来自于他的《兰亭》八跋。
其首先认为定武兰亭“实兼南北派书理”(14),进而在《跋国学兰亭旧拓本》中申述:
“此帖虽南派,而既为欧摹,即系兼有八分意矩,且玩《曹娥》、《黄庭》,知山阴棑几本与蔡、崔通气,被后人模仿渐渐失真,致有昌黎俗书姿媚之俏耳。
”对于这几种《兰亭》“至为心醉”、“爱玩不释”的何绍基,以《兰亭》归入南派,又认为经过欧阳询摹勒之后的《兰亭》应该“与蔡、崔通气”,兼有“八分意矩”,实际是赞扬欧阳询以南派而兼北法。
联系其《定武兰亭》跋,可知何绍基心中所轻视的并不是《兰亭》本身,而是其所不喜欢的褚临《兰亭》。
这一点与其前的书法界并无区别。
至于包括褚临《兰亭》在内的初唐诸家临本与王羲之书法的差异,何绍基认为是非常明显的,其形成原因主要是时代悬隔,而初唐诸家临本深得其章草笔意:
“右军行草书全是章草笔意,其写《兰亭》乃其得意笔,尤当深备八分气度。
”(15)这里所谓王羲之行草“全是章草笔意”、《兰亭》应“深备八分气度”等,与前文论欧临《兰亭》相呼应,为典型的碑派眼光。
这也正是何绍基不否定未见的王羲之行草与《兰亭》真本的原因。
可以说,对于作为经典的王羲之的重新诠释是何绍基重塑经典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这一点是其后包括李文田、赵之谦、康有为乃至郭沫若等人批评《兰亭》都使用的方法。
从《兰亭》中见出“八分气度”,与何绍基独特的视角有关。
他自己的隶书创作与师承固然为其原因之一,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清代前碑派中隶书热潮所带来的视角变化,这也是将《兰亭》作八分观的时代必然性(16)。
可以认为,简单地说何绍基反对《兰亭》的认识是靠不住的。
不能否认的是,何绍基尊崇《定武兰亭》而贬低《褚临兰亭》的观念,既是对阮元观念的继承,又反映出何绍基“兼有南北法”的艺术追求。
更须注意的是,何绍基认为《兰亭》应该具有“八分气度”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乃师的观点,这也是后来“兰亭论辩”中所谓“王羲之书法应具隶书笔意”之滥觞。
何绍基之后的李文田由此出发进而否定《兰亭》,诠释了这种思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光绪己丑,也就是与李文田交恶的年轻的广东同乡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完稿的这一年,李文田在扬州写下了著名的《兰亭题跋》。
他果断地认为:
“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
”李文田的极端化为典型的反帖学立场。
此种观点上承阮元、何绍基,下启郭沫若,与康有为二王“体兼汉魏”说相呼应,影响极大。
(17)附和李文田之说者,李瑞清可为代表。
其《跋自临兰亭》云:
“李仲约侍郎有三可疑之说,如道人胸中所欲语。
今世所传《兰亭》与《世说新语》多异,‘莫春’作‘暮’、‘禔’作‘禊’、‘畼’作‘畅’,唐以来俗书也,晋代安得有此?
此余所大惑也。
”以《世说新语》之《临河序》与《兰亭》比较,这又为20世纪的“兰亭论辩”提供了一个证据。
(待续)
康有为所谓二王“体兼汉魏”说,与其推广碑学的主张密切相关。
尽管他并没有直接讨论《兰亭》真伪,而是从风格与取法上进行了论述。
在康有为所企图变革的经学与书学领域,绝对经典的“圣人”孔子与王羲之早已深入人心。
康有为深知,对于“圣人”的完全否定时机还没有成熟,绝不能简单否定(19)。
因此,他想出了十分高明的招数。
首先,在经学领域,康有为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树立起“托古改制”的孔子形象(20)。
范文澜认为:
“他把孔子描绘成维新运动的祖师,面貌与古文经学派的孔子截然不同。
就是说,古文经学派的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保守主义者,而康有为的孔子是托古改制的唯心主义者。
”(21)蒋廷黻说得更为直白:
《孔子改制考》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
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
与被尊为“圣人”的孔子相似,书法史上的“圣人”王羲之也在康有为著作中得到了同样的尊崇。
康有为深知,抓住了王羲之,书法史上的观念改革也就可以说成功了。
(22)因此,康有为直接将王羲之诠释为起源于汉魏碑派书法的帖学家,进而将其从帖学的祖师装扮成推举碑学的“傀儡”。
康有为特别标举了传为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所描述的王羲之师承:
右军自言见李斯、曹喜、梁鹄、蔡邕《石经》、张昶《华岳碑》,遍习之。
是其师资甚博;岂师一卫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范围千古哉!
(《购碑第三》) 自唐以后,尊二王者至矣。
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
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
(《本汉第七》) 至于传为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王世贞认为此篇或为蔡希综所见本,或即是《用笔阵图法》,另名《笔阵图》而已。
无论如何,《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并不是王羲之自己的论述则基本可定。
而康有为就是根据这一并不可靠的王羲之自述来推断出其师承渊源。
当然,突出这一师承对于宣传其碑学主张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因此,康有为找到了一个不能上追王羲之的最佳理由:
“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如此。
今人未尝师右军之所师,岂能步趋右军也。
”(《本汉第七》)进一步,他提出要学习王羲之,不应该直接学习《兰亭序》、《圣教序》,而应“师其所师”,以古为师。
纵观书法史,康有为认为,只有颜真卿、杨凝式为活学王羲之的典型。
他认为:
“二千年来,善学右军者,惟清臣、景度耳。
以其知师右军之所师故也。
”(《本汉第七》)换一个角度,可以认为,康有为眼里的颜真卿与杨凝式是值得赞赏的书家,而其值得赞赏之处恰恰在于师法碑学。
当然,康有为标举王羲之及后世帖学家师承源流的目的,并不是主张取法篆、隶,而是在于将优秀帖学家纳入其碑学体系,从而达到提倡“上法六朝”的目的。
他又将文学与书法的取法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为散文者,师法八家,则仅能整洁而已,雄深必不及八家矣。
惟师三代,法秦汉,然后气格浓厚,自有所成,以吾与八家同师故也。
为骈文者,师法六朝,则仅能丽藻而已,气味必不如六朝矣。
惟师秦、汉,法魏、晋,然后体气高古,自有遒文,以吾与六朝同师故也。
故学者有志于古,正宜上法六朝,乃所以善学唐也。
(《导源第十四》) 可以认为,六朝为康有为头脑中可资取法的书法作品的时间下限,这再次呼应了前文所讨论的不学唐人的观点。
其《卑唐第十二》再次表明:
“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
若唐后之书,譬之骈文至四杰而下,散文至曾、苏而后,吾不欲观之矣。
操此而谈,虽终身不见一唐碑可也。
”“古文家谓画今之界不严,学古之辞不类。
学者若欲学书,亦请严画界限,无从唐人入也。
”对这种师法六朝的观念,当时就有张之洞表示强烈不满,其《哀六朝诗》云:
“古人愿奉舜与尧,今人攘臂学六朝。
白昼埋头趍鬼窟,书体诡险文纤佻。
上驷未解昭明选,变本妄托安吴包。
”“政无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皆为妖。
原告礼官与祭酒,輶轩使者分科条。
文艺轻薄裴公摈,字体不正汉律标。
”(23) 从表彰二王到推举碑学,虽则看来毫不相关,但是康有为找到了王羲之师法汉魏碑版这一切入点,进而把王羲之诠释为高举碑学旗帜的书家,为其碑学主张服务。
在康有为那里,帖学家王羲之已经被改头换面,其行草也与隶书紧密地纠缠在一块了。
当年奉劝康有为埋首书法著述的沈曾植则提出“心仪古隶”说:
“右军笔法点画简严,不若子敬之狼藉,盖心仪古隶章法。
由此义而引申之,则欧、虞为楷法之古隶,褚、颜实楷法之八分。
”
(24)沈之所谓“心仪古隶”说与康有为之“来源汉魏”说近似,无非是想将王羲之上溯到隶书,从而令自己的章草取法能有历来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作为楷模。
这与今文经学对孔子的重新诠释是一个道理。
“我注六经”式的自由解说使经典具有了“为我所用”的随意性,这与从《兰亭》中见出“凝厚”、“八分气度”等有着同样的思维角度。
碑派意识的不断介入为晚清帖学的一大特征,而其介入的目的则是将王羲之逐渐异化为碑派之代表,进而否定帖学传统以推崇碑学。
从阮元《兰亭》为梁陈人书到何绍基的“八分气度”说、“章草笔意”说,再到李文田的“二爨笔意”说、康有为的“来源汉魏”说、沈曾植的“心仪古隶”说、李瑞清对《兰亭》的怀疑,可以说构成了否定《兰亭》的观念链条。
这些观念的提出者多有碑学背景,其立场多是碑学的。
因而,其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
19世纪以来对于《兰亭》笔意的碑学阐释链条,实际上是从主观怀疑开始演变到全盘否定的思潮。
现在回头去看,非常清楚的是,这种观念链条恰与近现代的疑古思潮相联系。
从对于古代圣贤或者经典的点滴怀疑开始到全盘否定,不只在书学领域,即便在历史文化的许多领域也在几十年内达到了高峰。
否定《兰亭》就是如此。
郭沫若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将,在历史研究中就有许多疑古而驳古的例证。
尽管其论点在很多时候是颇费推敲的,但也不排除其个人好恶,如对于杜甫的批评与对于李白的推举。
与其一贯研究一样,郭沫若也颇费推敲地在否定《兰亭》的时候找出了许多例证。
除开出土实物证据外,其所举之历史文献则多为上文所提及之晚清否定《兰亭序》的碑学观念链条。
观念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变革的需求,与《兰亭序》的艺术性本无直接因果。
正因为这种需求,《兰亭》才被加以新解,而“兰亭论辩”也才得以进行。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19世纪以来对于《兰亭序》的品评并非一种观点的一统天下,而是两种观念并行。
一种观念是以上所论的以碑法观念逐渐异化《兰亭》与王羲之书法,另一种是传统帖学观念的承继:
嘉道年间,从王宗炎“神物说”,到英和、翁方纲、成亲王等对于火烧本《兰亭》的赏玩、临摹,再到吴荣光自比“萧翼赚兰亭”、郭尚先对《褚临兰亭》“飞动处仍是沉着”的评价与取法,无疑都是崇尚《兰亭》的观念。
咸丰、同治年间,鲁一同作《右军年谱》,钱泰吉评其为“娟秀、清朗、沉雄”,蒋光煦重刻《兰亭》;光绪年间,收藏《兰亭》之风大盛,吴云“二百兰亭斋”、钱塘陈氏“句山精舍”、遵义唐氏等均为收藏大家,沈曾植等将《兰亭》作为书家一大关折,也都是传统帖学观念的延续。
20世纪,以沈尹默为代表的帖学家坚守二王传统,捍卫二王经典地位,使《兰亭序》占据重要位置。
与《兰亭》一样,19世纪以来,作为帖学经典的《淳化阁帖》也经历着类似的重新诠释与承继。
一条线索为推崇《阁帖》者:
嘉、道年间,从李兆洛所谓“足以慰饥渴”,到英和“得数行学之,便可名世”,再到张鑑、包世臣、吴德旋等人的临摹、郭尚先的“古意”说、吴荣光的“日日摩挲”及其“虚和朗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