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docx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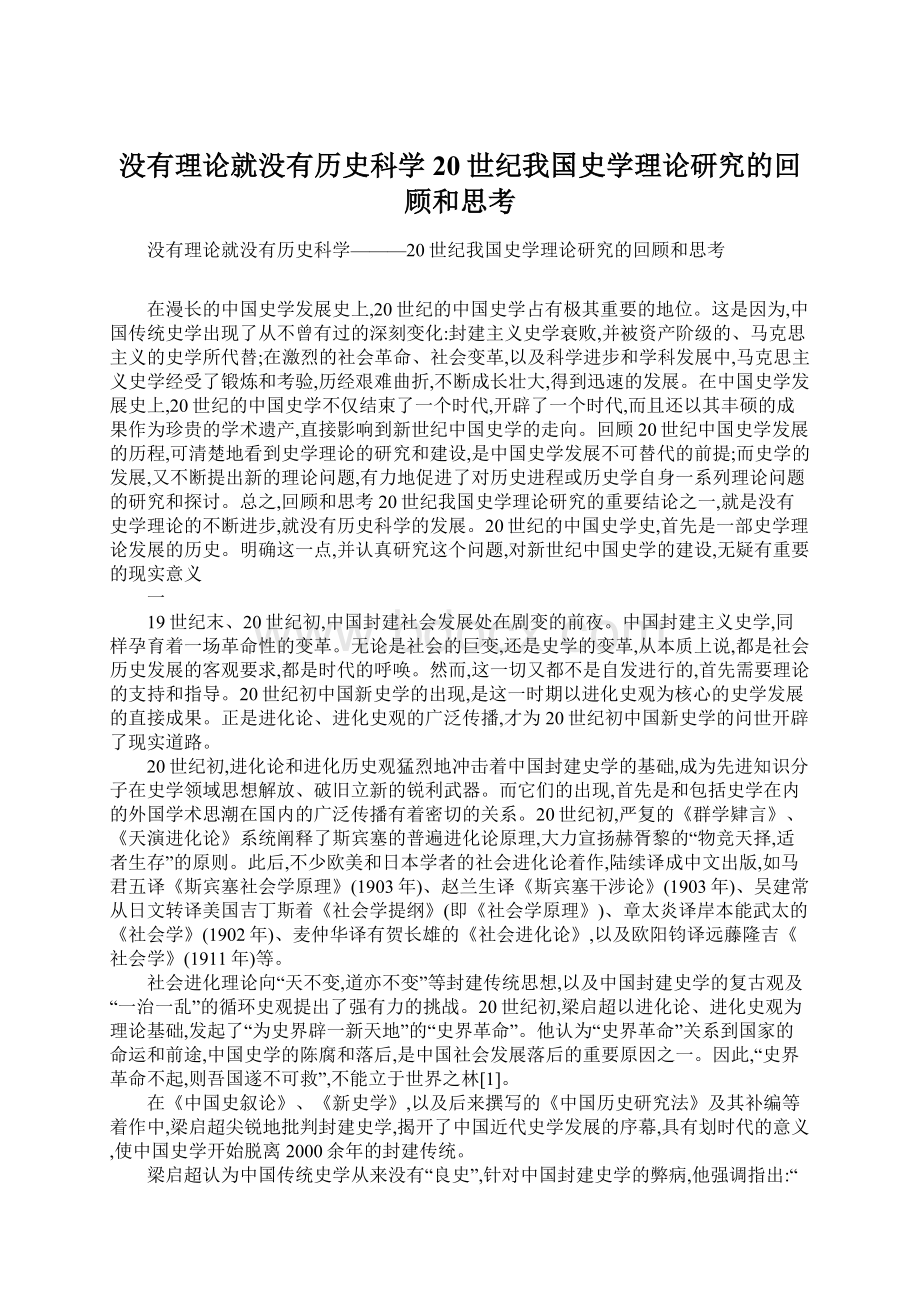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出现了从不曾有过的深刻变化:
封建主义史学衰败,并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所代替;在激烈的社会革命、社会变革,以及科学进步和学科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历经艰难曲折,不断成长壮大,得到迅速的发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仅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以其丰硕的成果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直接影响到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可清楚地看到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替代的前提;而史学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对历史进程或历史学自身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总之,回顾和思考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没有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首先是一部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
明确这一点,并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建设,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
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
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
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
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
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着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着《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
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1]。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着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
“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
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
“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
梁启超力主历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
在他看来,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将历史纳入现代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并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史学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
“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
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
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
除《新史学》(1924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
“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
一些史学家在积极介绍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有益内容的同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开始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
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外,还有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要论》(1930年)等。
这些着述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在中国史坛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派。
“五四”时期,疑古史学思潮的出现和疑古史学的兴起,是中国古典学术“疑古惑经”传统继承和发展的产物,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他的观点得到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知名学者的支持,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史学的疑古派或古史辨派。
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
该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
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着名的命题:
“历史学不是着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
一些论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一个在史学革命尝试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在文化构想层面上有独到的思路。
[10]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短,但直至半个世纪之后,学界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
[11]
20世纪上半期,除了上述论及的“新史学”、“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史料学派”、“战国策派”史学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
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上、地下的文献资料相结合,尽可能地运用更多更新的资料相互印证,去进行历史研究,以求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陈寅恪曾概括指出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以下3条:
(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
(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12]王国维的史学方法是新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是20世纪初中西史学交融的产物。
陈寅恪提出“诗史互证,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主张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将其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和分析。
因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13]他还主张历史研究应有一定的时代的特点,顺应历史的潮流。
他说:
“一时代之学术,比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潮流”。
[14]
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
陈垣虽致力于古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使其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通鉴胡注表微》,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官场的腐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及蔑视。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
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19l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
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
[15]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
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着;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着。
他说:
“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
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
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
”[16]他还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
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
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
[17]李大钊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
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
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着作,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
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迫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即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或经过了那些发展阶段?
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3个:
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
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
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广大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
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那些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而苦闷彷徨,看不清中国革命前途的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绝对统治地位。
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两大方面:
其一,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以其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
其二,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建国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着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
《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文集。
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1954年,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唯心主义批判时,史学界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展开了批判。
不久,陈梦家、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人的史学思想及方法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戴上“反动”、“反马列主义”的政治帽子。
当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以个人治史的切身体会,向学生讲解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时,也受到“为什么不提马列主义这把最灵验的钥匙”的责难。
1958年春,在陈伯达的推动下,史学界开始了所谓的“史学革命”,通过在史学领域大搞“拔白旗,插红旗”,使简单化、概念化、绝对化和庸俗唯物论盛行一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受到严重破坏。
建国后到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不仅批判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而且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争鸣和讨论,都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说,“我国史学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
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
”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
”[18]
当时展开热烈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其中前5个问题被人们称之为“五朵金花”。
这些讨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文革”前,三联书店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景珩、林言椒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史绍宾编)等文集,人们从中不难看到当时讨论的热烈情况。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介绍每一问题的研讨情况,更不可能就每种观点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
下面仅就两三个问题的讨论略作介绍,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仍可从中感受到当时学术讨论的特点。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新建设》杂志1952年5月号即已提出,但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
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论文《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19]对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
范文澜根据斯大林指出的民族的4个特征,(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认为秦汉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民族”的这些特征,同时他又提出“独特的民族”的理论。
强调“汉族自秦汉以来既不是国家分裂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
章冠英等同意范文澜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阶段所占较长,由此产生与欧洲封建社会许多不同的特点。
民族可以形成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秦汉以后的汉民族只能是一种低级阶段的民族”,“只能是一种独特的民族”。
[20]另一种观点表示反对,反对的主要依据是:
按照斯大林所说“民族”的定义,资本主义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因为作为“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的民族市场还无法形成。
他们认为范文澜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理解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是不妥的。
[21]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
范文澜、吕振羽、岑家梧、翁独健等人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即自秦汉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到了清代,我国的版图和疆域便确定下来了。
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起主导作用,其余各个少数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也都为祖国的缔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历史上的中国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中国的历代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也包括少数民族独自建立的国家或政权的辖区;不能将历史上的中国与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与汉王朝划等号。
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长时间互相影响,友好共处,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共同缔造了祖国。
[22]孙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提法,是一种缺乏科学性的论据,存有明显的漏洞。
“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
他认为,凡在封建王朝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应包括在当时的中国范围之内。
以今大的祖国疆域来判断历史上汉王朝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这是荒谬的。
[23]翦伯赞不同意孙祚民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能把少数民族作为“外国人”看待。
[24]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
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是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
翦伯赞早在建国前就提出重视历史主义的问题。
[25]建国后不久,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26]在这之前,范文澜也提出了纠正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问题,他还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为例,进行了自我批评。
[27]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历史研究实践中出现了运用阶级观点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
针对这个问题,翦伯赞提出只有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复杂的历史过程或历史人物做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
[28]
翦伯赞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学者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3个问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如何做到两者相统一等。
当时发表的主要文章后收入《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6年)。
应当指出,当时各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从学术上进行讨论的,正当人们深入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时,戚本禹在1966年初发表文章,从政治上宣布“历史主义是对阶级观点的反动”,[29]从此“历史主义”成为人们不能继续研究讨论的“禁区”,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继续展开讨论。
建国后,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是和新中国的史学建设积极联系在一起的。
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的合理的内容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不良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倾”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不能得到克服。
1961年,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
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的任务。
同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
与会者认为,学习西方史学史,对高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讲,是十分必要的。
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现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的教学计划中。
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
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
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着选》,以及西方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着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着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成果问世。
[30]但是,不少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6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反动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批判。
这样,刚刚起步的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只是停留在规划上,很快就夭折了。
三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
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造谣惑众说: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
”[3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国历史科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革”结束后,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
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