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曾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docx
《陈师曾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陈师曾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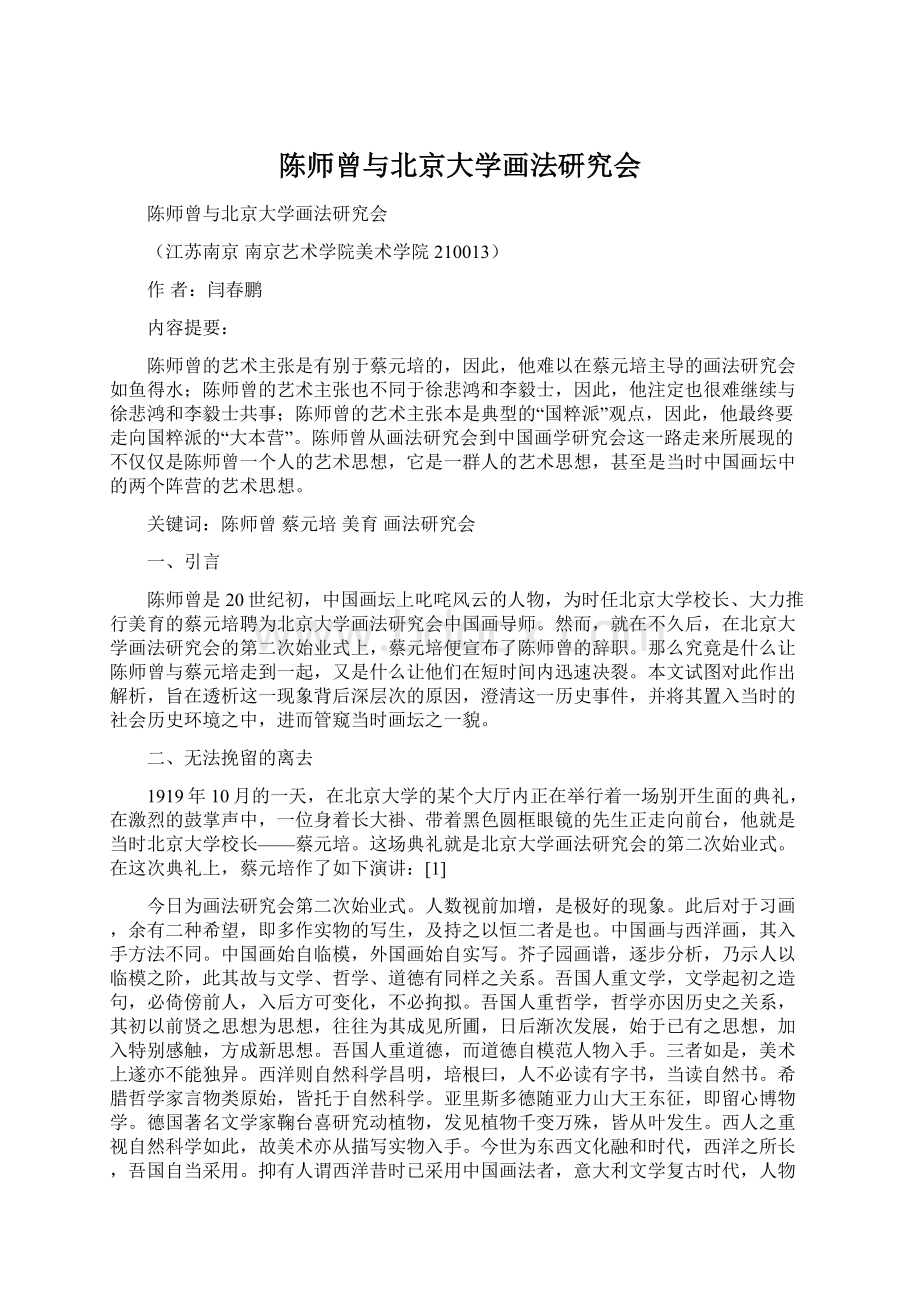
陈师曾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
陈师曾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
(江苏南京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210013)
作者:
闫春鹏
内容提要:
陈师曾的艺术主张是有别于蔡元培的,因此,他难以在蔡元培主导的画法研究会如鱼得水;陈师曾的艺术主张也不同于徐悲鸿和李毅士,因此,他注定也很难继续与徐悲鸿和李毅士共事;陈师曾的艺术主张本是典型的“国粹派”观点,因此,他最终要走向国粹派的“大本营”。
陈师曾从画法研究会到中国画学研究会这一路走来所展现的不仅仅是陈师曾一个人的艺术思想,它是一群人的艺术思想,甚至是当时中国画坛中的两个阵营的艺术思想。
关键词:
陈师曾蔡元培美育画法研究会
一、引言
陈师曾是20世纪初,中国画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力推行美育的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中国画导师。
然而,就在不久后,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第二次始业式上,蔡元培便宣布了陈师曾的辞职。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陈师曾与蔡元培走到一起,又是什么让他们在短时间内迅速决裂。
本文试图对此作出解析,旨在透析这一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澄清这一历史事件,并将其置入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进而管窥当时画坛之一貌。
二、无法挽留的离去
1919年10月的一天,在北京大学的某个大厅内正在举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典礼,在激烈的鼓掌声中,一位身着长大褂、带着黑色圆框眼镜的先生正走向前台,他就是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这场典礼就是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第二次始业式。
在这次典礼上,蔡元培作了如下演讲:
[1]
今日为画法研究会第二次始业式。
人数视前加增,是极好的现象。
此后对于习画,余有二种希望,即多作实物的写生,及持之以恒二者是也。
中国画与西洋画,其入手方法不同。
中国画始自临模,外国画始自实写。
芥子园画谱,逐步分析,乃示人以临模之阶,此其故与文学、哲学、道德有同样之关系。
吾国人重文学,文学起初之造句,必倚傍前人,入后方可变化,不必拘拟。
吾国人重哲学,哲学亦因历史之关系,其初以前贤之思想为思想,往往为其成见所圃,日后渐次发展,始于已有之思想,加入特别感触,方成新思想。
吾国人重道德,而道德自模范人物入手。
三者如是,美术上遂亦不能独异。
西洋则自然科学昌明,培根曰,人不必读有字书,当读自然书。
希腊哲学家言物类原始,皆托于自然科学。
亚里斯多德随亚力山大王东征,即留心博物学。
德国著名文学家鞠台喜研究动植物,发见植物千变万殊,皆从叶发生。
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如此,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
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和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
抑有人谓西洋昔时已采用中国画法者,意大利文学复古时代,人物画后加以山水,识者谓之中国派;即法国路易十世时,有罗科科派,金碧辉煌,说者谓参用我国画法。
又法国画家有摩耐者,其名画写白黑二人,唯取二色映带,他画亦多此类,近于吾国画派。
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
故甚望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像及田野风景,今后诸君均宜注意。
此予之希望者一也。
又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
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
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美虽由于天才,术则必资练习。
故入会后当认定主义,誓以终身不舍,兴到即来,时过情迁,皆当痛戒。
诸君持之以恒,始不负自已入斯会之本意。
此予之希望者二也。
除此以外,余欲报告者三事:
(一)花卉画导师陈师曾先生辞职,本会今后拟别请导师,俟决定后再行发表。
(二)画会会所急求扩充,俟觅得相当地点,再行迁徙,与各会联络一起。
(三)上学年所拟向收藏家借画办法,本年拟实行,拟请冯汉叔先生筹之。
这篇演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蔡元培的绘画思想,对研究蔡元培的画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但除此之外,演讲中还透露了其它的、更为重要信息,那就是在这里他宣布了画法研究会花鸟画导师陈师曾的辞职。
这很可能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
时间回溯到一年多以前,同样是在北京大学的某个大厅里,画法研究会才刚刚开始它的始业典礼,按照计划,作为画法研究会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的蔡元培将要进行一场演讲。
他为此次演讲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并特意撰写了《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
[2]
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之要纲,而大学设科,偏者学理,势不能编入具体之技术,以侵专门美术学校之范围。
然使性之所近,而无实际练习之机会,则甚违提倡美育之本意。
于是由教员与学生各以所嗜特别组织之,为文学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等,既次第成立矣。
而画法研究会,因亦继是而发起。
既承本校教员李毅士、钱稻荪、贝季美、冯汉叔诸先生之赞同,复承校外名家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诸先生之指导,会议数次,遂成立简单如左。
所欲请诸会员注意者,画有雅俗之别,所谓雅者谓志趣高尚,胸襟潇洒,则落笔自殊凡俗,非谓不循规矩,随意涂抹,即是以标异于庸俗也。
本会画法,虽课余之作,不能以专门美术学校之成例相绳。
然既有志研究,且承专门导师之叔率,不可不以科学之精神贯注之。
庶数年以后,成绩斐然,不负今日组织斯会之本意,与诸导师热心提倡之盛意焉。
上下二篇短文,一前一后,同出蔡元培之手,前后时间跨度不足两年,却印证了陈师曾和蔡元培以及画法研究会的合与离。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让陈师曾对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望而却步,放弃了首席校外名家外援的位置,辞职不就呢?
笔者认为这还要从陈师曾和蔡元培的艺术思想说起。
三、陈师曾的艺术主张
陈师曾(1876-1923),名衡恪、号朽者、朽道人,又号槐堂、染仓室、安阳石室,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
陈师曾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字右铭,曾任湖南巡抚,在任时与张之洞、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交往。
他厉行新政,变士习、开民智、饬军政、公官权,开湖湘文化一代新风。
师曾父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光绪12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是著名的“同光体”代表诗人。
这种家庭环境使得陈师曾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国学熏陶,这对他后来坚定支持文人画有着重要意义。
他的胞弟陈寅恪也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之下成长为我国近代史学界的泰斗。
由于陈师曾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再加上他聪慧过人、敏
而好学,使得他在6岁随祖父游杭州西湖时就能写西湖之荷花,并无师承。
10岁时正式随长沙尹和白习画。
1898年,23岁时入江南陆师学堂,1902年,27岁赴日留学,初在弘文学院学日语,后进高等师范学校习博物科。
在日期间与鲁迅、李叔同等人交往甚密。
1909年回国,被聘为江西教育司长。
1910应张謇之邀请,任南通师范教员,与李苦李交往,常随其一起去拜访吴昌硕。
1912年5月在《南通师范校友杂志》发表译文《欧西画界最近之现状》。
1913年任湖南第一师范教员,不久,辞职入京担任教育部编撰,主持图书编辑工作近十年。
在京期间他成为北京画坛的中坚人物,正像阮荣春先生所说的,“如果没有陈师曾,北京画坛或许会暗淡无色”。
[3]在此期间,他还先后受聘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国立北平美术专门学校,参与了宣南画社、中国画学研究会等社团组织,曾先后5次会见了日本文人画复兴运动的发起者大村西崖,[4]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论著,主要有:
《绘画源于实用说》载于《绘学杂志》第一期,1920年6月。
《对于普通教授图画科意见》,同上。
《清代山水之派别》,同上。
《清代花卉之派别》,同上。
《文人画的价值》,载于《绘学杂志》第二期,1921年1月。
《中国画是进步的》,载于《绘学杂志》第三期,1921年6月。
《中国人物画之变迁》,载于《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0年9月。
《中国绘画史》(北京美专讲稿)和《中国画小史》(山东讲稿),1925年由其门人俞剑华在济南翰墨缘出版。
此外,1922年还有《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它共收录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由陈师曾翻译的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的论文《文人画之复兴》,另一篇是陈师曾自己的《文人画之价值》。
陈师曾进入北京画坛之时,正值康有为等人发起美术运动。
他于1917年抛出了著名的《万木草堂论画》,成为美术运动的发端。
文中康有为历数近世中国传统文人画之种种弊端,声称:
“近世中国画衰败极矣,此事亦当变法”。
[5]要求“以复古为更新”,“以院校为正法”,主张借鉴西方美术,改良中国画。
此论一出,一呼百应,陈独秀和吕澂遂举起美术革命之大旗,认为:
“画家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用洋画写实的精神”。
[6]徐悲鸿也认为:
“西方之物质可尽艺术,以此略逊”。
[7]这样,一股革新之风愈演愈烈,他们依靠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对中国传统美术发起了凌厉的攻势,史称“革新派”。
面对革新派的中国画不如西方写实美术的观点和改良中国画呼声,陈师曾并没有盲从,而是进行了冷静的思考。
他针对康有为、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中国文人画不如西方写实绘画的观点,先是发表了《文人画之价值》,指出了文人画的价值所在。
文中他首先澄清了文人画的概念,认为:
“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此之谓文人画。
”[8]又说“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
非机械者也,非单纯者也。
否则,有如照相机,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
何重乎于艺术邪?
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
而文人又其个性优美、感想高尚者也。
其平日之所修养,品格迥出于庸众之上,故其于艺术也,所发表抒写者,自能引人入胜,悠然起澹远幽微之思,而脱离一切尘垢之念。
”[9]这样一来,他把文人画看成是一个画家内在修养在绘画上的体现,他反映出了的是一个人的学问、才情、画中功夫,当然还有画家的人品。
文中他还针对有人提出的文人画中常见的形体不准、肆意涂抹、以丑为美的情况做出回应:
“旷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
!
”[10]他连用五个“何等”,对文人画的景仰之情,表露无遗。
陈师曾在肯定了文人画的价值之后,紧接着就于当年6月发表了《中国画也是进步的》。
他在文中写到:
“我常听着有些人说中国画退步不进步,所以我却不以为然,要说点证据来完满我的意见。
”[11]他首先是对“进步”一词作了详细的阐释:
“说到进步的原则,就是由简单进于复杂,由混合进于区分,不拘滞,善转变。
动植物的繁殖,世界人类之文化以及各种学术之发达都是由这个途辙,经这种阶级缓缓而往前进。
所以我说中国画也是这样。
”[12]接着陈师曾又从中国绘画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画的发展过程,揭示中国画的发展规律,进而证明中国画也是进步的。
除了这篇《中国画也是进步的》外,他的《中国人物画之变迁》,也是站在历史学的高度,对中国画的进步性作出了更深层次的阐释。
他在文章中再次写到:
“现在有人说西洋画是进步的,中国画不是进步的。
我却说中国画是进步的。
”接着他又讲:
“从汉时到六朝的人物画,进步之速,已如上述。
自六朝至隋唐,也有进步可见。
不过自宋朝至近代没甚进步可言罢了。
然而不能以宋朝到现今几百年间的暂告停顿,便说中国画是不进步的。
譬如有人走了许多路,中途立住了脚。
我们不能以他一时的止步,就说他不能步行。
安知中国绘画不能于最近的将来又进步起来呢?
所以我说中国画是进步的。
眼下的中国画进步与否,尚难为切实的解答罢了。
”[13]此外,陈师曾的《清代山水之派别》、《清代花卉之派别》等文章也肯定了清代的山水和花卉的价值所在,实际上也证明了中国画确实是进步的。
陈师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关头肯定文人画,对中国画的发展有着独特的意义。
正如刘晓路说的,“如果没有师曾,也许就没有今天的齐白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画成绩”。
[14]因为陈师曾所生活的社会历史时期,“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向西方学习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众多的仁人志士纷纷向西方投去了学习的眼光,“西学东渐”之风大为盛行。
反映到中国画坛上就是,有众多的画家、学者以及学生开始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去接纳和吸收西方的文艺理论和思想。
其中还有一大批人开始走出国门,进入了更开阔的空间。
他们有的东渡扶桑、有的远渡西洋,他们惊叹着、以狂热的态度追随着西方美术,将其视为艺术救国的灵丹妙药。
于是当他们归来时,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展开了。
西方的哲学、美学、艺术理论、艺术思潮以及艺术创作风格等等像一股强劲的狂风,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在这股强劲的狂风中,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就像一座危楼摇摇欲坠,处于一种被西方美术强行入侵的危险境地。
而陈师曾能在这种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站在历史潮流得对立面,是十分可贵而又必要,同时也是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极大的勇气的。
他的这种勇气源自于他对中西艺术的深刻理解。
正因为他了解西方艺术而不盲从于西方艺术,正因为他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才认识到了时代赋予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他也必须站出来。
不过,正是这些缘于陈师曾对中西艺术内涵深刻把握而产生的一系列论理,却经常被认为是受到了大村西崖的影响。
大村西崖(1868-1927)是日本著名的美术史论家,对中国美术史颇有研究。
他著有《东洋美术大观》(15册,1908-1918)、《东瀛珠光》(1908-1909)、《支那美术史.雕塑篇》(1915)和《密教发达史》(5卷,1918)等著作。
此外,他的专著《中国美术史》由陈彬和翻译,于192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然还有前面提及的与陈师曾合著的《中国文人画之研究》(1922)。
由于大村西崖在日本主要是从事文人画的复兴运动,这与陈师曾在国内提倡文人画步调一致,又加上陈师曾曾经留学日本,于是就有不少观点认为陈师曾是受了大村西崖的影响,才在中国提出了《文人画的价值》等一系列理论。
事实上,这种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从大村西崖的主要著作的出版时间就可以看出,陈师曾留学日本时期,大村西崖有影响的论著尚未发表。
陈师曾也不可能在当时看到他的著作,而受到其影响。
至于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一文更是发表在陈师曾的《文人画的价值》之后。
关于这点陈池瑜在发表于《东南文化》(2006.9)上的《陈师曾中国画进步论之意义》中论证地十分确凿,本文不再赘述。
大村西崖后来之所以能和陈师曾合出《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一书,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艺术主张上有相似看法。
也正是因为二人在艺术主张上有所趋同,大村西崖也才于1921年10月首次通过金城介绍而在北京认识了陈师曾。
也就说他们二人的正式交往是从1921年之后才开始的,此时,他们各自的理论系统已都基本提出。
因此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是肯定存在的,但决不是一个人的思想导致了另一个人的思想的产生。
所以,本文对刘晓路的“只有大村西崖才真正称得上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开拓者”[15]的观点是不敢苟同的。
尽管如此,陈师曾和大村西崖前前后后的5次会面,在当时异常艰难的环境之下相互鼓励、相濡以沫,肯定也是对他们各自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并让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道路上俞走俞远。
大村西崖对于陈师曾的意义也止在于此。
所以,陈师曾逆潮流而行的一系列文人画理论,并非是受到了大村西崖的影响才提出的。
此种理论的提出,得益于他家学渊源,得益于他深厚的国学功底,也得益于他对西方文化艺术的深刻理解。
然而,正是这些基于家学、国学、西学而建立的文人画理论,能够为科举出身的蔡元培的认可吗?
这不得不从蔡元培的美育说起。
四、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和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成立
蔡元培[16]对中国当代之最大之贡献莫过于其美育思想的提出与推行。
早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蔡元培便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戈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拙。
”又曰:
“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
顾抛弃京职,而委身教育。
”[17]遂于1898年冬返乡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后来因为与校内其他教员之旧思想冲突而辞职。
于1901年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司,班中学生有邵闻泰、洪允祥、李叔同和黄炎培等人。
是年冬,蒋观云等人发起学校,蔡元培和陈梦坡等人积极响应建成爱国女校。
初由蒋管理后由蔡接任。
1902年月,寓沪教育家叶浩、蒋观云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推蔡元培任会长。
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开始着手革除封建教育制度,并仿照西方,建立起我国近代教育体制。
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把清末学部制度的忠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实等五项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旨改为新的五项宗旨,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
并提出“注意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这样蔡元培就在教育方针上正式确立了美育的地位,使其成为国民教育的一个基本宗旨。
那么蔡元培所提倡的美育究竟是什么呢?
蔡元培自己曾经在《美育与人生》中对美育及其作用作出过这样的解释:
“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
要转弱为强转薄而溪厚,有待于陶养。
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
”[18]1930年他又在《教育大辞书》中对美育作出如下定义:
“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说的美育就是美感教育,是要通过美感教育,激发、陶冶和完善人们的高尚感情,达到美与善的和谐统一。
因而他又说:
“顾欲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
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也。
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
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
从以上蔡元培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蔡元培所倡的美育精神实际上也是非常符合他自己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的新五项宗旨的另外一项,那就是实利教育。
因为在他看来,美育首先就是提高学生道德的一个操之有效的办法,即以纯粹的美育,激发、陶冶人们的感情,使之有高尚纯洁的情感。
让人们:
“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
”[19]
其次,美育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一种动力。
蔡元培之所以主张科学与美术并重,是由于他认为这两者,即智育和美育应该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互为动力的。
他觉得“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
[20]他以为只有人们具备了高尚的思想情操、强烈的感情推动力,就能够有在科学上探求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
而这种必须的情操和感情正得益于美育的进行。
因而他又说“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
[21]
再者,美育可以培养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革除不良习俗,给人以正当有益的娱乐,提起治学的兴会。
他说:
“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
这使低劣的娱乐消遣活动得以产生,危害身心健康,使他们“不但对于自己毫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就是对于所治的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决没有创造精神”。
[22]
鉴于美育所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蔡元培自然没有不大力推崇的道理。
因此他说:
“教育的方面虽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于科学与美术”,以进一步突出美育的重要性。
又说“文化进步的国民既要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以鼓励美育的推行。
(需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美术的概念乃是借鉴了西方美学思想之中的内容,指的是一种大的美术范畴,所有具有艺术美的形式者,皆属于美术。
就像他自己曾说过的:
“美术本包有文学、音乐、建筑、图画等科。
”因而,这里蔡元培所说美术教育就是他之前所讲的美育。
)
于是,当蔡元培到任北大校长时,他便不再隔靴挠痒,美育也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他开始倾尽全力、身体力行的推进他的美育了。
他不仅是在理论上又相继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新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等言论,而且在北京大学展开了实质上的、更为直接的行动。
他在1917年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亲自主持北大校务。
同年他应邀在北京神州学会做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他认为宗教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于知识的要求、意志的作用和感情的需要。
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知识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进而可以脱离宗教。
随着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发展,意志的作用也脱离了宗教。
“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着,唯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
”然而“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长受宗教之累”,[23]因而,美育也要脱离宗教。
可是,美育脱离了宗教之后应该以何种方式继续进行呢?
事实上,蔡元培早在《美育与人生》中,对美育作出解释的时候就予以了说明。
他说:
“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实际上就是指出了美育的进行要依赖于“美的对象”。
也就是说所有的美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美育进行的工具,音乐、舞蹈、绘画、书法、雕塑、文学、诗歌无不有可能。
因此当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他便主导成立了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等等一系列社团组织,以弘扬美育精神。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于1918年经蔡元培发起成立,它初建时的宗旨是“研究音乐,陶养性情”,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二年他们就成功出版了《音乐》月刊。
至1920年10月,音乐研究会将其宗旨明确为“研究音乐,发展美育”。
[24]
和音乐研究会一样,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也是在蔡元培的主导下发起成立的,它成立的具体时间是1918年2月22日。
还和音乐研究会一样,画法研究会也在成立后不久的1920年6月成功发行了自己的《绘学杂志》,并且还有一些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文章在上面刊发。
它们之间所不同的是,蔡元培在发起成立画法研究会之时要比成立音乐研究会之时具有更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要发展美育。
这可以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中看出,“提倡美育之本意”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而相比较而言,音乐研究会却直到1920年10月,才将初建时的宗旨“研究音乐,陶养性情”,明确为“研究音乐,发展美育”。
对于这种现象的发生,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音乐、绘画自身的特点和美育之间的关系直接相关。
音乐与绘画都可以成为美育的工具,但是二者却又有所不同。
我们都知道,在1917年康有为在他的《万木草堂论画》中就指出:
“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此事亦当变法”。
也就是要向西方学习。
而在音乐领域则没有人大声疾呼:
“中国近世之音乐衰败之极矣”“亦当变法”之类腔调。
究其原因无非是康有为等人所见到的西方美术,确切的说是写实美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不仅仅符合了一些人的审美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在实用功利的这一层面(比如工业设计、图案设计等等)赢得了人们的青睐。
相比之下,音乐则不具备同样的条件。
因此,可以说绘画对于发展美育较音乐更为有力,也更符合蔡元培“实利教育”的原则。
蔡元培在旨趣书中特别强调“不可不以科学之精神贯注之”便是证明。
然而,尽管如此,蔡元培也并非认为所有的美术都是适合发展美育的。
资料显示,他在当时曾对人说:
“我期望这个研究会对中国画坛的除旧布新能起一点启蒙作用,才强调从事美术的人要终身不舍,兴到即来,时过情过,不持之以恒,断无成就”[25]在他看来,旧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显然是不利于美育的进行的,同时也没有起到实用功利的作用。
要推行美育,就必须借助于西方写实美术,这样既推行了美育,又符合了他“实利教育”的思想。
实乃一举两得之策。
于是他用了两个感情色彩异常强烈的词,一个“期望”,一个“除旧布新”。
此话一出,他对待传统美术与西方写实美术的态度就分外鲜明了。
实际上,他对待写实美术的态度,在他的两次演说中均有所体现。
他在画法研究会的第一次演讲就谈到:
“画有雅俗之别,所谓雅者谓志趣高尚,胸襟潇洒,则落笔自殊凡俗,非谓不循规矩,随意涂抹,即是以标异于庸俗也”。
这里看得出他对待“随意涂抹”这一文人画所常表现出的特征是很不屑的。
虽然“志趣高尚”“胸襟潇洒”是文人画本质的特征,但“不循规矩”、“随意涂抹”也往往是文人画的外在表现。
蔡元培这里之所以否定“不循规矩”、“随意涂抹”,实际上还是由于蔡元培对文人画持一种戒备态度。
因为“不求形似”和“肆意涂抹”是和他写实美术的思想乃至美育精神相背道而驰的,也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既然如此,他还为什么还要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