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神病人的恋爱.docx
《一个精神病人的恋爱.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个精神病人的恋爱.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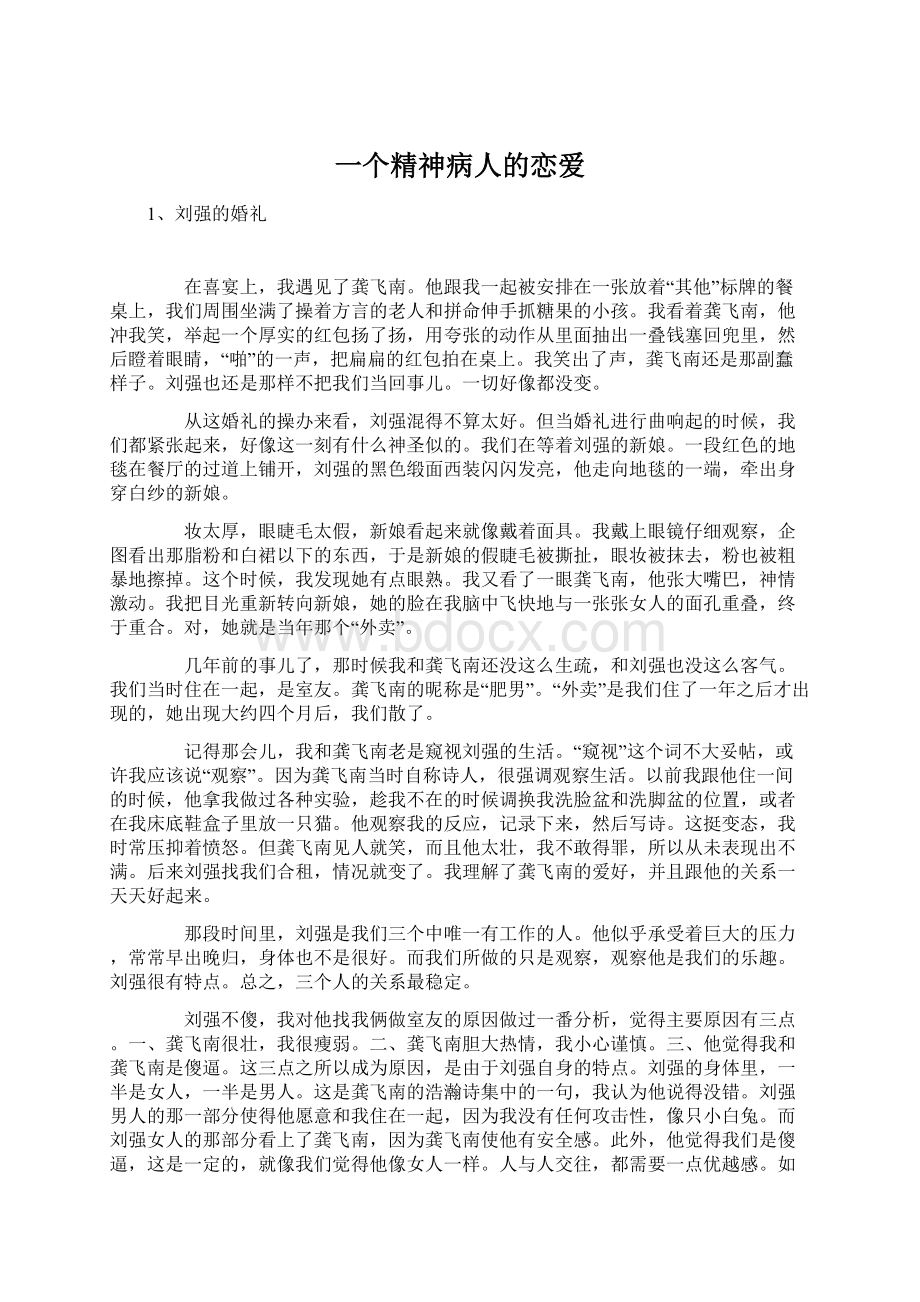
一个精神病人的恋爱
1、刘强的婚礼
在喜宴上,我遇见了龚飞南。
他跟我一起被安排在一张放着“其他”标牌的餐桌上,我们周围坐满了操着方言的老人和拼命伸手抓糖果的小孩。
我看着龚飞南,他冲我笑,举起一个厚实的红包扬了扬,用夸张的动作从里面抽出一叠钱塞回兜里,然后瞪着眼睛,“啪”的一声,把扁扁的红包拍在桌上。
我笑出了声,龚飞南还是那副蠢样子。
刘强也还是那样不把我们当回事儿。
一切好像都没变。
从这婚礼的操办来看,刘强混得不算太好。
但当婚礼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们都紧张起来,好像这一刻有什么神圣似的。
我们在等着刘强的新娘。
一段红色的地毯在餐厅的过道上铺开,刘强的黑色缎面西装闪闪发亮,他走向地毯的一端,牵出身穿白纱的新娘。
妆太厚,眼睫毛太假,新娘看起来就像戴着面具。
我戴上眼镜仔细观察,企图看出那脂粉和白裙以下的东西,于是新娘的假睫毛被撕扯,眼妆被抹去,粉也被粗暴地擦掉。
这个时候,我发现她有点眼熟。
我又看了一眼龚飞南,他张大嘴巴,神情激动。
我把目光重新转向新娘,她的脸在我脑中飞快地与一张张女人的面孔重叠,终于重合。
对,她就是当年那个“外卖”。
几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我和龚飞南还没这么生疏,和刘强也没这么客气。
我们当时住在一起,是室友。
龚飞南的昵称是“肥男”。
“外卖”是我们住了一年之后才出现的,她出现大约四个月后,我们散了。
记得那会儿,我和龚飞南老是窥视刘强的生活。
“窥视”这个词不大妥帖,或许我应该说“观察”。
因为龚飞南当时自称诗人,很强调观察生活。
以前我跟他住一间的时候,他拿我做过各种实验,趁我不在的时候调换我洗脸盆和洗脚盆的位置,或者在我床底鞋盒子里放一只猫。
他观察我的反应,记录下来,然后写诗。
这挺变态,我时常压抑着愤怒。
但龚飞南见人就笑,而且他太壮,我不敢得罪,所以从未表现出不满。
后来刘强找我们合租,情况就变了。
我理解了龚飞南的爱好,并且跟他的关系一天天好起来。
那段时间里,刘强是我们三个中唯一有工作的人。
他似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常常早出晚归,身体也不是很好。
而我们所做的只是观察,观察他是我们的乐趣。
刘强很有特点。
总之,三个人的关系最稳定。
刘强不傻,我对他找我俩做室友的原因做过一番分析,觉得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龚飞南很壮,我很瘦弱。
二、龚飞南胆大热情,我小心谨慎。
三、他觉得我和龚飞南是傻逼。
这三点之所以成为原因,是由于刘强自身的特点。
刘强的身体里,一半是女人,一半是男人。
这是龚飞南的浩瀚诗集中的一句,我认为他说得没错。
刘强男人的那一部分使得他愿意和我住在一起,因为我没有任何攻击性,像只小白兔。
而刘强女人的那部分看上了龚飞南,因为龚飞南使他有安全感。
此外,他觉得我们是傻逼,这是一定的,就像我们觉得他像女人一样。
人与人交往,都需要一点优越感。
如果我不如你会挣钱,那么我的老二就必须比你的大。
尽管没有机会验证,但我们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因此我们的房间分配也是这样,肥男付最少的钱,住靠门最近的小杂物间。
我住在一个小而温暖的客房里,付多一点儿的钱。
刘强则住在最大的卧室,付最多的钱。
肥男当时在厅里摆放着各种体育器材和诗集,有他在的日子里,我们从来没有锁过大门。
新郎新娘从穿过酒席的红毯上走过,拿着筷子的都停手,喝着酒的也把酒杯放下。
让我们为这对俊男靓女祝福!
俊男靓女,我笑了。
这司仪的价格一定不高,但嗓门还是很亮。
大家在他的鼓动下稀稀落落地拍了手。
我的目光掠过新人的假脸,扫向四处的宾客,成功找到了新郎的父母亲戚。
婚礼上我最爱看的就是这个,人只要上了年纪,甭管穿什么衣服,这半辈子过得怎么样,基本还是写在脸上。
我看刘强他妈那身衣服,一定不超过两百块钱,还是新的,笔直的领子一路上去,举着一张旧报纸似的老脸。
我的目光又转移到刘强的脸上,刘强胖了,脸上长出许多粉刺,油汪汪地封锁在表面的那层妆下。
这与我记忆中的他有很大差别。
那会儿他白白净净,春夏只穿x款白色纯棉衬衫,秋天则加一件x款米色大衣,冬天再加一件x款白色毛衣,总之他所有的衣服都是那几个颜色。
住在一起之前我曾以为他不换衣服,直到站在他的阳台上,我被那一片整齐的白色惊呆。
再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习惯了刘强的发胶、粉饼、卸妆油和丝袜霜,他甚至还用丝袜霜!
但我们每天还是把它们当作新鲜事来说。
强儿又在洗澡澡了,强儿又在搽香香了,强儿又在扑粉粉了。
我和肥男当时都是单身,也没有固定工作,夜里只能对着电脑,不是打游戏就是看片。
而刘强告诉我们,他有个日本女朋友。
这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浮现出日本色情片里的女优。
她长得一定不差,因为刘强是个很挑剔的人,他的各种行为和一屋子进口日用品都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们期盼着那个日本女人的出现,但她从没有来。
后来,我们互相暗示刘强是个同性恋,肥男当着他的面开玩笑,赞美他的臀部和大腿,有一次甚至还伸手掐了一把。
这个时候刘强都会咧开嘴笑,那种表情就像大人哄小孩子。
网上有新闻说,这个时代的审美观在变化,男人都追求精致的五官和搭配,漂亮得像女人,还举出好些当红的男明星作例子。
我和肥男都说这是狗屁,女人永远不会喜欢像女人的男人!
大概就这时候,“外卖”出现了。
刘强说这是他同事,我们信了。
半个小时之后,房间里传来男人的喘息和女人的叫声。
我平时不关门,站起来转个身就到了门口,厅里特别暗,肥男竟然没开灯,我愣着站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黑暗,看见肥男坐在沙发上,手机屏幕上的光映着他的脸。
他看着我,招招手,轻声说,过来。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的一张独立的沙发凳上坐下了。
刘强的门缝里透出光,女人的声音又响起来。
“够专业的啊!
”肥男说。
我说:
“那声音就像刘强拿着根一米长的棒子追着她捅似的。
”
肥男笑出声,拍着大腿对我竖起大拇指说:
“你应该写诗!
”
后来就安静了。
房间里响起拖鞋敲打在地面上的声音,床吱呀一声,有人站起来,脚步声也响起。
门锁动了一下,房门开出一条缝,屋子里的光线透出细细一条。
我和肥男都很紧张,开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俩就这样双双坐在沙发上,面朝刘强的方向,一时间脑子空白。
如果刘强走出来,打开灯,看见我们俩对着他的房间坐在黑暗里,会怎么想。
门轻轻地开了,屋子里射出的光线让我们飞速眨了几下眼睛,随后一个披散着头发的女人暴露进我们的视线,她双手扶着两边的门框站着,看起来有些疑惑,很长时间都没有移动步子。
我突然想到,她从光亮的地方进入黑暗,有那么一会儿是看不见的。
并且,她也不知道电灯开关在哪儿。
我们只是静静坐着,她有些慌张,手在墙壁上摸了几下,跌跌撞撞地走到玄关,打开大门走出去。
肥男站起来打开灯,对我笑了一下,十二点了,他说。
后来,我们就开始在背后叫她“外卖”。
一个女孩,第一次去一个男人的出租屋,二话不说就上了床,完事儿之后,男人躺着,自己摸摸索索走人。
半夜十二点,叫个车都难。
“她不是鸡是什么呢?
”肥男说,一边扒拉快餐盒里的饭。
新郎新娘举着杯子朝我们这桌走来。
真是一个土气的婚礼,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刘强穿西装的样子蠢得要命,新娘倒是比以前漂亮了,妆画得得体,头发盘得好看,举止也大方。
记忆中外卖的样子在现场冲击下变得模糊。
我大学老师曾说,现代社会女人的适应能力比男人强,她们更易摆脱阶层的影响。
我想他说得没错,目光下移,我看见新娘的小腹微微隆起。
大家都站起身,举杯。
龚飞南已经独自喝了很多酒,他神情凄惶地看着新娘,像条狗。
我也盯着她看,想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们,她没理由不记得,但她就是没看我们一眼。
他们俩对这桌的客人一视同仁地笑笑,在一堆人的簇拥下转到下一桌。
那一桌差不多都是我们的同龄人,却很热闹,我猜那些应该是他的同事什么的,新郎新娘站在那边,笑得也比较大声。
我环顾我们这一桌的客人,除了龚飞南,都是老人、妇女、小孩。
刘强还是那样不把我们当回事儿。
我记得当初合租的时候,他对送外卖的都比对我们热情,让人家下雨天小心,戴手套带伞,弄得那个送外卖的大叔受宠若惊,一定要帮他倒垃圾。
我和肥男从没领教过他这样的态度,那个大叔都够当他爸了,他讲话就像领导慰问受灾群众。
旁边那一桌在起哄,他们拉着新郎新娘,似乎是要他们交待认识经过。
我竖着耳朵听,听见断断续续的几个字,好像是旅行、培训班什么的,刘强又大声炫耀了一句:
“我老婆很厉害的,还会说日语。
”我觉得好笑,当初我和肥男都觉得她是网站上叫来的,或者是手机上约的。
刘强说的是同事,她当然不是同事。
因为刘强从来不让她跟我们说话,我猜他是怕她露出破绽。
这就使得她更像“外卖”了,因为每次她都一言不发,来了就进房间,办完事儿就走。
其实这有什么?
刘强何必在意,叫鸡就叫鸡吧。
至于他的日本女朋友,我们确定她一定不存在。
有些事情刘强不知道,要是他知道了,一定不会请我们来他的婚礼。
我们本来就淡薄的情谊,早就该烟消云散。
事情回到当年当月,那天晚上十二点过后,外卖已经离开,我回到房间锁了门,打开吉泽明步的片子狠狠撸了一把。
所以说我是个孬种,上天永远不会眷顾我这样的人,因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肥男追了出去,他在附近的一个路口找到了孤零零的“外卖”,她在那儿打车。
肥男是这样讲述的:
“那天的马路是一条黯淡的星河,她纤细的手臂在夜空中平举,仿佛即将起舞。
”我敢保证那段时期肥男见到任何女人都想来一发,他二十七年从没交过女朋友,没约过炮,也没叫过鸡,他肯定憋坏了。
据肥男说,那天他陪着外卖沿河一路走。
他说要帮外卖打车,外卖接受了,但俩人等半天也没见着车。
河岸边种杨柳,还种着其他花草植物,路面铺着小石子,外卖穿着高跟鞋,走两步就崴个脚。
俩人越靠越近,肥男闻着外卖身上的香气。
其实很难说那香气到底是外卖的还是刘强的,因为刘强总是很香,外卖出来也没有洗澡。
反正管他呢,肥男就是闻着外卖身上的香气,身体一阵战栗。
他在月光下仔细观察外卖,外卖低头不说话,头发盖住半个脸,他只看见外卖的鼻头,这鼻头略大,但是光滑细腻,白净水润,上面好像附着薄薄一层汗,又好像萦绕着淡淡雾气。
一个夜间跑步的男人喘着气从他们边上跑过去了,大概因为静,或是男人已经跑得很累,他的喘气声特别大,就像对着肥男的耳边吹气一般,肥男又战栗了。
他一直陪着外卖走,走到再也没有小路和植物的地方,他们俩暴露在大马路上。
出租车来了,外卖走了。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有没有对话,应该是有的,也可能没有。
肥男自认为是个诗人,他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诗性”,但配合他的人并不多。
外卖能在大半夜和他这样无声地并肩走,也挺不容易。
此后的每个周末外卖都来,基本上情况和第一次一样,进门、打炮、出门。
只是有了一点小小的差别,她进门如果看见肥男坐在沙发上,都会对他笑,嘴也张得大大的,好像要说什么话。
这时刘强会有些尴尬,他显然不愿意外卖开口说话,三步两步走进房间,外卖只得紧随其后。
刘强怕什么呢?
怕我们怀疑他们的关系?
怕我们询问他的日本女友?
他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那些个周末太难熬,外卖无休无止地在刘强的房间里叫。
她的行为也日渐大胆,从踮着脚进门到踩着高跟鞋踏在地板上。
那地板可是我和肥男拖干净的,一三五是我,二四六是他,刘强永远早出晚归,拖地的事儿从来不干。
外卖就那么踩在我们地板上,高跟鞋哒哒响,就像踩在我们脊骨上似的。
有时她还穿着雪白的浴衣从洗手间出来,裸露的肌肤上漂浮着带香味的水蒸气。
我们四只眼睛扫射着她,她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最后我们用一种很男人的方式报复了她:
她洗澡的时候,肥男用我做的飞机杯撸了一管,然后在她的鞋子里放进那只用过的避孕套。
我还记得那天她绷着脚尖往鞋子里踩,发出的那一声尖叫。
不久之后,肥男告诉我,他和外卖恋爱了,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
龚飞南在我眼里,一直还算正常,虽然他有时候会做出一些出格的行为,但我始终认为,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并且知道分寸,因为他从未真正惹出过什么事儿。
大学时候,他曾经号召同学罢课,理由是他认为自己没学到东西,并且不知道我们专业开“思想政治”课有什么用。
他在下课之后堵着门,把我们所有人关在教室,让我们投票,胆小的女生们都缩在一边,吓坏了。
男生们则各有各的态度,这事儿最后当然没成,他也没再闹腾。
后来,他要求在这门课上读诗,读他写的诗,他写毒奶粉、地沟油、塑料、甲醛、转基因,然后跳起来骂“我操你们的妈”。
他的口水四溅,额头上密集的红疙瘩由于震怒而爆裂,流出黄色黏稠的液体。
我们温柔美丽的女老师被吓坏了,她说:
“飞南啊,你不要这么愤怒,你找个女朋友,谈谈恋爱就好了!
”再后来,他翘掉了思想政治课。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老拿思想政治课出气,大概是这门课的女老师太漂亮了。
特别归特别,评奖评优,入团入党,龚飞南什么都没落下。
他总是在大家聚会的时候板起脸,质问我们为什么不严肃,然后露出被世俗所伤的表情。
他似乎藐视一切,却喜欢在简历的背后附上长长的一封信,列举学院各位教授的各种头衔,然后加上一句,他们肯定了我。
尽管如此,这样一封长信也从未帮助他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现在,我看着餐桌另一头的龚飞南,他的样貌与几年前无大改变,甚至还穿着当年寝室里那件大红运动服,唯一的差别只是那红色有一点儿淡了。
龚飞南的目光扫过来,和我对上了,我连忙低下头去,有些后悔自己对他那一笑。
我打开手机游戏,感觉到一个身影在身后晃了几晃,龚飞南似乎有些犹豫,但还是拍了拍我的肩。
“你还玩儿这个呢!
”他说,是我熟悉的嘲讽语气。
我抬头看他一眼,重新把手机插进兜里,冲他笑了笑。
“出去聊会儿?
”他说。
当初肥男告诉我,他和外卖恋爱了。
但事实是,外卖依旧每个周末进出刘强的房间,叫声也没有变得小一点儿。
肥男对我的解释是:
“这两者并不冲突。
”
肥男在每个周末的夜里,都会在外卖走后的五分钟之内追出去,追出去的时候他穿着跑步鞋、运动衣,当外卖看见他的时候,他以专业的姿势在跑步。
外卖没有打到车的时候,一个人沿着马路向前走,肥男在离她不远不近的地方跑,偶尔停下来做个锻炼,压压腿之类。
肥男还有绝活,他在大学的时候是“跑酷”社团的,动不动就能飞檐走壁。
因为这个做不好很危险,肥男很少在我们面前尝试,但在跟着外卖跑步的一个夜里,他做到了。
当时四周寂静无人,他像闪电一样击中了外卖前方五米处的水泥围墙,然后一个后空翻,翩翩而落。
外卖尖叫了一声,随即说:
“你好厉害!
”
肥男对外卖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觉得性和爱是可以分开的么?
”
外卖对肥男说的第二句话是:
“我鞋子里那只避孕套是你放的么?
”
我不敢相信肥男和外卖就这样开始了恋爱。
从那时候起,每个周末外卖从刘强的房间出来之后,肥男就像保镖一样站起来,为外卖打开门,护送她离去。
剩下的近一个小时,就是肥男和外卖的约会时间,这段时间他们都走在大马路上。
外卖其实住得不远,不用一个小时就走到了。
现在女孩子出门都爱打车,逛街却永远不累,外卖也一样。
她能够每次都让肥男陪着步行回家,实属难能可贵。
就这一点,日后便被肥男列为他们之间爱情存在的佐证。
“她绝对、绝对、绝对是喜欢我的!
”肥男说。
我不知道肥男和外卖在一起的具体情况,只知道肥男在那一段时间里的思想和行为都超出我的理解。
客观地说,这可能发生吗?
一个女人跟一个屋子里的两个男人恋爱,跟一个打完炮之后,由另一个送回家?
但事实就是这样,我经过一番思考后得出三种可能性:
一、三个人中有一个人不知道这种关系,只能是刘强不知道。
二、三个人中有两个人不是恋爱关系,我倾向于肥男自作多情。
三、三个人中没有恋爱关系,也就是说,外卖是个“鸡”,她下班之后,谁管她干什么。
列出以上三种可能性之后,我突然又想到一种可能性,这最不符合常人的逻辑,但最符合肥男的叙述:
四、肥男确实在恋爱,外卖是个“鸡”,她上班的时候和刘强打炮,下班的时候和肥男恋爱。
肥男不是说吗?
“这两者并不冲突。
”
这符合肥男的救世主心态,他一直想做点特别的事儿,那次他终于做了。
2、谁他妈的需要救世主
其实当初我和龚飞南并没有真的认为外卖是鸡。
我们只是嘴上说说,她和刘强或许是平等的“炮友”,而不是买卖。
“鸡”这个称呼比较难听,“外卖”好一点,我们不过是开个玩笑,私下叫叫。
并且,我现在敢于承认,当时我对刘强是有些嫉妒的,我想肥男也一样。
刘强当时在一家很大的金融公司工作,早出晚归,过着紧张的上班族生活。
我们却像小老鼠一样躲在出租屋里,对周围的一切既鄙夷又慌张。
肥男永远在一个工作和下一个工作之间跳跃,我则窝在房间里替网站写论文为生。
我们三个在刚刚搬到一起的时候过了一段充满希望的愉悦时光,一起添置家庭用品,买菜做饭打dota。
直到刘强进入万恶的金融公司上班,我们的关系一天一天在变化。
刘强的话变得少了,他的生活变得独立,用老话形容,“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他像一颗加工考究的钻石,对我们呈现出每一个切面的光滑。
所以当我们看见外卖的时候,有些希望她是“鸡”,并且是最下等的“鸡”,最下贱的“鸡”。
龚飞南此刻搭着我的肩往外走,另一只手顺了饭桌上两瓶啤酒。
我个子比他矮,后颈被他夹在胳肢窝里,油腻腻的,很不舒服。
走出喧闹的大堂以后,街面上的凉风贴地而来,绕着我脚脖子打着转往上走。
我闻到龚飞南身上强烈的汗骚味,试着挣了一下,他松开我,递给我一瓶啤酒。
“怎么样啊?
”他说。
“什么怎么样?
”我说。
他看我一眼,目光闪烁,又马上转移到别处,然后扬起头喝了一口酒。
路灯下我看见他下巴上有一溜胡子没刮,挺长了,看那走势,不像故意留的。
“没怎么样!
都没怎么样!
”他扯着嗓子怪叫,几只栖在暗处的鸟扑腾着翅膀飞起来。
他咕噜几下把剩下的酒全灌进喉咙里,然后向前一阵小跑,加速、用力,他踩上一颗老树,向上几步、跳跃,他要后空翻了,我忙不迭叫了一声好,只听见树皮哗啦一响,他像只被射伤的巨大的鸟,重重地落在树叶和尘埃里。
“你没事吧?
”我跑过去扶起他。
“没事。
”他说,“你先别扶我,让我看看这星空。
”
肥男告诉我,他和外卖恋爱的时候,在一起讨论了非常多的“哲学问题”,他们俩从“性和爱是否可以分开”一直聊到婚姻制度,又从婚姻制度聊到黑洞,从黑洞聊到达尔文,又从达尔文聊到马克思,从马克思聊到弗洛伊德……我忍不住打断他,我说一个做鸡的懂得这些?
肥男很郑重地说:
“她或许不懂,但她懂得倾听。
很多人说自己懂,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不懂自己不懂,还不如她懂自己不懂。
她懂得这一点,就已经胜过很多人。
她很简单,也很纯朴,我在启蒙她,但她或许很快就会胜过我。
还有,周光明,你以后不要再叫她‘鸡’,她才不是‘鸡’。
她是性爱自由。
‘鸡’是什么称呼?
你太不尊重女性!
”
肥男比我壮,否则我肯定会揍他。
肥男是认真的。
他甚至计划了他和外卖两个人的未来。
那时候他就像个小男孩,用想象力把所有不合理的都合理化。
他每个周末都坐在沙发上等外卖从刘强的房间里出来,然后陪着她一路走回家。
每次他回来都跟中了大奖似的,跑进我的房间里喋喋不休。
他告诉我,外卖从小生长在海边的一个小渔村里,父亲以打渔为生,母亲整天坐在家里补网,腌鱼,卖鱼干。
后来她父亲在一次出海时遇到大风浪,卷到水里被渔网缠住淹死了。
母亲哭瞎了双眼,无以为生,她带着母亲一路乞讨来到城市,后来遇到一个按摩师收留了她们,但当她十五岁的时候,按摩师逼迫她从事性服务,她为了生存忍受屈辱,最后在一个夜晚带着母亲逃离了他的家……
“够了肥男,她电视剧看多了,你也信?
”我说。
龚飞南当时很震惊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的震惊从何而来。
当我抬起头看他的时候,他眼睛里已经有了泪花。
“至于吗?
”我笑着说,“你们拍电影呢?
”我想缓和一下气氛。
“周光明!
”他大声说,“人类需要悲悯!
”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回应他的,他的吼叫让我觉得十分没面子,我大概想给他一个不屑的表情,但是面部肌肉还没来得及调动,左颊上就挨了一拳。
肥男每天四十公斤的哑铃不是白举的,那一拳让我省下了拔智齿的钱,我从客厅的沙发上一直滚到餐桌脚下。
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疼痛中震动起来,发出嗡嗡的叫声。
我再也不管龚飞南的事儿了。
从那以后,他的行为变得更加疯癫,他有时候一个人在屋子里,摇滚乐震天响,有时候又一个人在阳台上傻笑。
我那些天常常想,肥男的父母是什么样儿的,他们为什么能养出这么个奇怪的儿子。
接下来的时间里,微妙的情愫就像喝了尿的青苔,在刘强二十平米的卧室暗暗生长。
当它终于蔓延开,从门缝潜入我们客厅的时候,肥男发现已经晚了。
刘强第一次在我们面前和外卖有了交流。
我相信肥男和我一样都听到了那几句话。
男:
“外面在下雨吗?
”
女:
“在,咳咳。
”
男:
“你穿得太少了,有点感冒了吧?
”
就这么几句,刘强演绎得极其温柔缱绻。
那天刘强的房门虚掩,里面不断飘散出食物的香气、电影嘈杂的对话和配乐,屋子里一直笑声不断。
我不知道肥男是怎么度过那几个小时的,他一直坐在沙发上发呆,晚饭也没有吃。
夜色包裹了他,他就像个天桥下的流浪汉一样蜷缩着,直等到外卖推开房门。
他又看见外卖呆立在黑暗里,只是这一次她说话了,很娇憨的语气:
“好黑啊……”那个“啊”字拖得很长。
刘强从房间里出来了,他为外卖点亮了一盏灯。
“开关在这”,他抓着外卖的手按上去,“啪”的一声,悬在肥男头顶的那只巨大的吊灯亮了,肥男被那突然的光束罩住,他闭着眼睛在那片耀眼的光中站起来,就像一个要谢幕的演员。
我后来陪着肥男一起去找了外卖,外卖和我们住的地方其实只隔着一条河,但我们不能游泳、或者划船过去,我们得沿着大马路走,再爬过立交桥。
过了桥之后,肥男带着我穿过水果摊、烧烤摊、菜市场、废品收购站,我们走到一片被拆了一半的居民区中间,肥男指着其中一扇亮着灯的窗户说:
“她就住那儿。
”
我看见一幢歪歪斜斜的三层小楼,表面的涂层掉得干净,只剩下光秃的水泥,亮着的那扇窗上贴着一个惨淡的红色“?
帧弊郑?
窗子下边有一道横幅:
“国法在哪里?
公民的人身权利在哪里?
”横幅旁边有一道竖幅“坚决抵制暴力拆迁”。
我反复看了几遍,最后目光停留在“人身权利”几个字上。
“你确定是这儿吗?
她带你来过?
”
“没有。
”肥男说,“她每次都让我送到前面那个小区。
”他往前指了指。
我看见远处隐约有一个装着欧式大门的小区,上面镶嵌几个字,好像是“什么什么苑”。
“她还挺讲面子,那你是跟踪她了?
”
“不算吧,你看这小楼比那小区显眼多了,是谁都会看两眼。
而且……”肥男又指了一下,“没什么隐私的。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果然,屋子里的人站起来了,真的是外卖,她身处的狭窄空间看起来并不比那扇窗子大多少。
她咬着半个苹果走到窗边,只穿了件吊带背心,或许是因为热,她把已经打开的窗又推了推。
“一个人住在这可真够大胆,走吧!
”我说。
“喂。
”她说。
“我……我是龚飞南……” “我知道,你有什么事?
”她在苹果核上啃了最后一口,然后向外一抛,苹果核在我们眼前划出长长一道弧线。
“我,我在你家外面呢,想跟你谈谈。
”
我看见外卖定住一秒,然后慌张地把身子往窗外探,肥男赶紧拉着我后退几步,旁边一个破旧的雨棚耷拉着,勉强能遮挡我们。
我和肥男赶紧往“什么什么苑”那里走,过了十几分钟,她真的从大门里出来了。
她披了件松松垮垮的衬衣,穿着紧身短裤,人字拖鞋,个子不高但身材不错,丰腴型的,我不禁想象起她在刘强房间里的样子。
她远远看见肥男旁边还有个人,立刻像受了惊吓似地停住了,我猜她有些近视,便上前几步,举起手摆了摆。
“哦,是你。
”她说,勉强笑了笑。
“你们有什么事?
刘强知道你们来吗?
”
我摇摇头,肥男一言不发,气氛有点奇怪。
肥男身高一米八八,柱子一样杵着,神情像个被侵犯的小女孩,这使我也变得可笑,就像是个讨说法的单身妈妈。
“你是刘强的女朋友吗?
”我一开口就感觉到自己的愚蠢。
“你不是我的女朋友吗?
”肥男说,“我们都说好了,今年过年我会带你回家,见我父母。
你可以在我家乡的旅行社找份工作,我表姐表姐夫都是旅行社的;你也可以去移动通信营业厅,我大姑二姑都在那。
你妈也可以接过来,我三叔的老房子能住,我会帮忙照顾她……”
我看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