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族与国族之间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docx
《在种族与国族之间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在种族与国族之间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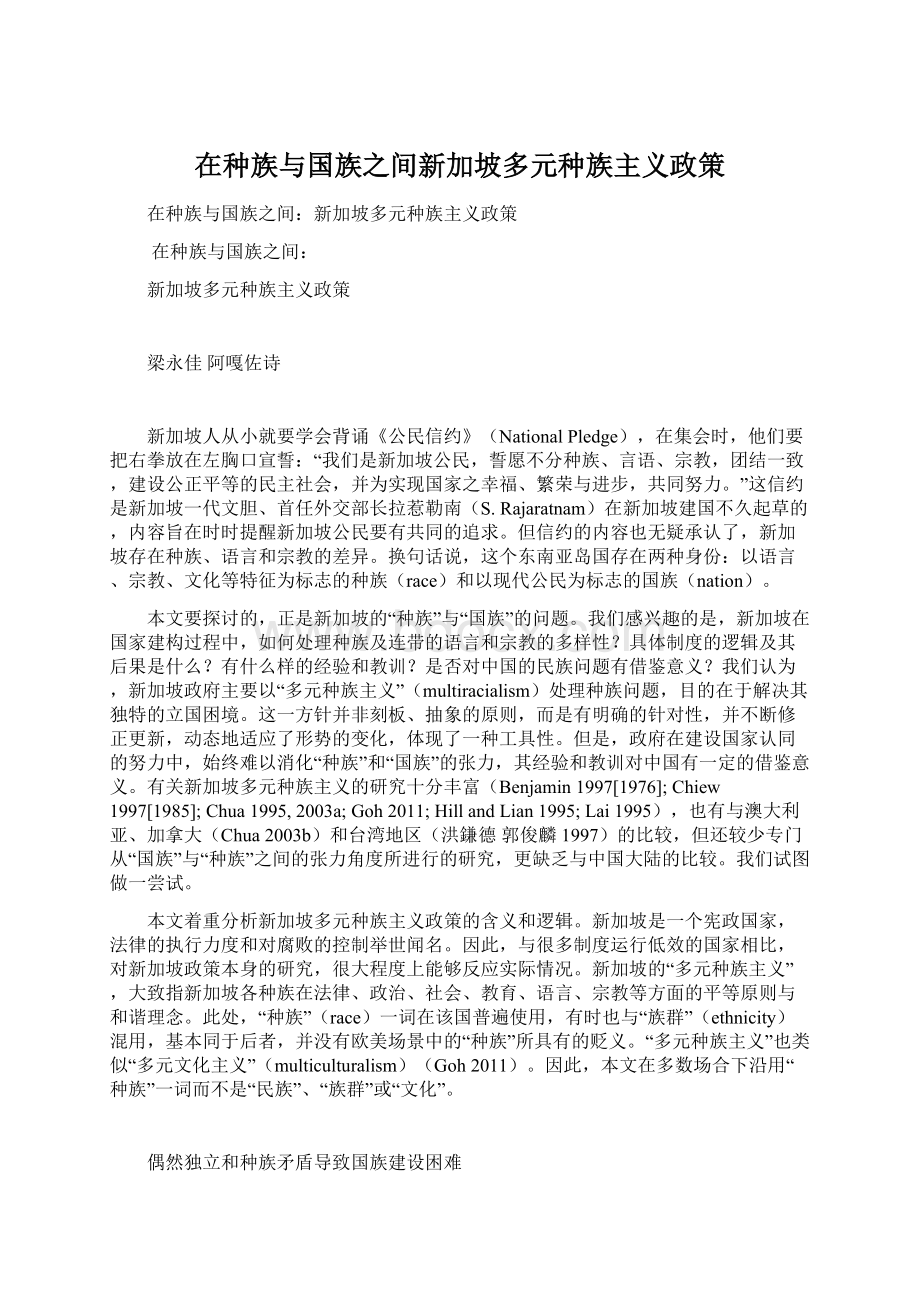
在种族与国族之间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
在种族与国族之间:
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
在种族与国族之间:
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
梁永佳阿嘎佐诗
新加坡人从小就要学会背诵《公民信约》(NationalPledge),在集会时,他们要把右拳放在左胸口宣誓:
“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这信约是新加坡一代文胆、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S.Rajaratnam)在新加坡建国不久起草的,内容旨在时时提醒新加坡公民要有共同的追求。
但信约的内容也无疑承认了,新加坡存在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
换句话说,这个东南亚岛国存在两种身份:
以语言、宗教、文化等特征为标志的种族(race)和以现代公民为标志的国族(nation)。
本文要探讨的,正是新加坡的“种族”与“国族”的问题。
我们感兴趣的是,新加坡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处理种族及连带的语言和宗教的多样性?
具体制度的逻辑及其后果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是否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借鉴意义?
我们认为,新加坡政府主要以“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alism)处理种族问题,目的在于解决其独特的立国困境。
这一方针并非刻板、抽象的原则,而是有明确的针对性,并不断修正更新,动态地适应了形势的变化,体现了一种工具性。
但是,政府在建设国家认同的努力中,始终难以消化“种族”和“国族”的张力,其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有关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的研究十分丰富(Benjamin1997[1976];Chiew1997[1985];Chua1995,2003a;Goh2011;HillandLian1995;Lai1995),也有与澳大利亚、加拿大(Chua2003b)和台湾地区(洪鎌德郭俊麟1997)的比较,但还较少专门从“国族”与“种族”之间的张力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更缺乏与中国大陆的比较。
我们试图做一尝试。
本文着重分析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的含义和逻辑。
新加坡是一个宪政国家,法律的执行力度和对腐败的控制举世闻名。
因此,与很多制度运行低效的国家相比,对新加坡政策本身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能够反应实际情况。
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主义”,大致指新加坡各种族在法律、政治、社会、教育、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平等原则与和谐理念。
此处,“种族”(race)一词在该国普遍使用,有时也与“族群”(ethnicity)混用,基本同于后者,并没有欧美场景中的“种族”所具有的贬义。
“多元种族主义”也类似“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Goh2011)。
因此,本文在多数场合下沿用“种族”一词而不是“民族”、“族群”或“文化”。
偶然独立和种族矛盾导致国族建设困难
现代新加坡没有拥有主权的“土著”,这是“多元种族主义”的一个前提。
历史上,新加坡虽然时常因贸易而导致人口聚集,但一直不是一个定居地(MiksicandLow2004)。
1819年成为新加坡历史的转折点。
这一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代表莱佛士(StamfordRaffles)来到此地,利用马来半岛的政治矛盾,从廖内柔佛(Riau-Johor)苏丹手中购得这个被称为“淡马锡”的小岛(阿嘎佐诗2007:
28-30)。
购买手段虽受到争议,但马来人却因此丧失了对该岛的所有权。
新加坡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人口由1819年的150多人(120名马来人,30几名华人)增长到1871年的97,000人,华人也成为主体(56%),并在1921年达到75%。
从此以后,新加坡的四个种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其他人,人口比例基本稳定在75:
13:
9:
2。
这些人都是移民,在英帝国开埠之前也没有一个政体,甚至没有固定人口,其殖民化并非武力征服,而是商业开埠。
因此,虽然新加坡地处“马来世界”(Nusantara),虽然华人占据四分之三强,但马、华两族都称不上对新加坡拥有特权,更不用说其他种族了。
新加坡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立颇为偶然。
1957年,英国政府兑现二战期间的承诺,让马来亚(Malaya)独立。
而与马来亚经济一体、政治密切的新加坡则保留在英帝国内,并于1959年获得除外交、国防、财政之外的自治权。
李光耀(LeeKuanYew)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在大选中获胜组阁,并执政至今。
为了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和华人民族主义势力,李光耀力主新加坡加入马来亚。
马来亚首相东固·阿都拉曼(TunkuAbdulRahman)也担心左翼势力坐大,同意将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北文莱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
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大英帝国,将新加坡的“SI”两个字母放入新的国名,成为马来西亚(Malaysia)的一部分。
但是好景不长,新加坡政府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分歧很大。
马来西亚处处突出马来人的土著特权,并以马来语为国语和通行语言,华商又因与苏加诺独裁政府过于密切而遭到排挤。
新加坡华人众多,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受到不少限制。
与此同时,新、马两地的种族冲突在合并后持续恶化,东固首相逐渐感到无力驾驭局势,终于要求新加坡退出联邦。
1965年8月9日,在与东固会面之后,李光耀悲伤地宣布新加坡独立,并一度哽咽失声,这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独立场面。
独立的偶然性给国家认同带来巨大困难。
新加坡缺乏“想像共同体”的基本素材。
首先,新加坡一直属于大英帝国,并一度属于马来西亚联邦,本土民族主义从来不是选项。
其次,新加坡的三个主体民族来自三个强大文明,且都已经获得独立,民族主义强烈。
很多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刚刚迁来不久,或者只是移民二代。
他们各自忠于自己的“母国”,到此地只是谋生或躲避战乱,对新加坡缺乏认同,时刻准备回“家”。
要说新加坡有民族主义,那只有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民族主义。
第三,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既没有一部殖民之前的“史前史”可供追溯,也没有一部争取民族独立的“血泪史”可供夸耀。
新加坡的独立是被迫的、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
没有人为独立流过血,因此也没有光荣可言,连英雄纪念碑或无名烈士墓都无从建造。
最后,独立后的经济前景也十分黯淡。
新加坡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马来西亚的橡胶和锡的转口,英军在此时撤出更使当地失去了至少五万个工作机会。
新加坡不仅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可供开发,连淡水都无法自给自足。
独立后的新加坡在国家认同上几乎处于“赤贫”状态。
更为头疼的是种族之间的冲突。
英国殖民者分类管理的做法,使新加坡形成了各种族聚居区,如华人的牛车水、马来人的芽龙、印度人的小印度等。
日本占领的历史和新加坡随后的合并、独立,导致种族冲突加剧。
1950年12月,新加坡法院裁定13岁的女孩玛丽亚·赫托(MariaHertogh)抚养权归属其荷兰天主教亲生父母。
玛丽亚二战期间被其生母交给一个穆斯林家庭养育,她只懂马来语并且一直接受伊斯兰教教育。
当她在圣母像前祈祷的形象公布之后,穆斯林社区发生骚乱,马来人和少量华人走上街头袭击欧亚混血人,酿成18人死171人伤的严重种族骚乱。
另一场骚乱同样与日据时代有关。
日本军队在占领期间(1942-1945)将马来人、印度人与华人区别对待,要求前两者成为顺民,促使大量马来人与日本占领军合作。
但华人则受到严厉镇压,数万人被怀疑支持中国本土的反日斗争而惨遭日军杀戮(Blackburn2005:
92)。
日本战败后,共产主义等左翼政治理念在华人当中传播很快,更加剧了马来人与华人的矛盾,并随着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而激化。
1964年7月,在穆圣诞辰庆典的游行过程中,新加坡马来人与华人发生冲突,导致23人死亡,454人受伤。
有人认为这是新、马分家的导火索(Lee2011:
262)。
总之,如何发展经济、防范种族冲突、建构国家认同,成为新加坡成立之初的当务之急(Chua&Kuo1991)。
多元种族主义是一种国家治理术
为处理棘手的种族问题,新加坡建国之初就将“多元种族主义”确定为宪法原则。
不仅宪法规定种族在权力、义务、教育、工作等方面一律平等,而且专门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少数民族权利总统理事会(PCMR)”和“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PCRH)确保各项法律和政策必须维护“种族和谐”。
45年以来,“种族和谐”在社会政策和公共舆论中无孔不入,总理和政府官员、议员在国会辩论、施政演讲、国庆集会、社区视察等几乎所有场合,都不忘连篇累牍地强调“种族和谐”,强调和谐来之不易,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强调种族和谐的国家之一。
实际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为何新加坡如此不遗余力地突出它的“多元种族”特性,并在公共政策中如此彻底地贯彻多元种族主义原则呢?
答案就在于,多元种族主义不仅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国家治理术。
用蔡明发的话说,多元种族主义被塑造成一种“公共的善”(Chua2003a)。
新加坡对各种族的定义采取了不同的标准。
殖民时代的人群分类,并非仅仅四个种族,有时人口统计竟然可以多达200多个。
新加坡正式认可的四个种族(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其他族)是一个斯科特(1998)所说的“国家的视角”,其目的在于避繁就简,其代价是也正是斯科特所说的“地方知识”(Metis)的流失。
由于冷战环境,使得新加坡必须避免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穆斯林国家的夹缝中制造“第三个中国”(当时很多国家仍然与台北保持“外交关系”),使用“华人”(Chinese)是为了强调与“中国人”或“汉族”的差异。
在新加坡的华人虽然多数来自闽粤两地,但他们基本是按方言聚集的,主要为福建话、潮汕话、广东话三种方言,此外还有闽南话、客家话、海南话等方言社区。
其结社方式既有家族又有地域,甚至有同姓结社,形成新加坡著名的“宗乡文化”(Liu&Wong2004)。
华人的宗教活动也千差万别,有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组织,也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徒。
此外,早期华人移民也在长期的本地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即近年蜚声海内外的“巴巴娘惹”)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宗教多受马来文化影响,并且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李光耀就来自土生华人家庭。
因此,很难说存在一个统一的“华族”。
华族是通过语言建构的。
新加坡独立后,实行“双语制度”,即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同时,要求各种族必须学习自己的“母语”。
华人由于方言众多,政府就规定“普通话”为华人母语,要求华人子弟学习,并禁止媒体使用方言。
这导致不少“地方知识”的流失。
首先,很多从小说方言的华人不得不像学习外语一样学习普通话,但收效并不理想。
虽然政府曾开展过“说普通话”运动,教育部也多次降低华语门槛,甚至取消高等学校入学中的母语考试,但由于英语在谋生方面的优势,使得很多新加坡华人长期轻视普通话学习,流利使用普通话的人一直算不上很多,只是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才有所改善。
其次,由于方言的边缘化,导致大量只会说方言的华人失去就业机会,很多家庭在祖孙之间无法沟通。
笔者经常能在新加坡的公共熟食中心,看到老年华人守在无声或声音很小的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台湾的方言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往往长达数百集,深受华人欢迎。
但由于必须用普通话配音之后才能播出,以至于这些老人无法听懂,只能看华文字幕!
总之,华人之间的公约数被指定为“普通话”和华文,“华族”因此也是用语言创造出来的种族。
“马来人”(Malays)内部也有区别,可以分为爪哇人、巴达人(Batak)、博亚人(Boyanese)、武吉士人(Bugis)、米南佳保人(Minangkabau)和马来半岛人,但其公约数并非通用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语(Bahasa),而是被定义为“伊斯兰教”(新加坡华语沿用“回教”)。
也就是说,一个不说马来语的穆斯林华人、南亚人或阿拉伯人,都成为马来人。
为了平息马来人的挫折感和回应来自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压力,新加坡规定马来人享有宪法赋予的土著身份,马来语也被定为“国语”,国歌也用马来语写成。
但是,根据双语政策,非马来族公民无需学习马来语,以至于很多国民并不太清楚国歌的内容是什么。
可见,马来族是通过“宗教”想像的。
新加坡的“印度人”(Indians)更是一个地理概念,即南亚次大陆的移民或移民后代。
他们虽然人口很少,但却无法用“语言”或“宗教”统一。
虽然多数印度裔人来自印度南部或斯里兰卡北部的泰米尔地区,并且信奉印度教,但印度种族中,也有锡克教、耆那教、赛巴巴教、佛教等教徒,说印地语、乌尔都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
作为大英帝国的扩张中心,南亚次大陆的各个民族长期向亚洲、非洲,甚至太平洋群岛迁徙,并在客居地以殖民者的面孔出现,与英国殖民政府紧密合作,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印度人”认同(Metcalf2007)。
新加坡政府继承并强化了这种认同。
政府建立了印度教(新加坡华语称“兴都教”)和锡克教等宗教基金会,又允许他们以各自语言为母语。
印度人虽少,但他们却成为重要的“第三方”,避免了华人和马来人矛盾过于明显,也为多元种族主义的“多”字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其他人”(Others)是指不能归为上述三种的种族,其主体为欧亚人(Eurasian)。
他们的数量很少,多半是英、葡、荷、西、法等欧洲人与亚洲人的混血后裔,此外还有少数独立后入籍的犹太人、日本人等。
这些人的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已经达到12万5千(2010年),占总人口的3.3%,政府对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常与印度人放在一起。
总之,新加坡使的“种族”并非体质差异(种族一词的本意),而是语言(华人)、宗教(马来人)、地理(印度人),或者“三者皆非”(其他人)的区别。
“多元种族主义”的工具性十分明显。
新加坡对各种族的治理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对华人和马来人尤其如此。
对于华人,政府致力于消除其内部亚族群组织和泛华人组织,边缘化其语言,力图将华人分解为一个个公民,直接面对国家。
华人自开埠以来,以迁出地或姓氏为单位,自行组织了各种祠堂、宗乡会、商会,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形成了一套华文教育体系,课本也直接从台湾或者香港运来。
辛亥革命以来,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在华人中间有巨大影响,秘密会社的活动在不同职业中十分活跃,中国国家认同较强。
上至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很多华人终其一生只说华语。
全岛最大的华人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SCCC)更于1955年创建了以华语为教学语言的南洋大学(NanyangUniversity),并聘请林语堂为首任校长。
人民行动党执政后,认为如果强化国家认同,就必须拆解华人组织。
政府于是以国家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逐渐取代这些组织的功能,并以“华人沙文主义”为名关闭大量华文报纸,还以普及英文教学的方式排挤华文学校。
最终,政府以中文文凭不具备竞争力为由,关闭了南洋大学,使很多华人至今对此仍耿耿于怀。
但这些举措,使华人不再具有完整的自我更新体系,不得不通过“公民”身份直接面对政府。
政府对马来人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将其组织起来,以共同体身份与国家产生关系。
在法律上,全体马来人属于一套特别的法律体系管辖,即《施行回教法法令》(AMLA)。
根据这一法律,马来人的最高权力归“回教事务部长”(MinisterforMuslimAffairs),下设“新加坡回教理事会”(theIslamicReligiousCouncilofSingapore,马来语称MajlisUgamaIslamSingapoura),其中包括“回教法庭”(ShariahCourt)的“回教宗教司”(Mufti),负责与伊斯兰法律有关的事务。
这一机构管理包括清真寺和伊斯兰婚姻在内的宗教和家庭事务。
作为具有土著地位的马来族,马来语教学对全体国民免费,但马来人传统上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弱势(Lai1995)。
政府拨款通过马来议员建立机构,提高马来儿童的学习成绩,也曾一度负责解决吸毒问题。
(后来由于新加坡动用重刑禁毒,使毒品在新加坡基本绝迹。
)
作为传统聚居区的马来社区,则受到有意的拆解。
此处,将“community”理解成有地域含义的“社区”还是无地域含义的“共同体”十分重要。
实际上,拆解马来社区是创造马来共同体计划的一部分。
此处涉及新加坡闻名遐迩的“政府组屋”计划。
新加坡从60年代开始,就成立了建屋发展局(HousingandDevelopmentBoard,简称HDB),负责拆除村落和贫民窟,大规模建造廉价公寓楼(新加坡称“政府组屋”),并以99年为限出售给家庭。
这一计划获得极大成功,既避免了政府承受巨大财政负担,也让民众有了自己的家。
今天,高达85%的新加坡人住在“政府组屋”中,新加坡也因此成了少数几个成功解决住房问题、消灭贫民窟的城市,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对象。
但政府开发组屋,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散传统的种族聚居模式。
从1989年3月起,政府更为严格地实施打散方针,规定组屋必须按固定的种族比例出售。
其中,华族在每个社区比例不得超过84%,每一栋组屋公寓楼内不得超过87%;马来族分别为22%和25%;印度族和其他族一起,不得超过10%和13%。
政府组屋计划旨在拆解传统社区,让各族比邻而居,增加了解,打破社区封闭性。
但这一举措主要受到影响的是马来人。
穆斯林习惯上在清真寺周围聚居,并在局部成为多数。
实行组屋计划后,马来人和印度人在任何地方都成为永久少数,而华人则在任何地方也成为永久多数。
这一计划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组屋转手的时候,经常因种族配额已满而无法卖出好价钱。
而且,十分重视邻里关系的马来人和印度人,经常无法在组屋附近找到可以分享宗教和传统知识的同族家庭。
政府对于马来人的另一个特殊措施则与马来人在区域内的微妙地位有关。
新加坡马来人基本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的议员、社区领袖经常评论在新马来人的境遇,而新加坡马来议员常常反唇相讥。
2001年,新加坡总理评论在新马来人学校成绩优于马国马来人,导致马来西亚传召新加坡驻马大使。
在新马来人由于同马国和印尼的穆斯林有着“兄弟情谊”,很多人有着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以至于政府对他们在国家安全上心存戒心。
新加坡从1968年开始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度,中学毕业的男子一律服役两年,但马来人直到70年代才允许服兵役。
政府的理由是,一旦与邻国开战,马来族军人将处于两难境地:
是向新加坡国民开枪,还是将枪口指向邻国的穆斯林兄弟。
可以说,通过独立法律体系和专门阁员的方式,马来人和新加坡国家之间植入了一个中介。
这与处理国家与华人关系的做法相反。
虽然存在专门针对某一种族的政策,但总的来说,在政治和社会权利上,新加坡特别重视保护少数种族,以体现各族平等的政策。
例如,国家机构和国有企业必须平衡种族身份,其份额甚至具体到分支部门。
所以,在新加坡工作,你会发现同事中3族俱全,尤其那些稳定的工作位置更是如此。
公共服务设施也必须有4种文字标识(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国家媒体必须有4种语言频道,公共熟食中心必须有3种食品供应,清真和非清真摊位相邻但又严格区分餐具,公共卫生设施必须有能满足3个种族习惯的装置。
此外,政府还会动用《国内安全法》、《煽动法》、《维持宗教和谐法》,起诉那些公开发表破坏种族和谐言论的人,包括外国人,甚至在国外发表危害新加坡种族和谐言论的外国人,也可能在访问新加坡的时候,遭到起诉。
在政治权利上,新加坡于1988年引入“集选区”(GRC)制度。
在集选区参选的政党,要推出4名候选人,其中一人必须是少数族裔,其身份必须经过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少数民族权利总统委员会”认可。
得票最多的组合“通吃”整个选区4个议席,共同进入议会。
这个制度,保证了少数族裔的政治地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多元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简化原则,方便国家治理。
种族的分类原则各不相同,对待种族的政策也各不相同。
实际上,多数政策和原则是针对某一特定问题制定的,并不一定惠及或伤及所有种族。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家对于种族问题极为重视,且不遗余力地将多元种族主义贯彻到方方面面,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种族成为一个随时随地都会见到且需要处理的因素。
国族与种族的张力
无处不在的“多元种族主义”,将国民的种族身份固化了。
长期以来,一个新加坡人必须属于而且只能属于一个种族,一般根据生父的种族确定。
一个人要学习本族语言和英语,熟悉本族的风俗习惯。
这使种族身份不强的家庭也可能产生种族意识强烈的后代,或者让种族意识不强的人持续处在焦虑之中。
例如,一个华人基督教徒要熟悉被其宗教排斥的华人民间宗教节日。
一个从小只说英语的华人,可能因为不懂“母语”而遭到奚落。
一个沾过酒的马来人,更要面对马来共同体的巨大压力。
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曾在给笔者之一的课程作业里写道:
“我有一个印度名字,因为我父亲是印度族,但我却长着一副华人的面孔,像我母亲。
在机场打计程车的时候,督导员经常以为我们是两拨人,把我和母亲指向一辆车,再把我父亲指向另一辆车。
我跟母亲说海南话,全家人都在的时候说英语,我的泰米尔语一直不好。
”强制单族归属的政策,导致种族互动困难,个体难以摆脱种族标签所施加的压力。
种族之间只能共处,无法融合,彼此了解仅流于表面。
多元种族主义突出“集体间平等”的原则,而不是个体间平等。
所以,上面几个例子中,本属个体权利的语言权利、宗教权利、饮食权利,都不得不让位于集体权利。
蔡明发称之为“社群主义意识形态”(Chua1995)。
更大的困难在于国族认同。
早在1976年,本杰明就用韦伯的“理想型”模式,分析了多元种族主义的“文化逻辑”。
他准确地预测到,过分强调种族将使身份固化,融合困难:
“紧紧抓住多元种族的社会模式不放,等于关闭了其他非种族的社会模式……有些人或许多多少少已经厌倦了专门为多元种族主义生产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他们终究会在脑海中冒出些奇思怪想,构想出某些与多元种族主义相反的非种族模式。
问题在于,新加坡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是否灵活到足以允许人们做出这样的改变”(Benjamin1997[1976]:
80)。
身份固化导致“种族”与“国族”之间持续存在紧张关系,使国族认同的资源捉襟见肘。
因为语言、宗教、服饰、饮食、艺术、家庭模式等领域都已经贴上了种族标签,可供“新加坡特性”(Singaporeness)占领的空间变得非常少。
政府为此动了不少脑筋,四十年来推行了众多促进国族认同的政策。
除了世界各国司空见惯的国族认同手段,如国家象征、纳税、服兵役、普及教育等,新加坡还尝试了不少独特的国族建构政策,有的行之有效,有的半途而废。
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就将英语设为通用语言,又将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英语设为官方语言。
逐渐形成了用英语交流的模式,很多家庭都以英语作生活语言。
政府将殖民者的语言普及化,是因为英语的“中性”,可以避免华语或者马来语造成的、其他种族或周边国家的反对。
使用英语也使得新加坡在吸引外资方面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经济快速起飞的原因之一。
但实际上,所谓英语的“中性”,只是在种族意义上说的。
能讲好英语的人,多出自中产阶级或精英阶级。
由于英语在华人中的普及,原本英语程度较好且与殖民政府合作紧密的印度人,逐渐失去了在政府部门中的优势地位,英语也成为日常使用的语言。
但是,多数人的英语语法简单,有自己的口音,很像洋泾浜,新加坡称之为Singlish。
即使英语已经成为多数人的母语,Singlish依然可以在街头巷尾随处听到。
政府多次开展“说好英语”运动,但收效欠佳。
吊诡的是,政府反对的Singlish,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新加坡特色之一。
很多普通新加坡人都喜爱Singlish,认同其地方性。
精英中也不乏以Singlish为豪的人。
像“说好英语”运动这样的计划,反映了新加坡政府的一项重要原则——贤人制度(Meritocracy)。
政府以“现代主义”为旗帜,特别强调国民之间的公平竞争、任人唯贤。
“现代主义”在建国之初体现为“生存”的话语,政府要求民众为生存而努力奋斗。
随着经济奇迹般的发展,新加坡迅速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现代主义又从“生存”转换成了“繁荣”的话语。
纯粹个体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的竞争,成为每个国民根深蒂固的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