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志寰访谈录.docx
《傅志寰访谈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傅志寰访谈录.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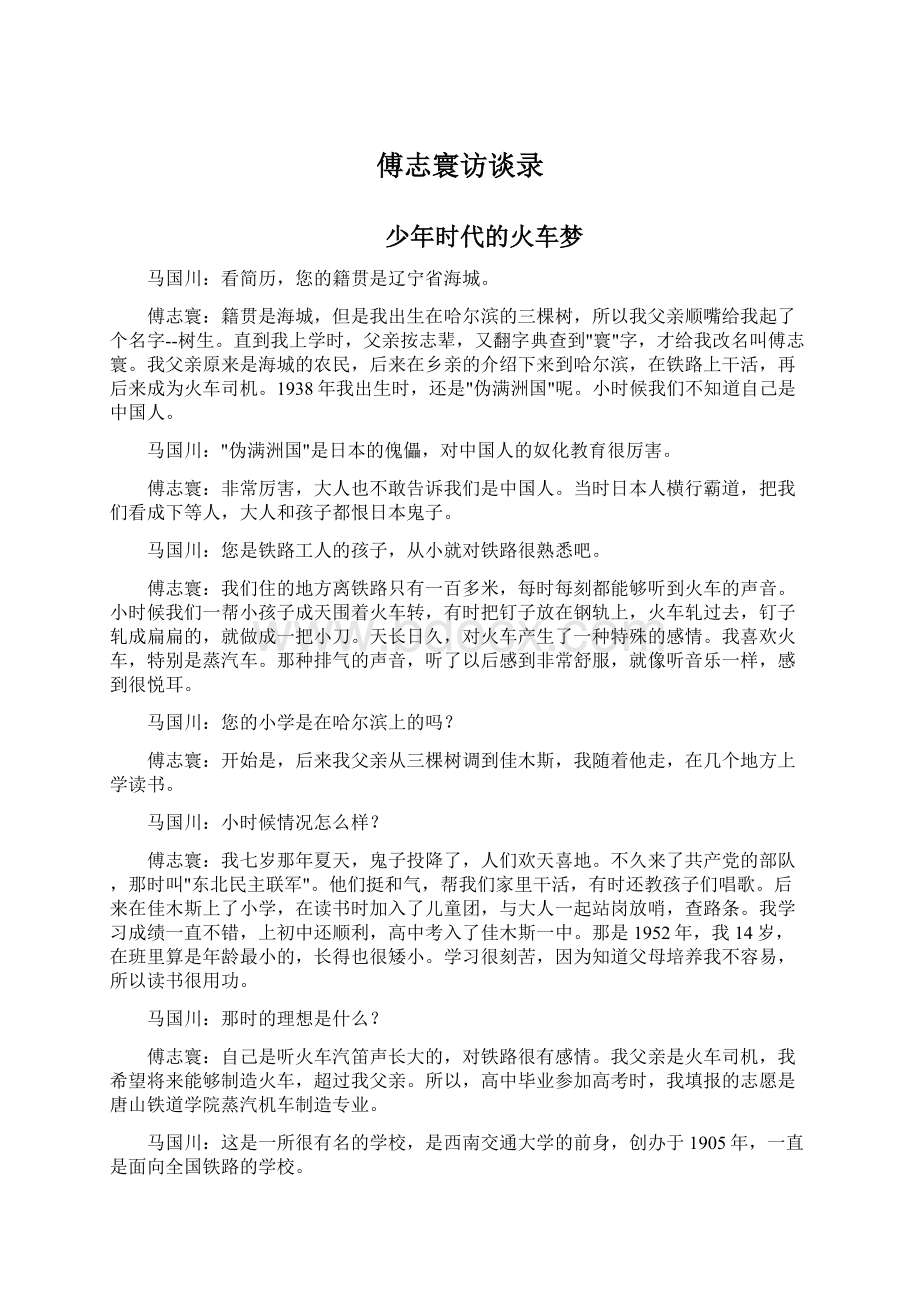
傅志寰访谈录
少年时代的火车梦
马国川:
看简历,您的籍贯是辽宁省海城。
傅志寰:
籍贯是海城,但是我出生在哈尔滨的三棵树,所以我父亲顺嘴给我起了个名字--树生。
直到我上学时,父亲按志辈,又翻字典查到"寰"字,才给我改名叫傅志寰。
我父亲原来是海城的农民,后来在乡亲的介绍下来到哈尔滨,在铁路上干活,再后来成为火车司机。
1938年我出生时,还是"伪满洲国"呢。
小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马国川:
"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对中国人的奴化教育很厉害。
傅志寰:
非常厉害,大人也不敢告诉我们是中国人。
当时日本人横行霸道,把我们看成下等人,大人和孩子都恨日本鬼子。
马国川:
您是铁路工人的孩子,从小就对铁路很熟悉吧。
傅志寰:
我们住的地方离铁路只有一百多米,每时每刻都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
小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子成天围着火车转,有时把钉子放在钢轨上,火车轧过去,钉子轧成扁扁的,就做成一把小刀。
天长日久,对火车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喜欢火车,特别是蒸汽车。
那种排气的声音,听了以后感到非常舒服,就像听音乐一样,感到很悦耳。
马国川:
您的小学是在哈尔滨上的吗?
傅志寰:
开始是,后来我父亲从三棵树调到佳木斯,我随着他走,在几个地方上学读书。
马国川:
小时候情况怎么样?
傅志寰:
我七岁那年夏天,鬼子投降了,人们欢天喜地。
不久来了共产党的部队,那时叫"东北民主联军"。
他们挺和气,帮我们家里干活,有时还教孩子们唱歌。
后来在佳木斯上了小学,在读书时加入了儿童团,与大人一起站岗放哨,查路条。
我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上初中还顺利,高中考入了佳木斯一中。
那是1952年,我14岁,在班里算是年龄最小的,长得也很矮小。
学习很刻苦,因为知道父母培养我不容易,所以读书很用功。
马国川:
那时的理想是什么?
傅志寰:
自己是听火车汽笛声长大的,对铁路很有感情。
我父亲是火车司机,我希望将来能够制造火车,超过我父亲。
所以,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我填报的志愿是唐山铁道学院蒸汽机车制造专业。
马国川:
这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905年,一直是面向全国铁路的学校。
傅志寰:
当时佳木斯一中内定我可以报考留苏预备生,但还要和其他同学一样填志愿。
我一直学习成绩稳定,不怕考试,可是高考前一天失眠了,结果自己感觉考试成绩不理想,很郁闷。
等了很久,有一天我接到了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的通知书。
马国川:
这意味着您可以到苏联留学了。
傅志寰:
留学是年轻人的梦想,尤其是到苏联留学更了不起,当时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中,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
在上世纪50年代,年轻人都喜欢看苏联电影,唱苏联歌曲,读苏联小说。
当我拿到从北京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时,全家都非常高兴,母亲正在切菜,激动得把手切破了。
因为像我这样的工人家庭,在解放前,根本没有条件供我上大学,更谈不上留学了。
上北京,我背着铺盖,带着母亲煮的十几个鸡蛋,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
当时还有前门火车站,我在那里下了车,坐了一辆三轮。
经过天安门时还觉得奇怪呢,天安门怎么变矮了?
不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么高。
马国川:
到北京来是为了补习俄语吗?
傅志寰:
对,我们这一批学生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补习俄语,也进行政治学习。
考大学时,我报的志愿是蒸汽机车制造。
组织上跟我说,苏联大学已经淘汰了这个落后的专业,你还是学电力机车吧。
我当然很高兴,从此我就和电力机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去苏联前国家出钱给每人制备了两套西服,还有大衣、衬衫、内衣,整整两个箱子。
在苏联留学的日子
马国川:
1957年你们去苏联留学,还是坐火车吧。
傅志寰:
先坐中国自己的火车,然后到满洲里换上苏联的火车,开往莫斯科。
我们穿越了整个辽阔的东西伯利亚和半个欧洲,路上走了七天七夜多。
马国川:
感觉枯燥吗?
傅志寰:
一点儿也不。
漫长的旅途本来是枯燥的,但对我这个十分向往苏联的年轻人,一切都很新鲜,只要天没黑,两眼就盯住窗外。
看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赤塔、伊尔库斯克、新西伯利亚……还有农村、森林。
从前没见过的电力机车、内燃机车一路上看了个够。
每次停站,我都要下火车,走到列车前面仔细看看火车头。
一到莫斯科,我就给两个高中同学写了封长达十页纸的信,让他们也分享我的兴奋和喜悦。
马国川:
在莫斯科您进的是莫斯科铁道学院。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傅志寰:
莫斯科铁道学院是20世纪初建立的著名的老学校,在苏联很有名。
但有些条件不如当时我国的名牌大学。
教学楼不大,是由三个不同年代的建筑连接起来的。
校园里没有操场,得乘两站电车到公共体育场上体育课。
但是,教师却是一流的。
数学教授讲课不带讲义,只用粉笔在黑板上推导公式;电机学教授把枯燥的原理讲得引人入胜。
实验设施也是好的。
与国内不同,大学里学习和生活都由学生自行安排,没有辅导员。
这有利于锻炼我们的自立能力。
马国川:
初到苏联,上课听得懂吗?
傅志寰:
开始,上课听不懂,课堂笔记根本记不全,我们的俄语程度不行。
由于语言不过关,常常闹出笑话。
有一次到商店买猪油,售货员怎么都听不懂,原来是我把猪油说成"牙"油了。
校方为了给外国留学生创造说俄语的环境,把我们安排和苏联同学一起住。
我和两个俄罗斯及一个乌克兰同学住在一间宿舍里,处得挺好,成为好朋友。
苏联同学非常热情,课下,借笔记给我们,还帮助解答问题。
马国川: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特意到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您参加了吗?
傅志寰:
参加了。
那天我提前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但会场已经座无虚席,只好站在后面。
当毛主席出现时,全场雷动,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湖南口音很重,讲了大约四十分钟。
讲话富有哲理,十分风趣,他还不断地与台下的同学对话,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的那句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在座的同学个个热血沸腾,领袖的殷切期望对年轻的留学生是巨大的鼓舞,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激动之余,我们也都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亲自聆听毛主席教诲的我们,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和自己肩负的责任,努力克服语言方面的困难,起早贪黑地苦读,不到凌晨一两点不睡觉。
周末宿舍里举办舞会,我们基本不去,所以被称为不会生活的"面包干"。
二年级,我的俄语听力有很大提高,各门功课全部是优秀。
三年级,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上了光荣榜。
马国川:
在苏联的留学生活怎样?
当时国内经济很困难。
傅志寰:
那时,国家为了保证留学生的学习,每个月发500卢布,用这些钱在国内可以养活六七个家庭。
留苏五年,我尽量省吃俭用,钱都买了书,没买照相机,所以大学时代的照片很少。
除了在照相馆拍了几张,都是别人给照的。
由于技术不过关,现在都发黄了。
到苏联买的唯一大件就是一块莫斯科牌手表,因为没有手表没法掌握时间。
马国川:
在苏联五年学习生活,对于苏联的了解更深入了吧。
傅志寰:
五年里,总的来说对苏联的印象是好的。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深入地接触生活,逐渐感到苏联也并不都是那么美好:
不少大学生旷课,考试作弊;酗酒,缺乏信仰;党、团组织凝聚力不强。
1958年暑假,我与苏联同学一起坐几天火车去了哈萨克斯坦收小麦,国营农场管理之差令人吃惊。
收下的粮食没人晒,发了芽;守着粮食没人做饭吃,人们饿着肚子不出工;9月末下雪了,庄稼还没收完。
这一切都使我隐隐约约感到苏联在制度上出了点儿什么问题,直到回国后才明白了一些道理。
马国川:
大学毕业前后的情况如何?
傅志寰:
1961年初,为收集写毕业论文的材料,我去了诺沃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其规模之大,令人羡慕。
我的论文写的是中国型交流电力机车。
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想回国后可派上用场。
我的导师叫扎哈尔钦科,是一位资深的电机专家,50年代到过中国。
在他的指导下,我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答辩。
我们是1961年夏天毕业回国的。
大家都是年轻人,热情很高,想立即把学到的知识献给祖国,对于别的考虑得很少。
在填写志愿时都表示:
坚决服从祖国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几天后我接到了通知,去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工作。
有人问我,你不想留在北京吗?
我说能分在北京,比如铁道科学研究院,当然很好。
分到株洲,我坚决服从,因为那里有我的电力机车事业。
马国川:
这是你们那一代人的语言,总是充满豪情。
傅志寰: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想法,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不是说空话,其实自己不是没有困难的。
在报到之前,我回到了黑龙江,看望父母。
当时母亲患的癌症已经扩散,十分痛苦。
我告诉家人要去远离千里的湖南工作,母亲非常舍不得,但很理解。
其实我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到了株洲后时刻惦记着她。
由于信件太慢,电话打不通,我隔几天就发一封电报询问病情。
八个月后,她永远离开了我们。
虽然男儿有泪不轻弹,我还是偷偷地哭了几次。
至今我仍记得与母亲分别的那一瞬间,她也许想到可能是最后的离别了,消瘦的面孔淌着泪水,眼睛里闪着忧伤。
而我出家门的时候,几乎是一步一回头,母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刻成了永久的记忆。
激情燃烧的岁月
马国川:
请讲讲您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的情况。
傅志寰:
研究所并不在市区,而设在五公里外一个叫田心的小镇上,紧挨着田心机车厂。
这个工厂原来是修理蒸汽机车的,1959年,铁道部决定在这里试制电力机车,同时成立电力机车研究所。
当我来报到时,研究所只有两年历史,老技术人员只有几个,还有几十个新来的大学毕业生。
由于刚刚建所,办公室也是借的,一间房子摆了二十几张桌子,一个人打电话,全屋不得安宁。
马国川:
条件很差,和您想象的不一样。
傅志寰:
不光是工作条件跟我想的有很大不同,气候也不适应。
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去湖南前,想象那里的冬天一定暖和,可是雨下得很多,非常冷,是从里面往外冷。
那里一年到头离不开胶鞋和雨伞。
马国川:
现实与理想差距这么大,对您来说是一个考验啊。
傅志寰:
我是带着年轻人的美好愿望去株洲的,现实与理想差距确实大,但是没有消磨我的意志。
我从小家境贫困,吃得惯苦。
在事业面前,苦真的算不了什么。
我国电力机车从1959年开始按照苏联的图纸试制。
由于当时苏联同类机车也处在试验阶段并不成熟,所以头两台新试制的样机质量很差,不能上线使用。
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专家撤走了,技术难题留给了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实现技术突破,铁道部下决心组织攻关。
那时可以说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憋了一口气,不相信离开洋人,就一事无成。
发愤图强,日夜攻关。
马国川:
当时提倡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傅志寰:
我们就是依靠自己奋斗,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进行攻关。
当时办公室晚上灯火通明,夜以继日地工作、研究、试验,对机车进行改进。
我是研究所里少有的几个喝过"洋墨水"的人,知道大家对我抱有期望,所以更加努力。
1962年初,我被派到北京环形铁道参加研究试验。
半年以后,又去了宝鸡-凤州铁路。
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全长90公里,电力机车在那里做运行考核。
开始毛病很多,但通过处理故障,自己学到了很多知识。
就这样边干边学,实践使我对机车有了全面的了解。
马国川:
60年代初的那几年,正是国民经济困难的时期。
傅志寰:
那几年生活比较困难,常常饿肚子。
人们对粮食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较",单身汉的眼睛都盯住了食堂。
60年代在中国不怎么说客套话,而我却按苏联人的习惯,每次在食堂里买完饭就道一声谢谢。
有一次卖饭的老太太生气了,她指着我:
"以后不要再说谢谢了,别人以为多给你打饭了。
"当时由于领导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所以大家的牢骚并不多,工作也很有劲头。
我参加工作的第四年,由于"山中无老虎",我被任命为研究所总体线路室的负责人。
全室三十多人,没有别的"头"了,我是唯一的"官",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这段时期我开始谈恋爱,对象叫唐曾妍,她在北京有个很好的工作,是我在环形铁道试验时认识的。
为了能在一起,她宁愿调到条件较差的株洲。
我们结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大串联,火车上人满为患,回东北已不可能,于是去了上海的岳父家。
到了上海,娘家人见我穿得太差,由内弟陪同买了一身蓝布衣服。
第二天请几位亲戚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婚事就算办完了。
回到所里,由于没有住处,双方各过自己的单身生活。
一年后分到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既没有卫生间,又没有厨房,由于通风需要在墙上打了个洞,邻居放个屁都能听到,被戏称为"P"型住宅。
就这样我们已经感到不错了。
马国川:
"文化大革命"期间您受到冲击了吗?
傅志寰:
"文化大革命"湖南折腾得很厉害,初期我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受到了多次批斗后下车间当了蒸汽机车修理工。
由于人缘不错,两年后获得"解放",当上研究所的"生产组"组长。
后来又被任命为副所长,负责研究开发工作。
当时压力很大,非常忙。
记得,在研制一种半导体器件时,多日没有回家。
一天晚上,唐曾妍到试验室找我说,她去上夜班,两岁女儿已经睡了,要我回去陪陪,我满口答应。
由于试验不顺利,我把这件事给忘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想起来。
邻居说,半夜孩子找不着妈妈,嗓子都哭哑了。
房门上了锁,他们干着急。
现在想起这件事还感到内疚。
马国川:
条件艰苦,又有政治运动,电力机车的科研进展如何?
傅志寰:
我们苦战了十年,经历多次失败,先后成功研制了韶山1型、韶山2型、韶山3型机车……使我国电力机车技术实现了飞跃。
马国川:
为什么以"韶山"命名呢?
傅志寰:
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湖南以毛主席为骄傲,所以起了这个名称。
马国川:
改革开放后,研究所有什么变化?
您对研究所的感情是不是很深?
傅志寰:
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团结一致,埋头苦干,株洲所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几次搬迁,越建越大。
不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研究所,而且还研制了一批新机车,在全国电气行业的知名度也很高。
说实在的,我在株洲所工作的二十三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1999年建所40周年时,我与老同事聚会,说了一番发自内心的话:
研究所的变迁凝结了我们大家的心血。
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志都退休了,头发白了,有的牙也掉了,但是看到了我们现代化的研究所,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
来所初期,吃不饱肚子,但是研究所的办公室经常彻夜通明。
小伙子没有穿过西装,姑娘们没有抹过口红……我们是从困难中走过来的,但我们却非常自豪。
在座的江慧写了一首诗,名叫《无怨无悔》,读后引起了我的共鸣。
的确,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但是无怨无悔,感到最骄傲的是为铁路电气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我们想想看,天上飞的是外国造的空客、波音飞机,地上跑的是奥迪、桑塔纳等国外品牌的汽车,但是在我们的铁道上,奔驰的是中华牌,是用我们的心血创造出来的韶山型机车。
就是这一点我们无怨无悔。
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很大的回报,这个回报不是对个人的,而是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回报。
我的一席话激起在场老同志的共鸣,有的甚至流出了眼泪。
马国川:
听说您认为田心最美丽,为什么?
傅志寰:
关于什么是美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
田心虽然是个小地方,气候不好,但它却是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是我奉献青春年华的地方,还有我同甘共苦的朋友,那才是我最留恋的土地。
提速的梦想
马国川:
您在株洲工作了二十三年,以后的工作有什么变化?
傅志寰:
1984年我离开电力机车研究所,调入铁道部科技局。
在此之前,1981年我被派往联邦德国学习电力机车设计制造。
一年多时间,先后在几个著名公司里进修,自己受益匪浅。
德国发达的工业、优美的环境以及德国人对工作的认真态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德国铁路为增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列车速度,也开拓了我的思路。
马国川: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傅志寰:
德国铁路的快速。
当时德国铁路已经达到时速200公里,而我国列车最高时速才100公里,整整差了一倍呢。
人家的列车像风一样呼啸而过,而我们的火车一路都是"哐当哐当"声。
之前,我们国家一直在闭关锁国,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
德国之行让我开了眼,也让我产生了一个梦想:
中国的铁路也要达到这个速度!
马国川: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坐在日本新干线,他对随行的记者说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觉:
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傅志寰:
中国也需要跑啊,不跑起来就追不上先进国家。
让中国列车提速,后来一直是我追求的梦想。
回国后不久,我调入铁道部科技局,先后任总工程师、局长,恰好用上了在德国学到的东西。
科技局给了我一个托梦的平台。
我在全国调研,寻找可以进行提速实验的线路。
1988年我来到广东,觉得广深线铁路比较特殊,它以客运为主,白天跑的多是客车,夜间大都是货车,互不干扰,和西德铁路运行方式十分相像。
其长度为147公里,线路改造花钱不会多,且沿线经济发达,人们能承受提速后的较高票价。
所以,回京后我立即向部领导建议将广深线作为提速试验线。
马国川:
铁道部领导支持吗?
傅志寰:
当时,公路、民航崛起,火车速度落伍,铁路客运市场份额持续下滑,"铁老大"被一些人称之为"夕阳产业"。
部领导都认识到,再不提速,火车就没有竞争力了。
他们同意把广深线作为提速试验线,并决定进行技术改造。
马国川:
听说您在提出建议不久就到哈尔滨工作了,是这样吗?
傅志寰:
是的。
1989年3月我正忙于筹划对广深线提速进一步调研时,领导找我谈话,说你的工作要变动一下。
我问去什么地方,他说去铁路局。
我提出,要去,最好不去哈尔滨,因为我生在那里,亲戚同学多,做一个铁路局局长,有这些关系不容易开展工作。
后来组织上还是决定派我去哈尔滨了。
事后才知道是要我熟悉铁路运输,经受实践锻炼。
哈尔滨铁路局有近7000公里的铁路、27万职工,是一个大的铁路局,对于从未干过运输工作的我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安全情况不好,设备比较差,很多老职工退休,子女顶替,来不及培训就上岗,素质不佳。
一年中要发生很多事故,这是最揪心的了。
当地有一句话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
半夜来电话肯定不是好事,睡觉也不安稳,总是吊着一颗心。
为了解情况搞好工作,我上机车、下现场,跑遍了管区内主要站段,请教有经验的老同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管理思路。
在哈尔滨工作虽然不到两年,但却如同上了一所社会大学,学习到过去不了解的知识,积累了经营管理经验,为日后工作打下了基础。
那段时间,正如所预料的,有不少熟人来找我走后门,但基本上被我回绝了,所以得罪了一些人,尤其是我的亲戚。
马国川:
回到铁道部您是不是又关心提速?
傅志寰:
1991年初我回到北京任铁道部副部长。
当时我分管机车车辆工业、科技等工作,这些都和提速有关。
1993年我到东北哈大线检查工作,无意中了解到,日伪时期蒸汽机车牵引的"亚细亚"号列车最高时速已达130公里,而解放后最快的列车仍未达到这一速度。
让我深感不安。
所以我多次向别人提起这件事。
几十年前日本人就做到的,难道我们就做不到?
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我国铁路大面积提速势在必行,于是又向部党组提出了建议。
恰好于1994年底广深线提速试验取得巨大成功,时速达到160公里,最高可达200公里,全路上下深受鼓舞。
次年韩杼滨部长主持部长办公会议,作出在既有线大面积提速的决定。
按分工我负责两项工作:
一是领导研制新型提速机车车辆;二是组织提速试验。
马国川:
有反对声音吗?
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傅志寰:
是有不同声音。
那些年安全大环境不如人愿,发生了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所以一些人提出,如果提速了,事故率会不会更高?
出了事谁负责?
马国川:
提速必须有机车车辆作保障。
您分管工业生产,在提高我国的机车水平上做了哪些工作?
傅志寰:
当时我国机车车辆产量上得很快,但是产品质量不高。
我提出今后主要不再是上能力,而是上质量、上水平。
经过各企业和研究所的多年努力,开展自主创新,相继研制了包括提速电力机车、内燃机车、动车组和客车在内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车车辆系列,产品质量和档次有了很大提高,品种也增加了很多,同时还向国外出口。
为了适应提速需要,我们安排了很多试验,检验机车车辆水平。
1997年1月的一天,在北京环行线进行提速试验,我上了机车。
列车不断加速,一直达到时速212公里,实现了中国铁路进入高速领域的突破,司机室里一片欢呼,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研人员的斗志。
当天晚上本来不喝酒的我和大家一起共饮。
事后有人问我,这是破纪录的试验,你不怕冒风险吗?
我说,试验已做了充分准备,是有把握的,但既然是试验肯定会有风险,我作为主管副部长来承担责任,可增强大家的信心。
由此可见,我们自行研制的机车车辆水平有很大提高。
马国川:
有个问题我感到不解:
为什么要提速,而不直接建高速铁路?
机车车辆自己研制而不是直接购买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
世界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了,德国列车在80年代初不就已经达到时速200公里了吗?
傅志寰:
当然提高列车速度的一种办法是跟着发达国家走,就是建设高速铁路。
但是,工程决策不能只按照美好的愿望寻找"理想答案",正确的决策应是在约束条件下作出具有现实可能的决策。
当时的约束条件是什么?
我国铁路提速决策遇到的主要难点是资金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铁路建设由国家投资,每年只有几十亿元,不到目前水平的1/50-1/20,新线年投产不到200公里。
高速铁路的造价是常规铁路的3-5倍,在当时的情况下走建设高速铁路的路子是不现实的(京沪高速铁路论证了十五年才开工)。
因此,当时提高客车速度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对既有铁路实行提速改造。
虽然发达国家有成熟的包括机车车辆在内的先进技术设备,但对于中国铁路这样大规模、连续推进的提速工程来说,我们不可能单纯依靠引进,其中重要原因是中国铁路承受不了其高昂的价格。
马国川:
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外汇去购买先进技术。
傅志寰:
有没有外汇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铁路工业已具有相当的基础,我们相信自己的技术研发能力。
我不反对拿来主义,但核心技术必须是自己的,否则永远受制于人。
事实证明市场是难以换到核心技术的。
我们要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路线。
不能光引进,否则我们买来的是表面现代化,牺牲的是内在创造力。
引进与自主开发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引进是手段,而培育自主开发能力才是目的。
就这样提速之始,我们就明确打出了"国产牌"。
为大提速预热,铁道部组织研制并批量生产了东风11型、韶山8型、韶山9型等提速机车、客车、电动车组系列,时速达到160公里、200公里,同时研发了信号、通信、轨道结构等新技术。
马国川:
我国铁路提高列车速度的难度在哪里?
与国外相比,我国铁路提速是不是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傅志寰:
中国铁路里程较少,运输强度是世界之最,是美国的39倍、法国的8倍。
因此,在这样高强度运输,而且客货混跑的情况下,铁路提速不容易。
日本的铁路速度比较高,因为日本的铁路主要跑客车;欧洲的铁路速度比较高,是因为白天跑客车,晚上跑货车。
打个比方,高速公路汽车之所以跑得快,因为拖拉机、自行车不能上路。
中国铁路繁忙干线运输能力十分紧张,客货列车共线运行,在同一条铁路线上既要开行特快旅客列车,还要开行大量重载货物列车,而后者是很难提速的。
这就使各种列车之间出现了速度差。
速度差越大,对列车密度和运输能力的影响越大。
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允许拖拉机上道,速度能跑200公里的奔驰车,在这种情况下也许速度跑不到100公里。
由于我们进行了技术创新、运输组织创新、安全管理创新,所以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深挖了世界上最繁忙铁路的潜力,在中国特殊复杂的运输条件下实施大面积提速。
马国川:
看来,安全问题一直伴随着铁路提速。
傅志寰:
那时,我国铁路装备较差,管理水平不高,重大伤亡事故时有发生,安全风险很大。
铁路提速会不会造成事故频发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一直有质疑之声。
一些朋友也劝我"三思",但我想,作为部领导,总得给铁路干点事,国外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到呢?
外国的机车车辆水平高,我们的水平也不低啊,起码超过了俄罗斯,风险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加强管理加以化解。
铁路再不提速,火车就没人坐了。
为了化解提速的风险,我们通过采用新的技术,实行科学管理,尽可能把不确定因素转化成可控因素,使安全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层次。
至今铁路大提速已经超过十年,由于采取了很多措施,安全情况很好,没有因提速造成旅客伤亡事故。
199